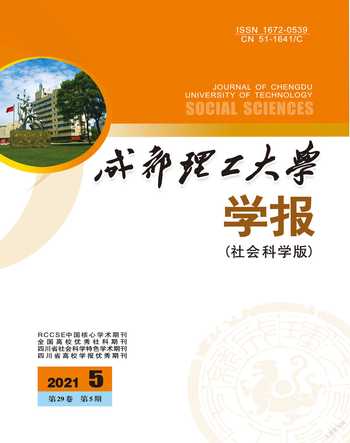论朱祖谋的词法宗尚
作者简介:舒乙(1994-),男,贵州铜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诗词学。
摘 要:清代词学承宋词学而来,并有颇多取法。朱祖谋作为清季词坛中心领袖,学词有颇多取法。其词以辛亥革命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学吴文英,重“涩”调,主要与当时主流词坛尚常派,师事王鹏运,及身为晚清臣子与吴文英成异代知音有关;后期兼学苏轼与吴文英,重“重”调,主要受常州词派界内新变尤其是重、拙、大词学理论的影响,也与他在清亡后的个人遗民悲愤离不开。其词以其苍凉深涩的艺术风格被“海内言词者奉为斗杓”,这与他的词学主张与实践的呼应,以及对吴文英、苏轼的宗尚融合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朱祖谋;吴文英;苏轼;词法宗尚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5-0051-08
朱祖谋,原名孝臧,字古微,号沤伊,又号彊村,世居浙江归安之上彊山麓,自号上彊村民,因题其集为《彊村词》。少时随宦河南,遇王鵬运,交甚得。光绪九年,以二甲第一名进士,官礼部侍郎。后又担任过江西乡试和朝廷会试同考官。官至礼部右侍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赴京师,与时任御史之王鹏运举词社,得王“时时语以源流正变”[1]722,后弃而专攻词,晚年删订其作曰《彊村语业》。辛亥革命后,不问世事,往来于湖淞之间,专心著述,以酬唱为娱,终以清遗老自居。朱祖谋为“晚清四大家”中年寿最长、词学成就最突出者,被时人推为词之“宗匠”,以其幽怨苑悱、苍凉深涩的艺术风格为清词“一大结穴”。时贤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词坛点将録》评之曰:“彊村领袖晚清民初词坛,世有定论。虽曰揭橥梦窗,实集天水词学大成,结一千年词史之局。”[2]980
在晚清那个风云交汇的时代里,朱祖谋词承常州词派而来,受王鹏运影响,尊学吴文英与苏轼,既有苏轼苍劲的一面,又有梦窗晦涩的一面,词风精密绵邈、苍凉艰深。朱氏现存词六百余首,时间跨度为1897-1931年,词境、词风、词情不尽相同,主要与其前后期词学宗尚的转变有关。蔡冠洛《清七百名人传·朱祖谋》即曰:“祖谋词,初学吴文英,晚又肆力于苏轼、辛弃疾二家。”[3]281在张尔田复夏承焘中叶说:“接孟劬先生复,谓彊村词以碧山为骨,梦窗为神,东坡为姿态。”[2]979可以确定的是,彊村词前期主要学吴梦窗,后期主要学苏轼。正是因为学词宗尚的变化,其前后词风也发生了转变。那么如何明确彊村词前后期具体时间段呢?与之交甚的王鹏运即明确说:“公词庚辛之际是一大界限,在辛丑夏与公别后,词境日趋于浑,气息益静。” [4]8404“庚辛之际”即光绪庚子年和宣统辛亥年之间,朱氏词风变化在王鹏运看来是在辛丑年(1901年)夏与彊村分别后开始慢慢变化的,是年王鹏运离京南下,寓扬州,二年(1904年)后在苏州病逝,一生之灵魂师溘然长逝,其悲伤想见。1902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回銮后,彊村虽被擢为礼部侍郎,但他目睹了国家所受一系列之屈辱过程,心中不免怅触。此外,彊村自己也有将自己的词作以宣统辛亥年分期的意识,在刻《彊村词》时增益接近于宣统辛亥年所作之词足为四卷,1918年又復取旧刊之词集增补辛亥后作,删存一百一阕,为《彊村乐府》,与临桂况周颐之《蕙风琴趣》以活字版合印为《鹜音集》。1923年,彊村续加订补刻《语业》二卷为定本,而二卷实为辛亥前后词。1923年后又将所刻之《语业》卷三定位为续刊。其弟子龙榆生也承彊村临卒之遗志,“仿先生刻半塘翁词例,取诸集中词为《语业》所收者次为《剩稿》二卷,而以辛亥后存入手稿不入《语业》卷三者别为《集外词》”[5]726,并未改动其词集序列,可见一斑。当代词曲学家万云骏对于彊村词的分期也颇有创见之论:“予谓彊村词可分二期,辛亥以前为第一期,辛亥以后为第二期。大抵彊村辛亥以前词,伤时念乱,哀感悱恻。杜鹃再拜,则少陵之赤心;春花比艳,则玉溪之诗笔。此一时也。而国变以后,则心怀旧国,梦恋故主,黍离麦秀之歌,铜驼荆棘之感,磅礴郁积,有触即发,风骨亦弥为遒上。此又一期也。”[6]79可见,朱祖谋词体创作大体以辛亥革命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学吴文英,重“涩”调。后期兼学苏轼、吴文英,重“重”调。朱祖谋处于晚清历史大变幻时代,其词随着社会环境及内心感触的变化而有不同走向,苏轼与吴文英颇符合朱氏师法倾向,便自觉向二人借鉴,使之真正完成了对词内质的体认。本文拟分析彊村前后期的词法宗尚及其原因,以摸索朱祖谋的身世遭遇、环境改移与其词风转变之间的关系,以期较为恰切地评论其词作的艺术价值。
一、学“吴”重“涩”——辛亥革命前之词作
辛亥革命前,朱祖谋主要为做官和学词阶段,这是他奠定自己主导词法宗尚及词风基础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大约28年,主要在北京、广东、江浙(主要为江苏、吴兴)一带,积极奔走参与政事,得王鹏运指点学词,“常约为词课,痛世运凌夷,发愤叫呼,拈题刻烛,喁于酬唱”[3]281。彊村少时随父宦河南,后遇王鹏运并与之相交甚欢。光绪九年(1883年),以二甲第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戊子科江西副考官、戊戌科会试同考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教习庶吉士,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迁侍读庶子,至侍讲学士。为官期间“遭世变,私有深念,屡有章疏,皆识议通明,维大体”[5]743,以“有风节”为世所称。
这一时期,彊村词主要学习梦窗词,长于用典、音律和谐、词意深远艰涩。王鹏运《彊村词原序》曾说他:“自世之人知学梦窗,知尊梦窗,皆所谓但学兰亭面者。六百年来真得髓者,非公更有谁耶?”[2]979王易《词曲史》也说其“专宗梦窗,订律精微,遣词丽密”[7]328。这一时期,在艺术实践上,他四校梦窗词,以自身实践推扬梦窗词。在其大力提倡下,词坛风气在事实上向吴文英转换,导致清末民初“梦窗热”的形成,并蔓延至二三十年代,同为晚清民国词学大家的吴昌绶就说“走之尊梦窗者,正所以儆古微”[8]12。在艺术上,彊村词得吴词所长,学梦窗而胜于梦窗,但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吴词艰涩隐晦的弊病。吴昌绶就说他“古微学词在我后,专意振朱、厉、郭之颓风,又不欲强附常州流派,遂成此面目。走故从而敛手,则成佛在后,升天在先者,其专挚不可及”[8]12,表彰之意显然,然亦不无微词,直言朱氏学梦窗之流弊。梦窗词丽密深婉、设色浓艳、结构复杂,如唐之李商隐,但由此而引发的语言晦涩、意指朦胧的弊端也无可避免。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文英天分不如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9]447《乐府指迷》也评价他:“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人不可晓。”[9]447如吴文英词《祝英台近·春日客龟溪游废园》:
采幽香,巡古苑,竹冷翠微路。斗草溪根,沙印小莲步。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又身在、云山深處。
昼闲度。因甚天也悭春,轻阴便成雨。绿暗长亭,归梦趁飞絮。有情花影阑干,莺声门径,解留我、霎时凝伫。[10]290
此词朱祖谋选入《宋词三百首》,为吴文英代表作之一,是其客居龟溪村时,寒食节游览一废园时有感而作。是词用“幽香”“古苑”“冷竹”等意象写出废园荒芜冷落的特征,用触目环境入笔,而以“竹冷翠微”概之,“斗草溪根”句则全在“路”中,“自怜”句则是从“小莲步”的活泼反衬而出。逮至两词下片筋节扭转处,也如上片一般运笔蹈然。用语晦涩,含蓄蕴藉,意象隐密,幽思飘渺。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评曰:“花影絮香,作片时流恋,于无情处生情,词客每有此遐想。”[11]365如若不深入了解此词意象,不借助其他历史背景资料,很难真正把握其中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
再看朱祖谋《祝英台近》:
烛花凉,炉穗重,妆面半帘记。罗扇恩疏,消得锦机字。绝怜宽褪春衫,窄偎秋被,楚云重、梦扶不起。酒边事。
因甚一夕离悰,潘鬓竟星矣。相忆无凭,相怜又无计。愿将心化圆冰,层层摺摺,照伊到、画屏山底。[5]9
此词作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988年)戊戌春日,朱氏收入《彊村语业》卷一,是其早期词代表作之一。王鹏运有和词,《鹜翁集》序云:“古微见示新作,吟讽不能去口,依韵赋此,不足言和也。”[5]10戊戌后,彊村移居上斜街查德伊故居,邻小秀野草堂。面对朝局翻覆,国是未定,纪纲日隳的情状,朱祖谋借此词抒发其对朝局的担忧,欲将一身热血投入国事之中。此词以氛围起笔,而以“妆面半帘”提之,又以一“记”字转入“罗扇恩疏,消得锦机字”的回忆,“绝怜”句又从“消得”处引出,直是学梦窗,在意象的隐喻、章法的运用上颇相似。朱氏弟子杨铁夫曾记录其师教词之法,其中有提到一点:“师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从”[12]13,“罗扇恩疏,消得锦机字”句用班姬典故,梦窗《莺啼序?荷》有“怕罗扇恩疏,又生秋意”句。“愿将心化圆冰”句,化用骆宾王《别李峤诗》“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与龙辅《烈女志》“中镜名圆冰”典故,合用二事之意,“照伊”应指德宗光绪皇帝,在戊戌政变前夕,当慈禧与光绪矛盾日益激烈之时,彊村决意倾心于皇帝,此点半塘最为激赏之,和有词“悔轻到碧油簾底”句。同样地,若仅从词句本身来理解,不深入此词本事背景,所得仅为男女个人之情,而不能觉朱氏艳情下伤时念乱,哀感悱恻的苦闷情怀。
彊村早期词风直接受王鹏运影响。王鹏运为传统常州词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与创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常州词派的基本特点。在词的技法上,半塘承周济而追求“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喜欢把心绪隐藏在某一物象之中,营造出朦胧的意境。在词的学习上,他也学常州词派,推崇梦窗,在他的词集《半塘定稿》及删落稿中,步梦窗词韵十九首。他自幼出生在书生门第,长大后又沉迷于词的校勘,致使他的词浸润着书斋气,喜欢运用典故,常“以学问为词”,在创作中化用唐宋名家作品,词中亦具有学梦窗而来的艰涩难懂之病。王鹏运与朱祖谋联系密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朱祖谋受王鹏运“强邀”入“咫春词社”,开始了词的创作。叶恭绰《广箧中词》说王鹏运“于词学独探本原, 兼穷蕴奥, 转移风会, 领袖时流, 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 非过论也。彊村翁学词, 实受先生引导……清季能为东坡、片玉、碧山之词者,吾于先生无间也。”[13]608张尔田也说:“彊村早年从半塘游, 渐染于周止庵绪论也深。”[14]437在王鹏运的悉心指导下,他不仅从词的源流入手进行学习,也开始了词的校勘,和王鹏运一起校对《梦窗词》,并时时有酬唱之作。如在王鹏运书斋依白石“不肯寄语误后约”为韵赋词,彊村《水龙吟·四印斋赋白芍药,分得肯字》,王鹏运分得“后”字。再如王鹏运《蜩知集》有《鹧鸪天·读史偶得》二首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召用康有为议行新政,为翁同龢被罢免而作,彊村亦有《丹凤吟》词言其事。王鹏运对朱祖谋影响深远并受到其尊崇和感激,朱祖谋晚年曾评价王鹏运“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15]1859王鹏运与朱祖谋于词皆推学梦窗,是晚清民国“学人之词”的代表,王鹏运《半塘定稿》有书斋气,朱祖谋《彊村语业》多书卷气。王鹏运是朱祖谋学词的启蒙者和推进者,他的创作观念和词作特点是彊村学“吴”重“涩”的直接原因。
彊村词受清季词坛风尚尤其是常州词派的影响颇深。清代词坛自浙西词派后,就已困守于雅词体系之中,浙西词家宗尚南宋之姜夔、张炎等“醇雅”之词,浙派盟主朱彝尊就说“填词最雅,无过石帚”[16]308。至常州词派则在浙派基础上有一定新变,前期张惠言以“有无寄托”论词,推五代北宋之词;中期之周济崇尚“比兴寄托”,以南宋碧山、梦窗、稼轩、清真为宗法对象;晚期则由四大家皆共尊吴文英。清季整个词坛的风尚大体是一致的,鲜有出浙派与常派的词学圭臬,以至吴梅《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叙》有“近世学梦窗者,几半天下,往往未撷精华,先蹈晦涩”[17]1之语。临桂词派又称“彊村派”,在词系传承上属于常州词派,彊村词学实承周济、端木埰等人而来。常派重要词人周济认为,词创作应遵循一定的途径,即“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将吴词奉为圭臬。在词风上,他极力追求“空”,认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介存斋论词杂录》),而梦窗词“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此外,在近代词学师承中, 导师对弟子的词学宗尚、治词路径、成才自立皆有极大影响, 优秀弟子也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他们多谨守“家法”, 偏于保守 [18]75。端木埰为清代常派著名词人,朱祖谋自称为端木氏弟子。端木埰词学发展方向大体承张惠言、周济一脉, 重比兴寄托, 对王沂孙咏物词寄托家国之情评价甚高。他也曾批注张惠言《词选》数首, 语多精到,同时又重声律, 对张惠言词重意格、轻声律之弊有所补救, 还对张惠言穿凿附会解词之法提出批评。端木埰最早提出“重、拙、大”词学理论, 由其弟子王鹏运、况周颐继承光大。而临桂词派的中心领袖是朱祖谋,朱氏门弟子众多,相继宣传标榜。派内与朱氏相交甚得的况周颐在词学理论上更有建树,其《蕙风词话》系列词论著作所提倡“重”“拙”“大”的词学理论与朱氏在相当程度上是契合的。张尔田云:“先生所为词,跨常迈浙,凌厉跞朱,逌然而龙鸾翔,鬯然而兰苕发。拟之有宋,声与政通,如范、如苏、如欧阳,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三薰三沐,尤近觉翁。” [5]2然之所以同侪名家皆称朱祖谋得梦窗神妙,主要是因为他继承常派的传统表现手法与梦窗的潜气内转,“彊村派”所标举的词学理论和四大家的词学实践以及子弟相承的词学理念皆是承常派而来。朱氏弟子龙榆生在1941年在《同声月刊》上发表的《晚近词风之转变》明确将王鹏运与朱祖谋归为常州词派,认为“晚近词坛之悉为常州所笼罩也”[19]380。观彊村早期词作,实可称得上是延续“常派”系统的词学理论批评著作,常派尊梦窗、学梦窗的词学理论和实践也对彊村早期词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词风偏好外,个人际遇与时代风潮的相似性也促使了彊村早期词作不自觉向梦窗靠拢。梦窗生活在南宋末年,此时元已代金,社会矛盾激化,南宋政权岌岌可危,时局风雨飘摇,他终身不仕,以南宋遗民自居,只能通过词作寄寓家国情怀,抒发飘零之感。如他的《古香慢·赋沧浪看桂》中用比兴的手法抒发对南宋国力衰颓的哀伤,《西平乐慢·过西湖先贤堂》中以今夕对比感慨世事变迁,抒发悲凉之感,《水龙吟·送万信州》书写朝政黑暗,抨击国事日衰。再看彊村,他生活在清朝末年,社会剧变,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辛亥革命以前,彊村目睹了戊戌变法,维新失败的结局;经历了庚子国变后丧权辱国《辛丑条约》的签订;出广东学政时,上疏禁绝“围姓”,以肃国纪清世风,后终因科举将停以充军响为便而搁置。面对攸关存亡的世局,朱祖谋已隐约察觉到国将无以复继的社会现实,乙巳年(1905年),以修墓请假回籍,第二年以病解职,卜居江浙一带,“回翔江海之间,揽名胜,结儒彦自遣”[5]744,并自觉用词作揭露社会现实,表达伤时忧愤之情。正所谓“彊村辛亥以前词,伤时念乱,哀感悱恻。杜鹃再拜,则少陵之赤心;春花比艳,则玉溪之诗笔”[6]79。如他的《鹧鸪天·庚子岁除》抒写了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国仇家恨;《高阳台·除夕和韵》中“虚堂冰雪凌兢甚,怕过时、春不归来”一句也道尽了伤国情怀。此外,彊村论词特别注重词人的身世遭际和内心情感的共鸣,其作于辛壬之交(1911-1912年)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中论蒋春霖云:“穷途恨, 斫地放歌哀。几许伤春忧国泪, 声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贼中来。”[5]448作为“清代三大词人”之一的蒋春霖,早年负文学气,为官十年,后请辞,流浪海滨,徜徉于阁楼酒肆中,常溯写风流以自适。中年以前用力于诗,后弃而一意于词,晚年删存数十阕,为《水云楼词》,多写其身遭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兵事,多感伤之调,自有其境界、气格,有“词史”之称。“伤春忧国泪, 声家天挺杜陵才”句将蒋鹿潭与杜少陵对比,认为二人对家国飘摇,人民流离失所的情状皆有深沉描绘。论徐灿云:“双飞翼, 悔杀到瀛洲。词是易安人道韫, 可堪伤逝又工愁。肠断塞垣秋。”[5]459徐灿为明末清初女词人,其词与李清照一样多抒发故国之思,兴亡之感,多悲苦哀怨之情。而这些都与朱氏自己的身世遭际、哀苦愁闷的情绪是一致的,足以见彊村推梦窗之心意。許伯卿说过: “在宗国覆灭、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时代的哀痛也会时不时、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的笔端滴落,聚合他们的心窝,洇红他们的清欢。”[20]144彊村与梦窗都身处社会更替之时,时代的悲音趋使彊村词作自觉不自觉地向梦窗靠近,二人成为“异世知音”。
二、兼容“苏”“吴”重“重”——辛亥革命之后词作
辛亥革命后,朱祖谋主要以清遗民身份隐于淞沪之间,前后近20年,主要活动地点为江浙、天津、北京一带,这一时期是彊村词风转变,词法炉火纯青的关键时期,也奠定了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徐沅《词综补遗序》所论颇精:“辛亥变后,诗道益穷,樵风、疆村诸家,尤工变征,乃以扈芷握荃之致,寓苕华离黍之悲,盖世于是为陆沉,词于是为后劲焉。”[15]1921是时辛亥国变,清廷被推翻,事实上成为清遗民。乙卯年(1915年),旧僚袁世凯为总统时曾至旧京,拒绝袁其为聘高等顾问之职,并断绝来往。乙丑年(1925年),谒溥仪天津行在,忠诚靖献典学生计之事。六十岁后唯一之子丧殁,与之友爱最笃,相依为命的孝微季弟早世。一生娶妇不贤,悍拓异常,夫妇不和睦。面对凄苦之身世,接连的不幸摧伤致病,身体日益衰弱的现状,心境悲凉,却不得不放开胸襟,强作旷达,想以写词来取得某种慰藉与平衡。加之此时的彊村由于不再过问世事,有了更多更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进行词法的切磋、探讨和总结,其词的艺术性日益精进,对词体特质有了深入的认识,也逐渐认识到学梦窗而日益显现的弊病。
朱氏作为当时词坛领袖,其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当时词坛师法对象的转变。在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们的推衍下,词坛学梦窗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学梦窗在当时一度非常火爆。大多数人学梦窗但得辞藻华丽,晦涩难读,而少梦窗之气韵浑成。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就说:“填词必拈僻调,究律必守四声,以言宗尚所先,必唯梦窗是拟。其流弊所及,则一词之成,往往非重检词谱,作者亦几不能句读,四声虽合,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绝顶聪明,而专务挦扯字面,以资涂饰。则所填之词往往语气不相连贯,又不仅‘七宝楼台’,徒炫眼目而已!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吴,则词学将益沉埋,梦窗且又为人垢病,王、朱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19]385鉴于此种情形,晚年的朱祖谋努力寻找补救之法,寻求词风的转变,开始向苏轼学习,出入梦窗与东坡之间。龙榆生《答张孟劬先生》说:“疆丈之翼四明,能入能出,晚岁于坡公,尤为笃嗜。梦窗佳境, 岂俗子所知, 浮藻游词, 玩之空无所有, 强托周吴以自矜声价, 其病亦复与伧俗相同。”[21]他试图用苏词中的清旷之气冲淡吴词中的艰深晦涩之语,使两者达到完美的平衡。一方面,用许多精力编选词集,《彊村丛书》辑唐宋金元词160余家,为晚近辑刻词学丛书所收词人最多之一种,《彊村丛书》亦被称为“清代词学四盛”之一。其所编《宋词三百首》为最流行的宋词选本,《词莂》为清代典型词人词作的精悍选本。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校正《东坡乐府》,为东坡词编年,其《东坡乐府编年》是成为近代以来第一种苏词研究专著。在治苏词的同时,自觉向苏轼靠拢,将苏词的艺术创作方式融合进以补救之,在词中化用诗词,以诗论词,这在其《望江南》词评著作中表现最为明显。如评李武曾、李分虎“不分诗名叨一撰,居然词派有连枝”化用曹贞吉《秋锦词序》引《自吟》:“儿童莫笑诗名贱,己博君王一饭来。”以诗论词亦是朱氏学苏合吴的重要体现。朱氏推尊词体,常用评价诗歌语言评价词,创造性地吸收诗学中的重要理论。他认为诗与词是有密切联系的,词从诗而来,诗与词都是作者情感性情的表露,不仅评价诗歌的方法可以用来评价词,而且写诗之法也可用来写词。如将陈洵词与陶渊明比较,说陈洵“《风入松》阕淡而弥腴,如陶渊明诗,殆为前人所未造之境”。以诗境评词境,认为如果词境不能达到诗境,就无新意可言,亦无法深入词的内质,仅能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词与诗同样具有纪事记史功能,小词不限于抒发男女个人相思离别之情,同样还可以像诗一样抒情言志,言家国之志。兹举彊村后期代表作之一《曲玉管·京口秋眺》:
野火黏堤,寒云齧垒,霜空竟日飞鸿响。客里登楼穷目,衰柳无行。尽回肠。冷眼论兵,愁心呷酒,无多景物供吟赏。最爱青山,也似北顾仓皇。寄奴乡。 霸气消沈,剩呜咽、回潮东注,永嘉几许流人,惟馀叔宝神伤。感茫茫。又玉龙吹起,一片西风鳞甲。江山如此,几曲阑干,立尽斜阳。[5]259
此词作于民国二年癸丑,彊村57岁,时事转换,宋教仁被刺,国会成立,北京讨袁兵败,熊希龄组内阁,袁世凯当选总统。此时的朱祖谋,以遗民隐居,面对国家“垒齧”的现实,“穷目”所见皆为“野火”“衰柳”,没有景物可供吟赏。“冷眼论兵,愁心呷酒”句化用东坡诗《九日黄楼作》“把酒对花容一呷”句,“霸气消沈”句化用苏轼《仲天贶王元直自眉山来,见余钱塘,留半岁既行,作绝句五首送之》“遥想扁舟京口,尚馀孤枕潮声”句。“一片西风鳞甲”句苏轼也有“千山动鳞甲”句。但“最爱青山”,心中时时怀念着清廷,渴望为清廷为国家一展抱负,但四次觐见溥仪无奈社会现实下,这一理想成为泡影,只能“寄奴乡”托心于著述,与“永嘉几许流人”诗酒自娱,唏嘘慨叹,发抒对世运艰难之凄苦绝望的心绪,他的这种遗老多情形象在后期词作中并不鲜见。
彊村词风的转变与常州词派界内新变有关。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王鹏运、况周颐合结《薇省同声集》,常州词派内部发出了新的声音。常派周济也认识到苏词与主流词学的契合之处。周济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22]12“韶秀”与“粗豪”对举,则其清丽婉约之义可见。在这一时期,临桂词人兴起,王鹏运和况周颐在创作方法上推崇“重、拙、大”,“重”是指词的表现内容应厚重深刻,“拙”是指词的创作风格应稚拙自然,“大”则主要指词应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与博大的个人胸怀。彊村作于辛亥之际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提到庄中白与谭献说:“皋文说, 沆瀣得庄谭。感遇霜飞怜镜子, 会心衣润费炉烟。妙不着言诠。”[5]444彊村论词, 守周氏正变之论, 大体以婉约为正, 不轻忽苍劲之作, 重视体格, 由此可见彊村对常派意格论与寄托论的承继与挥张。
清末民初,社会处于动荡和转型时期,临桂词人身处于社会剧变的漩涡之中,经历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他们希望以词这种文学形式一吐胸中之块垒,抒发自己的悲愤情怀。在这种词学创作理论的指导下,词坛开始鄙弃浮华词风,重视词风的豪迈阔达,以词来抒发家国身世之感。朱祖谋《半塘定稿》序就提及:“及庚子之变,欧联队入京城,居人或惊散。予与同年刘君伯崇就君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凌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约为词课,拈题刻烛,于隅唱酬,日为之无间。一艺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谈谐间作,心神洒然,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而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也。”[23]5因此,朱祖谋选择了苏词,以“苏”疏“吴”,这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第一,辛亥革命后,朱祖谋不再过问政事,以清遗老终。沈轶刘《繁霜榭词札》中赞同施蛰存对朱祖谋的评价:“云间施舍评朱祖谋‘自居遗老,迷恋封建朝廷’,可谓至当。”[24]202朱词中时时有着遗老型词人情多的形象,《鹧鸪天》中不仅说自己“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强被减奇温”,也写道“可哀惟有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正是他矛盾心绪的反映。彊村的这种矛盾心态与苏轼词作中展露的矛盾态度不谋而合。苏轼一生虽然才识极高、有着宏伟的政治抱负,但命途多舛、屡遭贬谪,一生都在出世和入世中徘徊,苏词中旷达的处世态度有助于缓解彊村心中的苦痛。正如冯煦在《东坡乐府·序》中说道: “前辈(朱祖谋) 早登鹤禁,晚棲虎阜。沉冥自放,聊乞玉局之祠。峭直不阿,几蹈乌台之案。其于东坡,若合符契。今乐府一刻,殆亦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乎?”[25]534朱祖谋对苏轼是敬佩的,内心里也渴望成为苏轼那样的人,拥有苏轼那样旷达情怀和襟抱,在面对沧桑之变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排解之时,苏轼旷达恢弘的襟度和不同时代背景下爱国士大夫共同的心理正是其排解的突破口,与东坡“若合符契”。朱祖谋《东坡引·庚午岁除》词中“筇悭雪霁。探梅误年例。一炉商陆闲窗底。瞢腾惟有睡。瞢腾惟有睡。○椒花罢颂,屠苏无味。更禁断、宜春字。乡儿解叩承平事。新年明日是。新年明日是。”[5]501此种百无聊赖的闲情,与苏轼赋闲东坡之闲情相比较,皆为一种无可奈何之闲情。他的《定风波·为潘弱海题画松》“苍虬根干。不管人间风日换。龙性谁驯。貌此嵚崎历落人。○含豪犹怒。那便蜿蜒霄汉去。规作新图。待访家山第四株。”彊村虽以遗民隐居,但心中时时怀念着清廷,渴望为清廷为国家一展抱负。面对“苍虬根干”的社会现实,无奈只能“规作新图。待访家山第四株”,诗酒自娱,心痛凄惋。朱氏與很多封建士大夫一样都具有“东坡情节”,辛亥年底作的《浪淘沙慢》《祭天神》《摸鱼子》等也都表现了他怀念清室,对社会巨变的悲痛情绪,充斥着浓浓的易代愁苦。
第二,除情感上的相似性之外,彊村之所以推崇苏词也与苏词的风格有关。朱祖谋非常推崇苏轼词中疏朗清丽的那一类艺术风格,曾云:“两宋词人,约可分为疏、密两派,清真介在疏、密之间,与东坡、梦窗,分鼎三足。”[26]86夏敬观亦指出:“侍郎词蕴情高夐,含味醇厚,藻采芬溢,铸字造辞,莫不有来历。体涩而不滞,语深而不晦,晚亦颇取东坡以疏其气。”[26]86严迪昌《清词史》也认为朱氏《彊村语业》多书卷气,独见深苍,是融合苏吴的学人之词[27]552。《宋词三百首》所选苏词亦是疏朗清丽的那一类。但与朱氏推尊词体、专意于学词不同的是,苏轼仅将词当成他抒发性情的载体,而对于文体本身,却并未下足功夫揣摩。周济称苏轼是“每事俱不十分用力”[28]160。大抵缘结于此了。若按江弱水先生对诗人的分类,苏轼便是很典型的“赌棋型诗人”[29]10-12,因此,他的诗词水平并不会跟吴文英、周邦彦等词人一样具有稳定的发挥,而是会随着境遇的迁延形成强烈的波动。钱穆在《国史大纲》曾说道:他(苏轼)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30]。故而,我们只能通过苏轼的词看到他的思想、性情、趣味,却少见苏轼为词体完善而架设的法轨,即便是他对词体贡献尤大,也是打破藩篱,解放词体的贡献。尽管如此,朱祖谋仍选择苏轼,看重的是他疏放清新的词学风格。这样一来,引苏入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调节梦窗词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后,“酷嗜坡词”(冯煦《东坡乐府序》)的朱祖谋在创作上进行以苏入吴的艺术尝试,学习东坡词疏雄雄浑的艺术手法,放弃梦窗晦涩的一面而学其密丽一面,这对矫正当时学梦窗之弊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其自己的创作亦渐趋浑成,疏密并有,不可谓不是“打开异境”之奇想,时人、后辈莫不激赏至极,蔡嵩云谓彊村词的融合是“彊村慢词,融东坡、梦窗之长,而运以精思果力。学东坡,取其雄而去其放。学梦窗,取其密而去其晦”[31]4。卢前称其词是 “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32]511,夏承焘亦云:“论定彊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33]76彊村的词作往往为世人所乐道,于当时朝政及变乱衰亡之原由多有表现。永嘉徐定超为《庚子秋词》作序时就谓其为“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者”“忠义忧幽之气,缠绵悱恻之忱”[5]728。与之交游的陈三立亦称赞“勤探孤造,抗古迈绝,海内归宗匠焉。晚处海滨,身世所遭与屈子泽畔行吟为类。故其词独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进为国直臣,退为世词宗”[5]744,奖褒之义显见。这与他词学主张与实践的呼应以及对吴文英、苏轼的继承融合是分不开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朱祖谋前后期词风转变主要与其词学宗尚的变化有关。他的词以辛亥革命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学吴文英,重“涩”调,主要与当时主流词坛尚常派,师事王鹏运,及身为晚清臣子与吴文英成异代知音有关。后期兼学苏、吴,重“重”调,主要受常州词派界内新变,尤其是重、拙、大词学理论的影响,也与其在清亡后个人的遗民悲愤是离不开的。徐沅《词综补遗序》关于此论颇精:“辛亥变后,诗道益穷,樵风、疆村诸家,尤工变征,乃以扈芷握荃之致,寓苕华离黍之悲,盖世于是为陆沉,词于是为后劲焉。近三十年作者云起,掣其旨趣,要不出文、朱二家,及时收拾,亦犹《诗》录《下泉》,居变风之终,于乱极发思治之情耳。是则词虽小道,托体并尊,光宣以降非常变局,赖长短句以纪之,寻微索隐,差于世运有关。”[15]1921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朱祖谋前后期词学宗法对象发生了变化,词作艺术风格也有不同。但以朱祖谋初编稿本、初刻本、重编本、三编稿本的四个《宋词三百首》选本及彊村语业的整体风格趋向来看,朱祖谋的审美旨意依然是偏重于吴文英的,故而他后期以兼学苏、吴的尝试,依然是希望将吴文英当作主体,进而吸收苏轼的风格来补足原有的弊端,所展现的依然是吴文英“密丽绵邈”的风格,只是在吴文英词主体风格上融合了苏轼清新疏放的风格而已。正是这一融合,使得彊村后期词显得更为沉着老辣,苍劲艰深,夏孙桐就说他“穷究倚声家正变源流,晚造颇深”[5]741。探究朱祖谋的词法宗尚及其造成原因,对于进一步认识其词学观念与实践的关系,整体把握清末民国的词坛风气与学词路径是有价值与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王鹏运.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跋[M]//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
[2]尤振中,尤以丁.清词纪事会评[M].合肥:黄山书社,1995.
[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4]朱孝臧.彊村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朱孝臧.彊村语业笺注[M].白敦仁,笺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6]万云骏.读彊村词[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5):79.
[7]王易. 中国词曲史[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
[8]朱祖谋.《彊村叢書總目》稿[J].新宋学,2019,(8):11.
[9]马承五. 唐宋名家诗词笺评[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上彊村民.宋词三百首[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杨铁夫.改正梦窗词选笺释原序[M]//吴文英.吴梦窗词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13]张璋.历代词话续编:上[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14]夏承焘.夏承焘集:第5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15]孙克强,杨传庆,裴喆.清人词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16]孙克强. 唐宋人词话:增订本:上[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17]吴梅.乐府指迷笺释序[M]//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8]欧明俊.近代词学师承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75-80.
[19]龍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0]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1]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J].词学季刊,1935,2(2):1.
[22]周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M]//顾学颉,校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3]王鹏运.半塘定稿[M].北平:京华印书馆,1948.
[24]沈轶刘.繁霜榭词札[M]//刘梦芙.近现代词话丛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
[25]苏轼.东坡乐府编年笺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6]上彊村民.宋词三百首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79.
[27]严迪昌.凊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8]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29]江弱水.诗的八堂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0]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31]郑文焯.梦窗词跋[M]//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2]况周颐.蕙风词话补编(卷三)[M]//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33]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编辑:黄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