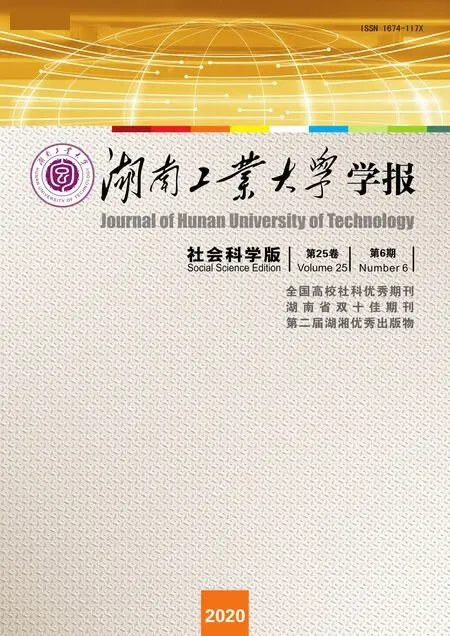湖北宜城方言变韵探究
胡 伟,刘新红
(1.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2. 湖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宜城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东界随州、枣阳,南接钟祥、荆门,西邻南漳,北抵襄阳。该市现下辖10镇4乡3个街道办事处,人口约56万人。宜城方言属于西南官话鄂北片。关于宜城方言变韵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宜城方言的颤音方面。有关宜城方言颤音的研究有李宇明、周继圣、谭麟、王群生、胡伟[1-5]等。以上研究集中介绍了宜城方言的颤音现象并描写了宜城方言颤音的声学特征,并未系统地探讨宜城方言的变韵现象。
一 宜城方言的声韵调特点和语音特点
宜城方言共有18个声母,32个韵母,4个声调。
(一)声母
宜城方言共有18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具体如下:

(二)韵母
宜城方言共有32个韵母,具体如下:


(三)单字调
宜城方言共有4个声调(不包括轻声),即:
阴平 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412
宜城方言两字连读,前字一般会发生变调,其规律如下:(1)前字调为阴平,后字调为上声时,前字阴平变为21调;(2)前字调为阳平,后字调也为阳平时,前字阳平变为34调;(3)前字调为去声,后字调为阴平、上声时,前字去声变为42调;(4)前字调为去声,后字调为阳平、去声时,前字去声变为34调;(5)后字调为去声时,表现为41调。
二 宜城方言的名词变韵和动词变韵
宜城方言变韵情况比较复杂,可分为名词变韵、动词变韵和代词变韵等。本文将D变韵、Z变韵、儿化韵等放在名词变韵的范围下探讨。
(一)D变韵
宜城方言的D变韵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动词变韵,为避免重复,D变韵中的动词变韵将在后文统一讲述。宜城方言很少有形容词、副词和象声词的D变韵。
(二)Z变韵
Z变韵,即子变韵,是以韵母和声调的变化表示类似普通话“子”尾意义的一种构词法[11]215。子变韵较常见于晋南豫北的晋语区。宜城方言也有较为丰富的Z变韵,如:

宜城方言的Z变韵与晋南豫北地区的表现不同,没有U化的倾向,而是表现为一个颤音r,可称之为颤音化变韵。宜城方言的颤音r不能独立存在也不能出现在词首位置,当“子”音独立存在或出现在词首时,无法发成颤音。宜城方言的颤音r不是独立音节,只是前音节的黏附成分。颤音r双音节样本词的前音节承载重音,颤音r不承载重音。时长是宜城方言重音的主要物理相关物,能否承载重音是颤音r是否发成颤音的前提条件,颤音r只能在轻声条件下发成颤音[5]。
王福堂把Z变韵的情况分为三种:拼合型、融合型和长音型。拼合型是指“子”尾与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成子变韵后,“子”处于韵尾位置,可以在语音上和韵腹元音区分开来;融合型即“子”尾和前一语素的韵母合音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韵母,“子”尾在其中已经无法辨认出来;长音型即“子”尾音节的声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融入前一音节,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12]。按照王福堂先生的分类,宜城方言的Z变韵属于融合型,但又与上述分类有所不同;宜城方言的Z变韵中的“子”处于韵尾位置,可以和韵腹分开,且保留了一定的音长。关于融合型是否保留音长的问题,王福堂先生没有提到,但从山西闻喜方言,郑州荥阳、广武方言和开封方言的例子来看,融合型的“子”尾没有音长延长的问题[13]。因此,宜城方言的Z变韵的“子”尾可以看成融合型的一个特例。
综合宜城方言、襄阳方言(主要指现襄州区、襄城区和樊城区的方言,不包括现襄阳市所辖的南漳、保康、谷城、老河口、宜城、枣阳等县市的方言)、河南中北部方言和山西南部方言关于Z变韵的描写材料,笔者建立了一系列Z变韵的过程。宜城方言的Z变韵表现为一个颤音r;襄阳方言的Z变韵表现为闪音或边音l;河南中北部方言如浚县、开封、封丘、长葛、荥阳等的Z变韵系统比较一致,大都走U化的路子[13-15];而山西南部如运城等地的Z变韵则表现为长音和变调[16]。这些共时的材料并非孤立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内部有一定的联系和先后顺序,犹如同一个水平面的地层,不同的地段所代表的地质年代会有所不同。这些共时的变韵证据只是变韵的历时过程的共时化,其内部有很强的规律性。拉波夫就主张用共时变异来研究历时演变[17]27,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现在来解释过去,共时语音变异蕴含着历时演变的动因、过程和方向。因此,共时层面上的各个方言的Z变韵的类型很有可能蕴含着历时层面上Z变韵的演化阶段和方向。
回到王福堂先生对Z变韵的分类,笔者发现,宜城方言的颤音化变韵只能非常勉强地被分到“融合型”:“子”作为一个黏附的音段占据前字韵尾的位置,可以在语音上与韵腹主元音区分开,却保留了自身的音长。因此,笔者认为,宜城方言的颤音变韵应该是融合型变韵的前奏,其变韵发生的时间晚于“拼合型”但早于“融合型”变韵。从频谱上看,宜城方言颤音的平均颤动次数是二到四次,而襄阳方言闪音在发音时只颤动一次,颤音发音时长比闪音要长。因此,襄阳方言的Z变韵是比宜城方言更靠近“融合型”变韵的一种范例。河南中北部方言的Z变韵多表现为U化韵,U化韵属于“融合型”,即后音节的特征融入前音节的整个韵母,在语音上与韵腹主元音不能区分开。山西南部方言如运城方言和闻喜方言的Z变韵则表现为“长音型”,即“子”尾音节的声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融入前一音节,生成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王洪君指出,汉语的合韵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两个普通音节;第二,一个普通音节加一个轻声音节;第三,一个长音音节;第四,一个普通音节[11]201-203。显然宜城方言和襄阳方言的Z变韵处于第二阶段,且襄阳方言更靠后;山西南部方言的Z变韵处于第三阶段;而河南中北部方言大都处于第四阶段。
综上,笔者认为,方言的Z变韵一般经历了弱化、颤音化、闪音化或边音化、长音化和U化这几个阶段。弱化是Z变韵的开始,颤音化是初级阶段,而U化则是Z变韵的较高级阶段。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方言Z变韵的阶段
关于方言的Z变韵是否属于词缀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说:“(汉语词缀)不单用,但是活动能力强,结合面较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之前,或别的语素之后,或两个语素之间。这是所谓‘前缀’、‘后缀’、‘中缀’, 可以总的称为‘词缀’或‘语缀’。”[18]55-56吕叔湘指出了词缀的黏附性、定位性、能产性、轻声性等特点,也注意到了词缀在能产性和轻声性方面的限制,因为能产和轻声特点只适用于部分词缀。
王力指出,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短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者叫做词缀[10]504。这表明词缀具备以下特点:(1)词缀具有黏附性。词缀必须附着于其它成分之上。(2)词缀具有定位性。特定的词缀只能附着在词根的前面或后面。(3)词缀能标示词性。词缀可以用来标明词根的性质。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明确解释了词缀的特征:“词缀都是定位语素……我们管前置的词缀叫前缀,营后置的词缀叫后缀……其次,真正的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关系,没有意义上的关系。”[19]28-29这就是说,词缀的两个特征是定位性和黏附性。
马庆株指出词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词缀分布特征具有定位性,不定位的不是词缀。(2)词缀的语义特征具有范畴义,除了由虚词发展而来的词缀,其余词缀的意义都不是该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只能是后起的引申义。(3)由词缀构成的词的结构特征具有模糊性,其内部结构特征只能说是黏附关系。(4)词缀有易变性[20]。
朱亚军认为汉语词缀具有以下特点:(1)位置的固定性。词缀必须是定位的虚词素,它只能放在其它词素之前或之后。(2)语义的类属性。汉语词缀的类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词缀具有类义功能,即词缀的范畴义;二是指词缀可以决定词的语法属性,即或肯定原词根所反映的词性,或改变原词根的词性。(3)构词的能产性。能产性是指词缀在构造新词时具有一定的类化作用,一个词缀可以孳生大量的新词,除了某些叠音后缀不具备类化作用外,汉语里几乎看不到只依附于一个词根上的词缀。(4)结构的黏附性。词缀黏附于词根之上,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它们之间一般不能插入其它成分,否则,不宜算作词缀,起码不宜算作十足或典型的词缀。(5)语音的弱化性。由于词缀原来的主要词汇意义已消失,它的读音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汉语中绝大多数词缀已不能构成重读音节了,其读音或多或少地弱化了[21]。
综合以上学者的讨论可以看出,定位性与黏附性作为词缀特征,得到诸位著名学者的一致认同;语义的类属性也常被提及。因此笔者认为黏附性、定位性和类属性可作为词缀的主要特征,三者分别表明了词缀的性质、位置和作用。而词缀在构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都只能算是词缀的次要特征。原因有两点:首先,这些特征都可以从词缀的主要特征推导出来。比如,词缀的黏附性导致词缀本来的词汇意义消失,使它的读音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部分词缀在语音方面表现为轻声。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词缀都能表现出构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比如,王洪君、富丽认为词缀、类词缀(即意义的虚实介乎词根和词缀之间的语素)和助字的组合能力都很强,但词缀的新生类推潜能极弱,甚至弱于一般词根。与之相对的是,类词缀的新生类推潜能却很强,以致统计出的搭配频率总赶不上变化[22]。这表明并不是所有词缀都拥有能产性。部分词缀,如“子”后缀在现代汉语中已丧失了类推构造新词的能力,作为历史造词的遗留,成为凝固词语。部分词缀,如“化”“家”等在语音方面也没有表现为轻声。这表明轻声并非语素成为词缀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23]12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宜城方言的Z变韵虽然已不具备能产性,但仍是构词的成分,属于词缀,至少是类词缀。宜城方言的Z变韵丰富了词缀的表现形式,增加了方言词缀的类型。
(三)儿化韵
宜城方言有大量的儿化现象,经调查,此方言32个韵母均可儿化,形成儿化韵。以下是部分儿化韵的例子。

从特征扩散的角度看,宜城方言儿化韵的“儿”字很有可能将[+卷舌]特征向左扩散给了前字的韵母,然后在特征层级的根节点将自身特征值[-前部]、 [+卷舌]等删除。宜城方言的儿化韵有指“小”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有表亲切的感情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王洪君把北方儿化的合音分成6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两个音节阶段,即合音尚未开始的阶段;第二,一个半音节的阶段,这是合音的第一步,后字声音弱化;第三,长音节阶段;第四,长度正常的特殊音节阶段(上);第五,长度正常的特殊音节阶段(下);第六,正常单音节阶段[11]201-210。若以王洪君的划分为标准,宜城方言的儿化韵处于第六阶段,即正常的单音节阶段。
(四)其他名词变韵
除了D变韵、Z变韵、儿化韵,宜城方言还有一类名词变韵,参与变韵的都是实词,如:

宜城方言的这种名词变韵是在语速较快时由连读产生的,以上例词均有其对比形式。如下所示:

以上对比例表明,宜城方言的这种实词变韵是一种语流变韵。较快的语流导致第二个字的读音弱化,声母脱落,并最终合并到前字的韵母,造成变韵。其演变过程如图2所示(以女伢娃儿为例):

图2 宜城方言实词变韵的线性推导
(五)动词变韵
宜城方言有大量的动词变韵。该方言中的动词变韵现象涉及及物动词变韵、重叠变韵和不及物动词变韵。及物动词变韵的例句如(1)至(12)所示。


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具有时体意义,大多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状态的持续。如,“我吃三个馍馍”中的“吃D”,以及例(2)、例(3)中的“骑D”“死D”等变韵词,相当于普通话中的 “吃了”“骑了”和 “死了”,表示动作的完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例(2)和例(3)“骑D走了”“死D走了”,这种方言在“骑D”“死D”等表达后面还可以另加动词,动词后面还可以加“了”,组成“V D V了”结构。这种现象在宜城方言中比较常见,用以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对现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他吃D吃了,玩D玩了,都没留下一句好话”这句话表明说话人对施动者或体验者有一种正面预期,但结果恰好与预期相反,因此施动者或体验者的动作或经历的事情实际上对说话人目前的状态或评价造成了负面影响。再比如,“老张死D死了,还阴魂不散”。老张作为体验者已死亡,但其仍“阴魂不散”,显然,老张的死亡对目前的状态造成的影响或评价是负面的。例(4)~(7)中的“轮D”“送D”“瞄D”“挨D” “等D”相当于“动词+到”。“轮D”和“送D”表示前一动作的终止;“瞄D”“挨D”“等D”的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盯着”“沿着”和“等着”,表示动作的持续和进行。例(9)(10)中的“背D”“走D”相当于普通话的“背着”和“走着”。“背D”表示动作的进行,而“走D”则表示动作进行的方式,因为“走D去的”的意思是“走路过去的”。例(11)(12)中的“死D”“卧D”相当于“死在”和“卧在”,表示状态的持续。需要注意的是,例(3)和例(11)中的“死”并无“死亡”之意,只是当地人一种表示厌恶或戏谑的说法。
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还有一种动词重叠变韵,具体例句如(13)至(16)所示。

动词重叠变韵与一般的动词重叠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动词重叠变韵表完成,这与其他动词变韵所表达的意义相同;其次,动词重叠变韵带有一种责难、批评和埋怨的语气。比如例(13),就是A批评B不该在大晚上出去转悠,例(14)表达了A对于B重复自己的劳动的不满。同理例(15)和(16)都暗示着说话者的不满和责难。若仅仅是重叠,则无法表达出这种语气色彩。
宜城方言还有一种不及物动词变韵,所谓不及物,即动词后无宾语或其他补充成分。如例句(17)至(20)所示。

不及物动词变韵,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给D”“走D”“扯D”“是D”分别相当于“给你吧”“走吧”“胡扯吧”“是吗”等意义,表达祈使、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
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句子的体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而非形态层面的构词成分,这一点与名词变韵不同。因此,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不是后缀。鉴于“D”表现出的时长短,音强短,响度低且不能独立存在的现实情况,笔者倾向于将动词变韵的“D”称为体黏附语素。
(六)代词变韵
宜城方言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代词变韵。代词变韵主要分为两种,人称代词变韵和指示代词变韵。以下列出的是部分代词变韵的例证。

指示代词变韵方面,“这D”表示“这个”,“那D”表示“那个”,而“哪D”表示“哪个”。“D”的功能相当于量词“个”。指示代词变韵在北方方言中比较普遍,如北京话也经常把“那na”说成“nei”,实际上也是一种变韵。
值得注意的是,宜城方言去声的各类变韵的声调都没有改变,保持了基调412的调型和调值。而在非变韵的情况下,去声做前字,阴平、上声做后字时,前字去声变为42调;去声做前字,阳平、去声做后字时,前字去声变为34调;去声做后字时均表现为41调。按照非线性音系学的理论,声调和载调单位处于不同的音层,载调单位发生删除、增加、融合时,声调调值可以保持不变,并在后期的操作中,重新连接到已经改变并且稳定了的载调单位上[24]30-52。如果把412看成HLH调,则可以用图3来解释(以“弄”为例)。

图3 宜城方言变韵的声调
去声字受后字的影响,凹形调调尾脱落,变成41或42调,H漂浮。后字由于变韵,失去了自己的声调,在这种情况下,与漂浮着的H调相连,形成HLH调。去声看似没有变调,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变调和调值与载调单位重配的过程。
三 总结
宜城方言变韵可分为名词变韵、动词变韵和代词变韵等。
宜城方言的D变韵情况与河南境内各方言D变韵情况一致,也是因合音而成,经考察,合并对象为“家”字。宜城方言的Z变韵表现为一个颤音r,无U化的倾向,河南中北部方言的Z变韵多表现为U化韵;宜城方言的Z变韵处于一个普通音节加一个轻声音节时期,这是Z变韵的早期阶段,早于襄阳方言、河南中北部和山西南部方言的Z变韵。这是因为方言的Z变韵一般经历了弱化、颤音化、闪音化或边音化、长音化和U化这几个阶段。弱化是Z变韵的开始,颤音化是初级阶段,而U化则是Z变韵的较高级阶段。笔者认为黏附性、定位性和类属性可作为词缀的主要特征,三者分别表明了词缀的性质、位置和作用,而词缀在构词方面的能产性、韵律方面的轻声性和结构方面的模糊性都只能算是词缀的次要特征。因此, 宜城方言的Z变韵虽然已不具备能产性,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仍属于词缀的事实。宜城方言的儿化韵表现为一个舌尖卷舌的无擦通音,“儿”已经融入前字的韵母,属于融合型。该方言的儿化韵有指小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有表亲切的感情色彩义和表口语的语体色彩义。宜城方言其他名词的实词变韵是语流变韵。较快的语流导致第二个字的读音弱化,声母脱落,并最终合并到前字的韵母,造成变韵。宜城方言的动词变韵,大多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进行、状态的持续;动词重叠变韵表完成且带有一种责难、批评和埋怨的语气;不及物动词变韵,大都由语气助词引起,表达祈使、命令、征询等语气色彩。人称代词方面,宜城方言的人称代词变韵具有表复数意义的功能;指示代词方面,“D”的功能相当于量词“个”。宜城方言动词变韵的“D”主要表达句子的体特征,是句子层面的构形成分,不是后缀。鉴于“D”表现出的时长短,音强短,响度低且不能独立存在的现实情况,笔者倾向于将动词变韵的“D”称为体黏附语素。
——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