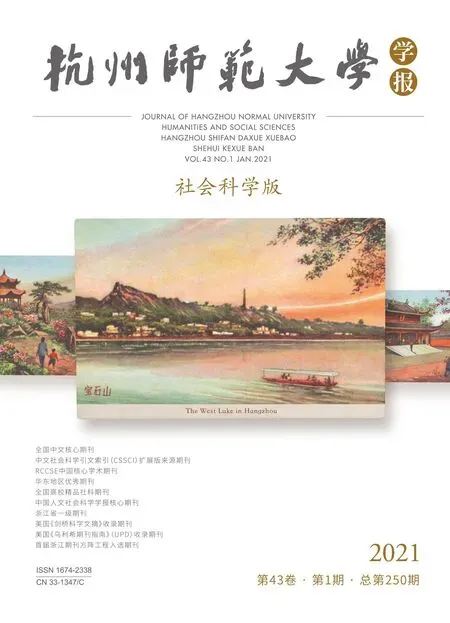动画电影的中国气韵生成
——以传统题材国产动画为例
刘毅青,廖芝林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自“万氏兄弟”于1941年拍摄国内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开始,由传统题材改编而来的动画电影产量非常丰富,收视与口碑屡创高峰,被国际评论认为“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1]。但之后的中国动画并未随着国家经济的崛起迅速成长,反而在国外动画的冲击下,沦为“洋动画”的加工厂。动画人才断层,加上长期机械地模仿国外动画,使观众已经习惯了以美、日为代表的动画艺术风格,这也促使中国动画界一再以国外的动画模式作为创作标准,久而久之国产动画不仅在制作技术与视图观感上极尽效仿之能事,连内容与价值意涵都带入了美、日经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腾飞,文化期待复兴,国产动画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一环,开始意识到回归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对国外动画长达数十年的效仿使得中国动画界仍然存在思维惯性,即便想要创作独具民族特色的原创作品,也因无法找准发力点而显得后劲不足,以至于一度呈现出文化焦虑和技术掩盖故事的局面。长此以往,独具想象力、灵动感的动画电影十分稀有,更不用说观众能从中获得民族性审美感受与精神共鸣。
近年来国产动画一改90年代以来的发展颓势,向着质与量齐头并进的方向踏步前进。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为代表的国产动画电影将先进的技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相结合,带着好口碑与高票房重新夺回本土市场。取材于文化经典、神话传说的国产动画为何能在市场瓜分渐成定局的情况下开疆拓土?这在于创作者与观影者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创作者利用动画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作了当代呈现,观影者也从审美感知层领略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然而,这些作品与曾经的“中国学派”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种距离表现在由动画作品形式到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民族艺术特性与文化价值的缺失:即坚持手绘的中国学派,形式上将气韵生动的画稿作为影片构图设计的基础;内容上,将民族精神之“气”与民族文化之“韵”相融合,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的同时从精神上引起观众共鸣。反观当前国产动画电影,不乏有将“中国”作为一种元素,镶嵌在外来美学与艺术创作观念之中的表达,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很难具备“气韵”之审美状态。本文以近来中外动画电影的对比分析指出国产动画(尤其是传统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从形式到内容尚未具备“气韵”的美学品格,接着以《哪吒》为例,探讨传统题材国产动画电影生成“中国气韵”的可能性路径。
一、气韵与动画电影的双层关联
将气韵引入动画电影理论研究,需要对气、韵二字做分解性理解。“气”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多综合性地指称为“生命力”,其本身具有贯通性、流动性与形而上的哲学审美意味。将“气”引入个体生命,则源自孟子,孟子将道德内涵注入气论思想,“气”成为个人意志与生理互为表里的一种生命力。后被引用为文艺创作的内在生命力,正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徐复观先生认为“一个人的观念、感情、想象力,必须通过他的气而始能表现于其作品之上。同样的观念,因创作者的气的不同,则由表现所形成的作品的形相亦因之而异”[2](P.137)。以绘画为基础形式的动画电影同样灌注着创作者之“气”,当动画创作者将“气”装载到其观念、情感、想象力上去,倾泻于动画作品中时,“气”便成了有力的塑造者。“韵”字起用于汉魏之间,最初意与音律相关。后被用于艺术的人伦鉴识,指一个人外在流露出来的清逸、放旷等情调,即从“第一自然”进而把握神形合一的“第二自然”,“第二自然”即“气韵”的萌芽性说法。顾恺之画论中所谓“‘传神’,正是在绘画上要表现出人的第二自然,而气韵生动正是传神思想的精密化”[2](P.150)。“韵”由绘画引入到文学领域始于刘勰《文心雕龙》中“异声相和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所以“韵”无论是从音乐、人伦鉴识、绘画还是文学角度,都指向审美对象的内在和谐,是与形式对立的,侧重于审美对象内在的精神特质。动画电影之韵就是指其“第二自然”,即超脱荧幕之外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传达。
“气韵”一词的合成运用最早出现于谢赫的《古画品录》,后世多作为画论出现,将气韵引入动画电影研究有其理论关联性。“动画,最早外国人管它叫卡通,但是现在欧、美、日,许多动画艺术家也称它为动画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动画实际上是‘活动着的画’。”[3](P.40)津坚信之认为“在包括实拍电影在内的所有影像艺术中,动画片最独特的点是它的影像是运用“绘画”表现出来的,因此能够将繁杂和多余的信息排除在画面之外,从而使表达内容更为直接或抽象”[4](P.2)。也就是说无论是手绘动画还是CG动画(计算机动画),均以绘画为基本形式,且对画稿有超越写实的诉求。罗宗强在《论“气韵”与“神韵”》一文中指出,“气韵”是画作与鉴赏家共言,画作提供客观条件而鉴赏者在审美素养与能力的前提下提供理解力,是二者的合成。以“气韵”论动画电影,同样在于动画作品本身与观众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审美感受,基于民族精神文化之“气”是连接创作者、作品与观众之间的纽带。高超、孙立军以“神韵”引入动画电影研究,在《“中国学派”动画电影中的东方神韵及其现实意义》中指出,“神韵”成就了“中国学派”在国际上的地位。文中对神韵的定位是“具有动态生成性的美学特质”,但从传统美学来看“神韵”,它侧重于审美对象自身形而上的状态,不注重与欣赏者之间的沟通。即便万籁鸣说“我是主张要致力于人物形象特征和神韵的描绘”[3](P.25),这里的“神韵”也是针对画稿本身究竟应该写实还是传神这一问题。动画长片以“第七艺术”——电影为承载,其传播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沟通的必要性,具有流动、贯通特质的审美范畴“气韵”相较于“神韵”有其超越性。
“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5](P.89)宗白华先生以生命精神来诠释气韵,进而强调其“动”的美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气韵”引入国产动画理论研究,尝试做这样的定义:“中国气韵”是基于民族性精神文化的一种审美经验,它由内而外地体现在动画作品的艺术美感中,通过创作者、作品、观者之间的循环沟通,在共同的“呼”与“吸”之间,以共鸣的方式感受着动画电影中蕴含着的内在韵味。为便于作品分析,姑且从两条路径着手:一是形式层,以“气韵”引入画稿标准;二是内容层,主题要以民族文化为背景,根植民族精神之“气”,创作者与观影者才能以共鸣的方式烘托动画电影之“韵”。
二、国产动画从形式层还未走向“气韵”
以“气韵”论动画电影,一是指画稿本身呈现出来的“气韵”。动画电影的基本形式——画稿,是为主题与内容服务的,所以不仅对绘画技术有要求,还需要创作者在对作品整体理解后将个人观念、情感与想象力投注其中。
当前传统题材国产动画的画稿,受国外动画影响严重,极力追求高科技特效而忽视文化特性,使得动画构图缺乏民族独创性。以“神”“妖”形象为例,作为传统题材动画电影中必不可少的角色,反映在当代动画电影中很难找到本民族的审美定位。《大圣归来》中,体格健壮、身形魁梧的大圣不再是传统审美下灵性十足的美猴王,更像是以美国漫威系列为蓝本、以孙悟空为原型塑造的中国英雄。《白蛇·缘起》中身着低胸装、袒露大长腿的狐狸精形象与传统审美下的妖怪形象相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神还是妖都是一种无法说明的精神观念的投射,更注重投射对象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正如《搜神记》中言:“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而不是体型之怪与肉体欲望。这些基于模仿而非在观念、情感、创造力支配下融入“气”的动画形象,是无法呈现神形兼具之“韵”的。由无数仿作画面构成的动画电影从形式层也难以呈现其“第二自然”。那么,动画电影如何在形式上生成气韵呢?“中国学派”做出了卓越示范。以“狐狸精”为例,《铁扇公主》中的玉面狐狸 “倒挂八字眉,高鼻梁,樱桃嘴,具有国画写意画的风格韵味”[5]。片中并未过多袒露玉面狐狸的身体,但无论是对镜变脸还是曲意逢迎,举手投足间都让观者感受到这是一个卖弄风骚的女妖怪。再如《鹿铃》中的惜别片段,小鹿从见到父母的疑惑与兴奋,到对小孙女的不舍,再到分离,整个片段没有一句对白,全靠鹿的“眼神”来完成情感转换。椭圆形的眼神意味着疑惑与迷蒙,五边形的眼睛传达着惊讶与不安,半圆形的眼神透露着无辜与不舍,最后以月牙形的眼睛传递出释然与深情。中国学派的创作者们始终看重画稿的内在韵味,认为“人物形象的特征和神韵恰如山中之仙,水中之龙,有了它,插图中的人物就能栩栩如生,神采流动,没有它,人物就会显得平淡呆滞,黯然失神”[3](P.25)。这里所谓的“神采流动”即创作者运用“气”将文化观念、民族情感、想象力等通过画稿的方式进行的具象表达,从而在动画形象中呈现超脱于画稿之上的“第二自然”即“气韵”,由无数以“气韵”为审美标准的画稿剪辑而成的动画电影自然能有生动之美感。
以气韵融入画稿的创作理念不仅成就了中国学派的辉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动画界的创作。日本的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白蛇传》改编自中国神话。日本动画开山鼻祖手冢治虫在自传性动画电影《手冢治虫物语:我的孙悟空》中明确表达,《铁扇公主》中“孙悟空”就是激发他走向动画创作之路的根源。当代动画大师宫崎骏的成功更是离不开其坚持手绘的创作理念:“全世界的动画都在向 CG 发展,宫崎爷爷却与之背道而驰,执着于手绘,哪怕短短4秒的动画也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1)参见纪录片《永无止境·宫崎骏·梦与狂想的王国》,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914399/。即便是宫崎骏在2018年首次采用CG 技术制作的动画短片《毛毛虫菠萝》中,就菠萝出生时的一个转头动作便做了两个多月,宫崎骏认为动画师做出来的效果并没有将菠萝初次看到这个世界的天真表现出来,“基本上就应该比较迟钝,世界对它而言还是陌生的,这个动作全都是文化”(2)参见纪录片《永无止境·宫崎骏·梦与狂想的王国》,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914399/。,这里所说的“文化”便是创作者之“气”在画稿中的投注。CG动画通过数据测算固然能做出仿真式的画面,但技术侧重于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而缺少手绘赋予画面的艺术灵动感。基于此,将气韵引入动画电影理论研究,它不局限于国别,以民族文化与艺术特性为要;也不局限于古典审美范畴中形而上的审美内涵。它可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存在,在动画电影形式层知识性地分解为创作者基于对作品的理解之上,倾注于画作之上的情感、观念、想象力,和观赏者基于创作者之“气”上,产生“韵”的心灵脉动与气质情调。所以,国产动画电影尤其是传统题材国产动画电影从形式层引入“气韵”的审美,无须以一个又一个的悬念推动情节发展,甚至无须过多的对白与音效,仅从一张张气韵生动的画稿中就能将观众拉入故事情境,这便是“气韵”在动画电影形式层中运用的魅力。
三、从“气韵”的内容层观照动画电影
将“气韵”引入动画画稿,它从形式层连接着创作者、作品与观影者,在视图观感层将观者带入一个特定的民族场域。那么,内容层如何走向“气韵”?这关涉到“气韵”在动画理论中的第二重路径,也是动画电影生成“中国气韵”的根本,即以民族文化之“气”为精神根基烘托动画电影之“韵”。主题是气韵之根,文化为气韵之魂,而当前动画电影在主题表达非中国化的同时,也没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
(一)主题非中国化
抛开审美素养与鉴赏能力,观众观影之后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主题。基于民族精神文化的主题可以将形式层中“气”的连接效用发挥到最大,继而在无意识层面与观影者达成交流。“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中,虽然包含着一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不被社会、道德、审美所接受的人性原始欲望的内容,但顾明栋在此基础上认为“文化无意识现象,不仅是一种心理功能和被压抑的记忆和情感的表现,更是一个以不知不觉的方式产生有意识的认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思想机器”[7]。动画电影作为新时期文化无意识的载体之一,其价值观念往往以民族文化为基础。所以,透过《料理鼠王》《冰雪奇缘》或是漫威英雄我们能从中看到美国文化中对梦想与自由的追求,哪怕是改编自中国题材的《花木兰》《功夫熊猫》,也折射出美国梦的意识形态意义;在日本动画中,从《悬崖上的金鱼姬》到《千与千寻》再到《天气之子》,对青春之爱的赞颂是永远绕不开的情节。回到中国动画,早在“中国学派”时期,动画电影极力建构民族风格之外,也在情节之中融入了意识形态内涵。1941年上映的《铁扇公主》传到日本后不久便被禁止播放,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部体现了反抗精神的作品,粗暴地蹂躏中国的日本军,遭到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的痛击”[3](P.91)。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动画电影主题就像是无意识层面的一个触角,通过精神层面的交感,与观众无意识层面的文化触角产生共鸣。
然而,当代中国传统题材动画电影,在国外艺术创作观念与价值意涵的严重侵袭下,民族性主题表达已十分罕见。2015年上映的《大圣归来》,看似是对《西游记》的创造性改编,但单线式的故事与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结局,与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主题极其相似。同样以传统题材作为改编对象,影片中的木兰替父从军,在大军溃败之际,既无体力又无武力的她以智慧为武装力挽狂澜,以一己之力救百姓于危难,一举成为人人崇拜的民族英雄。这是美国英雄的经典模式:心怀梦想的凡人——强烈的戏剧冲突下发掘个人潜力——怯懦自我与梦想自我的对话——梦想战胜怯懦——正义战胜邪恶个体拯救集体。以此模式来套用《大圣归来》,大圣就是美国故事中的“凡人”,旅途中与江流儿之间的情节发展就是“自我与内心”的对话,“山妖”作为片中反派,最后落败于大圣的脚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圣归来》可以说是以中国动画的形式塑造了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国产动画的主题受他国价值观念的操纵,使得以“大圣”“花木兰”为代表的传统题材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元素,镶嵌在国外动画的艺术创作观念与价值内涵中,而中国“气韵”毫无体现。
(二)价值观偏离本民族文化
当传统题材改编而来的国产动画电影将中国(故事、民俗、建筑等)作为一种元素在使用时,作品本身就成为了在中国传播他国价值观念与艺术审美的流水线产品。长此以往,此类动画电影既无法引起共鸣,也失去了民族独特性,实际上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2017年上映的《大鱼海棠》可作为价值观偏离本民族文化的典型,影片中“责任、爱与守护”的主题一直为人诟病,主人公为个人情爱不惜牺牲集体利益的行为被观众指责为“三观不正”。主创梁旋坚持“故事的原型,包括设定的原型,这些完全是从中国文化里来的”(3)参见《中国动漫创造自己的风格需要一个过程——〈大鱼海棠〉主创访谈》,2016年,中国作家网。。诚然,电影中空灵澄澈、随顺自然的浪漫情怀,舍身救人、善恶分明的情义确实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主人公为了个人的“爱与守护”,进行损他利己的行为是无法引起观众共鸣的根本原因。即主创者只看到电影主题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没有将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衡量主题的表达方式。
以青春之爱诠释“责任与守护”的主题并非中国的文艺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情感是建立在仁义道德、家国情怀之上的。所以在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爱情始终无法战胜纲常伦理,多以悲剧收场。中国普世价值中对纯粹的爱与性避而不谈;但在日本的文化中,它们却是生命力蓬勃旺盛的象征,且有其美学渊源。日本自江户时代开始便“产生了一种以肉体为出发点,以灵肉合一的身体为归结点,以冲犯传统道德、挑战既成家庭伦理观念为特征,以寻求身体与精神的自由超越为指向的新的审美思潮”[8](P.6)。自由情感、身体美逐渐剥离了世俗的粗鄙定义成为美学范畴“意气”的重要部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及文学艺术。在这种美学传统下,日本影视文化中对青春纯爱的赞颂遵循其文化历史,自然能引起日本民众文化无意识层的精神共鸣。动画电影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突破一切固有的形式,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既超越现实又合乎情理的理想世界。而《大鱼海棠》中,椿为了鲲的生命不惜葬送全族利益,这种情节设定与传统文化中舍己为人、克己奉公的思想相悖。
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的社会以伦理为核心,追求的是由家到国而天下的人伦温情,家国情怀才是传统美学的主流。有学者认为《大鱼海棠》展现出了一种艺术之光与人性之美(4)参见贺敏、王宁于《电影新作》2019年第2期上发表的《大鱼海棠:人性之美与艺术之光》,文章认为大鱼海棠中是对人性真善美的歌颂。,特指椿、湫、鲲三人之间为了爱不畏牺牲的勇气。诚然,传统文化中,爱与善是光辉的人性,但这种人性美远没有与家国利益抗衡的能力。面对质疑,主创梁旋将电影主题归结为人性在善意的驱使下做出的抉择,“很多问题你需要做选择。所以,椿是一个善良的人,她觉得不管怎么样要把鲲救活。面对生死问题,其他的东西可以往后排”(5)参见《中国动漫创造自己的风格需要一个过程——〈大鱼海棠〉主创访谈》,2016年,中国作家网。。生命诚然可贵,但在家国利益面前,君子必然心怀“杀身以成仁”的志气。《大鱼海棠》历经12年的苦心匠造,是肩扛重返“中国学派”之重任的,在考虑无拘束表达、展示民族艺术特色的同时,更要站在民族文化的视野下以主题为牵引搭建与观众之间的精神桥梁。正如万籁鸣先生在历经20年的创作实践后提出的“美术片走民族化道路是关系到我国美术电影艺术能否跻身于世界美术电影之林的大问题”[3](P.129)。
四、《哪吒》——生成“中国气韵”的尝试
传统题材国产动画电影从形式到内容尚未具备气韵之美学品格,面对这一现状,我们很难说明中国气韵具体包含哪些方面,因为它正需要创作者转变视角,从以往经验性的“仿日赶美”上升为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下的动画作品,从而进行理论的发现与再创造。这一创造首先要求动画作品要深植民族文化精神;其次,以绘画为基本形式的动画作品,其画稿需洋溢着一股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给人以 “气韵”之审美感受。最为关键的是从精神层面引起观者共鸣的同时,还需体现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反思与对人类生存问题的追问。就此而言,《哪吒》做出了较好的示范,为传统题材动画电影生成“中国气韵”提供了一条可能性路径。
(一)形式层:以哲思入画境
“气韵”在《哪吒》的动画构图中,以一种方法论的形式存在。“气韵”与“气化论”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万物根源于气,气在哲学范畴中既指客观存在的质料之气,也包含主体在内的一切生命存在的内在活力与精神性情。然而气不是静止的,“动”是其根本属性,且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和方向运动才能具有审美特质,否则会与期望值相悖而出现错乱。“韵”的本义是音律的和谐,将“韵”作为“气动”的规律,动画构图必然呈现和谐的美感。
以“气韵”的哲思引入动画构图,这在《哪吒》的人物形象设定中最为直接。混元珠作为哪吒与敖丙的原生之气,之所以仙气魔气缠绕、善恶不分是因为吸收的天地灵气过于驳杂,原始天尊的炼化过程就是循着内在规律将驳杂之“气”一分为二,在这个过程中,“韵”是天地灵气运行的规律,同时也是力求达到的审美之境。此外,太乙真人与申公豹作为影片中最具颠覆性的形象之一,他们剥离了传统思维定式中对仙神的形象塑造,而将性情与外在之气融为一体,这种由“气化形、形传神”的动画形象还有龙王、长生云、夜叉、坐骑等。以“气韵”入画境的创作理念在影片中营造出了万物皆有灵的动画效果,极具审美张力。
以“气韵”为方法论是为了呈现“和之美”。回到造型设定,太乙真人与申公豹作为魔丸与灵珠的派生形象,并没有带给观众一种善恶对立的情感冲击,其审丑化的外在与世俗化的性情中和了观众思维定式中仙神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增强影片趣味性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心理满足感。其次,《山河社稷图》的情节设计,既是中国画结合现代技术做出的动画实践,同时也通过动画的方式展示了山水画的精神意涵。历史上的画山水观念起源于文人墨客对修身悟道的追求,正如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言:“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古典文化中,山水具有与哲学层形而上之道相连通的意涵,所以在传统观念中,画山水、观山水画是现实世界体道、悟道的实践方式。《哪吒》中《山河社稷图》的环境由仙术构建且区隔于世俗,这与哲学范畴中与形而上之道连通的自然山水相似。再次,哪吒带有先天魔性,太乙真人令其进入图中就是为了能让他在象征着天人合一的图画世界中修炼,以中和其身上的戾气。《山河社稷图》的情节设计,预设了山水画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意义,而哪吒以“进入”的方式修炼自身与古人画山水、观山水画悟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动画电影“不只要求有合乎情理的故事、有结构完整的情节和符合艺术真实的形象,还必须有戏剧剧本和一般影视剧本所没有的完全属于动画的独特创意和表达”[9]。《哪吒》在形式层追求“气韵”之美的过程即动画的独特创意与表达,且与曾经“中国学派”所追求的“诗性”“禅意”等古典美学品格相比有了进一步的超越。它从作品整体出发,以现代化的技术将传统哲学与美学进行动画实践,使观影者能从文化无意识层接受这种创作精神的同时又能直接领略到其生动有趣的表达。
(二)精神气韵:“我命由我不由天”
如果说形式层往“气韵”美学靠拢是创作者自觉走向民族化的体现,那《哪吒》中基于美学传统传达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价值内涵才是生成中国气韵的根本。它以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结合社会现实生成了《哪吒》之精神气韵。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带有民族标识的精神性产物,其起源与道教内丹术相关。张伯端在《悟真篇》中云:“一粒金丹吞入口,始知我命不由天。”内丹术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性命修炼,通过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四个阶段的苦修,以期打破虚空,成就不死之身。其“天人合一”的理论根源于传统哲学“气化论”,即天地万物为一气流荡之大生命,“气”既是万物之源,又是其生命意义的呈现,所以人亦能通过修炼内丹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从气化论理解“我命由我不由天”指向双重关系:其一,“我命”与“天命”是两相对等之物;其二,“我命”不仅指自然生命,还包括个体锐意进取的精神,且这种精神可作为天人感应的媒介。《哪吒》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表达与传统思想十分契合。影片中,哪吒之命与天命始终保持平衡姿态,促使哪吒打破魔丸命定论的是民族文化中“忠孝”的伦理观念。哪吒何以能逆天改命,其力量无非来源于两点:一是以“孝”的方式对父亲用换命符救他这一举动做出回应,哪吒深知李靖希望的无非是陈塘关百姓的安宁(这也是他对百姓的“忠”);二是从集体的认可中获取精神动力,当哪吒以“孝”的方式对父母做出回应时,百姓们的态度由偏见转为尊敬,这也将他“逆天改命”的行为推向了更高的精神境界。
具有精神气韵的主题表达,向来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即便是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表达的方式也有差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忠、孝为代表的伦理信念远优先于个人利益;而在西方文化中,基于自由的个体性构建更受关注。以中国故事“花木兰”为例,中国文化环境中的花木兰是忠孝文化的典型人物,其女扮男装为父尽孝、血战沙场为国效忠、胜仗归来为光宗耀祖。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弱化了个体对家、国的责任与牺牲,而将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木兰的个人品格之上。所以我们在迪斯尼动画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坚毅果断又勇于追求真爱的现代女性形象。不同的文化直接影响着动画电影中的价值观念。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由何而来?梁漱溟曾言“中西文化不同,实从宗教问题分途,而中国缺乏宗教,又由于理性开发之早”[10](P.109),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受宗教影响深远,而中国人持有的是非宗教的世界观。受“气化论”影响,中国自古以来追求天人合一之道,且占据中国文化半壁江山的周孔教化,渗透式的将祭天、祭祖等神灵崇拜的内容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没有宗教的束缚,加上儒道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中始终趋向理性和自信,思想上的紧箍咒是以家、国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而西方历史长期受一神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使其近代开始了思想上的觉醒,觉醒的首位就是要尊重并肯定人的欲望,恢复个体自由。由此,西方动画电影强调的是一种极具自由精神的奋斗观,其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而更为关注完善的个体性人格建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价值理念之所以能成为《哪吒》的精神气韵继而引起共鸣,正因其从中国民族文化的角度契合了当代人的深层伦理意识。
(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当代意义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熏陶下形成的。” [11](P.22)植根于传统哲学思想之上的“自立自强”的精神即为民族的“共同心理”,“我命由我不由天”即是从中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念。所以,当怀有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观众去欣赏《哪吒》时,本能地会与之产生情感交流,最终达成共鸣。当然,我们说“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带有民族性标识,并不意味着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兴旺发展都离不开这种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这在美国的动画电影中表现尤为明显,漫威系列中的英雄大多是平凡之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获取拯救世界的能力;即便是以童话为创作题材,公主和王子也要拼尽全力战胜邪恶的力量才能收获幸福。动画艺术本就是舶来品,中国动画电影更是在对国外动画的效仿与学习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受国外动画技术与艺术审美的影响不可避免。然需指出的是,《哪吒》是中国动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做出的巨大突破,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内涵深植于民族哲学,从文化无意识的角度结合社会现实,展现了个体叙事中的中国故事。影片所传达的“自强不息、逆天改命”精神与当代社会正面价值观十分契合,可谓是奋进中的中国社会群像。
有学者指出:“当下中国动画创作的当务之急是升华故事思想,并积极探索民族化表演与现代视听语言的结合方式,从而创作出富有时代风貌与民族气韵的动画作品,接续动画‘中国学派’的民族化道路。” [12]以民族文化为精神根基,形式层自觉向传统美学靠拢,足以体现《哪吒》走民族化道路的自律性。而以艺术化的方式提炼现实,弘扬与当下正面价值观相契合的精神是《哪吒》展现时代风貌、生成中国气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偏见”作为影片的核心问题,创作者并没有站在某一个角色的角度去批判,而是从不同的角色视角对其进行全面展示。哪吒、敖丙看似一正一邪,实则命运共生,他们都受到个体所在领域内伦理道德的支配,竭尽所能的完成伦理设定下的使命,所以观众不仅为哪吒逆天改命的努力而感动,也为敖丙肩扛龙族复兴的使命而心疼。这也是为什么疫情当前,当全国各省市驰援武汉,发出“把最硬的鳞给你”这样的声音时,能引起强大的社会共鸣。此外,影片中还包含着对父母之爱、朋友之谊、师生之情的赞颂,这都与当下中国正面价值观相契合。
当今社会,我们赞扬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更提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百折不挠的奋斗中形成,也成为了我们筑梦、追梦的内生动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人间万事出艰辛。越是美好的梦想,实现起来越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无论民族复兴之梦,还是个人幸福之梦,奋斗都是筑梦圆梦的底色。”[13]从民族精神文化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路,生成了《哪吒》中国气韵的品格,由它带来的精神激励与社会价值也远远超出了其作为动画电影艺术所承载的功能,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呼唤国产动画电影走向“中国气韵”的根本原因。
结 语
以气韵引入国产动画理论研究并非全盘以古典美学的标准来要求作品,过于形而上的表达极考验观影者的审美素养,反而将大量观众挡在门外。动画理论中的气韵要廓旧创新,走民族化道路的同时体现时代气韵,精神上立足于民族文化,形式上以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又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荧屏呈现。《哪吒》就是在古典美学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以一种全世界都能读懂的方式对“中国气韵”做出的卓然呈现。这既是对中国精神文化与美学传统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动画电影在民族思想、美学熏陶下对动画表现形式的突破与创造。动画电影作为文化自信道路上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关键领域,创作出具有中国气韵的动画电影不仅关系着国产动画在国际动画界的地位,也是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侧面体现。“世界美术片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越是具有民族特点的影片,就越是具有世界意义,越能赢得外国的观众。”[13](P.130)反观当下国际动画领域的发展,IP创作渐成趋势。由此,传统题材国产动画极占优势,因为在本民族文学艺术大花园中,奇卉异葩,蔚为大观,题材广博,风格多样,正等待动画创作者的深入挖掘。而将“气韵”引入国产动画理论研究,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创作出富有时代风貌与民族特点的动画作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何来胜《李白忆东山(其一)》
- 黄印凯《听风》
- 崔水良《龙井方向》
- 顾致农《高山流水》
- 徐境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 林浩浩《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