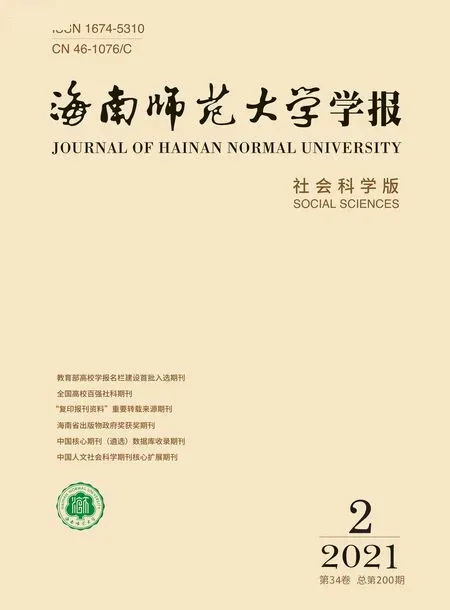论乡村教育价值取向之“离农”与“为农”的悖论
陈雯婧,汪建华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乡村教育价值取向是指参与乡村教育活动的主体在面对或处理乡村教育活动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倾向(1)李森、崔友兴:《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75页。。教育价值取向有着极强的实践品格,在乡村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工作者基于自己的价值立场,发挥自身能动性,创造出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教育。简言之,乡村教师期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教给学生什么知识、以什么方式教以及如何评价学生等一系列观念的形成,无一不受其教育价值观的影响,甚至由其教育价值观直接决定。
一、乡村教育“离农”与“为农”的产生及释义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要求全国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全力推进工业现代化。乡村教育价值取向是在服务于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优先地服务于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建设,向城市输送人才。(2)李森、崔友兴:《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第76页。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村社会,人们将教育作为出人头地的跳板,通过受教育进入城市,进而改善自身经济物质条件与社会地位成为普遍现象。“离农”的乡村教育价值取向主张乡村学生“跳出农门”,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取向(3)肖正德、卢尚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教育变革:文化境遇与文化选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具体而言,乡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物化的,极具功利性,其价值取向就是提高乡村学生的文化素质和适应现代工业、城市生活的能力,为其进入城市谋求一份可观的收入做准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成为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乡村教育工作者必须认识到,虽然在政府与人民的不断努力之下,乡村每家每户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但是在精神层面,价值观的传递尚未得到有效筛选。因此,在乡村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关注学生在知识层面的发展,更要关注学生更深层次的内在的成长需要,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为本地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为价值取向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在全国兴起;1988年5月推出的“燎原计划”要求“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农村教育应当面向当地农村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大力发展活泼多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学好文化课的基础上强调实用技术和经营本领的掌握,以期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5)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854页。;在当代社会中,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导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已有学者将目光置于乡村本身的发展。“为农”的乡村教育价值取向主张乡村教育应当立足于农村、以农民为主体。具体而言,就是在乡村中小学教育中重视对学生农业技能的训练,为学生毕业后能很好地立足于乡村社会做准备。(6)肖正德、卢尚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教育变革:文化境遇与文化选择》,第4页。
二、乡村教育“离农”与“为农”的悖论分析
运用演绎、逻辑推论的方法理解“离农”与“为农”两种乡村教育价值取向,在应然层面上,两者看似能构成一对矛盾,人才是否应离开乡村、是否要建设乡村、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等都会成为矛盾的一部分;在实然层面,二者却构成一个悖论,片面地理解“离农”与“为农”两种乡村教育价值取向,极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首先,“离农”与“为农”的释义不能简单化;其次,乡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乡村学生的发展,使学生能够立足于现实,从而更好地融入生活、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而不是成为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边缘人;最后,乡村教育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系统,它在受到社会各个方面制约的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但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一)“离农”与“为农”在应然层面构成一组矛盾
基于演绎法,“离农”的乡村教育价值取向主张乡村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当是离开农村、面向城市的。一方面,乡村学生通过这种教育,皆有可能实现社会流动;另一方面,“离”代表分离、离开,以“离农”为导向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是不属于乡村的,他们所受教育的目的、内容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受教育就是为了跻身城市发展的浪潮,成为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毕业后不会建设乡村,也缺乏建设乡村的乡村视角。生于乡村、被养于乡村却没有乡村情怀和精神上的归属感,这被认为是乡村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此一来,乡村教育的社会功能没有被实现,乡村建设也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为农”的乡村教育价值取向常被经验性地等同于“为乡村服务”,乡村又以第一产业为主,那么乡村教育就应该大力培养学生的农业技术,有时“为农”的教育更是被狭义地理解为“务农”的教育。(7)邬志辉、杨卫安:《“离农”抑或“为农”——农村教育价值选择的悖论及消解》,《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1期。基于逻辑推论,以“为农”为导向的乡村教育主要传授农业知识,培养建设乡村的专才,从而缩短城乡经济差距,促进乡村的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这样的教育不仅带有浓厚的社会改造主义色彩,甚至还有失教育公平。
(二)“离农”与“为农”在实然层面构成一个悖论
1.“离农”“为农”释义的简单化倾向
“离农”的乡村教育价值取向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我国自古就有乡学、私学、义学等多种形式的乡村教育,春秋时期私学的产生,更是为乡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以前,乡村教育的内容大多是社会伦理道德教化以及关于生产生活的基本知识(8)李森、崔友兴:《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第55页。,乡村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被广泛接受。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式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使乡村文化的主流地位受到威胁,加之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逐渐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到了20世纪30年代,代表着西方现代化价值体系的新式学校已经遍及中国乡村,“这种长期推行的学制意味着乡村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对已有的城市与工业的移植与照搬的过程”(9)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科技与人文知识等教育内容,进一步催化出了这种脱离传统乡土社会的“离农”乡村教育价值取向。在当代社会,少数乡村学生通过参加高考进入城市,另外也有大量的农村学生因高考失利无法进入城市,并被贴上教育失败的标签,他们将走出乡村的梦想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10)张济州:《离农?为农?——农村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3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实现阶层社会流动的“幸运儿”,到城市生活,成了大多数乡村学生所背负的梦想。然而,人才的离开是暂时的,能否回流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因为乡村教育为城市输送了人才,就说“离农”乡村教育价值取向与建设乡村是矛盾的,更不能将之作为乡村人才流失的原因。
针对“为农”的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社会上存在片面化、简单化理解的倾向,“为农”的乡村教育被等同于“务农”教育,甚至被看作乡村发展的救命稻草。198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农村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11)魏峰、张乐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嬗变》,《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农村教育教学改革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1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3年9月17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tnull_27725.html.。2011 年,教育部等九部委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强‘三教统筹’,推进农科教结合,培育新型农民”(13)魏峰、张乐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嬗变》,《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11期。。可见,从“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工业化的进程”,到最终“为了新型农民的发展”,在实然层面,“离农”和“为农”这两种乡村教育价值取向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而难以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对“为农”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释义应具有相对性,要结合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进行理解。
2.乡村学生发展的双重边缘人倾向
将“离农”与“为农”这两种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置于矛盾的关系中,难免使乡村教育的发展进入误区。绝对的“离农”乡村教育,其教学内容较少涉及乡土知识;在判定其教育活动的价值时,往往采取外在的工具性评价标准,却忽略了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价值主体的内在要求。这不仅强化了乡村教育对于城市教育的依附性,也令乡村学生缺乏文化归属感。一方面,部分成功“跳出农门”的学生,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市学生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地生活,却总感觉与城市格格不入;再加上面临找工作、购房、结婚和生子等困难,长期难以在城市立住脚跟,基本无力照顾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另一方面,在考试角逐中失利的乡村学生,由于一直接受“离农”价值取向下的乡村教育,并未掌握能在乡村生活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再加上乡村产业链的单一等现实,他们往往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处境。
片面化的“离农”教育使受教育者处于乡村与城市的边缘,成为双重边缘者。(14)田夏彪、张琼:《当前我国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误区及其危害》,《教育探索》2009年第2期。而在片面的“为农”乡村教育价值观指导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培养的不是建设乡村的人才,而是一种理想化人才。将乡村本身的发展作为乡村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夸大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同时也给乡村教育赋予沉重的任务,使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边界扩大化、模糊化。教育虽具有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必须基于教育活动,并最终通过学生的发展来实现。即便“乡村专才”的培养具有实践意义,也有违教育公平原则。有学者提出:“乡村教育的开展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其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保障四千多万乡村学生的基本人权和发展权利,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途径”(15)范先佐:《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在乡村教育中,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当更多地强调教育内容的基础性与普适性,不能过早进行职业教育,更不能代替受教育者选择职业。
3.乡村教育实施的画地自限倾向
乡村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出更多能够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人”,这种画地自限的农村教育观,实际上是预设了农村可以远离城市而发展的虚幻前提。(16)葛新斌:《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弃儿及其前景》,《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12期。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命运共同体、加强沟通与合作是大势所趋,而自力更生成为一种过时的浪漫,倘若硬要将乡村教育的发展置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中,让它成为一座孤岛,那么乡村的崩溃和断层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一部分的发展都与其他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乡村教育也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系统。因此,应当避免看着乡村谈乡村,不能忽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自我调节功能,更不能关起门来做研究。首先,乡村教育的现代性不会导致第一产业的发展无人问津。一方面,农业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有专业人员为了推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而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另一方面,国家与市场自会调节各产业之间的发展,它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此消彼长。其次,努力构建政府——企业——学校共同体,已经成为乡村教育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我国较偏远的乡村,政府“牵线搭桥”,企业与中小学、高校与中小学、中小学与中小学之间进行一对一帮扶和对口资源共享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另外,早已有学者将乡村教育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乡村之外,着眼于整个社会。他们将乡村教育定义为“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服务的一切教育”,其教育活动发生的场域并不局限于乡村,也包括城市;不局限于学校,也包括社区;不局限于普通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
三、乡村教育“离农”与“为农”悖论的消解
(一)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随着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乡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学生的教育需求也趋于多样化。因此,乡村教育的价值取向应当对此作出回应,对“为农服务”“以农为本”予以重新认识和定位(17)洪俊:《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兼论农村教育必须坚持为“三农”服务》,《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同时综合考虑乡村教育地位的基础性、发展的不均衡性、形式的多样性、空间的分散性等特点。对于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研究应当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运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为农”和“离农”的乡村教育价值观的冲突很难调和(18)王本陆:《取消“双轨制”: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伦理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但是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要求打破城市与乡村相互分割的堡垒,促进城乡一体化,其中就包括教育发展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建设不是指所有乡村学校都向县城转移,更不是排斥差别,而是更好地利用差别使教育、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更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一方面,乡村教育价值取向应坚定地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要求,坚定地为 “三农”的发展服务。(19)洪俊:《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兼论农村教育必须坚持为“三农”服务》,《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期。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教育要挺直腰杆地成为“为农”的教育。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及其附带价值观的多向交换成为可能,乡村教育在内容、形式、方法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都打破了传统、单一模式的趋势。从这个层面看,乡村教育确实是“离农”的教育。不论是“为农”的教育,还是“离农”的教育,实际上都是为了使学生通过教育获得发展,使“强农”成为可能。最后,要使“三教统筹”落到实处,而不是口号化、形式化,就要通过乡村教育引导乡村学生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开阔视野,使他们即便无法成功升学也能在乡村谋求好的出路。
(二)乡村教育价值中的人文关怀
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人才,而乡村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是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乡村人才的流失也是“离农”乡村教育价值取向被批判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人才是否建设乡村并不是由倡导“离农”“为农”的乡村教育价值取向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除了需要建设者有知识、有能力之外,更需要建设者对所在乡村有情感、对乡村建设有坚定的信念。新保守主义提醒我们:教育自身应该被看作是目的,而不仅仅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工具主义者的立场);传统虽然能够维持既定利益,但同时也是维护与发展学校标准的关键,还是一种创新和生产新知识的条件。(20)[英]迈克尔·扬:《把知识带回来——教育社会学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的转向》,朱旭东、文雯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5页。因此,在探讨乡村教育问题时,不仅要将目光投向教育的价值取向,还应引导乡村学生弄清楚乡村生活本身的特点及其文化底蕴。教育本身就具有人文意义,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投射以人文关怀,乡村教育理所应当地关心乡村儿童的存在、生活的意义和生命价值。(21)郭元祥:《课程观的转向》,《课程·教材·教法》2001年第6期。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是“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在同一地域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血缘、地缘关系构成以共同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22)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页。这种乡村自治机制赋予家族“长老”以及地方士绅合理权威。(23)[美]费正清、[美]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R.)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页。然而,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这种自发且自律的管理模式受到挑战与威胁。乡村本身的知识和价值在以城市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遭遇贬低和排斥,乡村教育存在的价值也变为仅仅是为城市输送劳动力和少数精英(24)翁乃群:《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0-141页。。再加之新式教育的兴起,传统的前喻文化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并喻和后喻文化更是后来居上,乡村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老”的权威被削弱的同时,其文化影响力也大大下降,他们渐渐成为了没有生产力的独居老人、留守老人,但他们仍然是最熟悉所在乡村、并且深爱那片土地的“守望者”。老人们对乡土的热情如果能够被引进到乡村教育现实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成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一部分,成为课程创生活动的主题之一,那种热情应该能够引起有效在场者的共鸣,这样的课堂,是乡村学生、乡村教师和村民了解自己所在乡村并成为乡村建设积极参与者的第一步。
(三)乡村教育要回归乡村生活
乡村文化在近代衰落已经成为共识(25)郝锦花、王先明:《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因此,继承和发扬乡村优秀文化就成了“强农”教育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乡村生活中曾经的“长老”、现在的“守望者”们,正是让乡村优秀文化“活”过来的关键。他们了解并热爱乡村,这样的“归属感”是可以传递的。除了依靠政府支持乡村教育中的文化建设,乡村还应该发展文化产业,向外输出优秀文化的同时,将故事性、情境性的文化教育带入学校和社区。通过内外双向信息交换,乡村不仅能吸引游客、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创造经济收入,还能对乡村文化进行再继承、再创造,引领乡村文化的建设。这也是乡村社区与学校协同合作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方式之一。在乡村教育中,引导学生理解“乡村”时,不能仅仅强调“乡村”的物理空间属性,更要强调乡村是乡村学生成长、发展的精神场域和文化场域。乡村教育的开展必然要以乡村生活世界为基础,成为乡村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的基本背景。(26)刘铁芳:《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对于乡村学生而言,“当外来文化价值渲染日渐强势,本土文化可能成为其排斥的对象,进一步内化为他们的自卑情结”(27)刘铁芳:《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读书》2001年第12期。,看不起、瞧不上所在的乡土是文化和人才急速向城市“看齐”的原因之一。因此,乡村教育要回归乡村生活,重视乡村学生的内在精神需求,通过开发课程、变革教学方式和建设校园环境等途径培养乡村学生对乡村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引导他们产生文化自觉和自信,进而热爱并愿意建设自己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