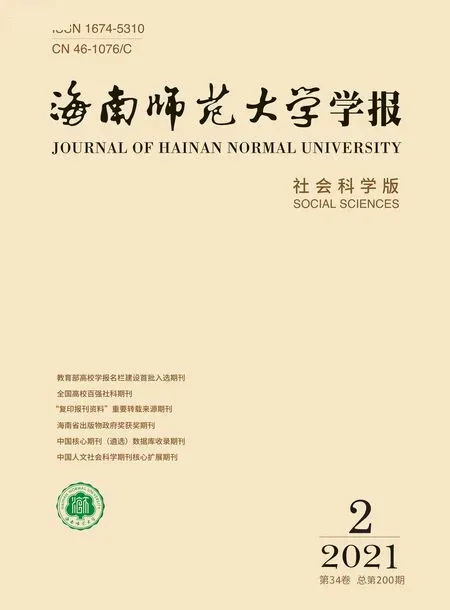从《粲花斋五种曲》的婚恋模式看吴炳的情与理
肖明玉
(澳门城市大学 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澳门 999078)
一、吴炳的“情”与“情邮”
吴炳(1595—1647),字石渠,一字可先,又号粲花斋主人,江苏宜兴(古称阳羡)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卒于清顺治四年,终年53岁。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崇祯时任江西提学副使,南明永历王朝时,任兵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为清兵所俘,绝食而亡。所作传奇五种,总名《粲花别墅五种》,均有存本(1)因论文重点在于分析吴炳情学思想,依据《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和各家考究辨析整理,故选择五本均存的暖红室版本作为研究底本。;著有《绝命诗》一卷(共百首,现仅存一首)、《意园集序》和奏疏《亲贤远佞意疏》(见录于《宜荆吴氏宗谱》,后一种失传),另外还著有《说易》《雅俗稽言》《督学吴公祀名宦录》,但均失传。
吴炳的作品只有《粲花斋五种曲》(《绿牡丹》《西园记》《画中人》《疗妒羹》《情邮记》)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因其平生所著文章大多散佚,当中唯独在《情邮记》传奇前撰写的一篇小记,较为详细地阐发了他的“情邮”论说,从中可大致看到吴炳对于“情”的一些想法:
传中载刘生遇王慧娘贾紫箫事,偶在邮舍而名曰情邮。有说乎?曰“有”,夫邮以传情也。人若无情,有块处一室,老死不相往来已耳。莫险于海,而海可航,则海可邮也;莫峻于山,而山可梯,则山可邮也。乃至黄犬走旅邸之音,青鸟啣云中之信,雁足通忱,鱼肠剖缄,情极其至,禽鱼飞走,悉可邮使。又何待津吏来迎,而指云生东海;驿人偶遇,始忆春满江南哉!盖尝论之,色以目邮,声以耳邮,臭以鼻邮,言以口邮,手以书邮,足以走邮:人身皆邮也,而无一不本于情。有情则伊人万里,可凭梦寐有符招;往哲千秋,亦借诗书而檄致。非然者,有心不灵,有胆不苦,有肠不转,即一身之耳目手足,不为之用,况禽鱼飞走之族乎?信矣,夫情之不可已也!此情邮之说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惟情亦然,若云人生传舍,天地蘧卢,人知情之为人邮,而不知人之为情邮也,则又进之乎言邮者矣。粲花斋主人题。(2)[明]吴炳撰、[清]吴梅校正:《暖红室汇刻传奇 粲花斋五种》,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55页。
吴炳开篇便强调“情”的重要性,其认为人若没有情义,近在咫尺也如同远隔天涯,同时也认为“情”无止境,世间万物也因为有“情”才有了灵性。其次,在“情”的基础上,吴炳主张还需要“邮”,即通过情感传递,并且要善于利用耳目手足来传情。这种想法与汤显祖所秉持的观点相近: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3)[明]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96页。(《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4)[明]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徐朔方笺校,第1497页。(《耳伯麻姑游诗序》)
二者皆认为世间万物为情而生,为情而动,但汤显祖认为情不会因社会和个人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消亡殆尽。而在吴炳看来,如果情感没有经过外力媒介传达则也就无动于衷。最后,吴炳又使“人”与“情”发生倒置,感叹人们知晓“情为人邮”而不知“人为情邮”,体现出他对“情”这一概念的复杂态度。
虽然吴炳的“情邮”论说主要围绕《情邮记》而阐发,但其他四部传奇里作者欲表达的主题亦与该引子所隐含的“堪笑人生驿站,纷纷碌碌,总跳不出情字里”的观点有所关联,并多处存在对汤显祖“至情论”的有意模仿,如《画中人》里借华阳道人之口提到的“有情无情说”:
天下人只有一个情字,情若果真,离者可以复合,死者可以再生。(第五出 示幻)
除此之外,吴炳还摹写《牡丹亭》中柳梦梅拾画叫画的情节,将其移植到庾启与郑琼枝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结识中,演变为:有情则画中人走下画来,无情则画中人又回到画上去;包括后来庾启辗转找到再生寺,使寄顿于此的琼枝躯体复生,此处真情又被作为复活画中人的最关键因素,正所谓“情之所在,岂异生死”,与汤显祖提出的“至情说”如出一辙。
再者,吴炳在《疗妒羹》中不仅引入戏中戏,还让剧中人直接谈论《牡丹亭》,借笔下人物抒发了对汤显祖所著传奇的钟爱。清人梁廷枬评价其中《题曲》一折尤其“逼真牡丹亭”,“此等曲情,置之《还魂记》中,几无复可辨。”(5)[清]梁廷枬:《曲话·卷三》,上海:有正书局,1916年,第6页。此外,《西园记》中的赵玉英生前有言“可怜红粉,岂委白丁?誓不俗生,情甘怨死。”其尔后抱恨身亡,不惜以牺牲青春性命的悲剧来反抗父母安排的婚姻,宛如再生杜丽娘。吴炳在传奇中多次模仿《牡丹亭》手笔,写赵玉英鬼魂深夜探访张继华,与其往来幽会,成就人鬼痴情,正是延用了原著里的幽媾情节。
然而,“情邮之说”的起始一句“偶在邮舍而名曰情邮”又带有逢场作戏之嫌,要论断吴炳对“情”的态度是否承继汤显祖至情一派,果真如其“情邮之说”所言,仍需回归到传奇文本中的叙述。
二、重才轻情的婚恋模式
(一)内在因素:才华学识
戏曲文学中的才子佳人们经由《西厢记》到《牡丹亭》的突破,已能大胆相爱并自由结合,逐渐打破了情爱禁忌与传统礼教的规范,吴炳在《粲花斋五种曲》中塑造的六对才子佳人亦如此,男女结识皆始于对对方学识才华的爱慕,通过才艺联络感情并缔结婚姻,信物也由珠石簪钗类物品变成了极具文人特色的诗词纸笺。
《绿牡丹》中,双旦均被塑造成女才子形象。沈婉娥“既擅女工,兼耽文藻”,车静芳更甚,不喜女工,独好“研朱弄墨,看书仿帖”,二人因羡慕对方才华结成姐妹,于闺房内能够互相唱和,不但自己有才,还极爱才,把才华作为品评婚恋对象至关重要的条件。剧中两位才子亦是如此,谢英、顾粲二位一向都是姓名见于诗刻文章中的知名之士,同时也非常在意别人对自身学识的品评。这边厢,谢英与车静芳各作一诗交换诗笺,传情达意,两人正是“才华并称,少不得风华凑成,这诗盟已早把姻盟订。”那边厢,顾粲也是因才爱人,对沈婉娥写的诗爱慕不已,反复玩味以至沉浸其中。
《西园记》里,男主角张继华被誉为“当今第一名士”,王玉真出生自学行书香之家,赵玉英亦“承传班姬之训,欲以谢庭之咏媲美其兄”,均为聪慧才女。起初,张继华因梅花坠落而撞见王玉真,误以为王小姐有意于己,于是赋诗一首相赠,俘获王玉真芳心,此间来到阁楼的赵玉英恰巧也听到张继华念诗,不觉悄声称赞,对张生其人其才生出倾慕之意,诗作成为了男女间传情达意的媒介。
《画中人》里,庾启出场自报家门:“八斗才华天赋成,洛阳年少早知名。寥寥自信文章好,落落谁知富贵荣。……小生誉满文林,刘子政之藜。”可知他出生仕宦之家,祖上世代簪缨,自恃才高,其后在呼叫画中美人时也极具文人思维,认为“绝世佳人,定爱才子,且把我做的文字请教。”其中,“定爱才子”暗含吴炳的价值取向,即唯“才”取人,而画中走出的郑琼枝小姐就是位才情颇高的大家闺秀,从画中下来后不时赏玩庾启的书籍诗词,欣羡其才华,还有感题诗。
再看《情邮记》,开篇刘乾初就表明自己空有抱负,乃是姻事寡谐的穷书生,他在驿站后院赋诗抒怀,因墙上题诗得到两位佳人的欣赏,最后在机缘巧合下结为美满姻缘。两位佳人分别是王慧娘和贾紫箫,王慧娘乃是“德性温淑,颇涉书史”的名姝,跟随其一同长大的婢女贾紫箫亦“颇有几分颜色,淹通词翰”,两人阴差阳错见到壁上诗句,对这位题诗才子产生好感,各自写诗唱和。
《疗妒羹》里的杨不器是个喜好诗酒生活的士子文人,乔小青亦为才貌两全的绝世佳人,自矜堪可媲美卓文君和谢道韫这两位大才女,后其因向杨不器夫人颜氏借阅书籍的缘故,不慎连带自题小诗一并还给颜氏,令在书房翻阅到此笺的杨不器心神荡漾。随后二人于西湖游览时吟诗作对,小青也为杨不器的风度才华所倾倒。
总的看来,《粲花斋五种曲》中男女之允同往来皆建立在双方学识才华的基础上,而关于这种爱情书写与文人意识的关系,龚鹏程先生在论及明中叶后戏曲雅化现象时曾有分析:“剧中男女交往,基本上是文人相与之模式。男主角大抵为才子……女主角亦往往是才女,需要亲试男子之才,吟诗作对一番,方能大生知己之感,托以终身。”(6)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下)》,台北:里仁书局,2010年,第323页。正因知己之感是文人们最注重的,粲花曲中的才子佳人们结成的也多半为看似理想的伙伴式婚姻,因文才相惜,少有展露更私密真实的情感。再者,吴炳写才子对理想女性的爱慕情感,一般不予女主角容貌以直接描摹(除了《画中人》剧情需要的缘故),而是写才子们为她们出众的才能而倾倒,注重其内在涵养修为,力图使男性求偶的心态合乎“礼法”,反之,吴炳写女子之所以对男性有“情”,皆是因才华出众而为之倾倒。
(二)外在因素
剧中婚恋模式重才轻情的取向还存在身份地位、制度掣肘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1.干扰因素:白丁恶人
干扰因素的设置属于制造戏剧冲突的方法之一,明中后期的传奇作家们就常利用“错认”和“破坏”这两种技巧写离奇曲折之事,力求故事引人注意,从而形成了晚明传奇中兴起的一种尚奇风气。吴炳亦多用心编排,善用“破坏”,以小人作梗使坏使剧情跌宕起伏。
吴炳著墨最多的小人物,即为破坏有情人团圆的投机取巧的小丑白丁,这类人物大多家中富贵,无甚学问,多为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形象,学文人风范附庸风雅,抬高身份,更反映了当时社会里普遍存在的暴发户心态。其中,最为典型者就是《绿牡丹》中的车本高和柳希潜,两人不但不学无术,还想充名士娶才女,设计中榜的骗局阻拦两对真才子佳人成亲。类似人物,还有《西园记》里的酒色之徒王伯宁,其名字的方言谐音即为白丁,王伯宁生前贪淫无度不好读书,因长时间沉迷酒色而暴病身亡,死后偶然遇见赵玉英的游魂,便以生前已下聘赵家为由仍对赵玉英纠缠不休,以不守妇道谴责之,并阻拦她去找心上人张继华,企图重新霸占。又诸如《画中人》的小人胡图,虽然是男主人公的好友,但却是个既愚蠢又险恶的典型白丁,还是被郑琼枝骂作“癞蛤蟆井底蛙”的好色之徒,求爱不成,更以卑鄙手段偷偷换取了真画轴,险些导致庾启和郑琼枝这对才子佳人就此阴阳两隔永不得相见。
以上这些卑劣小人的群像,不只是吴炳为制造戏剧冲突而设置,其中还融入了他对科场僵化徇私舞弊现象和腐朽吏治的观察,所有的净丑角色均演其角色的龌龊之能事,目的也是为了反映他们无才无学无养的一面,并借以在剧中进行揭露批判;其次,又出于场上戏剧扮演和营造喜剧氛围的需要,这些净丑人物基本也都担负着制造笑料、活跃气氛之任务,因此多可见到五种传奇里男女主角团聚之路上即使多穿插有小人陷害,但最终邪恶力量未能得逞的安排,甚至在剧作结尾中,这些人物经由教化和劝勉竟还摇身一变化身为男女主人公成婚的媒人或见证者。就这方面而言,吴炳娱己娱人的动机可见一斑,使得剧作整体趋向游戏之作,遂大幅冲淡了原本剧作主题的严谨性。再者,剧中才子佳人的结合还不乏充满侠义精神之人物的拔刀相助,他们锄强扶弱,协同一起对抗邪恶势力,缘此也让剧中的情理冲突荡然无存,转变为善恶势力间的交手。
2.保障条件:科考功名与家长意志
无异于大多数风情题材传奇剧,《粲花斋五种曲》亦都以大团圆作结。才子佳人能终成眷属,莫不是因为有一层现实伦理的保障,即应试中举获得功名地位,才是达成男女主角婚姻的最直接途径,其一出自文人身份的男主人公之自我期许和使命承担,希望求取功名来施展自身才华,企图达到亨通人生境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家长宗族为保证婚姻在礼法上更名正言顺而对男性身份所提出的要求。
比如《绿牡丹》中的沈重老爷,在谈到小女婚嫁问题时的态度是需“登科”才“纳采”,虽相较《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中因对方家道中落意欲毁亲的王闰香其父,还有《牡丹亭》里强行为女择取婚配对象的杜太守,沈重已算宽容,但这种宽容建立在作者所安排的“认定真才者”的价值判断上,具有偶然性。
男女婚姻仍不脱宗族父权的成全,《西园记》中的张继华与赵玉英小姐魂魄人鬼相恋,一边又无奈在赵老爷的安排下入赘赵园与王玉真成亲。《情邮记》中的刘乾初通过考试发迹获钦赐状元,任淮阳路参知,这才有了后面的剧情:救岳丈,娶王娘。《画中人》中更甚,虽然郑琼枝被庾启救回生还,并私许姻盟,其父仍然坚持榜后送亲,即使庾启是出身簪缨世家的名士,但依旧要中榜才能兑现娶亲之诺,待至后来高中状元,在皇帝御诏亲临下完成婚约,可见男女婚姻要符合情理,不仅需要经由明媒正娶的程序,必要时还需有掌有话语权者的保障。
由此可见,剧中男女的姻缘结合无一不是靠男主角通过考取功名或顺从家长意志的形式才获得保证,虽然吴炳强调以情取胜,但这些才子佳人的婚姻仍然严格地遵照传统规范完成,非常符合吴志达先生曾谈及的一点:“才子佳人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郎才女貌为爱情的基础,这比‘门当户对’、‘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自然是一大进步,但最后必以金榜题名为合法婚姻的条件,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没有突破‘门当户对’的规范,也符合父母的意志……”(7)吴志达:《明代文学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5页。因此,反观剧中这些男性主人公,《绿牡丹》的顾谢二生、《画中人》的庾启、《情邮记》的刘乾初、《西园记》的张继华和《疗妒羹》的杨不器,身为书生文人的他们具已具备才华学识,基本都是在赴科举高中后取得功名,获皇帝赏识从而跻身士大夫阶层,之后才会选择荣登娶妻,其实这种固定模式的形成,也与影响文人至深的儒家思想文化价值分离不开,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士人的生命理想中,国家、君父、朋友,才是最重要的,先做到自身功成名就与治国安邦,其次才会考虑小家的存在,只有在受排挤下、落寞时,小家与情爱相思才会成为他们生活的点缀和慰藉。
《粲花斋五种曲》中才子佳人的爱情总体说来仍旧不脱“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的程式格调,组合模式不外乎为才貌双全和琴瑟和鸣的叠加,再经由战胜邪恶势力的一环,最后达到情理和谐之状态。其中,吴炳写他们由才方生情,爱情皆缘于对对方才华和人格的仰慕,却刻意回避了人性中好色感官的一面,使正常情欲无欲化;同时,吴炳并不重视写人物内心情理相争的想法,而强调外在力量对男女结合造成的阻碍,最后的婚姻也多拜家长意志所赐,合乎正统礼教的规制从而实现道德化。
一言以概之,吴炳注重的是爱情到婚姻的完成结果,他将玉茗堂一派“真情至情”的思想延续发展至自身的“情邮”理念,实际塑造的却是注重辨真去伪、真才获得真爱的文雅喜剧,这种初衷与叙述的错位,以及他对回环曲折最终又回归团圆喜剧模式的钟爱,则不难看出他所秉承的儒家之醇厚中正的审美观,同时也反映出其内心思想的理想化,下文将结合吴炳其人生平经历作出分析。
三、士子文人的理想投射
重才轻情的婚恋模式使《粲花斋五种曲》呈现道德化倾向,也透露出吴炳精神层面的理想性,而此种理想化实质是吴炳对不理想境遇的一种回避。清代钱谦益在题李玉《眉山秀》传奇时就写道:“元玉管花肠篆,标帜词坛,而蕴奇不偶,每借韵人韵事,谱之宫商,聊以抒其垒块。”(8)康保成:《苏州剧派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180页。文人创作传奇故事,无非就是借此达到自娱、寄托与自显这几个目的,吴氏宗谱中就指明吴炳创作传奇是为了抒发愤懑之情:
先生词章妙天下,所著乐府五种盛行于世,特以发抒愤懑、不得志,而托于骚人逸士之文。(9)[明]吴炳:《绿牡丹》,罗斯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1页。
鉴于传奇体裁叙述的特殊性,作者通过代言体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发表自己的想法,结合其生平经历与时代背景,可推知吴炳于传奇创作背后的价值观念。
(一)写文自况,补现实之恨
按吴炳生平考据得知,粲花曲的五部传奇皆应创作于崇祯四年(1630)之前:
按《粲花五种》写作时间,除《情邮记》有“小引”确知为崇祯三年庚午(1630)外,余皆难以确考。五种今存全为明刻本,除《情邮记》为崇祯三年原刻本外,其余四本均为崇祯间两衡堂刻本。据此,可知吴炳在崇祯年后完全停止了传奇创作。(10)孙秋克:《吴炳年谱》,《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7期。
此前,吴炳曾就任湖北蒲圻知县,并多次入湘主持乡试,天启七年(1627)时吴炳升工部员外郎,启奏《亲贤远佞意疏》,提出澄清吏治的主张,这在崇祯三年付梓的《情邮记》中有所再现,与剧中刘乾初以“亲贤远佞论”谏言皇帝的举动非常相似。尔后崇祯二年(1628)吴炳转任福州知府,因其为人正义耿直,崇祯四年(1630)时力拒熊文灿贿庇科场弊案而得罪巡抚,看尽官场黑暗,于是被迫从福州知府任上称病乞假还乡,退隐于宜兴五桥庄,新筑“粲花别墅”继续其戏剧创作并蓄养家班,彼时吴炳35岁,此去六载后,直到崇祯九年时(1636),由大司马陆完学推荐补任浙盐运使,吴炳才重新在朝廷复出。概言之,步入仕途的吴炳始终坚持正直操守,向来善政恤民,却又因刚正不阿的性格不肯同流合污,还屡屡遭受党派之争风波的政治牵连,以至于触怒权贵利益者,剧中怀才不遇的书生实可视为吴炳之自况。
吴炳前半生仕运不济愤而退隐,很大程度也是由于明末不清明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在创作传奇时,吴炳其一方面正身陷个人才华抱负无法施展的窘况中,另一方面更遭受国运衰亡形势下严峻大环境的煎熬,两者一并激发了他以传奇来抒写内心悲愤。
除这两方面之外,《粲花斋五种曲》的写作也与吴炳在文场笔苑中不太顺利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吴炳诞于宜兴望族,但从其父辈已开始家道中落,因此吴炳在年幼时便为仕途上郁郁不得志的父亲所激励,立志发奋读书。然而,他在第一次乡试中因同场吴氏宗族有四人同时中举而备受怀疑,不幸被取消成绩,遭遇挫折,直到第二年京师复试考中进士,才得以证明自己的真才实学,此事在无名氏《石渠公传》中有记载:
乙卯,举于乡。吴为宜邑巨族,同举者四人,众疑且忌,为礼科所纠,因停会试。明年春,与会元沈同和等同覆试皇极门,先生下笔不休,事得白。(11)[明]吴炳:《绿牡丹》,罗斯宁校注,第170页。
可知吴炳因乡试蒙冤而参加复试,复试时遇沈同和科场舞弊案发,又遇波澜,所幸终于凭藉自身的真才实学才去伪存真,因此吴炳对“真”与“假”格外看重。故而反映在《粲花斋五种曲》中,多见吴炳穿插许多展现社会现实的内容并进行针砭时弊,此举更是为了衬托真善美之可贵,突出真才实学者的气度风骨,无论是寄人篱下的穷馆师谢英,还是遭受怠慢的刘乾初们,这些不卑不亢的士子们,在阅尽社会险恶后能一如既往做到洁身自好,这与吴炳自身颇为相像。
(二)以文代言,诉世俗心理
1.女性之才非为娱己
前辈学者曾谈到《粲花斋五种曲》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吴炳塑造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女性人物,这些女性形象区别于关汉卿、汤显祖塑造的女性形象的不同点即在于“把这种被动接受转化为一种更富有积极意义的主动选择”(12)于成鲲:《吴炳作品中的女才子形象》,《上海戏剧》1986年第5期。,她们似乎不像一般传统女性习惯逆来顺受,而是勇于追求个人幸福,表现出抗争自主的姿态,然而细看却经不起推敲。像敢于壁上题诗抒写内心因而有缘与才子刘乾初相知相爱,得以摆脱给人做小妾遭虐待的命运的贾紫箫,其主体性也仅仅体现在对自身社会身份的体认上;因自身才华得到杨氏夫妇青睐,由此改嫁的乔小青,她所找的幸福,也不过是委曲求全另找一个相对靠得住的庇护者而已;最有个性的当属勇于自择婚配对象的车静芳了,其亲设考试测人才学,就算是敢于为己自聘,最后也还是要在沈父的安排下得以嫁给如意郎君。
固然,吴炳大肆渲染这些女性并非一般闺阁少女,表现她们才情之高,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理念俨然相悖,看似持有开明的女性观念。然而,男性对女性教育的认同感大多建立在有限的基础上,其一,明代中后期闺塾发展之势热烈,十六七世纪时,“妇女教育被认为是齐家治国的关键”(13)[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女性接受教育的正当性包含有娱亲成分,像《绿牡丹》中沈重出场时自报家门,提到自己只有一女沈婉娥,说她既耽文藻,也可以“粗娱膝下,聊慰目前”,闲暇时亦可“唤来消遣则个”。同时,女性才德也可视作为家族增添声名的一种价值,“各色各样交易中的女性价值,是由才、德、美的结合所决定的,对上流之家的联盟建立策略而言,教育良好的新娘非常重要。”(14)[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第275页。江南地区许多上流富庶的宗族家庭注重教育,有意将女儿或女性晚辈放在闺塾中学习培养,抚育目的之一是为了不给家族门楣丢脸,女性才学在于相夫教子。
其二,相比普通庶民,吴炳所代表的士族文人阶层拥有更高的文化层次和精神需求。在士绅的互相标榜下,明代中后期发展出一种文人风雅之气,不仅体现在起居用度的精致讲究上,而且还相当注重声色之好,并且,这种情色娱乐逐渐化为士人文化的一部分。前辈王鸿泰先生曾单独挑出“情色”,他在《明清间文人的女色品赏与美人意象的塑造》一文中认为:
(士人)对女性的情欲内涵也随之开启出新的面向,在肉欲的层次上,别开生面地另外铺展出“美色”层次的相关活动与论述,由此建构新的女性想像,以至塑造出“美人”的意象。经过这个层次的文化建构后,这个美人的意象乃成为文人情感投注与交流的对象,以至于由此开展新的互动关系,成为文人美感生活经营的一个重要项目。(15)王瑷玲:《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情、理、欲(文学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年,第191页。
这种文人美感的生活具体又体现为对情色的包容及欣赏,男性对异性伴侣的要求不限于满足颜色之悦的层面,更加希望德才貌兼备的对象与之相配。正如在吴炳的传奇里,女性伴侣形象扁平化,无一例外被塑造为能够欣赏男性才华的既美而慧的学伴。
2.男性好恶规制女性
在《粲花斋五种曲》中,吴炳就女性身份设置了贤妻、妒妇、美妾这三类人物,褒贬态度分明。作品当中,论及女性,每每“贤”“妒”并举,妻妾之间能友善相处,多半是妻子贤惠大度的缘故;反之,妒妻因丈夫娶妾而醋意大发,把怨恨的情绪转嫁到第三者身上,即欺凌小妾,从而引发家庭矛盾。
其次,丈夫对妾的期许实则还带有对现有妻子的不满,不满之处,可能是妻子未能承担生育之责,也可能指向妻子性格的缺陷,抑或是对礼教规范下仅存夫妻名分的婚姻的不满:“既然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然正常的婚姻途径上排除了情感的可能性,人们便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另一点:娶妾、娶二房夫人、拥妓,只能在礼教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去寻找那一份残缺的爱情。于是无爱的夫妻名分和真挚情感的追求便奇妙地糅合在一起。”(16)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于众多男性看来,娶妾是对现有婚姻的调剂,正妻是明媒正娶而来的贤内助,品性端庄贤淑,关乎家族地位声誉,而小妾就是提供消遣和精神交流的红粉知己,两者相互补充即构成男性心中完美的性欲与爱欲的对象。
《情邮记》即为典型,虽然剧前小引“情邮说”标榜着世间莫不有情的思想主题,可实质上,这种真情却逐渐演变为作者笔下津津乐道的双艳,吴炳对剧中刘乾初高中皇榜并娶得王慧娘、贾紫箫二姝的逸事是颇为艳羡的。从《琵琶记》发端以来,明传奇的多数风情剧更是延续了一夫双美的大团圆题材,这种拥双艳的风流婚姻是功成名就外美满人生的表现,是当时文人骄示人前的冀望,可谓是大登科与小登科的集体圆满。这一点,从明代《六十种曲》中的大量题材即可看到文人作者对双美情节的热爱,这也反映了当时广大男性文人对双美同归的向往。
《疗妒羹》中男主角杨不器的妻子颜氏,被塑造成一个知书达礼、贤良淑德的女性,由于未曾生育一儿半女,因而一直苦苦相劝丈夫娶妾来延续香火,这样的行为被赞誉为“这般贤惠”,由此营造了夫妻和睦,一家和气让人羡慕的氛围。而剧中褚大郎妻子苗氏与颜氏形成鲜明对比,苗氏被定位成一位丑陋善妒的悍妇,见到小妾屡屡发作,最后差点被杨不器好友韩向宸所杀,趁机教化要学习贤妻,化妒为怜。这种结局安排,蕴含妒妇最后都没有好下场的惩戒之意,目的在于教育为人妻者应该顺从大度,又回复到惩处妒妇、表彰贤妻的正轨上来。《情邮记》里的枢密府夫人同样也是丑角,被塑造成一位凶狠泼辣的妒妇,不容许丈夫纳妾,一旦发现丈夫偷腥,则对丈夫小妾非打即骂。
作为正妻而言,一旦不能生育儿子,丈夫娶妾便顺理成章,自己就有极大可能因此失宠,既然无法再限制丈夫娶妾,所以最为理智的做法就是主动为其置妾,以显示自己贤惠大度,从而讨得丈夫的宠爱与信任,像《疗妒羹》中的妒妇苗氏与杨夫人讲到娶妾生子的事,说“这不过是门面事,讨了一个,省得外人说我不贤。”(第六出 贤选)杨夫人颜氏或许也是碍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迫不得已而为之,相较之下,杨不器自始至终都未出过一份力,全程都是其妻颜氏在主动操办,包括最初物色、计策营救及最后结亲,言语处处显露了对丈夫娶妾的认同,但她在丈夫面前亦会假装吃醋或假嗔,以此试探杨不器的真实态度,反过来又可显示自己的大度体恤,也正因如此,颜氏赢得了丈夫的信任和感恩,获得了其舅舅颜大行、朋友韩向宸等一众人的夸赞,保全了自己的正妻地位。颜氏因贤惠大方主动为丈夫纳妾,最终与乔小青也各生一子,这种巧合安排实质也是在借机宣扬贤妻行为。
《情邮记》中,贾紫箫和王慧娘同嫁给刘乾初后更加相怜相惜,贾紫箫本为刘乾初正妻,得知丈夫新纳的妾是王慧娘后,再三推让将夫人官诰让给王慧娘,连王仁夫妇也称赞“难得你这等贤达”。贾紫箫十分注重婚前主婢之身份地位,以及婚后妻妾纲常名分的严格规定,认同并谨遵尊卑次序,为此刘乾初也上奏皇帝,赞叹妻妾二人贤孝之风,吴炳在此也达到了以正风化的目的。
总体而言,《粲花斋五种曲》中的女性主要呈现为两类,一类是有着歇斯底里气质的“妒妇”“丑女”,另一类则是男性文人所欣赏的知书达礼的“贤妻”“才女”。在吴炳所代表的士人群体眼里,前一类女性必定相貌丑陋,脾性恶劣,被作者大肆丑化贬抑,下场往往不好,正如“‘无子’虽是利器,却未必能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同时,也无法完遂男子贪花恋色的癖好,即此,又不得不转移目标,将妒妇的‘罪’,穷形尽相地表现出来。”(17)林保淳:《三姑六婆 妒妇 佳人——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台北:暖暖书屋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92页。妒妇的夸张塑造多是男性作者有意为之的缘故,他们将男性贪恋美色喜新厌旧的品性归咎到女性的妒意上,更是借打压妒妇来捍卫父权尊严。后一类女子则兼具姿色和才情,与才子士人有共同话语,因而在选择伴侣上也相应产生了新标准,他们不只是希望女性才貌双全,还有了更高的冀望,即期望女性大度,这体现了士人群体对理想女性特质的新的建构。并且,吴炳始终未对女性内心情感做过多的描摹,而是代入男性的主体意愿塑造女性角色,男性本位思想决定了他对情的理解是片面化的,书写的仍然是士子文人普遍的世俗理想。
四、结 语
在明清文坛上,尤其是文人传奇创作方面,心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渐渐改善了原本的酸腐说教风气。虽说“以理抑情,以情抗理”的新兴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传奇创作题材内容、思想的走向,也出现了像汤显祖这样颂扬至情的戏剧大家,但大部分士人传奇作家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自身思想构架中根深蒂固的儒家理念的影响,按照郭英德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从文以载道观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传奇作家,表现出两种创作倾向:一是张扬言情,一是调和情理。”(18)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又由于士人阶级的局限,无法真正摆脱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因此在他们的传奇写作中,依旧融入了明确的善恶是非评判,吴炳就是典型。
《粲花斋五种曲》中,矛盾从情与理之间转移到情与邪恶势力两者上来,“发乎情,止乎礼义”,重新演变成情理和谐并存的产物。汤显祖《牡丹亭》中稍微闪现的“情”的文学观念,也再没有完成质的飞跃和转变。因为作家们并不追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乃至彻底决裂,而是追求二者和谐圆满的调解,吴炳的传奇作品也就是在这种追求情与理之间和谐并存状态的层次上挣扎徘徊。从根本上看,吴炳所处的时代不具有强大坚实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我国传统观念的稳定性,以及内部平衡的统治体系,决定了明末出现的些许启蒙之光早晚会被传统社会所湮没,吴炳的《粲花斋五种曲》仅仅是死水微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