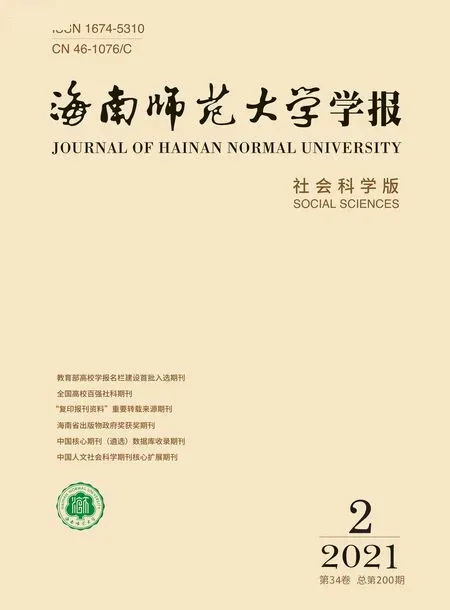绘色绘形绘民间
——论莫言审美观的视觉法则
周雅哲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莫言的小说有着充沛的生命情感体验、“藏污纳垢”的民间形态和个性鲜明的审美表达,这三者之间的交织融合给其作品带来了巨大的艺术张力,成为开放的文学空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笔下“声色民间”的审美表现。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活动,涉及到人的精神、情感、想象等高层次的品质,并需要借助独特的色彩、韵律和形象来表达。西方审美传统更注重对视觉的表达与展现,其中“自恋(Narcissism)”式的视觉隐喻(1)意指西方以视觉性形象为基础,以视觉性隐喻为框架的审美传统,可参考弗洛伊德、拉康、克里斯蒂娃关于自恋的诠释及其文学隐喻。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东方传统则是注重金声玉振的韵律,即“艾科(Echo)”式的听觉表达(2)意指以“韵”和“意境”为核心的具有流动性特征的声音形象为基础的中国审美表征,可参考古典文论中对于词曲诗乐的分析阐释。,但汉语的象形特征与意象化的表达方式也为视觉形象的存在做出了保证,即苏轼总结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3)原文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参见[宋]苏轼:《东坡画论》,王其和校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50页。。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使莫言同时受到东西方审美因素的影响,韵律化的语言和众声喧哗的复调是莫言关于向古典文化“大踏步撤退”的探索和追问,而他创作中浓烈的色彩渲染和表现各异的怪诞形象构成的奇特视觉景观,却是他感知世界和表达情感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了解读他审美观念的重要注脚。
一、剧烈的色彩体验
孙郁曾经指出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背景的缺失,造成了当代作家们作品呈现出较为单一、不明晰的色彩,但是莫言的横空出世为当代中国文化找到了表达乡土的底色(4)孙郁、莫言:《说不尽的鲁迅》,《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31页。。莫言的小说自《红高粱家族》开始,就表现出明丽丰富的色彩特征,其颜色浓烈程度可与塞尚、梵高相媲美。此前的研究者们也有相似意见,如张志忠论述了莫言的艺术感觉和感觉的爆炸(5)张志忠:《奇情异彩亦风流——莫言的感觉层小说分析》,《钟山》1986年第3期。,陈思和则分析了莫言早期小说《红蝗》《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文中的色彩奇观和对颜色进行渲染的艺术手法。(6)陈思和:《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作家》1987年第8期必须指出的是,莫言对色彩从不自觉到有意识的使用,除了受西方后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以外,也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承续和变异。对现代绘画技法的吸纳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学表现领域,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内核又隐在他的创作中,为其提供持久的生命力。
莫言对现代绘画的学习始于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当时他热衷于去图书馆观摩后印象主义画派的画作。塞尚、梵高和高更对于色彩的直观体验和表现技巧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塞尚擅长于让画面产生“变形”,率先将画面拉平,并用各个色块有节奏的跳跃变换来替代固定的透视画法,以寻求色彩与构图的和谐。梵高绘画的主要特征则在于其天才的想象力与表现力,正如在《文森特在阿尔的卧室》中表现的那样,卧室中除了颜色,没有其他的东西,画面中充满了高色彩饱和度的橙色、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这些高亮度的色彩让画面光线十足,以至于整幅画作中没有任何阴影存在。同时,梵高排斥现实主义的立体画技,他用独特的透视关系让画面停留在二维平面上,在个性的色彩和特别的形式中表现出深刻寓意和悲剧精神。而高更则是厌倦了现代化工业社会,转而寻找单纯直率的美,他反对传统绘画的优美典雅,从化外之地寻找艺术的生机,强调艺术的抽象美,重视直观感受、个体经验和对气氛的渲染。他们对感性经验的重视和极富个性的色彩运用给了莫言极大的震撼(7)孙郁、莫言:《说不尽的鲁迅》,《莫言对话新录》,第30页。,这些印象派画作的艺术精神潜移默化到莫言的文学创作中去。
莫言对感性直观的发掘为文本带来了丰富的寓意,不再对现实世界做简单的反映与模仿,使他摆脱了早期无题可写的困惑。色彩作为隐在的情感因子,渗透在小说的故事结构与情节展演中,并以高悬之姿笼罩着整个文本格局。小说中的背景由此模糊,话语也表现出绘图化和旋律化的特征,客观映现与主观体验都在色彩上交融了。事实上,尽管莫言架构的是一个多维色彩的“声色民间”,但是我们不会把无数色调中的每一种都用一个特殊的信息录制下来,而是“仅仅录制几种少数可以由之推衍出其色彩的最基本色彩或色彩域限。”(8)[德]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66页。对红、黑、黄三色的使用构成了莫言文学的底色,其中红色更是绚丽民间的缩影和主色。
如同莫言高昂的生命意志一样,其笔下的色彩也是高饱和度、高对比度的,最为明显的就是将红色与绿色对比呈现。红色和绿色在色彩学上互为补色,且都是饱和度极高的色彩,红色使人感觉迫近与膨胀,绿色则显得较为后退而收缩,在有限的文本格局里,它们的组合使画面产生鲜明的对抗。在《红高粱》中,被压倒的暗红色穗的高粱淌出的却是绿色的汁液,紧张又兴奋的游击战士们的脸变得半红半绿, “我奶奶”被流弹击中后“洁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绿了,又染红了”(9)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60页。。这些颜色描绘使文本产生了跳跃感,画面逐渐流动,从而推动情绪活动的进行,形成了文本的叙事节奏。红绿的同时映现和交替进行填充了文本的空隙,画面呈现出紧凑饱满的特征,鲜亮的色彩将与死亡有关的灰色和硝烟驱逐出去,战争的冷酷与坚硬被还原到嘈杂而鲜活的情感体验中。这种表现手法与梵高在创作《夜间的咖啡馆》时提及的“用红与绿来表现人类可怕的情调……表现出人们的火热的情绪活动”(10)[德]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0、465页。的方法类似。
色彩既然已经隐于文本的结构中,除了构成叙事节奏,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独立意义,成为了精神性的情感符号。莫言对色彩的这一处理也可以视作对庸常生活的反叛。《红高粱》是莫言色彩表现的典范之作,篇首写的是铺满地的红色高粱地,渲染出关于鲜血与爱情的氛围,而后高粱地中充斥的悲怆而热烈的鲜血则提醒读者这又是一场关于复仇和英雄的战争。作为情绪的渲染物和激发者的红色,以酣畅淋漓的泼墨式渲染和光影明灭的映现,使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文本的情感流动。而在《枯河》中,父亲满眼绿色的眼泪和像青虫似蠕动着的血管的描绘,则颠覆了大部分读者的习惯认知。当代社会对绿色的认知是平静、希望、生命力,但莫言的绿色显然指向的是粘腻的污秽和冰冷的死亡,是没有希望的晦暗颜色。此外,他还直接在《欢乐》中痛斥“绿色非常肮脏,绿色是浑浊的藏污纳垢的大本营。”(11)莫言:《欢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40页。莫言小说中的绿色与蠕虫、蛇、青蛙等生物以及潮湿、毒素、黏滑感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于灰绿与暗绿的不饱和色彩。有趣的是,这种对绿色的认知与18世纪前西方社会的观念很是接近,即认为绿色“象征着一切短暂的、变化多端的事物,还有一切骗人的、虚假的、谬误的幻象,是一种善变、欺骗、不可靠的色彩,一开始给人希望,结局却令人失望。”(12)[法]米歇尔·帕斯图罗:《色彩列传:绿色》,张文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44,146页。
不同于对绿色的厌弃,莫言对黄色和黑色展示了很高的热情。《白狗秋千架》里暖黄胡子黄眼珠的丈夫和她同样土黄色眼珠的孩子;《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丁师傅老婆的黄色葵花团放射着光芒的仿绸衬衫;《红高粱》描绘的高密的黑色原野;《透明的红萝卜》中金色太阳和黑孩的灰白眼珠;《檀香刑》里黑蛇似的棍子……这些颜色以最直率坦陈的状态呈现出来。黑色是初始之色,它“一方面与节制、权威和尊严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又使人想到黑暗、痛苦与罪孽。”(13)[法]米歇尔·帕斯图罗:《色彩列传:黑色》,张文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2页。“黄色用来指向人的精神状态时,所表现的也许还不是精神病的抑郁苦闷,而是其狂躁状态。”(14)[俄]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2页。这些不同的色彩在文本的各个维度中交织混杂,既相互否定、相互对抗,又相互烘托、相互包容。色彩的喧嚣激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当这种视觉映现扩张到一定程度时,颜色就会跳出文本,成为情感的话语和同构形态,文本也因此获得巨大的张力。由此,莫言作品中的色彩既是关于视觉的思维,也是文学的话语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符号,与其他要素一起架构成整个文本。
二、重构古典色彩的现代性寓言
对色彩的直观感受不是指对现实的反映和模仿,而是指由人及事的生命体验。塞尚曾形象地比喻:“对于一个人,一切物体通过色彩像一杯酒进入喉管”(15)[德]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译,第280、465页。,他指称色彩映照着自身,思考着自身,人化着自身。莫言多次表明,作家的创作应该是建立在生存经验之上的独立思考,而非对现实的简单模仿,作家应当保有独立的人格和写作风格,这或许可以视作对塞尚呼吁的回应。他将自身的观念投射到色彩上,通过象征授予色彩叙事话语的权力,使之成为一种近似于符号化的语言,“人们能够依据色彩及其具体语境识别它所叙之事。”(16)李彦峰:《中国美术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这里的色彩不仅是个体对于现实的反映,而且还是故事的潜在话语,是情节递进的情感推力,更是悬于小说文本之上的现代性寓言。
人的审美结构中已经具有抽象的经验和摹仿性的“心理视象”,小说中倾泻而出的色彩描绘很容易唤起这些隐而不发的集体潜意识——关于色彩的文化表象。这些色彩表象能“在非真实的情况下给形式以新的体现,使它脱除在真实实物中的正常体现,以便能够由其本身而为人认识,也能够依照艺术的最终目的——荷载意义或表现逻辑——而自由地表达,自由地组织。”(17)[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1页。在中国古典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莫言丰富的视觉想象不仅为小说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路径和创作手段,而且借助这些色彩表象的深层意义为之复魅,塑造出了新的现代性寓言:赤色神话与种的退化。
色彩有着丰富的文化寓意。就红色而言,格罗塞认为它表达的是一种生命的张扬与追求。在近现代西方文化传统中,红色通常代表着死亡、恐怖和激烈冲突,但在中国传统中,红色则代表了喜庆、吉祥,还拥有驱邪和治愈的力量。国画又被称作“丹青”,而“丹青”指的就是丹砂和青鎙,丹砂是红色的铁矿石和朱砂,青鎙是颜色深红发黑的矿石。因此,自旧石器时期,红黑二色就是中国绘画的主色,这在自然存留的岩壁画或是墓葬出土的帛画中都容易得到印证,如湖北包山大冢的《车马出行图》、西汉马王堆帛画等可考的艺术作品都围绕着这两种主色进行使用和变化,颜色在被人类使用之初,就表征着族群最早期的审美观念,如四色四时说、四色四方说、五色五德说。
“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18)柳宗元:《柳宗元〈非国语〉评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页。,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先民对体现了太阳、火和鲜血的红色怀有特殊的情感,红色因此被认为是生命的象征,更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巫术力量。而材料上的容易获得和颜色上的相似,使矿物颜料本身的属性也逐渐让渡到红色中去,朱砂这类矿物所具有的药性和持久性开始进入赤色神话中。其后,赤色神话被指称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关于新生与喜悦、驱邪与避害的色彩。赤色神话作为最早的神话观念,表达了初民们最虔诚的愿望,并成为古典美学的色彩基因和文化符号,根植于族群的集体潜意识之中。
纵观莫言的小说,篇名中有“红色”就有《红蝗》《红高粱》《红耳朵》《红树林》《红床》等,而《爆炸》中对“李铁梅”“红鞋,红裤,红袄,红腮,两眉之间点一个拇指大的红胭脂,长辫子上扎着红绳,手里提着红灯”(19)莫言:《欢乐》,第196页。的戏台亮相更是冲撞而出,接连七个“红”字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画面充满了跳跃的火焰,既是美又是狂怒与暴力,在刻画出人物火热跳跃的性格的同时,将时代的底色一并呈现出来。这些作品中呈现出的红色,如“红萝卜”“红高粱”“红马”“红树林”“红灯笼”等事物,首先就带有潜在的色彩记忆,又因为个体的质料之别而造成象征意义的区别。东北乡的红高粱,有着饱满、粗粝而干燥的质感,和扎根原野努力繁殖的特质,与情感浓烈而淳朴的东北乡人相呼应。莫言在进行小说叙事时,只需要抓住这一特征,将成熟饱满的红高粱、被践踏颓倒了的红高粱和穗粒灰绿的杂种高粱等场景记录下来,将这些瞬间以固定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就能将小说中的事件和时间凝结为一个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事物的质料和色彩被固定的一瞬间,过去的已然性、当下的必然性与未来的可能性都归结到这个视觉形象中,这一景观被赋予了丰富的内容,并在文本中的重要节点反复出现。景观化了的高粱红仿佛是笼罩在文本空间中的薄雾,成了当代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美学坐标。
“种的退化”是莫言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混杂”——生殖力的衰弱,具体到视觉图景中,种族的混杂又以色彩混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红色的特殊地位是对赤色神话的崇拜与赞美,那么将色彩与伦理关联起来的神话思维则是早期人类的审美观念的深化。早在商周时期就产生了五原色论,将常用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正色”作为一种使用至今的绝对性概念复活了先民的审美观念,它因为不掺杂其他任何色彩而获得了一种至高的纯粹性,这使“正色”超越了颜色的自然属性获得了神话内涵——最纯粹的色彩代表了最正统、最旺盛的生命力,由此成为艺术表达中最深奥的力量。莫言创作中的“红色”以正色的姿态驾临,高粱红表现了饱满的欲望、圆融的生命和不灭的激情。“色彩符号所表现内容的对抗性和悲壮性,以巨大苍凉、神秘、幽深的特殊环境,以形式构成的粗砺感等共同造成图像的崇高性特质。”(20)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但是,当红色开始混杂后,弱化的间色就出现了,间色的色彩度和巫术力量都远远及不上正色,于是衰弱的特征就此出现。《红高粱》中的杂种高粱好像不会成熟一样,永远半闭着它们那些灰绿色的眼睛,小说中最纯正的红高粱被引入的杂种逐渐替代,杂种的晦色对纯种的高粱红造成了混杂与侵害,间色高粱所拥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不禁要受到质疑。这片土地上高粱的生殖力因此被大打折扣,与小说中一代代“种”的逐渐衰弱与人的阉寺性遥相呼应,一个关于“种的退化”的现代寓言由此展现出来。
第一,隐私权保护。这一保护模式为美国法所推崇,是将个人信息置于隐私权中加以保护。美国《隐私法》(1974年)规定了对各类信息的收集、持有、使用和运输保护之条款。⑫“个人信息本质上是一种隐私,隐私就是我们对自己所有信息的控制。法律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隐私加以保护,界定其权利范围。”⑬大数据革命使信息收集、利用变得迅速并不易察觉,增加了控制难度,但并不意味着“隐私的死亡”。在美国,大数据保护论争通常在隐私权语境下展开,譬如责任规则的适用,究竟是适用侵权责任还是合同责任规制不当观察、捕捉、传播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都在隐私权语境下探讨。这与美国实用主义的法治传统不无关系。
三、异化:身体经验的投射
在莫言的创作观念中,人物始终是小说的灵魂和叙事的核心,他们贯穿了文本的形式层面与内容层面。莫言的描写对象中充斥着外貌或性征突出的成人、残缺或怪诞的儿童、夸张的动物,形成了当代文学人物形象中的独特景观,也形成了他审美表征的独特侧面与象征维度。莫言多次强调典型人物形象的重要性,他将笔下的人物置入宏大的文本格局和生命伦理语境中,通过人物的体验来展开小说的叙述,展开对人性的描绘与刻画。尽管莫言致力于创造出典型的或永恒的人,但“零度的写作”是不可能存在的,写作是作家“天然的内分泌”(21)《“语言是作家的内分泌”——著名作家莫言访谈录》,《北京日报》2001年10月2日。,与个体的经验紧密相关。身体经验是审美活动的前提,只有主体的经验经由加工转换后,才能引起审美对象情感的激荡。因此,作为最重要的主体和客体的身体,就成为了莫言文学创作的主要来源和文本表征的重要手段。在由形色塑造的“声色民间”(22)莫言:《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1期。中,浸透了莫言的审美意趣和生命经验。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始终是第一要义,对成长的希望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求深深扎根在人的潜意识中。就莫言个人而言,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对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占有与索求成为他最原初的欲望,对饥饿的真切体验贯穿了他的童年。《蛙》中描写的以万小跑为首的一群孩子啃食燃煤的情节,正是脱胎于童年莫言对饥饿的切身体会。如果说成人的经验是在社会规训和习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既成体验,那么孩童时期的身体感受则是由生物本能主导的个体生命感受,它们最为纤弱敏感,这时环境对身体的感受和认知的形成造成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因此,莫言也认为“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23)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51页。。童年记忆不仅仅为莫言提供了独特的儿童视角和儿童形象,还为其天才式的艺术加工提供了丰富的身体感知和情感经验。
“人的食欲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强烈的破坏力量”(24)莫言:《碎语文学》,第51页。,对旺盛生命力退化的巨大恐惧和充斥着食欲的童年经验投射,使莫言作品的题材中出现了食材化的倾向。人类的理性精神和关于良心、尊严的道德规范逐渐析出,与退化为容器的身体欲望产生了巨大矛盾。由于食物的匮乏,对莫言文学世界中的罗小通、铁孩、黑孩和万小跑们来说,浓缩为了“食欲”,这些儿童既是最机敏的精灵,也是最粗野的儿童;生铁、煤球等异质食材和牛蛋、婴儿等稀有食材在他的小说中占据了大量篇章,这两种食物奇观的出现正是莫言饥饿体验的直接投射。童年经验中食欲的驱动使莫言选择了倾泻式的叙述,强烈的破坏力量使他采取了狂欢的态度。铁孩大嚼铁块时的贪婪和丁钩儿吞咽红烧婴儿时的兴奋,给文本带来了一种关于吞噬和饱足的奇异快感。身体的欲望让渡到食物的狂欢中,而对食物变态的补偿性叙事又成为了情感的直观体现,映射着异化了的身体经验。
除了饥饿经验的直接投射,莫言的创作中还存在对身体经验的抽象异化。童年时期热烈的政治氛围和被排斥于主流外的社会处境,使莫言很早就领会到了孤独。无书可读的他只能去公社牧羊,与自然的频繁接触和天性中的思维发散使他的想象力极度膨胀,整日处于想入非非、半梦半醒的状态中。知觉素材的逐渐累积,进而经由思维加工被抽象成概念,主体思维与饥饿的肉体开始产生了分化,思维穿透身体直接对自然界进行畅想,主体得以超越匮乏的身体直接与对象进行交流。身体在与精神分化的同时,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审美关系中重要的媒介。莫言小说中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意义承担者,或者是简单的象征物,而是用以传达丰富内涵的基点。因此,莫言可以随时将传统意义上的“人”从身体中剥离,仅仅借助身体来进行言说、表现意义。作为媒介的“身体”成为了莫言创作的一种固定模式,他无需通过发掘或建构新形态的对象来进行书写与思考,这些“身体”和身体的延伸所创造出的复杂媒介就足够实现文本的纵深叙述,表现大部分的精神诉求。
小说中的身体并不是简单的躯体(body),而是有能动作用的灵活的身体(soma),能够置入环境并与之接触,并在其中经验它,成为感知的主体与感知的客体。从二元论出现开始,人们就倾向于将身体与灵魂分割开来,认为身体的作用是负面的,是人类之所以不能解脱的囚笼和诱人犯罪的根源,人必须脱离肉身才能领悟到灵魂的真谛。针对这一观念,梅洛-庞蒂就批驳道:“精神并不利用身体,而是透过身体,通过使身体超出于物理空间之外而实现自身。”(25)[法]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05页。因此,正如美国学者舒斯特曼论述的那样,身体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内在知觉的关注,它常常突破自身脆弱而模糊的边界,延展变化到周遭的环境中去,甚至可以说世界也是身体的延伸:“这一并非自我的世界,我与它也如同与我自己一样紧密联结,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过是我的延伸。”(26)转引自刘连杰:《梅洛-庞蒂身体主体间性美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5页。因此,通过考察莫言小说中的身体经验来辨别创作对象的诸多形象变化也是厘清他艺术法则的出发点和重要手段。
四、形变:身体的伦理构建
视觉审美化有两个重要的特质,一是秩序感,一是比例感。除了行为的异变,莫言还通过描写人物体貌的变形,打断了情节的渐次递进,调整了小说的叙述节奏与空间样态。它们将许多杂乱无章的元素重排,组合为适合心理节律和生理快感的形式构成,这些形变在产生强迫性注意的同时,还直接指向文本的伦理构建,引发了智性思考。无论是《食草家族》中生蹼的孩子、《幽默与趣味》中王三化为绿脸猴子这类夸张变形,还是《蛙》中肖上唇被剃阴阳头、姑姑由于“过于革命”而留下触目疤痕这类常态变化,都在文本视觉上获得了极大的张力,进而促成了情绪的变形。通过这些变形,我们能轻易找到过去社会留下的烙印,“这些欲望、失败和错误……在身体中结合在一起,在此突出表现出来。”(28)刘小枫、倪为国:《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88页。《蛙》中计生政策推行后,“我”再一次见到姑姑时,发现她额头缠着被血染红的绷带,她的面部肌肉已经变得僵硬,表情也似乎是坚毅甚至有点凶狠的样子,“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29)[美]理查德·舒斯特曼:《通过身体思考:人文学科的教育》,胡永华翻译,《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姑姑彻底地褪去了作为女性柔软的、光洁美丽一面,甚至在亲自指挥对王胆的追捕时,被刺中了大腿而险些死去。这些都是社会环境给姑姑印上的标记,通过对身体和身体习惯的强力改变让我们直接看到文本的冲突。社会环境对身体的改变越大,烙印越深,冲突就越激烈。
然而身体改造者们对于自身的变形是未经反思的,身体的变化又是精神转化的开始。姑姑在得知情人叛逃后激动地割脉并留下血书,宣告“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之后,她遭遇了王仁美母亲的刺伤,被张拳砸出了疤痕,乃至每天的进食只是为了保存肉体不被消亡,身体形象的存在被最大限度的压缩,真正成为一尊肉体,不被反思的迟钝肉体。虽然身体的变形没有在当下被反思,但其变化始终是隐蔽存在的,并使文本画面的建构产生了奇妙的认识改变,让读者观看时不能不瞥见,再也不能继续保持凝神静气的观看。身体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诸多含混性:“力量与虚弱、高尚与耻辱、尊贵与粗野、知识与蒙昧”(30)[美]理查德·舒斯特曼:《通过身体思考:人文学科的教育》,胡永华翻译,《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从而勾画出伦理事件的图谱,伦理也成了身体自我解构的场所。
柏拉图曾经判定“身体是灵魂的监狱”(31)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这一认识后来被福柯改写为“灵魂是肉体的监狱”(3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2页。。社会的在场像是来自外界的规训和强势的指令,是永无休止的压迫,在与消费文化的合围中,“阶级、性别、民族与劳动等维度的身体,已被尽可能的遮蔽与忽视。”(33)廖述务:《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19页。在《蛙》中,“大鼻子”陈鼻在李手经营的“堂吉诃德”小餐馆里靠扮演“死去的名人或虚构的怪人”(34)莫言:《蛙》,第245页。来维持生活,而其女儿陈眉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子宫找到存在的意义。“拥有多重意义的身体被孤立、具体化和碎片化,身体被当作一种外在的工具,一种可以被解剖、被拆割为一些相互分散区域的机械装置。”(35)[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1页。身体已然不完整,不能完全感知、体验生活和社会,无法发出行动,也被取消了思考的资格。由时间所带来的消极的压迫感是衰退的一大表现,而身体又绝不是仅仅限于躯体的老化,衰弱的身体所表征出来的意识透露的是社会的衰弱,也表征着文化的衰微与救赎的无力。这种画面的不断波动变换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情感体验,使人与社会的冲突达到顶峰,暴躁、疯狂的视觉形象跃然纸上,“我们”的负罪感也由此产生:“这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罪恶:即间接的、非个人的、借助于复杂的组织和机构的作用的作恶。”(36)[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87页。
五、结语
莫言藉由天才的想象,将经验外化为文学形态,并通过形色交融打破了单线历史叙事的局限,取消了文本事件的列次排布的单一结构。文学与形色民间的互相渗透成为他的艺术法则,日常经验通过艺术加工变形为文学元素,又依据不同的需要表征为新的内容,构建出新的形式。莫言通过在创作中的诗性编码,重构了生活经验的形式,从而赋予了文学和民间新的内涵。这也意味着,他的文学是一种可变化的文学,在这种文学模式中,事物可以轻易越过原本严谨的分类边界,跨域进入文学的领地。当代文艺中盛行“艺术的终结”这一说法,如果说艺术的死亡指向的是商品的兴盛,那么莫言的创作中关于文学与生活的互相转化的法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路径。他作品中丰富的包容性、宏伟的气魄和诡谲的艺术手法,为当代衰微的严肃文学创作提供了参考。因此,尽管莫言在文本的视觉展现上存在狂滥的词语堆积和过度的情感表达,但他在“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37)莫言:《檀香刑·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 , 2001年,第518页。的过程中建构出的形色民间和视觉法则,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的价值判断和“我也有罪”的深刻自省,将文学书写变成了人性的永恒悲歌和现代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