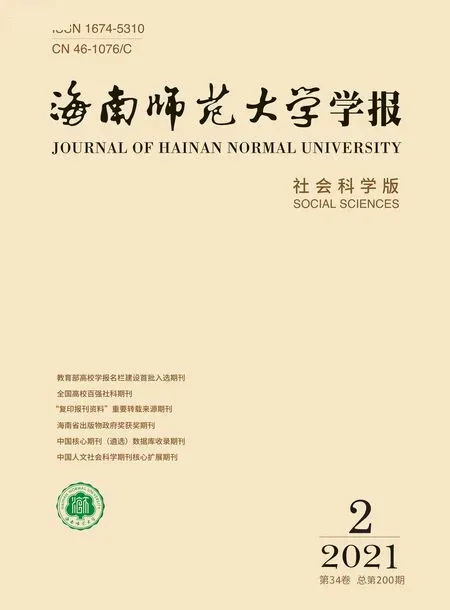“民间”何以“五四”?
——施章的“农民文学”观例说
冯 波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作为致力于社会革新与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旧”之别从来都是其现代意涵的重要表述内容。诚然,“除旧布新”抑或“革故鼎新”的线性历史进化装置唯有在“旧”的否定意义上才能获得“新”的合法性。然而“民间”虽带旧色,却非全然陈腐;虽呈俗态,但仍鲜活可爱的底层文化特质是否应该理所当然地被排除于“五四”叙事之外?换言之,作为极具本地、民族底色的“民间”是否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是以何种方式或途径参与的,又具有怎样的具体形态呢?注目于施章及其“农民文学”观,即是希冀以此为例对如上问题予以探究,这不仅是对“五四”的反思,更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应有之义的阐扬。
一、“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
提及施章(1)据李昌《施章生平事略》,以及《云南省志(卷75)社会科学志》《云南省志 卷80人物志》《官渡区志》所记可考:施章(1900—1942),初字佑文,又改仲言,昆明市官渡区六谷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尤爱民族民间文艺,曾在昆明县立师范学校和省立高级师范求学。1924年,施章考入中央大学文学系深造,1927年毕业,几年后考入中央研究院,毕业后留校,研究国学。著有《新文学论丛》《新兴文学论丛》,均由中央大学出版。另据蒙树宏《施章三题》对施章著述补充:“《读了〈坚决号〉后》,署名为施孝铭,发表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30年1月15日。”查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发行部1930年7月出版施章著《新文学论丛》内收《读了〈坚决号〉后》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所刊文章一致。由此可知,施章、施孝铭当为同一人。另据《施章生平事略》所述:“民国十五年春(1926年)施高等师范结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继续深造……中大毕业后,复考入中大研究院。得受黄侃(季刚),汪东(旭初),诸先生熏陶,为季刚先生收为门下弟子,获得中大文学院文学士学位及中大研究院优秀研究生的称号。论文写成《新兴文学论丛》和《新文学论丛》二书,均在中大艺林社出版。”查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发行部1930年7月出版施章著《新文学论丛》一书,内收《提倡农民文学的商榷》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中的施孝铭《农民文学的商榷》一致。由此可知,《农民文学的商榷》应是施孝铭(施章)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参见李昌:《施章生平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集萃》(第1卷),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蒙树宏:《施章三题》,《昆明市官渡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昆明:昆明市政协机关印刷厂印刷,1993年;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志 卷75 社会科学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志 卷80 人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李政章主编、官渡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官渡区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想必知者寥寥。作为“小学”大家黄侃弟子的施章,既未在古典文学界闻名,也很少为新文学界所知晓。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敢于挑战当时文坛大佬郁达夫,并不相信其为权威,实可谓“勇气可嘉”(2)施孝铭(施章):《农民文学的商榷》,《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15号。。然而,施章的意义却远不止一个无名青年的义气之举这般简单,时为古典文学研究生的施章以一篇研究现代文学的学位论文显身于现代文坛的意义正在于:他对所谓“农民文学”的“商榷”实则是对民间通俗文艺资源的现代价值的独特阐发。而循迹施章的一系列关涉农民文学抑或民间文艺的理论著述,我们尤其可以看到作为“民间”的文学是如何在“五四”的现代叙事中努力自证,进而纳入中国现代文学一脉的意图。
由“大众”而论“农民”就是一条颇有意味的论证路径。在《什么是农民文学》一文中,施章首先将“农民文学”定义为“已普遍于欧美的各国中”“以代表各国的大众底生活”(3)施章:《什么是农民文学》,《新兴文学论丛》,南京:南京印刷公司,1930年,第49-50页。,描写农民和工人生活的文学。“农民文学”的产生,“这并不是迫于接受外来的世界潮流而转变,实在是为自己的生活之需要不能不产生”(4)施章:《什么是农民文学》,《新兴文学论丛》,第50页。,是世界新兴文学潮流激荡自然而然的结果。其次,施章又强调作为“新兴文学之一源”的“农民文学”又是“由各社群中底自我的劳动文学之产生”(5)施章:《什么是农民文学》,《新兴文学论丛》,第50页。的。如此一来,施章就将“农民文学”与“新兴文学”建立起了紧密的逻辑关联,这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大众”,也就是说,“农民”是大众,农民的生活是大众生活的重要来源,“新兴文学”又代表大众生活的文学,因此“农民文学”就是“新兴文学”中描写农民生活的文学,这就赋予了“农民文学”以“新文学”的品格。而施章将农民置于集体性“大众”之中,不仅是让“农民”获得“大众”的审美观照与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让底层的“农民”文艺与“五四”高唱劳工大众的“新兴文学”具有了同样的现代意涵。然而施章并不甘心将“农民”俯就“大众”,反倒是要凸显“农民”的独特意义,这就使得他视农民为“大众”的观点又与彼时“新文学”倡导者所言的“大众”呈现出微妙的差异。
譬如,郁达夫在《〈大众文艺〉释名》中就说:“‘大众文艺’这一个名字,取自日本目下正在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的所谓‘大众小说’,是指那种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等而言。现在我们所借用的这个名字,范围可没有把它限得那么狭。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它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6)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1928年创刊号。显然,郁达夫强调的“大众文艺”是普遍的,而非某个阶级专有的、非庸俗的文艺。因此,他进一步将“大众”引申至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众”概念。于是,郁达夫接着说:“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需是关于大众的。西洋人所说的‘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的这句话,我们到现在也承认是真的。”(7)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1928年创刊号。反观施章在《农民文学的商榷》中开篇即指出,“近来问题方向的转变,已否定了个人主义的文学,而趋向大众生活或集团生活的表现。所以描写工厂生活,社群生活的文艺变成了主潮。然而我们中国的大众,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所以提倡表现大众生活的文学,农民文学自然居其中的主要位置。”(8)施章:《农民文学的商榷》,《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15号。可见,施章所言“大众文学”/“农民文学”是以个人主义的文学为对立面的,强调的是农民的社群属性。施、郁二人对“大众”的不同解读、审美重心偏差的背后实则折射了诉诸启蒙的功利性与致力于通俗的、民间的价值诉求的分野。
由于施章对于“农民文学”所表现的大众的通俗性并未完全遵循新文学者的启蒙逻辑,因此,他对于新文学者所强调的“农民文学”的阶级性、革命性就表现出既认同又有所保留的复杂态度。准确地说,施章对“农民文学”的阶级性、革命性的理解更多地指向了农民日常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譬如,他不满谢六逸“农民文学,就是指那些描写被近代资本主义所压榨的农民的文学”(9)谢六逸:《农民文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第2页。的观点。在施章看来,中国的“农民文学”“一部分是由于地主绅豪之掠夺,社会习俗压迫之反动(如私恋歌等),而另一部分则是农民自己的需要,而产生农民之人生观与伦理观的作品”(10)施章:《农民文学的商榷》,《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15号。。不难看出,施章并未将农民阶级置于压迫与被压迫阶级的框架内理解,而是立足在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此外,施章对所谓“地方文艺”的辨析也使他有别于为“革命的大众”呼号的新文学的主流之声。譬如,谢六逸认为,“田园诗只写田园的美,或称颂田园,乡土诗歌只写一地方的独特世态人情,它们的表现是以抒情为主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已经是过去的了,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农民诗。真意义的农民诗是田园的且是乡土的是把握着经济意识;自觉而且肯定阶级意义,由此以反抗争斗的精神力之具体的表现”(11)谢六逸:《农民文学ABC》,第13-14页。;任白戈也认为,“一种歌咏田园底风光或民间底疾苦的作品到(倒)是有的,但那也不过是士大夫之流底抒幽洩怨之作”(12)任白戈:《农民文学底再提起》,《质文》1935年第4期。。但在施章看来,“关于地方色彩的农村文艺,我以为中国则不管它是否与都会文艺对立。而在它能确切的表现出地方的特有的色彩,——如社会的特有风习或各社群的普遍心理。——才是我们理想的地方文艺。至于对于乡村的热爱与否也不必管他。只要具有农村生活意识形态而是坚执着现实生活的作品。无论他对于乡村热爱也好;或对于乡村增(憎)恶也好”(13)施章:《农民文学的商榷》,《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15号。。“确切的表现出地方的特有色彩”即“如社会的特有风习或各社群的普遍心理”就是他不断强调的“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
也正因此,施章一方面认同破浪斯基对作品社会意义的强调,另一方面又肯定卢那卡尔斯基强调民众在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他所谓的“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呈现出阶级性与社群性兼而有之的特点,具体而言就是弱化了阶级性,强化了社群性。进一步说,这种“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其实更接近一种底层农民的生活经验。譬如,施章对辛克莱的《石炭王》描写矿夫生活惨状的真切就极为叹服,他说:“总之要有农民生活的实感而从客观的立足点来描写农民生活,才能唤起农民中大众的同情。也如美国描写石炭坑的生活的辛克莱(U. Sinclair),要投身于矿夫生活中,才会了解矿夫的炭坑生活的惨状,而描写出惊动世界的作品石炭王来”(14)施章:《农民文学的商榷》,《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15号。。这不仅指出矿夫们被压迫阶级的社会地位,还是意在藉由《石炭王》的成功来强调说明:正是因为辛克莱有着丰富的矿夫生活经验,所以才能深切地写出那种生活惨状的真切。这与郁达夫认同辛克莱(U. Sinclair)视“都会文艺”为“有产有权阶级的毒瓦斯弹幕”(15)[美]辛克莱:《拜金艺术》,郁达夫译,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12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的观点,实不可以道里计。因此,施章虽不否认农民的阶级性,但他更重视的还是农民的社群性,甚至是“底层性”,然而“底层具有阶级性,但并非所有底层同属于一个阶级。因此,他所谓农民文学的阶级性讲的其实是社会底层性。”(16)冯波:《三十年代多元理论资源的选择与“农民文学”之辩》,《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不论是“通俗的大众”抑或“革命的大众”,在施章这里都转化成了“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施章的理论站位是底层的农民视角,审美内容是农民的生活,价值诉求是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情感诉求。它并不必然导向现代理性精神、阶级反抗,甚至革命斗争。施章在面对一个新兴概念时,既未全盘接受新文学者的理论主张,也并非标新立异、自成一家,而是依靠“农民”至“大众”这个关键词的转化,在“通俗”与“革命”间努力找到了一个既能被“五四”以来要求社会变革与个性解放的主流思潮所接受,但又不失自我民间价值立场的独特站位。
二、“永久的”“原质的”民间性
“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是施章的农民本位的价值在场,而民间通俗文艺则是这一理论外在的重要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从施章论及民间文艺的史料看,其论述不但指向地方戏曲、歌谣,而且还注目于西方的歌剧或话剧。我们看到,在广义的“俗文学”的中西视阈内,施章往往以西方价值理念来论证地方乡土性。他不仅将歌谣、戏曲的地方性、民族性作为“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重要表征,而且力图赋予超越地方性、民族性,甚而走向人类的终极价值的追问,以获得永恒的现代意义。
在1933年的《民众杂剧概论》中,施章将作为“农民文学”重要表现形式的民间杂剧视作“民众文学”,并援引俄国瓦勒夫松(Volphson)在《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文中的论述加以佐证。同时,他还指出,民众艺术是原始艺术的起源,而且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的,“民众文学是民众们自己本自己的观察,体验,和内心的要求而流露出来的产品。一方面他们表现出他们的现实生活和他们的理想生活。他方面他们凭籍着他们的作品而获得正常的享乐”(17)施章:《民众杂剧概论》,《云南民众教育》1933年第1卷第1期。。这样的观点仍是他立足于农民本位的价值取向的体现,我们并不陌生。不过施章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指出“民众文学”是相对于印刷文化而独立存在的口头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民间文学因包藏着“民族心”和“国民性”而应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向上发展所“应当尊重的;而且是应当培养的。”(18)施章:《民众杂剧概论》,《云南民众教育》1933年第1卷第1期。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施章梳理了民众文学的发展历史,并认为各时代的“新文学”都是受民间文学影响而兴起的创作。如此一来,施章就在本源的意义上肯定了民间文学与所谓新文学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这与所谓“民族性”“国民性”的吁求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他认同周作人提倡将民歌供新诗变迁研究的主张,对英国民歌研究者吉特生的理论也甚为叹服。经过如上论证,施章就以“传统”重新阐释了文学的“现代”,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文学”/民间文学也因之在现代民族国家精神的承继与建构的层面获得了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巩固“民间文学”在“五四”所开创的现代叙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施章还将这种“民间性”视为世界文学的重要呈现方式。他先是详细地分析中外文学大家及其经典作品与民众文学的密切关系。譬如,歌德、席勒受日耳曼民族的歌谣和传说的影响,《浮士德》与德国的神话、传说,魔术有密切关系;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英国谚语和格言;日本宝冢少女戏剧的“正之冒险”对中国神话“霓裳羽衣谣曲”的接受与改编(19)日本对“霓裳羽衣曲”的接受主要有三个根据:一、《本朝事迹考神社考》;二、《丹波风土记》;三、《海道记》,“此曲本由《婆罗门曲》,转为中国音乐,本来是宗教音乐;但是如中国后宗教性已经消失;而日本《羽衣谣曲》,反赋以宗教意味,都可互相印证。”宝冢戏剧又此基础上加入了“氢气球”、“枪”等现代元素。参见徐嘉瑞:《霓裳羽衣曲与扬子江》,《文学周报》1925年第200期。所体现的“太和魂”“武士道”精神等。接着通过这些跨文化的参差对照,将结论最后落脚在“民众文学”对“民众精神之表白”“民众生活的真象”,以及“民族心理的倾向”等具有文学普遍性与永久性的“主要原质(Element)”(20)施章:《民众杂剧概论》,《云南民众教育》1933年第1卷第1期。的强调上。那么,何谓“原质”?从施章对于西方经典戏剧的评论我们可窥一斑。譬如,他曾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创作颇为关注,对其评述也颇有见地。早在1930年的《长风》上,他就撰写了《易卜生的创造精神》,之后又在1932年第2期、第3期的《云鹤》上以《易卜生的创作精神》为题再次发表。论述焦点始终不离“五四”以降所谓“新文学家”们对易卜生的误读:一是将易卜生看作是“写实主义的社会文学家”;二是将易卜生的戏剧创作看作社会问题剧。譬如,施章认为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将易卜生看作“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的社会问题的病理诊断者”(21)施章:《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1930年第3期。是对易卜生大大的误读;指出潘家洵因以问题剧来看待易卜生,“要于人生中寻求问题,或捏造问题,因(此)产生的戏剧只是问题的化妆表演,而不是出自心之深处的文学作品了”(22)施章:《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1930年第3期。,这是“中国人以功利的问题剧的眼光”(23)施章:《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1930年第3期。来看待易卜生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施章通过易卜生好友勃兰兑斯认为易卜生发表的通信“大半是保护他的利益”的观点,来质疑胡适以易卜生1882年通信来肯定易卜生写实的“创作精神”的可靠性。接着,施章又根据易卜生与勃兰兑斯的交往,探究了创作“娜拉”的动机,即“娜拉”的原型其实是因为用假支票取钱买一套新家具,所以受到丈夫的斥责,而并不是出于为救她丈夫的性命这样高尚的目的,这刺激了易卜生的“幻想力”,遂有了《玩偶之家》。施章以易卜生“并不想到为妇女们要吐万丈火焰,他只是在作诗,并不知别的一切”(24)施章:《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1930年第3期。的自述反驳胡适,强调易卜生的创作并不仅是出于唤醒女性独立意识的目的(易卜生起先是反对的),易卜生的创作应当是“诗”而非写实的。因此,胡适视易卜生为“写实主义的社会文学家”实在是皮相之谈!而易卜生在文学上的伟大正在于:他早已在“人人不经意的现实生活”中感到“极端的痛苦”以及预感到“十年后的不安生活”。(25)施章:《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1930年第3期。进而言之,“易卜生所表现的是人生的或个人的悲剧,并不是什么问题不问题,更没有想到国家方面,社会方面”(26)施章:《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1930年第3期。,易卜生的精神实质是理想主义,易卜生是要使人“猛醒后自己发现道路”,他是如勃兰兑斯所说的“理想家”“奋斗者”(27)施章:《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1930年第3期。。
将“人人不经意的现实生活”中感到的“极端的痛苦”以及预感到“十年后的不安生活”视作易卜生的创造精神,其实正是永久的、普遍的“主要原质”的表现。换言之,施章关注的不仅仅是戏剧中现实的、具体的、带有历史局限性的情感特质,更注目于一种集体的、普遍的、触及到人类精神困境的东西,一种永恒的人性的叩问与追索。譬如,在读了穆木天翻译的法国维勒得拉克的《商船“坚决号”》后,施章将作品的主旨阐释为人类对于自由的哲理沉思。“衣都是彻底了解自由的老人了,而且是有自由的人。然而他被还叹惜他常常被酒壶嘴吸住。(是)人间什么是自由哩;巴斯其延式的人,是有了自由,结果或许未免作茧自缚吧;瑟卡儿是独自去坚决号上寻得自由,有了自由也未必是幸福罢。可见追求自由,也是绝渺茫的事。”(28)施孝铭:《读了“坚决号”以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7期。这种对于自由的辩证认知,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无奈,都可视为人类永恒的精神困境。因此,施章认为,“《坚决号》是一本剧诗似的散文剧本,他是以现代社会为背境(景),将社会上的各种不同的人物,缩成几种型来表现,其中本性的表现,可以当作几种个性型‘或范畴’的表现。他不惟是人生的表现,同时也是人生的批评。是很足以供人反省的作品”(29)施孝铭:《读了“坚决号”以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7期。类似的批评在施章专门评介莎士比亚名剧《凯撒》(JuliusCaesar)中也不难找到回音。(30)施章:《莎士比亚名剧“凯撒”之介绍》,《文艺月刊》1934年第7卷第1期。在如上的认识基础上,施章的“新文学”观也就具有了基于本土/传统文化,又具有域外/现代精神的特点。譬如在《科学对于印象派之贡献》中,施章指出,艺术的每一次巨大变革都与科学有密切的关系,抛开科学只谈艺术是十分危险的。(31)参见施章:《科学对于印象派之贡献》,《昆华读书杂志》1933年第1期。在《世运与文学》中,他说:“总之,人的一生总是在苦痛与欢喜里面交错着,总是在战斗与获得两条大路上走着,这种交错的过程”(32)施章:《世运与文学》,《新声月刊》1931年第3卷第1期。。这就是世运,是“生命波流的总和”,而文学是“生命总和用具象方法的表现。”(33)施章:《世运与文学》,《新声月刊》1931年第3卷第1期。反之,当施章重新审视本土的民间文学时,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发现,在他看来,《朱买臣休妻》(《烂柯山》)“又何尝不是中庸的和平的全无果决的国民性的表现;又何尝不是被征服的奴隶性的表现”(34)施章:《民众杂剧概论》,《云南民众教育》1933年第1卷第1期。。
由上而观,施章所谓的“永久的”“原质的”民间性,其实是他将民众文学/农民文学包蕴的“民族心”和“国民性”与来自西方的、对基督教道德和浮士德精神的反思结合起来的产物。一方面,施章强调民众文学/农民文学的民间性是具有普遍的、一般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他又执着于农民个体在现实生活的经济困境,乃至人类所面对的普遍精神痛苦。所以,正如他所概括的,“民众文学”的特质是一种创造的、共有的文学;是将国民性和民族性充分表现出来的文学;是蕴含着现代理性精神,表现出时代和“社会的风习或背影”来的文学。
三、作为“民间”的“五四”
农民本位的价值取向,取法西洋却立足本土的跨文化实践,这样一种既新且旧、土洋杂糅的理论形态使我们强烈地感到:施章仿佛处在“新”“旧”的夹层,既不突围,也非裹足不前,而是在历史的皱褶里,努力发出自己的现代之声。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民间”与“五四”的复杂关联,而对此的回顾或曰反思其实正是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乃至民族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换言之,“民间”何以“五四”的叩问,正是要彰显“民间”自觉的现代嬗递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意义。
我们知道,“五四”以降倡言民间文学并非新闻。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说:“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它)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35)仲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晨报副镌》1922年4月13日。,一度将民间文学提高到了“民族的文学形式”“民族艺术的基础”的高度。1933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又指出“纯文学”是从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层层累积而来的”(3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页。。顾颉刚也认为民间文学蕴含着深广的社会道德意义。如上所述的民间文学、民俗研究者对民间文学与“纯文学”关系的研究和对民间文学现实意义的关注,其实都是意图赋予民间文学以新文学特质的努力。以此而观,施章的“农民文学”观也正是要强调民间文学具有与“纯文学”不分轩轾的独特的现代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边缘的民间文学的现代之声大多还是被“新文学”启蒙与救亡的主流叙事所淹没。虽然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的文艺主张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民间文学以理论想象空间,但是被纳入革命宏大叙事的“民间”却难以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充分彰显其现代性。而基于“本地”的民间与以“欧美”为师的“五四”又并非服膺于同一的现代性概念,因此,作为现代的“民间”与“五四”在理性的启蒙精神层面上也难以真正建立紧密的逻辑关联,二者实则是隔膜的、游离的。加之当时国民政府对民间文学的疑惧、打压(37)“据艾伯华的观察:‘南京政府视民俗学为危险的学问,指责民俗学者散播迷信意识和信念。’”参见Laurence A, 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49. 转引自[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页。,民间文学自身在创作与理论上的现代转型也就更加困难了。
“民间文学”与“五四”的隔膜与游离,部分是因为民间想象与主流启蒙革命叙事之间的所谓“滞后”,部分也是因为作为民族记忆岩层的民间文学所显示出与时代的某种脱节,这使得它很难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但更深层次的冲突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带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西化的现代话语内处理传统的、民族的现代性自觉时的矛盾与两难。而施章的“农民文学”观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视角,因为他虽古典文学出身却多注目新文学,所以他能够更多地从文学的历史纵深去审视大多西化的、激进的新文学创作;因为他并非以新文学创作为志业,所以他较少急迫的现实功利性期待,而能溢出文学在更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审慎对待文学的“民间性”。这种居于新文学发生现场的旁观姿态使得民间文学被纳入“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成为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在那个谁不喊两句“马列”就自感落后的时代,施章身上的“土滋味”“头巾气”反倒有了几分难得的冷静与自信。
而如果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面向谈,民间之于“五四”的意义就不仅是对文学多元的现代生成方式的提点,更是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甚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因为从中国与域外(主要是西方)、民族与世界的角度说,民间所表现出的本地性、民族性其实也可看作是对西方价值理念冲击的回应。民间文学强烈的“乡土性”不仅是对于全球一体化的抵抗,更有着反思西方,彰显民族独特性以自立的强烈期待,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党派利益或者话语价值诉求的争夺更值得深思。因此,诸如施章立足于农民本身、重视通俗化形式的“农民文学”论者,“他们的‘商榷’抑或‘二三意见’就并非现代性冲击下被动的防御性拒绝,它并不构成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反向书写,反之,它也是要努力探寻地方文化与意识形态化的现代‘中国’之间的微妙互动,即接续传统民族记忆探寻其现代质素以争取对‘正宗’的文化中国的阐释权。”(38)冯波:《政治复调与民间狂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文学理论的历史症候》,《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这可从以下两点管窥一二。
一是在古今流变的视域内重审民间性,并由此将民间性升华至民族性。仍以施章为例,在《关于农民戏剧的话》中,他就认为,“过去的民间文学,如国风值得研究,孔雀东南飞值得赞扬,无名氏的元曲值得欣赏,那末(么)与这过去民间文学有同等价值的现代民众文学中农民们所创作的歌剧更值得注意,更应当研究。因为古代的民间文学,只足以表现过去的民众生活。而现代的民间乐府——农民歌剧——是直接代表现在的民众生活。我们要了解现代民众中的农民的人生,非由农民自己的社群中产生出来的文学中探寻不可。”(39)施章:《关于农民戏剧的话》,《新兴文学论丛》,南京:南京印刷公司,1930年,第100页。在1930年第3期《时事月报》的《湖南农歌与婚制(附图)》中,施章直言:“湖南现代的民歌,知道的人很少,他(它)将来在新文学上的影响如何,现在尚难估定。退一步说,纵然他(它)在新文学中没有古代的影响大,但他(它)在民众文学的立场上仍是有价值的。”(40)施章:《湖南农歌与婚制(附图)》,《时事月报》1930年第3卷第3期。不仅如此,他还将湖南民歌中的农歌提高到了整个中国民族的高度上加以肯定,“我觉得湖南民歌中的农歌,他(它)的价值也与广东的蛋(疍)歌,客音的山歌,梅县的山歌等,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它——湖南农歌——所表现的生活,不仅足以代表湖南,或许也是中国民族最近的缩影。”(41)施章:《湖南农歌与婚制(附图)》,《时事月报》1930年第3卷第3期。
二是批评智识阶层与民众的隔膜,对其启蒙予以质疑。譬如,在施章看来,作为大众文艺的农民文学必须是通俗的,因其通俗才能广播于农民,诸如郁达夫等智识阶级因缺乏农民生活体验,语言与形式不符合农民接受特点是不能创造农民文学的。施章引用卢那卡尔斯基将“民众”的生活视为艺术家使命的观点,不满鲁迅认为“山歌野曲”并非“平民文学”,他甚至从宪政时期提倡民众教育存在的问题入手,将民间杂剧(民众文学)看作是启迪民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施章强调“民众文学”对底层民众自己生活的真切表现是智识阶级的知识教化所不能及的,他批评智识阶级“他们只会拿他们的特有技能——文字——,跪在君主或权贵的膝前作种种阿依(谀)奉承的卑劣运动,以取悦权贵”(42)施章:《民众杂剧概论》,《云南民众教育》1933年第1卷第1期。。再如,在《国防文学的管见》中,施章认为尽管新文学不断“花样翻新”,但其内容仍旧老旧,只因这些作品没有流入大众中去,没有“指导大众的生活”,因此也就无法“向上与世界潮流同进”(43)施章:《国防文学的管见》,《火炬》1937年第1卷第5期。。在《农民文学的商榷》一文中,施章更是不无感慨,“可惜我国的智识阶级——文学家或思想家——他们没有农民生活之意识形态虽有同情于农民的意识,而发挥成他们提倡农民文学的伟论,因此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弱点”(44)施章:《农民文学的商榷》,《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15号。。这些不无偏颇的观点,正是其对话语权争夺的功利性使然。
四、结语
施章的“农民文学观”在内容上以农民生活为主,在形式上取法民间文艺,在语言上提倡方言土语,在传播上重视口头文学的直接与便捷。其本质是一种基于农民生活体验,以民间文艺形式为主,既容纳普遍的国民性、民族性,又注目于人类永恒精神困境的现代民间文艺理论。与同期及之后的民间文学提倡者不同,施章既非泥古不化,也不追慕新潮。他所坚执的文学立场保证了他依旧注目于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构成方式,他没有,也不愿意将民间文学导向一种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而是努力在其审美内容及其形式上探寻民族精神文化独特的质素。
而施章对新文学既接近又保持距离,既吸纳西方又立足本土的民间话语姿态,则给我们反思“五四”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视角。一方面,它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五四”以降,在东亚现代性裹挟下的社会革命与民族自强,其实大多还是一种西化的策略,本土的、抑或民族的文化精神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反思与整理。面对中西理论资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45)“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为王汎森在论述刘师培等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在面对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变革时所指出的自我挣扎的两难心态。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224-263页。的自我挣扎其实正是现代民族文化心理重构的艰难写照。另一方面,施章对看似“落后”的民间通俗文艺资源现代价值的充分肯定,所展现出的与同时“进步青年”不同的“进步”意义恰恰提醒我们,当我们回首将“进步”作为“五四”不容更质疑的标签时,所谓“进步”到底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阐释?而对此问题的追问不仅是对主流现代文学史的纠偏,更是对中国文学现代生成多元性、复杂性的彰显,它使我们尤其感到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