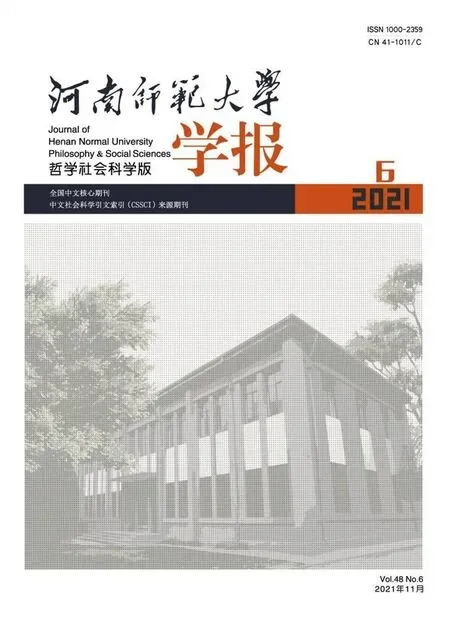女国民:近代中国的女权乌托邦
——以金天翮的《女界钟》为中心
刘 钊
(长春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研究基地,吉林 长春 130032)
晚清社会内外矛盾尖锐,外来思潮纷至沓来,作为拯救民族国家的一种设计方案,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小说进入发达时期。20世纪初,近代中国女权(1)妇女、女性、女权、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性别等概念,是女权思想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差异性表述。本文对于这些概念的使用依据具体语境。关于这些概念的辨析,参见刘钊:《启蒙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女性写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30页。思想发轫。粗略统计,1900-1919年间,以女权为主题出版发行的单行本小说作品便有百部左右(2)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民国小说目录(1912-19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散见于各种大小报刊的数量就更多。阿英专章分类论述过晚清“妇女解放问题”小说(3)阿英:《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104-115页。;司马涛也指出,“假如没有关心妇女情况的重要情结,那么,20世纪初中国小说的图景就不算完整”(4)司马涛:《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顾士渊。葛放,吴裕康,丁伟强,梁黎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07页。。妇女问题小说是政治小说中的组成部分,亦被冠以“女权乌托邦小说”(5)周乐诗:《清末小说中的女性想象(1902-19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5页。。除小说之外,宣传女权思想的弹词、传记、诗词、论说文、演说词等其他多种文体的作品更难有准确的数字统计。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发表,它以女权革命为中心,描画了理想的“女国民”形象,并将20世纪文明美好的未来寄托于女子世界。所以,晚清是乌托邦小说的时代,更是乌托邦思想与文学的时代。
一、《乌托邦》:关于男女平等的元叙事
“乌托邦”(Utopia)是托马斯·莫尔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本意为“乌有之处”。1516年,托马斯·莫尔完成了他的著作《乌托邦》,该书的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作者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假想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乌托邦新岛”。为避免枯燥的政治纲领式的书写,莫尔采用了“既有益又有趣”的游记方式和第三人称叙述。莫尔本是一位勋爵大法官,英国国王麾下的第一号要人,因在宗教改革问题上违抗亨利八世而被判处死刑。他生前没有料想到,《乌托邦》这本“金书”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源头启迪了后世对于人类社会的思考,“‘乌托邦’一词成为‘空想’的同义语,并被知识分子用作对未来良好社会幻想式描绘的称呼”(6)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李灵燕,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正是这部宣传自己见解的政治文本,成为后来英国乌托邦小说的原始经典范本。
《乌托邦》围绕乌托邦新岛上居住的“乌托邦人”而展开叙述,包括乌托邦人的城镇、行政长官、职业和生活方式、人与人的交往、旅游、奴隶和婚姻、军事训练和宗教等。在莫尔想象的完美国家中,人与人是平等的,包括男女平等,这是莫尔的乌托邦性别理想。乌托邦城尚处在农业文明中,由于农业知识高度普及,男人和女人都能从事农业生产。此外,也有羊毛或亚麻加工、泥瓦工、金工或木工这些特殊的职业,但是,各种职业本身是平等的,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会受到尊重。“绝大部分女人从事羊毛和亚麻加工(这类职业与她们的柔弱相称),而将粗重的活留给男人们去做”(7)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李灵燕,译,2016年,第41页。。这是基于身体差异而进行的劳动分工,但女人并没有受到轻视。乌托邦城中女人与男人还可以不受限制地交往,男女平等的关系由此确立。
莫尔主张所有乌托邦人具有劳动自觉的品行,劳动成为人们生存的需要。但是,他不主张妇女多干活,理由是“如果极少数妇女很勤劳,那么她们的丈夫一定很懒惰,加上一大批游手好闲的祭司和所谓的神职人员,再加上所有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拥有地产的、被称作贵族和绅士的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道构成中看不中用的懒汉群体”(8)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李灵燕,译,2016年,第43页。。这说明,他已经具有了朦胧的私有制观念和阶级意识,劳动量的差异造成社会分层,劳动妇女承受着来自丈夫和祭司等“上层”人的双重压迫。为了降低劳动量以减少妇女遭受的压迫,他细致地规划出乌托邦人简朴的生活,他们对于物质没有奢侈的要求,都满足于拥有一套服装,一套衣服常常要穿两年,且不加任何染色,以减少妇女的劳动。“行政长官从来不会让人们从事不必要的劳动,因为,他们的体制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公众的需要调节劳动,并允许所有的人拥有改善精神世界所必需的时间,他们认为,这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9)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李灵燕,译,2016年,第45页。。由减少劳动而获得开展文学艺术活动的时间,从而改善妇女的精神世界,这表明了莫尔的性别立场,他同情妇女为劳动所累的命运,也相信女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艺术才能。这幅所有人将获得幸福的美丽图景,寄托于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为理想社会种下了两性平等和谐的希望,具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萌芽。
乌托邦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平等本身正是乌托邦思想的实践过程,男权中心的权力不被颠覆,人类两性平等的美好夙愿便无以实现。当下学界的“女性乌托邦”概念,可以指代社会理想中的性别建构,“是女人追寻的梦境,也是整个人类可以期许的家园”(10)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6页。。然而,回到20世纪初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女权思想进入中国,承担起了拯救民族国家于危亡的历史使命。晚清乌托邦思想及文学异军突起,负载着政治诉求的“女权乌托邦”成为晚清乌托邦潮流的分支,为破坏旧政体、建设新未来提供思想动力,具有特殊的时代内涵,与“女性乌托邦”存在差异。
无论是“女性乌托邦”,还是“女性主义乌托邦”,在当下中国都还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晚清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激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诉求,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为涌进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思潮,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清末“新小说”中出现的不可抵挡的乌托邦氛围了。作为政治观念极强的小说文本“有益”却未必“又有趣”,诸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相比之下,金天翮的《女界钟》称不上“小说”,但其以“爱国与救世”的公德思想勾勒出的“女国民”形象,又不能不说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况且他本身就是文学史上于诗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均有创作的一位有名的革命作家。
《女界钟》发表时署名“爱自由者金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爱国女学校总发行,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再版,以“天赋人权”“不自由,无宁死”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基调而提出女权问题。著述广泛借鉴了弥勒和斯宾塞的自由主义女权论说,还汇聚和借鉴了国内思想界对于国家、民权、女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和论述,是以女子问题为主题探讨民族国家出路的思想读本。全书正文包括十个部分,除小引、绪论和结论外,包括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权利、参政、婚姻七个方面的分析评述,将启蒙思想家当时热衷的“国权与民权”“公德与私德”“破坏与救世”等思想融合、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质的女权思想,“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一条光明之路,自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树起一道丰碑”(11)熊月之:《金天翮与〈女界钟〉》,《史林》,2003年第3期。。
《女界钟》的核心是女权革命。作者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为未来的新中国勾画了美好的女性社会生活图景。尽管它没有采用《乌托邦》“未来完成时”的叙述模式,但它以“一般将来时”的叙述方式对未来整个20世纪加以描绘。它与《乌托邦》一样,以虚构性和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使政治文本呈现文学特性。《乌托邦》作为经典的乌托邦小说模式后来被打破,分化发展出反乌托邦、恶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多种称谓和流派。欧美“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与西方政治氛围有联系的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两次繁荣。阿英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的那些政治小说大多为乌托邦叙事。
此处命名的“女权乌托邦”既不是单指女性小说创作,也不是当下的“女性主义乌托邦”所着重强调的女性主义立场,而是指20世纪初期形成的女权思潮中包含乌托邦思想倾向的作品。在民族国家命运大动荡的时代,新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对于未来新国家新社会的建立充满期待,加之朦胧的社会主义观念传入,清末出现了乌托邦思想的高峰。简单地说,“乌托邦有三种,一是理想社会,二是理想社会的反义词——灾难性的社会,三是讽刺性的乌托邦”(12)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女界钟》批判“灾难性的社会”,同时又极力建构“理想社会”,正符合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所提出的“批判性的乌托邦”特质。
二、爱国与救世:女国民的政治蓝图
《女界钟》提出的女权是在国权前提下,与民权居于等同地位的女权。为了突出女权的特殊地位,金天翮指出:“请试言之: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13)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上海大同书局,1904年(光绪三十年),第13-14页。他以“国民之母”称呼女子,对其进行了社会身份的价值判定。1904年1月,《女界钟》发表不久,江苏同人丁初我创办《女子世界》月刊,金天翮为其撰写《发刊词》,转而以“女国民”称谓女子,乌托邦思想精彩毕现:
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文明之花也。婵媛其姿,芬芳其味,瑰玮其质,美妙其心。欧风吹之而不落,美雨袭之而不零,太平洋之潮流,漫淫灌溉而适以涵濡滋润助其发达也。玉井之莲,望之而心折;罗浮之梅,对之而色变;富士山之樱,见之而将羞死也。然而,花不自知其美乃闭其彩,幽其芬,摧折其蓓蕾。而吾乃焚香缥笔,问花之神,祝花之魂,愿花常好,以为二十世纪女国民。(14)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1904年第1期。
金天翮在这里用极有诗意和赋有象征性的语言赞美了本国女子,称其为“女国民”,突出了本国女子的现实性,又将美好理想直接展现出来。从现有史料看,“女国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留日女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共爱会的章程中:“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15)《日本留学女生共爱会章程》,《江苏》,1903年第2期。因此,这是来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称谓。但是,《女界钟》里先提出的“国民之母”一词在当时有很高的社会认同度,极易与日本的“贤母良妻”概念混淆。梁启超认为女子教育是“急保种之远谋”(16)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提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1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41页。的观点,得到保守派们的赞同。虽然日本女子教育中所提倡的“贤妻良母”强调了国家主义和国家立场,但日本的性别观念还是趋向于女子从事家庭内部的劳动。贤妻良母教育,是教育者“对于女子只因其要做男子底妻与母而施以教育,而不认女子本身有与男子对立的人格,只视之为男子底附属物”(18)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276页。。这正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女国民教育和贤妻良母教育两种思想的分歧。女国民教育“不是贤母良妻的教育,也不是纯粹女子的教育,而是偏重于国民义务的女子教育”(19)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278页。。
金天翮在《女界钟》里规划了女子教育的八个项目:“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20)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54-55页。这是女国民的人格育成目标,被金天翮称为“教育的方法”。前三项的核心词分别是从西方吸收的“天赋人权”“自由”和“男女平等”。由于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下,金天翮希望女子“思想发达”并无贬低女子的意思,“男性”为男子之特性,与“思想发达”相对应。如其所言,“我中国二万万同胞兄弟,沉睡于黑暗世界”,我二万万女同胞“绝不知文明国自由民,有所谓男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也”(21)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11-12页。。作者让女子成为与男子完全一致的人,从侧面反映了女子更需要接受教育的紧迫性。第四、五项表达了作者寄予女子先行觉醒并带动女界改变恶俗风气的愿望。第六、七、八项的核心词分别是“国民”“公德”和“革命”,这正是作者要着力提倡的女国民思想核心,也是“男女平等”的一种指向。
《乌托邦》是以虚构性叙事代政治言说的。无论是政治文本还是文学文本,人始终是文本关注的中心。《女界钟》关注的便是女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忽视女德教育,但是将女子拘限在深闺,隔绝了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女权乌托邦的社会性别理想是两性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公德是维护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两性有共同的公德标准是达成和谐的前提,解放妇女就必须使其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金天翮的《女界钟》发表时间与梁启超发表《论公德》《论私德》的时间大致相当。梁启超认为中国道德教育发达极早,但偏于九成为私德,公德阙如,不到一成。他将爱群、爱国、爱真理视为公德的表现,“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22)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20-23页。。金天翮则指出恶劣的“吾国民之魂”,使“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23)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他将女子的公德概括为“爱国与救世”,与改良派的保守主张截然不同,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破坏”的渴望。
金天翮的爱国思想在诗歌创作中得以抒发。《感事》《政变》《吊长兴伯荒祠》《辽东》等诗作表达了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恨,他不禁为祖国招魂:“十万头颅供一掷,血溅梅花殷红色。古雄若在祭坛结,魂兮归来我祖国。”(24)金天羽:《招国魂》,《天放楼诗文集》,周録祥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1页。他翻译了日本人宫崎滔天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和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1903年,他在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下有女子教育团体爱国女社(即爱国女学)。学校重视女子的精神教育,培养女子独立人格,也重视革命暴力精神的培养,“其时教授的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25)蔡元培:《爱国学社社章》,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他为革命刊物《江苏》《苏报》撰稿。《女界钟》正是缘于“苏报案”发,他被迫返回家乡之后的写作。如果说,女权是民权的性别体现,那么,通过对金天翮这一时期渴望暴力革命的互文性阅读,便可以获悉他在《女界钟》中的“破坏”的决心,“兼采他国之粹者”改造、锻铸国民新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26)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他彻底革命的决心与梁启超旧道德层面的“破坏”想法大相径庭。
金天翮对于国民性的认识既有深彻的剖析,又有民族的自信。他在谈及女子的道德缺陷时,并不是站在指责的立场,而是将女子的恶习归咎于负面文化之训诫。他认为女子受到缠足之害、装饰之害、迷信之害和拘束之害,如果去掉来自外界对女子造成的障碍和加害,中国女子之品性是“完全无缺”的。这种思想符合社会性别理论,即他不认为女子恶劣的品性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影响、塑造的结果,是被教育所建构起来的,所以他提出女子教育的方法。中国的男子受教于“奴隶”的教育,女子为男子的奴隶,为奴隶之奴隶,而且失去受“奴隶之教育”的权利。相比之下,欧美的女子教育科学深邃、思想发达、尊重人格,所以他鼓励女子游学欧美,从而跳出中国的旧风气,以改造为新风气。“学成而归,彼中之政党、国会、医业、辩护、新闻记者,我同胞其择之可也”(27)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32页。。他认为,经过现代欧美式的教育,可以发挥女子的天赋,使她们“恢复”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六项权利。“恢复”一词表明了他的态度:女子教育的失败导致女子品质上的缺陷,从而使女子失去了本来拥有的就业、参政等“权利”。
梁启超以“独善其身”为私德建设的途径,金天翮则认为教育是养成女子优良品质的根本,因此,他细致地为女学设置了课程。应该说,欧美波澜壮阔的女权运动给了中国的思想家们太多的想象,金天翮对于女子参政的认识便来自“欧洲女权第一革命之声”(28)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66页。。“茶花女、罗兰夫人、苏菲亚等西方女性,曾频繁出现在晚清小说中,不仅构建出‘英雌女杰’的群像谱系,还为讲女学、兴女权的‘女国民’话语推波助澜”(29)马勤勤:《通俗翻译与“女小说家”的中西杂交:从包天笑、周瘦鹃的同名译作谈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但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女子取得政治选举权的先例,金天翮便有远见地指出:“二十世纪女权之问题,议政之问题也。议政者,肩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之两大职任者也。”因此,《女界钟》彰显了公德的革命性,突出了破坏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建构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质的女权乌托邦思想。
三、文明与幸福:女国民的精神家园
将奴隶的奴隶带进文明的新世界,是晚清常见的表达语式。中国受欺凌的现实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爱自由、尊平权、男女共和,以制造新国民为起点,以组织新政府为终局”(30)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92页。是金天翮倡导女权的革命目的。“男女共和”既是男女一同建设民主共和制度的期盼,又是建立两性和谐幸福关系的祈求。金天翮一再强调夫妻平权,建立男女极为自由平等的关系。不改变“一为主,一为属”的野蛮风俗,夫妻之间必无真爱情(31)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33页。。文明、爱情、幸福这一系列词汇构成女权乌托邦对女子在家庭伦理生存的观照,和谐的两性关系是“幸福”之门,而两性的和谐幸福是建立在道德原则统一基础上的“新伦理”。
“女性者,文学之优美,哲理之深秘,技术之高尚,宗教之翕合,姿势之纤美,语言之柔和,疾病之阴郁,恋爱之附着,皆是也。”(32)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51页。这里“女性”之“性”仍指特性。中国女子的天赋品性优劣俱在,而且感化力强大,必须进行“私德”的改造。女子的道德与伦理关系表现在自身、与男子之间和家庭之中三个方面。男女之间是阴阳调和、情爱归宿、品性交换、学问商榷、道德补助的关系。他与莫尔一样,希望女子从奴耕婢织中、碎屑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键户而出耶,旅行、游学皆可也;当户而居耶,跳舞延宾、摊卷修业亦可也”(33)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20页。。女子获得在公开场合自由交往的权利,才可能发扬女子的才能和天赋。他认同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但从遗传的角度来说,两性仍然是平等的。因此,他反对日本女子在男子面前缺乏人格的卑微姿态。
中国思想界最早是在日本接触女权思想的,而日本在对女权思想的接受时,依照本国风俗对它进行了改造。例如,1884年5月 23 日《自由灯》上报道了日本有关“女权会”的信息,将要设立的女权会却是“以修好女道、确守贞操节义、扩张女权为目的”(34)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须藤瑞代,姚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页。,歪曲了女权本义。1886年5月至6月,福泽谕吉的《男女交际论》一文在日本《时事新报》显耀的社论板块中连载8次,后又以单行本出版,影响力极大。1900年3月,《清议报》第38期节选了《男女交际论》,在介绍作者时出现“女权”字样,但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放开男女交际,使女子在社会公共领域更好地为男子服务,此为“女权”概念首现于中文。金天翮并不认可日本男女的相处之道。他认为日本女子对男性躬身顺从的礼俗是对女子的不尊重。她们“见男子则跪,见客则跪,入户而嬉,共池而浴”(35)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32页。是恶俗,告诫我国女界赴日游学者,要留心于学问和工艺,不要被日本女界的恶习污染。他也批评了日本铃木力《活青年》所言男女阴阳的性别本质之说,反对依男女阴阳属性而确定“丈夫之责任”和“女子之本分”的做法。他承认女子的特性有别于男子,也承认妇女的“母职”作用,胎教和母仪是女子的擅长,女子性格近于小儿、善诱、心细、不鲁莽、容易相处、没有登科中的谬想和恶风等,这些都是履行母职的优势。同时他也指出,家政并非“米盐琐屑”,而是育儿、卫生、经济、法律、用人、行政管理等现代知识能力。他提倡突出女子特长,开设女子师范学校,仿效欧美开设现代科学教育课程,使女子做蒙学教员、幼稚园保姆,管理学校,并游学欧美,充分发挥女子自身的优势,实现女子的人格独立。这与日本放开女子社交的目的截然不同。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社会 “爱情翕合,坦然约契” 的两性关系,自然引发了中国男子的向往:
我同胞欲实行其社会主义,必以一夫一妻为之基础。红袖添香,乌丝写韵;朝倚公园之树,夕竞自由之车;商量祖国之前途,诞育佳儿其革命。婚姻之好果,孰有逾于此者哉!我瞻西方,吾眼将花,吾心醉矣。美人赠我青琅玕,何以报之?自由平权。(36)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40页。
这一段畅想社会主义、幻想一夫一妻制、描绘爱情婚姻美好图景的优美语言,在当时看来都是典型的乌托邦式想象,遭到了当下女性主义批评者们的嘲讽,她们认为作者站在男性本位的立场上,体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价值取向(37)王政,高彦颐,刘禾:《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事实上,《女界钟》问世之时,西方女权思想刚刚译介过来,我们并不能苛求一位传统知识分子在思想转型过程中能够形成自觉的、以女子为主体参照的性别意识,这与他接受的西方思想资源有关。《女界钟》里处处可见《乌托邦》思想的影子,在家庭权力分配上,莫尔陷入了“妻子服从丈夫,孩子服从父母,总是年轻的服从年长的”(38)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李灵燕,译,第45页。伦理陷阱。如果说,《女界钟》体现了以国族主义为出发点的男性主体立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它对文明、爱情、婚姻的向往被指责为男性受到性的压抑后而产生的对女性的想象,又不完全公允。作者明确地表达了尊重女性人格、赞赏女性能力、以自由平权换取两性爱情的甜美与婚姻和谐的思想,这是男女两性共享的精神体验,人类共同的向往,如果说存在以男性为主的立场,只能说这是时代所带来的局限。
除了莫尔的《乌托邦》,金天翮接受的女权思想明显来自马君武当时翻译的斯宾塞、弥勒等人的著述。在维新派启蒙声势浩大的舆论中,他能够在认同女性特质的前提下,以“爱国与救世”为目标推动女权革命,已经大大迈出了维新改良的窠臼,纲领式地建构了女权乌托邦思想。“使中国而为女子参政之国,理想国也。理想者,含有哲学与小说之两部分。中国小说,其腐败矣,然而理想有极高者。夫不见有锦心绣口,而对策于殿庭者乎?夫不见有绛唇玉貌,而出将以入相者乎?夫不见有双刀匹马,汗血疆场,以显祖国之荣誉者乎?夫不见有青裙素服,怀刃宫禁,以雪父夫之雠毒者乎?此正吾同胞所思之烂熟者也。彼亦犹是人,我亦犹是人。监督与组织,要求与破坏,总之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愿吾同胞亦死不瞑!”(39)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75页。这一段的表述正是金天翮为自己的女权乌托邦文本所做出的注脚。
《女界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当时民族国家矛盾在性别上的投射,也开启了女国民形塑的历程。以《世界十二女杰》(40)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赵必振,译,东京广文书店,1902年。为源头,清末《女学报》《女子世界》等妇女报刊形成了中外女杰传记写作热潮(41)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近代中国第一本女子教科书迅速问世,“列乎前者,我中国新女国民已去之导师也;列乎后者,我中国新女国民未来之摄影也”(42)杨千里:《导言》,《女子新读本》,文明书局,1905年,第3页。。多种版本的《女国民歌》一再被修订,不断转载:“新乾坤,须整顿。好男儿,未醒。女国民,要自警。”(43)汪毓真:《女国民歌》,《女子世界》,1904年第9期。应该说,女国民思想强调女子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特别强调女性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担当,这在民族国家再次陷入危机的时候得到了印证。1937年,抗战的烽火燃起,女作家关露再创《女国民》一诗:“我们的心已经震荡,/我们的血已经沸腾,/旧时代说我们是无用的妇女,/新时代认我们是民族的子民。//起来,/女同胞们。/我们要保卫伤的士兵,/挽救危亡的国土,/打退民族的敌人!”(44)关露:《女国民》,《抗战三日刊》,1937年第3号。这种为国牺牲的爱国情怀与1903年拒俄运动中留日女学生们的宣言何其相似。不得不说,20世纪初以女国民为核心的女权乌托邦与民族国家追求民主、独立、自由的思想实践,引领中国妇女走上了自我解放的道路,这也正是《女界钟》为代表的乌托邦思想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