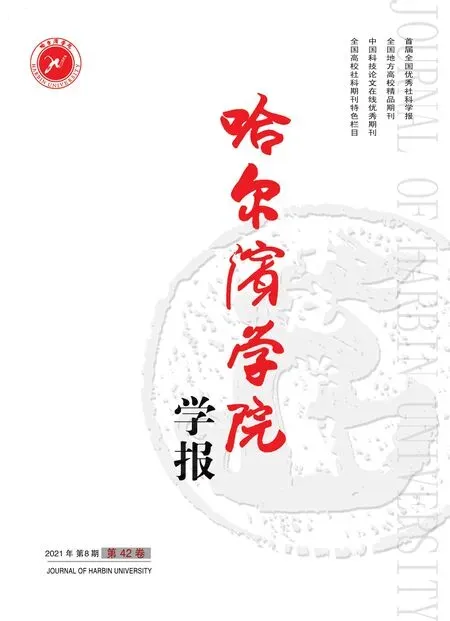德里达幽灵学的文化批判理论之探
白宇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500)
德里达身处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传统的工业社会主义相继离场的后现代主义时期。时值苏东剧变,历史终结论开始广泛传播,持这一理论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的终点和降临人间的福音”。[1](P9)德里达认为,因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不再属于某种实际制度,而成为了“幽灵”,这一“幽灵”将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德里达开启了复杂的解构主义的文化批判,此复杂性可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以下简称《马克思的幽灵》)中明显看出:在后现代语境“脱节的时代”中,文化批判的话语以两种不同质的形式解构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化身为“幽灵”,对马克思的遗产有选择地给予继承,延续马克思的遗产价值,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蕴涵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他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2](P21)在这里,德里达继承了马克思的遗产和精神,以解构主义的方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起了幽灵学的文化批判。
一、解构主义视域下幽灵学的出场
解构主义是与结构主义相伴的一种批判话语,斯特劳斯为了与存在主义相区别,在《忧郁的热带》中道出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是差异的聚合造就历史,拒斥从总体性出发的方法,转而去追求事物间的差异。这一方法论逐渐取代了人本主义与存在主义而风靡一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从这一立场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批评结构主义一味地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结构,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及其丰富的内在性,并通过《力与意谓》开始了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所推崇的结构架构往往蕴涵着内在的矛盾,他着意于找出这种蕴涵于结构中的矛盾力量,从而使结构主义理论从内部瓦解进而崩溃。
德里达的“幽灵”正是在解构主义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的出场形式,这个“幽灵”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幽灵”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理论形式。“幽灵”一词三次出现于《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之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3](P26)这个“幽灵”是内含着革命意味的文化批判范畴,马克思的“幽灵”即意谓反对一切旧势力、彻底推倒旧社会的大变革。德里达指出,他的解构主义更多地指向实践,而马克思的精神遗产也正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德里达正是在此处寻到了他的解构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得以相融之所在,并以此为基点将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这一融合产生的结晶即《马克思的幽灵》。
“幽灵学的中心话语自然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德里达就是通过幽灵出场、幽灵在场、幽灵退场和幽灵再出场的话语逻辑构筑其幽灵学的。”[4](P99)可见,德里达所谓的“幽灵”实无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宗教神学的意味,而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域出发,对文化批判理论的新的诠释。德里达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使马克思的“幽灵”以《马克思的幽灵》的形式重新出场。
二、幽灵学的文化批判的展开方式
德里达幽灵学的文化批判以解构主义为根本立场。换言之,德里达正是用解构主义的文化批判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诠释的。解构马克思就意味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剥离出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东西,德里达借用《哈姆雷特》中“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出场”代表着《共产党宣言》的诞生、“退场”代表着苏东剧变,“再出场”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延异。“幽灵”通过从出场到再出场的游荡方式,向世界昭示着真正的民主与正义永远在正在到来的路上。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他幽灵学的文化批判是通过如下三个方面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即异质、激进和延异。
首先,异质就是德里达反复强调的在结构框架或文本中寻找差异,寻求蕴涵在结构中的矛盾力量。简言之,异质就是制造差异。德里达正是采用了不断异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为他继承马克思遗产的合理性做辩护,进而展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其次,激进就是批判,就是对权威和传统的否定,通过批判以往的理论从而达到超越传统的目的。德里达指出:“在我看来,除了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它至少是这样。因此,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2](P129)德里达认为解构的基本精神就是激进化,这种激进化就意味着对以往的一切权威,包括形而上学、逻辑中心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最后,延异,这一概念是基于符号学提出的,是以符号来指称符号的无限运动。延异在解构马克思主义中即意味着以发散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创造,用马克思来批判马克思。换言之,德里达通过他自己对马克思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变革与再阐释,从而产生了解构主义的幽灵学马克思主义。[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在德里达这里,异质、激进和延异这三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在根本上都是他解构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反映。
三、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
德里达时逢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创,资产阶级学者福山趁机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德里达公开为马克思主义辩护,通过“幽灵学”来批判“终结论”,并同时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艺创作成为了为资产阶级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统治使广大民众逐渐迷失了自由自觉的主体意识,而成为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下的某个字母。
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在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商品拜物教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本)取得独立地位,成为了价值判断的依据,获得了“上帝”的属性。德里达认为,当进入市场的大众文化商品化后,“拜物教”就会应运而生。德里达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他对“脱节”的时代这一社会现实的认识:首先,资产阶级运用大众传媒等手段宣扬金钱至上、资本就是人生目标的文化观念,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及其行为,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其次,在商品化的大众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也随之商品化了。
德里达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直接来源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话语,以现代科技作为传播媒介,具有明显的同一性、标准化的特点,这种标准化的大众文化就像是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大工厂”式的文化生产输出其文化模式、意识形态,以求达到控制世界话语权的目的。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一充斥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自发地受这种文化模式的支配,人们实际上成为了被统治阶级操纵的“人偶”。德里达认识到,标准化的大众文化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盲目相信这一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体现了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不自由。
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将会阻碍“弥赛亚性”的未来社会的到来。一方面,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大众文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色彩;另一方面,标准化使人们盲从于这一文化模式,使人们丧失了主体性和超越性。如此,人们则会失去革命精神与批判意识,完全沉醉于资本主义世界。德里达认为,作为马克思遗产的继承者有义务和责任打破资本主义的桎梏,通过革命与批判使每个人得到自由且全面的发展。
四、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德里达早期偏向于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包括形而上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到了晚期,他将思考的重心由理论批判转向现实,转向了对正义和“弥赛亚性”的民主政治的思索。在德里达那里,正义凌驾于一切法律和政党之上,正义不能被解构,因为解构就是正义,正义永远在到来的路上。德里达所期望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根本符合人自身发展要求和社会进步需要的社会。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身份、姓名之别,甚至也没有国家、阶级、政党之分。那是一个永远不会脱节的社会,因为它一直处于自我批判、自我协调以及自我重组的过程中。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副标题中将这一未来社会称为“新国际”,“新国际”是他正义理念的寄托之所。
第一,德里达认为,“新国际”是一个真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实现人权、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们在继承马克思的遗产中取得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从内部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获取革命胜利的力量;其次,当我们分析和处理国际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并对其进行批判时,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批判精神的继承。
第二,德里达指出,在政党自身的结构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即通过革命与改革来占领国家,进而使国家灭亡、政治本身终结。[6]此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会再度出场。在“新国际”中,可以在根本上规避政党通过革命占领国家的形式使国家灭亡、政治终结,因为在“新国际”中是无政党、无国家同时也是无阶级的。这并不是说“新国际”放弃了对实践和组织形式的尝试,而是在超越阶级的情况下重新对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实践和组织。德里达要求人们冲破一切统治话语与统治意识,去采取一些有效的行动形式、实践和组织等。这表明德里达的“新国际”虽然从根本上对政党形式、国家或国际的某些组织形式加以否定,但这并不能表明他放弃了实践和对正义组织形式的探求。
最后,在德里达那里,“新国际”的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德里达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及提问方法,高度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和他未来政治制度的设想。同时,德里达强调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以使马克思主义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在构想未来社会的民主制度时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重组,以适应新的形势。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提出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这一根本概念,这无疑是德里达思想发展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二者的融合。这一理论转向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及合理性:首先,是由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功能决定的;其次,二者在政治的维度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相似性。可以说这一转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二者思想脉络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让德里达自发地向马克思主义靠近;另一方面,蕴涵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批判精神和解构功能也吸引着德里达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基于此,德里达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将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由此而创生了幽灵学的文化批判理论。这一理论的目的就在于使“共产主义的幽灵”降临,建立正义的“新国际”,拯救被资本主义笼罩的世界。但是,马克思的“幽灵”对德里达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对即将到来的绝对未来保持开放的经验的运动,[7]正义的“新国际”必将到来而且即将到来,它永远在到来的路上。通过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已经成为了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何种态度,无论人们是否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都已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着作用。
从总体上看,德里达是非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并以此批判、重组以往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种方法对我们而言也有着深刻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从此出发,马克思主义必将在21世纪的今天焕发新的活力。
——以《在法的前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