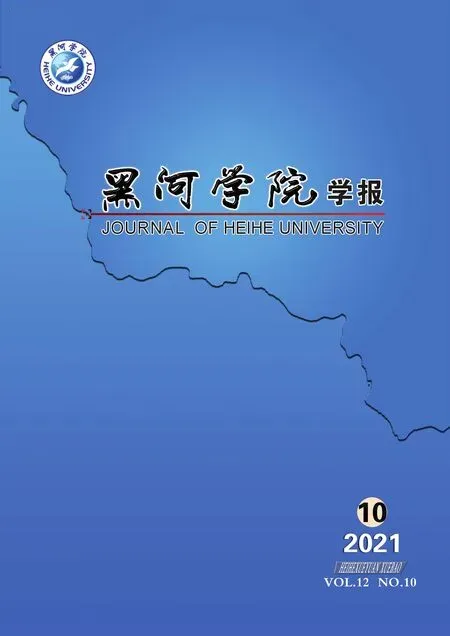《没有指针的钟》谢尔曼的身份认同危机
未 伟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河南 郑州 450000)
《没有指针的钟》是20世纪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于1961年出版。谢尔曼·登是白人生母已婚情况下与黑人生父私通生下的弃儿,天生的黑皮肤和蓝眼睛是谢尔曼矛盾性存在的标志。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认同”由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最早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创造了“身份认同”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术语。身份认同主要包括社会身份认同和个体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是个体的社会性维度, 是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是对个体属性的认同, 指的是“一种内在性认同,一种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而社会身份认同则是指人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
一、社会身份认同——边缘群体中的边缘人物
20世纪50年代,种族歧视的毒瘤依然存在于美国土地的各个角落。1862年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实际上仅仅让黑人从身体上得到解放,黑人没有与白人自由平等的权利,处于社会的底层。在米兰镇,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其间又泾渭分明。广场上有专门的白人喷泉,车站里有专门的白人候车室,小镇最大的教堂浸信会教堂是白人教堂,黑人要去专门的黑人教堂等。这些社会性的惯性区分将白人种族与黑人种族割裂,无时无刻不在向黑人种族传递着被歧视的信号,也将黑人种族推出社会主流,将其边缘化。老法官克兰恩家中的黑人女佣薇罗莉,勤勤恳恳为老法官工作了十五年,老法官对薇罗莉赞誉有加,但当薇罗莉向法官争取自己应得的酬劳时却被痛斥不懂感恩,最后离开。薇罗莉的侄子格柔恩·博伊在大街上被法官的孙子杰斯特追赶,而被赶到的警察一棍打死,只因为在白人的惯性认知中,黑人被白人追赶一定是黑人罪恶滔天,所以,黑人遭到粗暴对待是理所应当,即使黑人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过。身处社会中,黑人不可以争取权利,更没有争取权利的权利。黑人命如蝼蚁,可以随意践踏而不必受到惩罚,在社会中被边缘化。谢尔曼从一出生,黑皮肤便使他天然划归到黑人种族这一边缘群体中,自小便受到各种侮辱与不公平对待。
但即便在黑人群体中,谢尔曼也被边缘化,并没有获得归属感。谢尔曼在法官家中受到其他黑人佣人的排挤,因为一双蓝眼睛证明了其不是纯种黑人;11岁时被养父史蒂文斯先生性侵,长大后依然被名义上的哥哥芝宝恶意伤害自尊。谢尔曼在白人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在黑人群体中也被视为异类,受到异样眼光。“社会身份认同强调社会的各种决定作用……承认身份认同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2]。这使谢尔曼的社会身份认同产生危机,成为边缘群体中的边缘人物。谢尔曼最后申请搬到白人社区便是他向社会释放愤怒的抵抗,但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二、个体身份认同——“非我”与“自我”
1.以蓝眼睛看世界——白人“非我”的认同
谢尔曼出生便被遗弃在教堂的长凳上,他通过一双蓝眼睛观察世界,也是这双蓝眼睛使得他在潜意识中设定了一个白人的非我身份,希望以此可以获得尊重与重视。“自我与非我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用语。在《知识学基础》一书中提出,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自我’指认识主体和意志主体,是唯一的实在;‘非我’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由‘自我’设定的”[3]。谢尔曼白人的“非我”认同促使他从方方面面包装自己的外在身份。在生活方式上谢尔曼努力向白人靠拢,所以他只喝九十八度的陈年佳酿——卡尔费特威士忌,因为这是广告上“卓越人士”喝的酒。他穿海瑟薇衬衫,配上黑色眼罩,床单是百分百的人造丝。他充满自豪地向别人介绍自己居住的“豪华”公寓,但再大的冰箱也无法掩饰只有一颗不新鲜蔬菜的现实。他为自己包装左右逢源的人脉,抬高自己参加的“金色俱乐部”的入会资格。
不仅如此,谢尔曼因为自己的文书工作而暗自得意,因为这份工作干净轻松,还能颐指气使,他也不会被当作仆人对待,可以吃厨房里的任何东西。并且老法官是华盛顿州众议院的议员,能为这样有身份的人工作令他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有身份的人。谢尔曼企盼自己出身高贵,所以,城中每一个有声望的黑人妇女都曾是谢尔曼想象中的亲生母亲。在一次与杰斯特的争吵当中得知安德森夫人可能是生母后,谢尔曼连夜殷勤地给安德森夫人去信,并殷切等待回信。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大失所望。
谢尔曼受到其“白人”非我认同的内在驱动,竭力通过外在包装为自己建构一个白人身份,是其在长期被边缘化后,迫切在社会寻找存在感的证明。私生子的身世、幼年被养父性侵的经历、深受歧视漂泊无依的生活,以及缺乏存在感,这些复杂因素产生的合力是谢尔曼出现非我认同的原因。但即使在“非我”主导下,谢尔曼也会时不时流露出对白人的轻视与不懈。靠近但不得,向往又鄙视,内心的极端矛盾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谢尔曼的非我认同是深处深渊的谢尔曼为了自救而产生,只有这样谢尔曼内心的痛苦才能被转移,否则内心的痛苦与绝望会将他吞噬殆尽,使他无力生存。
2.以黑皮肤被凝视——黑人“自我”的显现
谢尔曼在白人的“非我”认同主导下,费尽心机与黑人种族决裂,但社会凝视谢尔曼的标准仍然是黑皮肤。在得知自己身世后,谢尔曼的“黑人”自我愈发显现。从外在现实看,谢尔曼的名字谢尔曼·登是按照黑人的起名方式来起的,很多生活习惯都与黑人一样。从谢尔曼的心理反应看,他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场合会不自觉地为黑人种族辩护,会因为老法官重拾奴隶制的言论而暗自生气,尽管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愤怒。这些都间接表明谢尔曼在内心深处将自己与黑人群体置于一隅,这是其“黑人”自我的隐约显现。
谢尔曼的身世一直是一个谜团,他一直认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白人,奸污了自己的黑人母亲,迫于现实母亲不得已将其抛弃。但谢尔曼无意中在法官办公室发现了当年有关自己身世案件的报纸,从而得知父亲是黑人,母亲是有夫之妇。这与谢尔曼长期以来想象中自己的身世南辕北辙。身世的真相给谢尔曼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于是他开始在生活中尝试做各种越矩的事,甚至将杰斯特心爱的狗勒死。最后,谢尔曼选择搬进白人社区,即使报纸上已经报道过有黑人家庭因搬进白人社区被炸弹炸死的事件。种种行为都是其“黑人”自我主导下的结果,在身世的刺激下,催化了谢尔曼的“黑人”自我,使其更加明显地显露。
谢尔曼声称自己不需要朋友,其实除去母亲,他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朋友。但当杰斯特向他释放善意时,他又总是恶语相加。拥有一双蓝眼睛没能帮助谢尔曼得到白人群体的认同,拥有黑皮肤却又无法融入黑人种族中去。谢尔曼的两种自我认知使得他内心极度的痛苦和矛盾,无时无刻不处在挣扎和矛盾当中。谢尔曼遭遇了个体身份认同危机,他不知道自己属于白人群体还是黑人群体。当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出现时,便造成了其心理的矛盾与异化。
三、于被动中主动选择毁灭——身份认同危机的苦果
从外部现实来看,谢尔曼在社会中的身份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人物,遭受歧视和排斥;从内在心理来看,谢尔曼的“黑人”自我设定了“白人”的非我身份,这些因素导致谢尔曼产生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最终导致谢尔曼的毁灭。
谢尔曼得知身世后,愈发占据主导的“黑人”自我促使他选择向充满歧视的社会发起挑战,他渴望得到社会的重视,而不是从始至终的忽视与不在意。谢尔曼的心里想着自己要“有所为,有所为,有所为”[4],于是他到法院广场的白人喷泉里舀水喝,去车站的白人候车室,坐在浸信会大教堂后排座位上,甚至将胰岛素换为水为法官注射,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谢尔曼极力获取别人的关注,甚至不惜用自己幼年被性侵的事情作为谈资,但这只是揭开自己的伤疤给别人看,可怜至极。
谢尔曼申请搬进白人社区,尽管杰斯特冒着风险劝告谢尔曼离开,但内心绝望的谢尔曼选择留下,最终被素未谋面、固执愚蠢的白人邻居投掷炸弹死亡。谢尔曼与自己曾经嘲笑的博伊一样,被愚蠢刻板的白人随意杀死,如同蝼蚁一般。谢尔曼身处种族歧视的社会中,无奈又被动,谢尔曼无力改变社会,对社会绝望至极,明知会有危险却选择留在家中便是其内心幻灭、主动选择毁灭的有力佐证。谢尔曼极力争取被看见、被重视的权利,在他搬进白人社区之后终于如愿,却也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投掷的炸弹造成了谢尔曼肉体的死亡,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使得谢尔曼在博弈中精神幻灭,生存无望。
麦卡勒斯塑造了谢尔曼这一矛盾体,将社会中白人和黑人种族之间的对立矛盾透过黑皮肤和蓝眼睛聚焦在谢尔曼身上,并通过谢尔曼内心矛盾与冲突的博弈表明了作者对种族歧视的反对与思考。按照拉康心理学理论,“主体的身份认同需要经历两个过程:一是在他者的凝视中,主体完成社会认同的过程;二是在镜像阶段‘理想自我’的凝视中,主体完成自我认同的过程”[5]。谢尔曼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最终都没有完成,最终造成了他的毁灭。“人终将一死,但死法千差万别”。书中开头的一句话仿佛预示了书中人物的结局。谢尔曼主动选择踏入一场由众人齐力点燃的大火,这是内心幻灭绝望之举。“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自我和社会构成了身份认同对应的两极。”[2]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认同都陷入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在自我与非我认同的博弈中,谢尔曼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与折磨,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谢尔曼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昭示压制与抵制之间的张力, 凸显后殖民、女权、少数话语等文化批评流派的批判意识和强烈入世关怀”[6],告诫世人明确而坚定的身份认同于个体的重要性。
——M4X谢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