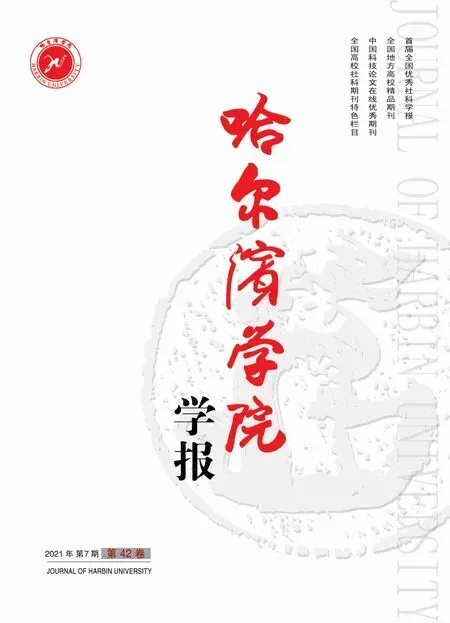先秦与秦汉时期儒法合流的趋势及其对当代法治的启示
李 淼
(铁道警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3)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大变革阶段,群雄逐鹿,时局动荡,社会变迁。各诸侯国都在寻求适合本国的治国方略,以期达到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求生存的目的,这种政治需求催生了各种思想学派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古代各种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各学派的思想家纷纷献计献策,社会进入“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著书立说,思想碰撞,辩论激烈。其中关于法律思想的论争,以儒法两家最具代表性。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的可能性
儒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点是服务于统治者建立的贵族政权,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要求老百姓安分守己。在继承西周“礼治”和“明德慎刑”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礼治”“德治”“人治”的法律观点。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法律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地位次于礼乐教化,因为法律只是客观地约束人们的言行,并未触及人们的内心,以致不知犯罪的可耻;而道德与礼教不但可以规制人们的言行,而且可以教化内心,使人们自觉地守法。孔子认为,法的核心要旨应当是“人之常情”,亦即孔子所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法律必须顺乎人情,才能使民风淳朴,社会长治久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法律思想,认为情是检验一切的标准,为了合情,可以变礼,法更是在可变之例。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孔子认为人的作用是首要的,提出“为政在人”,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所指的“人”只能是“有道”之君,其极力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当权者是否贤明,而不在于法律的善恶有无。
荀子将孔子的“为政在人”思想系统化,提出著名的“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进一步说明国家的兴衰存亡,在人不在法,认为“君子者,治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但是又认为“隆礼重法”的前提是道德教化。在儒家的法律思想体系中,礼与法虽不可分割,但却有明显主次之分。礼是法律的目的和灵魂,处于明显主导地位,不可随意改变,为了维护礼,甚至可以屈法为代价。[1](P58-59)
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学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主张“以法治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法家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各诸侯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对各国的变法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力。从时间上看,法家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商鞅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不可改变,只有刑赏才能统一人们的言行,并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治国理论,认为“仁者能仁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相爱。是以知仁义只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此乃由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因此,仁义道德不能治理天下,只有“法治”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另外,申不害的尚法重“术”以及慎到的尚法重“势”思想为“以法治国”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路径。到了战国后期,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对“法治”理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在“以法为本”的前提下,要将法、术、势三者结合,才能达到治国的效果。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一言以蔽之,儒家主张以伦理道德的教化方式实现“王道”,而法家主张依靠法律制度的刑罚方式实现“霸道”。需要明确的是,儒法之争只是形式上的分歧,根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随后的儒法合流具备了可能性。
二、法家思想的独尊时代
从秦国到秦王朝,法家功不可没;从统一到覆灭,法家思想中的极端因素亦难辞其咎。战国中后期,井田制全面瓦解,奴隶制度逐渐失去经济基础,私田制逐步建立,代表新生力量的地主阶级逐步壮大。有了强大后盾的法家开始与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儒家展开论战,故此,这一时期的儒法之争异常激烈。最终商鞅携《法经》入秦,秦国厉行法治,一跃成为七国之首,灭六国,一统天下,法家思想也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治国理论。
在这一阶段,法家思想之所以在与儒家思想的对决中取胜,完全是因为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满足了历史的需求。战国中后期,奴隶主阶级逐渐被历史所淘汰,作为新生力量的地主阶级,势必要夺取政权,建立统一的封建集权专制国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建立在人性“好利恶害”的基础上,“刑无等级”,赏罚分明,在“定分止争”“兴功禁暴”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这是“德治”与“人治”所不能媲美的。因此,这一时期实行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历史的必然。其间,商鞅携《法经》入秦,先后主持两次变法,改革措施卓有成效,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依《法经》为蓝本制定的《秦律》,对于秦的统一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致使秦汉以后的传统法典皆以“律”为名。虽然商鞅惨遭车裂,但“秦法未败”,其法家思想对秦有着深刻影响,“缘法而治”、重刑主义贯穿秦律的始终。商鞅之后,秦始皇重用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李斯,同时又极其崇拜韩非之学,对法家的法治主张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因此,秦统一之后,国家法网日益严密。
这一时期的法家法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影响利弊兼有。有利的方面:“以法治国”“事皆决于法”,对于否定先秦以来等级特权思想有重大意义,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商鞅在“缘法而治”的前提下,提出了实施法治的方法,在《商君书·修权》中提道:“国家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首先,认为治国不仅要有法,而且要守法。守法问题,不仅包括百姓的守法,更涉及到君主的守法,且君主守法问题是法治的根本问题。商鞅认识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这一点体现了商鞅法治思想的深刻。《商君书·画策》中指出:“国皆有潜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如果君主不守法,则毫无办法。其次,认为实行法治的关键是要取信于民,执法守信,必须做到“信赏必罚”。《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商鞅徙木赏金的事件,这一做法尽管有使用权术之嫌,但执法守信以贯彻“法治”的思想,即使在当代依然有可借鉴的价值。再者,关于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商君书·赏刑》记载:“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罪死不赦。”韩非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韩非子·有度》记载:“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种“刑无等级”的思想,针对贵族特权,旨在批判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做法,成为后世反抗特权的理论基础,意义重大,值得肯定。
不利的方面:尽管法家的理论满足了历史发展的需求,但是其局限性亦非常明显。首先是“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法家思想中“缘法而治”的“法”,强调的是“法自君出”,并且必须君权独制。因此,法家推行“法治”的前提是君主专制,而过度的君主集权专制,反过来又会严重地破坏“法治”。其次是“刑无等级”的局限。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在反抗旧贵族特权方面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其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刑无等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有着本质区别。法家的“刑无等级”是将君主排除在外,将法律视为君主的御用工具,强调君主在用刑时,对于“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的臣民,都要“罪死不赦”。再次,重刑主义,以刑去刑,最终导致血腥残暴的统治。商鞅的轻罪重罚、以刑去刑思想,充分体现于秦律中,加之秦王朝统一之后身为丞相的李斯形成了极端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强调君主对臣下的“督责”与“重罚”、专任刑罚的治理政策,[2](P249)主张以法为教,禁绝百家之言,最后以“焚书坑儒”践行了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可见,缺乏道德教化的社会,国力虽强,但并不安定。这种弃礼任法,专任刑罚,绝对专制,最终导致法制畸变以及秦王朝二世而亡。
综上,法家的“法治”思想既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面,又有过于极端畸变的一面。但是,其严密法网、追求法律体系完备的做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建立是功不可没的。
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法合流的开端
汉代自汉武帝之后,从表面上看是儒家独尊,而实质上却是儒法交融。
1.儒法合流的内在基础
秦亡汉兴,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暴政而亡的教训,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与民休息,约法省禁。这实质上是一种以道家思想为本、儒法融合的思想体系。一方面,虽然“专任刑罚”是秦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抹煞法家“法治”思想的合理因素。因此,无论是汉初的黄老思想,还是汉武帝之后的“独尊儒术”,在根本上都未摒弃法家“法治”的内核,这就成为儒法合流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即使秦王朝推行重刑主义,但儒家的忠孝思想以及对老幼、废疾的恤刑思想均在“云梦秦简”中有所体现,不仅规定有维护皇权的谋反罪,还有维护父权的“不孝”罪,以及维护宗法伦理观的强奸、通奸罪。在恤刑方面,以身高为标准来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未成年人(男六尺五寸,女六尺二寸以下)犯罪则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刑罚;对于老人,秦律则规定有“免老制度”“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3](P313)
这种儒法合流的趋势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况的思想之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一直抑法重儒,推崇孔子为儒家的典型代表,荀况的思想不被重视,但事实上荀况的思想却是儒法合流的理论根源。尽管荀况详细阐述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思想,但是亦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王”“霸”并举,并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法律在矫治人性、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荀况为儒法合流的出现开了先河。
2.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经过汉初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西汉的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繁荣富庶景象。但是,这种过于宽松的统治政策使整个国家缺乏凝聚力,与统治者尤其是有着雄才大略积极进取精神的汉武帝刘彻的意愿相悖。武帝希望加强专制皇权,抑制离心倾向,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而黄老思想是无法实现这一愿望的。相反,宣扬大一统理论以及宗法等级理论的儒家思想,满足了汉武帝通过统一思想、提高修养,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是,此时的“儒术”已非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而是以儒为宗,兼采各家,尤其是法家思想的新型治国理论。从此,中国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并逐步形成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法律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过程是法律被儒家化了,而实质却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这对于统治者维持统治的稳固意义非凡。大儒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核心是“德主刑辅”,即主张在治国策略中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以刑罚惩治为辅助手段,借此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在实施过程中应“大德小刑”“先德后刑”,“德”“刑”两者缺一不可。
四、秦汉儒法合流的趋势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1.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强调以民主为前提
从先秦到秦王朝,法家所谓的“缘法而治”“以法治国”,虽强调“刑无等级”“法不阿贵”,但同时又主张“法自君出”,极力推崇极端的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梁启超曾指出,“法家最大的缺点,在立法权上不能正本清源。”在当代中国,民主与法治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基本内容,民主为法治奠定基础,法治为民主提供保障。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制定出的法律制度,才更能体现公共利益的导向,切实保障人权。否则,法治就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沦为专制的工具。
2.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道德教化两手都要抓
秦亡汉兴,汉承秦制。尽管汉初摒弃了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但是从“约法三章”到《九章律》的制定,汉朝依然在践行法家的“缘法而治”,即便是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缘法而治”的治国方式仍未改变,所以被称为是“儒表法里”。这就意味着早在汉代,统治者就意识到,“以法治国”与道德教化两者的地位虽分主辅,但却都不容轻视,只有两手都抓,统治才能稳固。在当代中国,虽已进入文明的法治社会,但依然不能忽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应当二者统一,不可偏废。我们不能把道德与法律完全对立起来,法律的实施有赖于道德的支撑,加强道德教化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
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做好基础工作:严密法网,做到有法可依
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王朝,秦的法制可以说是相当繁密。据“云梦秦简”可知,秦律涉及国家行政组织及吏治管理方面的问题,所有权、债权及婚姻家庭问题,各种刑罚原则及刑名、罪名,还包括内容详备种类繁多的经济管理法规,等等。其中,在婚姻家庭方面,秦律规定,夫殴妻属违法行为;在手工业管理方面,对产品的规格有严格限定;在刑罚原则方面,有区分故意过失的“端”与“不端”、共犯加重处罚等,不一而足。汉初统治者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归为法网过于繁密,然事实却是,随着汉的统治稳固和社会发展,其法律逐渐由“约法三章”发展为《九章律》,进而又有《傍章》以及各种律令。所以,导致秦亡的是专制与暴政,而非法网严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只有更系统更完备,才能适应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的需求。我国目前除了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大的部门法仍在不断地进行修订增补之外,《环境保护税法》《水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等一系列涉及国民切身利益的生态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也在陆续出台。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备前提。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4]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秦汉儒法融合过程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探索更切合我国国情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