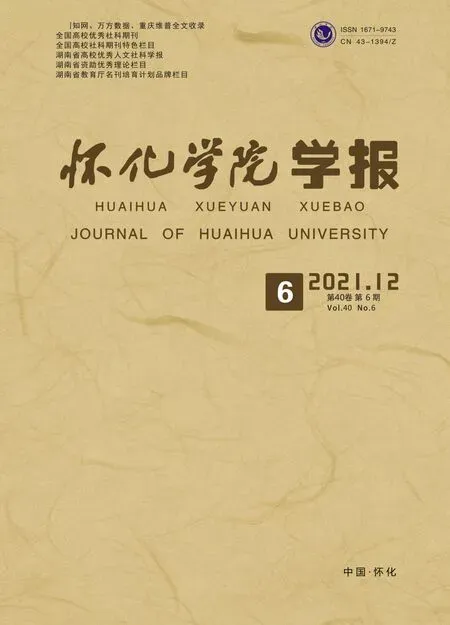从代县花馍文化的变迁看物与人的互为主体性
郭莉芳,杨 卫
(1.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2.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8)
代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内有雁门关,在古代是“内地与塞外、中原与漠北、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分界线”[1],可以说是政治军事、商旅贸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塞;南邻五台县,是那些“从西藏、青海、蒙古等地长途跋涉前往五台山的虔诚僧人”[1]的必经之地。官员、商人、军队、僧人等各种类型的人员流动,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元素,为代县文化注入了活力,使代县文化丰富多样。代县花馍(也可以称为代县面塑)正是孕育于这样一种多元文化之中,见证了代县千百年来的风雨沧桑,承载了代县民众的文化记忆,寄托着代县民众对乡土的热爱、对生命的珍视、对未来的希望。
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我国对文化遗产日渐重视。各级政府积极进行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代县花馍因其自身的特色,入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但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有断裂的趋势,代县花馍面临认同危机和传承人断层等问题。因此,代县花馍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如何适应新时代新需求,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本文试以代县花馍为研究对象,把代县花馍放入民族学“物”的研究范畴内,通过描述花馍的制作工艺、花馍种类、使用情形及变迁轨迹,着重探讨物与人的互为主体性,以期丰富对代县花馍文化的研究,并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一、前言
(一)物与人关系的相关研究
民族学对物的研究由来已久,进化论学派将物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程区隔的标志,传播学派将物作为鉴定不同文明亲疏关系的工具,功能学派将物视为人类适应环境的辅助,结构主义学派将物作为探究社会内核的门径。此时物成为人的实践客体,人对物具有主体性地位。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的主体性地位遭到质疑,民族学界也开始反思人与物的关系。阿帕杜莱的著作《物的社会生命史》[2]中收录的论文均指向物自身,彰显出物本身的能动性。因物“在不同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通过追溯物在不同时段的变化来为物立传成为对物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3]物质文化研究代表人丹尼尔·米勒[4]试图在人和物之间建立一个非二元的模型。他认为物与人是相互构成、相互界定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拉图尔认为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主客二分。“要深入到主客二分如何得以可能的生成根源上去揭示其真正的基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存在论’的方式对待物,从而达到与物的‘共存与共生’,而非在人给予物之意义的认识论层面上将物当作可以改造、利用、索取与掠夺的对象。”[5]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物从民族志中零星的描述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物与人、文化、精神之间的对立渐渐消解,形成了物与文化联系、物与人互相定义、物具有自身意义的讨论路径。”[6]舒瑜[7]认为可以通过研究物的流动与交换来研究区域社会。吴兴帜[8]认为物是文化的储存器,以物为媒介能解读物背后的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马腾嶽[9]指出人赋予物意义并将记忆投射其上,物成为记忆的对象物,参与了人的各种实践,规范了人的生活,与人类主体相互定义,乃至形塑人类集体的共同意识。郑家闽[10]认为物与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人选择物、使用物、使物获得身份的转换,同时物的存在对人具有一定意义。李忠丽[11]运用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和异化理论,阐述了《爵士乐》中新黑人族群在对物的符号消费过程中,其精神状态、人际关系以及身份认同受到的影响。
物不再是人的附属品,其塑造、规约人的能动性被凸显出来,人与物关系方面的研究呈现由“‘主—客’对立演化成为‘主—客’交融”[12]的发展趋势,但是以人与物的互为主体性为主题且通过实例探讨人与物如何保持互为主体性的良性互动方面的研究还是较为缺乏,这为笔者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二)关于代县花馍的研究现状
经查阅,以代县花馍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两篇。一篇是安昊帅的硕士学位论文《代县花馍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研究》[13],该文以代县花馍为个案,希望能够以设计作为社会创新工具,找到一个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其自身价值在现代社会发展和延续的空间。另外一篇是孙颖的《代县面塑制作的民俗心理分析》[14],此文简单介绍了代县部分面塑蕴含的民俗心理。以上研究侧重于代县花馍的传承危机、解决路径及民俗心理分析,对代县花馍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涉猎很少。
代县是笔者的家乡,结合自身记忆及对邻里乡亲、花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花馍老艺人的访谈,可以发现代县花馍技艺产生于代县民众的生产生活当中,花馍文化表现于花馍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人制作和使用花馍,赋予花馍不同的外在形态、文化内涵及多重功能;花馍也会对人的技艺、情感、信仰、人与人的关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产生作用。可以说,在代县人的社会、文化当中,代县人与花馍处于互融互构、互为主体的状态,共同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及社会的发展。
二、代县花馍的制作和使用
(一)代县花馍的制作
对于花馍的制作这一部分,本文试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部分。
1.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家家户户的主妇们都会制作花馍,只是制作技艺有所差别。几位做得最传神和最逼真的女性会得到全村人的称赞,经常受邀为村里其他人制作婚礼或丧葬这样大型仪式中使用的花馍。她们通常在事后会得到回礼或金钱上的回报。那时花馍的主要原料——白面(代县人称小麦粉为白面)受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战争、政治等因素影响极大。山西地区小麦的种植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南部产麦多,而越往北杂粮的种植比例越大。代县处于山西东北部,产麦量并不大,但是小麦在代县人民的心目中地位很高,像祭祖和贡神这样的神圣场合以及婚礼、丧葬这样人一生中最重大的仪式以及春节、中秋节这样的岁时节日都需要白面制作的花馍。原料少却用处多,于是代县花馍与晋南地区花馍相比相对小巧一些。
面对有限的白面,代县人对小麦格外珍惜。收回来的小麦首先要用水洗,去其土气。晒到八成干后上石磨磨,头道、二道、三道、四道白面要分开存放。一般制作花馍要用二道磨的面,这样的面精细,易捏制,蒸出的花馍光滑细腻。也正是因为白面的珍贵,主妇们对花馍的制作充满热情和期待。
每到捏制花馍的重要日子,她们早早用老酵头和面,面要和的稍硬些,反复揉面上百下,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大概6到10个小时(时间因环境温度不同会有浮动),直到面发满盆,抓开呈蜂窝状才可以。备好剪刀、针锥、梳子、几根高粱秆皮、一小把高粱籽、一把红枣,家里的女人们——母亲、祖母、婶婶、大大(代县人称伯父、伯母为大爷、大大)、姑姑齐坐炕上,互道邻里趣事、家长里短,也互相学习交流制作花馍的技艺。热热闹闹、开开心心,仿佛要将所有的技艺、热情、希冀、信仰揉捏进那些小巧的花馍中。不管是谁捏出了传神、漂亮的花馍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夸赞,“手巧”“好看”“喜人”这样的赞语是最常见的。当捏到一些有特殊美好寓意的造型时还会说上一说,比如“捏个兔子,孩子以后聪明伶俐”“捏个老虎,孩子胆大有威严”“捏条鲫鱼,年年有鱼”“捏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上述的吉祥语和祝福语既是说给自己,也是说给家人,更像是说给内心的神,仿佛说出来或者心里想一想,哪怕仅仅是捏出来就能让神知道,使愿望成真。家里的孩子们或站或坐在旁边,有的听个热闹,有的也想上前捏上一捏,有的玩玩面盆、擀面棒。当她们长大以后,自己制作花馍或者看到花馍时,这种儿时对家人制作花馍过程及话语的记忆会再次浮现而引起情感共鸣。
花馍捏好造型后要醒面一段时间,拿起花馍来感觉其变得轻盈就可以放入笼屉蒸了。水开入锅,大火蒸30分钟,停火后再闷五到十分钟。出锅稍散散热气就可以画了。
讲到“画”,所用颜色仅红黄绿黑四种,是一种民间食用色素,但就这四种颜色就像画家调色盒里的原色一样,按不同的比例去调出新的色彩。花馍里面的男女、仙人形象是仿照戏曲人物来捏制、描绘的。当妇女们拿起画笔那一刻便十分的专注、虔诚,尤其是各个仙人形象,动作、服饰、眼神画的栩栩如生。最后为了使其色彩更亮丽,要在其外表涂刷一层素油。对于形态较大造型复杂的花馍,要分开制作,蒸熟后经过彩绘再用高粱秆皮穿插组合。
花馍蒸好、画好之后,常有小孩儿迫不及待想要摸一摸、玩一玩、尝尝味道。一般都会受到母亲或祖母的严厉制止,因为“点画”(指画了颜色,即使是一个红点)过的花馍是要先献给神或祖先的,随意摆弄就会“不当了”(指对神仙不敬会惹恼了神仙带来灾祸)。只有供奉神仙或祭祀祖先的仪式结束了,人才能食用花馍,而且据说食用后对人有好处,即能给人带来好运。
2.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之后,白面可以自行购买,花馍原料被限制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有了充足的面粉,家庭主妇们就有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有的在大小上面做文章,想要捏出最大的和最小的花馍;有的人在数量上面下功夫,一个大石榴馍上面或者一个大枣饼上面能加上几十个文化元素,看起来绚丽多彩、生动形象、寓意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社会分工明确,信息更加畅通,交通日益发达且人们对教育更加重视。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打工或求学,都走出了农村,到各个城市去体验新的生活。主要以口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的花馍工艺同其他民间工艺一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和传承危机。
在这样一个花馍技艺传承的危机时期,国家意识到了花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为响应国家政策,代县政府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寻找和确定花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政府帮扶、传承人创业、传承人与企业合作等方式对代县花馍技艺进行保护及创新性发展。
商品化的花馍对制作花馍的技艺和对花馍市场的把握等方面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技艺方面,要求其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在寓意方面更加丰富,既要有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传统情感及价值寓意,又要有新时代文化特色;在市场营销方面,要求拓宽销路,创作适用于更多场景和仪式的花馍造型。当花馍成为商品,花馍制作者们同时也是花馍销售者,她们希望将花馍产业做大做强,让工艺继续传承下去。她们有的开设培训班,招收学员;有的与企业合作试图找出花馍产业发展的新路子;有的赋予了花馍适应新时代文化的寓意,为花馍设定更多的主题,使其适合更多场合、仪式;有的与其他地区花馍手艺人交流、切磋,提高技艺。当然也有的人并没有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竞争的新规则,既没有打开销路的渠道也没有将花馍产业做好的决心和勇气,于是黯然退出。
(二)代县花馍的使用
在历史长河中,代县花馍在使用情况、使用场合、使用数量方面因各种因素影响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中。下面仅详述从传统到现代都最受重视的几个仪式和节日中花馍的使用情形。
1.人生礼仪
代县文化中的人生礼仪主要包括满月、婚礼和葬礼。
(1)满月。满月使用的花馍比较简单,通常由小孩的姥姥制作两个“奶头馍”,顾名思义,形状像奶头一样。里面包白糖,上面插上五男二女,一方面祈盼小孩能吃到充足奶水,茁壮成长,另一方面也是多子多福思想的体现。在满月宴这一天姥姥将奶头馍带到小孩家中,并记入礼账,一起入账的还有给小孩的衣服等。如今满月礼大多被折成“干礼”,即将赠送的东西折成钱入账,姥姥家一般要上一千到一万不等的礼金,加上金或银制小手镯。
(2)婚礼。婚娶时,男女两家都要做很多花馍。
男方家娶媳妇要做“石榴馍”。通常是三个小石榴馍为底,上面一个大的石榴馍,再在上面插上配饰。配饰一般为龙、凤、一对男女、全花、鱼等形象。石榴馍第一点讲究要“开花”,也就是石榴馍蒸好时裂开了缝儿,象征着这桩婚事很般配,很喜气,连石榴馍都笑开了花。第二点讲究要“全花”。所谓“全花”指的是必须包含“事事如意”“牡丹”“福寿莲花笙”的造型,寓意从此福、寿、富、雅、多子、顺遂的完美人生。这样一套的石榴馍共需要三个。主要用于新郎将新娘迎娶回家后拜堂仪式中。
女方父母陪嫁闺女的花馍称为“食贺”。是一种需要两个人抬的木质的大方盒,里面的花馍共有32个,分为花果类、动物类、娃娃类、十二生肖、也有小的石榴花馍(相对于男方的石榴花馍)等,具体捏哪几样没有硬性规定,不过虎和蚕是必须有的。这些花馍,要摆在桌子上供人们观看。第二天女方回门时,男方要回赠给女方一半的花馍,其中“虎”与“蚕”是必须回赠给女方家的,其他的可随意。“虎”代表新郎去到女方家里时有底气有威严。“蚕”代表新娘回到娘家时变成一个难缠的人,不能在娘家多呆。另外,“食贺”里还放有做针线活的工具、送给新娘的衣服、送给新郎及其父母的鞋子等礼品。现在结婚时男方还是要准备石榴馍,因为拜天地和拜人仪式时要用到,而由女方准备的食贺则可做可不做了。
(3)葬礼。葬礼是人的一生中最后一个仪式,当然离不开花馍。
葬礼上的花馍有三种。一种叫面席,由死者亲属关系中最近的女性晚辈来制作、供奉,如儿媳妇、女儿、孙女,各准备一桌。一桌面席通常是六六席或八八席,即一行六个一共六行或一行八个一共八行的花馍数量。涉及的造型有八洞神仙、十二仙女等仙人形象,各种吉祥寓意的花儿形象,各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形象等等。第二种是大祭,与面席一样由死者儿媳、女儿、孙女准备。大祭的造型都一样,是一个长面馍两头尖尖弯回来,两头各放置一个红枣,像牛角的形状。到三周年的时候制作的大祭是两头相接的圆环形状,寓意三年守孝圆满完成。大祭除了供奉死者,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出殡那天由孝子揣在怀里,带到坟地,叫做“揣富贵”,回家的路上要取出来或者给它翻个身。之后可以自家食用,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也可以分送给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第三种是面羊面猪,也就是用面捏的羊、猪形象,包含在亲属关系稍远一点的女性晚辈,如外甥女、侄女等准备的肉席之中。
2.岁时节日
(1)春节。春节期间代县人都要蒸供来敬神、祭祖。最常蒸制的两种造型是元宝馍和普通圆馒头。元宝馍和圆馒头没上色之前是可以自己食用的,上面点红点之后,元宝馍是要供奉给家里的各路神仙,圆馒头是在初二带到坟地给先人们拜年、祭奠先人时使用。每到腊月二十九或三十时,每家每户都开始发面准备制作元宝馍和圆馒头。蒸制完成后,按照家里神仙每位五个,祖坟先人每位四个的量来点红点。到除夕夜与大年初一的分界点00:00分的时候,是接神的时间。家里的男性们开始放鞭炮、发旺火。旺火是代县人用煤炭和木材搭起来的下圆上尖的架子,底部有用来引火苗的干高粱穗和干玉米壳,发旺火时火苗越旺代表新的一年人畜兴旺。家里的女人们则准备供奉神仙的元宝馍、贡菜、水果、干果、糖果等贡品,至少五种,摆在各位神仙灵位前。然后给每个灵位上三炷香、烧事先准备好的黄裱纸、跪下磕三个头并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神仙们能满足她们内心的愿望。之后全家人坐在一桌,吃有红糖的糖包、喝红糖水,期望来年甜甜蜜蜜。
(2)清明节。清明节要捏“寒燕儿”。传说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介子推曾经割股为他充饥。晋文公归国为君后分封群臣,却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老母隐居于介休绵山。晋文公得知后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藏山中。晋文公下令放火焚山,逼介子推露面,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晋文公下令晋国人在介子推死难之日不准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节。后来随着历史发展、朝代更迭,寒食节慢慢淡出,与清明节融为一天。在这一天家家都要蒸制寒燕儿,形状有小燕子、鱼、青蛙、虎、羊、兔等动物形象,还有瓜果、娃娃、花儿,各个小巧玲珑、逼真可爱。用柳枝穿起来挂在门头,吃的时候取下来,酥松又有嚼劲,好吃、养胃、助消化,深受小孩们喜爱。在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县面塑传承人张桂英的采访中,她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树上结的、地上的花花草草都能做成寒燕儿。寒燕儿要是上坟用,鸟不能剪开嘴,怕吃东西,不能剪开翅膀,怕飞了。”
(3)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蒸面人。据说元朝时期,为了统治汉人,朝廷实行了十户制,以十户为单位将百姓划分开,派一个叫十户长的蒙古人进行监视、管制。百姓私下称这些蒙古人为鞑子。这些鞑子平时就由这十户人家养着,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甚至享有管辖区内新媳妇的初夜权。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终于想出了反抗的好办法。他们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具体时间写好,放入面人中,在七月十五这一天通过互相赠送来传递消息。鞑子们未觉有异,被杀个精光。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压迫运动成功之后,七月十五这一天就有了亲戚朋友互赠面人的习俗。发展到现在,七月十五只捏制一些趴娃娃、坐娃娃等各种姿态的娃娃花馍送给一岁以内的小孩,有祝愿小孩健康成长的寓意。
(4)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蒸花糕。将发好的面擀成薄圆饼状,上面撒一层红枣,再用一张薄圆饼盖住,两个圆饼要一样大小。再搓一小条面,长度和宽度要正好圈住一个红枣。将其按扁,用刀背压两道平行纹路,圈住红枣。然后做多个这样的面枣,摆放在刚做好的面饼上,尖的一头朝向圆饼的圆心,从外向内一圈一圈将圆饼摆满,最后中间放置一只玉兔形状的花馍。有的人还会加上盘龙、祥云等花馍置于其上。到晚上能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会把花糕、时令水果、毛豆角、半个西瓜、月饼放在院子里贡桌上,然后跪下叩头三下,请月神享用美食。贡完月神后,花糕会被切成三角状,分出一部分供家人食用,剩下的第二天送给亲戚、邻居们品尝。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日益丰富,可供赏玩之物太多,而且全球化程度日深,外来的价值、审美、时尚潮流对中国人影响越来越大,蕴含传统文化的花馍越来越不受关注。在访谈中,一位50岁的代县女性就直言“现在的娃娃们有福了,耍活儿(玩具)多的,没人耍面人,一摸一手颜色,脏的。”另外,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都用科学来武装头脑,鬼神之说被认为是迷信,绘在花馍上的颜色也被认为是脏的、有毒的,对人体有害。那些色彩艳丽的花馍失去了神性和食用功能,被使用过后逃脱不了被任意毁坏、丢弃的命运。再加上现在大多代县人已不会制作花馍,对花馍没有多少感情,购买婚礼上使用的花馍至少需要花费三百块钱,有些人认为买花馍是很大的浪费。笔者四叔嫁女儿时就没有准备花馍,他这样说,“用上一下全扔了,纯粹浪费钱了”。
市场经济时期的花馍逐渐成为商品,被明码标价,高低贵贱一目了然,一方面被塑造为象征新时代文化特色的符号,另一方面被塑造为象征地位、财富、身份的符号。此时,花馍的制作者与使用者已然分离,花馍之中缺少了使用者的文化记忆、情感价值及精神信仰,反而在花馍与使用者之间增加了金钱作为中介,使得人们对花馍的热爱转为对金钱的追求。在使用者的内心,花馍的价值由金钱来衡量,花馍与金钱画上等号。在旁观者眼里,花馍不再单纯是祝福、吉祥、孝顺、般配、美好之类词的代表,而更多的是财富多少、身价高低的表现之一。
三、人与物的互为主体性
(一)人对物的主体性呈现
人对物的主体性指的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将自己的意志作用于物、改造物,赋予物外在形态、内在含义,通过物建构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习俗和秩序。以代县花馍为例,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就人对物的主体性予以阐述。
1.人赋予物外在形态
旧时信息传播的平台有限,仅能通过看戏曲、说书、集市上的表演、话本等几种传播媒介获取外界知识。外来元素、生产生活经验和有关花馍的历史记忆一同构成花馍捏和画的灵感源泉。
代县花馍三分捏,七分画。捏好画好方算高手。不同的仪式,不同的情境,需要表达的寓意不同,形状也会有所不同。画的过程主要参考戏曲人物,再加上个人经验及想象来绘制。一方面使花馍造型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把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审美观念赋予花馍,另一方面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神圣性。
在传统社会,代县人创作的花馍造型主要用于仪式、节日,造型和种类在较长历史时段基本无大的变动。当下的代县人处于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之下,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在制作花馍方面吸纳了更多时代特征,制作出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纪念花馍、杨家将风采观赏花馍、上海世博会吉祥物花馍等专供观赏的新类型。
由上可知,人在制作花馍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认知、记忆结合社会的需求、时代的发展特征,通过手作用于花馍,使花馍的形状和色彩都烙上了人的烙印。当然,烙上人的印记的不只是物的外在形态,还有隐藏于物背后的情感、观念、价值等文化内涵。
2.人赋予物文化内涵
人赋予物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人对物进行的身体实践中。首先,部分花馍的造型体现人对多福、多寿、多财、多子的追求。如婚礼仪式中必须要有的“全花”,包含“事事如意”“牡丹”“福寿莲花”的造型,象征多福、多寿、多才、富有、顺遂的完美人生。其次,部分花馍体现了人的生育观念。如奶头馍上面插“五男二女”七个小宝宝造型,说明人们认为孩子多是好事,而且男孩要比女孩多。再次,部分花馍体现了代县人对男女的不同要求。如送给男孩“虎”,暗示男孩要威严、有气势;送给女孩“兔”,寓意女孩就要乖巧、灵动。最后,仪式中对花馍的使用方式,体现了代县人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如春节的接神仪式中将花馍献给神明和祖先,认为神明和死去的祖先具有超自然力量能帮助生者摆脱困境。
由上观之,人根据不同需要通过对不同形状的花馍造型赋予其不同的文化内涵,使这些文化内涵在建构秩序、维系人情、固守习俗、沟通人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要想使上述文化内涵的诸多功用得以实现,就需要赋予花馍多重功能。
3.人赋予物多重功能
据笔者调研发现,代县人主要赋予花馍交换、观赏、食用等诸多功能。
在花馍的交换功能方面。人制作花馍赋予其以静态性,人使用花馍又赋予其动态性,这一动态性集中表现在交换功能方面。花馍的交换功能主要集中于两个空间: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从七月十五的互赠面人和八月十五的互赠花糕到仪式花馍的分食,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都属于世俗空间的流动。花馍在人与神圣空间的交换最主要的就是除夕夜与大年初一的分界点00:00分的接神仪式。接神仪式中花馍从食用之物转变为神性之物,实现了花馍从世俗空间向神圣空间的流动,使人与超自然力量建立了联系。
在花馍的观赏功能方面。传统社会可供观赏、装饰的物质缺乏,通常在仪式结束后,人们会争先恐后的将花馍带回家中,摆在显眼的位置上,供人欣赏,装饰房间。
在花馍的食用功能方面。旧时代县人认为画了颜色的花馍是不能直接食用的,要先献给祖先、神仙,然后才自己食用,而且祖先和神仙享用过的就带有了神性,吃了对人有好处。例如寒燕儿要用柳条穿起来,挂在门头上观赏几天后才食用,老人们讲小孩吃了寒燕儿有健胃消食的功效。婚礼上的石榴馍和食贺也是先观赏一段时间再食用。元宝馍要在贡神结束后才能热来吃。面席要在葬礼结束后在家里观赏几天再吃。大祭和面猪、面羊是葬礼结束、分送给各位帮忙的邻居们朋友们以后,剩下的切片晒干,慢慢吃,据说是能给家里带来好运的。
而现代社会物资丰富,在食用、观赏和使用方面有太多的替代品出现,再加上现在大多代县人已不会制作花馍,购买花馍花费较高,于是花馍的观赏功能、食用功能和使用功能都不同程度受损。人的观念发生变化时,物的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人对物的主体性呈现可知,人对物的主体性表现在人首先赋予花馍外在形态,而后通过花馍的各种外在形态承载当地民众的情感、价值、观念、习俗等文化内涵,最后通过赋予花馍的各种功能使花馍在群体内部形成共享的文化符号,达到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情感、互动等方面的需要。
(二)物对人的主体性展现
在对代县花馍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在人对物具有主体性的同时,物对人同样也具有主体性。物对人的主体性是指在人制作物和赋予物外在形态、文化内涵及多重功能之后,物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人的生产生活中,并影响人的生产生活。以代县花馍为例,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1.物帮助传统文化实现代际传承
“在具体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的塑造下,物作为一种社会生物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文化之物,一个饱含并充盈着特定精神情感的生命体。”[15]在花馍制作和使用这样的身体实践中“直观地展示了祖祖辈辈无须言说的思想内涵与世界观,实现了日常生活的最高理想与完美意义的传承,构建了饱含人们祈求健康长寿、多子多福、丰收富足等美好文化认同。”[16]代县花馍正是通过其外在形态、内在隐喻,将代县人的情感记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最终帮助当地传统文化完成了代际传承。
2.物对人的行为有规范作用
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附着着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小小花馍之中蕴含着代县人对花馍形态、情感的记忆,对群体行为、价值观念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在一个小型社会中很容易形成“价值共意”[15],对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形成规范、约束作用。符合花馍中情感、行为和价值观念要求的人会得到群体的尊重与认可,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价值。代县花馍技艺的实践主体基本上是女性。那些把花馍捏得很漂亮、传神的女性会得到群体的认可、尊重与赞美,通常被称为心灵手巧、有本事的女人。那些知道什么仪式制作什么花馍的女性,因其对本土传统文化中的礼、孝观念,追求多福多禄多寿、多子多孙的思想有充分了解和深度的认可,被称为懂礼的人。正是这样一套评价女性价值的标准,通过花馍规约着女性,延续和巩固着社会秩序。
3.物是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沟通的媒介
物在世俗空间的双向流动,促进了人与人的互动、喜悦与悲伤情绪的共享。情意与凝聚力便在这种礼尚往来中产生、延续。物在世俗空间的单向流动,则表达了晚辈对长辈的孝顺、尊敬之意及长辈对晚辈的关心、爱护之情。
物在神圣空间中流动则是作为人与神、祖先的沟通媒介,一方面为了表达人对神的敬仰、对祖先的尊崇,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而寻求超自然能力的帮助或者得到心理慰藉的方式。例如在葬礼之上,与死者关系最亲近的女儿、儿媳将为其捏制的面席、面猪面羊供奉给死者,并跪拜、哀悼死者。春节用花馍供奉神仙时,也有烧纸、跪拜的仪式。当家中无大事时就祈盼来年顺遂,家中有大事就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全家逢凶化吉,避开灾祸,一切顺利。一套仪式下来,人的情绪便有了出口、情感也有了慰藉,仿佛心里从此有了底气。可见,物作为人与人、人与超自然力量建立联系的中介,不仅使人与人关系拉近、使人得到他人和先人的认可,还可以使人得到心理的慰藉、诉说的渠道。
由物对人的主体性呈现可知,物以各种形态将附着于其间的传统文化进行代际传递,使生活在其间的民众通过物这一载体的各种展演能够熟稔自己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同时使自己的价值行为受到规范,促使他们恪守本分、尊重分工、注重人伦、遵守秩序。更为重要的是,物通过充当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的媒介,使当地民众能够通过物在人与人、人与神之间进行交换,这既能使他们在俗世获得安全和温暖,同时也能从神圣空间获取慰藉和希望,这就会使当地民众能够通过物获取生之乐趣和死之无畏。
综上所述,人与物的互为主体性,可以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形成良性互动。就人与人来说,以物为载体,可以传递真情厚意、规约价值行为、践行性别分工、遵守俗世秩序。就人与物来说,通过相互呈现,可以彰显人的灵动、物的万象。就人与神来说,以物为媒,可以予神以敬畏,予人以期盼。通过上述三重维度的互动,在人、物、俗世、神圣之间打开通道,使其各得其所、各有所归,最终建构起人、物之生态,俗世、神圣之秩序。
四、结语
本文通过代县花馍的文化变迁探讨人与物的互为主体性。由上文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前,代县人赋予花馍外在形态、内在含义及多重功能;相应的,花馍也为代县人的信仰、价值观、文化的传承提供平台,规范着人的行为,维系着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代县人与花馍是相互融合,不可分离的。改革开放之后,花馍虽然仍在代县人的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扮演着一定角色,但逐渐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这一时期,花馍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基本上成为人们展演自身各种诉求的工具,但需要指出的是,人在异化花馍的同时也异化了人本身,使邻里之间的真诚之意、人神之间的敬畏之心逐渐减弱,从而使人丧失了一定的互助之念想、慰藉之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成为孤独之人。故而,可以看出,人与物若想互为主体性,就需要尊重物性,只有尊重物性,才能以物之自然性为本根、物之世俗性为内核、物之神圣性为皈依,在此彰显敬畏之心与真诚之意,使人境、物境得以吻合,使人们在物之情境下深受人情之感染、物性之熏陶、俗世之规约、神圣之护佑,真正达到物人互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