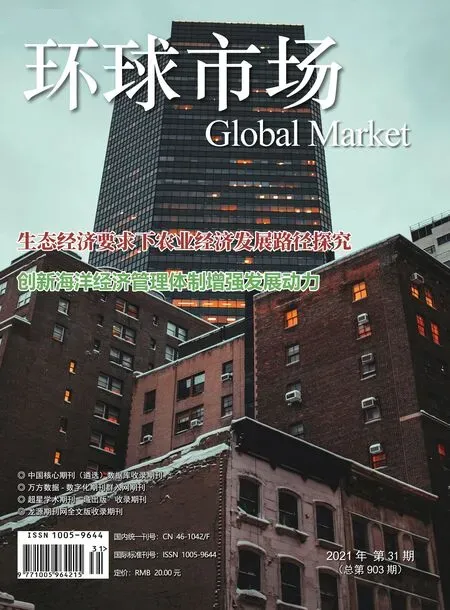从经济效应角度思考反向混淆理论的正当性
程亚楠 西北师范大学
公平和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要义,一直以来是人们公认的事实。但是,当前法律经济分析日益得到学界很多专家的认同,它强调一个好的法律制度,除了对公平的追求外,也应纳入经济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的考量,让社会资源做最有效率的利用。不同于传统法学把法律视为一个所有法律事实都可以囊括的规范体系,法律经济分析提出法律是一个需要检验证实的规范工具,这点和其他社会制度类似。其运用经济学的方法与理论,检验法规范的妥当性或者预见性,同时考量何种财产权归属方式以及如何保护财产权,可以让社会资源在交易成本最少情况下,得到最有效率的分配,最后透过个人财富最大化的累积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因此,立论于理性(rational)自利的人性及有限社会资源的假设前提,法律经济分析利用“交易成本”“效率”等概念,针对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分析,希望建构一个“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法律制度。因此,本文拟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思考反向混淆理论,试图分析反向混淆理论是否有必要明文规定于商标法中以保护在先商标使用人的权益。
一、何谓“反向混淆”
近年来,一件涉及商标侵权的案件使得全社会将目光转向了商标反向混淆,该案打破了小企业侵犯大企业权益的固有思路,这个被外界戏称为“蚊子叫板大象”的案件就是浙江蓝野酒业有限公司诉上海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再加之美国相关案例,各国纷纷开始讨论确立商标反向混淆侵权类型,该理论的目的在于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法律都应当公平保护。
反向混淆概念最早是由Holmes法官对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Associated Press一案的不同意见书上提出:“一般侵权案件多为被告仿冒原告商品的情形,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即消费者将原告的商品视为源自被告的商品,这种情形虽然少见,但是亦会出现。传统的商标正向混淆指的是在后商标使用人为了利用在先商标使用人的商誉,在自己的同类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得消费者产生在后商标使用人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在先商标使用人的误认,以此获得不当利益,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搭便车”。而本文讨论的反向混淆不同于传统商标侵权“小企业攀附大企业”的搭便车,反向混淆案件恰巧“反客为主”,在先商标使用人即商标侵权人拥有的商标本不具知名度,通过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在后商标使用人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下,营造了系争商标的品牌价值,但同时却也弱化了系争商标与在先商标权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造成消费者认为此商标属于在后商标使用人即侵权者的错误印象,从而造成在先商标使用人无法完全自主地行使自己的商标权利。
二、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寇斯定理”
“交易成本”作为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理论,系指当事人在交易过程前后产生的与此交易有关的成本,通常可分为事前的信息搜寻成本、执行的成本及事后维护的成本(例如诉讼的成本)。因为此理论由寇斯(Coase)所提出,故人们多以“寇斯定理”陈述相关理论。“寇斯定理”的核心概念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财产权在初始阶段如何界定,社会资源的运用都会被最有效率的分配。”也就是指通过自由交易,社会资源最终流入有能力使得资源产生最大价值的人手中。但是,将交易成本假设成零,这是乌托邦的理想境界。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互动一定会伴随着成本的产生。假如交易成本过高,则会出现“市场失灵”,造成交易困难,形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经济问题。由于法律透过财产权的赋予扮演着社会资源分配者的角色,但是资源是有限的,信息又是不对称的,一个好的法律规范在界定财产权归属时,除了公平正义的追求外,还必须保证外部干预最小,即尽量避免制定规范本身会产生过多成本,最终实现“效率最大化”。
在此思维下,权利原则上应归属于交易成本较高之一方,这样可以降低当事人之间因协商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交易成本低,意味着资源的运用愈有效率,而有效率的资源运用又可创造财富的最大价值,因此一个好的法律制度,除了界定好财产权之外,财产权归属后的保护方式也需采用成本效益的思维方式使得纷争解决的成本越小越好。按寇斯所言,许多财产权纠纷所造成的损害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 nature),亦即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方使用资源常会因压缩他人使用相同资源的空间致使发生冲突。在大多数无法明确可归责于某方的情况下,冲突的发生是必然的,因此,解决冲突的思维就不应是单单决定谁是谁非的责任归属,而是寻找怎么才能让双方的损害减至最小,这才是有效率的方法。
三、利益冲突的平衡
商标侵权案件的处理,一般都是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对于商标权人,我国商标法赋予商标权人排除妨害请求权,类似于美国禁制令的概念,美国主要的法律救济方式是禁制令,这可以让被告最直接的停止侵权,美国商标法规定处理商标侵权案件时,法院有权依据衡平原则给予禁制令。但在反向混淆案件中,考虑到在后商标使用人投入的大量精力及财力,如果直接要求其禁止使用系争商标,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不合理,因为在先商标使用人可能根本对系争商标没有做过多的努力,其只是对系争商标简单注册了一下而已,而在后商标使用人可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这时我们可以考虑换个方式解决商标侵权案件。禁制令虽然做到了个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原则,但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显然未让社会资源做到最有效率的分配:在后商标使用人也就是被告为提升系争商标的价值,投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消费者将系争商标与被告的商品或服务产生错误的连结又已是一既定事实,而禁制令的结果造成被告先前对系争商标的所有投入化为泡影,并且使得消费者又得花更多的成本搜寻自己想要的商品,并且由于消费者之前已经误认系争商标与商品有紧密联系,被告所做的这些联系并不能由原告所当然继受,原告可能短时间内无法让系争商标与其商品又恢复到之前的紧密联系状态,这可能会使得系争商标的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因此,让被告停止侵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很大意义,反而减损了系争商标的利用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解决反向混淆侵权纠纷,在后商标使用人可以协商、授权等各个做法来继续使用系争商标,则不会出现上述的一些问题。诚然,当事人之间协商以降低交易成本是寇斯定理最推崇的理想状态,也是反向混淆案件的最理想解决方案。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类案件如果不采用继续使用的解决方式,被告的损害肯定大于原告的损害,原告将作为最大受益者,这会使得原告产生拒绝将系争商标授权给被告使用,或者将提出很高的使用费,迫使在后商标使用人使用系争商标的成本增加。如果被告发现使用商标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不使用商标的成本时,基于利益的考量被告不得不放弃系争商标的使用,最后因被告放弃,原告无力提升而使得系争商标无法做有效率的使用,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就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商标价值逐渐消失。
反向混淆理论的正当性争议所体现的是一个利益冲突问题,亦即商标法注册保护主义的维护与商标价值最大化的取舍问题,商标法注册保护主义着眼于保障商标权人的财产权,商标价值最大化本质则是强调社会资源有效分配的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观点。当公平正义原则依旧是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时,反向混淆不会是一种问题,因其仍在传统商标侵权范围内,作为起到分配社会资源的作用,法律规定确实是具“相互性”的妥协产物,亦即对某些人的保护系以牺牲他人权益代价换来的,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外部性。然而,商标所使用的文字、图形或记号等素材皆取自公共财产,特殊情况下,准许这些素材所构成的标识为个人所专有。在此理解下,商标法的注册保护主义虽维护了个人财产权,但是其外部性造成了社会上仅有的社会资源被极少数人垄断。假如法律评价的重点由传统的公平正义原则,延伸至吸纳实质的经济效率考量时,反向混淆理论独厚原告的作法似乎值得商榷。商标保护的宗旨已逐渐由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侧重倾向为强调公益的消费者保护,而且商标的产出本身并非如著作权、专利权般的心智活动,而是商业活动的一部分,亦即商标使用背后所代表的是一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自由竞争市场,商标只是用以振兴商业活动的手段之一,经济上的实质获利才是商标权人使用商标的最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法律是人类社会经验的反映,法律存在的价值为社会冲突的调解,又因社会资源有限,作为社会资源分配者角色的法律,诚如法律经济学派的重要人物 Posner 法官所言,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只注重成果,而无视代价(成本)的付出,也就是说“公平正义”及“经济效率”两者皆为法律制度的重要内涵。在此理解下,反向混淆案件中给予停止侵害这种强调全有或全无的做法,不能做到增进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最后,反向混淆案件中,赔偿方式独惠原告而非兼顾原被告利益的做法,明显违背社会资源做有效分配的现实社会氛围,多位学者建议以授权金模式取代,笔者认为合理授权金方式最能有效反映系争商标被使用的真实价值,学者间亦普遍认为此方式较能填补反向混淆理论所衍生的法律漏洞,减缓与现实社会的脱节现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考虑,当被告使用商标的社会价值明显大于保护原告的个人权益时,应允许被告也就是在后商标使用人继续使用此系争商标,被告多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有能力满足原告的补偿要求,因此降低反向混淆的保护程度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作法。
四、结论
反向混淆案件中受影响的关系人有原告、被告及消费者,允许被告继续使用商标可避免让被告之前的大量付出归为泡沫;另外,消费者也已习惯于将系争商标与在后商标使用人的商品或服务之间进行联结,这样也可降低其搜寻成本,整体而言产生正面的外部性,此时对于原告商标排他权损害的补偿,即以法律强制授权金作为被告先前不法使用及日后继续使用商标的代价。如此一来,原告继续持有商标权,并享受商标价值授权应用带来的好处,被告也可继续对商标价值进行最大化的投资,消费者因此可享受高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整体社会都会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