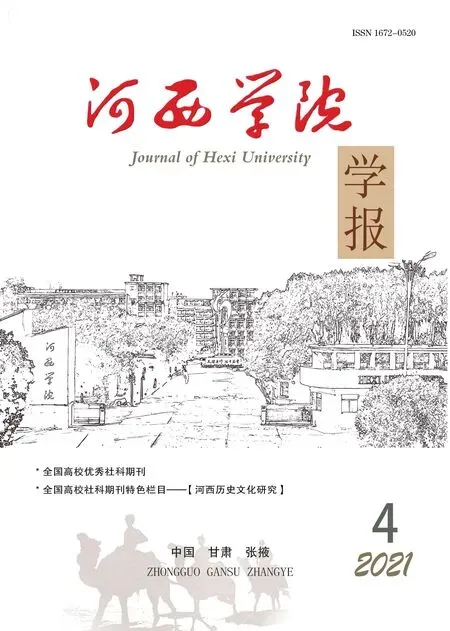锐利而陌生的丧恸
——狄迪恩非虚构作品《奇想之年》修辞解读
吕玉铭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琼·狄迪恩(Joan Didion,1934年-)是美国著名的随笔、编剧和非虚构作家。她从二十岁开始写作,一生以文字为生,用她的话说“把毕生都献给了写作”。[1]5狄迪恩的写作视野开阔,叙述独特,艺术性强,常给人陌生新奇之感。2004年狄迪恩完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奇想之年》,依然延续了这种叙事风格,被称为“丧恸文学的经典之作”,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部作品以丈夫约翰突发冠心病去世后自己陷入“丧恸”之中为主线,采用碎片化的叙述、时空交织的立体结构、情感的陌生化、以点带面的叙述视野等修辞手段,将“丧恸”这一情感表现得宏大而陌生,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本文拟从修辞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以求方家指正。
一、碎片化的叙述
2003年12月30日,狄迪恩和丈夫约翰在探望重症监护室的女儿回家后,约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发冠心病离世,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狄迪恩瞬间陷入巨大的丧恸之中不能自拔,后经长达一年时间的调整,才缓过劲来,最终动笔完成了非虚构长篇巨制《奇想之年》。而“丧恸”也成了贯穿全书的一个突出主题被作者反复提及。
一个人的“丧恸”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成为自哀自怜的倾诉人。众所周知,自哀自怜无论其体量还是其内涵充其量都是个人化的,其受众狭窄,社会化程度不高。但狄迪恩毕竟是老作家,她深知其危害,有意克服了这些弊端,以敏感的触角、成熟的思维、老练的语言以及丰厚的艺术修养将本属于自己私人化的丧恸之情体验处理得烽烟四起,博大雄宏,使得文本成为普通人关照婚姻、家庭、亲情、人生和生死的一面镜子,显示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性。
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说与她选择的叙述方式不无关系。狄迪恩所采用的叙述方式具体说来不是线性的,即不是以丈夫发病,抢救,治疗,死亡,埋葬,清理遗物,走出哀伤,开始新生活等一系列事件为线索,而是以自己陷入丧恸的情感变化为线索。而众所周知,丧恸是一种大的情感状态,它由许多更为细小的情感组成。这些细小的情感受时空以及人与物的变幻而不断变化,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换言之,在整个事件中,时空以及人与物什么时候出现,以何种形式出现,出现之后会让人想起什么,联想到什么这些都是不可把控的,是随机的,当然激起的情感变化也是随机的,把这些随机的情感记录下来,决定了文本的叙述只能是碎片化的。
那么,碎片化的叙述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收放自如。丈夫突然去世,狄迪恩陷入巨大的丧恸之中,在这种状态中任何一个与丈夫相关的人、物或者事情的出现都会引起她对往事的追忆,都会引起她心理或者情绪的变化,对此她并不回避,而是遇到什么人和事,引起什么情绪变化就写什么,完全遵从情感的流动过程,将事件的外壳打碎,让叙述呈现出开放的状态,收放自如。换言之,作品完全遵从情感自然发生的状态,不做删减和调整,但又能围绕核心事件展开,既放得开,又收得拢,体现了非虚构写作的基本特点。
以作品12部分(145页-158页)为例加以说明。
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按照先后顺序分别讲述了以下内容:与女儿金塔纳乘飞机转院到瑞斯克研究院治病——结束陪伴,回到洛杉矶夏天的生活——在家中收到丈夫同学寄来的丈夫中学纪念册——浏览纪念册的内容——丈夫四年级在学校的演讲——丈夫在中学参加合唱团的情形——纪念册中同学的讣告——上网搜索《普林斯顿校友会周刊》的讣告——丈夫用浅淡的铅笔印记罗列出小说《一无所有》中死者的名单——由浅淡的笔记想到了生的白与死的黑——兄长尼克死去的女儿多米妮克重病之后治疗的情景——朋友去世——重读《阿尔刻提斯》,思考生与死——打电话时翻到眼前丈夫去世前翻动的词典——收到普林斯顿寄来的丈夫的样书《真诚忏悔》——丈夫小说《竖琴》写作中两个人的交谈——想到丈夫去世时是不是也和他所写的一样经历了痛苦——一九八七年丈夫做心脏支架的情景。
以上就是12部分的全部内容,如果仅看罗列,相信给人一种缺乏逻辑的混乱感,不忍卒读,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因为乱只是表象,其内在逻辑一点都不乱。因为其内在逻辑是情感。换句话说,情感变化是有逻辑的,这种变化既不脱离事件,又能放任情感自由流动,具有收放自如,自然流畅的特点。
第二,强化了叙述密度,增加了文本的内涵。所谓叙述密度是指在很短的时间内讲述了大量的信息的叙述。如前所述,碎片化的叙述表面上看很乱,但因为遵从了情感的变化,而情感的变化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这就使得叙述不断向四处蔓延,既涉及家庭生活,又涉及亲情,既指向朋友,又指向工作,既面向过去,又顾及当下。一言之,碎片化叙述既涉及我与丈夫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涉及黑与白、生与死、婚姻与家庭、亲情与朋友、工作与学习这些社会问题,大大增加了文本的社会内涵,使得文本的内涵溢出丧恸之外,辐射到了更广阔的人生之上。
非虚构的基本前提是必须遵循事态发生的自然状态。情感的生发往往是碎片化的,遵循情感生发的这种特点,其实也就是遵循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作品能够被称为非虚构经典之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时空交错的立体化结构
《奇想之年》的叙述线索基本上是以时间的顺序展开的,即文本整体叙述的轴线是围绕作者在丈夫去世后一年内的生活展开的。但由于狄迪恩与丈夫毕竟有着四十年共同生活的漫长经历,在这期间两人居住地不断搬迁,同时也认识了不少人,经历了各种风雨的考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当丈夫去世后,这些时光痕迹和生活轨迹不可避免地激发作者追忆亡者的窗口与契机,将这些痕迹和轨迹连接起来,能看到时空密集交织的景象。对此,谭君强也认为:“生活就其整体性而言,事件的发生是立体的。无论就世界这一无垠广泛的范围还是一个远为有限的狭小范围而言,每一个‘当下’,都有无数的事件在同时发生。”[2]118是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无数的事件发生,这就是时间的流动性,也是空间的流动性,这也是《奇想之年》结构的基本形态。
《奇想之年》涉及的时间跨度远到20世纪60年代,近到了2004年10月,地点也很多,远到缅甸、巴黎,近到纽约、洛杉矶、加利福尼亚,这使得文本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宽广复杂。最主要的是,这些时间和地点都有具体的节点,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着的,是和自己、丈夫以及相关事件、人物相联系着的,有时间出现就有地点出现,有地点出现就有人和事出现,它们相互交织,构筑起了作品钢筋水泥般牢固的结构。
以作品的第5部分(62页-76页)为例分析。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提到的时间和空间具体交织如下:2003年12月22日至30日下午1时,一周,地点:贝斯以色列北院重症监护室,事件:女儿金塔纳因流感引起全身感染进行抢救;1964年1月30日,地点:加利福尼亚圣贝尼托县的施洗者圣约翰天主教堂,事件:作者和丈夫约翰结婚;2003年7月26日,地点:也是施洗者圣约翰天主教堂,事件:女儿金塔纳结婚;丈夫去世后的一两周,地点:家中,事件:作者看到家中的走廊贴满了照片,而这些照片的时间和地点各不相同,每一张都有具体的人和故事发生,作者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分别对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和发生的故事一一进行了追忆。这种大时段中套用小时间,地点也随之不断变化的结构方式,最明显的修辞效果就是使得文本的叙述经纬分明,看起来就像是用时间为经线,地点为纬线编织的一张大网,读者跟随叙述,流连在这样的结构迷宫之中,仿佛在时空的隧道中来回穿梭,看到的是不同的生活,体会到的是人生的各种况味。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采用这种时空交织的修辞方式,可以将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出现的人和事有效地连接起来,填塞满时空的各种缝隙,从而使得结构更加密不透风,给人以厚重稳健的好印象。
三、陌生化的情感表达
在丈夫去世后的一年时间内,狄迪恩一直都走不出丧恸的阴影,这让她充分领略到了丧恸的折磨和艰难,使她对丧恸所包含的情感有了更细微的体验。在狄迪恩看来,丧恸其实是比悲伤更深的一种痛苦。父母去世时,我们也难过,但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悲伤,只是沉浸在无尽的悔恨中,“悔恨逝去的时光,悔恨没能说出口的话语,悔恨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分担”[1]26,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去世带来的丧恸,而“丧恸没有隔阂”,“像海浪,像疾病发作,像突然的忧惧,令我们的膝盖孱弱,令我们的双眼盲目,并将抹掉生活的日常属性。”[1]27换言之,狄迪恩体验到的丧恸和常人有很大的不同。常人因为事不关己或是感觉迟钝对丧恸缺乏敏感性,甚至将丧恸平庸化,但狄迪恩本性敏感、神经质,现如今又处在这种状态,她感受到的丧恸层次更丰富,强度更猛烈,内涵更深刻,印象更惊悚,因此也更陌生。
为什么呢?南帆认为,这是因为“日常的现实磨钝了人们的感觉,人们按照习惯或者常识看待身边的世界,强大的惯性致使人们目光陷于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见的境地。人们的所有感觉都因为不断重复而机械化、自动化了。”[3]4感觉迟钝导致习以为常或熟视无睹,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文本表现平庸的原因之一。但狄迪恩不同,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她对世界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更何况现在她面对的是和自己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丈夫在自己眼皮下突然离世这样的突发事件,其突然的刺激和猛烈的惊吓都是前所未有的,她不可能若无其事,也不可能淡定自然,感受自然就十分强烈,和常人不同。具体到文本中,有如下内涵和状态。
麻木的冷静。2003年12月30号,当狄迪恩和丈夫从贝斯以色列医院看望在重症监护室抢救的女儿金塔纳回到住所准备吃晚餐时,约翰突然一动不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狄迪恩先是以为约翰只是被食物噎住了,接着看到约翰重重倒在地上,然后她打了医院急救电话,看着医护人员在自家客厅地板上抢救,再然后匆忙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这中间她像个木偶,机械地听从所有人的安排,麻木而冷静,用社工的话说“她表现得特别冷静”。[1]15其实,那不是冷静,完全是一个人面对亲人突然离世时惊慌失措的表现,还感受不到悲伤。
海浪般的窒息。“基本上每一位体会过丧恸的人,都会提及‘海浪’的症状。”[1]27这是一种什么症状呢?狄迪恩引用了20世纪40年代主持过麻省综合医院精神科室的埃里克·林德曼的研究报告做了描述:“躯体不适的感觉像海浪一般袭来,持续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喉咙发紧,因为透不过气而窒息,总想要叹息,有空腹感,肌肉无力,以及强烈的主观不适,通常被描述为紧张和精神痛苦。”[8]约翰去世后狄迪恩就经常感到这种症状,约翰去世七八个小时之后,她独自在公寓醒来,不知道自己昨夜哭了没有,只记得“事发之时,我进入了某种惊悚的状态。”[1]27
无穷无尽的自责。丈夫在自己眼前突然倒下离世,作为妻子狄迪恩慌张之后,冷静下来,开始反思。首先她感到自己有过错。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认为要么是自己没尽力,要么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总觉得自己要是能做点什么或多做点什么,都不会是这个结果。这种想法导致她陷入了无穷的自责中。比如在文本中她连用了好几个包括“我应该”字样的句子来表达这种情绪:“比如说,我应该取出约翰的病史概述,这样就能带它去医院。比如说,我应该熄灭炉火,因为马上就要出门了。比如说,我应该去排队。比如说,我应该想办法安排一张配遥测设备的病床,如果约翰要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他会用得上。”[1]28即便是后来从医院回到家中,她觉得她应该也有事情要做,“我首先应该把事情告诉约翰的兄长尼克”,我虽然不能告诉还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金塔纳,但“我应该告诉她新婚五个月的丈夫杰里,也可以告诉我的兄长吉姆。”[1]28“我应该”的另一层意思是“我不应该”,不应该无论从口吻还是意思都更像自责。自责使得丧恸多了些许沉重,这也是为什么事情过去了那么久,她还久久不能释怀的原因所在。
认知障碍和行为偏激。处在丧恸中的人,由于受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往往会出现认知障碍而行为偏激,但大家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病症。对此狄迪恩引用了弗洛伊德写于1917年的文章《哀悼与忧郁》中的话做了阐释:“丧恸的行为‘意味着要向正常的生活态度致以严肃的告别’”,“当它出现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从来都不把它当作一种病症,因而也不会寻求医疗帮助。”[1]33缺乏求助,任由情感发展是的狄迪恩出现了以下一些症状:1.人际交往恐惧症。丈夫去世,狄迪恩需要陪伴,但她却陷入了与人交往的恐慌之中:“此时此刻,我该如何应对他人的陪伴?”[1]29。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别人的关怀,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2.反胃。身体出现不适,“那天晚上我发现,只要一想到食物,我就会呕吐。”[1]34。3.拒绝。当她的嫂子琳恩给《洛杉矶时报》打电话刊登讣告,她表示强烈拒绝,因为“我能够应对‘尸检’,但还没有想过讣告。”拒绝别人的陪伴,拒绝送走丈夫的衣物,拒绝接受丈夫已经死亡的事实。4.思维混乱。在丈夫去世好几个月,冬去春来,狄迪恩意识到她常常无法正常思考,“我的思维方式犹如一个稚嫩的孩童,仿佛我的想法或是愿望能逆转故事的走向,改变最终的结局”[1]44。5.怀疑。在承认丈夫已经死亡,举行葬礼之后,狄迪恩仍然疑虑重重,对神学家认为“仪式也是一种信仰”的观点表示强烈怀疑,因为她遵循仪式举行了葬礼,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将他带来。”[1]2286.干预女儿的治疗。由于固执,狄迪恩对女儿的治疗方案和医生发生了严重冲突,干预女儿的治疗方案,反对医院实施造口术。7.较真。由于总觉得自己没做好,便到医院打印了丈夫抢救的记录,甚至找来大楼门禁日志加一对照,试图确认丈夫几点几分去世的真相,几乎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如此等等。
总之,不能不承认,上述这些情感特征和所作所为均已超出了正常人对于丧恸的态度,是病态化使然的结果,这就使得她的丧恸比常人多了几分坚硬而锐利的性质,直击人心,令人惊悚,让人陌生。与此同时,这些病态化的表现还大大强化了她的丧恸所具有的情感密度,把个体死亡事件所包含的思想内涵推向了更为深广的生活和社会领域,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意义。
四、以点带面的叙述视野
任何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写作视野。通常,写作视野决定了作品的容量、受众面和社会化程度。视野越宽阔,作品的容量越大,受众面越大,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则不然。视野的这种效果被众多作家所看重。然而,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轻易获得这种宽广的写作视野。很多时候,作家的写作视野由他的胸襟和修养所决定,胸襟决定视野的宽度,修养决定视野的厚度,一切均需要长期培养。从这个角度讲,狄迪恩显然具备这种胸襟和修养。《奇想之年》尽管事件的出发点很小——丈夫约翰去世,但狄迪恩却通过自己宽阔的叙事视野,成功地将读者带到了天南地北,带到了过去与现在,走遍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学到了各种知识,认识了不同的人,体验到了不同的生活滋味。
比如在第2部分,按写作的顺序作者带领我们学会了如下的知识、看到了她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体验到了大千世界不同人生:1.学会了心房颤动和心室颤动的区别,前者不会引发心脏骤停,后者则会;2.知道了医院对病人抢救的流程和秩序;3.体会到了陷入丧恸导致的神经质行为;4.看到了她和丈夫的日常工作交流;5.看到他们在布伦特伍德帕克游泳、写作、看电视剧;6.认识到了丧恸的理性价值和意义;7.体会到了自责和拒绝的心理。
再比如在第6部分中,按照写作的顺序作者带领我们经历了以下的生活:1.梦境与死亡有着密切的关系;2.防止出现认知问题,玩《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自救;3.惊悚于临近死亡的人的预感,追忆约翰说过自己活不了多久,进而回忆约翰做心脏起搏器的手术;4.回忆他们一起去巴黎领取圣餐的情景;5.回顾丈夫感到人生没有价值,自己没有在意丈夫出现的抑郁情况。
其实,不仅仅是以上两个部分,在整本书中,这种叙述也很普遍,而且每讲到一个地方、一件事情、一个人物都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或者丈夫的那个私人化圈子,而是尽可能地把视野伸向更远更广阔的角落,将个人体验融入日常生活,唤起普通读者的共鸣,将小众化的事件变成了大众化的反思,从而使得文本具有了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换言之,虽然我们读到的是作者一家人私人化的生活,想到的却是普通人都绕不开的生与死、亲情与婚姻这样的人生大问题。
借助丈夫去世这一私人化事件完成230页的非虚构巨制《奇想之年》,这在常人看来不可想象,但狄迪恩却做到了。这里面除了取决于事件本身的容量外,更多的还是与作者高超的修辞能力和灵活多变的修辞技巧有关。最突出的几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述过了,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并没有提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比如作品对主题的表达,采用复沓的修辞方式不断进行强化,使得文本的主题鲜明突出;比如作品采用圆点荡漾式的叙事思维,使得作品的叙述具有了形散神不散的特点;还比如采用已有研究成果和调查结果,使得某些观点的表达更理性、更客观,诸如此类,如果缺少了高超的修辞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不可能被读者所接受的。
其实《奇想之年》与其说是作者对丈夫的一种哀悼,不如说是对自己无可奈何的哀悼,因为正如她说:“我也明白了要继续我们的生活,就必须在某个时刻放手,让他们走,让他们死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