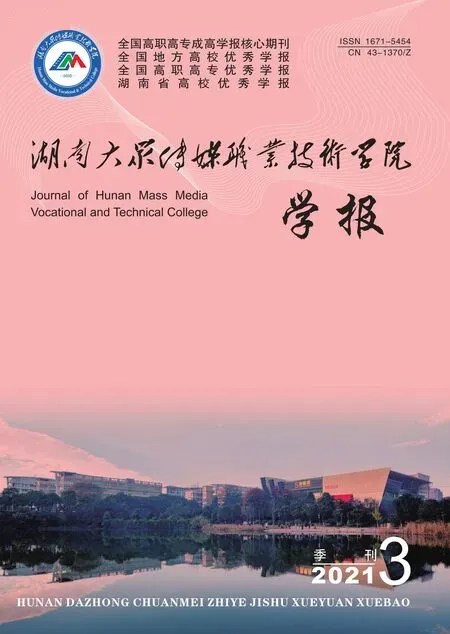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漫游者意象分析
赵红勋 王 飞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57001)
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极具典型性。在香港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王家卫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导演。王家卫的作品个人风格鲜明,其中,漫游者是一个反复指涉的电影形象,如《旺角卡门》中的阿华、乌蝇,《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阿飞正传》中的阿飞等。这些角色游离于都市空间之中,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香港的城市变迁及现代人心境的变化。在《东邪西毒》这部影片中,王家卫对典型意象漫游者的呈现成为其导演风格的显著特征。
一、他者凝视下的漫游者
“漫游者”(flaneur)是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通过波德莱尔作品所阐释的一个重要概念。“街道成了游手好闲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1]漫游者与街道、废墟、拱廓等空间有着高度的关联,尤其在现代化的都市空间中,他们仿佛被置于米歇尔·福柯所言及的全景敞视主义一般,一直处于他者的视角下被注视。在《东邪西毒》这部电影中,王家卫镜头下的漫游者意象不仅凝聚着香港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性特征,还隐喻着香港人身心的变化。
首先,作为他者景观的边缘漫游者。他者并非现实的他人,而是自我的一个影像或者投影。在精神分析学的范畴中,他者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对自我的构造,对作为主体的我们,对性身份的认同都是如此。[2]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漫游者成为现代化城市边缘的群体,多以失败者、浪荡子的形象呈现,并在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下逐渐汇聚成一个他者景观。他者景观并非一个图像的集合体,而是基于他者视角下的、客观化的世界。在《东邪西毒》中,欧阳锋、洪七、盲武士等人都是沙漠小镇的旅客,他们远离都市在沙漠小镇做着非法的工作。例如,欧阳锋因情感问题选择逃离白驼山来到沙漠小镇,白驼山隐喻着欧阳锋的都市生活,而他选择离开进行隐居;盲武士因妻子与挚友出轨而选择离开桃花,桃花不仅象征着他的妻子,也隐喻他逃避现实都市;洪七为赢得江湖名誉而离开妻子来到沙漠小镇,不惜委身刀客来博取声誉。他们都是沙漠小镇的旅居者,都逃离自己原本的所在而开始漫游者的生活。他们处在都市边缘(沙漠小镇),是各自心中都市/社会的观察者,只不过他们闲游的地点从街道、拱廓转移到荒漠。他们身处社会边缘地带,环视着周围的/过往的社会,同时他们也被别人的目光所凝视。在王家卫的镜头中,他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被凝视者。
其次,《东邪西毒》中的每个漫游者有着各自远离都市的往事。例如,欧阳锋在大哥的新婚之夜与大嫂发生乱伦关系,从此隐居在沙漠小镇;慕容嫣为追寻黄药师来到沙漠小镇;盲武士因妻子出轨而不愿归家。他们出于各种原因而选择游荡远离都市,却又嵌入社会的观察与干预,如洪七为女孩的一个鸡蛋而接受她的请求帮她复仇、盲武士接手铲除马贼的工作。此时的沙漠小镇俨然成为一个被法制抛弃的无主之地。欧阳锋、洪七、盲武士等人以社会边缘漫游者的身份呈现出来,他们充当着社会的观察者和现代性的反抗者,用游荡式的观察来审视外显的现代化景观,从而揭露出现代性的双面性特征,即在资本化时代下,香港经济腾飞的光明前景无法掩盖社会深层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心灵上的荒漠、情感上的孤寂等。王家卫借用追寻者(洪七)、逃避者(欧阳锋)、独立女性(慕容嫣)等角色,来丰富漫游者的构成。他们既游离于现实社会又介入边缘化社会,他们对正常的社会心存芥蒂,在边缘化的社会中一边探寻自己的目标,一边对现代性生活进行旁观性考察。正如欧阳锋在剧中所自述的那样,“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再翻过来,可能会觉得这边会更好。”这种拒绝融入、拒绝交流、拒绝幻想的角色,正是王家卫对于当时香港纸醉金迷背后迷失的青年群体发出的感叹。
二、漫游者的身体表征
身体是直观对象的最佳方式,19世纪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把人看作身体的存在。后来米歇尔·福柯继承了这一观念,把身体与权利理论糅合,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等著作中拓展了身体理论的研究,指出“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3]。王家卫镜头下的漫游者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身体,他们往往身着随意却追求豪华、沉默寡言却爱好吹嘘、面无表情却情感敏锐。这种矛盾的性格特征,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言的“他们都彬彬有礼、于众无害”[1]。在王家卫导演的影片中,漫游者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彬彬有礼、于众无害的外显表征,背后却经营着正常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工作,如《旺角卡门》中的黑社会成员、《2046》中的妓女、《东邪西毒》中的刀客等。这些漫游者的身体影像共同建构了镜像身体与社会身体相互交织映射的互文场域。尤其在影片《东邪西毒》中,欧阳锋、黄药师、洪七等漫游者集体游离于沙漠小镇空间之中的相互指涉,成为观众凝视漫游者的一个渠道。
首先,漫游者的镜像身体。在精神分析理论的视域下,雅克·拉康认为世界就是一个镜子,孩童最初并不具备“我”的概念,而是通过照镜子意识到“我”的物像,因此“我”从一个意象回归到象征秩序之中。在王家卫的电影中,“镜子”无处不在,身体自然成为观众最直观的客体之一。在《东邪西毒》中,一直以欧阳峰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开展叙述,导演这是在暗示观众,每个人都可能是欧阳锋,而观众也在观看过程中逐渐体会欧阳锋这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在爱情中固执、傲慢,甚至达到狂妄的地步;他被白驼山所抛弃,并保持着与社会之间的疏离与隔膜,乃至情感上的抗拒状态;他以高傲的姿态来睥睨他人,又以精明的商人自居给往来旅客介绍他的生意。他的身体意象是具有普遍性的——不着调的着装、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的性格是具有普适的——冷漠的神情、利益至上的心理,这些都使得观众能够切身体会到现实社会的冷漠与逐渐原子化的个体,“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界限在区域模糊并逐步消融”[4]。同样,其中的黄药师、慕容嫣、洪七、鸡蛋女、盲武士等人物都变成了“镜子”。“身体必须栖居于某个特定的地方,给我们一个感知或观察的视角。”[5]《东邪西毒》中漫游者的身体镜像能够让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在《东邪西毒》的镜像化身体中,各个角色既具有漫游者的特征,又具备审视现实生活的经验。
其次,漫游者的社会意义上的身体。在电影中,漫游者的身体不仅具备镜像层面的含义以映射现实生活,还具备社会层面的价值,“社会上主要的政治问题都反映在身体上,而且通过身体来表达”[6]。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飞涨带来消费主义的侵蚀与情感的荒芜。《阿飞正传》《旺角卡门》《花样年华》等王家卫执导的影片,无一例外地都在讲述经济发展的环境下香港如何面对变革。《东邪西毒》是王家卫于1994年拍摄的电影,在香港回归前夕,它不仅隐喻了香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欲横流,还蕴含着面对回归的复杂心情——以何种心态来回归祖国的怀抱。由此从社会意义的范畴出发,王家卫在《东邪西毒》中打破了单一的身体隐喻传统,对其人物的容貌、神情、性格、经历都并未过多介绍,而是致力挖掘人物所处境况的心境变化,靠细腻的独白塑造出一个个不能融入正常社会的漫游者形象。在影片中,欧阳锋细腻的情感、丰富的心理活动使观众不由得以代入感来看待他的经历。此时,欧阳锋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个体的身体符指,而可以视为当时的香港——分离已久,终要回归。
三、漫游者的身份赋予
在社会学的意义范畴中,身份既是个体进入社会诸多场景的外显表征,又是呈现差异的重要标识,因为它能够揭示“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7]。在《东邪西毒》中,“我”视角贯穿叙事始终,它以个体视角为表征,用“我”来讲述正在发生或经历的事件,其身份的建构也依附于自身的话语权力,并通过自我身份的更替来映射现实香港社会群体的身份变迁。如影片开始时,欧阳锋便以主人翁的姿态介绍沙漠小镇,尔后出现欧阳锋的特写镜头。此时他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出现,向顾客介绍他的杀手生意,他的身份界定也是在其叙述视域来展开的。欧阳锋作为一个典型的漫游者,其身份必然是以被凝视、被压制的方式来呈现。他的身份建构一方面源于自身,另一方面依附于他人的话语权力。
再如,影片中慕容嫣作为沙漠小镇的边缘漫游者,通过“我”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身份,即以“大燕国贵族”身份自居。她与黄药师喝酒时,以男性装饰出现的“慕容燕”成为“我”视角下的身份。而当黄药师说出“你要是有妹妹,我一定娶她为妻”时,她的主体性便被解构,随之替代的便是自我身份的变化——朝向女性转变。此时的慕容嫣/慕容燕是缺乏主体性的,她的主体性完全取决于他人的看法,以至于她把欧阳锋幻想成黄药师,并向其询问“是否她是黄药师最爱的女人”。得到欧阳锋的回答后,慕容嫣便离开了沙漠小镇,江湖中也不再有慕容嫣或慕容嫣,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剑客——独孤求败。此时的孤独求败具备了自身的主体性,而镜头中慕容嫣与独孤求败的身影交替变换暗示着其主体性的逐渐独立。她不仅是个体身份的代表,还是王家卫镜头下香港青年群体的缩影——似乎没有过去也没有结果,唯有复杂的情感使其追寻自己的身份并逐渐脱离他人的描述。慕容嫣的亦男亦女的身体,也交替讲述着她在自我身份追求上的努力,从“大燕国的公主”到“黄药师最爱的女人”,再到“孤独求败”,都是她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她的身份追寻隐喻着香港青年群体对于自己身份的疑问与渴望,而王家卫在影片中以“孤独求败”的身份赋予来完成这种身份界定。
换言之,《东邪西毒》中漫游者对自己身份的探寻贯彻始终,不仅仅是慕容嫣,欧阳锋、洪七、盲武士等人物都是来寻求自己身份的。洪七在面临鸡蛋女的请求时,回归自己本来的身份——侠客,而并非一个单纯的杀手,并与妻子回到社会之中;欧阳锋在得知大嫂死亡后,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最终烧了旅店回到白驼山;黄药师尽管处处留情,最后也明白了自己的心意所属,回到桃花岛;盲武士在临死之前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却为时已晚。在王家卫的镜头下,各个角色尽管散发着追悔莫及的情绪,最终都回归到正常社会的象征秩序之中,并逐渐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而并非一直游离于社会边缘。
纵观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从最初的《旺角卡门》,到随后的《阿飞正传》,再到《东邪西毒》,关注的角色大多是都市生活的漫游者,而他们的情感生活、物质状态无不反映着现实香港的生活状态。正如美国哲学家阿诺德·贝林特所言,“电影超越塑造了构成人的现实的知觉素材”[8],漫游者这种意象为导演提供了表现的素材,对观众而言则是审视社会的一个题材。漫游者意象直接、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的精神面貌,并介入观众对于当下社会的反思中,这正是王家卫导演通过电影想要诠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