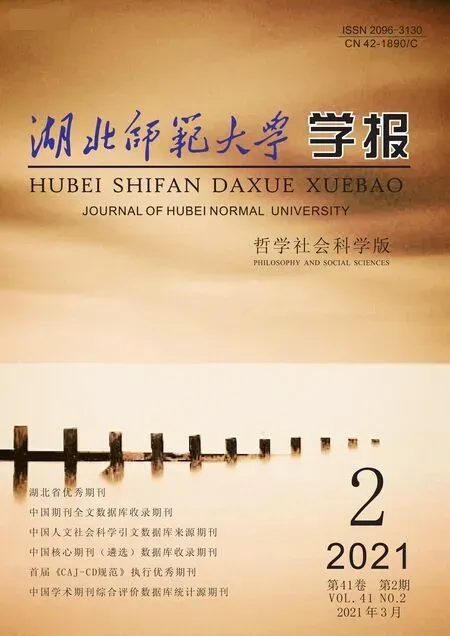城市经验与哲思性书写
——王威廉小说论
姚耀飞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引言
与其他80后作家以青春和成长为主题不同,集学者、作家、评论家于一身的王威廉在书写城市的同时进行深刻而鲜活的哲理思辨。
“作为迅速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王威廉)的写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拓宽了小说这种文体的可能性”(谢有顺评论语);“王威廉的中篇小说叙事充满思想和艺术张力,语言既有形而下的鲜活感,又有形而上的思辨度,其对人性的解剖鲜血淋漓,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与震撼力,显示了诡异而神秘的气质”;[1]“王威廉:思辨的现代主义者”。[2]这些评论都展现出其“思辨”特征;而更多的研究将指向其书写内容与表现主题,如生存困境、虚无;写作手法,如荒诞书写、灵魂叙述、比喻手法的运用、第二人称叙述;单个作品的解读和小说创作观的研究。诸多研究为我们深入解读王威廉作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展示出王威廉创作的丰富性和小说内蕴的深刻性。
王威廉从西北小镇来到广州求学,对于城市表现出既向往又畏惧,既渴望又排斥,既熟悉又陌生的多维的情感,有了现代化城市中个体的撕裂和无力感的体验,他“以内在于城市的视角的”的立体城市书写,展示他视域中的城市生活及城市人;而作为学者,他并不止于对城市做简单的展示与描绘,而是力图超越传统城乡的二元对立,使得文学的反思功能建构在非常鲜活的生命体验之上。
二、书写城市人的困境
王威廉自2007年以《非法入住》进入文坛,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创作发表了中短篇小说30多篇,内容涉及到现代人的精神困惑、青春理想、历史记忆、生存困境等。纵览之,其小说多取材于城市,将故事发生场域放置于现代城市,如《北京一夜》中的北京,《水女人》《老虎!老虎!》《父亲的报复》中的广州,《你的边际》中的成都,然而更多的是指向并不明确的现代城市,如《全世界受苦的人》《铁皮小屋》《飞升的雅歌》中没有具体的名称但充满着商业的喧嚣和生活的艰难的城市,这正是中国城市的真实写照。
对现代城市和城市文学,王威廉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期待:“现代城市不再仅仅意味着地理学意义上的闭合空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开放的、没有边界的文化空间。……城市文学不能是一种仅仅针对城市的文学,它针对的其实注定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成熟的城市文学要以内在的精神关联塑造出当代中国的整体景观。”[3]
这里城市不只是一种地理空间,更是一种生活和思维方式。“城市在作家的叙事中获得了更多的人性温度,渐具一种生命形态的自足性”。[4]在王威廉的小说中,城市不止是一种故事发生的场地,更是一种写作场域和叙事视角,如《北京一夜》中北京的深厚与包容,《父亲的报复》中广州的排外与自傲,《你的边际》中成都的悠闲与诗性,《梦中的央金》中青海湖的澄净与淳朴,《飞升的雅歌》中小镇的浮躁与自律,让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文化的建构与呈现的功能。
科技快速发展,全面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悄然介入到人类的精神世界,“技术成为了一种难以察觉的意识形态,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5]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威廉开始关注科技对现代人生活的影响,创作了一系列有关科技的作品:《没有指纹的人》直指指纹技术,《当我看不见你目光的时候》展示影像科技,《后生命》关注大脑芯片、克隆技术,《无据之夜》《你的边际》关注智能机器人在写作领域的表现,《退化日》涉及到地图导航、智能驾驶、人脸识别、技术监控技术。
科技所带来的改变远不止科技本身,同时也催生出了科技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在相辅相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冲突,成为世界发展的极大障碍。这种冲突体现在各个方面,只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让这种冲突变得更加隐蔽,并以一种方便的形式进行伪装与掩饰。
《没有指纹的人》中指纹科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应用极大地方便我们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异端,指纹科技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勤、汽车指纹锁、买房、银行支付等,指纹成为个体身份的特征,同时也是个体获取生物身份和社会身份的主要途径,在这过程中,科技对个体自由空间不断地逼迫与压缩,生活的便捷多了、诗性的空间少了。
如果说《没有指纹的人》还是停留于科技对人自由空间的压制,《当我看不见你目光的时候》和《退化日》则是反思科技对人所带来的逼迫感和随之而来的人性的物化。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像给人更多的是管控,监控所带来的是被监视的压迫与束缚,同时,监控权力所带来的偷窥的狂欢,使得保安职业的文樱父亲沉迷于此,最终走向极端而被捕入狱;而游戏所带来的快感让男友乐此不疲,并最终也迷恋上监控所带来的权力快感,然而最终受不了被人监控而自杀身亡;《退化日》中的我因受不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所造成的压力,最终辞去了看似轻松体面的生活。在科技无处不在的城市中,人的自由、经验、记忆、主体价值进一步压缩与丧失,人逐渐成为科技的附属与控制对象。
《无据之夜》和《你的边际》中关于智能机器人写新闻报道、写诗在客观展示的同时也对此表示怀疑和惴惴不安,正如:“对这本诗集却依然带有轻蔑……,我的心情一下子糟透了……但是诗歌,是彻底无限的、微妙的、神秘的,并且与人类的至高天性——审美有关,如果冬心知道了机器人也在写诗,不知她会怎么想呢?”[6]
虽然如此,作为学者和作家,王威廉始终相信:文学永远不会被技术制服。因为人类灵魂的崇高存在是一切文学的前提与假定。
科技支撑下的未来具有无限的可能,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王威廉开始了他对未来的想象与思考:我们的现实同时经受着未来的侵袭,未来不再是时间之线的另一端,未来就是现在;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
《后生命》为我们展示大脑芯片下的世界,技术支撑下的意识可以克隆与移植获得永生,但作为个体却一直拒绝和排斥着这种意识的永生,最终以李蒙的大脑芯片研究的失败来否定了人类可以轻而易举永生的假设。
在城市的快速发展裹挟中,诸多农村群体被纳入城市生活,同时诸多外来人员主动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个体,他们是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在城市理性而紧密的秩序之中显得格外无力,呈现出无根的游离状态,“生命与时空的关系变得不再像农业文明那样是固定的、情感的、诗意的,而是无根的、游离的、偶在的。”[7]在这种丧失家园与身份的无根状态中,个体要面对自己的身份失衡问题,即怎么在城市里面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
在这种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有人继续漂泊、无所适从,如《辞职》中的我;有人却以抗争来赢得自己的尊严与身份,如《父亲的报复》中的父亲,《看着我》中的我;有人选择妥协,如《谁是安列夫》中的安德;有人选择逃离,如《城市海蜇》中的张锋、《倒立生活》中的我和神女,有人选择失忆,与过去进行切割,如《水女人》中的丽丽和方文、《病足》中的瘸腿男人。据此可知,在王威廉笔下,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精神需求,底层的劳动者、小职员他们希望获取城市的接纳与许可,进而获取城市生活的现实通道;知识分子需要进一步获取发声通道和话语权,进而实现其影响和改造社会的理想。安列夫是著名的传记作家,丽丽是图书编辑,掌握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在现实中他们也经历着个体身份迷失和寻求的努力,如安列夫被宣布死亡,不得不以安德身份生活。
在王威廉的笔下,现代的社会生活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城市是现代人灵魂的聚集地,但也正是在这里,人们迷失自我,丧失自我“人”的属性。
《谁是安列夫》中,安列夫对自我认同的焦虑;在《看着我》中,图书管理员存在感的缺失;在《父亲的报复》中,父亲以抗拒拆迁来证明自己比本地人更热爱老街;《秀琴》由于精神失常,成为一个寻找自己的女人;而《水女人》中丽丽在丧失记忆之时一次次地追问着“我是谁”。
与自我迷失对应是真实身份的隐藏与掩饰,秀琴因为对丈夫的挚爱而把自己当成丈夫,替丈夫活了十几年;《魂器》中姐姐(梅香)因为自私而把陌生的我当作妹妹(梅清)的未婚夫,我被迫成为她人的魂器;《城市海蜇》中张锋因为无法忍受现实逼迫而以整容伪装成女友,《谁是安列夫》中安列夫因他人的报复而不得不假名为安德;《没有指纹的人》中的我因为没有指纹而不得不盗用同学的指纹。
这种群体性的身份迷失与寻求,正是城市中的个体的不断物化现实与精神自由空间的艰难寻求的真实写照。身份认同作为现代人的又一困惑,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个体的身份认同焦虑成为当下生活中颇具普遍性的现象。
知识分子作为城市中特殊的群体,有体面的职业,有稳定的收入,使其没有太多物质上的困扰;拥有部分话语权和有效的发声通道,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和使命感,同时也多了份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然而在城市生活中,在一个竞争无度、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知识的效用却极其有限,既不足以丰盈自己也不足以改变社会,现实中他们也面临着高房价、学区房、物价不断上涨等生活困境,精神上也面临着虚无、孤独、无力感等困惑。有在快节奏生活中的无所适从,如《老虎!老虎!》中的老虎在北京曾多次自杀;有因感情缺失而失衡,如《内脸》中的女上司、《水女人》中的丽丽、《北京一夜》中陆洁和家桦;有因失去生活目标而感到虚无,如《铁皮小屋》中的孔老师。王威廉笔下的知识分子困境有来自精神和情感上的困惑,更多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
更为指向性明确的是:王威廉笔下一批接受人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了群体性失败,或自杀、或被杀、或杀人、或放弃、或被排斥和边缘化,如《铁皮小屋》中诗人身份的孔老师自杀身亡,《你的边际》中火锅店老板诗人被杀、诗人齐冬心逃离,《水女人》图书编辑丽丽的失去记忆,《看着我》中的诗人杀死上司、《我与世界的连通器》中图书管理员的被排斥,《北京一夜》中陆洁不再写诗,他们或是诗人、作家、编辑、图书管理员,其受接受的人文教育在这商业的城市中,并不能给予人们谋生的技能,让人们在层级化的社会结构中走向权力和利益金字塔的顶端。相反,它们加深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的冲突。
而更多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问题之时束手无策,尤其是在面对人的精神困惑之时,很多时候既不能自我救赎,也不能开导他人,如《我与世界的联通器》中的我选择与他人偷情来逃避现实中的困境,《老虎!老虎!》中作家的巴特尔无法走出失恋的寂寞而要求他人分享,《捆着我,绑着我》中的女作家对于业务员的精神困惑束手无策,唯有以捆绑的方式帮其对抗虚无,《无据之夜》中作家的我在面对师妹自杀时也无计可施,唯有眼睁睁地看着小师妹跳河轻生,《老虎!老虎!》中作为同学的我们(记者和作家)均无法为老虎开导,而唯有看着他跳江自杀,《身体在黑暗中发光》中的我也无法开导嫂子,进而一同步入叔嫂情感迷失。
三、 寻求精神的自由
作为人文学者,王威廉小说中有诸多形而上的哲理性话语,不断地发问与反思,从而使得小说具有哲学反思的深度。作者在书写科技中的人、城市中的外来者、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生存困境时追问:在现代化城市普遍的物化背景下,个体如何实现精神的自由,作家如何实现精神的自由?
王威廉在《文学的思想》中写道:“人是没有庇护的存在,也许在人的孤独之途中,他所寻找的只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据点。……当我们不断向内心深处挖掘的时候,我们反而以一条奇怪的道路靠近了那个悬浮着的庇护所。写作,与许多事情一样,便是这样的挖掘。”[8]
有此信念,王威廉小说中有诸多与文字工作相关的群体(诗人、作家、记者、图书编辑、图书管理员),他们或直面生存的困境,如王木木、齐冬心、丽丽;或以旁观者对城市底层人予以关怀,如我对秀琴的叙述;或以精神的庇护者对他人予以帮助,如女作家对业务员生活的介入。
在书写城市之时,作家为我们展示出诸多艰难生存的个体群,《城市海蜇》中逃离大城市的张锋,在小县城依旧无法得到心灵的安放,因此他选择隐藏自我来进行逃离;秀琴夫妇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谋生,然而城市给予她们的却是屈辱;李金在城市中遭遇挫折之时选择了去远方寻找精神的涤洗;《铁皮小屋》的孔老师在获得学术上的成功后依旧无法摆脱虚无与黑暗的吞噬;《信男》《我与世界的联通器》中的图书管理员在困境的现实中无以应对,进而患上了社交障碍症;孤独中的业务员、郁郁、大山,他们都是一个个没有庇护的个体,裸露于现实和精神的困境之下,他们需要用文学的力量来实现精神的庇佑。因此,王威廉小说中常常出现写作和写信的行为,他们或以写作为杖,或以书为镜,从写作和阅读来获取精神的支撑,实现自我的救赎与解脱。如《云上的青春》中的我以写作来对抗青春的迷茫,《书鱼》中的老中医用大声阅读古书来治疗书鱼之疾,《信男》的王木木以写信来对抗现实的困境的压抑,《辞职》中鹳的父亲用写诗来舒缓职业对心灵自由的压制,《你的边际》中冬心在历经童年时刻的至暗时刻,试图以文学(写诗)来走出自己的困境。
如此,这种写作行为就有着更深的寓意,同时也看到王威廉对这种以写作来实现拯救的信念的并不坚决和犹豫:《铁皮小屋》中的孔老师最终仍是自杀;《看着我》中“写诗的我”最终将上司杀死;《无据之夜》中作家对师妹的轻生也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师妹轻生;《捆着我,绑着我》中女作家只能以捆绑来帮助业务员对抗虚无;《老虎!老虎!》中阿华写诗也没能阻止老虎的自杀;《身体在黑暗中发光》中的我并没有以写作来完成对嫂子的拯救,而只能以肉体暂时狂欢来对抗死亡所带来的黑暗与虚无。
作家以写作来达到精神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自我告白;只有不断地精神思考才能进入自我心灵的最深处,而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才是作家获得的自由。
四、 深度现实主义写作
“我想一种能打动人的写作,就不仅仅要呈现经验,还要反思经验、穿透经验,才能让作品获得照亮的能力。这就需要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彼此介入、血肉相搏的写作方式,思想诞生在这样的辩论当中,像是光束探进了黑暗,事物不仅获得了形状和颜色,世界也由此有了维度与景深。这便是写作的深度现实主义。”[9]
在本节计算中,均取H=10 km,U=10 m/s;并均用格点数对垂直和水平坐标轴进行标注。其中,1个格距垂直方向为125 m,水平方向为500 m。本节中所取的a、b均为常数,且以H为单位。在本节的附图中图最下方的实线给出了地形相关函数f(x)的形状。
王威廉在书写城市人困境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惑,个体精神的虚无、情感孤独、彼此隔膜等,而这些精神困惑又被城市生活所掩饰,呈现出整体的繁华与热闹。
现代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学和哲学合流,即借用文学媒介,表达作家的哲学思考,王威廉从现代主义里寻找精神资源,力图将个体对生命的体验熔铸到这种叙述方式中;他发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荒诞,力图客观有效地呈现,在荒诞的社会里,如何抵抗虚无,寻找有意义的生活。
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荒诞与写实并存,自《非法入住》发表以来,诸多荒诞小说成为其展示对现实理解的主要方式,《倒立生活》《书鱼》《鲨在黑暗中》《没有指纹的人》《捆着我,绑着我》《市场上的鳄鱼肉》《后生命》以荒诞手法将生活中的某些不合理集中放大,进而对矛盾予以呈现与揭示;同时,在《沉默天使》《身体在黑暗中发光》《生活课》中却以写实的语言书写了身边的熟悉故事。这里,荒诞与写实都是其展示对现实生活理解的方式与途径。
同时也发现其荒诞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与借鉴,《信男》《我的世界连通器》《看着我》这三篇小说中的人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笔下的那些“不正常的人”属同一精神谱系;而其中出版社的“仓库”与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和“地下室”从具体造型和意义象征均有着诸多的相似;而《信男》对卡夫卡《城堡》模仿得明显;《获救者》与《1843年》有很大的相似,《捆着我,绑着我》取名西班牙电影;《佩索阿的爱情》以佩索阿的“自我分裂”为切入口,其进行主题与思想模仿;然而其模仿的背后是形式与内容的创新,有着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
王威廉的小说,虽然一贯强调思想性,却也不曾忽略可读性。他的小说,有严肃的思想探索,又经常会借鉴很多通俗小说的写法,努力让小说的乐趣和复杂性并行不悖。
许多小说以荒诞为主题和叙述,但在风格上,王威廉的小说在哲思的格调中保持了引人入胜和富有感染力的叙事特性。在具体的叙述中,并没有让可读性成为精神内涵传达的阻碍。离奇的情节和充满漏洞的解释并没有指向猎奇,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逼近生活的真实。
《内脸》作为现代都市爱情故事,有多边的情感纠葛、有权力下的男女关系,有脸与权力的对应关系,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然而王威廉却并未简单止笔于此,将其简化成爱情纠缠的情感故事,也未俗套于权力与感情的游戏;而是将其升华为权力与脸的关系的哲理思考,并将这种思考以《第二人》中另一种叙述模式予以充分的展示。
《听盐生长的声音》《你的边际》同样叙述个人如何走出记忆创伤这一主题时却以不同的叙述来展现,《听盐生长的声音》中故事的推展完全掩藏于其抒情般的自我叙述和内心的表达;而《你的边际》中的故事则推动着哲理的展示,他们在面对过去“至暗”时刻所造成的情感创伤也都有逃离与回避,但都选择了个人的思想蜕变来勇于面对,从而实现个人的成长。
《梦中的央金》《禁地》《铁皮小屋》《父亲的报复》《绊脚石》中的故事完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的同时其哲理性明显:寻找央金行为本身就代表着都市中的现代人走出精神的困境的突围;走进“禁地”所体现的是人对自身束缚突破的欲望;铁皮小屋所代表的是毫无功利的纯粹阅读;父亲反抗拆迁行为是身份宣示与表达;《绊脚石》中安置铭记牌于路上代表铭记历史;《书鱼》中以传统医学来治疗“书鱼”之疾其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哲理表达。
然而王威廉笔下的虚构却常以“比喻”为旗号,表达着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哲理的表达,实现他深度的现实主义的“照亮现实和抚慰灵魂”的文学追求。
王威廉的小说有他独特的个人追求,它们具备一种特殊品质和能力,能将卑微人物的荒诞人生,演绎得丝丝入扣,并在荒诞和严谨的对峙中,饱含浓郁的时代忧思和精妙隐喻。
《禁地》中的“禁地”、《梦中的央金》中的央金、青海湖、祭海仪式、《信男》中的图书资料室、王木木的写信行为、《水女人》的失记、《书鱼》中的古老医疗方法、《鲨在黑暗中》的侏儒、《绊脚石》中的历史铭牌、《铁皮小屋》中的《中国现代诗歌选》以及县城的“铁皮小屋”都具有较强的象征功能,人物本身的设置、行为,其寓意都远超本身。
以隐喻之笔,书写荒诞现实,是王威廉小说的重要特征,但在荒诞的表象下,潜藏的却是他对生活世界的理性思考,并把个体对生命的体验熔铸到荒诞的叙述方式之中,并实现文学与哲学的合流。如《梦中的央金》的青海湖祭海,既是当地的一种祭祀仪式,更是一种现代人所需要的精神洗礼;《禁地》中的军事基地既是当地人无法接近的禁地,更是一种个人难以接近和实现的禁地,其中我对其的向往与突破更具有哲学表述的内蕴。
五、 结语
80后作家王威廉,其作品有时代的烙印,更有个性的凸显,正如评价“以飞扬跋扈的想象力对抗虚无与绝望”,表现出其对时代的理解和文学的担当。
同时,他集学者、作家、评论家于一身,其“小说呈现出诗歌的简洁、评论的理性和散文的细腻”,[10]展现了其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哲理性思辨。
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王威廉深刻地感受到“极度光鲜的城市外表与破败无助的底层生活之间的张力”,[11]对城市生存的艰难有着切身体会,以逼真的实在感书写城市生活的艰难;虽然如此,但他始终坚信,文学的价值与情感力量,始终以文字表达自己世界的理解,用文字寻求精神自由,用文字庇护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