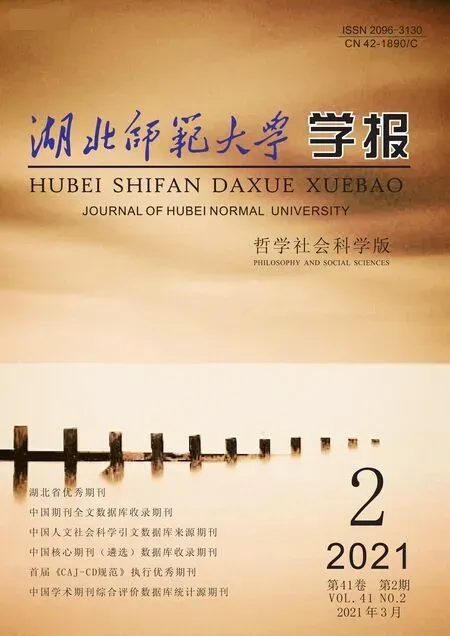意大利抵抗运动与战后欧洲联合
严双伍,徐遐舒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30072)
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之后,反抗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斗争也就随之出现。与欧洲其他国家抵抗运动比较,意大利抵抗运动有着明显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在与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做坚决斗争的同时,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较早地就开始思考战后欧洲的未来,明确提出了战后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政治主张,努力在欧洲抵抗运动中广泛传播这一思想,并积极推动欧洲各国抵抗运动联合起来。
一、意大利抵抗运动中的欧洲联邦主义代表人物
二战期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在遭受法西斯直接侵略战事失败后才逐渐兴起了抵抗斗争。但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法西斯专制统治建立后,不少进步人士就开始了抵制和反抗。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为意大利的解放和战后建设一个新欧洲而鼓与呼。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各国,意大利的联邦主义者可谓卓尔不群,出现了若干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
卡尔诺·斯福尔扎(Carlo Sforza,1873-1952),意大利外交家。1940年6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他经英国最后辗转到美国,在美国继续进行反对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斗争,加入了反法西斯的“马志尼协会(Mazzini Society)”,联合海外各派反法西斯力量,成为“自由意大利”运动的领袖。1942年8月,他出席在乌拉圭召开的“美洲意大利人大会”(Italian-American Congress),提出了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意大利的“八点议程”(eight-point agenda )。会议通过了这一议程并确认斯福尔扎为意大利美洲反法西斯组织的精神领袖。斯福尔扎著述丰富,出版有《欧洲独裁政权》《当代意大利,或欧洲合成体》《真正的意大利人》等著作,以及大量的抨击和批驳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文章。斯福尔扎在1943年盟军解放意大利南部后,于10月回国。1944年4—6月任巴多里奥(Badoglio)临时政府的不管大臣。
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1881-1954),著名政治家,二战后曾连续八次担任意大利总理。战争期间,他积极从事抵抗运动,所领导的天主教民主党抵抗运动组织成为意大利重要的一支抵抗力量。在政治主张上,天主教民主党在各类政策声明中,均明确强调“国家 主权原则已经过时,将来必须予以限制。”该党在1943年7月发表的“天主教民主党关于战后重建的若干主张”(Idee ricostruttive della Democrazia Cristiana)中,提出应组建一个“具有洲
际和国际联系的联盟组织”——它与国联不同的是拥有超国家的决策权,以及一个由各国政府和公众代表组成的联合议会。[1]1943年盟军解放意大利南部后,加斯贝利在巴多里奥临时政府中曾担任外交大臣。
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i,1907-1986),出生于罗马,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和最具代表性的欧洲联邦主义者,被誉为“欧洲联盟奠基者之一”。1938年他决定放弃青年时代的信仰,脱离共产党。在文托泰内岛囚禁期间,经狱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推荐,他开始接触到联邦主义的著作。最初读的是路易吉·伊诺第[2]1919年化名撰写的两篇短文,文章批评当时刚刚成立的国联,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不充分的国家之间的联盟,作者提请人们注意美国的联邦制。对斯皮内利产生影响的还有英国“联邦协会”成员、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两本著作——《计划经济与国际秩序》和《战争的经济原因》。从这时起,斯皮内利转向了联邦主义,他确信自己“找到了创造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广阔天地”。[3]斯皮内利认为,欧洲现存的政治学说,自由、民主、政党、社会主义等,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演进中产生的,本质上都一味追求本民族的强大和自己国家的强盛,因此它们不可能克服和消除当代现实政治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对抗的深刻矛盾。斯皮内利的反复思考形成了他关于欧洲联邦的主张,认为只有建立欧洲联邦,才能终结极权主义的统治和避免欧洲崩溃的结果。只有在整个欧洲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才能实现欧洲的政治改造,实现欧洲联邦的蓝图。
以上三人只是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联邦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在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为建立一个新欧洲奋斗不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为实现其理想和目标而继续努力。斯福尔扎在意大利全境解放后,主持非法西斯化工作,担任咨询会议主席和后来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战后欧洲外交界积极推动欧洲联合事业。加斯贝利在战后多年担任意大利政府总理,在冷战开始的背景下,该政府对外积极推行欧洲联合的政策。马歇尔计划出台后,意大利政府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欢迎和接受,并明确地把该计划“看作是通向欧洲统一的基础性步骤”。1948年8月,意大利正式提出“斯福尔扎备忘录”,建议“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应逐渐向更高层次发展,其活动不应局限在经济领域,还应包括文化、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内容,包括建立一个法院,使该组织成为未来欧洲联邦的一个体系完整的核心。”[4]加斯贝利倾力推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设,与法国的罗伯特·舒曼、让·莫内、德国的阿登纳一起被誉为欧盟之父。1954年5月加斯贝利接替莫内担任欧洲煤铁共同体主席。斯皮内利则一生为欧洲联合而努力,战后他继续担任战时就成立的“欧洲联邦主义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不顾盟军占领当局的反对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宣传和讨论欧洲联合思想,吸纳新成员,定期出版《欧洲联盟》(L'Unità Europea)刊物,并致力于“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组织的创建工作。[5]在意大利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经过该组织的努力,制宪会议将“限制国家主权的必要性”写入了宪法第11条。斯皮内利20世纪50年代发表《欧洲联邦主义者宣言》一书,通过对民族国家的批判,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联邦主义的政治目标,即通过制定一部确定国家联盟的组织形式的宪法,把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转让给一个跨国共同机构。他在剖析欧洲现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欧洲合众国是欧洲人对历史向他们发出的挑战所能做出的惟一回答。建立欧洲联邦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的呼唤和回答,这种呼唤要求欧洲各国人民变成一个单一的欧洲人民。”斯皮内利在提出政治立宪主义主张的同时,坚持欧洲联合进程应当遵循社会契约论的模式。认为欧洲联邦应该是欧洲人民意愿的一种体现,即公民是构成“联邦共同体和各联邦国家的共同基础”。[6]由此可以看出,战后斯皮内利的思想已经实现了对战时思想的升华和超越。斯皮内利长期致力于推动欧洲议会议员的直选,终于在1979年成为现实。
二、“文托泰内宣言”
战争期间在意大利拉齐奥大区文托泰内小岛上,囚禁着大约800名政治犯,这其中就包括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领袖罗西和斯皮内利。他们在和一些狱友交流讨论的基础上,1941年2月两人写就了著名的联邦主义文献——“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7]其正式标题为《走向自由而统一的欧洲:宣言草案》。宣言开篇就把自由视为人类进步的成果,强调它是现代文明的突出原则,指出“曾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积极意义的民族国家的作用已经完结,已经退化,并导致了极权国家的诞生”,因为“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招致了它们中的每一个国家力图统治其他国家,这一主宰愿望必然的结果是最强大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宣言号召联邦主义者积极联合起来,为重获自由,“彻底铲除把欧洲分裂为各个主权民族国家的现状”,以便“建立一个将成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范围内出现的最伟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创造物的新机体”。这个新机体——“欧洲联邦”将有效地解决欧洲现存的诸多问题。在宣言中,作者还把欧洲的统一与维护欧洲文明联系起来,提出了划分进步与反动的新标准。进步便意味着全力承担起保护“欧洲文明”的职责并把欧洲推向统一,而反动则意味着与此截然对立。进步政党与反动政党的分界线已不再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民主,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社会主义这种形式上的分野,而是一种崭新的、实质上的分野,这种分野将两种人区别开来:第一种人把获取民族政治权力这一自古以来的目的视为斗争的根本目的,而他们这样做,即便是无意识的,也将有利于反动力量,将使民众激情的炽热熔岩凝固于陈旧的模子当中,并重新酿发过去的悲剧。第二种人则把创建一个牢固的国家联盟视为中心任务,把人民的力量引向这一目标,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后,他们将首先把这种权力作为实现国家联合的工具来使用。
宣言强调,法西斯暴政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正义力量走到一起,反对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必定胜利。但宣言不认为仅靠打败法西斯就能拯救欧洲,战后欧洲的两大任务一是实现欧洲统一,二是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如果战后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就不可能克服欧洲旧的固有矛盾。因此“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彻底消除欧洲划分为民族的、主权国家的状态,否则进步就只会是徒有其表”,斗争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宣言确信“欧洲联邦不再只是规范欧洲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可能”,而是绝对的“现实的要求”。并且认为,未来的欧洲联邦主义运动不是一种“夺取政权”的起义运动,而是通过签署条约,把社会改造进程全部纳入一个社会契约的模式当中。[8]
当然,“文托泰内宣言”所体现的联邦主义思想并不完全是斯皮内利和罗西的思考,他们从其他人的思想中受到不少启发,如英国“联邦协会”的文献,特别是意大利本国一些先驱者的影响,如朱塞佩·马志尼、本尼迪托·克罗齐、路易吉·伊诺蒂等。作为斯皮内利的前辈并与其交往甚为密切的伊诺蒂,在一战后就曾提出,欧洲各国应该效法美国,制定统一宪法让渡主权,以建立“欧洲合众国”。事实上,“文托泰内宣言”激进联邦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也并不系统和完善,甚至存在着不少偏颇。但是,这并不影响宣言的重大意义和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文托泰内宣言”通过抵抗组织的地下情报网络,被秘密传递到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抵抗组织。其后不久,斯皮内利和罗西又先后分别写就了《欧洲合众国与不同的政治趋势》(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and the Various Political Trends)[9]、《明天的欧洲》(Tomorrow’s Europe)、《联邦主义者的倾向》(Federalist Tendencies)等一系列宣传、讨论联邦主义的文章或小册子。这些文献均通过地下机构秘密油印出来,广泛传播到各地抵抗组织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鼓舞着抵抗战士为反抗法西斯统治和建立新欧洲而坚持斗争。
“文托泰内宣言”之所以诞生在意大利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绝不是偶然的,这其中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仅抵抗运动产生于意大利,而且抵抗运动中的联邦主义,它的‘欧洲主义’也是在意大利找到了最早的清晰表达。”[10]在思想史上,意大利学者一直对于从但丁到马志尼的那些精英所阐述的统一欧洲的方案感到自豪。近代那些追求意大利民族统一的仁人志士,也只是把意大利视为欧洲整体的一部分而已。从现实来看,不仅因为二战前意大利知识界的欧洲联合思想就已活跃,而且还因为二战中意大利的特殊情况所致。墨索里尼是将意大利绑在希特勒德国的战车上卷入战争的。1943年7月25日法西斯政权垮台后,德国迅速出兵占领北部,意大利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完全是德国人的摆设,而南部的巴多里奥政府由于在意大利的处置等问题上与盟国的分歧,加之意大利战场战事进展缓慢,南部管理功能实际上由盟国管制委员会掌控。
三、意大利抵抗运动组织关于战后欧洲联合的主张
在意大利众多的抵抗组织中,1942年成立的行动党(Partito d’Azione,该名称马志尼曾经使用过)是一个欧洲主义思想非常活跃的组织。该党是由早期一些抵抗组织分化、合并而来,如“自由义勇军”(Giustizia e Libertà)、“自由社会主义者”等,其欧洲观念,与激进的联邦主义者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行动党的基本文件是1942年6月4日发表的“七点纲领”,它体现的是“自由义勇军”和自由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主张。行动党的一些领导人虽然也非常熟悉“文托泰内宣言”,也主张“废除国家主权”“重塑国际关系和价值观念”,“与所有民主国家进行密切和持久的合作”,然而他们设想的“欧洲联邦”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认为在战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培养一种“欧洲联合的意识”。行动党还草拟了一份“欧洲联邦国家宪法草案”(Progetto di costituzione confederal europea ed interna),这是意大利人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欧洲联邦的宗旨、责任、权力和机构进行勾画的文件。[11]
由于看法的不同,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之间便出现了一场关于欧洲联邦的讨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纷纷在地下刊物上撰文,阐述自己的看法。1943年8月,罗马的联邦主义者专门编辑出版了刊载讨论文章的《欧洲联盟》第2期。埃季尼奥·科洛尼(Engenio Colorni)在他的“欧洲联邦宪章”一文中,提出关于欧洲联邦的目标和结构形式的观点。他认为联邦的主要目标应是保证国际和平,保证各民族的自由,消除经济自给自足,创建统一货币,废除殖民帝国等。为实现上述目标,联邦的结构形式应建立在“由各自由民族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政治机构”之上。[12]罗西则对行动党的“七点纲领”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认为它是“谨慎、中庸和不明确的”,如果消极地去等待一个“欧洲联合的意识在战后出现,势必将丧失建立联邦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罗西在回顾了一些意大利精英设法促进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后,建议联邦主义者充分地“运用他们对获胜国家当权者的影响”,争取“参与对国际形势走向的控制”。[13]
这场讨论直接导致了意大利“欧洲联邦运动”(Movimento Federalista Europea,缩写为MFE)的诞生,该组织于1943年8月27日—28日在米兰成立,是欧洲的第一个联邦主义者社团。实际上,“欧洲联邦运动”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其成员分别来自而且依旧属于各抵抗派别,只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早在文托泰内时期,那时的一些联邦主义者就商定,为避免与其他抵抗派别的矛盾,以“运动”的名称来代替“政党”,参加“运动”的成员其个人身份是双重的。在成立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中,包括一份“工作指南”(Direttive di lavoro)。指南建议,为推进联邦主义的欧洲观念,欧洲联邦运动应与“每一个进步的社区、党派以及各种团体建立紧密的关系”。该文件还第一次提出召开国际联邦主义者会议的动议(该会议后于1944年春在日内瓦召开)。以“工作指南”为基础拟订出来的“欧洲联邦运动总方针”,规定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在社会政策上持不同观点的成员彼此应该进行合作。会议还通过了由斯皮内利起草的体现《文托泰内宣言》基本精神的六点“政治纲领”(Tesi Politiche)。罗西和斯皮内利被共同推举为欧洲联邦运动的书记。[14]
欧洲联邦运动是一个意大利联邦主义者联系非常密切的小圈子。该团体的成立使各成员彼此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联邦主义的事业。他们以抵抗运动的喉舌《欧洲联盟》刊物为主阵地,不断宣传他们的主张和思想。考虑到当时信息传递、收集之困难,应该说该刊无论是消息报道还是政论分析、理论探讨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广度。《欧洲联盟》刊载的文章涉及盟国政策、战后计划、意大利对外战略、跨国合作以及联邦主义在国内外的发展等方方面面。其中一些理论文章尤其引人注意。齐奥尔齐奥·帕伊罗纳尔(Giorgio Peyronel)的“联邦主义、地方自治权和自治”(Federalismo, autonomie locali, autogoverno)一文,将国内的分权制与超国家联邦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斯皮内利的“意大利外交政策之路”(Le vi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表达了联邦主义者对南部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不同意见,认为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太过于民族主义化了。[15]另一联邦主义者M.A.罗内埃(Mario Alberto Rollier)则以笔名埃德加多·蒙罗(Edgardo Monroe)在“自由意大利”(L’Italia Libera)上发表了“欧洲联邦同盟”(Unione Federale Europea)的连载长文,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介绍联邦主义的思想。[16]在意大利全境解放即将到来的1944年初,罗马的地下组织出版了“文托泰内文件集”,并附有详细的说明介绍。
意大利其他的抵抗组织,甚至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部分人士,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观念。共和党是联邦主义者的坚定的同道人,“都灵协议”郑重声明他们完全赞同“欧洲联邦运动的目标”。在天主教抵抗运动中,欧洲联邦的思想主要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他们在1943年7月提出的“米兰宣言”中,开篇就提出在战后要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联邦”。宣言第一部分就指出:“在一个重新建立的国际社会——它是所有各国人民团结的表现——体制内,将产生一个由自由制度管理的欧洲国家联邦。在这个联邦中,除了政府有直接的代表外,各国人民也有直接的代表——各国人民在联邦中和在各自的国家中都有代表。”[17]比较起来,意大利自由党则相对含糊一些,其纲领在政治上只表示了对“任何形式的国际联盟”的支持,仅主张建立“一个欧洲经济联邦”。
四、意大利抵抗运动推动欧洲各国抵抗运动联合的努力
由于抵抗运动所处的极端险恶的环境,使得绝大多数抵抗组织的活动只能局限在本国或本地区范围之内。在必须严守秘密和独立活动的前提下,同一国家的抵抗组织之间进行联系已属不易,跨国的交流自然就更为困难。除非在战前彼此就很熟悉了解并信任,否则一般很难发生交往。但每一个抵抗组织都非常清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们是相似的团体。一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都坚持自己反抗暴政、捍卫正义的斗争,以其力所能及的各种方式与法西斯分子战斗;另一方面,他们都坚信胜利必定到来,战胜邪恶之后,必定有一个正义、公平和美好的未来。遍布欧洲各国的同类组织的存在,使抵抗运动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的斗争是一场超越国家范围的运动。1941年,各国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及其精英几乎用一致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认识,这就是“从英吉利海峡到爱琴海”正在进行的抵抗战斗是一个整体——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共同的敌人,他们都对人类尊严和法治原则抱有同样的信念,他们都把创建欧洲联邦(或某种欧洲组织)视为消除过去纠纷、永葆欧洲和平的惟一途径。1944年3月26日,法国抵抗运动领袖亨利·弗雷内,在其“战斗”组织的一次大会上就指出:“我所得到的大量证据表明,欧洲被占领的每一个国家,其抵抗运动的目标和希望同我们是惊人的相似。本来也是,我们怎么会有真正的差别呢?!年年月月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遭受同样的困苦,冒着同样的危险,进行同样的战斗。为了同样的自由和正义的理想与共同的敌人及其(反动的)价值观战斗。此外,他们和我们一样认识到,分裂是虚弱的根源,我们明天的力量一定来自于联合。”[18]同样,德国“克劳塞集团”的领导人毛奇,为同各国抵抗运动建立联系也在不断地努力。他先后与挪威的埃温德·伯格拉夫(Eivind Berggrav)主教,荷兰领导人范·阿斯贝克(Van Asbeck)、G·.J·斯科尔顿(G.J.Scholten),以及波兰克拉科克大主教萨皮耶哈(Sapieha)取得了联系,向他们转达“克劳塞集团”有关联邦欧洲的设想计划。毛奇相信,抵抗运动的共同目标将为未来提供所必需的团结。他认为“与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在战争期间的联系都是实践欧洲政策的一部分,是为新欧洲的重建做准备。”[19]
虽然各国抵抗组织都渴望彼此取得联系和加强合作,但客观现实却困难重重。根据掌握的现有资料,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不同国家间抵抗组织正式签署的协定,除了日内瓦会议的几份宣言之外只有两份,这还是在战争最后阶段德国的控制不断削弱的情况下方才实现的。一份是1944年5月7日,意大利东北部的“意大利阿尔托民族解放委员会”与铁托游击队的代表签订的互助条约。双方友善地将一条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留待以后在欧洲的“总体安排”框架中去解决。另一份是1944年5月,意大利皮埃德蒙(Piedmont)的抵抗组织和法国马赛地区的“抵抗统一运动”组织签署的协定。协定不仅规定了在军事上彼此团结合作,而且“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将双方战后欧洲重建的共同目标界定为:“在一个自由的欧洲共同体内致力于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20]
意大利抵抗运动领袖罗西和斯皮内利,早就在思考如何把欧洲各国抵抗运动联合起来,积极寻找各种可能存在的机会。经过反复讨论和商议,他们看中了瑞士作为中立国的地位可予利用的可能,希望在这里召开一次各国抵抗运动领导人的会议,以制定一个战后欧洲建设的共同计划。他们认为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应该从战争中获取教益,达成共识,而一个共同计划的制定,不仅可以统一各国抵抗运动的认识,而且将使他们的观点对盟国的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1943年秋,两人带着这一目的来到了瑞士。经过多方努力之后,1943—1944年的冬季,以“致全体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公开信”的发表为标志,终于形成了一个欧洲抵抗运动领导人联络交流的内部小圈子。罗西和斯皮内利赢得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邦迪的信任,通过邦迪,进而又结识了法国“抵抗统一运动”组织在日内瓦的代表让·玛丽·苏图。苏图促成了他们两人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总秘书长、荷兰抵抗组织与伦敦荷兰流亡政府之间的调停人威廉·A.维塞尔特·霍夫特(Willem A.Visser’t Hooft)的接触。[21]霍夫特立马发现意大利和法国抵抗运动的新欧洲思想,与自己多次表述过的观点竟不谋而合。他当即决定将自己在日内瓦的住所作为拟议中的会议的召开场所,但会议必须秘密进行,以免给希特勒提供侵犯瑞士中立的借口。
1944年3月31日、4月29日、5月20日和7月7日,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等九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日内瓦四次聚会,为战后欧洲勾画一幅各国抵抗运动都能认可的联邦主义的蓝图。出席会议的有意大利代表3人,法国代表2人,德国代表2人(从第二次会议时开始参加)、荷兰代表2人,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各一名代表。由于大多数人使用的均是化名,1名荷兰代表和后5国代表的真实姓名一直无从知晓。[22]3月3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采纳了“抵抗不仅意味着拒绝错误的价值观念,也意味着对积极价值观念的肯定”的原则,并据此一致通过了第一份宣言——“团结声明”。宣称因“同一原因所造成的一切牺牲和痛苦使得抵抗运动相互间产生了亲如手足的联系,在自由人民中诞生了新的欧洲团结的道德良知,维护这种团结将成为和平最基本的保证之一。”[23]在4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提交了第二份宣言的草案,试图准确界定欧洲联合体的类型。讨论“显示了意见相当的不一致”,分歧不是要不要联合体的问题(这一点并无疑义),而是在于要什么样的联盟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除了丹麦、挪威代表外,明确地将超国家联邦视为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原则。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一是“民族国家政府权力限制的范围”(意大利、法国代表期望走得更远),二是“英国和俄国与欧洲联邦的关系”。5月20日第三次会议经过讨论,终于达成第二份宣言的折衷意见,即“关于欧洲联邦的宣言草案”。在这份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文件中,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建立欧洲联合体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外交、经济和防卫职能在内的欧洲联邦政府,并规定任何保证民主体制和个人自由发展的欧洲国家或部分欧洲领土的国家均可获得成员国资格。[24]5月20日之后,两份宣言一起被尽可能多地送往各国的抵抗组织,并希望他们给予答复。在接下来的时间内,陆续收到了一些抵抗组织积极的反应,但在数量上比预期的要少。原因很简单,一是诺曼底登陆后,欧洲大陆迅即掀起了解放的高潮,而获得解放的地区又面临着建立新的政权结构的紧急任务。二是已经控制局势的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其政策拒绝考虑任何具有欧洲联邦色彩的要求。解放导致了民族感情的上升,流行的观点是盟国另有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决定了7月7日最后的一次会议无法产生新的成果。但是,在5月20日建立的负责联络的机构——“欧洲联邦筹备临时委员会”,却一直继续运转到1944年底,并出版了《联邦主义者欧洲》杂志。1945年春,该委员会更名为“争取欧洲联邦行动中心”,他们把收集到的有关抵抗运动的文件和材料,以《明日之欧洲》为题整理出版。25日内瓦会议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未能获得任何预计中的实际成果,但它却是欧洲联合起来的抵抗运动,渴求建立一个新欧洲的愿望的强烈表达。
综上所述,意大利抵抗运动孕育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联邦主义者,他们继往开来,以自己的艰难探索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为战后欧洲重建绘就出了一幅崭新的蓝图,为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历史功绩,值得今天的人们肯定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