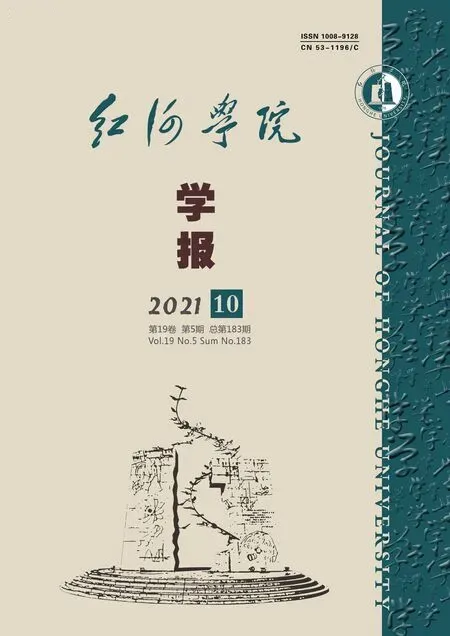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现状梳理及传承研究
——以乌铜走银工艺为例
王皓纯
(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昆明 650500)
一 乌铜走银研究背景
乌铜走银是云南独有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始创于清雍正年间石屏县,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民国《石屏县记》载:“以金及铜化合成器,淡红色,岳家湾生者最佳。按乌铜器唯岳姓能制,今时能者日众,省市肆盛行,工厂中有聘做教师者。”[1]在过去,乌铜走银工艺品多为文房用具,这与乌铜走银本身的材质与制作工艺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其材质以及复杂的工艺导致了其必将价值不菲,其购买人群主要是当时的一些具有经济能力以及文化内涵的上层人士和文人。所以乌铜走银产品多为文房四宝、烟具、酒具、茶具等上层人士使用的物品。这些器物大多呈椭圆形、圆形,具有原始的形态之美。其中文房四宝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文房四宝之所以如此普遍得益于其实用价值,乌铜走银将其自身的手工艺特点与文书工具相结合,不仅保留了其传统精髓,并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艺术。同时乌铜走银的装饰纹样也极具文化内涵,其中最具民族艺术特色的是匠人们将汉字以书法的形式融合到这一传统手工艺之中,这便是最常见的乌铜走银手工艺品。乌铜走银还有奇特之处在于每一件乌铜走银制品都会受主人把玩以及汗液的影响逐渐变化,黑色更黑,银色更亮。每一件乌铜走银制品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呈现出其独一无二之处。
二 乌铜走银研究现状
乌铜走银制作工序非常复杂,所需材质也非常昂贵,这导致其成品量非常少。如此昂贵的材质加之复杂的工艺制作出来的乌铜走银定价颇高。因此为达官贵人私人定制成为了乌铜走银的主要销售渠道,并且是唯的一渠道。现在,乌铜走银的主要生产模式仍是家庭作坊式,往往是一人身兼数职,不仅要制作还要负责销售甚至包括售后服务,而当今社会一个成功的产品背后依靠的是一个完整的经营团队,每个人分工明确,精益求精。乌铜走银图案装饰纹样也与当下生活几乎没任何关系,在造型的设计上似乎忘记了审美标准,但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传承人一味地依赖于传统造型,并没有积极去开拓当下的市场,对于自身的发展状况似乎过于满足和乐观。在装饰图案上虽下了一些功夫,但略显单一,并没有质的飞跃。装饰手法依然以大小、粗细均匀的线条来呈现图案,这种手法本身就缺乏层次感,难免让人觉得有些生硬。
乌铜走银造型老、装饰纹样陈旧,似乎存在其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令人堪忧。乌铜走银的大师可谓是人才济济,但大师们创作出的工艺品却大同小异。由于造型上主要依托传统的文房四宝、烟具、香炉、茶具、酒具、摆件等,装饰上更是常用的仿古纹饰,主题思想依旧主要用来表达文人思想和情趣、文人志向、富贵吉祥的人物山水、花鸟草虫、飞禽走兽、书法篆刻等。如此这般,即使大师再多,不加以创新,产品无非也就这些简单的搭配融合。如:云南昆明金永才艺术大师的墨盒制作团队制作的墨盒与云南省晋宁画家袁昆林大师、保山画家万光红大师所设计和制作的“不谋而合”。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2]。简单地说,乌铜走银在造型和装饰上过于保守,并长期传承过程中仍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创新性匮乏成为其当下发展的根本问题。乌铜走银的生产受限于其合金铜片保密性的影响,导致难以大规模生产,制作工序不仅复杂而且仍依托于手工制作,效率低而产量难以得到保证。乌铜走银产品的价格和器型致使其收藏和观赏性方面价值较高,但也造成实用功能性较低。乌铜走银制作工艺从古至今脉脉相承,但匠人们思想并无太大转变,前些年还保持着“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思想,对于创新技术不以开放的态度甚至产生抵触。这是工匠们对于传统技艺深入灵魂的尊重以及保护,担心新技术对传统工艺产生冲击和破坏,害怕手艺的精髓消失难寻。这是因为乌铜走银匠人们对现状过于乐观,没有意识到现在的社会变化,缺乏对潜在市场的开拓,也就缺乏对相应产品的投入和开发。
三 乌铜走银传承情景和困境剖析
目前,整个云南掌握乌铜走银技艺并且能够独立制作出来的匠人十分稀少,不超过10人,乌铜走银核心技术的传承一直是十分保守的,尤其是核心技艺的传承有很长时间都是实行单线传承模式[3]。这也说明了乌铜走银的传承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已经出现教育传承的模式,但因推出时间较短,所以还难以涌现一批成熟的乌铜走银手艺人。但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乌铜走银传承工作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不仅对熟练掌握这项手工艺的工匠颁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证书,也从多方面大力支持此工艺的传承。然而,乌铜走银想在当今这个电子信息大数据时代下生存发展,这只是一个开始。官渡古镇“金李记”标志着乌铜走银走出传统,开始积极转变,走向市场化运作。
现如今乌铜走银传承困境主要有三个方面:消费群体的滞后和生产效率问题及乌铜走银的定位问题以及宣传问题。乌铜走银制作受多方面的影响:昂贵的材质、复杂的制作工艺程序、全靠纯手工制成,造成乌铜走银产量低、价格高的局面。通过对乌铜走银的走访调研发现,其目前的消费人群仍然是以高端为主。这种思想无疑让乌铜走银的销路变得狭窄,难以扩张自身生存的市场,让自身发展举步维艰。装饰上的墨守成规,造型上仍依赖传统,缺乏创新积极性,影响限制其发展。而要想传承下去,占领大众市场是重中之重。当前形势下,想要工艺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就必须在原料、工艺、价格上进行革新。要充分了解消费大众的目标需求,以目标需求为导向,在原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泊,大众想要的或许只是乌铜走银的外在特点,而这些是可以通过科学的配方加上合理的做工就可以做到的,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要降低产品价格。当下,乌铜走银对于目标群体的认知存在偏差,导致乌铜走银存在滞后性,在了解目标需求上还需多调研多走访。与此同时,要将产品进行层次划分,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设计不同层次产品。一个乌铜走银产品需要一个熟练的师傅耗时一个月左右,一方面反映了乌铜走银制作的复杂工序,另一方面说明了纯手工制作导致的效率低下,并目前传承人稀少,根本无法满足大批量的乌铜走银订单的需要。所以在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前述大多传承人视乌铜走银产品都为高端产品,而如今所有的乌铜走银产品大多都被作为装饰品,几乎不具备实用功能,个别具备功能的烟具、酒具却价钱昂贵。为了扩大市场进行更好地传承,我们可以设计专门的乌铜走银生产线,可以大量机械化、批量化生产价低廉美的乌铜走银生活用品。乌铜走银的生活化同样可以为其发展传承提供重要作用。
四 乌铜走银传承模式思考
笔者通过对于金永才先生的采访了解到,目前乌铜走银的传承模式分为家庭和师徒传承模式,教育传承模式以及品牌传承模式。乌铜走银工艺最初奉行“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观念,都以家庭式作坊的纯手工生产以及掌握配方的人员极少,导致每年不仅仅乌铜走银的工艺品非常有限,而且掌握配方传承人也是极其稀少。但传至第六代金永才先生打破了传统的传承观念,首次创立云南省第一家传习馆——“乌铜走银传习馆”“乌铜走银工艺馆”,面向社会收徒12人。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陈旧观念,呈现师徒传授方式。除此,乌铜走银传承也具有区域鲜明性,现仅限于云南。由此可见,乌铜走银传承方式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虽然现在出现了师徒传承,但收徒的门槛也相对高。
不过,乌铜走银传承人也在对外交流中不断吸收养分,金永才先生首次提出:教育传承,将乌铜走银从传统的“家族传承”“师徒传承”转变到“教育传承”的高度上,并在教育方面提出新的理念,即“三品人生”。所谓三品人生,说的是人品、作品、精品三个层级。人品是第一位的。一件工艺品反映的是手艺人的气质,没有好的人品就不能打造出好作品。有了好的人品还不够,还要肯钻研,七八年才能出作品。要达到精品水平,再要打磨十一二年。人品的不断升华,使得对作品的追求不断提升,熟能生巧,巧能生精。精品不仅需要时间积累磨合研发,更需要制作人品与心术的正直,对作品的不断追求才能打造出精品。所以在此基础上金永才先生又将“师徒传承”上升到“教育传承”的高度,将乌铜走银引入高校的课程中,加大力度培养创新制作人才。2018年建立国家非遗文化“乌铜走银”人才培养基地落地到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按照计划,每年都将有不少于800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乌铜走银的制作工艺。接着又提出了昆明试点非遗传统技艺融入职业教育的理念。这也是职业教育与非遗技艺结合的首个案例,并且传承乌铜走银工艺是第六代传承人金永才大师为首的工艺美术专职教师团队。课程主要内容为乌铜走银线、打、顶、錾、踩五大传统技艺,让学生们充分了解乌铜走银的基础知识,并立志于将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乌铜走银匠人。传统手工艺想要不断传承,就要大胆走出去,让乌铜走银走向市场,这样一来工艺美术专业人才的缺失问题就迎刃而解,乌铜走银发展前景广阔,其工艺产品不仅在国内备受喜爱,在国外也是吸引了一大批收藏家。但是专业人才缺失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导致了供需不平衡,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消费者需求。现在的职业教育多为汽修、会计、导游等专业,但对于正在产业化蓬勃发展的手工艺产业却没有相关专业,工艺美术特色化、专业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不仅仅需要对于技术工艺的掌握,更需要吸纳其文化精髓,这就导致短期内无法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满足市场所需。如此背景下,手工艺人才培养需要重点探索如何将传统非遗融入进校园,吸引更多人才,进行专业教育,让传承人队伍日益壮大。
金永才将乌铜走银制作工艺引入高校的课程之中,这也是创造性转化下传承方式的一大转变,不再担忧技艺失传,也让更多对乌铜走银感兴趣的人接触到乌铜走银,学习掌握乌铜走银这门技艺,从而带给乌铜走银发展和传承更多的可能性。
以传承人金永才为例,其不仅全力做好了教育传承,而且一直在不断对乌铜走银进行创新,从“师徒传承”“教育传承”的概念转变到“品牌传承”的理念,创立了金大师&乌铜走银品牌,并提出可以提取乌铜走银的元素,用更好的方式去呈现,允许乌铜走银外在载体形式进行一定的改变,其改变的最终目的则是更好地传承、保留传统工艺,为消费者带来种类更加丰富的乌铜走银产品。这也是一种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的方式,使大众能够轻易地理解和接受,并且按照受众将乌铜走银在原有基础的种类中发展创新出更符合当今社会的样式。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高端收藏类,如文房四宝、香案供具、酒具、茶具、烟具、玩赏系列、其他;二是高端时尚类,如高端时尚首饰、高端时尚生活饰品及其他高端时尚品;三是高端旅游商品,如具有云南地域特色元素的高端旅游商品;四是高端礼品定制,如提供高端礼品的定制及定向开发服务。
在品牌宣传方面,以金大师&乌铜走银品牌为例,如今不仅仅与CCTV《探索发现》《我有传家宝》等这些电视栏目合作宣传乌铜走银,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乌铜走银这项传统手工艺,并且利用互联网平台,借助自媒体、新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和推广,定期更新、发布有关乌铜走银的知识与鉴赏小视频,真正让这门手艺成为世人皆知的文化符号,闻名遐迩。
以乌铜走银的家庭传承模式、师徒传承模式与教育传承模式和品牌传承模式对比来说,乌铜走银作为传统手工艺品,每年制作的作品非常有限,家族成员之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传统正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纯手工时间长,加上手艺人少,所以乌铜走银很难永久传承下去。传至第六代金永才打破了家庭成员之间传承的局限性,向社会招收徒弟,一方面增加传承人,让技艺传承更久;另一方面人数多,想法多,有益于技艺创新,不仅可以让作品越来越多,也可以让作品越来越好,精益求精。打破原有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让乌铜走银融入更多的活力,迸发出更好的作品。传承创新不断,从家族成员传承到师徒传承,让传承方式越来越多,使乌铜走银也能越走越远。金永才将师徒传承提升到教育传承。教育传承相较于家庭成员传承和师徒传承有四点好处:一是通过教育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乌铜走银,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二是吸引更好的艺术人才,从兴趣出发才能有更好的灵感,通过精心传承,发现更多对乌铜走银感兴趣的人才,使得更好地传承,也会做出更好的作品;三是培养新型技术人才。在市场不断开拓的环境之下,工艺美术特色化、专业性、技能型人才的输送无法满足工艺美术市场的需求,将乌铜走银工艺与教育结合,也是让教育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授传承虽然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但起码保证可以传承下去。那么师徒之间的传承可打破局限性,让乌铜走银走出门来看世界,让乌铜走银传承有了宽度,并教育传承则彻底改变了乌铜走银的维度,不仅使人才涌入,还使乌铜走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新性,让更多的人喜欢乌铜走银,也发现更多真的想学想传承的人。同时品牌传承则是让乌铜走银几乎随着时代永远前行,品牌的影响力,品牌的忠诚度,一方面保护了传统技艺,另一方面乌铜走银更让普通人可以接受,使艺术离大众更近,不再是展览馆中触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得的工艺品,保证了乌铜走银可以不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有更好的宣传力和影响力,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传承,也可以不断吸引“粉丝”,从而鼓励激励创新,实现手艺人与消费者之间相互激励,相互支撑,相互吸引。
五 乌铜走银传承经验总结
(一)重视手工技艺
乌铜走银是全靠纯手工制作的,所以技艺在传承中最为重要,最为关键,要将技艺做到炉火纯青,在传承中精益求精。因而在原有的技艺保护好,同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创新。
(二)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
好的技艺需要更好的手艺人。在传承过程中,技艺固然重要,但没有人传承不行,没有人创新更不行。要不断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保证技艺不丢失的情况下,更好地创新适应时代的变化,不能固步自封。我们可以通过与校企合作的方式,培养传统技艺传承人。对于乌铜走银工艺品在高校选拔的创新人才中,则重点放在艺术院校有美术基础的设计类专业的学生之中进行。这样才能选拔到有美术功底深、审美能力强、设计能力强的高创新人才。
(三)利用科技手段不断创新制作时代精品
如前述,乌铜走银材质昂贵,工艺复杂,制作耗时长,但产品实用性不强,导致大众需求量较低,所以要不断创新作品,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利用科技手段,生产体现时代特色的实用性强的民族文化产品,这样才能带动消费,增强市场竞争力,让作品被大众接受。
(四)打造民族工艺精品意识
其实这里说的也就是对于传统工艺创新发展的问题,使民族文化走出去,形成影响力。随着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断追求,精品意识对于消费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好的品牌可以更吸引大众的消费,打造精品可以保证工艺永远存活于大众的心目中。
(五)加大宣传力度
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感受到。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扩大乌铜走银的宽度,让更多不同领域的人了解乌铜走银;另一方面可以增长乌铜走银的长度,好的宣传可以影响产品的价值,使其长久不衰的传承下去。
六 结语
乌铜走银技艺具有民族灵魂、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是我们先辈们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将乌铜走银技艺传承、保护、发展的生态环境氛围,努力经营好是对先辈最好的敬意,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如果说传承是创新的前提,那么创新则是传承的目的。我们要想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跟上时代的步伐,并随着时代推移,不断创新,不断传承,让经典永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