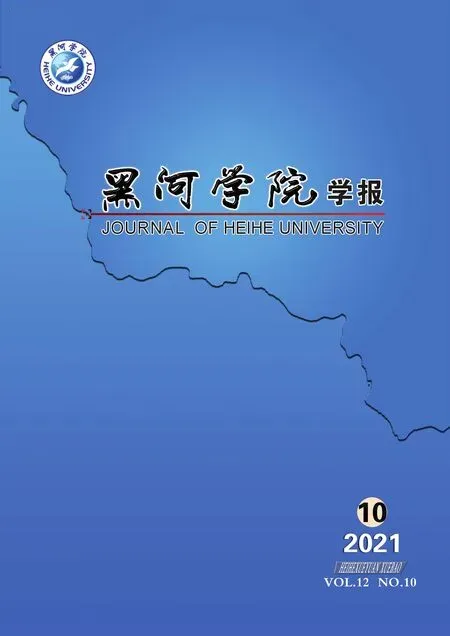胡远濬“以佛释庄”说解
李加武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老庄思想曾对佛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佛学又为中国士人全面深入理解老庄思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自魏晋时期僧肇、支遁首开“以佛释庄”的先河以来[1],直到清末民初,这一支脉历久而不绝。其间鸿篇伟著、特见卓识者叠出,较具代表性的有唐代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疏》、北宋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南宋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明代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以及憨山德清的《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论》、晚清杨文会的《南华经发隐》、清末民初章太炎的《齐物论释》。而自晚明以降,桐城派亦“与庄子结下不解之缘”[2]167,并且从明清易代之际的方以智、钱澄之开始,桐城派的庄子学研究就镌上了浓厚的“以佛释庄”色彩。这一方面当与他们的家学渊源或治学经历有关,如方以智的庄学思想即深受其外祖父吴应宾(吴氏为憨山德清弟子)的影响,而后又直接受到“金陵天觉寺爱国僧人觉浪道盛的影响”[2]167;另一方面,又与其因亡国破家之恨而产生的遗民心态有关,即他们寄希望于借助庄、佛来排解心中愤懑,并守护个人的“出处进退”[2]168之志。其后社会情势虽在不断变化,但此一释庄倾向却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在姚鼐的《庄子章义》、方潜的《南华经解》、马其昶的《庄子故》、叶玉麟的《白话译解庄子》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而作为民国时期皖江地区庄子学研究大家,以及桐城派著名学人吴汝纶的紧密追随者,胡远濬(1866—1931)①关于胡远濬的生平简介参见李加武.胡远濬庄学思想研究[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也深受这一思潮影响,这从作为其庄学思想结晶的《庄子诠诂》一书中即可明显看出。在该书的“序列”中,不但高度评价杨文会、章炳麟等人“旁摭释氏”以注《庄子》的做法,认为他们的这一做法“能补诸家所未及”[3]10,而且还躬身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道的成果。本文即以《庄子诠诂》一书为依据,集中讨论胡远濬“以佛释庄”思想的表现、特点和价值。
一、至人、神人、圣人
围绕《逍遥游》“至人、神人、圣人”三种人格形态的确切所指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三者间有无高下之分的问题,历来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宣颖、刘凤苞认为,自“故夫知效一官”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句,为一意义独立之段落,且末句为本段主旨之总结。据此,则宋荣子当为“圣人”之代表,列子当为“神人”之代表,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则为“至人”之代表[4]。如此,则“至人”的境界当在“神人”之上,“神人”的境界又在“圣人”之上。胡远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相反,他指出,“至人、神人、圣人”三者虽然在称谓上有所差异,但这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言说同一种理想人格而已,郭象在《外物》篇所言:“圣言其外,神言其内,至言其体”,即是其明证,这就表明在三者之间实无深浅高下的分别。为了增强己说的可信度,他以佛学术语“法报化三身”为喻。其中,“法身”原是指“中道之理体”[5],代表佛的本质,在这里则象征着“无己”的至人;“报身”原是指“为行六度万行功德而显佛之实智”[5],代表佛的功德,在这里则象征着“无功”的神人;“化身”原是指“诸佛为化度众生而现种种之身”[5],代表佛的种种形相,在这里则象征着“无名”的圣人。“法报化三身”的具体所指虽有不同,但这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言说同一对象(“佛”)罢了。
二、吾丧我
《齐物论》开篇即以颜成子游请益乃师的三问三答为人们塑造出一个“嗒焉似丧其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体道者南郭子綦形象,并通过他的切身体证向人们呈现出一幅“吾丧我”的得道妙境。在这段文字中,尤其能激起研究者兴趣的是“吾”“我”二字的独特内涵及其区别,而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学界也是见仁见智:或谓就己而言曰“吾”,因人而言曰“我”[6];或谓“吾”是真我,“我”是形体之我[7]168;或谓“吾”为主体,“我”为意欲[8];或谓“吾”是超越对象的自由存在,“我”是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存在[9]。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与上述诸说不同,胡远濬则另辟蹊径,他在不脱离具体语境的前提下,又能充分参考姚鼐、杨文会、章炳麟诸人之说,指出“吾丧我”实与佛学所谓破除我法二执义同。析言之,“我”是指“我执”“我见”,亦即通常所说的认识主体;“嗒焉似丧其耦”的“耦”字乃“对待”之义,是指“法执”,亦即通常所说的认识对象。由于我法二执乃同时出现之一对概念,其共同本质是将由因缘所生法看做固定不变的有自性之物,因此,“丧我”和“丧耦”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也就是佛学所谓破执释智、明心见性、彰显真我的过程。从佛学“破执”观的角度出发,将“我”理解为“我执”、“吾”理解为破除“我执”后彰显的真我,是胡远濬对“吾”“我”二字的新诠,充分体现了其“以佛释庄”的思想特色。
三、养生说
《养生主》首段“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三句话关系一篇之宏旨,然而关于其实际所指,研究者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截至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将“善”“恶”理解为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行”和“恶行”,那么这就是告诉人们,做世俗之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之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受刑戮之害,顺着自然之常理而行即可[10]115;二是将“善”“恶”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善境”和“恶境”(即顺境和逆境),那么这就是要求人们,面对善境不要有求名之心,面对恶境不要因之伤害精神,要时刻保持住内心的虚静[7]421;三是将“善”“恶”理解为“善于养生”和“不善养生”,那么这就是提醒人们,善于养生无近于虚浮,不善养生无近于伤残,要顺守中道以为常法[11]100。联系本篇主旨,胡远濬首先指出这三句话当是就“养生”而言,“如不就养生而言,则曲说岐见滋多矣”[11]101。在此基础上,他从华严宗“理事无碍”观出发进行创造性阐释:“理事无碍。就理言:‘缘督’,乃依乎天理之喻;就事言:‘为善’三句,亦即养生家治心为于无为之要诀”[3]39。“理事无碍”,原是华严宗所立“法界三观”之一,其中的“理”代表“真如的理性”,类似于通常所说的事物的本质;“事”代表“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类似于通常所说的事物的现象;“理事无碍”原是指“观真如的理性能生万法,故万法就是真如,好像水就是波,波也就是水一样”[12]。“理”与“事”、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即不离、不一不二的辩证关系为胡远濬解读“为善”三句的丰富意涵提供了有效参照模式。在他看来,“缘督”一句是强调从养生之“理”的角度关照具体的养生行为(“为善”“为恶”),从而时刻保持住内心的虚静无为(“督”);“为善”两句是强调从具体的养生行为(“事”)角度贯彻和落实养生之“理”的要求,恪守自然之常理常道。从华严宗“理事无碍”观的角度出发,将“为善”三句理解为是在探讨养生之原理与行为的具体关系问题,不可不谓是胡远濬的一个创见。
四、同异观
《德充符》开篇即描绘了一个“行不言之教,而有潜移默化之功”[10]169的得道者王骀形象,他在鲁国的影响力可与孔子相匹敌。而其过人处正在于他有着统一的世界观,即“把万物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物视其所一)[10]169。庄子在这里以孔子的口吻对王骀做了以下一番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个人对万物同异的看法:“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3]53这段话是说,如果从万物相异的一面来看,那么即使近如肝胆也会远如楚越;如果从万物相同的一面来看,那么它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关心耳目的特殊偏好,而只会寻求内心在道德的汪洋中畅游。如果从万物相同的一面来看,就不会有任何得失的感觉,因为万物都是在道的范围以内,只是在不断改变着存在的形态而已,因此,王骀能够将失去一条腿当作遗落一块泥土一般。这实际上表达的就是庄子的“齐物”观。
在胡远濬看来,庄子的这一观点与《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为大乘佛教的基本经典,《大乘起信论》创造性地提出“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所谓“一心”即众生心,因为此心有觉与不觉之分,故析为“二门”,其中,心之觉者称为真如门,心之不觉者称为生灭门。心真如门具有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性质,为绝对的无差别相,是本体;心生灭门具有生灭、增减、垢净等性质,为相对的有差别相,是现象。这“二门”的关系犹如海水与波浪的关系,虽说海水会因风动而起波浪,然而于海水之本性则不生变化,故海水与波浪两者为毕竟不二[12]的关系。同理,心真如门虽会因烦恼而现种种生灭变化,然而于心之自性则不起变化,两者实为一体之两面。据此,胡远濬认为,“自其同者视之”是从“心真如门”的角度出发,扬弃了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的差别相,而把握住它们在内在本质上的同一性,这也就是庄子说的“以道观之”或佛教所谓“真谛”;“自其异者视之”是从“心生灭门”的角度出发,只是把握住了万法在现象上的差别,而没有注意到它们在本质上的相同性,这也就是庄子说的“以物观之”或佛教所谓“俗谛”。而王骀之所以能够达到“视丧其足,犹遗土”的境界,即在于他已了然于“一心二门”之义,而证得差别即平等、平等即差别之实理。
五、体道过程
《大宗师》通过发生在南伯子葵和女偊之间的一段对话为我们完整呈现出学道的整个过程,同时还将这一过程划分为由浅入深的七个阶段,即“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为了让读者对此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胡远濬借助于佛教的修正术语以说明之。在他看来,从“外天下”经“外物”到“外生”,是成就“生空观”的次第;从“朝彻”经“见独”到“无古今”,是成就“法空观”的过程;而“入于不死不生”则达到“远行地”的境界。这里的“生空观”“法空观”和“远行地”都属于佛学名词,其中,“生空观”原是指观察到“众生为色受想行识五蕴假和而成,实无常一主宰之我体”[12],它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所共有之观见;“法空观”要高于“生空观”,达到这一境界就能体悟到“万法为有条件、幻假之存在,无有自性”[12],它是大乘菩萨所独有之观见;“远行地”又在“法空观”之上,它是菩萨十地中的第七地,达到这一境界则可“住于纯无相观,能证无生”[12],即“入于不死不生”。经过此番解说,道家的体道过程就和佛教的修正次第相互对应起来。庄子所谓“入于不死不生”,原是指修道者在得道以后的澄明状态,因为“道”是不死不生的永恒存在,但根据这一说法,道家眼中的“博大真人”也就只能算是佛教中的第七地菩萨了,这无疑带有浓厚的判教色彩。
六、机
《至乐》篇结尾一段文字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自然界生物演化图景,涉及到植物、昆虫、鸟类、哺乳动物、人等不同种类生物二十余种,并以“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语作结。对于这里的两个“机”字,一直以来即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以成玄英为代表,认为“机”乃自然、造化之义[10]536,这句话是说万物皆出于自然、入于自然;第二种以马叙伦、胡适为代表,认为“机”即本段开头说的“几”,是一种极为微小的生物[10]536,这样本段首尾就呼应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幅生物演化的循环景象。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实际上都承认这段文字是在说明自然界的生物演化现象。然而,胡远濬对“机”字的理解却迥异于前说,他在吸收杨文会等人相关说法的基础上,认为“机”即佛学概念中的“阿赖耶识”。根据唯识学观点,“阿赖耶识”能够变现万有,故云万物皆从此出、复从此入,这也就是《至乐》篇“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语的实际所指。但是这样的解释无疑割裂了本句话和整段文字的内在关联,给人以明显的牵强附会之感。
七、道物论
《知北游》提到“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3]185这是在说明“道”与“物”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其中,“际”是边际、界限之义,“物物者”是指“道”。在庄子看来,“物”是有边际和界限的存在,而“道”则没有边际,故云“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且“道”并非存在于物之外,而就在物之中,故云“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为了阐明“道”“物”之间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胡远濬借用了佛学中的“色空”理论。《般若心经》中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语,其中的“色”从广义上来说,是现象界一切事物之总称。由于在佛学看来,现象界一切事物皆为因缘和合所生,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实体,在本质上是“空”的,故云“色即是空”;虽然如此,但在因缘和合处即有色相之产生,是空无异于色,故云“空即是色”。如果按照通常的说法,“色即是空”是从本质上而言,“空即是色”是从现象上来说,二者实乃一体之两面。在此,胡远濬以“色”指“物”、以“空”喻“道”、以两个“即”字说明“道”“物”之间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色即是空”表明“物”在本质上是“道”的作用结果;“空即是色”表明“道”只有通过“物”才能体现出来,“道”在物中而非物外。他的这样一番说明确实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道”“物”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但是对于能否径直将“空”等同于“道”“色”等同于“物”的问题,则是值得商榷的。
八、人见其人
《庚桑楚》说:“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3]195-196其中,“宇”指“心”,“天光”即“自然的光辉”,这句话是说,心境安泰平静的人能发出自然的光辉,能发出自然光辉的人不但能显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而且还能照见万物的天然本质[10]700。这句话原是在强调心之自然宁静的好处,但在胡远濬看来,此句中的“人见其人”四字当与《圆觉经》所言“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色身见法身”同义。这里的“幻灭”者是指“色身”,即肉身;非“幻灭”者为“法身”,即具一切佛法之身。这是要人通过观察“色身”的幻起幻灭,体悟“法身”的自在永恒,即由幻显真、由色身见法身。胡远濬以此解释“人见其人”四字,认为第一个“人”字指“色身”,第二个“人”字指“法身”,这是在说“由色身见法身”的道理。显然,这种解释有悖于本句话的原旨。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胡远濬的“以佛释庄”思想具有以下三点特色:第一,受到姚鼐、杨文会、章炳麟等人的深刻影响,这从他对三人注《庄》成果的大量引用和高度评价中就能看出。第二,借助佛学的说理方式或者理论结构诠释《庄子》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这是因为在佛学和庄子思想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辩证法因子,在论证上确有相通之处。如他以华严宗“理事无碍”观解读庄子的养生说、以《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思想诠释庄子的同异观、以《般若心经》“色空”观说明庄子的道物论,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加深对庄子思想的理解。第三,以佛学术语诠释《庄子》中的一些疑难概念。如他将《逍遥游》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理解为佛学所言“法报化”三身、将《齐物论》中的“我”“吾”二字分别理解为“我执”和破除“我执”后彰显的真我、将《至乐》中的“机”字理解为佛学中的“阿赖耶识”。由于庄、佛毕竟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相似性,但终究各有其特殊意涵,所以这样的直接比附难免显得牵强。总而言之,胡远濬以佛学理论解读庄子思想的做法,虽然在某些地方确实有不相契合乃至过度诠释之嫌,但无疑拓展了人们对庄子思想的理解维度和深度,因而自有其思想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