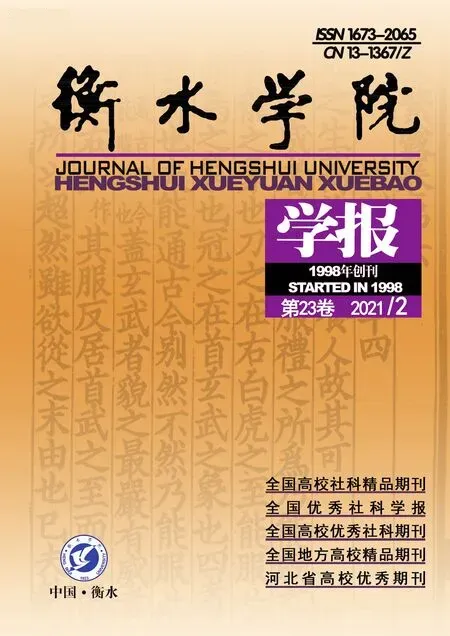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交汇下的二程学术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北宋中期,对儒家而言,是一个受本土文化(魏晋玄学为主)与印度文化(佛教为主)的双重激发而进入一个思想运动的新的高潮期,而就现实政治来说,又是一个各种治理危机出现与政治改革相交融的特殊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受到多方面影响、各种矛盾与因素共同促就的文化大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中说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脱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据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从历史发展来看,儒学走向心性义理层面是循着汉魏隋唐的演进规律而来,有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及其必然性。然对于二程来说,他们并非是刻意为了融合性理之学而建构新儒学,而恰恰性理之学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出发点。同时,作为士大夫,二程与北宋中晚期的政治运动亦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卢国龙即认为:“就问题意识而言,二程洛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其所以采取推阐天道性命之理的抽象理论形式,是由北宋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及其历史进程所决定的。”[1]300可以说,二程并非先在地把握历史规律而主动地迎合政治文化运动,使之产生一个新儒学的结果,而是二程本身就是政治文化运动的结果。
二程在道德方面的崇高表现,是建立在自我的精神追求、人格塑造和对道义的具体践行之上的,表现出了精神境界、德性践行与政治关怀相交涉的特点。二程以对道的体认为基础,贯通自己的整个学术体系,在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特殊的王道政治观念,并对行道的宏观策略进行设计。与道合一的境界是二程学术的根本所在,这需要以工夫修养来达到。同时,二程提倡对道义应持续和一贯地践履,体现为他们的义命观。此外,二程的德性践行之学还有着现实之目的性的宏观面向,那就是对建设社会伦理规范和政治秩序的深切期望,反映了理学视阈下学术、个人与政治的关联性与复杂性。
一、由精神境界来贯通义理原则
二程在学术上是早熟的。仁宗嘉祐元年,二程二十四、五岁时与张载交流《周易》,就被后者赞叹为“深明《易》道,吾所弗及”[2]437。同一时期,程颐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为学路径:“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2]577这段话表明了二程探寻真理的途径是通过认知自我的本性,从而通晓宇宙本质以及万物之法则。概括而言,就是“自明而诚,尽心知性”。可以说,二程延续了《中庸》《孟子》的思想逻辑,他们理解世界万物、了解宇宙苍生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首先就在于实现自身本质,即贯通天道。
贯通天道,在二程又谓之得“孔颜之乐”。少年时,二程就曾在周敦颐的指点下寻找孔颜之“乐”处。程颐说道:“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佗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2]127所谓“乐”,并非是把道作为一个可以认知的对象,而是对道之实有诸己的实现。程颢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2]59,正是与道为一的自然挥洒。可知,二程所感知的道是活泼泼作用着的宇宙、生命的本源之真,在自我生命的内在跃动中表达其存在,而非有一个外在的迹象可得。这与庄子所言有相通之处:“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3]可以说“孔颜之乐”是超乎世俗的精神境界,是获得自我本质实现、将自我生命契入宇宙大生命之中的人生境界,代表了极致的价值追求。在这样的价值诱导下,二程不入俗流,决心认知世界最本质的规律,踏上了一条能够使自己富贵内充、尘视金玉的求道之路。
二程对道体验的基本效验,首先在于个人将会以宇宙本真作为真实的自我,而有与物同体的精神境界。在《识仁篇》中,程颢说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2]16又说:“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2]17这里,程颢将贯通天道的步骤称为“识仁”。仁是宇宙之真源,是自我生命、万物存在的本真。以仁体为真正的自我时,个体与万物将不再是割裂的,而是在真源意义上获得一体同根、血脉相连的关系,“原本被看作外在于自我的他人、万物在仁的体验中通为一体”[4]。推而言之,个人的生命活动,就不是与其他事物无关的,而是整个宇宙生命和谐有序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自我将不只是代表形气小我之利益,所代表的乃是宇宙整体的利益。正如程颢所指出的:“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2]7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程极力称赞张载的《西铭》,认为其“备言此体”。由万物与我同体而爱之如四肢百骸,就可以看出,二程抱有待万物如一的公心。公心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是从二程的精神境界中直接导出的,其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私意以及利己之心是对立的。如刘宗周言:“盖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见伎俩,与之凑泊。才用纤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劳矣,安得有反身而诚之乐。”[5]由纯粹天理出发,公心无私、关照整体利益,是二程思想的基本特点。
二程对道之体验的效验,还在于认识到天道本源的圆满性、自足性,一任天道流行的个体自足。程颐曾说:“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2]697-698天的作用,其一就是化育万物,使世界丰富多彩。程颢亦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2]120其二,就是赋予万事万物以规范性。所谓:“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2]132这就是说,天具有义理性。义理之天是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动力,是万物之所以然的依据。人能够反身而诚,复归本性,便能够在自身开显天道之德,而实现自身在义理上的自足性。如程颢言:“人须知自慊之道,自慊者,无不足也。”[2]130这样,人与天道相合,自然能够顺应天所赋予的义理,而融入万物之化育不息的过程中去。《定性书》中所讲的“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2]460,正是这种境界——人的活动便是纯粹的天理流行。其中“情顺万事”,即是顺应事物的本然之性,避免人为的、主观的原因违逆天理。如此,便能够做到不劳己力,顺理而为,所谓:“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2]123不以私意,而以义理自足之心应对万事万物,这是二程对人面对世界之方式的根本指导。正是在此基础上,二程树立了儒家制度及其伦理条目为人道常则的观念。这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二程虽然强调顺理而行,但是天理概念在二程那里有化育万物的含义,是决定世界面貌的根据,所谓顺理而行,不应该是蹈空的伦理要求,而是人在遵从本性的基础上与外物感通互动的丰富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其对现实活动有着开放性与包容性。
事实上,二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人的现实活动符合义理。将天人为一、与物同体的体认看作一种合乎宇宙实然的体察,正是二程为人们构建义理规范的出发点。二程在学术上、政治上的观点以及对他人与自己之分歧的理解,也总会回归到这里。如程颐对英宗皇帝谈到最为根本的立志问题时说:“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2]521
二、以工夫论和义命观引导践行
梁启超认为儒家学问当称为“儒家道术”为好,他讲道:“道是讲道之本身,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6]这就突出了儒学与纯粹思辨哲学的区别,彰显了儒学之实践性与方法层面的指导。围绕二程之精神境界与所产生之效验的,是他们的工夫论与义命观。二程的学说对现实实践是开放的,他们实现精神境界、塑造现实秩序的根本路径,亦是依赖践行、落实在践行上的。也就是说,二程的工夫论和义命观,在本质上都是以践行为基础的。综合这两方面来看,可以更为到位地了解二程如何实现德性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引导与规范。
熙宁变法时期,程颢因新法施行而与王安石产生了分歧,并进而过渡到了学术层面。《遗书》记载:“荆公与明道论事不合,因与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2]255可见,程颢与王安石在学术上是有着原则性的对立的。在后来的批判中,二程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归结为安石未能真正认识道。他们谈道:“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佗不知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2]6对道的体认是有根本的重要性的,至南宋,朱熹仍然强调:“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7]对二程来说,熙宁变法中的争议暴露出来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能够认识道而进行政治实践的危害性,这也是程颢告诫人们“学者须先识仁”的现实因素,并直接促使他们转向了文化建构,以培养能真正识道、行道的人。
二程认识到,治理主体能否体认道并获得符合伦理原则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是政治振兴、秩序重建的关键。对二程来讲,重视工夫修养正是使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得到符合儒家伦理品质塑造的途径。二程与安石在学术上的破裂,诱发了工夫论在政治文化上凸显了出来。这也使得二程的学术彰显出德性践行的特点,与单纯的义理之学相区别。不过,在具体的教法上,二程的工夫路径各有特色。在程颢,偏重于体察识取,他有一些不同常人的行为,如观看草木、小鱼、小鸡等,以得到万物皆有天道生意的启示,帮助自己识取天道理体。然非识取而已,乃是“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2]16。诚敬存之,就是有一个不断地打磨、去除不合礼义之习气的过程。他说道:“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2]17可见,程颢要求人们在对理之察识的基础上时时端正自我,以使自己的行为出于一种本真的、不受旧习染污的状态。在程颐,则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2]188,既以“敬”明天理,又重视从伦理规范来贯通天理,倡导格物穷理。一方面,程颐解释:“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2]149另一方面,他又讲到:“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2]323程颐认识到,不但可以通过敬作为直内之道,使天理自然显现,而且也可以在事物上看到天理的表达,从伦理条目上洞察其所以然。本迹合一,互参互证,有力地捍卫了儒家伦理条目的落实。相比之下,“程颢比较重视‘诚’,而相对地程颐很重视‘敬’,‘诚’源于乾道,‘敬’源于坤道,源于乾道者高明,源于坤道者沉潜”[8]62,虽然工夫的特点不同,但是都是贯通天理的方式。重视工夫以及修养方式的丰富圆融,使得二程开创的理学所导向的社会生活方式,有着既有超越精神维护的伦理原则,又不至于以真背俗、脱离生活实际的双重品格。
工夫作为穷理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是属于进修的手段,而二程之愿景还在于对整个生命展开之过程的持续关怀。在二程看来:“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2]290所以穷理,就可以洞明天地造化,并了知天命。他们说:“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则谓之命,命者造化之谓也。”[2]274二程认为,天命是天道之用的显示,是造化的实质,并由此出发建立了自己的天命观:“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2]1144一方面,二程认为有天命的制约,人当顺受之。“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须知佗命方得。‘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盖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于困穷之时,须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祸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2]31-32。命决定着人的得与不得,君子知有命而不妄求,不会过分僭越人道规则而行邪道。另一方面,二程认为命非是有一套规矩可循,而是可达之者。他们说:“理则须穷,性则须尽,命则不可言穷与尽,只是至于命也。”[2]27这就是说“至于命”乃穷理尽性的自然结果,程颢讲道:“‘乐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圣人乐天,则不须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是矣。”[2]125这句话直接说明知命乃是人对天道的实现。对人而言,要坚持有命存在的信念,而实际上只遵循天道即是安命。他们更进一步指出:“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于义。……上智之人安于义,中人以上安于命,乃若闻命而不能安之者,又每下者也。”[2]194这就更加点明了所谓天命观就是一种义命观念。从效果上来讲,相信天命则有着劝慰人行义的作用,而从本质上来讲,行义就是至于命、安于命。为了凸显义命观念的本义,他们甚至还讲道:“言命所以安义,从义不复语命。以命安义,非循理者也。”[2]588可见,二程讲天命就是为了使人有一种内在的天赋使命感,而安心行义,践形蹈性。
工夫论和义命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巩固了德性践行,有助于将人们的现实生活导入道德原则的规范之中。工夫论旨在通过精神境界的提升从而塑造人们的现实表达、现实呈现,其效验落实于生活实践,是实现普通人与圣人转换的桥梁,彰显了二程思想中以人为出发点的成德之教。义命观念,则是对人生命过程的持续展开为考量,是以德性践行为目标的人生教导,只有人们持续地以义为路,循圣人之则,才有社会秩序规范起来的可能。此二者分别解决了个人明道和行道的问题,强化了重塑社会秩序的实践基础。
三、怀道义、忧天下的政治担当
二程探索符合宇宙应然秩序的常道,非以个人成圣为最终目的,而是从万物一体之公心出发,怀有革新天下的抱负。陈畅即认为“宋明理学除了是今人熟悉的思想运动外,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运动”[9],从这个视角来看,二程学术至少还包含着重塑现实政治的层面。二程所做的不单是自己践行道义、阐述王道原则而已,还要解决治道与实际政治结合的问题。他们探索治道与实际政治结合的过程,正是其对政治现实、学术现实进行反思、适应和回应的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完善了自我表达,勾勒了富有艺术性的行道路径。这些方面的建设,补充和丰富了二程的德性践行之学。
二程探索以道治国的具体策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程颐写作《上仁宗皇帝书》至程颢因反对新法被贬离京师。由于学术上的早熟,二程很早就表现出了以道化行天下的志向。面对政治上积弊严重的时局,如粮食储备欠缺、冗兵繁多、重敛于民、外敌强盛等,要求革新已是天下有识之士之所同然,18岁的程颐就写了《上仁宗皇帝书》,言辞恳切,要求改革。这次奏折在引君入道上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一是认可君主有仁心,但是没有落实在政治上,所谓:“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2]513因此,他希望通过劝慰使仁宗自觉“思行王道”。二是对“三代以上,莫不由之”的王道为何欠缺介绍,较为笼统。英宗治平二年,程颐又作《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给出了较为具体的、统揽全局的政治革新方案,提出应从三个方面作为根本入手处:“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2]521,认为“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2]521。而且他又进一步指出:“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2]521程颐绘制的政治蓝图是以皇帝来做王道的带领者,并依靠政府官员以及召集贤德之士共同作为行道的主体,共同担当重建秩序的任务。但同时也透露出了在行王道上过于依赖君主的缺点。熙宁变法前后,程颢亦从两个方面做了行道的工作:其一,是对神宗皇帝讲君道之则,辨王霸之别。如《上殿劄子》讲了定君志的重要,并建议神宗选用老成之儒安置身边,以“开陈治道,讲磨治体”[2]447。《论王霸劄子》进一步劝神宗要“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2]451。其二,则是对改革中认为违背王道原则之处,提出具体的意见。在这一阶段,无论程颐的设想,还是程颢的努力,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皇帝能够自发、主动地践行王道原则,其实质则是抱有执政者本身可以成为三代标准那样的圣人的幻想。然而,政治上的不顺,使二程深刻地认识到行道的现实困难,也促使他们重新考虑真理与权势相结合所需要的步骤。
第二阶段为程颢离开政治中心至旧党重新执政。在初步的政治实践中,二程没有达到以道革新天下的目的。一方面,二程认识到皇帝本身是难以主动推行王道的,提出了格君心之非的观点。他们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2]165另一方面,二程认识到必须进行更大层面的、更有深度的文化行动来扫除不符合王道原则的学术对君主、官员以及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其论新学之弊,说道:“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其如之何!”[2]50因此二程转而诉诸文化建构,以文化上的迂回来达到他们在政治上行义的目的。《粹言》记载:“明道补外官,入辞。上犹眷眷问政。他日,明道曰:当是时吾不能感动君心,顾吾学未至,德未成也。虽然,河滨之人捧土塞孟津,亦复可笑,人力不胜,以至于今,岂非命哉?”[2]1252从长计议,发展学术,改变君心,扭转时局,对治道进行体系性的理法论证,正是二程当时的真实心情。二程认识到要实现革新社会秩序的长远目标,对人的塑造是第一位的,转向了文化建构,并因而影响了儒家文化发展的品格。唐君毅即说:“汉代儒学之用,表现于政治,而宋明儒学之最大价值,则见于教化。”[10]当然,在二程那里,作为前提的教化还有改变现实政治的更深层的意图。因此,伴随着王道原则之理法论证的完成以及对时局的判断,二程提出了理学的道统论。元丰八年六月,程颢去世。程颐作《明道先生墓表》,讲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四千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2]640在这份道统论宣言中,程颐明确表达了道统是治理合法性所在,善治的原因在于行道,治统应该由道统来规范和统摄,表明了以道统政的根本立场。道统论的提出,表明了程颐有意识地为其倡导的治道原则进行历史论证,且有垄断学术正当性的意味,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是二程再次步入政治实践、解决道统与政治两分问题的前奏。
第三阶段为程颐进行政治实践时期。旧党执政后,程颐接受了崇政殿说书一职的聘请。对此,他自述道:“臣窃思之,得以讲学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臣以是慨然有许国之心。”[2]557对于通过讲学来培养人主,以此打破道统游离在治统之外的困境,对此程颐报以很大希望。程颐还进一步设想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人,也承担起行道的责任。他说道:“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2]540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11],但是将天下治乱系于宰相,是程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这将意味着宰相不能是听命于皇帝的工具,不能自私自利,而应担负道义责任,是行道的治理主体。在旨为“格君心之非”的经筵制度配合下,又提倡君臣共治赋予宰相以行道的责任,正是程颐对治理体系所做的全局性构想。在《周易程氏传》中,程颐论道:“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2]699“人君当与天下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2]767在这种君臣同治的设计下,君、臣都被作为建设天下秩序的主体,共同担负行义行道的责任。在政治上行道策略谋划的完成,使得二程倡导的王道原则有了理法性的体系论证、道统论的表达品格和具体的实践方案三个层面的建设,意味着二程在学术、政治上的探索趋于成熟和完备。
二程有着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他们绝不是一味地上达天道,而是要化导现实。程颢曾说:“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2]15卢国龙认为洛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天道性命之高深哲学,既以孝悌人伦、礼乐文明为基础,又力图融化到孝悌人伦、礼乐文明之中”[1]328。这表明了二程在现实的、政治上的目的,影响了文化建构;文化的建构,又反过来服务于政治实践。二程使现实政治的运作符合王道的探索,体现了二程对践行之学的宏观考量,反映了特殊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也反映了二程本身作为政治文化现象乃是学术与政治、精神实现与现实践行、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交织、相互融摄。
四、结语
程颢曾说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2]61二程本身就是以道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的硬脊梁汉。在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他们以身作则、以义作则,为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二程的道德、学问成就,是后人宝贵的精神资源,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财富。他们的思想以及对政治、人生、自然的态度,深刻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艺术。但也应注意到,二程的论学重点是对道义原则的坚守和儒家伦理规范的践履,而非对科学规律或生活具体问题之解决方法的实践探索,这与孔子同时以艺教人的习行是有区别的。如钱穆就认为,二程所讲的理“是人文世界之理,即性理,或义理;而非自然世界之理,即专限于物理”[12]。因此,二程理学虽然对现实活动表现出了开放性,但不可取代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人们应注重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否则就容易落入蹈空的偏颇之途。另外,二程顺天理、本人情,即能够不劳己力而解决现实问题的义理逻辑,与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是否内在地一致,也应该做细致的比较。这些考察有助于启发我们更好地追求伦理之善、坚守正义,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加有艺术地应用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