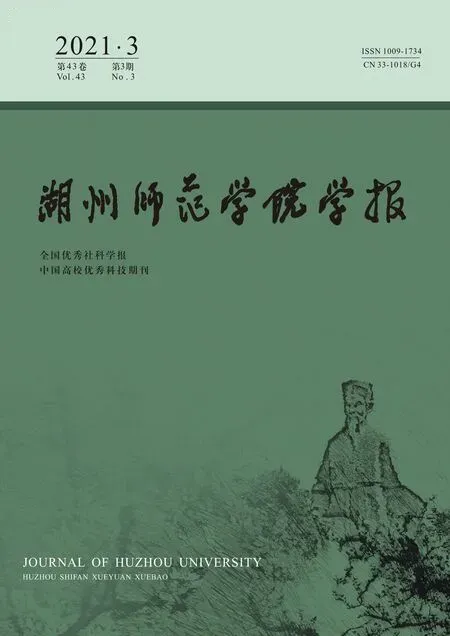从“鼓盆而歌”看庄子的生命美学*
罗惠龄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即是心灵持守着从虚到静的笃定状态。自我约束、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运用客观心态来观察事物循环往复的规律,可以说是代表着老子的思想。可到了战国中期的庄子时代,已然不能在安静中保持安全距离。因此,这个时候的庄子必须在心随境转的条件下,既要让自己顺应时代的变化,又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的干扰和伤害。基于此,庄子的生命美学也呈现出其个人特点及时代印记。
一、偃然巨室,向死而生
战国中期,诸侯国君大肆辟地充库,大臣士子弃义助纣为虐,野心政客变相攘夺政权以及混乱世局的倾轧争斗,带来杀人盈野的战争摧毁。“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期来得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春秋时期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期则短者要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1]47暴政衍生的失序,率兽食人、率土地食人肉之混乱污浊的黑暗世道,正是庄子所处战国时期的特征印记。惊涛骇世,正道不彰,邪道猖狂,时空次序颠倒错乱,价值观念扭曲变形,以致天下共苦,战争不休。于是,在满目皆是无可奈何的残忍现实里,如何在动乱中全身保身,重获安适心境的精神自由,这就需从个人的人生体验中反思惯常的价值观念。
庄子家境贫穷,入不敷出,向监河侯借米欲化解当下之危。“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子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得知监河侯非但不予救济,反而以其将得封邑百姓之租税自满骄人,心里不是滋味的庄子,岂能咽下这口恶气。“涸辙鲋鱼”,即是庄子无畏困窘及不被现实所屈的表现。天下大乱,战火频仍,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庄子的困境意识、忧患意识、沉痛隐忍的程度,对于时代灾难和人群祸患的敏感度,都远远超过了先秦诸子其他各家”[2]464-465。庄子虽处穷途末路的借粮之境,却不失清高孤傲的性情,对于监河侯落井下石的无理行径予以辛辣的讽刺。于此可见,在那个昏乱的时代里,清廉智士要持守贫穷不失志,是非常的艰辛困难和无可奈何。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是无数人梦寐渴求、汲汲营营之所在,无数人为此出卖人格蒙蔽灵魂,甚至铤而走险,不惜付出性命代价仍执迷不悔。“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不为世俗所羁,不被名利所动,不让高官厚禄束缚自我。深谙因果关系的庄子认为人生于世,犹如伴君伴虎般游于羿之彀中,处处充斥危机。因此,为能不为有国者所羁,追求自由而不愿做官,即便箪瓢屡空,穷居陋巷,仍甘于贫贱。《庄子·秋水》通过对庄子动作、神态及语言的描摹,刻画出庄子向往自由、超然物外的思想。终因不屑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其精神气象,自能流露出一种快意其志而尽逍遥之自由自足的充盈底蕴。
然而相对于社会动荡、人生无常、命若蝼蚁的人生困境,生之有限与死之必然之悖论当更为深重。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指出了“庄子认为人驰心于死生的问题,也和驰心于是非的问题一样,是精神的大束缚;所以他要解除思想问题的束缚,同时也要解除死生问题的束缚”[3]405。因为死亡是每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因此庄子苦心孤诣地将以“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养生主》)之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作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之一切束缚的解脱与自由。“人生来只是以受苦为目的,因此死亡是脱离悲惨世界的一种不错的方式,苦难直至死亡才结束。”[4]48因其“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庄子·让王》),故而才能在悦生恶死中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危机,才能认真严肃地思索生死,在不为利所役、亦不为物所累的无待境界中善待生命、善待死亡。而死亡始终存在于存在之中,承担死亡亦即担负起自我的存在。“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5]19偃然巨室,向死而生。唯有真正懂得生死,才能积极乐观地观照日常精彩,得以体验逍遥死亡的美学境界。
二、气聚则生,气散则亡
生命的生发在庄子看来是从无到有再至无的一种气化过程。“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庄子·知北游》)生死之气充盈于天地,并非撅然两分之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气聚则生,气散则亡,在聚散死生不断地交替流转变化中,洞察到生与死是共通相融之“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养生主》)不过聚散浮游之一气之化。生源自于天地,死生消散后又以之成始,从而体现出人之在世,安之非若丧耶之万物同化之普遍自然的生命过程。
这一哲学认识在庄子妻死一事上体现得非常具体。“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惠子不悦质问:妻子与你结发生活,为你生儿育女,抚养长大成人。如今年老去世,你不悲伤难过也就算了,居然还边敲盆边唱歌,这个样子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庄子答道:不是你所想的这样的。当她刚去世时,我又怎么会不哀伤难过呢?在哀痛之际,我思前忖后,忽然察觉到妻子她在起初时根本就是处于无生命的状态。不但没有生命的状态,而且根本是连个形体都没有;不但没有形体,而且还连个一丝气息也都没有。在若有似无恍惚之际,形成了气,由此一气变化出一个形体来,再由此一形体变化出生命。而此刻的生命又变回到原来的死亡,如此这般地迎生送死、生来死去的变化,就好似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想想如今妻子已然宁静安详地栖息在天地之间,我却还在这边哭哭啼啼的哀恸难舍,我认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便是太不通晓生命所赋予的伟大道理,正是因为明白了这样的缘故,所以才会停止哭泣。
生离死别是人生最难堪破的至大关卡。人生艰难唯一死,从没有人逃得过死亡所带来的焦虑恐惧以及伤痛的情绪反应。从前害怕死亡是因为死亡让我们感到孤单,忧心“我们”二字被彻底拆解掉了。因为一旦面临“死亡”,从前拼命努力所建立的一切关系即将全面瓦解。“死亡”在日常语境中代表着“去世”,不仅是生命的告终,亦代表着参与的社会活动终将被迫停止,从而崩解了辛苦建立的“我们”,吞噬掉绵延持续的“生活”。
在庄子看来,死生有命,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人生在世的最末一关,无法依恃任何客观的情势来扭转。既然来到人间无法自我主导,只能是被抛掷的偶然机缘,那么离开人世亦是无所逃的必然结局。因为从来就无人知晓死亡对人而言究竟是最高的祝福还是最大的诅咒,可人们却止不住担忧并径自将它视为最大的诅咒。来是偶然,去是必然。死亡便好似瓜熟蒂落般的自自然然洒落一地的种子,萌芽、长成、茁壮、开花、结果,灿烂一生,美好一世,最后再回归大地。生来死去,自自然然,不起执着,不生分别,不设好恶。最终,无边无际、无常无名之苦痛烦恼,便无法驻足于所有形式上的心头念想了。
庄子进而认为,生命的意义并非仅止于外在之形之“生”,更应指涉内在精神层面之“形”,形随境转,形变形化而为之“死”,生命由此自然自在地轮转运行,死亡便像是演戏之后的落幕,亦像是座通道,透过死亡而到了不同的生命境域。未知生,焉知死,谁又能清楚明白死后的世界是不是比我们自以为正在活着的世界更加美好呢。如此看来,顺应自然的生便不会执着于死,如果将死的这个死字都给消解掉,那么死不再仰赖生来制造,生便不会依恃死而作为结束。生死一贯,一贯生死,不要把死亡阴霾牢牢惦记而忽略了朗朗阳光的生存灿烂。于是,生命历程虽状似终结,但此生的美好总会永不消失地在彼端永恒存在着。
换言之,就庄子说法,妻子原来是不存在的,始自荒野里的一股气,这一股气莫名得到了形体,此一形体成为有了生命的妻子,妻子长大后便与庄子结婚生子,老了死后再返回最初无形体生命的状态,回归到初始的气里面了,安详自在地长眠于天地之间。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也就是说,“人之在世,安之非若丧耶?”“若丧”是自幼流落他乡之意,意思是人活在世上,你又怎么知道那不是年轻时候的离家出走呢?庄子此问,将生死之实与幻堪破了,是其生命美学的迷人之处。
进而言之,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现在”二字。努力在能够把握当下的有限生命中,如何不负光阴活得真实而充实,便能死得快乐而无憾。“积极面对生死问题,经由高度精神性的探索,获得生死智慧,从而安身立命。”[6]60因为形体只是暂居的过客,所以面对死亡,只能说是“化”,而非死。何谓化?即是此“身”在生死之间的转“化”中形“化”。人之在世,安之非若丧耶?何以故?离家出走后,最后仍须返回最初来时之地,过客终是归人。庄子参透了气聚则生、气散则亡的死生之道,接纳死亡大限的降临,明白生死必然之理。是故,面对妻死的庄子,其心早已超拔于生死之上,顿悟了死亡等于回家之钥,因此庄子不再伤感悲恸,转而敲盆助兴,最终便以欢送的姿态来祝愿他的妻子一路顺风。
三、虽死犹生,生不如死
庄子以其顺任自然的达观态度来面对死生。“在庄子看来,生死只是自然造化的规律,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和痛苦的离别,而是顺应天意,回归本真,让自己‘寝于天地之间,相与四季之运化’。”[7]171换言之,庄子不仅对于功名利禄不动心、不生情,在死亡大限降临之际,更能体现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养生主》)
生非乐事,死亦非悲情。“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庄子·齐物论》)“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铖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庄子·至乐》)对于骷髅头而言,人一旦死了,上没国君,下无臣子,没了四季该要打理的所有事情,自由自在地和天地万物并生共存,即便是拥有了能够像南面称王的快乐,也无法超越过它呀!庄子满脸狐疑,语带保留答道:若让司命官恢复你的形体,还原你的骨头肌肤,还给你父母妻子和乡亲故旧,觉得如何?难道不想要恢复作为人类原来所拥有的一切吗?骷髅头听罢,收敛笑容,愁眉深锁,沉痛且忧伤地说道:我好不容易死掉了,又怎么能够放弃掉南面称王的自在快乐,而重返人间再去辛苦地受累呢?
因为骷髅头深谙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以其一体而已,则世之贪生恶死者固非是,乐死而恶生者亦岜所以为一体邪?而庄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于贪生恶死,则南面王乐之说,岜无为而言之乎?”[8]578死生是无法改变的命定,必须从存在提升转往精神上的超越。“此段齐生死之意,当看得活动。《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即此意。若说庄子有厌生歆死之心,便是痴人说梦矣。”[9]187如果生是值得雀喜的事,那么就应该将死也等同视作是件值得欣慰的事情。颠覆了常人对于生存的恋栈及死亡的恐惧,从而领悟到生和死是能够有着不同转化选择的意义。暴君横虐、诸侯割据、烽火连绵、朝不保夕的种种生存恐怖压迫,正是庄子所历经的动荡时代。世道难为,现实充斥着苦痛曲折,还得艰辛地去承担日常所必须实践的社会责任。活着仍逃不过生不如死之痛苦,遂转往精神的高度延伸、超拔乃至解脱。庄子借骷髅之口,以死的无限性来讥讽生的有限性,坦然面对死亡无常之恒常,从而划出一道泯灭生死、超越苦乐时空限制的臻善境域。
但在现实生活世界里,“身”与“生”是拥有和掌握权势和名利欲望的表征。又,对于死后最为敏感的“鬼”字,《说文解字》解释为“人所归为鬼”[10]439。《尔雅·释训》:“鬼之为言归也。”[11]469也难怪骷髅头认为人死了,便是自我回归至上没国君,下无臣子,没了所有的所有,便可快乐自在地和天地万物并生共存。“通天下一气耳”本是“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前提。“‘乐死’是为了表达死生的随机性,目的在于破除世人对生的过分偏执。”[12]394与其痛苦活着,倒不如死后快乐恣意的样子,因虽死犹生矣,生倒不如死也,如此一来的死竟是如此的痛快和美好。“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肉体上的无,是人类无可避免的归宿;精神上的有,却是人类存活于世的最大收获和留给后世的最终遗产。但我们切不可走入重死轻生的另一个极端,庄子本意“却只在于引导人们以其‘死’来反省‘生’。似乎是在告诫世人‘有所待’的‘生’反倒不如‘无所待’的‘死’,并非重死轻生,更不是要人们舍生赴死。确切地说,只是以一种看似极端的方式说出了对其‘无所待’境界的向往”[13]46。换言之,无论生死,无所待才是庄子心中的至善世界。
四、如如来之,如如去之
一个人是否得以通达生命之真义,可观察他是否汲汲追求于生命中不必要的事物。没有死亡美学,生命仅是随便活着,任意死去。然而“庄子如此强调死亡的本己性,强调以超然达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死亡,不仅在中国先秦死亡哲学中是特别突出的,而且在整个中国死亡哲学史中也是特别突出的”[14]10。生命自然往返来去,最终形散气竭又归于自然。“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庄子·田子方》)因此,纷扰心田安宁的囿限生死自由,于庄子理想的精神气象是不存在的。“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仅从学生们欲厚葬庄子一事,便能知悉庄子不仅对于现世的功名利禄视如敝屣,对于传统礼法制度同样是不屑一顾的。按传统的礼法制度与习俗,丧葬可以说是一件大事。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战国时期还存在着野蛮的殉葬制度,贵族富豪死后仍用大量的珍贵物品随葬。其棺椁、连璧、珠玑、赍送,皆是古代丧礼的必备品。庄子却将天地视为棺椁,将日月当作连璧,把星辰看作珠玑,将万物用以陪葬,其生死一体、了无所待、万物同化的生命逍遥境界展露无遗。
庄子思想美学的立足点,即是对于个人精神自由宁谧的追求。活着的时候随任天体自然的运行,死去的时候更是化解掉人世间的所有束缚。天地万物皆生于道,人生于道而死后归之于道,所以乐生恶死实在没必要。既然生不足恋,那么死又何以惧之?尤其是仍醉心幻想死后还能享受生前快乐的世人,岂不愚蠢至极!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庄子认为死生犹如昼夜交替的自然规律,这是何等通达超脱的生命美学。因为了解自己的限制,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心转境转,换个角度思维,结果便大大不同。抛掷非可非不可的执念,好与不好的预设,便能从容愉悦的生活。接受安排,顺应变化,明白世间规则的变化,但又不被其规则变化所困扰。
古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能够了解到何谓“未始有物”。所谓“未始有物”,意思就是万物从来不曾真正的存在着。世事变化一如沧海桑田,如果从生前死后来看,人的存在不也像是没有具体存在,而是暂时过渡的阶段吗?庄子“其生命美学,便意味着以一种以探索生命存在与超越为旨归的美学”[15]32。换言之,若能超脱凡尘俗世,顺任自然规律,解放精神自由,便能无拘无束乐在其中。而庄子的快乐美学就在于他从不让自己陷溺在人间相对偏颇的价值观里面,而是觉悟到道是一个整体,是天人合一,是天地一体。既然生命在整体里面从来就没有损失消散,那又何来难过之有呢?正因为有如此豁达的生死观,故而才能理解生命存在之前本是无生命的状态,生命存在之后,依旧是无生命的形态。恍惚之际,形成了气、形、体、命,命逝之后,又回归于体、形、气。形聚为生,形散则死。尘归尘,土归土,生死一如昼夜更替,不过是宇宙循环、天地演化过程之一气之化的种种自然现象。
人生到了最后,需用什么样的心情,该用什么样的姿态,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跟这个世界挥手说再见。波斯诗人奥玛尔于《四行诗》中悟到:“喝吧!你来临的时候,不知其故;喝吧!你逝去的时候,不知其故。”[16]4好好整理当下人生,好好面对这个渡口,好好走向最后的渡口,好好地为自己寻找一条船,好好地为自己微笑送行。“如如来之,如如去之”,即庄子“未始有物”之“一气之化”的生命呼应。“如如”源自佛教语,意指永恒存在的真如,引申为永存常在,用白话解释就是随顺自然,应当如何就如何,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如来之,如如去之,一切皆是因缘和合,从哪里来便往哪里去。生是死的延续,死乃生之开端,没有生死,只有变化。把生都给放开了,死便没了立足空间,也只能是消失于无形无迹之中了。如此一来,便能够同情人的有限性,让遭逢挫折伤痛的人得到理解,并给出安抚,以获得希望,最终引领他走出桎梏的有限,从而朝向乐观阳光之永续生命的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