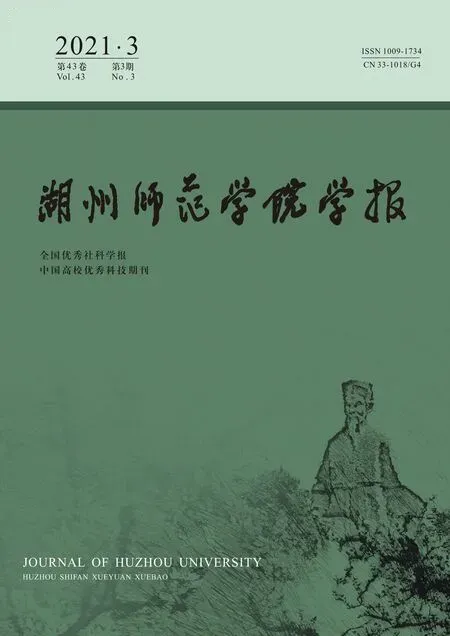教化观念对古代小说命名的影响*
宗立东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通识部,江苏 常州 213000)
一、教化小说观念形成的原因
《庄子》曰:“饰小说以干县令”[1]3,这是小说一词在词源上的首次出现。庄子在这里所提出的“小说”是相对于“大达”而言的思想言论,虽然是贬低之意,但它同时也使“小说”在产生之初就具有了说理明道的性质。《论语·子章》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1]3同庄子一样,孔子也是在贬低小说的大前提下,对小说的部分价值予以肯定,而就先秦诸子思想论辩的中心即强调各家学说对世道人心、江山社稷、重整乾坤的作用而言,孔子所肯定的“可观者”,也是从其一定的匡世、劝惩的作用而言的。
随着儒学被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论语》中关于小说的观念也顺其自然地被继承并发扬光大。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小说”作出了官方文献学的第一个定义,在《艺文志》中小说被归入子部则充分说明了小说明理的性质,在言及小说的作用时则直接引用了《论语》中的原话,至此小说的劝惩教化观念得到了完全的继承和确认。此后历朝历代史书中的《经籍志》《艺文志》对小说的立论和具体言辞,虽然偶有区别,但认为小说有谈说道理、教化劝惩作用的观念都得到了毫无例外的承袭。故胡应麟在谈及小说时言:“小说,子书之流也。”[1]27
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史官文化也凸显着这一观念,作为中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其“核心是‘敬天’‘明德’‘慎罚’‘德民’”[2]14,强化道德意识的意图已经体现得非常强烈。《春秋》又强调在“春秋笔法”中见出“微言大义”,而所谓的“大义”就是“记事之中蕴含着深刻的褒贬劝惩意味”[2]15。“史官文化中的隆礼、崇善、重人的精神内核,辐射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史传文学的这种历史文体意识表现在‘资治’‘劝惩’‘实录’三个方面。”“中国叙事文学强调‘教化’功能,主张讽谏,主张‘劝善惩恶’‘借古鉴今’‘大一统’等意识,无不浸染着史官文化的伦理色彩。”[2]9-11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责无旁贷地承载着浓厚的教化意识。
《周易·坤·文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太平经》曰:“善自命长,恶自命短。”同时,又提出“承负”之说:“力行善反得恶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信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六朝僧人慧远作《三世报》《明报应论》等文章(1)参考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相关章节的论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如此看来,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强调对世道人心进行劝善惩恶的教化,而中国古代小说在宗教的孕育下走向成熟,它的机体里也就很自然地注入了强烈的教化观念(2)参考韩云波:《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相关章节的论述,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这样,小说承载着厚重的劝善惩恶、匡救世道、补救人心的教化使命,并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小说命名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这些教化观念的影响。
二、教化观念在小说命名中的体现
(一)布道证教
在先秦和两汉时期,与其说出现了小说,还不如说出现了小说的诸多要素。中国古代小说的真正萌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动荡,百姓朝不保夕,这都给予宗教以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而宗教的想象和叙事都对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宗教小说。而“宗教小说实际上在小说文体的萌芽到自觉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萌芽阶段,宗教小说甚至是小说的主力军”[3]190。如《光世音应验记》《系光世音应验记》《宣验记》《冥祥记》《报应记》《感通记》《冤魂志》《幽冥录》《搜神记》《旌异记》等。这些小说也多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称的“释氏辅教之书”,鲁迅先生一方面表达了对此类小说的贬斥之意,而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了此类小说的教化意图。《光世音应验记》《系光世音应验记》都是记载光世音(观世音)显灵宣验的故事,信奉佛法则得福禄,不信佛法则遭报应,“无论遇到什么遭难,心念《观世音经》,便能逢凶化吉”[4]586。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十分简单,仅仅是按照这些简单的宣验因果观念而展开,是否信奉成为情节的关键,用小说来大谈因果、劝善惩恶、教化民众、宣扬佛法。小说的命名也开宗明义地指出神祗普度的意思,以感召人们信仰宗教。魏晋南北朝的宗教小说亦多是此路径,“古今善恶祸福征祥,广如《宣验》《冥祥》《报应》《感通》《冤魂》《幽冥》《搜神》《旌异》《法苑》《弘明》……”[4]579唐王朝佛教盛行,宗教小说的作者都是佛教信徒,“笃信大法,精勤不倦”“素信佛法”“持戒甚精”。小说的命名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说与宗教的渊源关系。
“佛教思想的传入,与传统儒道思想产生了互动的关系,逐渐形成兼括三教的同源思想。”[3]199因此,宗教所提倡的劝善惩恶、清规戒律,与崇尚儒家文化的上层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和世俗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形成内涵上的契合。这样,综合着宗教劝诫、道德说服的小说开始出现。唐临的《冥报记》成为较早例证,其书强调“冥界报应”。首先,唐临不是教徒,在其小说中他也只是借用“布道证教”的幌子,而实际进行的是“世俗说教”。这只需拿宗教小说的《冥祥记》与唐临的《冥报记》中的故事进行对比便一目了然。《冥祥记》“竺法义”条记,竺法义是佛门弟子,“疾病积时”,日益加重,其“唯诚归观世音”,晚间梦见一道人为其治病,而病愈。这个故事中“诚归观世音”是情节转折的关键,也是作者通过小说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而在《冥报记》“兖州人”条中,张生仅仅说了句庙中四郎神“仪容俊美”,天神就不惜下凡,携其上天入冥与之同游,并且在张生妻子亡故后,令其还阳。在这里没有对神灵的诚心信仰,没有反复的诵经祈祷,神灵也根本不在意这些宗教仪式和虔诚的考验,整个小说的宣教气氛十分淡薄。“(小说)到了自觉阶段,虽然宗教小说的形式技巧甚至故事原型都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但其根本立意却全面改观了。”[3]190宗教的“因果”“冥报”“吉凶”等观念,不再是衡量对佛祖、道仙信奉程度的标尺,而是成为小说的一种叙事元素,情节链条的一个部分。这样,小说及其命名,从单纯的宣讲教义转到了普世观念的表达,从宗教的神殿走向平民的市井。
(二)道德说教
“随着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也日益突出。”[5]27而且,随着宗教教化观的世俗化,宗教、儒学的教化形成混合的趋势,越来越面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世俗的道德层面。同时,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以“文以载道”为己任,在士大夫著书之时,教化劝惩也就成为他们着意表达之所在,道德规诫也就成为小说命名常见的观念。“如果说在原始形态的小说中,道德的教育意义还是通过题材直接流露出来的,唐宋以后的小说则开始将其作为小说的思想价值,在小说的功能上,不断加以强化,并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特点。不过,小说作为道德教化的手段,与一般的道德教化有所不同,实际上通过道德问题的思考,小说的世俗精神也有所加强,而这对小说的正面意义是不可估量的。”[5]27就小说的具体情况而言,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市民阶层,故此观念在与市民阶层接触密切的话本小说中较为常见。又因话本多是以小说集的方式存在,故“劝惩教化”成为话本小说集的主要命名观念,小说题目多“喻世”“醒世”“警世”之语,“是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6]901《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所载的故事多是贯穿着一定的道德理念。《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陈大朗淫人妻子,不仅自己客死他乡,而且妻子也嫁给所淫女子的丈夫,王三巧也由妻而降为妾;《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对施润泽拾金不昧的优秀品格进行着力刻画,通过对初拾金子的兴奋情绪和微妙心理的描写,赞扬其高尚的人格情操。本着“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6]902的创作精神,来达到“天下不醉人醉之,则天不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6]902的目的。劝善惩恶、褒扬道义、匡救世道人心的意图,在小说的故事内容和命名上体现得尤为充分。随之而起的是以此种观念为宗旨的话本小说的创作浪潮愈来愈汹涌,而且在小说命名上体现得愈加显豁。《型世言》的题目言之“为世立型”,小说集中共40篇故事,单篇题目采用对偶的形式,共80条,每个对偶句都有明显的说教意味,如“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秒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而且不乏直接标目“贞女”“烈妇”“孝子”“忠臣”等强调封建礼教的词汇,如“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烈妇忍死殉夫”“淫妇背夫造诛”,甚至对道德礼教的强调都已经达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而《醒风流》《警悟钟》《醒世骈言》等,题目中的醒世意味更是一目了然。
随着文人士大夫成为话本小说的撰写主体,小说命名中亦多用典故、比喻的手法,如《石点头》:“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石何异”[6]918,题目典出佛教典籍,教化劝惩意味明显;《鸳鸯针》:“世人黑海狂澜,滔天障目”“痛下顶门毒针”“针针见血”[6]920,将自己所作小说比喻“顶门毒针”,且小说的作者又自号独醒道人,取名源于屈原的“天下皆罪,唯我独醒”,“醒世”而唤醒教化众人的用途与动机,从作者字号的寓意注入小说的命名之中;《清夜钟》:“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谭说法,将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7]809,欲令阅其小说者有警钟长鸣的感觉;《醉醒石》:书名用“李赞黄之平泉庄,有醉醒石焉,醉甚而倚其上,其醉态立失去”之典故,“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6]919题目中都有让人幡然悔悟之意;《照世杯》:典出“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补之,亦未知其能补焉否也?”[6]940而《八洞天》亦为同一作者所做,则题旨亦然;《雨花香》《生绡剪》《跻春台》小说的题目也承续了教化的观念(3)《雨花香》化佛教普度众生之典,劝世之意自明。谷口生《生绡剪·弁言》云:“兹剪之者将以为衣,将习服勿忍遗。且剪有声韵,尤琐琐可听。比之坐屋梁,打细腰鼓,不既多乎善乎?”《跻春台》典出于《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话本小说的教化观念,兴起于以冯梦龙、凌濛初为代表的文人短篇话本集创作的明代中后期。明代中后期正是王阳明心学盛行,商品经济繁荣,人性、人欲萌发且大行其道的时期,而且冯梦龙又是深入其中,并且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代表人物,故冯氏的小说虽寄予教化,但小说之中不乏张扬人性和个性的精彩故事以及细腻传神的叙述。而延至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政权鼎革,一时间民族、阶级、思想等多方面的矛盾层出不穷、复杂交织,如火山一样轰然爆发,心学也沦落到被批判唾弃的地步,话本小说的教化功能也被极端化,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内忧外患更为严重的清中后期,直到末流的“劝诫连篇”,丧失了话本本身的特性。教化观的单方面强化与社会混乱、政治动荡的历史环境分不开,一方面文人希望通过小说来挽救世道人心,而就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整体环境来讲,他们当时所能利用的武器和理论也就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且由于心情的迫切性也促使他们把这种愿望表达得极端化;另一方面文人的关注点在于社会政治,当然也就无瑕顾忌小说的艺术方面。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一方面使得教化观在明清话本小说的题目中成为主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话本小说艺术的江河日下、思想的陈腐枯燥,满篇充斥着“烈士”“忠臣”“贞女”“孝子”,连篇累牍的说教取代了艺术的探索和思想的提升,导致了话本小说最终的没落。
章回小说的命名中亦有此类观念的体现,如《歧路灯》《善恶图》,亦多用比喻手法。如《歧路灯》喻指“歧路之明灯”,小说中讲述谭绍文少年亡父、母亲溺爱、不听规劝,因受纨绔子弟的影响,误入歧途。而后,其受家族败落、合家飘零等惨痛经历的洗礼,开始发愤读书,最终金榜题名、光耀门庭。李绿园正是希望通过小说达到教化劝惩、道德救世的目的。而这种道德救世的愿望在明末清初大的历史背景下,也形成了一股潮流,在戏曲领域有以李玉《清忠谱》为代表的创作。这些小说的说教多集中在社会道德、人伦世俗的领域,通过惩恶劝善、褒扬忠义、贬斥邪恶,以图达到提醒、警示、劝诫的作用。在具体叙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宿命迷信等思想也是他们常常利用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如《醒世姻缘传》所演“原来人世间如狼如虎的女娘,谁知都是前世里被人拦腰射杀剥皮剔骨的妖狐,如韦如脂如涎如涕的男子,尽都是那世里弯弓擎鹰绁狗的猎徒;辏拢一堆,睡成一处;白日折磨,备极丑行,不减披码勘狱。原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6]885;《三世报》(《三续金瓶梅》的别名)演绎“从古以来,福善祸淫之理,天故不爽毫厘。即或作善之人未尝获庆,作恶之人未见遭殃,亦皆不无可疑。然天道无私,不报与其时,必报于其后。不报与其身,必报与其子孙,从未有善人永不获福,恶人世享豪华者。报应之机,迟速不同,人特未之深观而默察耳”[7]1120。这两部书都是讲述民间夫妻伦理的故事,在前世里丈夫贪淫凶暴、女子淫荡乱伦,转世以后淫人者或坐视妻子被人淫,或无条件地接受原来妻子的惩罚折磨,淫妇或被上蒸下煮,或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时事小说亦是如此,如《警示阴阳梦》,其主要叙述魏忠贤的故事,魏忠贤在人间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淫威横行、不可一世,到了阴间其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也被上蒸下煮、受尽酷刑。总体来看,上述这三部小说都与当时的时事联系紧密,人们都有切身的感触,小说都直接指向了当时某些达官显宦、土豪劣绅。这三部小说所反映的教化劝惩、因果报应的观念,与其说受宗教劝惩观和儒家教化观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因不满现实而寄托来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观念。因此,“教化”常是官方的意图和文人的寓意,而“报应”多是市民的呼声。
综上,“布道证教”与“道德说教”是以教化劝惩为主旨的小说的两种命名倾向,前者有浓重的宗教意味,后者有醒目的说教色彩。由于两者在创作意图方面的差别,致使其作品有着不同的况味。前者通过教化劝惩来宣佛扬道、布施恩泽、“明神道之不诬”,让人信仰和皈依;后者则是通过教化劝惩来警醒世人、规范道德、修身齐家,让人清醒和通达。在小说命名上,前者具有浓郁的宗教氛围,而后者随着文体和读者的世俗化也愈加通俗化,常见的用典和比喻也只是文人的习气和书坊主的伎俩。同时,两者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布道证教”为古代小说的叙事提供了联系情节的必要链条,这些叙事因素也被“道德说教”的小说所继承。而且,随着小说自觉期的到来,“布道证教”逐渐走向世俗化、走向“道德说教”的层次,并且最后与之合流。而小说及其命名的“道德说教”趋势,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走向了更深层次的“针砭时弊”。
(三)针砭时弊
随着世风的江河日下,封建统治的日薄西山,各种危机频频爆发,各种丑恶现象大行于世。小说的教化也由旁敲侧击到了直刺时弊、淋漓批判,讽刺小说、谴责小说、时事小说的出现正是基于此种原因。故而在小说的命名上,也随之突出暴露、讽刺、斥责的用意,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梼杌闲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梼杌闲评》是魏忠贤倒台后,在短期内出现的反映魏忠贤发迹变态、倒行逆施、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小说。小说命名中“斥奸”突显了愤恨喷薄的感情、痛斥淋漓的激情、大快人心的豪情;“梼杌”是古代的一种凶恶的猛兽,人们将曾经不可一世、一手遮天的魏忠贤比作凶神恶煞,进行猛烈的抨击。小说指斥时弊、批判现实的用意,在小说命名上就已表现得十分清楚。《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形状》都是晚清著名的讽刺小说,两者在艺术上是承《儒林外史》之余续,痛心现实、触目伤情、指责时弊、披露恶行的程度更是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颊上之添毫,纤悉毕露,如地狱之变相丑态百出,每出一纸,见者拍案叫绝。”[6]814“政治之紊乱,社会之腐败,至清季而极矣。先生惄焉忧之,一一笔之于书,为董狐之史,魑魅魍魉,难逃犀烛。上自朝廷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倡优,无不收罗:此其取材之广而持论之精者二也。先生文章尔雅,是书叙事尤淋漓痛快,有嬉笑怒骂无不成文之观:此其文之佳而兴之至者三也。”[6]827两部小说对社会的揭露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官场政治、社会风俗、人情世故、官员贵族、贩夫走卒等,无不在作者的笔触下丑态毕现、恶迹昭然。虽然两部小说在艺术上有“辞气浮躁,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8]189的瑕疵,但其广泛地“揭发伏藏,显其弊恶”[8]189的创作宗旨和批判力度得到了人们的首肯,并且模仿其创作宗旨和艺术手法蔚然成风,形成“现形记”体和“怪现状”体。如《海上风流现形记》《和尚现形记》《滑头现形记》《商界现形记》《社会现形记》《警察怪现状》等,作家们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广泛地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界、商界、警界、妓院、教育界,且触及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如官员、商人、妓女、和尚、警察,整个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作者关注的范围之内。据笔者对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白话卷)的统计,“现形记”和“怪现状”体共有17种之多,可见涉及范围之广。
针砭时弊的小说,一方面是传统士大夫“匡道救世”社会责任心、使命感的体现,另一方面此类小说及其命名的出现也是当时社会世风日下、风雨飘摇的表现。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人们着重对晚明腐朽统治进行揭露;在清末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人们开始了对整个封建制度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小说的现实作用凸显,小说命名的趋势也随之进一步发展为控斥时政时弊,贬斥奸恶腐朽,揭露黑暗病态,不再局限于道德说教领域,而是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及《文明小史》《活地狱》等书。”[6]820在此类谴责小说中,一部分小说的命名较直露显明,体现出整个社会的丑情怪态,如上所举“现形记”体和“怪现状”体。而另一部分小说的命名,多采用比喻反讽的手法,如《文明小史》中的“文明”是作者着意揭露的社会丑恶现象,《活地狱》则是把存在着种种恶行劣迹的现实人间比作地狱,《何典》则是“今过路人务以街谈巷语,记其道听途说,名之曰《何典》。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实则不离乎开心鬼,扮脸鬼,怀鬼胎,钓鬼火,抢鬼饭,钉鬼门,做鬼戏,搭鬼棚,上鬼堂,等鬼箓,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此不典而典者也。吾只恐读是编者疑心生鬼,或入于鬼窠路云”[6]813,将人比作鬼。此一类的“寓鬼批世”之书,还有《斩鬼传》《平鬼传》等。此类题材的小说在命名时又都凸显出作者满腔愤慨、痛心疾首之情。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言:“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国家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此可看作是此类小说共同的情感指向,只是有的表现得激愤喷薄,有的则低沉沉闷,但感情都十分强烈汹涌。
从儒道两家文化对小说劝善惩恶观念的确立,到官方文化与史传文化对此观念的继承,以及佛教观念的推波助澜,终使教化观念成为中国文学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小说则是此观念一种具体且较为明显的体现,而作为小说显著标志的小说题目(命名)更是彰显了这一点。虽因社会环境、作家动机不同,或为宗教式(布道证教),或为道德式(道德教化),或为政治式(针砭时弊),形成三种侧重有殊的命名形式,然其教化的目的和宗旨则是相同的。所以,重视教化观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其亦是我们研究古代小说存在形态的重要视角和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