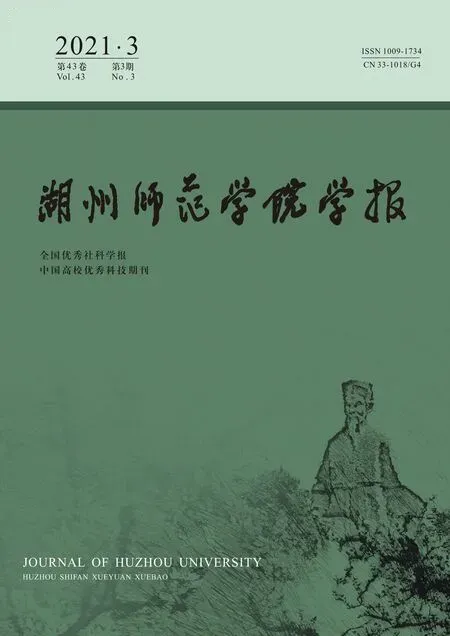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叙事技巧及其成因*
潘 浩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沈从文一直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习作,并非出于自谦,而是因为对于小说叙事技巧的训练几乎贯穿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沈从文初到北京练习写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创作方向,他最早的作品如《公寓中》《遥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都是从身边琐事取材,写日记般地叙事,在风格上明显受到郁达夫自叙传文风的影响。从湘西生活取材的小说如《夜渔》《代狗》《更夫阿韩》也都是流水账式地讲故事而已。在1924到1926这几年,沈从文的作品语言啰嗦,几乎没有结构设计,也谈不上什么叙事技巧。到1926年底,因为读者对湘西题材小说的追捧,沈从文开始更多地从湘西生活中取材创作,这种创作重心的转移不仅促进了沈从文创作思想的成熟,也促进了他叙事技巧的成熟。1929年至1931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期间,沈从文潜心研究小说的叙事技巧,在创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32年通过《从文自传》的书写,完成了对自己文学经验的梳理。1933到1934年所作的《边城》标志着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达到了巅峰状态。1935年,处于创作成熟期的沈从文专门写了《论技巧》一文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1]471。对于技巧的拿捏使用,沈从文也有自己的见解:“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1]472即使是在后来放弃文学创作后,沈从文对于技巧在创作中重要性的认识依然没有改变。1972年沈从文在给张宗和的信中提到汪曾祺时就说:“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2]39沈从文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曾回顾自己30年代的文学创作:“只有我还是一个死心眼笨的人,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地,才可能会写出点比较像样的作品。”[3]381
苏雪林1934年的《沈从文论》就注意到沈从文具有出色的叙事技巧:“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啰》;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来的,例如《男子须知》。他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a quick turn)。”[4]192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研究沈从文的学者越来越多,对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技巧的研究也趋于深入。金介甫在撰写沈从文传记时就隐约意识到,沈从文在《水云》中故意利用晦涩的叙事来遮掩婚外情经历。黄献文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中隐藏着“抛物线结构”[5]13,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状态呈现为接近幸福—遭遇变化—幸福消失。任晓兵从湘西民俗的角度切入,指出“沈从文并不是单纯地对涉及到的民俗做简单的描摹再现,而是在遵从自我乡土小说写作美学意图和叙事意识的基础之上,对这些民俗进行的主动叙事建构”[6]202。刘洪涛从叙事时间的角度切入,认为“对事件时间的顺从恰恰表明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重视。当小说情节进展动力剔除了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时,时间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顺其自然’,才得以让情节发展接受时间的约束和制裁,或者说,情节进展只是一大堆日子的延续,而时间的堆积产生出意义”[7]20。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得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技巧的研究得以深化。在此基础上,从小说语言、结构、手法等角度切入,总体关照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探究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叙事技巧,尚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研究尝试。
一、语言和抒情的节制
沈从文的创作经历了从稚拙到成熟的过程,在他早期的小说中,行文啰嗦的缺点非常明显。创作成熟后,沈从文在乡土小说的语言和抒情上都展示出了明显的节制,这种节制感往往从小说的开篇中就可见一斑。比如《雪》的开篇很简单:“天气变到出人的意外。”[8]15要读懂《雪》的开篇,就需要注意这篇小说写于1927年,沈从文的挚友叔远已经于1926年死于湘西。《雪》整篇写他住在叔远家时的温馨生活,基调明快温暖,但开篇的这一句话则点出了这是一篇沉痛的纪念文章。沈从文以住在叔远家时感受到的家庭般的温馨来衬托叔远去世后他心里的悲痛。开篇的这句话明写天气,实写人事变化的出人意料。《连长》的开篇写道:“军营中的上灯喇叭声音,在夏天时能使马听熟了也知道归回塞堡,入冬来,就只作了风的唿哨同伴,无聊无赖消失到那四面山林里去了。”[8]24这段看似在写军营生活,实则把全篇的故事脉络都交代出来了——军营的喇叭代表了军营对连长的约束,起初连长到年轻寡妇家幽会时,总是顾忌军营的约束,但在妇人的一次嚎啕痛哭后,连长则下决心娶了妇人。再如《柏子》的开篇:“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9]39这个开篇和结尾相呼应,结尾写道:“可是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9]46。船泊了岸,就如同柏子漂泊的生活暂时靠了岸,他把在船上做工所得的钱花在了河边吊脚楼的女子身上,这以后的半月或一月,他又将高高兴兴地做工,等着船再次泊岸,把钱再花到女子身上。《会明》的开篇写道:“排班站第一,点名最后才喊到,这是会明。”[9]84会明是农民出身,辛亥革命后到部队中做伙夫,他不懂战争,在前线时唯一关心的是他养的鸡,只要这些小鸡在战争中能够好好长大,会明就感到幸福而满意。《会明》的开篇实则写出了会明的军队生活状态——做事积极,但对于打仗他不关心。对于《边城》的开篇,许多人注意到了句式的美感,可能忽略了其中别的韵味。“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10]61将黄狗作为家庭的成员之一,不仅点出了翠翠生活的平淡和单调,更透露出了作者万物平等的生命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萧萧》《丈夫》《边城》这些优秀作品中,沈从文都偏爱用短句,叙事语言呈现出简洁平淡的风格。特别是这些小说的开篇第一句都很简短,在小说整体中占有极重要的作用。简短表达的背后,实则表明作者已经具有了高度凝练概括的写作功力。
这种语言和抒情的节制感也突出体现在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结尾设计中。沈从文许多乡土小说的结尾看似闲散之笔,实则精雕细琢,着力于拓展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在《菜园》的结尾,玉家菜园成了玉家花园,这看似闲来一笔中的深意需要联系小说的开头来理解。小说开头写道:“玉家菜园出白菜,因为种子特别,本地任何种菜人所种的都没有那种大卷心。”[10]278看似写白菜种子,实则在写人血脉的不同。正在玉太太憧憬着做祖母时,儿子和儿媳被县里抓走杀了,玉太太在寂寞中活了三年后,在儿子生日那天自缢死了。菜园变成花园,看似玉家白菜的种子断了,实则是玉家的血脉断了。小说开头点出玉家是清室旗人,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室。所以小说的更深意之处在于借写玉家断了血脉,而写革命让清室断了血脉。沈从在《牛》的高明之处在于用一个短短的结尾将小说的情节发展来了一个极大的反转——这里的牛都被衙门征用,大牛伯的牛也没能幸免,大牛伯开始后悔当时没把牛的后腿打断。这一结尾,将小说的角色互动从简单的牛—大牛伯,拓宽到牛—大牛伯—衙门,留给读者的咀嚼空间也随之拓宽。原本故事仅仅是农民犁田的事情,但加了这个结尾后,陡然用之前的感情铺垫衬托出衙门的征役带给农民的痛苦感。这篇小说看似写农民和牛的关系,实则借由结尾点出当时农民和官的关系。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结尾,既有和开篇形成首尾呼应的,如《萧萧》《菜园》《柏子》;也有反转式的,如《牛》《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夜》。沈从文通过精心设计的结尾,或拓宽小说涉及的人事面,或为小说情节提供了更多走向的可能,或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某种情感,总之拓宽了小说内涵的深度,从而使得这些精彩的结尾往往在小说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语言和抒情的节制感来自沈从文不断的写作训练。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叙事啰嗦,正如苏雪林所言:“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4]192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沈从文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学习将风景描写与故事叙述融为一体,从《史记》《世说新语》等古籍中学习用简练的笔墨写人记事,还从同时代作家的身上学习叙事的节制:“30年代的沈从文还从周作人以及鲁迅那里,领会到了节制的抒写和低调的抒情之好处,尤其是周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抒情格调,实在潜移默化了沈从文的写作风格,使他的小说不再倾情宣泄、一览无余,而逐渐变为含蓄隐秀且略带忧郁和涩味了。”[11]18虽然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是沈从文凭借自身超高的文学天赋,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创作风格日臻成熟。创作于1927年的《柏子》在写作上已经展现出了非常高超的语言节制能力。可以说,《柏子》的产生标志着沈从文由创作初期走向了创作中期,从流水账式的叙事方式走向了节制、含蓄、设计性的叙事方式。正如吴晓东在论及沈从文的创作时所指出的:“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12]87在掌握了节制抒写的叙事技巧后,或许是出于对不知节制的反感,沈从文在1930年的《论郭沫若》中,毫不委婉地批评郭沫若的文字热情有余、含蓄不足:“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废话在诗中或能容许,在创作中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他那长处恰恰与短处两抵,所以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1]154。沈从文在文中还提到了茅盾:“在国内作者中,文字的挥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1]155这种和其他作家的对照,也促进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上趋于成熟。
二、静动对照的结构布局
沈从文的许多乡土小说开始往往是描写湘西某处某些人日常生活时的情景,而后一些人、事的加入,使得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小说整体结构呈现出“静”与“动”、“不变”与“变”的对照。如《边城》中静的部分体现为祖父、翠翠、黄狗,一起守着渡船度日;动的部分体现为,翠翠随着年龄增长,产生了懵懂的爱情。而后大佬落水而死,二佬负气离开,祖父死去,一连串的变故让翠翠的生活接连发生了变化。作为《边城》的雏形,《三三》的结构布局同样呈现出静动对照的模式。《三三》中静的部分体现为母亲和三三守着碾坊度日;动的部分体现为城里白脸人的出现让三三心里产生了朦胧的爱情,结尾处白脸人病死更是给小说情节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力。《丈夫》中妻子老七像许多山里年轻的新婚女人一样,到吊脚楼下的花船上做妓女,这是小说静的部分;丈夫农闲时节到船上来看妻子,感受到种种难堪,乃至从心里感到屈辱,终于趁天没亮带着妻子回家了,这是小说动的部分。
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静动对照的结构布局有时还体现为城乡视野的对照,即通过外部社会的“变”来关照湘西社会的“变”与“不变”。在1927年创作的《柏子》中,沈从文叙述水手和妓女的露水情缘时暗含温情,这种叙事心态之中已经隐约显露出了城乡对照的视野。在1929年3月完成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小说结尾写道:“这故事北溪人不久就忘了,因为地方进步了”[13]192。看似闲来一笔,却将社会变革给湘西社会带来的影响蕴藏于其中。在1929年冬天完成的《萧萧》中,沈从文通过对“女学生”的描写,开始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呈现外部社会的变化对于湘西世界的影响。沈从文自己对于在作品中进行城乡的对照也有自觉的认识:“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晓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9]4沈从文将造成小说中人物生活发生变化的因素概括为“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多种因素。有些是外面的人进入湘西,比如《三三》中的城里白脸人、女护士,《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外部军队;有些是外部事件进入湘西,如《菜园》中的辛亥革命,《长河》中的国内战争;有些是人物自身情感发生变化,比如《边城》中翠翠爱情意识的觉醒,《丈夫》中丈夫在船上目睹了妻子的种种遭遇后“丈夫意识”的觉醒。当然,这些因素往往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在小说中相互糅合在一起的。
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偏好静动对照的结构布局,除了跟沈从文写作水平的提升和对湘西社会发展趋向的思考有关外,还跟沈从文创作背后的心理动因有着密切关系。通观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可以发现他的生活一直处在各种变动之中。其一,在家庭生活方面,沈从文遭遇了日常生活的重大变动。沈从文童年时代家境富足,但在其十五岁时,为给父亲筹钱还债,沈家变卖房产,家道中落。其二,在感情生活方面,沈从文也遭遇了重大的变动。沈从文少年时爱上了一个叫马泽慧的白脸湘西女孩,却被马泽慧的弟弟马泽淮将自己所保管的家中卖房所得的三千块银元骗去了大半。沈从文只觉没脸见母亲和亲戚,仓皇逃离家乡。其三,沈从文所见的湘西本身也在发生变化。1934年1月,沈从文因探望病重的母亲返回湘西,受时局影响,在家待了几天便匆匆返回北京。沈从文在家书中写道:“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14]2041938年1月,在前往昆明的路途中,沈从文带着几个人在沅陵住了三个月。这次返乡,他对湘西的变化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而萌生创作《长河》的念头。自己的家庭经历、爱情经历也好,湘西的人事也好,沈从文十几岁起就处在变动的生活状态中,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小说中也倾向于这种静动对照的结构布局了。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将自己与废名的乡土小说作了比较,认为废名所写的乡土小说“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1]150。废名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有爱、有憎、有忧郁,“但日光下或黑夜里,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和谐,非常宁静,缺少冲突”[1]150。而沈从文自己在成熟期的创作中则倾向于在乡土小说中将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放到各式各样的关系中,去动态地表现这些人的苦与乐。
三、娴熟的象征手法
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性与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象征手法在其小说中的娴熟运用。沈从文常常使用植物意象来做象征,比如在小说《凤子》中用虎耳草象征爱情。“这颜色值得称赞的草,它就从不许人用手去摸它折它。它的毒会咬烂一个人的手掌,却美丽到那种样子。”[15]111这里的象征用得还比较浅显,因为小说随后就给出了具体的暗示,“好看草木不通咬烂手掌,好看女人可得咬烂年青人心肝”[15]112。比《凤子》晚些写出的《边城》中,同样使用了虎耳草来象征爱情,不过在《边城》中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非常娴熟。二佬在溪对岸的高崖上唱了半夜的山歌,翠翠“在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10]122祖父拐着弯打听翠翠的态度,问翠翠说:“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预备怎么样?”[10]124翠翠自己只觉得梦得有趣,却并不明白虎耳草与爱情的联系。祖父又借虎耳草问二佬:“她梦的古怪,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对溪悬岩摘了一把虎耳草!”[10]133二佬明白虎耳草的寓意,但是因为大佬的死只能苦笑。翠翠因为心中朦胧的爱情,上山掘鞭笋时,摘了一大把虎耳草。虎耳草美丽而有毒性,沈从文借用虎耳草写出了爱情的美好与危险。另外这里的鞭笋也是一个意象,具有性暗示的意味,这一意象的使用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
沈从文也擅长用动物来做象征。比如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媚金与豹子相约在山洞中约会,豹子因为是初次和媚金约会,所以预备牵一匹小山羊送给媚金。“豹子家中无羊,到一个老地保家买羊去了。他拿了四吊青钱,预备买一只白毛的小母山羊。”[16]357对于羊的象征意义,小说中也给出了暗示:“地保见到豹子来问羊,就明白是有好事了。”[16]357媚金误会豹子爽约,把刀放进了自己的胸膛里,两人消除误会后,“豹子就好好把媚金放下,到洞外去捉那只羊。可怜的羊无意中被豹子掼得半死,也卧在地上喘气了”[5]364。沈从文在这里是将羌族成人礼中的羊文化进行了演化,将羊作为贞洁女性的象征。
沈从文还擅长用具有湘西地方色彩的事物来进行象征。比如《三三》中的碾坊、《边城》中的渡船,都象征着湘西古朴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对湘西传统生活的侵袭也体现在了这些象征事物之中——在《三三》中城里白脸人病死,碾坊需要加油;《边城》中祖父死去,渡船被大水冲走了。沈从文还会在小说中赋予人物象征意义。比如在《新与旧》中,用前清时当地著名的刽子手杨金标来象征传统的生活,在《菜园》中,用玉家母子来象征清室旗人。
中国现代文学自发端伊始就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沈从文在写作中擅长使用象征手法跟他熟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有很大关系。在20年代,《学灯》《晨报副刊》等杂志都介绍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大约是1929到1930年,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教学期间,“第一次从张东荪的《精神分析学ABC》一书中接触到弗洛伊德学说”[17]224。1931到1934年间,沈从文阅读了许多介绍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书籍,诸如朱光潜写的《变态心理学》,高觉敷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释梦》等。特别是在青岛大学教书期间,沈从文热衷于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其间所写的《八骏图》就是这种研究在写作上的体现。从沈从文的创作上来看,沈从文写于1931年后的小说中才出现比较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开始显得成熟。比如1929年发表的《牛》《会明》《菜园》,1930年发表的《萧萧》《丈夫》等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都比较成熟了,但是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还比较少。发表于1931年的《渔》《三三》中,开始大量出现象征的写作手法,特别是《三三》中多次出现对鱼的描写,可以看出沈从文这时对于在写作中通过象征手法来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已经有浓厚的兴趣了。正如金介甫所言:“像《八骏图》那样,用弗洛伊德观点来认识世界,是沈一九三一年到青岛以后作品中经常用的手法,也许是受到朱光潜、陆志韦的影响。沈现在承认,在他的代表作乡土文学作品《边城》中,也有弗洛伊德的气味。”[17]317在写于1933年的《边城》中,沈从文用白塔的坍塌象征男性守护者的消失,用渡船被冲走象征翠翠生活陷入困境,象征手法的运用已经非常娴熟。可以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不仅使沈从文对象征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也促使他在写作中更多地运用象征手法来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准,进而通过大量的写作训练,使得自己的象征手法越来越多样、成熟。
四、隐伏在叙事中的留白
沈从文在评传统山水画时说:“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不着笔墨处,因比例下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1]505像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一样,沈从文经常在其乡土小说的叙事中留出许多想象空间,使得文本更具有深度和广度。写于1931年的《渔》就凸显了这种叙事技巧。《渔》的故事充满寓意,叙事中有大量留白。对于老和尚的身份,小说中没有直接交代,但给出了许多暗示。比如老和尚会舞刀,和孪生兄弟的父亲认识,知道许多两族厮杀时代的事情。还有小说中多次提及丢在庙外石桌上的山桂野菊。沈从文在野花出现之前就有一处暗示,朝字辈的甘姓族人有一女儿在一次大水时被水冲走。在野花出现后,沈从文又有一处暗示,孪生兄弟从和尚处隐约得知,朝字辈甘姓族人还有在世的。将这些暗示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老和尚实为当年和孪生兄弟父亲厮杀的朝字辈甘姓,野花则是老和尚的女儿所遗。沈从文不将老和尚和他女儿的身份明写出来,实则是希望化解两方的世代仇怨。整篇小说的叙事脉络呈现为两族厮杀—两族准备毒鱼—两族仇人相会—两族河中砍鱼。再联系小说开篇提及的华山寨,不难发现,华山寨实为中华的隐称,甘家代指汉族,吴家代指苗族。汉苗两族在历史上争斗流血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今在小说中能够借猎鱼发泄蛮力,从而和平共处。《渔》和鲁迅的《药》有一些相似之处,《药》中夏家觉醒,华家愚昧;《渔》中甘姓觉醒,吴姓族人的哥哥愚昧,弟弟则开始觉醒。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书信中曾写道:“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14]188将《渔》中的留白梳理出来,方可发现这实则是一篇思考苗汉两族相处关系的小说。
写于1928年的《阿金》同样有大量的留白。小说中多次写道,地保阻止阿金去提亲完全是为阿金着想,怕阿金娶了那个克夫的寡妇。但从小说中的多处暗示来看,阿金的心理远非这么简单。沈从文每次暗示阿金真实心理时,都看似在为阿金的行为做辩解。“又笑自己做老朋友的,也不很明白为甚么今天特别有兴致,非要把话说完不可。”[9]79“地保奉劝阿金,不是为自己有侄女看上了阿金,也不是自己看上了那妇人。”[9]81但是从实际行为来看,地保和阿金谈过话后,就整天守在去媒人家的街口,阿金四次想瞒过地保去见媒人都没有成功。沈从文写地保就好似施耐庵写宋江,通篇没有明写一句讽刺的话,只是把人物行为摆出来给读者自己判定。通过地保的种种行为不难发现,地保阻止阿金提亲既是为自己侄女着想,也是为自己着想,他不愿意自己得不到的美妇人落给了阿金,他更希望做管事的阿金能带着丰厚的彩礼钱做自己的侄女婿。要进一步解读《阿金》中的留白,还需要注意小说中另外一处重要暗示:“阿金是苗人,生长在苗地,他不明白这些城里人的事情。他只按照一个当地平常人的希望,要得到一种机会,将自己的精力和身边储蓄,用在一个妇人身上去。”[9]80沈从文通过两者身份的界定,实则写出了他所理解的乡下人与城里人品行的不同。除了上文所举的《渔》和《阿金》外,《黑夜》中先前通讯兵的死因,《过岭者》中小头颅士兵平日的经历,《阿黑小史》中阿黑的病因,《雪》中叔远之后的遭遇等,都是沈从文在叙事中的留白处。
叙事中的留白不仅与语言、抒情的节制有关,还和思想意识与故事的融合有关。因为随着写作水平的提升,沈从文注意到如果只停留在技巧练习层面,写作很难形成大的格局。“文章徒重技巧,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1]474沈从文是在1929年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后,开始注重将思想意识巧妙地放入故事中:“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18]85在中国公学教学时,沈从文生活状态比较稳定,不用为生活所迫疲于写稿,有了更多的精力研究写作。“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18]85研究写作的效果从当时的作品中也可见一斑。1930年,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相继发表了《萧萧》《丈夫》,这两篇小说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当属一流作品,小说中对于思想意识的表达已经能够做到含而不露。比如《萧萧》中萧萧被骗失身后,萧萧的伯父被请来商议如何处置萧萧,小说中写道:“伯父不读‘子曰’,不忍心把萧萧当牺牲,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10]263。短短的一句话却有丰富的内涵意蕴。沈从文以“子曰”来代指儒家卫道者的思想,将老实忠厚的伯父与一些卫道者形成了对比。“牺牲”在这里用的是古意,指用来祭祀或祭拜的牲畜。可见沈从文在这句话里传达出的深刻意蕴,违反礼教的人在礼教护卫者的眼中如待杀的牲畜,而在老实忠厚的人看来,只是犯了错误的人。由此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的感叹:“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9]4沈从文在1950年写的《总结·传记部分》中说道:“是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个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了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18]86民国廿年,即是1931年,也就是说从1929年起有意识地将思想意识放入故事中,经过三年左右的创作,沈从文完成了这一阶段所作的写作训练。到了1932年,沈从文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从文自传》,“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和确立了自己”[19]127。
1934年,沈从文在家信中写道:“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14]188除了之前论及的语言和抒情的节制、静动对照的结构布局、娴熟的象征手法、隐伏在叙事中的留白等因素,以上这段话或许可以当作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的情感底色。在这种温暖生命观的烛照之下,沈从文将叙事与情感、思想融为一体,展现出高超的写作水准,使得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了穿越时代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