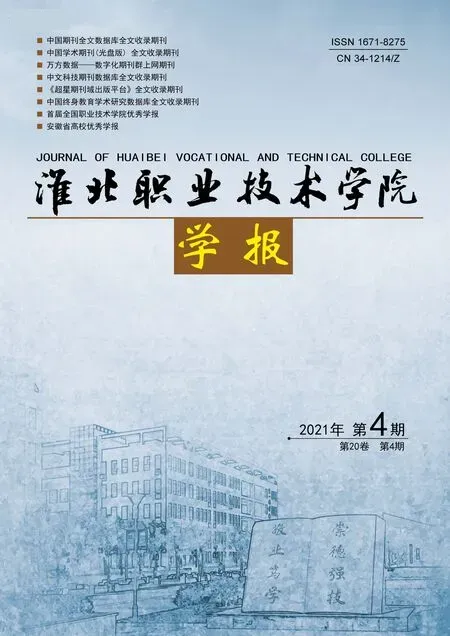论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跨体词
张 礼,周清玉,陈雅婕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10)
0 引言
华语是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在新加坡用华文进行文学书写是常见的表达形态,新加坡华文文学也因此取得突出成就,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因新加坡华文诗歌创作者多、作品丰富、颇具特色而引起海内外学者较多关注。
从语体的角度审视词汇,有通用词和语体词之分。通用词广泛运用于各种语体。语体词如口语词、文学词、科学词、公文词等,分别与相应的口语体、文学体、科学体、公文体等形成强适应关系。在实际运用中,出于特定交际需要,也会出现语体词的跨语体运用现象。这种在其他语体中运用的词即为跨体词。
本文以新加坡华文诗歌为研究对象,拟对其中的跨体词进行探究,以期拓展研究视角,取得新发现,推动海外华语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1 文献回顾
1.1 新加坡华文诗歌研究
对新加坡华文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发展轨迹、中国元素以及诗人诗作方面。陈贤茂勾勒了新加坡华文新诗自诞生以来60年的发展轨迹。[1]李庭辉专门就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从三个阶段进行了阐释。[2]宋永毅从“怀古咏史”题材和中国文化“原型意象”中发掘新加坡华文诗歌的“中国情结”,并从“吾土吾民的认同与归属”中探究其“南洋色彩”。[3]时梦瑶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思想内容、审美传统等方面细致论述其“中国性”特质。[4]关于新加坡华文诗人诗作的研究成果较多,王振科[5]、李雪梅[6]分析了“诗人家族”的创作特色。陈剑晖解读新加坡著名诗人周粲的诗歌世界。[7]朱立立就郭秀勇、五月诗人、淡莹等人的诗歌创作发表了系列论文。[8]专门研究新加坡华文诗歌语言的成果相对较少。
1.2 跨体词研究
学界对词语跨体运用现象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袁晖指出跨体成分是在具体的言语成品中出现的非本语体的成分,表现在词语、语句、篇章的板块等方面。[9]李琳就科技语体词的跨体使用进行了专题研究,结合具体用例分析其跨用情况、类型、原因及影响。[10]张礼描写了文艺语体词在非文学作品中的使用效果。[11]王召妍对艺术语体中科学词、口语词的跨用情况进行了分析。[12]邵长超认为,影响词语跨体使用有四个维度:语体范畴成员相似度、语体表达空位度、侧面特征凸显度、语境提示度。[13]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跨体词暂未引起足够重视。
2 新加坡华文诗歌中跨体词的类型及语言属性
新加坡华文诗歌数量可观,本文选择张松建、张森林主编的《新加坡华文现代诗选》[14]作为主要语料来源。该书选编了新加坡建国以来31位华文诗人的代表作,共262首,涵盖老、中、青三代诗人,技巧成熟,形式完备,较完整地呈现了文学史脉络,展现不同辈分诗人的贡献和时代交替的踪迹。从这部作品集里,我们通过人工检索和主动干预,共收集到比较典型的跨体词500多个,主要是口语词和科学词,各占一半。
2.1 口语词
新加坡华文诗歌中出现的口语词数量较多,我们从中挑选出口语色彩较为浓厚的词250多个,列举如下:
动词(97):办 憋 剥 吵 喘 串 吹 冲 蹲 屙 翻 飞 该 改 盖 赶 搞 够 关 光 滚 过 喊 害 花 会 挤 记 讲 浇 叫 开 啃 拉 来 老(死) 轮 晾 摸 眯 闹 尿 爬 怕 泡 瞧 上 松 伸 捎 塞 腾 提 吐 完 喂 洗 瞎 响 信 醒 学 咽 咬 要 争 种 罢了 变样 不了 掂量 罚站 打点 翻身 就是 开饭 靠边 磕头 来回 拼命 上班 上火 生怕 收拾 刷洗 算命 算是 投胎 淌血 硬说 再说 比不上 不消说 兜圈子 来不及 舍不得 由不得
名词(70):叉 粪 阿公 阿嬷 八哥 巴刹 馋嘴 爹娘 法子 公仔 狗屁 怪病 管子 汉子 猴党 后头 脚车 苦水 拉茶 懒腰 老汉 老六 零嘴 领子 罗厘 箩筐 名堂 娘胎 脑壳 脑门 泥巴 茄子 日子 晌午 身子 头上 瞎子 闲话 信儿 兄弟 袖子 样子 影儿 猪仔 大麻脸 豆芽嫂 翻肚鱼 鬼婆莲 鬼婆银 红毛鬼 鸡蛋婶 节骨眼 老百姓 马来鬼 猫儿腻 猫儿眼 青暝佬 天猛公 五脚基 小白脸 小孩子 小蛮腰 小燕子 眼珠子 野地方 印度鬼 玉蜀黍 左撇子 滚地葫芦 土地婆婆
形容词(33):惯 好 紧 快 懒 累 亮 乱 胖 偏 清 全 软 傻 熟 野 早 整 八卦 好看 花哨 滑溜 过瘾 老花 老练 冒失 顺手 眼花 不要紧 死心眼 土里土气 扭扭捏捏 坑坑洼洼
拟声词(16):当 叮叮 呱呱 咔嚓 咔蹦 呜呜 吱吱 哗啦啦 哔哔叭叭 叮当叮当 咕隆咕隆 咕咕索索 噼噼啪啪 嗖嗖嘀嘀 稀稀刷刷 吱吱喳喳
副词(16):真 老 先 硬 总 到底 反正 赶紧 明明 实在 早已 一口气 一个劲儿 一股脑儿 三天两头 一来二去
助词(7):吧 的 了 么 哪 呢 呀
代词(6):俺 咱 咋 哪个 哪里 大伙儿
量词(5):点 回 个 毛(一毛钱) 俩(数量词)
连词(4):跟 管 不管 还是
叹词(3):哎 哦 唉
介词(1):除了
从以上例词可以看出,新加坡华文诗歌口语跨体词数量最多的是动词,近百个,占比四成,且大多为单音词,符合汉语口语体词汇特征。其次,为名词,有70个,主体是双音节和多音节,其中包含具有南洋色彩的异域词,如“巴刹”“罗厘”“拉茶”“青暝佬”“五脚基”“印度鬼”等;由附加后缀“子”构成的词带有较强的口语色彩,新加坡华文诗歌中多有出现。口语中有大量形容词,但跨体使用到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只有30多个,占比偏少。拟声词是一个开放的类,多用于口语,以及小说、散文中的描写,在诗歌中并不突出,新加坡华文诗歌以其入诗,有近20个,且以四音节为主,较有特色。副词、助词、代词、连词、介词等均属于封闭性词类,数量不多,少量具有口语色彩的词在新加坡华文诗歌中也有出现,但频率不高。从词语所表示的概念义来看,这些口语词大多包含具象义,如动词多表示生活中的具体动作、名词多为日常中的人和物。口语词的多用,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新加坡华文诗歌的通俗性。
2.2 科学词
新加坡华文诗歌跨体使用科学词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在数量和频率方面都值得关注。我们从中挑选出较为典型的科学词近270个,列举如下:
名词(217):点 横 竖 撇 捺 提 暗喻 白昼 报表 北纬 本质 笔画 变种 病毒 病菌 病例 标题 草书 潮汛 齿轮 赤道 创口 垂线 大调 大气 大篆 单数 单眼 弹头 地表 典籍 叠韵 定律 定义 动脉 逗号 断面 法则 复数 复眼 负荷 睾丸 公海 关节 官话 光纤 国籍 国语 海拔 和音 后缀 话题 价格 纪元 甲子 金属 金文 句号 轨道 楷书 狂草 冷战 隶书 立体 两极 羚牛 流域 伦理 脉搏 冒号 明喻 能源 年轮 胚胎 频率 平面 脐带 蔷薇 切片 轻音 情报 曲线 人权 三界 声带 四肢 史诗 视觉 世纪 竖钩 双声 苔藓 体系 瞳孔 图腾 微粒 卫星 问号 物质 卧钩 西经 系数 系统 细菌 小调 小篆 行书 形体 休克 血液 氧气 样本 叶脉 哮喘 液体 遗传 蚁族 意境 意象 隐喻 宇宙 元音 原罪 圆唇 韵脚 沼泽 哲学 指纹 中锋 重音 主义 主旨 注解 子宫 族谱 坐标 白鳍豚 储水槽 丹顶鹤 二进制 e时代 方向仪 防腐剂 仿宋体 肺活量 焚化炉 伏羲氏 复系统 高频率 公约数 过去式 横切面 后遗症 花岗岩 华南虎 加速度 甲骨文 解剖刀 金丝猴 进行式 聚光点 临界线 麻风菌 马来语 梅花鹿 闽南语 木棉科 墓志铭 内窥镜 内燃机 曲折率 人民币 手术台 神农氏 燧人氏 失业率 微生物 维生素 未来式 慰安妇 X光片 消化液 心理学 休止符 异体词 有巢氏 诊断书 增长率 殖民地 重磅纸 注射针 专案组 存在主义 地心引力 防毒面罩 海峡指数 互联网络 跨国集团 耐力测验 苹果定律 切片报告 体能测验 热带雨林 生化武器 无期徒刑 阴阳上去 宇宙守恒 重吨炸药 大航海时代 反殖民主义 三百六十度 新冠状病毒 自然乘数法 地下操控中心 国民意识教育 经济增长指数 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
动词(49):加 减 乘 除 伴奏 变奏 濒临 并发 典当 顿挫 发酵 反刍 繁衍 复印 公转 过滤 记载 降位 解构 解剖 戒严 啃啮 溃烂 镂刻 轮回 埋伏 糜烂 排泄 匍匐 牵引 诠释 失调 守恒 透视 吞噬 象征 休克 修辞 氧化 遗传 移植 游离 愈合 蒸发 蒸馏 肢解 注释 注射 自转
形容词(2):宏观 孪生
这些科学词中名词占绝对优势,超过200个,占比八成;其次为动词,约占两成,从科学术语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极具名词性;科学词中的其他词类数量极少,甚至阙如,这是其不同于其他语体词的显著特征。从语音方面来看,以上例词中单音节词很少,基本上是双音节和多音节;在构词方面,组合式合成词占主体地位,且主要为偏正式。这体现了科学词的语体属性。从词义方面来看,这些科学词涉及生物医学、社会学、语言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及信息技术等,虽范围较广但仍聚焦在颇受民众关注的领域及元素。众多的科学词跨体进入诗的世界,这是新加坡华文诗歌在语体方面所体现的异域风格。
3 新加坡华文诗歌跨体词的运用方式及价值
3.1 运用方式
跨体词在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运用大体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因题而用,一种是因意而用。两者分别侧重交际内容和交际目的,与袁晖指出的引用型和修辞型,[9]以及袁晖、李熙宗阐述的被动渗透和主动渗透[15]相契合。
3.1.1 因题而用
这里的“题”是题材、题旨、话题的意思,可视为内容层面。有时,诗人的创作受交际内容的制约而需要跨体运用相关词语,这些跨体词在诗歌中通常提供其常规语义方面的支持,基本无变异特征。这种用法在新加坡华文诗歌中比较常见。例如:
(1)我对着鱼缸说国语
每一个元音像风打在镜子里
每一次顿挫像蚊子在跳舞
……
有时圆唇,有时不圆唇
圆唇时
是鱼 是语 是马来语 是ü
不圆唇时
是ikan 是English 是Inilah Singapura
——周德成《我们对着鱼缸说国语》
(2)不管您是木瓜
还是椰子,来生,妈妈
我都愿意投胎做您的孩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日子是一截截甘蔗
啃呀啃地,终究会啃出甜味来
——黄明恭《母子对话》
例(1):“国语”“元音”“顿挫”“圆唇”“马来语”等是科学词的跨用,这与诗的主题“说国语”有密切关系。例(2):“不管”“还是”“投胎”“孩子”“日子”“啃”“呀”等是口语词的跨用,这与诗的主题“母子对话”直接相关。这些跨体词虽不在其相应语体中使用,但其词义并未发生变异,其自身语体色彩依旧保持着,作者、读者均可按常规路径进行认知、解读。
3.1.2 因意而用
这里的“意”是指创作者的表达意图或交际目的。有时,诗人为增强语言表现力或某种表达效果而运用其他语体中的词,这些跨体词在诗歌中通常会发生色彩、词义方面的变异,与其在原本语体中的运用有较大差别。例如:
(3)如果一座城市如是繁华
却得了不治之症
谁来为她写
一篇又一篇的
切片报告
一纸又一纸的
社会诊断书
——黄明恭《切片报告》
(4)路灯与交通灯罚站成一棵棵树
铁牛在犁地上横冲直闯,行人
躲在阡陌间,用鲜血施肥
——希尼尔《花园城市》
(5)衣我、食我
养我、育我的这座城
只拥有一张脸孔
其流离的身世,考之无从
读你的表情,我惘然
要咔嚓多少声
方能留下一座城的沧桑与辉煌
——黄明恭《记载》
例(3):“切片报告”“诊断书”是科学词的跨用,其所表示的医学概念义在这里已发生改变,可以理解为关于城市问题的意见书、调研报告等,更有表现力。例(4)、例(5):“罚站”“咔嚓”是口语词的跨用,词义也临时转变为“竖立”“拍照”,表达也更加形象。这些跨体词因应作者特殊的表达需求,在诗歌语体中利用自已原本语体的词义及色彩基底,通过比喻、拟人、借代等修辞路径,起到更加积极的修辞作用。
3.2 价值
跨体词所具有的价值可以多方面解读。从言语交际来看,可以丰富表达手段,增强表达效果。从语言发展来看,可以促进词义衍生,完善词汇功能。从语体角度来看,可以促进不同功能交际元素的有机融合,甚至产生新的语体。就新加坡华文诗歌来说,跨体词的运用体现了新加坡华文写作者对诗歌创作的选择倾向或艺术追求,具有独特价值。
3.2.1 创构更多诗歌意象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元素,可以说无意象则无诗。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诗人将个人情思寓于意象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诗人通过审美活动创构意象,而通过词及其组合把意象传达出来。可以说,词或词组是绝大多数意象的载体。由于身处异域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中,新加坡华文诗人倾向于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审视周围的世界,善于在生活中寻找诗意,认为诗意无处不在。[16]这反映在语言上,则是很多跨体词所代表的物、事、人等均是当地诗人构建的诗歌意象,外延十分广泛。
新加坡华文诗人较为关注日常生活,注重发掘平凡生活中的诗意。在新加坡华文诗歌中,虫子、酒瓶、毛发、地铁、报纸、晌午、午后、喝茶、洗衣、等人、逛街、看算命、溜滑板、打电话等都是常见话题或题材,诗人藉此表现当地社会、人生,以及个人的情感及思考。在这些诗歌中,由口语词承载的朴素意象十分常见,如:人物类“阿公”“老汉”“瞎子”“大麻脸”,食物类“零嘴”“茄子”“玉蜀黍”,动物类“八哥”“小燕子”“翻肚鱼”等,以及更多的再寻常不过的普通事物类意象。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国家,新加坡华文诗人也特别关注当地华人之关切及都市生活、现代人复杂心理等题材。在这些诗歌中,华语和中华文化是一个重要主题,“横”“竖”“撇”“捺”“大篆”“小篆”“闽南语”“甲骨文”“伏羲氏”等科学词所承载的文化意象链接着跨越时空的“中国基因”。另一方面,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人自身和社会问题也进入诗人的视野,并以“病毒”“冷战”“防腐剂”“焚化炉”“内窥镜”“失业率”“防毒面罩”“生化武器”“地下操控中心”等科学词所承载的灰冷意象呈现。此外,自然物种、时事政治类意象也多有出现,如:“赤道”“地表”“年轮”“苔藓”“白鳍豚”“戒严”“慰安妇”“殖民地”“国民意识教育”等。
3.2.2 抒写诗人独特情感
诗言志,诗缘情。诗歌在本质上要抒情言志。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地域的产物。新加坡华文诗人,身处南洋,受当地风情及中华文化浸润,经历社会、历史风潮,对种种意象自有别样体验。跨体词的应用有助于诗人抒写自己独特情感。例如:
(6)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
我们怎可以不学
祖先的那个
大家努力学那个
先认识那个
早一点那个
三千多个那个快快那个
虽然专家说一千多个
也就够那个了
——梁文福《让那个更快乐》
例(6):全诗具有鲜明的口语色彩,这与“那个”“学”“先”“早一点”“快”“够”等口语词的跨体运用不无关系。诗中的“那个”可以理解为“汉字”“写字”“写作”等,其模糊、反复使用营造出轻松、幽默氛围,同时,表明诗人希望华裔子弟快乐学写汉字的态度。再如:
(7)夜被解剖
夜的断面,有凄厉的风声虫声
创口在愈合,血在凝聚
阳光以绢色的云,拭抹污痕
——南子《夜的断面》
南子是新加坡现代诗的开拓者,出版多部诗集,成就斐然。他的诗中出现了大量的科技术语,“出现频率之高,涉及学科之广,在新华现代诗人中罕有匹敌者,这不但造成了陌生化效果,也有助于知性抒情和硬朗诗风的形成”。[17]例(7):“解剖”“断面”“创口”“愈合”等科学词的跨体使用,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传达出其对“夜”这一常规意象的独特审美。
3.2.3 拓展诗歌叙事功能
在大众认知领域,诗歌是主情的文体。而事实上,叙事诗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悠久的传统,只不过在汉语诗歌中抒情诗更有成就。但就现代新诗而言,叙事已比较普遍。诗歌属于文艺语体,在词的层面最能体现文学色彩的是文艺语体词。这类词以形容词为主,长于描绘、怡情。而诗歌中的跨体词以名词、动词居多,更容易形成主谓、动宾或主谓宾结构,更长于叙事。例如:
(8)榴梿就是榴梿
管他规范,还是
不规范
我就是榴梿
木棉科
堂堂正正,无论什么理由
都休想
将我改成扭扭捏捏的“榴莲”
——梁钺《榴梿本色》
(9)将内窥镜引入更深的腹地
你会发现爪哇正在吞噬地盘
暹罗也像细菌来扩散实力
最后移植马六甲的伊斯干达沙
留下一张空床还有人不时来探访
——郑景祥《缝合一段记忆》
例(8)、例(9):两首诗均有很强的叙事性。前者表明诗人坚持采用“榴梿”这一写法为规范词的鲜明态度(这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书写习惯),由“就是”“还是”“管”“改”等口语词组成的口语句强化了叙事性。后者叙说的是新加坡王朝的一段历史,其后期遭受暹罗和爪哇的攻击,最后一任国王伊斯干达沙逃亡马六甲,灵柩存在当地供后人凭吊。诗人借助“内窥镜”“吞噬”“细菌”“移植”等科学词并通过比喻手法把这件事表达出来,其中也蕴含着其伤感态度和对新加坡历史的认同。可以说,跨体词的运用体现了新加坡华文诗人较为巧妙的叙事技巧。
3.2.4 营建非传统意境
意境是中国传统诗学、美学范畴体系中一个重要核心概念,其特征表现在“情景交融,意与境浑”,偏重表达“意向”或“志向”。[18]依据其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的表现又有诗境、画境、文境等之说。新加坡华文诗歌与中国诗歌同宗同源,而中国传统意境生发于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农业文化对自然、山水的亲和性是意境诞育的摇篮,意境作为一种审美崇尚已经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心理之中,并渐渐成为一种“无意识”状态。[19]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等是中华诗词传统意境所关照的主流。但是在新加坡,农业文明相对淡薄,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较早受到西方殖民文化和工业文明的洗礼,当地华文诗人的审美不可避免地由自然山川、田园风光等转向其自身所处的现代社会,在当下语境中营建不同于传统的诗歌意境。例如:
(10)生化武器藏在重吨炸药怒放的花心里
不在地下操控中心的厚度与宽度里
防毒面罩见证了一切猜疑后
尸沙漠
——董农政《二进制溃烂》
(11)周遭变了样
夜晚高楼探望的眼又能抚慰多少
孤独好久好久了
却怎么也想不通
当年那一只怪手
为何不把自己
带走
——寒川《牌坊独语》
例(10)、例(11):两例的审美客体分别是现代战争的场面和城市化拆迁的场景;前例有多个科学词的跨用,勾勒出壮、惨、“先进”的战争意境,融入了诗人对战争的敬畏及不支持意志;后例中多口语词的跨体组合,反映的是传统文化遭受破坏的冲突意境,融入了诗人的无奈、不解与惋惜。两首诗的意境营建与各自所使用的跨体词紧密相关。这里诗人建构的意境,并非华族群体或中华诗词传统的“无意识”状态,更多的是诗人个人的关注及审美体验的汇入。其所反映的正如南帆所言,一个人工的世界正在取代生糙的自然界,文明掩护着人类有计划地一步步撤离大自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程度超过了人与自然。[20]
4 结语
跨体词的运用是新加坡华文诗歌中值得探究的语体特征。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更真切地认识到新加坡华文诗人运用华语的方式和技巧,以及跨体语言在文学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基于这一视角,我们也需要辩证地思考,新加坡华文诗歌整体的语体特征如何,其诗意是否被削弱,华语的创造性如何加强。基于这一视角,我们也应该对新加坡华文诗人的身份特征、华语的地位,以及当地的文学创作生态等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相关问题我们将另文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