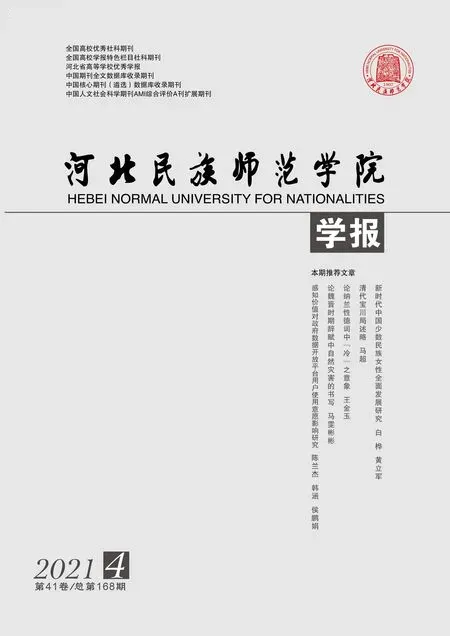《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一沉思中的“普遍怀疑”探析
何室鼎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作为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理性主义的先驱,力图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构筑哲学大厦。《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沉思”部分正是笛卡尔从传统以“存在”为基的知识主张转向以“自我”为起点的知识论路径之前的重要一步。笛卡尔提出了对他以往所涉猎的人类各学科知识可靠性及知识之间相互证明关系可靠性的怀疑,并通过不同类型对象的知识的怀疑(即“普遍怀疑”)得出了他自己所接触的以往所有传统知识和知识体系并不真实可靠,因此他需要从真正已知的内容重新奠基的结论。在此后的篇章中,笛卡尔以对知识的重新奠基为目标,逐步展开了对“我思”“我”的意识与认知活动、“我”意识之中的“上帝”观念和非“我”事物观念等一系列在近代知识论中举足轻重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考察。“第一沉思”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一书中和在近代西方真知探索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一、怀疑的动机、条件、基本方法及“原则”之思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沉思”开头提出,自己意识到自幼年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过来”,[1]14在此之后,又以这些实际上“非常靠不住”的东西为“原则”(principle)“建立”起来了一系列见解乃至一整套认知和见解体系。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并未给出对过去的他依据“原则”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的具体说明,只是做了这样的比喻:“拆掉基础就必然引起大厦的其余部分随之而倒塌”。[1]15而在“第二沉思”对“我”的存在进行论证开始之前(在原文中,这一部分是对第一沉思所得结论的进一步阐明,并未引入新的观点和论证)笛卡尔将自己在普遍怀疑之后从头重新寻找基础以建立知识体系的过程与阿基米德“只要求一个固定的靠得住的点”类比,称“如果我有幸找到哪管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那么我就有权抱远大的希望了”。[1]22显然,这种笛卡尔在《沉思集》第七答辩(法文第二版)中称之为双曲线的和形而上学的一般的和普遍的怀疑在笛卡尔的第一到第六沉思中只是手段和策略,方法论的意义更为突出,其真正的意图是通过怀疑和排除找到抵达真理的可靠路径,为建立他心目中的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对笛卡尔而言,普遍怀疑之前的“不可靠”的知识整体同普遍怀疑之后可以被重新建立的知识整体的结构相同,都是奠基在与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类似意义的“原则”基础之上,以这些“原则”为前提而被得出的,“原则”的可靠性保证了其后知识的可靠性。不过,“原则”与欧氏几何意义上的“公理”并不完全等同:前者可以被直接归结为命题(由作为“公理”的命题,通过特定规则得出作为结果或结论的命题),而后者则是心灵所感知到的、作为对象的观念——对这些观念的认知既给出了对这一观念本身的命题性认知,又提供了其他观念被心灵感知的可能。在“第一沉思”中,笛卡尔不断使用“东西”(things)而非“命题”“句子”一类词来指称被“我”所知道或相信的内容。在“第三沉思”中,笛卡尔对“我思考,我存在”这一“原则”与关于实体、上帝和其他非“我”自然存在物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在“第三沉思”中,笛卡尔则区分了三种观念:代表方式或者偶性的观念;代表实体的观念;代表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包含对象和对象意义上的实在性上有差异,其中作为原因的观念应当至少和作为结果的观念拥有一样多的实在性。笛卡尔认定“我”是实体,并且论证了“我”可以成为代表方式或者偶性的观念和代表实体的观念的原因;而上帝观念是比“我”的观念更为完满的,因此“我”不可能完全把握,也不能完全理解上帝的行为和意图。[2]30-32由此可见,笛卡尔所期待的认知不仅仅包括了做出判断的能力,还包括了作为做出判断前提的对观念的心灵把握/体会。(也因此,尽管笛卡尔是从“自我”这一主体出发去考察“主体”心灵或意识所把握或感知到的对象,但这种对对象的把握不仅仅局限于命题式的把握,“原则”与其他知识见解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是从命题到命题的推导,而包含了对不同层次观念的感知,因此笛卡尔的沉思探索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作现代哲学的“知识论”,笛卡尔所提供的图景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知识论”上的“基础主义”)这一点我将在就笛卡尔对各类“可怀疑的事物”的具体怀疑的说明中进一步阐明。
基于这样的观点,笛卡尔提出了进行普遍怀疑的基本方法:
(一)只要检查他已有信念所依据的“原则”就可以检查所有信念;
(二)在对“原则”作考察时,不需要确保基础信念完全错误,而只要发现其中有一些可疑之处、不能保证其为真(即不能作为知识结构的“原则”)就可以将其认定为错误、不可靠;宁可不认识任何真理,也应力求不作错误的判断。
对于第二点尤其值得细究,有必要详加说明:笛卡尔之所以在自己很清楚自己所怀疑的内容“在某种方式上是可疑的,然而却是十分可能的”,[1]19乃至“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相信他们而不去否认他们”[1]19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将这些不够可靠的内容视作错误,甚至是“千方百计地来骗我自己,假装所有这些见解是错误的”,[1]20也正是由于“原则”在这里是作为其他认知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一个具体认知活动的目标:因此,是否接受“原则”本身还要考虑到接受与否这一决定会不会影响到更多知识的获得,即“导向认知真理的正路”,即“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行动,而仅仅在于沉思和认识”。[1]20
二、对已有信念的怀疑
(一)对“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事物和相关信念”是否真实存在的考察
在普遍怀疑的开始,笛卡尔对于他现有已知的东西所组成的“大厦”的“原则”究竟是什么、甚至是什么类型都不甚清楚。此时的笛卡尔仅仅意识到,所有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的东西接受过来的,必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either from or by means of the senses),[2]13因此他选择从这些自己认为“真实”“可靠”的东西入手,寻找其中可怀疑和不可怀疑的部分,从而一步步寻找“不可怀疑”的部分,以期建立真正可靠的“大厦”。因此,如上文所述,这里每一步的可靠/不可靠判断都是以是否能够作为“原则”的标准而做出的。
笛卡尔首先考察的是感官或梦境所直接呈现出的具体事物。这其中有些事物如小的、远处的物体,感官给我们呈现得不够清晰切近、很明显会出错,因此我们可以轻易怀疑其可靠性[2]14。但对于另外一些感觉如与“我”的身体密切相关的感觉,看似不可怀疑,实则完全有可能是在梦境中想象所得(即便是“我”可以主动控制的手脚、全面的身体感觉也完全可以在梦境中出现);[2]14同时,梦境中的身体体验和清醒时的身体体验并不能通过某种清晰的标准明确区分开——看似梦境相较于清醒状态没有那么“清楚明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conclusive indications)也没有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2]14
在这一点上,笛卡尔和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Republic)①为行文方便,下文中将《理想国》现存文本的作者按照常见观点姑且简单地称为“柏拉图”。由于篇幅受限且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澄清笛卡尔的真知主张,此处不详细讨论历史上名为“柏拉图”的真实人物与现存《理想国》文本之间的关系。第六、七卷通过著名的“太阳喻”“线段喻”“洞穴喻”所表达的关于知识及其层次的主张有明显异趋——在柏拉图看来,只要有机会见到事物本身(而不是只见到过对事物模仿产生的“映像”),人是可以区分出更为真实的、作为映像原因的事物本身和它的映像的;而对笛卡尔而言,尽管在“第一沉思”之后的反思中笛卡尔提出梦境和想象只能对“我”意识已经感知到的内容进行重新排列组合,[2]14但这种主观排列组合的物的观念与作为其原型而直接被意识领会到的“原型”观念并不能被区分开来。在《理想国》第六卷的“线段喻”中,人是可以区分不同可感对象(映像和其所模拟的原型)、可感对象和可知对象(映像和其所模拟的原型)、不同可知对象之间(是否依赖可感映像和假设)谁更真实、更清楚的。[3]132《理想国》第七卷前半部分的洞穴喻也与之触类旁通:尽管会有一开始直视火光、日光的痛苦,起初会认为最初所见是比此时所见“更加真实”;[3]1133但“到了最后”他可以“审视和观察就是作为它自身的,以及就是处于它本身的位置上的它真实的所是”的时候,就可以得出结论,太阳是“对于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洞穴中所见的一切,它,以某种方式,都是它们之因”;[4]322“对于一切事物来说,它是那一切正确和美好的事物之因。在可见的世界中,它产生光亮和光亮的主宰者,在思维的世界里,它,本身作为主宰,是真理和理智的持有者;并且,凡是想要正确行事的人,不论在私人或是在公共事务上,都是必须对它有所见和有所认识的。”[4]324
笛卡尔试图去除梦境的影响——既然无法将梦境与清醒区分开来,就只能尝试寻找一种无论醒还是梦都能得出相同结果的东西,即“不依赖”醒觉或梦境而始终能可靠不变的东西。笛卡尔意识到,梦境不能够“加上”“完全新奇的形状和性质” (altogether new natures),[2]14梦境中呈现的东西总是梦境之外“我”已经感知到过的东西(将其暂时当作“真实的”东西而取用)的重新组合。因此,直接呈现在梦境或醒觉状态下的事物是由更加简单、更一般的东西(general things)在梦境或醒觉感知之中组合成的更为具体的完整事物、复合事物或个别情况(particular things)。而那些作为组成部分的较为一般的东西,“例如眼睛、脑袋、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1]17也不可能是在梦境中凭空产生的,因此如果它们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它们只能是在梦境中由更为简单、更为一般的东西组合而成。于是,我们可以不断将我们感觉到或梦到的事物分解,直至得到最简单、最一般的事物,这是无法在梦境中凭空形成的。由此,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以复合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1]17)的结论是可疑的;而最简单、最一般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1]19)看似是可靠的。
(二)对“最简单的”“最一般的”事物的认知是否真实可靠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笛卡尔判断“可靠”与否的标准已经和“事物”的观念是否来源于感官、对应的“事物”是否可能真实存在于外部世界没有关系了,笛卡尔仅仅能够确信“最简单、最一般的事物”的确作为观念出现在了“我”的心灵中,而并没有对它们究竟来自于哪里、如何被“我”意识到、是否与“我”的感官相关做认真严谨的考察。同时,在之后的普遍怀疑工作中,笛卡尔对真知的评判标准仅仅在于它们是否“certain and indubitable”,而不再考察相应观念的来源。可见,笛卡尔普遍怀疑所求之“真”与事物是否存在于自然界、是否通过感官获得并没有关系,而仅仅考虑它们是否“可靠”到足以作为“原则”,而“原则”能否成为“原则”的标准与是否存在、是否通过感官获得并无关联。
接下来笛卡尔尝试对最简单的、最一般的事物继续进行怀疑。由于普遍怀疑寻找“原则”的目标和基本方法的要求,笛卡尔需要对当时流行的全善的“上帝”的可靠性作反思,但又不能直接提出对“上帝”的质疑,因此他选择使用多重假设来避免表达自己的观点,使得这一部分的论证看起来十分复杂;但笛卡尔始终是沿着普遍怀疑、寻找不变、真实、可靠的“原则”这一基本思路进行探索的。为方便考察,笔者这里将笛卡尔的论证略作整理,其主要论证过程和论证目标如下:
1.上帝或妖怪可能做出的干扰:形成新见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干扰。
(1)两种可能在新见解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a)不但感官有可能和梦境混淆,感官本身也有可能被造假——“更一般的东西”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假的:“本来就没有地,没有天,没有带广延性的物体,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地点,而我却偏偏具有这一切东西的感觉,并且所有这些都无非是像我所看见的那个样子存在着的?”[1]18
b)在对所把握到的“更一般的东西”加以观察认知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弄错”“也可能上帝有意让我每次在二加三上,或者在数一个正方形的边上, 或者在判断什么容易的东西(如果人们可以想出来比这更容易的东西的话)上弄错”。[1]18
(2)上述潜在错误出现的可能原因:“上帝”或“妖怪”
c)笛卡尔认为“我”可能并非为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所创造(这里他借助“也许有人”的观点来表达这一怀疑,并从这些人的角度预设自己并非神创、并非完满,而“失误和弄错是一种不完满”且“我”的作者“越是无能,我就越可能是不完满以致我总是弄错”,[1]19从而继续推进普遍怀疑的考察),因此“我”可能不完满,理智能力可能有限,可能犯错和被欺骗。
d)同时,可能存在能够引起“我”意识之中幻觉出现的“妖怪”(为避免直接提出“上帝欺骗我”而放弃对上帝的直接判断,另外假设一个“妖怪”可能以上帝的方式直接干预“我”的感觉经验和“选择是否相信”的意识活动[1]20)欺骗“我”,让“我”对最简单事物的判断出错。
2.已有信念带来的习惯:“我”思维中已有的旧见解中可能出现的错误。
一些不够可靠但此前跟“我”又“相处的长时期的亲熟习惯”的旧见解会“不由我的意愿而占据了我的心”,从而被“我”轻信[2]16——并非依赖可靠的评判标准而接受了这些见解。
如上文所述,由于笛卡尔的目标依旧是寻找“原则”,因此笛卡尔选择无论多么可能正确的见解,都需要“假装所有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以保证在“correct perception of things”之中没有任何的“danger or error”。[2]16在这一目标下,笛卡尔于是决定,“如果用这个办法我还认识不了什么真理,那么至少我又能力不去下判断”,[1]20而这种做法在笛卡尔看来是不合常理的、仅在普遍怀疑和重新奠基的探索中才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感觉、认识不是truth之源
在“第一沉思”结束时,笛卡尔指出自己此前接受的知识和见解中没有能够满足他对找到可靠原则、建构可靠体系的要求的信念。因此,笛卡尔一方面不再能够相信既往的任何信念和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必须另外寻找可靠的信念原则来重新建立“大厦”。
这一结论的得出与笛卡尔对知识体系的“原则-大厦”构想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构想要求笛卡尔对知识可靠性的考察以“能否作为原则”为标准展开,从而一步步排除了他已知的所有知识。对于这一点笛卡尔是清楚认识到的,因此他也提到,他为追求可靠真知而否定掉的信念实际上也是“十分可能的”,而对于不持有他这样建立知识大厦的目标的普通“人们”而言,选择相信这些很可能对的东西才是更为理智(rational)的。[2]16同时,笛卡尔对人的理性也同样不够信任,认为人的理性是否是可靠的认知真知的方式、其错误是否可能克服都是需要进一步反思以确认的,因此提出了“上帝/妖怪”这一彻底否认理性认知可靠性的怀疑思考。也正因此,笛卡尔将不够真实可靠的知识和理智能力仅仅视作认识真知道路上的障碍,这与《理想国》真知主张之中将不够真实的“映像”当作灵魂适应理性认知和直观更真实存在者的必经阶梯、将理智视作可以精进以致求得真知的待琢之璞的态度迥然不同。柏拉图在线段喻中第三阶段的探索显示对可知事物认知的较低阶段,也为产生思想(thought)奠定了一定基础:他把可感的图形作为映像使用以凸显除了通过思想无从看见的那些事物本身。[3]1131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上升向理性本身把握的东西、形式本身),则需要借助上一阶段的假设当作“一些阶梯,一些跳板”,以“一直走向那个超越假设的东西”。[4]316-317在洞穴喻中,不同处境变换时需要“适应光线的过程”:直接观察光亮本身过于刺眼,需要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如从开始看水中的倒影到夜晚观看天宇上的东西和天宇本身,到最终可以直接观看太阳。[3]1133-1134不经历这一过程无法直面太阳,也就无法确定太阳的真实所是。
《第一哲学沉思集》之后的篇章对“我”的存在、“上帝”存在、可感物体存在的考察忠实地延续了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开启的方向——寻找“原则”,考察 “原则”是否可以当作“原则”及“原则”如何可以保持可靠不变。同时,其后的行文在普遍怀疑之后,坚持了只从“我”自身的意识活动和心灵感知出发、谨慎对待“我”之外来源的观念的路径(尽管从后人的角度看笛卡尔的一些具体论证对此坚持得不够彻底,如将思维活动中作为主体的“我”轻易视为始终不变的同一个“我”并将其等同于被反思的作为认知对象的客体“我”;但从行文中看,我们可以相信笛卡尔并没有故意加入这样的瑕疵)。因此,笛卡尔所提出的“我”和“上帝”观念是与既往神学和哲学提到的“我”/“人” “上帝”非常不同的,是在“我思”视野中呈现出的仅存有可以被“我思”捕捉到的“思考着的我”和“比我完满的我的原因”两条属性的、被全新提出的实体。
在《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探寻真理的方法》等著作中,“普遍怀疑”的精神一以贯之。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对感官的怀疑、对梦的论证、对欺骗的上帝的剖析最终导致了以下三者可靠性的瓦解:由感官而来的认识的可靠性、感官与外部事物的关系的可靠性、理智与外部事物的关系的可靠性。笛卡尔一反亚里士多德—经院主义的认识论,否定“所有在心灵中的东西无一不是在感官中的”,不认为观念是从外物而来的,使外物与心灵的关系脱钩,基于我、观念、世界的三元关系搭建起新的认识论。笛卡尔认为“所有在感官中的无一不是先在理智中的”,应当从心灵中的观念意识出发,来考察我们如何能够获得关于外物的知识,以及如何重建它们两者之间的关联。[5]
结语
经过早期对当时西方各门类知识的涉猎和探索,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以与以往西方学界科学、哲学探索截然相反的路径展开:笛卡尔否弃了“存在”问题在先思考、决定人类探索的方法和内容的传统路径,而尝试从“自我”出发,从心灵中的观念意识出发,探求理解和确证知识原则进而寻觅为“我”所接受的知识体系的可能性,以自我为准绳排除“我”的理性所不能确知的内容。如此鲜明高扬自我主体性的探索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笛卡尔在中世纪神学、哲学、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思维由从外在世界出发向以人的自身观念意识为立足点的彻底逆转,将自我意识、理性、意志带向哲学探索的前台,从而开启了此后数百年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探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