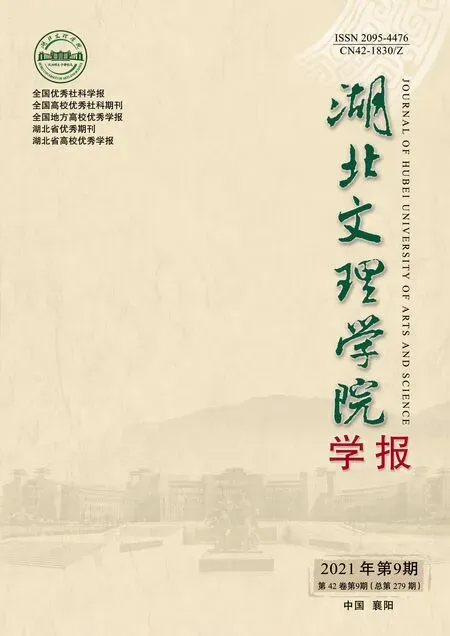宋高宗朝后期颂体词的承继与新变
——以曹勋为考察中心
陈修圆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颂体在文学史上具有久远的历史,最早可见于《诗经》中的颂,伴随氏族祭祀礼仪活动而存在。《文心雕龙·颂赞》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1]自秦汉以来,不仅诗、文这些传统体式中有“美盛德而述形容”的颂体存在,至词体兴盛的宋代,也相应出现了美颂的颂体词。目前学界较少有研究者以“颂体词”这一称谓对宋代的歌功颂德之词进行研究(1)目前以“颂体词”称谓关注到宋代美颂词作的仅有陈登平《北宋王朝的颂歌——论柳永颂体词》和赵惠俊《朝野与雅俗:宋真宗与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等少数论文、著作。,多以“祝颂词”“谀颂词”“应制词”等相近名称研究相关词作。但这些歌功颂德的词作并不都是应制而作,功能不仅仅用于祝寿,创作目的也不全是出于谄谀,在内容形态上应更加符合前述“美盛德而述形容”的含义。因此,将这些颂圣、歌咏太平的歌词称为“颂体词”较为恰当。
颂体词从北宋太宗朝就已出现,与宋王朝的礼乐建设与舆论营造息息相关。但目前学者以“祝颂词”“谀颂词”“应制词”等名目对颂体词展开的研究,多集中在颂体词繁盛的北宋徽宗朝和南宋孝宗朝,对承前启后的高宗朝颂词的探讨较为缺乏,对其中代表性的颂体词人曹勋、康与之的关注也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拟以曹勋为中心,考察高宗朝后期颂体词创作的承继与新变。
一、中兴盛世的营造:颂体词的复归与词人心态
颂体词至徽宗朝发展至高峰,为徽宗君臣“丰亨豫大”之说渲染盛世景象。靖康之变后,建炎年间,颂体歌词被视为亡国之音,高宗停止了多数节庆祭祀宴饮活动,并废置了教坊等音乐机构,颂歌一度沉寂。但到了高宗朝中后期,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太平歌词又重新出现并兴盛。
(一)谀颂之风与礼乐重举:高宗朝后期颂歌的复归
颂体词在高宗朝后期的复归,与当时谀颂之风的盛行和礼乐的重举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高宗对颂体的态度转变推动了颂体文学的盛行。绍兴和议之前,高宗与臣子以“中兴”为目标,号召将官“各务立功报国,共济中兴”[2]990;建炎年间,高宗还下诏禁止徽宗朝以进颂得官的官员南渡后重新得官[2]335,可见对颂体的遏制之意之坚。然而,绍兴十二年达成和议后,战事消停,高宗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赐诏秦桧曰:“朕闻贤圣之兴必五百岁,君臣之遇盖亦千载。……非乔岳之神无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任贤无以致中兴。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荣哉。”[3]2802高宗认为天下已然安定,“绍祚中兴”的大业已成,将秦桧比作古时贤臣,将自己视为周宣王一般的“中兴之主”。此时,高宗对颂体的态度转为大力提倡,要求士人言论和文学创作以渲染太平为主。“天下幸已无事,惟虑士大夫妄作议论,扰朝廷耳。治天下当以清净为本,若各安分不扰,朕之志也。”[2]2359他否定士大夫自由言政的权利,并要求他们为所谓的盛世营造相应舆论。婺州进士施谔“进中兴颂、行都赋各一首,绍兴雅十篇”,高宗便“诏永免文解”。其他进献颂体者,也都获得了物质赏赐或官位的提升[2]2748。按照帝王意志,宰辅秦桧更是以高压手段进行发挥,他实行文禁与语禁,从舆论和思想上控制打压异论[4],令科考试题均与“中兴歌颂”密切相关[3]13458,还不断创造出所谓盛世“祥瑞”。高宗君臣在根本上确立了颂体的地位,使绍兴后期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谀颂之风,无论是诗还是文、赋,均有大量歌功颂德、渲染太平的颂体作品出现。
与谀颂风气兴起相呼应,高宗在绍兴和议后下令重举礼乐,恢复了颂体歌词的生存条件。要渲染太平,礼乐自然不可缺少,韦太后的归来正是一个重要契机。绍兴十二年,高宗以迎奉韦太后为由,下诏解除了建炎年间的乐禁,“初以梓宫未还,故辍乐以待迎奉。至是太母还宫,将讲上寿之礼,故举行焉。”[2]2359绍兴十三年,曾被搁置的宫廷音乐机构重新补全人员,“(五月壬戌)太常寺言:‘郊祀仗内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乐工全阙,乞下三司差拨。’从之。”[2]2393同月天申节庆典,宰臣率百官上寿,奏乐阵仗、宴饮布置都恢复到了以往的宏大规模,“皆如承平时”[2]2395。不仅雅乐,教坊也获得了新生,绍兴十四年二月,“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十六人,以内侍充钤辖”[2]2426,燕乐重新拥有了发展繁盛的现实空间。
在谀颂盛行的背景中,乐禁的解除无疑为颂体提供了新的助力,早在北宋就发展成熟的颂体歌词由此在高宗朝后期重新兴盛,和颂体诗、文、赋一起构建出帝王理想中的“中兴”盛世景象。
(二)谄谀、认同与畏祸:颂体词人的创作心态
高宗朝后期,以颂体词创作参与到盛世歌咏中的作者颇多,身份各有不同。既有在京城和地方任职的普通官员如叶梦得、周紫芝、朱敦儒;也有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如康与之、曹勋。其中,曹勋、康与之等帝王近侍与周紫芝等人相比,有“出入两宫,奉清燕之闲,最承宠眷”[5]的机会,所作颂词以应制为主,数量更多,主题也更加集中,堪称当时颂体词创作的代表。
由于身份与政治态度的不同,这些词人的创作心态也复杂多样。部分文人以谄谀权臣为目的,或者真心认同绍兴和议后的所谓太平局面,因而主动献上颂歌。康与之就是颂圣以谄谀的典型。他因附会秦桧而得官,在宫廷之中专为“中兴”歌词[6],自然主动地歌功颂德。其为秦桧祝寿的《喜迁莺》,“宝运当千,佳辰余五,嵩岳诞生元老”“篆刻鼎彝将遍,整顿乾坤都了”[7]1689,将秦桧描述为开创伟业的元勋。周紫芝持主和立场,曾上书高宗,认为面对强大的金人应以“自治”为上策[8],因此和议后的局面自然与其本意相符。其《水龙吟·天申节祝圣词》就出于这种认同的心态,“万国朝元,百蛮款塞,太平多少”[7]1128可以说是心声的表露。
还有一部分文人,他们经历了南渡战乱,持有主战立场,对求和苟安的局面不可能做到真心认同,但在高压政治和谀颂风气的影响下,出于避祸心理,也不得不跟随时俗歌颂所谓盛世。如曾作诗痛斥秦桧、作词支持李纲和胡铨的张元幹也有《瑞鹤仙》《瑶台第一春》等为秦桧祝寿的颂词,将秦桧形容为“贤佐兴王”“千官师表,万事平章”[7]1423的贤相。曾主战的朱敦儒也在绍兴和议后为“瑞雪”创作颂词,为盛世“祥瑞”造势。
近臣曹勋也与上述心态离不开关系。他曾受徽宗半臂绢书逃归,先是主战,要求以武力迎回徽宗,因此忤逆秦桧,后自请身退而奉祠闲居。但在看到绍兴和议后的安定局面之后,其态度又转为主和。在时局之中,曹勋既有“自怜怯事如欣泰,止合抠衣扣子长”[9]的避祸心理,也有对“君臣之意定,则天下自定”[10]中兴局面的主动支持。政治态度之外,还有现实身份的影响。曹勋虽不是如大晟词人与康与之那样专职作应制歌词之人,但他曾担任知閤门事,不得不受到“掌朝会宴幸、供奉赞相礼仪之事”[3]3936职责的限制,在祝寿、宴饮、圣驾出游等场合创作出为皇室装点太平的应制歌词。正是在这样主动与被动糅合的复杂心态之下,曹勋写下了大量渲染太平的颂词。
二、颂圣与富丽:北宋颂体词传统的延续
高宗朝后期颂体词首先承袭了北宋颂词的创作传统,即称颂升平的内容与富丽雍容的审美风格。
(一)彰显升平:颂体词的基本内涵
作为颂体词,称颂太平盛世自然是基本主题。具体而言,祝寿颂词和节序颂词是其中两种不变的内容类型。祝寿颂词一般是为帝王、皇室祝寿而作,词中渲染功绩,描述寿典场面,塑造出庄严的帝王或后宫成员形象。如晏殊《喜迁莺》作于仁宗圣节所设的“象筵”间,并付与宫廷歌妓,配乐歌以劝寿酒[11]。王安中有《征招调中腔·天宁节》为徽宗祝寿,以溢美之词歌颂帝王功业[7]971。节序颂词则摹写节日盛况以彰显社会的安康繁荣。遇元夕、清明、中秋,皇帝与臣子常会出游或举办宴饮[12],万俟咏《三台·清明应制》就展现了清明时节朝野上下的太平欢庆[7]1047。
以曹勋为代表的颂体词人继承了这两大内容类型。一方面是祝寿颂词。称颂帝王的如《玉连环·天申寿词》,是曹勋为高宗生辰所作祝寿颂词。“端景命、符圣德,三阶正、万国归化,远胜文思睿藻,问寝格中天”(2)本文所引曹勋词均出自《全宋词》对松隐词的收集整理(唐圭璋编纂、孔凡礼补辑:《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标出。,上片数语铺陈宋高宗德行的至高无上与功业的巨大影响;“宫闱罄和气,浃南山。罩翠霭、上寿烟。祝无疆御历万万年。”下片结尾语句则是在一篇祥和与恢弘的场景之中,对君王发出万寿无疆的祝颂。在这首词中,一个建立了丰功伟业、开创了太平天下的圣君、明君形象跃然纸上。
曹勋还有为韦太后祝寿之作。作为出使金国迎回韦太后的功臣之一,曹勋自然对韦太后怀有特殊的感念之情,在太后诞辰时创作了一系列祝寿词,包括《大椿》《花心动》《保寿乐》《宴清都》等。以《大椿·太母庆七十》为例,“慈颜绿发看更新,玉色粹温,体力加健”数语勾勒出韦太后慈爱庄严并存的形容与气盛身健的精气神;“龙章亲献龟台祝,与中宫、同诚欢忭。亿万斯年,当蓬莱、海波清浅”则是在高宗亲自率众祝寿的盛大场面中,为太后献上长生的祝愿。词既赞颂了太后的形神与威仪,又突出了帝王的圣孝与场面的和乐盛大。
另一方面是节序颂词。以《东风第一枝·元夕》为例:“散万斛金莲,崇山秀岭,尽开花径”“月灯相映”写上元夜灯火辉映的美景,“四部箫韶,群仙奏乐,万光耀境”述奏乐开筵的繁盛,从视觉和听觉上呈现出治世的安乐美好,并在末尾以“真个乐,圣驾游幸”直接点明颂圣的主旨。不只是元宵,曹勋词中还表现了“佳丽拥缯筵,斗巧嬉游”的七夕妇女乐事以及“角黍星团,巧萦臂、龙纹轻缕。细祝降福天中,列箫韶歌舞”的宫廷端午风情等场面,落脚点都在于表现禁御的气象与社会的安宁。
因此,曹勋的颂体词在祝寿和节序书写方面,都继承了北宋以来颂体词的基本内容,顺应帝王意志,力图烘托“禁御中兴气象”[13]。祝寿词在渲染皇室成员的圣德形象和伟大功绩的同时,祝寿以颂圣;节序词则在摹写节日盛景中,构建出太平盛世的缩影。
(二)富丽雍容:颂体词的主要风格
与颂圣的内容相适应,曹勋颂体词在审美风格上也有着典雅、雍容、富艳的特点。无论是意象的选用还是语言手法的运用,曹勋都与北宋颂体词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一方面,意象的选用以富丽形态为主。北宋的颂体词意象多集中于富艳华贵之物。如:“瑶阶树,金茎露。玉辇香盘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14](夏竦《喜迁莺》)“斗储祥,虹流祉,兆黄虞。”[7]643(贺铸《天宁乐·铜人捧露盘引》)“玉辇”“珠翠”是与宫廷、帝王密切相关的富贵形象,“虹流祉”则是祥瑞,是治世与明君的象征。这些华贵典雅的意象形成了一套专用的意象系统,柳永就因曾在颂体词《醉蓬莱》中使用了“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这类“竹篱茅舍间”意象而被指责为不得体[15]。
曹勋的颂体词沿用了此意象系统。如:
应乘干、彩虹流渚,惊电绕、璇霄枢斗。
(《绿头鸭·圣节》)
罩翠霭,上寿烟。
(《玉连环·天申寿词》)
霜落鸳鸯,绣隐芙蓉小春节。
(《一寸金·太母诞辰》)
梅拥繁枝,香飘翠帘。钧奏严陈华宴。
(《大椿·太母庆七十》)
金殿箫韶备设。……赭袍绣拥,袆翟同诚,递捧玉杯欢悦。
单环刺螠体壁有较高的营养价值[1],体壁占整体质量的32%左右,单环刺螠体壁肌中氨基酸含量占体壁肌干重的57%,粗蛋白质22.84%、粗脂肪4.24%、粗灰分2.92%[3],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且组成模式与人体非常相近,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精氨酸、丙氨酸和甘氨酸5种呈味氨基酸[4-5]。
(《花心动·太母庆七十》)
可以看出,无论是天文自然、动植物、乐器还是陈设物品、建筑空间,其所使用的形象都与前人一样,与皇室身份、宫廷环境相互呼应。天文意象常用“虹”“电”“翠霭”“翠云”等,多与象征着圣君的祥瑞相关,也是词人用以颂圣的铺垫与契机;景物和动物以“鸳鸯”“芙蓉”“花柳”等秀丽形象为多,正与宫廷典雅富艳的氛围相衬;音乐意象是“箫韶”“丝簧”“仙乐”,呈现治世安乐之音;服饰形象是“赭袍”“袆翟”“翠衮”“冕旒”等皇室成员专用,代表地位之尊贵;陈设用品是“翠帘”“锦绣”“罗绮”“玉杯”“雕舆”等物品,无不凸显出宫廷器物的华贵;建筑使用“金殿”“绛阙”等语,烘托着宫殿的恢弘与辉煌。这些意象虽然种类不同,但在指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具有富丽雍容的特质。
与富艳意象相配合的,是铺陈与夸饰的手法。首先是铺陈,这在颂体慢词中较为常见,自柳永就已经开始,其《御街行》就是借鉴了赋法,铺叙宋真宗南郊祭天盛典的场面[16]。曹勋颂体词也采用类似方式来表现宴饮、节序等活动场景。如《一寸金·太母诞辰》:
霜落鸳鸯,绣隐芙蓉小春节。应运看,月魄分辉,坤顺同符,文母徽音芳烈。诞育乾坤主,均慈爱、练裙岂别。经沙塞、涉履烟尘,瑞色怡然更英发。上圣中兴,严恭问寝,宫庭正和悦。看寿筵高启,龙香低转,声入霓裳,檀槽新拨。翠衮同行乐,钧韶奏、喜盈绛阙。倾心愿、亿载慈宁,醉赏闲风月。
上片以自然环境起始,转入对太后仪容的叙说描绘,下片进一步使用赋法铺陈的方式展现寿宴场面,从皇帝恭祝太后写到寿宴开启,继而铺叙寿宴之上的舞女霓裳、乐曲歌声,并渲染宫殿之内的和乐氛围。词人以赋法铺陈的方式,逐步呈现太后帝王形象和寿宴之上的祝寿及娱乐活动场景,其中的庄严盛大被铺叙的笔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曹勋的节序颂词中也有铺陈之法的使用,将节序景象、节庆习俗、民众场面、圣驾游乐等节日相关场景一一勾勒出来,渲染百姓的安逸与君民同乐的盛况。
另一方面是夸饰,最常见的就是使用一系列夸大的数字来凸显气势的恢弘。这也是前人颂词的一大传统。如:“四海一家同乐,千官心在玉炉香”(晏殊《喜迁莺》)夸饰君主的臣民之众,“三千从赭黄”(万俟咏《明月照高楼慢》)形容君王随侍规模的盛大。曹勋词也不例外:
亿万斯年,当蓬莱、海波清浅。
(《大椿·太母庆七十》)
愿将亿万喜,住亿万、从兹无缺。
(《花心动·太母庆七十》)
和气暖回元日,四海充庭琛贡至。
(《保寿乐·太母庆七十》)
三阶正、万国归化。
(《玉连环·天申寿词》)
可以看到,夸张的数字在曹勋颂体词中出现较多,其中“亿万”等数字使用频率极高。特别是在祝寿颂词中,用“百岁”“千岁”作为祝福语已然不够,乃至以“亿万”来祝颂皇室福寿绵长。还有“四海”“万国”等数字词,显然也都不是写实之语。词人通过这些夸张甚至是极端的字词,营造出宏大气象,烘托帝王功业之伟大与圣恩之浩荡,达到歌功颂德的目的。
曹勋的颂词具有歌咏太平的内容与富丽雍容的审美风格,这正与帝王意志相合,承担起为君主营造盛世的政治功能。高宗朝后期,其他词人的颂歌也具有相同风貌。以周紫芝《水龙吟·天申祝圣词》为例,词中充溢着“青虹”“黄金双阙”“建章宫阙”“红鸾影”“云韶声”等华贵与祥瑞的意象,并结合祥瑞景象和祝圣场景的铺陈以及“万国朝元,百蛮款塞,太平多少”的夸饰,赋咏绍兴和议后的承平气象,同属富艳雍容之作[7]1128。此外还有康与之的元夕颂体词、朱敦儒的咏祥瑞之词等等,均具有类似特点,可见高宗朝后期对北宋颂词内容艺术基本风貌的承继。
三、丰富与雅化:高宗朝后期颂体词的新变
在承继北宋颂体的基本面貌之外,以曹勋为代表的高宗朝后期颂体词人还进行了一些革新,主要体现在题材与形式的丰富与内容意趣的雅化。
(一)题材形式的丰富:咏物颂词与音律出新
曹勋在题材方面将咏物词与颂体相结合,以咏物来称颂帝王、彰显太平;在形式上,则试图对部分北宋词调音律进行革新。
其一是咏物颂词的出现。咏物词自北宋前期就已成熟,柳永、苏轼、周邦彦都有不少咏物佳作,但在南宋之前,咏物词几乎未曾被运用到颂体词的创作当中。这种情况在高宗朝后期得到了改变。高宗朝后期一直到孝宗朝,宫廷中时常举行赏花宴游活动[17],这就为曹勋等人创作咏花应制的咏物颂词创造了现实条件。从存世的曹勋作品中,可以看到吟咏主要对象正是各色花卉。如咏牡丹的有《金盏倒垂莲·牡丹》《诉衷情·宫中牡丹》、咏海棠的如《风流子·海棠》《蜀溪春·黄海棠》、咏丹桂的有《浣溪沙·赏丹桂》等,总体咏花之作有《朝中措·酴醿芳架引繁英》《隔帘花·咏题》。此外还有咏枨之作《浣溪沙·赏枨》。
这些咏物颂词的内容模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描摹物态与直接颂圣相结合。如咏枨颂词:“禁御芙蓉秋气凉,新枨岂待满林霜,旨甘初荐摘青黄。乍剖金肤藏嫩玉,吴盐兼味发清香。圣心此意与天长。”先是写赏枨环境与过程,后描写模样、味道与香味,最后以一句直白的颂圣语“圣心此意与天长”收尾,显示出皇恩之浩荡。
另一种咏物颂词没有直接颂圣的话语,而是通过对所咏之物的描写,侧面烘托出“禁御中兴气象”,具有含蓄隽永的意味。以《金盏倒垂莲·牡丹》为例:
谷雨初晴,对晓霞乍敛,暖风凝露。翠云低映,捧花王留住。满阑嫩红贵紫,道尽得、韶光分付。禁御浩荡,天香巧随天步。群仙倚春似语。遮丽日、更着轻罗深护。半开微吐,隐非烟非雾。正宜夜阑秉烛,况更有、姚黄娇妒。徘徊纵赏,任放蒙蒙柳絮。
词人从牡丹所处的自然环境写起,到描写它“满阑嫩红贵紫”的姿态,再到“天香巧随天步”,以花香引入帝王赏花的仪容,巧妙精致。下阙则进一步表现牡丹花的艳丽与朦胧,并设想夜赏牡丹的欢愉情形。全词表面上主要呈现牡丹花的姿态与赏花情形,实际则通过描写牡丹花之富艳与宫廷赏花的悠闲和乐,衬托出“禁御浩荡”的气象,达到赞颂升平的目的。这类咏物颂词不是个例,如另一首咏牡丹的《诉衷情·宫中牡丹》“绮罗金殿,醉赏浓春,贵紫娇红”,也同样采用了类似笔法。
不只是曹勋,其他颂体词人也有咏物颂词。如康与之《舞杨花》,作于陪侍帝王慈宁殿赏牡丹之时,其词调为高宗自制曲[18]454。上阙摹写牡丹花经雨之后的“娇困倚东风”的娇妍姿态,下片开始展现后宫赏花宴饮的盛况,虽没有直接颂圣,但“三十六宫,簪艳粉浓香”“慈宁玉殿庆清赏”“良夜万烛荧煌”等话语侧面烘托出了富贵和乐的气象,摹写太平而意蕴绵长。在这些词人笔下,咏物词不再是单纯的游艺之作,而是顺应帝王统治意志,承担了彰显太平的政治功能。
其二是音律形式的出新。与咏物颂词的普遍性不同,音律形式的革新主要是曹勋个人的成就。曹勋父曹组曾担任过徽宗朝睿思殿应制,精通音律。受其影响,曹勋也熟知词的音律,并将这种才能运用到颂词音律的革新上。最主要表现在词调的使用方面。曹勋颂词所用词调并不限于常见词调,而是更偏向于前人较少使用的词调,甚至自创新调。首见于《松隐乐府》的调名有二十一种之多[19],其中用于颂体的就有《大椿》《保寿乐》《隔帘花》《夹竹桃花》《赏松菊》《十六贤》《清风挂满楼》《六花飞》等等,以新声渲染太平。这些词调的流传程度不高,可能是由于其音律之雅与演唱难度之高,导致其与民间传唱存在一定的距离,因而传播范围仅限于宫廷及近臣,没有进一步流播、发展的空间。但从留存至今的曹勋词作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为革新颂体词形式所作出的努力。
(二)内容的雅化:文人意趣的融入
高宗朝后期颂体词的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在内容层面的雅化,颂体词不再停留在纯粹的歌功颂德,而是在承担政治功能的同时融入词人的主体意趣。
这与高宗朝兴起的复雅风潮有关联。一方面,君王自身尚雅鄙俗。曹勋父曹组擅长写滑稽词,为“滑稽无赖之魁”,得到徽宗的赏识,但高宗对此却颇有厌恶(3)据王灼《碧鸡漫志》记载,曹勋曾为其父编辑刻印家集,尽管没有收录滑稽词,但高宗听说后仍然“有旨下扬州毁其板”,禁止了曹组词的流传。。另一方面,当时词论中多有对雅观念的推崇:鲖阳居士《复雅歌词》标举“复雅”“骚雅之趣”[20],崇尚雅正而摒弃浮艳,以儒家传统的诗乐观为依据;曾慥编选《乐府雅词》,在《乐府雅词序》中阐明了他“涉谐谑则去之”原则,认为“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将其艳词以“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而“今悉删除”[21]。颂体词人将这股风潮反映在了创作中,让颂词不再是对前人富艳雍容一面的复刻,而是在为帝王歌颂太平的过程中,融入了属于文人自我的风雅意趣。
这种倾向在新兴的咏物颂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曹勋《临江仙》:
中秋夜,禁中待月遐观,清风袭人,嘉气满坐。前夕连阴,至此顿解。少间,月出云静,瞻天容如鉴。上喜,以诗句书扇,臣谨以临江仙歌之。
连夜阴云开晓景,中秋胜事偏饶。十分晴莹碧天高。台升吴岫顶,乐振海门潮。桂影一庭香渐远,四并都向今朝。宸欢得句付风骚。围棋消白日,赏月度清宵。
词序正文都是在书写禁中赏月的和乐场景。上片先是叙说赏月缘起,接着展开“中秋胜事”。“十分晴莹碧天高”,在高悬的明月照映之下,可见高耸的楼台亭阁,耳闻震撼的丝簧仙乐之声,还有似有若无的淡淡桂香萦绕其中,一时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兼备,帝王也不禁被感染,以诗句书与扇面而赐给作为近臣的词人,“围棋消白日,赏月度清宵”,在和乐欢愉的氛围中,君与臣共同下棋、赏月,一起度过这美好的白日清宵。
这首颂体词,与以往的颂词存在较大的差别,虽也是应制之作,但较少有华贵富艳之气。一方面,对景的描写不再是华贵意象的铺陈,而是着重表现月光之清与月影笼罩下的环境之优美,突出景物背景的清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词人在清雅的场景之中,进一步写出了赋诗、书扇、下棋、赏月这一系列以往多出现在文人相交之时的风雅活动,消解了通常颂词中君主的圣人光环与臣子的伏首姿态,展现君臣双方相通的文人情趣,为“禁御中兴气象”增添了风雅的一笔。
曹勋类似的词还有不少,都是在称颂皇室的同时融入了主体情趣,以文士视角在庄严的颂词中增添风流元素。如在为太后祝寿时,以“倾心愿、亿载慈宁、醉赏闲风月”(《一寸金·太母诞辰》)为结语,将文人闲雅的生活姿态融入对太后的祝福中;在陪侍君王赏海棠时,将君王仪容与花容并提,“待得君王,看花明艳,都道赭袍同光”(《风流子·海棠》),帝王身姿与花色融为一体;还有词人的自我放言“须是对花满酌,不醉无归”,俨然一个沉醉花间的放浪名士。在这些颂体词中,君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庄严圣君,而是一名吟赏风月的风雅天子;词人也不再是仰望君主的近侍与粉饰太平的谀颂者,而仿佛是醉看盛世的才子雅士。
曹勋作为皇帝近臣,其应制颂词尚且能融入文人情怀,其他非近臣的颂体词人就更有可以书写文人风雅意趣的空间,朱敦儒的数首颂词就是如此。咏瑞雪时,“直须听歌按舞,任留香、满酌杯深。最好是,贺丰年、天下太平”[22]91(《胜胜慢·雪》),中秋赏月时,面对“桂子香浓凝瑞露,中兴气象分明”,心中所想是“今宵谁肯睡,醉看晓参横”[22]123(《临江仙·中秋》),在所描绘的太平盛景中举觞吟咏,醉赏风月。在谀颂之风弥漫的高宗朝后期,曾唱出“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的朱敦儒作颂体词虽不是出于本意,但仍在这无奈的颂歌书写之中,或有意,或无意,展现了属于自我的风流不羁的意志情怀,为颂体词的发展添加了一抹风雅的新色彩。
高宗朝后期复归的颂体歌词在宋代颂词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首先,这一时期的颂体词依然是特定政治需要下的产物,承担着为帝王渲染太平的政治任务。无论是近臣曹勋、康与之,还是朱敦儒、张元幹等普通官员,他们的颂体词都有特定的歌功颂德主题与固定的富丽雍容的风格,这些特点均体现了对北宋颂体词传统的承继。
而在继承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朝后期颂体词的新变。这些颂体词并不是对前人颂词的简单复制,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潮的涌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题材上,咏物颂词开始出现,咏花、咏月这些以往主要表现词人个体情感的题材被运用到了歌咏太平当中,拓展了传统颂词的表现范围。在形式上,曹勋力图在颂体词音律上有所创新,虽未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但也成为革新的一部分。而在内容意趣上,颂体词更是添加了文人特有的风雅情调,使颂词不再是帝王意志控制下单纯歌功颂德的工具,而是或多或少地开始与士人主体的意识情调相关联,大大丰富了颂体词的格调境界。
颂体词在高宗朝的复归,无疑是宋代颂体词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是北宋颂体词发展至徽宗朝达于鼎盛的延续,更是随后孝宗朝颂词创作新一轮高潮到来的先声。“应制燕闲,未可轻视”[18]451,此后曾觌、张抡、吴琚等新一代颂体词在咏物题材上的深化和文人意趣的进一步融入,与此前康与之、曹勋、朱敦儒等高宗朝后期颂体词人的努力离不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