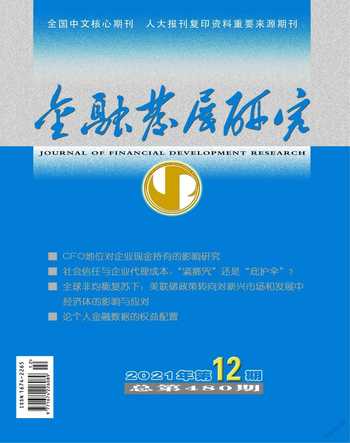论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
宋天骐
摘 要:民法典新增的保理合同是对商事实践的总结,对保理合同的解释应当结合保理实践的法律规范和行业准则。保理合同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要素,以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为限选要素,以账款管理和账款催收为任选要素的商事合同。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集中体现了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二者必有一项为保理合同的内容。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理商享受的追索权担保,二是虚构基础交易时保理商的保障。保理合同担保功能的实现体现于担保竞存时的权利顺位,而权利顺位则需要区分不同情形具体分析。
关键词:民法典;保理合同;担保功能;担保竞存
中图分类号:F840.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1)12-0077-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12.010
为适应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推动商业保理健康、有序、规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合同编第二分编“典型合同”中增设了“保理合同”。保理合同是一种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但因《民法典》对保理合同的规定较为简单,有关担保的内容和相关规则并不十分明晰,尚须依解释论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本文拟从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入手,就保理合同对保理商的担保功能作一解析。
一、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
(一)保理合同担保功能的基础——应收账款转让
应收账款转让的要义应从两个方面厘清:一是应收账款的法律内涵,二是应收账款转让的独特性。
1. 应收账款的法律内涵。“应收账款”并非法律概念,而是会计概念。从适用主体来看,按照国际保理业务通行规范,其范围不包括以自然人应收账款转让为基础的保理合同①。《国际保理通则(2019年版)》虽然没有明确排除自然人应收账款的适用,但其对国际保理交易当事人的规定实际上排除了适用以自然人应收账款转让为基础的保理合同②。《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以下简称《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4条规定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同样明确排除了自然人应收账款的适用情形。从适用范围来看,《民法典》允许“将有的”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合同③。从我国目前针对未来应收账款的法律规范来看④,原银监会颁行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保理暂行规定》)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对未来应收账款叙做保理融资业务⑤;银行业协会施行的《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以下简称《保理业务规范》)也禁止针对未来应收账款发放保理融资⑥。但从国际上看,法律并不禁止未来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合同。例如,《国际保理公约》第5条规定,合同订立时或应收账款产生时,可以确定的未来应收账款自产生时起自动转让给保理商,无须新的转让行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也对“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作出了明确规定,如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23条第3款(朱晓喆,2019)[1]、《日本民法典》第466条第6款(王融擎,2018)[2]、《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204条(a)等。
2. 应收账款转让的独特性。在实践中,保理业务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应收账款转让(陈娇,2019)[3]。在学理上,学界对保理合同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一定共识,即应收账款转让是保理合同的核心要素(李宇,2019;黄和新,2020;裴亚洲,2020)[4-6]。
在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与通常的债权让与、应收账款质押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转让不适用于自然人,而债权让与、应收账款质押并没有这种限制。第二,相比于应收账款质押,应收账款转让的公示方式为通知,登记只发生确定应收账款清偿顺序的优先效力,并不是转让的生效要件;而应收账款质押的公示方式为登记,且登记是质押的生效要件。第三,在应收账款转让中,“转让”应采扩张解释,即质押为转让的特别形式。从既有規范来看,《保理暂行规定》和《保理业务规范》对“转让”采狭义解释,规定应收账款质押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笔者认为,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宜采扩张解释,认可应收账款质押的保理合同效力。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在解释论上,上述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或行业规范的管理性规定,并不影响应收账款质押的保理合同效力(方新军,2020)[7]。其二,尊重和保护商事实践。在实践中,应收账款质押的保理合同并不少见,部分法院也对该类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⑦。其三,顺应国际保理业务的通行规则。在国际保理中,以应收账款质押为基础的保理合同已经成为共识(朱勇,1994)[8]。其四,应收账款转让与质押对保理商的意义相同,两者都属于信用担保,而非保理商取得保理合同收益的主要来源,保理合同的收益主要来自融资款利息和保理费用(朱勇,1994)[8]。
(二)保理合同担保属性的表现形式
《民法典》第761条对保理合同的界定与我国关于银行保理的既有规范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民法典》未明确资金融通、付款担保、应收账款管理和催收等四项保理商服务在保理合同中的地位,而银行保理的既有规范则明确规定保理合同应至少具备上述四项内容之一。简言之,对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服务内容的约定关系到保理合同的金融属性(王锐,2019)[9]和担保属性。
根据保理合同所约定的业务范围,保理可以分为完全保理与非完全保理(朱勇,1994)[8]。完全保理的金融属性和担保属性毋庸置疑,而非完全保理则涉及应当具备哪项服务内容的问题,学界对保理定义的分歧便在于此。有学者遵从我国银行保理的规范,认为保理合同只要具备任意一项服务内容即可(李宇,2019;徐同远,2019)[4,10]。笔者认为,保理合同的服务内容应作限缩解释,将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作为保理合同的限选要素(方新军,2020)[7]。如果仅以应收账款管理或催收为服务内容,那么保理合同的金融属性和担保属性便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单纯的应收账款催收业务可能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即催生以债务催收为业的“讨债公司”,进而引发可能的不法催收、暴力催收等情形,这也是保理业务监管中较为重要的监管内容⑧。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因应收账款催收而引发的保理合同纠纷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保理实践中以应收账款管理或催收为独立内容的保理合同并不多见⑩。由此可见,应收账款催收或管理一般不作为保理合同的独立内容,而是作为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服务的附属。
就保理合同的内容而言,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主要体现在资金融通和付款担保两个方面。在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到期提供的保理融资款是取得应收账款的对价,此时该保理融资款间接承担了一定的付款担保功能。
就文义解释而言,付款担保应解释为:在应收账款转让的前提下,保理商承担债务人违约风险,向供应商清偿应收账款。这意味着供应商将债务人的违约风险转移给保理商,此时应当适用于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
此外,资金融通与付款担保无法共存,其原因在于二者共存会使得供应商获得超出应收账款价值的超额利益,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同时,资金融通与付款担保都是一种金钱给付义务,二者共存意味着保理商负有两项内容相似的义务,而供应商却只负担一项应收账款转让义务,显然这种义务失衡是不合理的。
二、保理合同对保理商的担保功能
(一)保理商享有的追索权
《民法典》第766条规定了保理商的追索权,但并未明确追索权的含义和行使条件。
就追索权的文义而言,保理商在应收账款债务人未付款时,才有权向供应商主张权利。因此,追索权应当是指保理合同约定的事由发生时,保理商向供应商主张的权利,包括保理融资款本息返还请求权和应收账款回购请求权。需要注意的是,《保理暂行规定》和《保理业务规范》对返还请求权的返还范围规定为“融资”, 而《民法典》将返还范围界定为“融资款本息”。
追索权的行使条件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约定的追索权条件,另一类是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约定的追索权回复条件。就前者而言,追索权条件一般为应收账款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由于《民法典》并未规定追索条件,因此,只要当事人约定的追索条件不违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该追索权就应当成立;就后者而言,追索权的回复条件需要具体分析。从《民法典》体系来看,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是可以回复追索权的,其条件主要包括三种:第一,供应商虚构应收账款,且保理商不知情;第二,发生商业纠纷,如应收账款债务人对应收账款享有抗辩权、抵销权等;第三,发生其他非因应收账款债务人信用风险的情况⑪。
第一种情形下,保理商追索权回复的理由主要在于,供应商虚构应收账款构成欺诈。依据《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作为受欺诈方的保理商有权请求撤销保理合同,但撤销合同须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且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而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追索权的回复显然轻于撤销权的行使,保理商通过行使追索权也可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第二种情形下,保理商追索权回复的理由主要在于,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相当于以应收账款为标的的买卖合同⑫,作为保理合同相对人的供应商负有应收账款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徐涤宇,2019)[11]。因此,在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致使保理商无法得到清偿时,保理商有权向供应商行使追索权。
第三种情形下,保理商通常还会因应收账款被冻结或他人主张权利等非应收账款债务人信用风险而无法回收应收账款。此时,保理商追索权回复的理由与第二种情形相同。从反面解释来看,如果追索条件覆盖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就会使得买断型保理合同中供应商优化财务的目的无法实现(田浩为,2015)[12]。
(二)虚构基础交易的保理商保护
就虚构应收账款而言,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基础交易双方当事人虚构应收账款,二是供应商与保理商虚构应收账款。在第一种情形下,“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其法律含义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供应商与应收账款债务人构成“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无效;第二层次是当应收账款债務人明知应收账款会作为保理合同的标的,仍与供应商恶意串通,损害保理商利益,依据《民法典》第154条规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虽然虚假民事法律行为与恶意串通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相同,但虚假民事法律行为规制的是恶意串通手段的行为效力,并不能全面顾及恶意串通结果的行为效力,因此,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并不能替代恶意串通(张平华,2017)[13]。在第二种情形下,供应商与保理商虚构应收账款构成“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该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无效,供应商应当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保理合同而言,“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商,其法律含义在于虚构的应收账款仅在基础交易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保理商不受保理合同标的虚假的债务人抗辩的限制。然而,保理商明知应收账款为虚构时,其并非基础交易合同的善意第三人,应承受相应的不利后果。应当注意的是,第一,保理商明知虚构并不是指保理商与供应商虚构应收账款;第二,保理商应知而未知虚构时,其仍有权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债权。《民法典》第763条仅规定“保理人明知虚构”,将保理商应知虚构排除在外,实属有意为之,其原因在于保理商应知而未知可构成追索权的回复,为保理商提供更大程度的担保,以减少保理商的坏账风险,推动保理业务的稳健发展。
理论上,发生虚构应收账款纠纷时,保理商的救济方法主要包括三种(李宇,2019)[4]:其一,善意保护制度下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同等付款责任,即基于应收账款的权利外观,将虚构的应收账款视为真实应收账款,由债务人向保理商清偿应收账款⑬;其二,侵权赔偿制度下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债务人侵害保理商对供应商享有的保理融资款债权,应在供应商未能偿还的保理融资款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⑭;其三,应收账款债务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受让应收账款的保理商作为债权人,有权因债务人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虚构行为而向其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众所周知,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范围是当事人的期待利益,而期待利益通常小于履行利益。善意保护制度和侵权赔偿制度均保护保理商的履行利益,但《民法典》第763条选择了善意保护制度,其主要原因是尊重传统民法中债权相对性的理论,强调虚假民事法律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体系思维。
在实践中,应收账款债务人参与虚构应收账款的情形主要包括书面确认应收账款、放弃对保理商的抗辩权、恶意欺诈或串通等。但是,债务人仅以书面形式确认应收账款可能并不构成真正的虚构应收账款,也就不需要向保理商清偿应收账款。换言之,在虚构应收账款中,需要平衡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务人两方的利益,避免倾斜保护保理商而忽略可能受害的债务人。因此,对“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的解释,应明确债务人参与虚构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即债务人参与制造虚构的权利外观,并以书面形式固定该权利外观⑮。依照这种限缩的解释路径,可以平衡保理商与债务人的利益,从而规范保理商“信假为真”的善意和督促其审慎核查应收账款,避免因“合同公信力”的形成而冲击物债二分的基本逻辑。
三、担保竞存时的利益平衡
在理论上,应收账款的担保竞存应限于一种情况,即应收账款本身存在多重负担,主要原因在于应收账款可以解释为保理合同中的“担保物”⑯,该“担保物”由非保理合同的债务人“提供”⑰,只有当该“担保物”上存在多重负担时,权利竞存才会发生。
(一)应收账款多重保理
《民法典》第768条规定了应收账款多重保理的顺位规则,但对该条的适用规范应当具体分析:第一,在规范对象上,该条仅规范应收账款债权人即供应商转让应收账款的情形,保理商就同一应收账款转让并连续叙做保理合同并非本条的规范对象。第二,在规范标的上,本条强调同一应收账款,换言之,多个应收账款转让并不适用本条。第三,在因果关系上,供应商的多重转让行为导致多个保理合同同时有效,并且多個保理商同时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第四,在顺位规则上,本条强调了登记优先,并指出未登记时转让通知的法律内涵,以及没有公示方式时依据债权比例清偿的规则。
笔者认为,《民法典》第768条并未厘清一个前置性问题,即应收账款债务人的清偿顺序与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应收账款债务人的清偿顺序与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是两个问题(朱虎,2020)[14]。应收账款债务人已经向转让通知载明的保理商清偿应收账款,而取得优先地位的保理商未获得该清偿款,此时,基于债务人保护的角度,应当认为清偿有效,应收账款债务人可以免除再次清偿的义务;但是,基于受让人地位保障的角度,应收账款债权的最终利益主体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保理商,其可以请求劣后顺位的保理商返还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履行。
《民法典》第768条仅规定了“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并未规定应收账款登记和转让通知并存时的顺位规则,那么登记和转让通知并存时保理商的顺位应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基于“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取得应收账款”的前置规则,在后登记的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这意味着应收账款转让登记是对抗要件,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高圣平,2020)[15]。
(二)应收账款保理与应收账款质押
应收账款保理与质押的竞存关系只发生在供应商或出质人就同一应收账款签订保理合同和质押合同的情况。保理商和质押合同权利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质押或转让时,并不发生竞存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应收账款质权设立在先,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此时,应区分质权人与出质人是否协商一致。如果二者就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合同协商一致,保理商自然可依据保理合同取得应收账款,只是出质人应当依据《民法典》第445条第2款,将所得保理融资款提前清偿债务或提存。如果出质人擅自就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合同,就存在两种情况,因为《民法典》第445条第2款“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应当解释为:“不得转让”为管理性规范,保理合同有效,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但出质人应当将保理融资款提前清偿债务或提存。这满足了三方主体的利益,即出质人解决了融资难题,质权人获得了清偿保障,保理商取得了保理利益。此外,当应收账款质权未设立时,该应收账款不得对抗第三人,即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有学者认为,应收账款质押与转让的生效要件采取双轨制并不合理,因为质权设立以登记为要件,转让以合同生效为要件,这可能会使得成立在先的权利人无法取得质权,如未办理登记的质押合同权利人无法对抗已经受让应收账款的保理商(李宁,2019)[16]。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应收账款质押与保理竞存时保理商的优先地位并不产生实质影响,因为在应收账款质权人都无法取得优先地位的前提下,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未办理登记的质押合同权利人更无法取得优先地位;同时,正如上文所述,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对三方主体都有利。
第二,应收账款保理在先,供应商就应收账款出质时,应收账款保理与质押竞存。此时,应收账款保理与质押的竞存关系应当参照适用《民法典》第768条的规定:已经登记的保理商取得应收账款,因为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具有对抗效力,完成登记的保理商可以凭借登记对抗第三人;未经登记的保理商,即使已送达转让通知,其也无法取得应收账款,因为其未取得应收账款转让的对抗效力,不能对抗已经完成登记的后位质权人⑱;未经登记和转让通知的保理商与质押合同权利人,可以根据保理融资款和质押金额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
应当指出,保理合同与其他担保物权无法发生竞存。依据《民法典》第416条规定,出卖人享有的“抵押物的价款”相当于应收账款。如果就该价款叙做保理合同,意味着出卖人(抵押权人)将该笔价款的付款请求权转让给保理商,该付款请求权就是出卖人(抵押权人)享有的主债权。而购买价款抵押权即为主债权的从权利,依据《民法典》第547条规定,保理商应同时取得与主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因此,保理商取得对抵押人的购买价款抵押权。若标的物交付后10日内办理了抵押登记,保理商则取得购买价款抵押权的超级优先效力⑲。
留置权的成立前提是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此时,如果留置权人就该笔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合同,则该笔保理业务只能是无追索权的保理。保理商受让应收账款时,由于留置权是担保应收账款主债权的从权利,所以保理商取得留置权(李运扬,2020)[17]。此时,供应商即原留置权人已经转让应收账款,不再享有相应权利,保理合同与留置权就无法发生竞存。
(三)应收账款保理与应收账款让与担保
当同一应收账款上的多重负担并非仅限于保理、质押时,保理商的权利如何保障,需要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以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来判断。其原因在于,《民法典》第388条规定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学理上认为该条款扩张了担保合同的范围,明确了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并为非典型担保合同准用典型担保交易的相关规则提供了解释前提(高圣平,2020)[15]。在《民法典》中,“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主要指所有权保留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和保理合同⑳,同时也可以涵摄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让与担保合同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担保合同(谢鸿飞,2020;高圣平,2020)[18,19]。
在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中,所有权保留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功能主要由所有权登记实现,二者可作一体解释。由于保理合同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二者必须成立在先才可能与保理合同发生竞存。出卖人和出租人将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合同,二者就处于保理合同的供应商地位,无法取得优于保理商的地位。同时,从所有权保留的从属性来看㉑,应收账款主债权转让,所有权保留的从权利也随之转让。此时,出卖人和出租人既不享有应收账款,也不再享有所有权保留的权利,二者无法与保理商形成竞存关系。
一般而言,让与担保合同因标的是否为应收账款而有所不同。非以应收账款为标的的让与担保合同与上文所述的所有权保留相似,遵从上文逻辑,其无法与保理合同发生竞存㉒。但是,以应收账款为标的的让与担保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可能与保理合同发生竞存。由于應收账款让与担保和保理都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基础,所以二者发生竞存时,可以参照适用应收账款多重保理的规则。具体分析如下:当保理商或担保权人即第一受让人转让应收账款时,那么无论成立在先的是何种合同,保理商或担保权人因处于让与人的地位,无法取得优于应收账款第二受让人的地位;当供应商转让应收账款时,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768条的规定。
四、结论
在民法典背景下,对保理合同相关规定的解释适用,既应遵循既有保理业务的实践逻辑,也应明确民法典体系思维的规则逻辑,如此才可以应对保理业务发展中的复杂纠纷,并以法治方式为保理业务发展保驾护航。因此,我们应当明确应收账款转让作为保理合同的核心地位,并在保理商权益保障中强调追索权的双重内涵,即追索权行使和追索权回复,以及善意保护制度对保理商权益的维护。保理合同的担保竞存主要是指应收账款存在多重负担的情形,包括应收账款多重保理、应收账款保理与质押、应收账款保理与让与担保等情形,相应的担保竞存规则,除应收账款质权设立在先外,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768条的规定。
注:
①关于自然人不能就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合同,还可以从自然人“将有的”债权叙做保理合同的风险角度来观察。例如,自然人转让全部将来劳动报酬债权,因可能剥夺自身生计收入而被认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该转让行为无效(黄薇,2020)[20]。
②参见《国际保理通则(2019年版)》第1条、第2条。
③有学者指出,担保标的由现有资产到将来取得资产的发展趋势可以在担保物权的发展历程中找到轨迹,并列举比较法上的诸多规范予以佐证(谢在全,2019)[21]。
④根据中国报告网观研天下集团发布的《2020年中国保理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规模现状与投资前景预测》,在我国,银行保理的市场规模约占三分之二。因此,银行保理的部门规章和行业规范对于保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对《民法典》中保理合同的解释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⑤《保理业务暂行规定》第13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未来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 未来应收账款是指合同项下卖方义务未履行完毕的预期应收账款。”
⑥参见《保理业务规范》第10条。
⑦参见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韶中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3)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612号民事判决书。
⑧2019年10月,银保监会专门发布《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强调商业保理企业不得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与商业保理无关的催收业务、讨债业务。
⑨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中,以“保理+账款催收”为关键词检索到742件案例,其中并没有单纯应收账款催收或管理的保理合同。
⑩实践亦是如此,笔者查阅国内保理业务的保理产品,鲜有以应收账款管理或催收为独立内容的保理产品。
⑪对非因债务人信用风险而导致的应收账款不能清偿,保理商仍有追索权(朱虎,2020)[14]。
⑫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又称买断型保理合同,学界认为买断型保理合同属于附条件的买卖合同(李宇,2019;田浩为,2015;陈学辉,2019)[16,12,22]。
⑬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第1821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第114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第322号民事判决书。
⑭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222号民事裁定书。
⑮实际上,这也正是比较法上善意保护制度的个别立法模式,如《德国民法典》第405条规定的债务人制作并出具虚假的应收账款证明,《瑞士债务法》第18条规定的债务人以书面形式承认虚假的应收账款(李宇,2019)[4]。
⑯与一般担保物实现方式的强制性相似,该“担保物”的追索权行使不需经供应商的同意。
⑰与第三人提供保证相似,非保理合同的债务人即是第三人,而“提供”保证是指该第三人清偿债务。
⑱如果认为应收账款转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那么质押合同权利人可以善意取得质权,而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应收账款上的权利负担应当消灭,此时,应收账款保理与质押不发生竞存。但是,由于应收账款作为债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所以前述假设并不成立(李宇,2012)[23]。
⑲虽然购买价款抵押权存在诸多复杂情形,但其作为主债权的从权利的法律属性并不因情形复杂而有所变化,保理商仍然可因受让应收账款而取得该购买价款抵押权(房绍坤和柳佩莹,2020)[24]。
⑳基于保理合同的追索权性质,有学者认为,“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中的保理合同应解释为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何颖来,2020)[25]。
㉑有学者认为,依据《民法典》第388条的规定,可以将价款债权即应收账款解释为主债权,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解释为从属于价款债权的“担保物权”(高圣平,2020)[26]。
㉒在比较法上,让与担保是否具有从属性具有不同的立法例,德国通说以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否认让与担保的从属性,而日本通说认为让与担保具有从属性。在我国,多数观点认为让与担保具有从属性(王闯,2016;高圣平,2017;谢鸿飞,2020)[27,28,18]。
参考文献:
[1]朱晓喆.资产证券化中的权利转让与“将来债权”让与——评“平安凯迪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执行异议案[J].财经法学,2019,(4).
[2]王融擎编译.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 [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3]陈娇.全球保理业务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J].北京金融评论,2019,(4).
[4]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论 [J].法学,2019,(12).
[5]黄和新.保理合同:混合合同的首个立法样本 [J].清华法学,2020,(3).
[6]裴亚洲.民法典应收账款质押规范的解释论 [J].法学论坛,2020,(4).
[7]方新军.《民法典》保理合同适用范围的解释论问题 [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4).
[8]朱勇.国际保理及其法律性质 [J].法学杂志,1994,(4).
[9]王锐.国际保理合同的认定与裁判方法——基于一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J].法律适用,2019,(2).
[10]徐同远.论民法典中保理合同典型义务条款的设计——以《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25条之一第1款为中心 [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4).
[11]徐涤宇.《合同法》第80条(债权让与通知)评注 [J].法学家,2019,(1).
[12]田浩为.保理法律问题研究 [J].法律适用,2015,(5).
[13]张平华.恶意串通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J].中国法学,2017,(4).
[14]朱虎.债权让与中的受让人地位保障:民法典规则的体系整合 [J].法学家,2020,(4).
[15]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优先顺位规则的解释论 [J].清华法学,2020,(3).
[16]李宇.民法典中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规范的统合 [J].法学研究,2019,(1).
[17]李运扬.担保的移转从属性及其例外——以中德比较为视角 [J].中国海商法研究,2020,(2).
[18]谢鸿飞.动产担保物权的规则变革与法律适用[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4).
[19] 高圣平.《民法典》物上担保制度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J].探索与争鸣,2020,(4).
[20]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M].法律出版社,2020年.
[21]谢在全.担保物权制度的成长与蜕变 [J].法学家,2019,(1).
[22]陈学辉.国内保理合同性质认定及司法效果考证 [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23]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 [J].法学研究,2020,(6).
[24]房绍坤,柳佩莹.论购买价款担保权的超级优先效力 [J].学习与实践,2020,(4).
[25]何颖来.《民法典》中有追索權保理的法律构造 [J].中州学刊,2020,(6).
[26]高圣平.《民法典》视野下所有权保留交易的法律构成 [J].中州学刊,2020,(6).
[27]王闯.关于让与担保的司法态度及实务问题之解决 [J].人民司法(案例),2016,(16).
[28]高圣平.动产让与担保的立法论 [J].中外法学,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