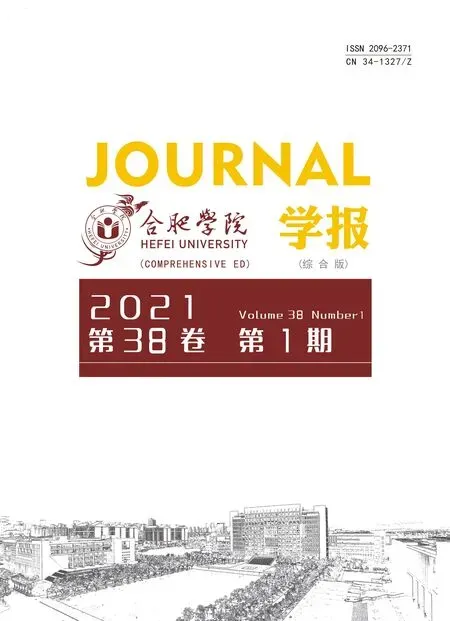门歌生涯六十载
——殷光兰口述史料的挖掘与整理
陈 晓
(合肥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合肥 230601)
殷光兰(1935—2019年),女,生于安徽省肥东县龙城乡龙城村,安徽省第三届、第四届人大代表,合肥市政协委员,安徽省30位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她曾7次赴京参会,4次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即兴演唱“门歌”,周总理称她为“农民的女歌手”。60多年来,她创作门歌作品800余首,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诗刊》《安徽文学》《安徽日报》等刊物;出版《放声歌唱红太阳——殷光兰民歌选集》《万里红光飘彩霞》《毛主席送我上讲台》歌集三册;出版盒带《殷光兰歌唱专辑》,其中《唱个门歌表心情》《东方送给歌到江河》《毛主席送我上讲台》等10首门歌翻译为英文、法文和俄文。2003年,殷光兰将其奖章、证书、郭沫若书信和出版物等共计348件,全部捐赠给“安徽省名人馆”建档保存,深圳“天下名人馆”设有殷光兰展柜(展柜号888)。2019年1月27日,笔者在肥东县对殷光兰进行了专访,肥东县新安江小学副校长黄烨,安徽文艺出版社音乐编辑王竹青,殷光兰次女《肥东报》编辑殷芳参与了访谈。
唐纳德·里奇说过,“口述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论述”[1]。口述史是采访人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非遗传承人是非遗的传承主体,传承人口述史是非遗保护的深层次工作,是记录、抢救、保护和延续濒危的根本举措。当下,非遗传承人面临着老龄化突出问题及现代信息社会冲击等现实困境,利用数字化方式对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口述史等工作,是在信息化时代非遗抢救性保护的有效手段。学界对门歌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仅见褚群武发表在皖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乞讨人艺术 门歌艺人沈成宇的人生》一文。本课题对门歌传承人殷光兰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研究,源于笔者在2019年获审批的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攻关项目《安徽民歌传承人口述史料采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源于笔者长期对区域音乐类非遗的尊敬与尊重,在课题申报前后,课题组数次对安徽民歌传承人进行了长时间访谈,并搜集了第一手资料,以文献(图片、文物)和音视频建档保存。
1 门歌的历史渊源与音乐特色
明初,皖中地区的农民惯用“一声高,一声低”的语调吟读唱本,后发展为简单曲调,称“高低调”,皖西地区因表演时以小锣、小鼓伴奏命名为“锣鼓书”。明末,江淮地区连年灾荒,卖艺人沿门乞讨演唱“高低调”。据老艺人项为先回忆,清嘉道年间,张连成全家游乡串户、挨门乞讨,用锣鼓伴奏唱门歌,门歌形成期下限以同治七年(1868年)《合同记》《打芦花》长篇为标志。同年,巢县知县陈炳禁约告示:“近倒七戏名目,淫词丑态,最易摇荡人心,关系风化不浅。”[2]清末民初,门歌与庐剧常交替演出,农忙分散唱门歌,农闲组班唱庐剧。王本银精通庐剧和门歌,被尊为庐剧宗师,王绍西以唱门歌《合同记》享誉一时。门歌以合肥为中心发展为中、西、东三路。中路分布在合肥及周边各县;西路分布在皖西大别山区;东路分布在滁州及合肥东南的巢湖、无为、宣城和长江两岸。[3]西路山区门歌高亢嘹亮;东路沿江地区门歌柔畅抒情;中路门歌兼具东西两路特色,门歌逐渐发展为中、西、东三路庐剧。①门歌为四乐句单曲体结构即“歌头、歌身、歌尾”3个部分。第一句为歌头,是起腔句结构稍长多为6小节;第二、三句为歌身,是中间句多为两小节;第四乐句为歌尾,其结构与歌头相同。[3]门歌被誉为皖中南民歌的“活化石”,2006年,入选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山王村俱乐部与门歌结缘
一首《十二月当兵》唱哭解放军 殷光兰出生不满四个月时,父母双亡,小光兰被抱到一王姓农家当童养媳,命运多舛的她生就一副好嗓子,当地流行的民歌曲调、歌词她都烂熟于心,王家是贫穷人家,认为女孩唱歌有失“家教”,便用打骂、饿饭等手段阻止殷光兰唱歌。1948年冬,肥东县定光乡山王村解放了!解放军在出操、开会和开饭前都要唱歌,唱完连长才喊吃饭。他们唱的《解放区的天》和《打得好》等歌曲殷光兰很快就学会了。在部队联欢晚会上一名战士提出欢迎山王姑娘唱首歌,殷光兰的小伙伴王书琴、王凤琴把她推到前面说:“山王唱歌要数她最好,她叫殷光兰,是天生的百灵鸟,欢迎她为大家演唱。”殷光兰唱了一首《十二月当兵》,歌词是:“正月当兵正月正,当兵的人受苦情,天天早上把步跑,晚上上床骨头疼。二月当兵龙抬头,当兵之人不自由,站岗要站三更后,起风下雨在外头……”士兵都夸她唱得好听,其中两名士兵低头擦泪,原来他俩是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兵。此后,每逢开会都要她唱歌,乡里开会指导员派人送信要她唱歌,邻村也“借”她去歌唱。
山王村俱乐部开启创作表演之路 1954年秋,肥东县政府要求各乡办农民俱乐部,先在定光乡山王村搞试点再到全县推广。县文化馆副馆长孙新、文艺创作干事王开明与村干部商定先留王开明驻村指导,文娱干事鲁受育、宣传干事熊远平、图书干事王娴云先后来到俱乐部开展工作。孙馆长和熊远平把几十公斤重的幻灯片、汽油灯、玻璃幻灯片、电子管收音机,印有苏联集体农庄的“电灯不要油,耕田不用牛”的宣传图片等挑到山王村,王娴云送书上门,鲁受育辅导歌舞和曲艺等,俱乐部的读报队、创作组、演唱队搞得有声有色。孙馆长拍摄的活动照片在安徽省文化局《群众文化简报》刊登,殷光兰仍清晰记得其中3幅。一幅是她的师傅王绍西在演唱门歌:“大年三十把塘挑,挖掉穷根栽富苗。太岁头上敢动土,三煞脸上甩大锹。”一幅是叫“羌毛”的小孩在打快板表演四句头:“小小羌毛四岁多,会打快板会唱歌,兴修工地来一段,惹得大家笑呵呵。”一幅是殷光兰在田埂上表演《创作人才到处有》:“创作人才到处有,个个都会顺口溜,儿童会把山歌对,青年人庐剧不离口,老年人更加经验多,他们是出口成章,望风采柳。”山王俱乐部编创了《抗旱抢种人人忙》《老绍坤卖余粮》《栽秧的人儿爱唱歌》等作品,培养了殷光兰、王书琴等集创作表演于一身的“农民门歌手”。
3 门歌创作与表演的深刻记忆
1955年8月,殷光兰创作的第一首门歌《栽秧的人儿爱唱歌》在省群艺馆《大家演唱》杂志刊登,此后的60多年她创作了门歌800多首。1956年夏,新华社记者于明专访殷光兰,通讯稿《农民女歌手——殷光兰》在195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孙启元在人民音乐1956年第9期发表了《农民女歌手——殷光兰》文章,“女歌手”殷光兰的门歌人生从此开启。
《整社七日》登上江淮大戏院舞台 门歌《整社七日》被推选为安徽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参演节目,该作品由殷光兰、王凤琴和丁守义根据农村初级社整顿的真人真事创作,经王开明5次修改,孙新馆长润色而成,殷光兰主唱,管华英伴唱。门歌表演是主唱起唱第一句帮腔邀台,主唱唱完每一段伴唱重唱跟进,主唱打锣伴唱打鼓:
队长听说整社态度立刻改变:“东家跑,西家唠,不喊大爷就是喊老表……”
社员提意见:“李二妈说了话,队长架子真是大,整天不脱鞋和袜,‘劳动牌’香烟手中拿……”
1957年1月21日,门歌登台江淮大戏院,一段“歌头”唱完台下顿时响起如雷般掌声!
《整社七日》前五天是交待政策,摆现象、说问题、提整改方案。
第六天是队长含泪检讨:“想起解放前受的苦,我和大家是一样,……我对不起上级党,我对不起父老们,要求给我来处分。”老张喊:“队里有缺点,不能样样怪领导,摸摸良心说实话,有些社员也不好……”
“第七天天气好,社员下田特别早,个个脸上都带笑,个个干活情绪高……只要整社常进行,保证整社能办好!”
殷光兰和管华英的表演诙谐风趣,演唱吐字清晰,296句台词一气呵成,最后一句唱完,台下顿时响起热烈持久的掌声!肥东的殷光兰和滁县的李传江获特等奖,当晚颁发了奖状、奖章和50元奖金。
回忆与严凤英“交换教唱” 1958年秋,鲁彦周的小说《三八河边》改编成电影,在安徽宿县三八公社开拍。该影片以省妇女代表团参观访问的形式,反映省劳模、宿县“三八”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女社长陈淑贞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的先进事迹。团长是省妇联副主任杨哲伦,成员有全国农业劳模龙冬花,省工业劳模韩翠英、许锦培,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和门歌手殷光兰。有一天下雨大家都待在宿舍里,严凤英对殷光兰说:“小光兰,你来,请你教我唱门歌。”殷光兰说:“行!那你要教我唱黄梅戏,我们来交换教唱”。严凤英说:“我先教你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一段吧。”殷光兰很快就学会了,但总觉得缺少黄梅戏的味道,根本原因在于严凤英用安庆方言教,殷光兰却用“合肥老母鸡”语调学。接着殷光兰选了一首叙事性门歌教严凤英:“想姐想得痴呆呆,干塘撒网等鱼来,身穿蓑衣盼下雨,手捧铁树望花开,十字路口等姐来……”教一遍严凤英就学会了,她还逐句给殷光兰分析应该用什么感情唱。殷光兰夸她唱得好,她笑着说:“你小妹妹都夸起我大姐姐来啦!”
“合肥门歌”唱响京城 1958年7月,殷光兰出席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即兴演唱《唱个门歌表心情》向领导献歌。同年8月,殷光兰受邀参加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90个曲种的167个节目,共安排演出95场。殷光兰演唱的门歌《歌唱总路线》在文化部大礼堂演出,唱完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竟站在台下等她。侯宝林疾步上前跟她亲切握手并连声说:“演得好!小兰子,祝贺你演出成功!门歌我听得懂,内容我听得清,咱们曲艺又添新品种啦!”[4]随后,记者纷纷采访殷光兰,专家学者也前来追问门歌的历史渊源。第二天,大会选派殷光兰到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演唱“门歌”,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为她拍摄专题《新闻简报》。殷光兰把合肥门歌从乡村田埂唱到北京天安门、王府井、中南海,全国放映的电影《新闻简报》更是让“合肥门歌”家喻户晓。在全体代表参加的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该会经1979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改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替代了原“中国曲艺研究会”),作家赵树理当选为主席,殷光兰加入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曲艺大辞典》增加了“门歌”辞条(殷光兰爱人熊远平撰稿——本文作者按)。
4 门歌歌集的出版发行与传承保护
1971年,殷光兰受邀到安徽大学执教,她深知自己文化程度低,主动选择指导安大工农兵学员演唱和创作门歌,学生把她在《人民日报》《红旗》《诗刊》《人民文学》等发表的60首歌词收集整理,中文系主任徐承志将歌词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郭沫若。1972年4月中旬,殷光兰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郭沫若在回函中用铅笔给《门歌集》改动了30多处,包括有误的标点符号,还把其中的一首词添加了两句,使其表达更加贴切。郭老在信中鼓励殷光兰继续创作,努力把门歌这种民间艺术传承下去,还给歌集题写了书名《放声歌唱红太阳》,安徽人民出版社希望能尽快出版,郭老得知后欣然提笔为歌集作序。1972年5月,殷光兰门歌选集《放声歌唱红太阳》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购书量突破100万册。因精装本制作量跟不上,仅发行了80万册。1976年10月,殷光兰作词,朱宝强、汪士淮作曲的门歌单行本《毛主席送我上讲台》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叙述殷光兰由一个童养媳成为一个农民门歌手的经历,歌词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安徽大学聘请她讲述创作体会和经验,门歌再次传遍大江南北。
进入21世纪,传统音乐文化受到全媒体时代娱乐多元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门歌这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作为非遗代表作的门歌有其自身艺术价值,这一传统的文化品种如何在当代社会立足,迫使我们用当代的文化理念去赋予她与时俱进的阐释,将传统的内容融入符合时代精神的形式中。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做好门歌的传承保护工作:首先,创新传承模式。要有专业研究人员收集整理门歌文本、音视频、演出剧照等资料,建立门歌档案。在保存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历史进程、分布地域、文化变迁和传承谱系等走访调查,撰写门歌志述丛书;还要充分借助新兴媒体,如广播电视台、微博等网络平台对门歌的理论、表演等专题报道等,扩大门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其次,挖掘和培养门歌人才。将门歌纳入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职业学校等挑选音乐方面有特长、喜爱门歌的好苗子重点辅导,课程设置要注重对门歌历史源流、文化背景和民风民俗等方面的知识普及。最后,完善师徒传艺体制。开办门歌培训班,以口传身授的方式提升传承人的演唱能力和表演技艺,确保传统门歌在当下能活态传承。
5 结 语
鉴于目前对门歌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研究成果较少,在采访中笔者并未追问一些学术性较强的问题,也无需请殷老师介绍,因为有些门歌的学术性问题不是传承人能够回答好的,应是专家学者的科研课题。本次采访,殷老师回忆了她几十年创作表演门歌的经历,是她一段精彩的生命历程,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同时对门歌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印证。门歌传承人口述史个案研究是学术工作的重要环节,没有扎实的个案学术积累,非遗传承保护的思考将成为空中楼阁。门歌是祖先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累积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传统音乐品种,当下门歌的传承保护工作任重道远,期待更多同仁坚持不懈的努力!
注 释:
① 庐剧,俗称“倒七戏”,下文庐剧和倒七戏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