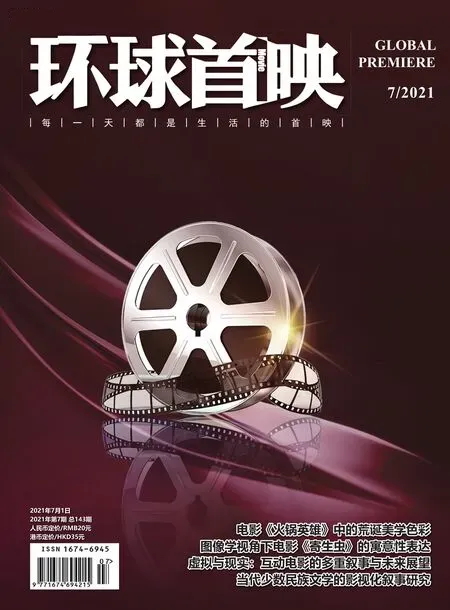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影视化叙事研究
张家荣 四川传媒学院
中国电影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在少数。少数民族的文学影视作品对观众的影响较为深远,包括审美价值、家国情怀等,它能给观众的精神与心灵带来无限的遐想空间与强烈的审美感受,塑造出更美好的精神品位。少数民族文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对其做一定的指引可以使中国电影行业的活力十足,以使民族电影意识表现得更加明显。
一、少数民族题材增强受众的生活审美情趣
影视化叙事是指以影视的方式对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故事进行叙述,或者是对一连串事件进行叙述。少数民族文学是成就当代影史的重要资源,它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被融入少数民族文学,而这种文学之美,借助影视化叙事,从而被人们感知,并让受众的审美情趣得到增强。
(一)少数民族题材引领整个社会美学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少数民族影视作品的创作题材多以意识流为主,使得受众在大脑中自行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描绘与刻画。少数民族的文学影视作品从原生态、聚生态到合生态的形式过渡,根据社会的多元化的发展,将少数民族做了更进一步的描写,使得生态审美化更加丰富多样。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周恩来同志鼓励应多加创作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电影,这对丰富人们精神、提升心理满足度、增强爱国情怀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的创作高峰期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题材的社会效用主要还是其能引领整个社会美学,改编的作品涉及到了所有少数民族,充分体现了“艺术没有界限”这一理念。有《蔓萝花》,通篇主要是讲述苗族的传说故事;叙述诗有彝族的《阿诗玛》和傣族的《召树屯》;壮族的《刘三姐》《百鸟衣》;满族代表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白族的《茶马古道》;塔吉克族的《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时代的美学潮流[1]。
(二)在作品中融入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格
在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当中,自然元素十分常见,民族风格一派天然。事实上,富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作品通常会广受人们的喜爱,由于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相处更加和谐默契,所以民族特色会发挥到极致。因此在创作时需要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异域风情等元素进行杂糅,使其能充分在影视作品中展现出来,同时还不会破坏原生态的生态伦理。创作以民族特色为主的影视作品的目的是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往来、强化人民的精神意志力、培养自身豁达的生命力、凝聚强大的民族精神。影视艺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弘扬光大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强化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记忆能力,从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生态性与生存价值。
二、家园题材可激发受众的生态审美理想
(一)融入家国情怀,唤醒人们的生态审美
文学是一种创造故事的叙事手段,它将理想与现实进行区分,通过影视化叙事从而创造出理想世界的情怀。可以将人们置于某种特定环境中,让其对该特定的自然环境进行打造,以凸显出爱护家国、保护故土的生态审美理想,以家园为题材可以充分地将国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阐述,它既将边界地区的居住群落、优美的生态环境进行描绘,又能切实将该区域的风土人情、经济情况以及政治文化进行描述,进而使得人文历史方面有更深刻的意蕴。少数民族多具有更强烈的家园情怀,因此在创作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需要充分将家园情怀融入其中,以此可最大化地还原少数民族的民风民情与他们的家国意识。少数民族对居住地的依恋与关怀程度不能用言语来描述,需要充分借助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来表述,而创作的影视剧作其宗旨应围绕着人与自然的亲密值来写,让更多人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以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审美目的[2]。
(二)将人格审美与自然之美进行刻画
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源应立足于脚下、扎根于土地,以此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将自然生态作为创造源,可以使得生态环境与审美创造充分融为一体,进而推动作品在实践过程中能更贴近于真实。可以将灵感想象与家园情怀充分融合到一起,促进生态审美理想与家园建设的有机统一,使得人们能无阻碍的回归自然,起到呼吁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作用。《冰山上的来客》就是着重刻画人与自然,然后是人与社会,也对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与矛盾进行描写。剧作中将守卫边防的军人与塔吉克族族人之间的活动进行刻画,并对他们携手保卫与共建美好家园的行为进行赞美,并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理想与奋斗目标全面地表现出来。
三、塑造生命至上的理论强化受众的审美感受
(一)融入自然环境的美学丰富文学内容
想让当下的影视文学超越原有的理论观念,需要对生态美学与影视艺术进行整改,以此可打破传统的人际秩序和伦理观念,从而构建出共同的生态伦理。在制作影视作品时需将少数民族的生态价值剧做深入的解读,以保作品内容能蕴含实际意义。同时还需要将主体伦理价值角度进行校正,以便于能树立正确的文化坐标,追求真实的审美文化和正确的生命观。以《刘三姐》这篇影视作品为例,它是歌舞剧代表作,是首创作品,具有积极的领导意义。剧作在凸显山水秀丽、景色迷人、风光无限好的同时,还将刘三姐的外表与心灵的美、歌声与智慧的美加以衬托,然后以艺术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对我国壮族女性的形象与爱情生命观做了诠释。刘三姐在追求爱情的同时将自由生命充分融合在一起,从主观行为到自然融入的状态,最终在追爱的过程中将生命的自由彰显出来。基于此,少数民族的影视应主观赋予其生命至上的理念,以达成影视文学的预期效果[3]。
(二)取材于生活,融入自然理念
以蒙古族长篇叙事歌《嘎达梅林》为例,其叙述了科尔沁草原上嘎达梅林为保护牧民利益而起义,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故事。由于统治阶级的短视和无知,人们在草原上大肆放垦,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嘎达梅林,为正义而发声,不畏强权勇敢地为民请命和抗争,一方面,讴歌了蒙古族人民的不屈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取材于放牧的生活实际,并融入自然理念,呼吁人们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期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人类虽然位居食物链顶端,但是自然生态环境需要所有生物和谐共处来维持,所以,需对自然怀有畏惧之心,尊重自然的规律,在保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同时,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该剧塑造的草原文化、反抗精神以及生态理念使得不同族群的人们产生了共鸣,让其对生命的价值重新做估量,引发了广大人民的审美共性,将草原人民的不屈不挠、尊崇自然的精神做进一步弘扬。
四、追求异域生态空间使受众形成审美
(一)电影空间中的影视艺术
影视文学采用精心设计的手法可以让电影空间内部的构图、光影、深度、色彩、形象等语言镜头有不一样的感觉,使得受众有无限的想象空间。空间内的电影文学由大量的组成元素构成,有影像资讯、主体人物、空镜中的背景物件,还有人或物的状态、空间范围内的气氛、人物的情绪以及动作,部分物件会有许多近距离的镜头,这表示它即使是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也有其存在的含义,给予其一定的画面可能是代指其他,也或许是想利用它传达某一事件的线索,抑或是可能承载着一段往事的记忆或意念,所以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人或物存在于电影空间中可以引领受众欣赏文学视域下的美学,使其能通过欣赏可以深化理解该文学艺术,进而使观众能联同生活一起想象,从而为其夯实联结记忆的基础。以阿凡提布偶戏为例,它采用了虚实结合创作手法将空间艺术朝着西域风格和乡土人情方向塑造,将维吾尔族的文化充分凸显出来,该影片主人公来自幽默与智慧并存的一个时空,使得影片人物在异域空间中的形象也可以更加饱满。如《东归英雄传》,全篇讲述的是自由和和平,它由自然欣欣向荣的绿草、漫天飞扬的尘土,以及蒙古族土尔扈特人用血泪与命魂谱写的和平之歌[4]。
(二)影像题材应来源真实拍摄
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影视化叙事当中,实景拍摄可以真正地从“影视化”视野中观察少数民族,能够实现民族性、时代性、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全方位表达。以刘三姐为例,事实上刘三姐的流传地极多,关于她的真实来源人们仍然无法确定,但是人们一致认为刘三姐的家乡依山傍水,位于江河沿岸[5]。所以,在拍摄影像时,也会选择真实的自然环境营造背景,能够为人们带来极强的代入感,将会基于真情与实景让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得到提升。
巴赞以电影理论家的角度进行思考认为,美学的特性应是将部分真实进行揭示。因此少数民族在改编文学时应取材于真实的外景,真实有效的拍摄影像可以将祖国的大好风光与异域风情生动形象的展现出来。如描绘丽水市缙云县美丽风光的《阿诗玛》、以雪域新疆为题材的《冰山上的来客》、内陆大西北西藏的《尘埃落定》、富有浓郁云南景色的《碧罗雪山》和《查马古道》等,它们将我国边境地区原生态的自然景色做了生动的描绘,揭开了它们的神秘面纱,将古老的传说、民谣、恋人物语、离家之情、生命意识融汇到影视文学中来,使得人们与自然恰到好处的容纳为一体[6]。
五、结语
少数民族文学是成就当代影史的重要资源,它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借助影视化叙事手段,少数民族文学之美广泛地被人们感知,强化了受众的审美感受,让受众的审美情趣得到增强,并激发了受众的生态审美理想,促使受众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