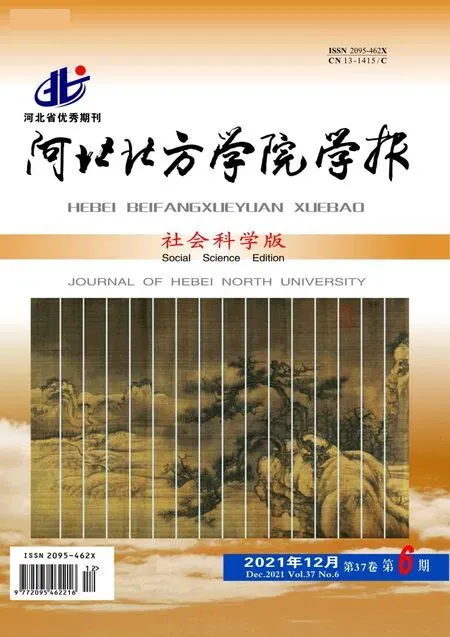白洋淀地区史前生业演进探析
王 菁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白洋淀地区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永定河与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平原洼地上,瀑河、漕河、唐河和潴龙河等河流在此汇集交错,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洼地。《新唐书》有云“鄚州有九十九淀”,可见当时淀泊之多。白洋淀在这片洼泽中面积最大。丰富的淡水资源孕育出悠久的人类文化,近年来此区域发现了较多史前时期遗址。随着资料的增加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目前学界对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编年序列和古气候环境等基本了解清晰,但对其生业发展的关注则比较少。下文以考古资料为出发点,在分析该地区生业演进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古地质古环境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其生业演进动因等问题。经过多年研究,白洋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已较为清晰[1],在此基础之上,对各相关遗址的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该区域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的种类、数量和比例等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体现出生业发展的不同特点。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生业发展
白洋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2 000~8 500年,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比较少,主要是徐水南庄头遗址,距今约1万年左右。该遗址于1987年[2]和1997年[3]经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有陶片、石制品、骨角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从动物骨骼遗存来看,狩猎在南庄头人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狩猎对象主要是鹿类,还有水牛、野猪、狗、兔、鼠和鸟等[4]。其中,哺乳动物占一半以上,其次为鸟类。以鹿为主的哺乳动物应是南庄头先民的主要肉食资源。南庄头还发现家狗遗骸,在中国史前狩猎岩画中曾出现很多狗的形象,南庄头人驯养的家犬或有辅助狩猎的功能。狩猎所捕获的动物除食用外,骨骼也被用来加工制作成工具,鹿角和骨骼经常被加工成骨锥和角锥等。南庄头发现了大量的骨锥和角锥。骨锥直径约在1 cm以下,形状笔直且粗细均匀,可能有穿孔缝制功能。角锥直径大部分在2 cm以上,保留了鹿角的自然弧曲,角尖磨光,可能是用于钻孔的工具,或用来刻划穿刺等。
除狩猎之外,采集业在南庄头人的生业中也有重要地位。南庄头遗址两次发掘发现的磨盘和磨棒可能是将谷物脱壳或研碎的粮食加工工具,有些研究据此认为这是早期旱作农业的反映。而相关植物孢粉研究表明,南庄头遗址高含量的禾本科花粉为野生禾草类[5],遗址内未发现石铲和石镰等农业开垦或收割工具,发现的磨盘磨棒等可能用于加工坚果和野生粟类作物。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能确证此时锄耕农业已经产生。但综合来看,亦不能排除南庄头人使用棍棒等工具进行简单的谷物栽培的可能性,或许其农业尚处于萌芽阶段。进一步看,磨盘和磨棒在南庄头人的生产工具中所占比例不低,1997年发掘的资料中,磨盘磨棒分别占据了石制品总数的23.5%和17.6%,这表明采集野生稻谷或野果进行加工脱壳是南庄头先民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此外,还发现了鱼、鳖和蚌等水生动物,但数量较少,说明渔业捕捞在当时生产活动中并未占据主要地位。
综合来看,在南庄头时期,白洋淀地区先民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的生业模式,捕捞业也有一定发展。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生业发展
白洋淀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8 500~7 000年,发现的文化遗存不多,主要以上坡一期[6]和梁庄下层[7]为代表。
上坡和梁庄遗址出土的遗物都比较简单,以石器和陶片为主,其中上坡遗址出土内容相对丰富。该遗址发现了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除了加工粮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外,还有用于开荒除草的石斧、石铲以及收割工具石镰等,这足以表明该时期已进入耕作农业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石器中并未见镞、球和砍砸器等狩猎工具,说明狩猎行为在此阶段经济活动中已减少。
在白洋淀邻近地区也发现了此阶段的重要遗址,如距白洋淀西北约70 km的易水岸边就发现了北福地大型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了集中分布的房址和1个大型祭祀场。祭祀场内集中放置了很多石器、陶器和玉器等。石质工具共8类41件,其中占比较多的石斧(39%)和石铲(29%)均可用于农业生产,此外还有石锛、石耜、磨棒和磨盘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件长达46cm通体磨光的大型石耜。石耜是用来深翻土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型农具的出现一方面体现出该区域史前农业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这些制作精致的农具使用痕迹很轻微[8],其可能是作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或者是祭祀的对象而存在。无论是哪种性质,都反映出农业生产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北福地的若干灰坑和房址内曾发现大量核桃楸果核,但不见动物和栽培谷物遗存。有研究者认为,北福地是一处季节性营地,先民为采集坚果而定期来到这里[9]。可见,除农业种植外,采集野果也是北福地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从遗址内出土的生产工具类型来看,虽然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但狩猎工具却很少,仅见少量石球和砍削器,占全部石制品总数的1%,这表明狩猎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白洋淀及邻近地区生业发展以农业和采集业为主,狩猎比重似乎较低。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业发展
白洋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7 000~5 000年,代表性地点有北庄[10]和北城村[11]遗址。
北城村遗址是白洋淀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史前聚落,位于大清河冲击扇上,距离白洋淀20多km,发现了房址和灰坑等丰富的遗迹以及大量遗物。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石质工具的类型和数量分别是斧8件、磨棒16件、磨盘6件、杵3件以及镰/镞、球和砍砸器各1件。对比来看,数量多的是石斧、磨盘和磨棒,而刮削器、石球和砍砸器等较少。目前,北城村未见石锛、石耜和石铲等农业开垦工具,出土较多的是石斧。但鉴于石斧可用于农耕、采集甚至建筑,因此还不能将其作为北城村农业活动的直接指征。巧合的是,该遗址同样未发现任何骨角器、动物骨骼或是栽培谷物遗存。北城村遗址发掘者认为其并非是人类长期生活的地点,理由是北城村不同层位的房址之间没有彼此叠压,说明该遗址可能存在于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此外,北城村房屋建造亦比较粗糙,居住面普遍凹凸不平,没有经过烘烤踩踏等加工程序,室内没有修筑灶穴,仅是将地势低洼之处作为火塘,显然北城村先民并没有在营造房屋上投入过多精力。结合出土较多的磨盘、磨棒和石杵等加工工具等综合观察,北城村应是一处先民采集果实并进行加工的临时营地。
北福地遗址也存在这一时期的遗物即北福地二期遗存,所出石制品从类别上看与北福地一期并没有很大区别,仍然以斧、铲、锛、磨棒和磨盘等为主,反映出鲜明的锄耕农业特色。值得关注的是,石锛的数量在这一阶段成倍增长。北福地一期除砾石以外基本完整的石器共计77件,其中石锛4件,占比5%;而北福地二期除砾石以外基本完整的石器共计66件,其中石锛8件,占比12%。这表明在北福地二期人类的垦荒整地活动较一期有所增多。
北城村与北福地遗址均没有发现动物骨骼遗存,这或许与当地的环境保存条件有关。但从狩猎工具的数量来看,北庄遗址未出土狩猎工具,北城村出土石镞和石球各1件,北福地二期出土石球1件,与前一阶段的情况相似。
总体观之,该阶段的生业特点与上阶段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是以农业和采集业为主。锄耕农具占比增多,且出现季节性临时采集营地,狩猎活动较少,捕捞业属于一种相对次要的生计方式。
四、新石器时代末期生业发展
白洋淀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约5 000~4 000年,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哑叭庄遗址[12]。该遗址距白洋淀仅15 km,第一期遗存属于龙山时代,年代大约距今4 600~4 000年。
哑叭庄遗址出土工具类型多样,包括指示农业生产活动的镰(14件)、锛(7件)和铲(23件);狩猎活动使用的镞(29件)、石球(1件)和刮削器(8件);捕鱼工具有网坠(245件)、鱼镖(4件)和鱼钩(2件);斧(4件)和刀(17)等工具可能用于农业或采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经非常发达,除了在生产工具上有所体现外,还发现了可能作为酒器使用的陶鬶和盅等,说明这一时期粮食生产已经足够富余。除此之外,渔业用具的迅速增多值得注意,仅陶网坠就发现了245件,超过了全部陶器总数的40%。该遗址还发现了很多蚌器,器类包括锯、刀、镰、铲和匕等,甚至在日常使用的陶器中也出现了前几个阶段很少出现的夹蚌陶器。可见,这一时期人类对水生资源的利用率显著提升。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龟甲、鳖甲、鱼骨、蚌壳和螺壳等表明水生动物成为哑叭庄先民重要的肉食来源。
除了种植农业和渔业捕捞外,该阶段家畜饲养也较为发达。哑巴庄遗址所出的猪类遗骸为家猪。除了家猪以外,驯养动物的品种还包括牛、羊、狗和鸡等。可见,这一阶段白洋淀先民的生业模式已较为多元化了。
五、环境变化与白洋淀地区史前生业演进
地质学研究表明,白洋淀地区的地层可以划分为古全新世、早全新世、中全新世和晚全新世4个阶段。
距今11 000~9 000年左右的古全新世时期气温迅速回暖,白洋淀地区为森林草原地带,有以松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及小型湖沼洼地[13],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和植物硅酸体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南庄头先民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一阶段主要的生业模式是狩猎采集,先民们采集野果并捕猎动物,用石锤或石球等敲骨吸髓。
到距今9 000~7 500年左右的早全新世时期,全球气候变干冷,在河流作用下,白洋淀地区森林面积缩小,草原面积扩大[13]。上坡一期和梁庄下层遗存大体处于这一阶段,所发现的农业开垦工具和收割工具等表明农业种植业已形成,并成为人类重要的生业模式之一。干冷期的到来使得季节变化更加明显,在寒冷的冬季人类很难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这种气候的变化或许是促进白洋淀地区种植农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为了应对季节性粮食短缺问题,农作物的驯化势在必行[14]。而这一时期食物短缺确实在考古资料中有所体现。森林面积的缩小影响到了先民的采集活动,当某一地域获得的食物不能满足他们需求时,他们便不得不进行迁移,去寻找更合适的采集地点,于是出现了季节性的采集营地。在北福地遗址发现了储藏坚果的窖穴,正印证了刘莉所讲的“如果一年之中总有食物短缺时期,那么采集和存储淀粉类食物将是应对环境挑战的最好办法”。除了采集业受到季节的制约外,湍急的河流也制约了渔业的发展,当水流速度快时,鱼类很难停留聚集,这增大了捕捞的难度。因此,在这一阶段较少发现捕鱼用具。当无法从环境中获得足够的食物资源时,白洋淀先民选择更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开垦田地,种植谷物,甚至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使得粮食增产。
至中全新世时期,气候变暖,降雨增加,白洋淀地区的地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由河相沉积突然变为湖相沉积,水生植物孢粉的大量增加表明这一阶段形成了较大的湖沼,范围可能比现在的白洋淀还要大[13]。但从孢粉反映的植被来看,距今7 000年左右曾有一次干冷气候,北城村、北庄和北福地二期恰逢这次降温,所以生业模式仍以农业和采集为主。但随着气候回暖,湖沼面积扩大,白洋淀先民对水生资源的利用逐步增多,在距今4 600~4 000年左右的哑叭庄遗址中,渔具已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人类不仅使用鱼钩、鱼坠和鱼鳔等获取食物资源,还利用水生资源制作工具,如蚌刀和蚌镰等,渔业成为与农业并重的生业模式。食物资源的富集也进一步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形成了农渔畜养的多元混合生业模式。
该文选取代表性遗址进行分析,历时性考察了白洋淀地区史前生业演进概况,整体而言,其生业由较单纯的狩猎采集逐渐发展到农业、渔业和畜养业并存的多元化混合经济。这一过程与环境变化呈现出某种耦合性,应进一步探究在白洋淀这一典型生态区早期环境变化与人类生业发展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