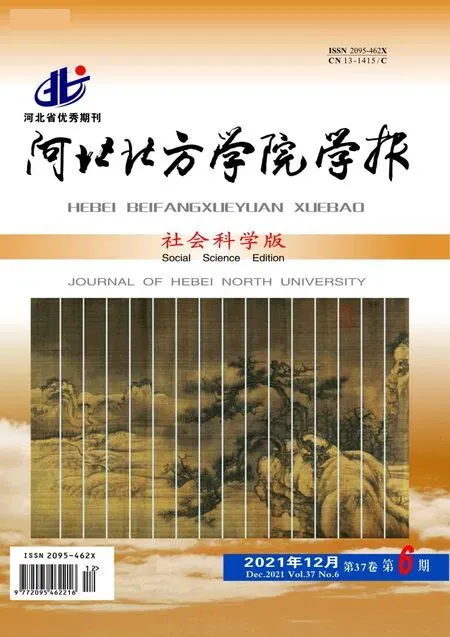金朝军须钱探析
刘 施 伟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军须钱亦称军需钱,是金朝特有的杂税之一[1]1102,始征于世宗大定三年(1163),一直沿用至金亡。关于金代军须钱问题,张博泉的《金代经济史略》[2]以及漆侠与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3]412中均有所提及。王曾瑜的《金朝军制》在论及金代后勤和军费问题时,简要地概括了军须钱的发展过程,认为军须钱在世宗时期成为战争期间临时性征税名目[4]。刘浦江在《金代杂税论略》一文中简述了军须钱的发展概况及输纳期限的变化,指出金朝后期征收军须钱是造成流民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5]。孙乐在《金末财政危机研究》一文中认为,军须钱属于政府剥削百姓和应对财政问题的方法之一[6]。吴树国在《金代杂税新探》中认为军须钱属于财政摊派性加征形式的杂税,在运行机制中呈现合法化和固定性趋向[7]。概而言之,目前学界对金代军须钱的研究仅在探讨金代杂税和军费问题时有所涉及,尚未有过系统研究。下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军须钱的创设背景及影响,从其发展概况分析军须钱与金代货币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征收军须钱的背景
传统史家称金世宗完颜雍“与民休息”,号“小尧舜”[1]222。实际上,其从即位的第三年就开始加征杂税军须钱,并一直沿用。
(一)大定三年(1163)前金朝铜钱的铸造与使用
金初未铸币,仍使用辽、宋旧钱和伪齐的阜昌通宝与阜昌重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货币总量已无法满足需要,正隆二年(1157)金朝开始铸造铜钱。由于铜源少,故“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1]1145。正隆三年(1158)置钱监,铸正隆通宝,但数量有限,政府命其与旧钱和交钞一起在民间流通。大定元年(1161),金世宗“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1]1145,大定四年(1164)因流通不便,罢用铁钱,但在此之前陕西地区应有一定数量的铁钱流通民间。
关于宋金争夺铜币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乔幼梅等在《辽夏金经济史》中指出,“在宋金贸易中铜钱成为双方竞逐的目标,为了将对方的铜钱吸引过来,并且制止自己的铜钱流到对方,在贸易领域里展开了一场争夺战”[3]378,并从4个方面论证金朝吸引南宋铜钱北流:一是发行交钞;二是以短陌钱吸引宋钱;三是压低物价,套购宋钱;四是在榷场贸易中吸引南宋客商过界,多得课税。汪圣铎在《两宋货币史》中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宋金之间不存在对铜币的争夺,“金朝争夺宋朝铜钱,是宋朝士大夫的主观猜测,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时期没有铜币争夺战,但有铜币保卫战”[8]。这两种观点皆认为1214年以前客观存在南宋铜钱大量北流的现象,其分歧在于宋金是否“争夺”对方铜币。从宋金争夺铜币问题可知,南宋货币在两国生产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遵循着由流通量充足向流通量不充足以及由购买力低地区向购买力高地区流动的商品货币经济规律。因此,在大定三年(1163)前应有大量的南宋铜钱通过宋金贸易渠道北流至金。
(二)军费支出巨大
海陵王完颜亮登基后,一改熙宗时对宋的政策,从正隆四年(1159)开始就积极筹备攻宋。先“造战船于通州”[1]122,后又“遣使分诣诸道总管府督造兵器”[1]122,一切军备费用皆取之于民。为顺利南征,海陵王又在民间大规模地扩充军队。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秋,金主命户部尚书梁球计女真、契丹、奚三部之众,不限丁数,悉签起之,凡二十四万……又签中原、渤海、汉儿十五道,每道各万人,合蕃、汉兵为二十七万”[9]457。军队规模的扩大使政府军费支出骤增,导致军费不足,以致需要“借民间税钱五年”[10]3228,百姓承受着巨大的军费负担。
正隆六年(1161),完颜元宜等反,海陵王被杀于军中。但对宋战争并没有因海陵王的死而结束,刚即位的世宗仍要面对巨额的军费支出。大定元年(1161),世宗“出内府金银器物赡军,吏民出财物佐官用者甚众”[1]139。为了节省财政开支,世宗还曾多次下诏减少宫中花销。另外,金朝内部也十分动荡,“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未久,国势易摇”[11]。为稳定内部局势,平定叛乱,世宗于大定二年(1162),“诏出内府金银给征契丹军用”[1]144。《金史》对这次助军金银的具体数目有明确记载:“出内府金银十万两佐军用。”[1]3014可见此时军费所耗甚大,国库已无力支撑。因此,针对严峻的内忧外患,世宗急需整顿军备以稳固统治,这当然要有足够的军费来支撑。军费最方便快捷的来源方式就是通过“开源”从民间获取。
(三)金世宗守成之政
海陵王在位时就曾为筹措南征军费向民间征钱。史载:“及将用兵,又借民间税钱五年”[10]3228,导致百姓因军费负担沉重,屡次发生民变。世宗即位后,常以海陵之失为鉴,然大定三年(1163)所创设的军须钱却是“借民间税钱五年”的延续。其原因除军费巨大的现实需求外,还可从世宗“守成之政”的角度进行剖析。第一,早在太宗时就有人提出征收铜钱以补军费不足。天会十一年(1133),“元帅府言:‘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将不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诏曰:‘官有府库而取于臣下,此何理耶。其悉从官给。’”[1]71。尽管太宗最后以国库有钱为由拒绝了元帅府的请求,但给奉行“守成之政”的世宗提供了可循之例。加之海陵王已向民间征收5年税钱,并将征收对象由太宗时的官僚阶层下移至百姓,且海陵王仅是将军费所缺摊派到百姓身上却未确立明确赋税名目,这就为世宗设军须钱铺平了道路。第二,征纳军须钱与世宗的“内外无事、天下晏安”治国政策相契合。世宗即位之初就着手与宋议和,以保持南北分治的统治格局。世宗迫切想通过打败宋朝以在议和中占据优势,进而保证利益不受损害。而要取得胜利,军队的俸饷和供给就必须得到保证。因此,世宗开始向民间加征军须钱。
综上所述,金朝征收军须钱的背景有三:一是海陵王在使用辽、宋旧钱和伪齐阜昌通宝与阜昌重宝的基础上开始自行铸币,加之宋金贸易中有大量南宋铜钱北流,民间有钱可征;二是海陵王发动的对宋战争一直延续至世宗时。国内同时亦爆发了大规模动乱,迫使政府急需通过开源来弥补巨额军费支出;三是设军须钱有先例可循,符合世宗的“守成之政”治国理念。
二、征收军须钱的概况
战争期间为临时加派赋税而创设的军须钱,一直保留至金亡,期间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和演变。纵观军须钱的发展,有3点表现非常明显:一是支撑政府军费支出,到金中后期战事频繁,其重要性更加突出;二是政府将征纳军须钱作为敛财手段;三是军须钱征收物的发展和演变侧面反映了金代货币经济的发展。
(一)由临时加派到岁课
大定三年(1163),世宗“南征,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官府止有二百万贯,外可取于官民户,此军须钱之所由起也”[1]1076。大定四年(1164),亦在民间征收军须钱,“元帅府乞降军须钱,上曰:‘帅府支费无度,例皆科取于民,甚非朕意。仰会计军须支用不尽之数,及诸路转运司见在如实缺用,则别具以闻。’”[1]1076。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军须钱是由国家统一征收,各路转运司上报地方军费缺额后由中央发放给元帅府,再发放至地方。“隆兴和议”后,金宋战争结束,然而军须钱并没有随之取消。大定十一年(1171),“(高)德基上疏,乞免军须房税等钱,减农税及盐酒等课,未报”[1]2119。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李革任韩城令时,“同知州事纳富商赂,以岁课军须配属县”[1]2329。可见,因军费不足而临时加征的军须钱已经逐渐变为地方每年征收的课税。
军须钱之所以在金宋战后未被取消,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世宗经略北边的现实需求。据《金史》载,大定三年(1163),“契丹余党未附者尚众,北京、临潢、泰州民不安,诏守道佩金符往安抚之,给群牧马千匹,以备军用”[1]2079。《金史》又载:“参知政事完颜守道经略北方……徙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极边安置,仍与泰州、临潢边堡相接。”[1]2147这说明在平定移剌窝斡叛乱后,金朝北方局势仍不稳定,需继续经略。政府修治西北与西南两路的边堡一直与泰州和临潢边堡相接,规模之大和所耗费用之多可想而知,而这仅是世宗经略北边的措施之一。第二,政府将军须钱作为聚财敛财的工具。大定十年(1170),有使者自山东回来,皇太子允恭问其民间疾苦,使者言:“钱难最苦。官库钱满有露积者,而民间无钱,以此苦之。”[1]448而在大定十二年(1172),世宗曾言,“今国家财用丰盈”[1]1147,说明此时国库充盈,政府掌握着大量铜钱,以至官库存在露积。反观民间竟是无钱可用。政府想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敛财,这也是军须钱未取消的原因之一。
(二)军须钱的征收标准
典籍中对大定三年(1163)军须钱的征收标准未有明确记载。据《金史》记载:“以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循宋、齐旧例,州县司吏、弓手于民间验物力均敷顾钱,名曰‘免役’,请以是钱赡军。”[1]1076此时,赡军的免役钱是以物力作为摊派标准,军须钱的征收大概亦应如此。
金宋战争结束后,军须钱照常征收。大定十年(1170),曾出使金的楼钥记述:“宿胙城县。途中遇老父,云女婿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为始,凡物力五十贯者招一军,不及五十贯者率数户共之。下至一二千者,亦不免。每一军费八十缗,纳钱于官。以供此费。’”[12]其中的“以供此费”就是戍边士兵衣装所需费用。政府规定物力至50贯者纳钱80缗,力不及50贯者多户累至50贯输纳。可见,大定十年(1170)的军须钱还是以物力为征收标准的,无论物力轻重皆在征收之列。李革担任韩城令时已经是大定末年,富商为逃避交纳军须钱重金贿赂地方长官,将其应纳税额分配给属县。这也说明到世宗统治晚期军须钱仍是按物力进行征收。
章宗承安年间,北部边境屡遭蒙古侵扰,所耗军费亦逐年增长。此时虽已随路赋调军须钱,沿途征收并“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1]263,但依旧未改变军费不足的局面。承安三年(1198),政府“以军须所费甚大,乞验天下物力均征。拟依黄河夫钱例,征军须钱,验各路新籍物力,每贯征钱四贯,西京、北京、辽东路每贯征钱二贯,临潢、全州则免征,周年三限送纳。恐期远,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输纳”[1]1076。此后需依照黄河夫钱征收军须钱,每征1贯黄河夫钱就要征军须钱4贯,输纳期限由1年3次变为半年3次。由于黄河夫钱是依据物力进行征收的,因此章宗时的军须钱名义上虽以黄河夫钱为标准,本质上征收标准却仍为物力。其中西京、北京和辽东路减半征收,临潢和全州免征,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北边屡遭侵扰,承安二年(1197)政府通检时规定:“边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1]1114而临潢等地正值战乱,不在通检之列,因此免征军须钱。第二,承安三年(1198)交钞雍滞,金朝“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1]1152。西京、北京、临潢和辽东等地应是存在严重的交钞雍滞,所以在这些地区政府采取限制铜钱的措施。
(三)军须钱征收物的变化
大定三年(1163),世宗开始征收军须钱,征收物为铜钱。通过前文论述可知,由于世宗初年民间流通着大量铜钱,因此政府在民间有钱可征。至章宗明昌四年(1193),“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宰臣以闻,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1]1151。军须钱作为杂税中的一项,此时在陕西地区由铜钱变为钱、钞并征。导致这一变化的缘由应从大定十八年(1178)铸造铜钱论起,是年“代州立监铸钱……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而后命与旧钱并用”[1]1147。由于大定通宝的铸造成本极高,所铸数量有限,因此政府命新旧钱并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金朝已经出现了铜钱短陌的现象,“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1]1147-1148。短陌严重会导致钱荒,民间铜钱流通十分艰难。大定二十九年(1189)甄官署丞丁用楫审查民间铸币后言:“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1]1149当时铜币铸造处于入不敷出的严重亏损状态,因而政府“罢代州、曲阳二监”[1]1149,停止铸造铜钱。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弥补铜币不足,金朝大量发行交钞,并废除了7年厘革的规定,造成交钞出多入少和日益雍滞的境况,直接影响到军须钱征收物的变化。
承安二年(1197),“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1]1152,侧面说明此时军须钱的征收物为银和钞。至于铜钱是否还在征收物之列,从下则史料中可探究竟。承安三年(1198),“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1]115。在交纳1贯以下的赋税时,百姓可任意选择钱、银或钞。因此,铜钱应在军须钱征收物之列,但所占比重较小。承安四年(1199),“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1]1153。按照政府规定,除京师、河南和陕西地区可以随意交纳银和钞外,其余诸路在交纳军须钱时银和钞各半。可见,在承安四年(1199)以前曾征收过少量的铜钱,此后军须钱的征收物为银和钞。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承安二年(1197),因“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1]1152,故政府铸造了银币承安宝货,此时应有一定量承安宝货在民间流通,为军须钱纳银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期间银钞雍滞,以致贬值,百姓生活受到冲击,且银钞贬值引致政府赋税收入的实际价值减少,造成财政损失。因此,为避免财政损失,政府对军须钱征收物进行了调整。
章宗泰和元年(1201)六月,金政府“初许诸科征铺马、黄河夫、军须等钱,折纳银一半,愿纳钱钞者听”[1]280。在交纳军须钱时,百姓须将一半折银,其余部分可以任意纳钱或钞。此时的军须钱为钱、钞和银并征,并一直延续至金末。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泰和元年(1201)六月,交钞雍滞的问题尽管已经得到缓解,但民间仍存在银价未平的问题。对此,通州刺史卢构提出:“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庶革其弊。”[1]1154然而“下省议,宰臣谓……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1]1154。宰臣认为银和钞均纳会影响到交钞的流通,从而再次造成交钞雍滞的困境,于是规定缴纳军须钱时需折纳银一半。就此条史料本身而言,政府是因银价未平而对军须钱征收物作出调整。不可否认,此项措施对平抑银价有一定作用。但究其根本,政府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避免国家财政收入遭受损失。
综上所述,因北部边防的需要及统治者的敛财私心,军须钱被一直保存下来,并演变为岁课。就其征收标准而言,有金一代,军须钱一直以物力为征收依据。就其征收物而言,军须钱征收物的变化与金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密切相关,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其进行不断调整。
三、征收军须钱的影响
征收军须钱对金朝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范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对统治阶级而言。作为金朝杂税之一,军须钱从创设之初就体现着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消极影响主要是对百姓而言。作为赋税的承担主体,百姓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一)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第一,军须钱弥补了政府巨额的军费支出。自大定三年(1163)始创军须钱以来,军费主要依靠征收军须钱来解决。章宗时期,北部边防屡遭侵扰,承安年间修建临潢左界北京路的壕障就花费百万,每年北边戍兵的军费支出至少有600万,可见这一时期北部边防就需花费近千万。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军攻金,“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9]850。在蒙古入侵的同时西夏也趁机扰边。金宣宗南迁后,又对宋发动了战争,而金内部亦有红袄军起义,可谓是三面交困,腹背受敌。此时战争规模之大和所耗军费之多都远超世宗与章宗时期,巨额的军费要靠征收军须钱来解决。
第二,金中后期政府调整军须钱征收物,以求疏通货币,稳定物价,其本质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维护统治者利益。随着金朝货币经济的发展,军须钱征收物随货币流通环境而变化,成为政府稳定货币经济的手段,钞多则多征钞,银多则多征银。此外,金宣宗南迁后,国疲民困,交钞有出无入,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贞祐三年(1215),河东宣抚使胥鼎上书宣宗:“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1]1159因此,金中后期对军须钱征收物的调整体现了统治者的利益和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货币流通。在此过程中,平抑物价也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益处。
(二)加重了百姓负担
军须钱作为金代杂税之一,是统治者鱼肉百姓的工具,自创设以来就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致使金末流民大增。承安四年(1199),应奉翰林文字陈载谏言四事,认为“农民困于军须”[1]274。贞祐三年(1215),黄河以北已被蒙古军占领,但政府仍“诏河北郡县军须并减河南之半”[1]336。经过蒙古和金的双重掠夺,“河朔饥甚,人至相食”[1]2524。兴定三年(1219),宣宗下令“免单丁民户月输军需钱”[1]370,此时军须钱的征收期限已从章宗时半年3次输纳变为每月输纳,征收频次增加说明政府所需的军费越来越多,百姓负担愈发沉重。兴定四年(1220),宣宗对宰臣说道:“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1]1138可见统治阶级对流民问题和军须钱的危害心知肚明。然而,在金末战事频仍的情形下,统治者只会加大掠夺百姓的力度,加重对军须钱的征收。哀宗时甚至出现“以牓召民卖放下年军需钱”[1]427,允许地方地主豪强扑买军须钱,这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对民间加征赋税以供军用是中国历朝历代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把军须钱作为赋税进行征收是金代特有的。世宗即位后所面临的政治动荡与财政窘困皆为海陵王正隆年间决策失误的余波。大定三年(1163)所创设的军须钱,自其产生就以物力为征收标准,是金朝军费支出的重要支柱。世宗时是军须钱的产生和发展阶段,根据统治者的现实需求,军须钱被保留下来,由临时性赋税逐渐变为岁课;大定四年(1164)后,军须钱多是充当政府敛财的工具,即使国库充盈也仍征收军须钱和其他杂税,世宗时百姓的赋税负担应重于海陵时。章宗时,军须钱发生了两次变化:一是军须钱的征收期限变为半年3次输纳,说明当时军费支出增大;二是军须钱征收物大致经历了钱—钱钞—钞银钱—银钞—银钱钞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中可管窥到金朝货币经济的发展历程,军须钱见证了金朝货币经济的兴衰。金末,蒙古军南下,金朝失去了大片领土,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赋税征收。这一时期军须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军须钱的征收频次变多,改为按月输纳;二是在金蒙战争中,金朝为保证战争所需军费,不得不在已经沦陷的地区征收军须钱;三是哀宗时在部分地区短暂地免除军须钱,这是金政权面对危机作出的自救,但仍无法避免走向灭亡的结局。军须钱尽管在解决军费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但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兼论 “训民正音”创制者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