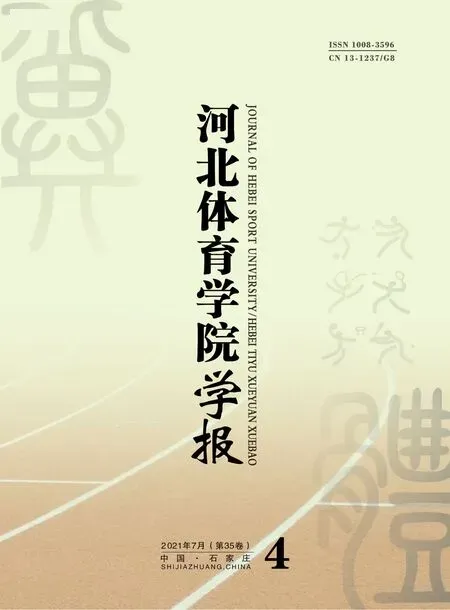仪式体育:北方巫傩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宗教祭祀研究
何胜保
(唐山师范学院 体育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滦河古称“濡水”,《水经注》载:“濡水出御夷镇东南”,发源于丰宁古道坝下谷底,流经沽源、锡林郭勒盟(多伦、正蓝旗、太仆寺旗)、喀喇沁旗,及辽宁省凌源、建昌后过潘家口穿长城进入冀东平原,而后入海,形成5.5万余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1],属于海河流域与辽河流域中间的过渡缓冲带。早期人类逐水而居的生存状态创造了广袤的滦河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滦河流域人类进化史上,多民族交替生息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多彩文化廊带,如红山文化、孤竹文化、燕文化及边关文化、游牧农耕文化、萨满文化等。在这些文化链上,一直伴随着宗教祭祀活动,而在诸多宗教祭祀活动中萨满跳神仪式从上古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滦河流域仪式体育文化记忆演变的历史仪轨。
萨满跳神宗教仪式文化本体的逻辑发生是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建立“天人鬼三界”联系,表演者面戴面具,身穿法衣,用典型巫傩祭祀遗风行人神共融、沟通阴阳之事[2]。萨满跳神仪式彰显滦河先民傩文化与身体文化二元相生相克,以达到生命本体的“阴阳平衡”,蕴含传统阴阳哲学思维。北方巫傩是萨满跳神仪式发生的原始形式,表演者试图用身体语言符号及身体情感演绎人类认识、控制万物的思维镜像,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形式操纵。萨满跳神文化与巫傩文化统摄引领成为滦河流域仪式体育发生、发展的叙事逻辑,借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把北方巫傩作为萨满跳神仪式演化生成的逻辑起点,探索滦河流域仪式体育的原始形态、文化内涵与嬗变程式,以弥补滦河流域体育史学研究的学术缺憾。
1 北方巫傩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的文化内涵
梳理宗教叙事与文化谱系不难发现,所有宗教的本质基因离不开信仰和仪式,信仰的原始意义在于表达对自然、神明、祖先的崇拜,而仪式则是为实现信仰所采取的程式性、象征性行动[3]。特纳(V.Turner)把仪式看成是信仰场域空间引发的规定性行为[4]。在各类宗教仪式中体育是表达信仰的社会行为实践,这些行动构成了仪式体育的原始形态。因此,仪式体育可以理解为:“人类按照族群精神信仰、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建立起来的具有程式性、象征性、规定性特征的体育活动行为。”
北方巫傩以内蒙古、河北傩祭仪式为代表,如蒙古族“送鬼仪式”和武安“捉黄鬼”“拉死鬼”等,在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后除保持原始信仰、仪式外,更是把民间信俗、艺术、体育融为一体,构建了集各种异质符号互渗、交流、制约的仪式场域空间,彰显人鬼同娱的精神慰藉。如巴尔特阐述符号学涵指系统一样,北方傩祭仪式符号表意系统表现为祈福免灾、逐鬼驱疫精神符号能指与所指共同构建的意指体系,实践着理念向往、娱神娱人、强身祛病信仰与仪式相互交融、互为一体的宗教范式。如今,在巫傩祭祀仪式表演中更加增加了武术打斗、民俗体育等内容,表现出追求健康幸福的现实主义宗教情感,使仪式化体育文化事相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赋予了原始体育具有象征符号学意义的精神皈依,彰显北方仪式体育“无意识”状态的信仰秩序法则与规范体系。
萨满跳神祭祀仪式在滦河流域广为流传,在内蒙、辽西、冀东地区都有深厚的基础,其中,现代蒙古族祭祀敖包习俗源自萨满跳神仪式,在信仰与仪式行动中做出各种蹦、跳、踢、扑、抓、打等身体动作,注重平衡、协调、节律、对称,彰显原始体育强烈的仪式色彩。滦河流域萨满跳神祭祀仪式实践了蛮荒时代原始宗教与体育互为载体的衍生范式,这种依附关系成为滦河流域仪式体育发生、发展、演绎的逻辑事相。北方巫傩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祭祀仪式中体育的出现赋予体育以神性象征,仪式体育生态文化内涵表现出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并按照宗教秩序法则确定仪式体育叙事话语,使体育文化与宗教文化相得益彰。在发生学意义上,萨满跳神仪式体育程式性、象征性、规定性的活动行为,可以解释为“行动为先”思维映射下的活动表征,成为主导滦河流域体育宗教文明演进的逻辑线索,实现了“体育实践与宗教实践、仪式实践”共同发展变迁的文化理路。萨满跳神宗教祭祀对仪式体育的全面掌控与支配,使体育表现出“蛰伏”状态的宗教仪式情感,对滦河上古体育形成立体渗透和影响,也是仪式体育对人的信仰展开全方位教化与规训的肇始。
2 北方巫傩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起源的考古推断
2.1 巫术向巫傩转向:史前北方无傩的学术纠偏
中国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5],巫术在颛顼“绝地天通”(《尚书·吕刑》)之前就已经非常普及。据考古发现,迄今两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就可能出现了巫术表演[6],仰韶文化时期的“巫师舞蹈做法”说明巫术仪式已经相当成熟[7]。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都有巫术占卜的记载,“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巫”同“舞”,利用巫术舞蹈达到对神灵的控制,巫术舞蹈构成了体育的原始形态,所以,体育“巫术说”在表述上更准确,体育“宗教说”在历史发生的现象逻辑层面上有失偏颇,因为宗教起源于巫术,但却是两类不同的祭祀文化形态。“及少皞之衰也……民神杂糅……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下》),说明在少皞时期不分社会阶层人人可通天神的“个体巫术”,试图通过巫术来控制天体神,用“超自然力量”主宰天地而凌驾于个体之上。颛顼时期“绝地天通”是巫术改革的早期范式,氏族贵族拥有沟通天体神特权,人神平等被“政巫合一”所取代,仪式、祭典活动中娱神、媚神事相的神灵崇拜推动了原始宗教的发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宗教祭祀成为隆重的国家仪典。“帝颛顼好其音……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吕氏春秋·仲夏纪》),颛顼作“承云”之舞祭祀神灵,此外,《仲夏纪》中记载帝喾时期“九招舞”表演时“凤凰鼓翼而舞”,此外还有“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舜典》)、“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史记·夏本纪》)等记载。宗教祭祀舞蹈“百兽”和“凤凰”是部落图腾形象,披着兽皮又具有巫性质的傩舞表演,也是巫傩文化的起源,实践着巫术与原始宗教(图腾信仰)的合二为一。考古发现,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出土的大量刻陶假面面具,证明7 000多年前我国北方就出现了傩文化,这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纹傩祭图几乎同时,也对北方无傩的学术纠偏提供了有力佐证,形成了史前南北巫傩文化对峙繁荣的文化镜像。
2.2 历史发生学: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活动探源
承德头道营后街88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学发现,把滦河流域古人类活动史推断到20万年前,同时,也印证了滦河源头是古滦河流域文明的形成之地。夏鼐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认为,氏族制度解体及有组织的阶级制度建立是社会文明转向的主要标识[8]。学界多把滦河流域文明史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红山后遗址、牛河梁遗址、西寨遗址等史前遗存的发现说明滦河流域上、中、下游至少有五六千年的文明史,先后被商初孤竹国华夏族、春秋令支国山戎族,及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满族等统治,确认了其由华夏族和戎狄各族共同谱写的文明史卷。梳理滦河流域人类文明史话,学界零星报道“遇冷”现象与地域深厚的文化脉系形成了极不协调的文化关系,这归结于滦河流域民族间因长期战乱融合而逐渐同化消失,很多游牧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造成地域文化记忆缺失,从而增加了研究考辨的难度。
自古以来,滦河流域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古滦河土方、山戎、靺鞨、东胡、匈奴、乌桓、柔然、高句丽、突厥、女真、鲜卑、契丹、室韦等20多个民族都有萨满信俗。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早期主要存在于中上游少数民族,但很多民族没有留下文本记忆,造成文化记忆链断裂,鉴于此,冀求从发生学角度给予合理性解释。“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三朝北盟会编》),“珊蛮”即为满—通古斯语“萨满”(Sa-man)的音译,这也是滦河流域满族先民女真人萨满文化的最早记载。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和魏家窝铺遗址发掘的祭坛、积石冢、女神庙、生育神和农神陶塑、石母像等,唐山迁西县罗屯镇西寨村发现的距今7 0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雕头像和石母像,以及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卜骨等,印证了滦河流域中上游与下游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凸显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特征,也是发现的最早具有女性崇拜性质的大型祭祀遗址,反映了早期滦河先民对萨满生育神的崇拜意识[9],进一步证实滦河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活动至少要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是滦河流域社会文明的起源,也是进入具有国家雏形性质原始文明的重要标识[10]。从滦河文明历史发生的角度来看,红山文化时期的萨满跳神仪式成为体育宗教文明发生、发展、演绎的标志性文化事件,由此做出滦河体育文明“萨满说”的学术推断。
3 北方巫傩对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统摄关系推演的合理假说
傩文化由巫派生而来,学术界称之为“巫傩”,在实然性意义上超越了巫时代的纯粹精神范畴,而被赋予宗教文明色彩,但其本体意义没有脱离“巫统”的神学框架[11],在供奉傩神的信仰系统中,用傩仪、傩礼、傩面、傩舞等多种活动表达祭祀祖先、神鬼概念的宗教思维指向。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北方的傩文化与滦河流域磁山文化相当,也与伏羲文化几乎同时,在时间线索上早于萨满文化。《禹贡九州图》显示,滦河流域属冀州之地。康殷先生在《文字源流浅说》中认为,“冀”字为假面舞人之形,这点与蚩尤戏相合。《列子·黄帝》记载了黄帝与炎帝率部族熊、罴、狼、豹等十大图腾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阪泉之战后,蚩尤作乱,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麦》),“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五帝本纪》)。阪泉、涿鹿之战与冀州均为滦河流域属地,从对滦河早期先民对动物的图腾崇拜到对蚩尤形象模仿,为滦河流域早期仪式体育文化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基因。《述异记》中记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头戴牛角而相觝”,表演者头上有角,面戴恐怖狰狞面具装扮蚩尤形象,成为滦河流域舞蹈祭祀的早期形态,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原始仪式体育宗教文化。
冀州具有敬神、娱人娱神意义的傩祭(跳傩)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同属北方自发产生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把人作为幻化的神灵形象,通过角色扮演转达神性至尊。跳傩仪式“绝地天通”的文化功能表现为以阴阳为纲纪,充分体现五方(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之维。从现象发生逻辑来看,北方巫傩文化要早于红山文化,而萨满跳神仪式与巫傩文化均表现为原始宗教自然化的进程中完成人神符号转换的认识学意义。萨满与巫傩确实有共同之处,其本质均属超越神灵的巫文化范畴,是北方巫傩仪式变迁的宗教实践。另外,在滦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出土的人面牌饰是东胡丧葬面具的渊源,与滦河流域契丹族佩戴假面葬俗表现出共同的精神信仰[12],是典型的北方巫傩文化遗痕,而这一时期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活动已经非常普及。综上,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生成逻辑线索按照“原始动物图腾信仰→蚩尤戏→跳傩→跳神”演变程式,阐明跳傩与萨满跳神发展逻辑,也是对二者内在推演关系作出的合理性假说。
4 北方巫傩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的哲学辨微
“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源于氏族社会人类对身体的感悟和对自然现象的体察[13],早期人类用阴阳思维来解释和认识客观世界,实现了宇宙由“气、行、质”浑然一体的“混沌”状态向天地“阴阳”二分,再到万物生成的演化图式,确定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学命题[14]。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五运历年纪》)、“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人道被置于天道、地道“阴阳”之间,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预示阴阳两分向“交感、平衡、转化”辩证统一转化的哲理性,表现出早期人类对生命本体认识超越的自然理性,人成为天地时空对接的通道,这也是把人类活动空间置于阴阳之间发生学解释之滥觞。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地交而万物通”(《易传·彖传上·泰》),“阴阳合德……以通神明之德”(《易·系辞下》),阴阳相交、配合才能使万物和畅,达到最高境界。在巫傩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的原始思维模态系统中,人们如何认识阴阳相交?在阴阳相合中发挥怎样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阴阳概念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如何进行思维活动和行为意向呢?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简化澄明或许在原始宗教哲理中有迹可循。
4.1 我思故我在:身体“在场”与“不在场”
对于巫傩阴阳之间关系模型的解释可以在西方哲学身体“在场”与“不在场”[15]的辩证关系中找到答案。“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认识哲学的逻辑起点,表现出“主体”取代“理念”的“在场”形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把“先验想象力”看成是对象“不在场”时表现出来的能力,强调自在世界的上帝、灵魂等超自然物认识,已然超越理性认识限度,自然陷入“二律背反”自解矛盾的思维批判中。针对西方“在场”“不在场”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性,胡塞尔、海德格尔发起对超感性世界和纯粹在场传统哲学的理性思辨,主张“心灵的存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知觉与想象联袂出场使“在场”与“不在场”结合为一,实现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突破。在场与不在场两个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统一,与巫傩文化阴阳思维确乎有诸多相通之处。巫傩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本身是一种超验性的意识,试图通过动态身体符号把个体情感附丽于现实之上,实现“实体”向“主体”回归,用身体“在场”来表达“不在场”的天神精神主旨或意愿,确立“天人合一”的阴阳哲学思维,引领生命个体的情感秩序并入“天地”格局。巫傩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的演绎风格表明,表演者希望借助“超验”力量和图腾形象行沟通阴阳之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形上的天道(天体神)与形下的地道(具象存在)不可须臾相离,不可感知的“道”与可感知的“器”之间形成“不在场”与“在场”的逻辑关系。巫傩与萨满仪式文化阴阳之间的哲学范畴在于实现矛盾对立转化,彰显“人道”对“天地之道”的顶礼膜拜,用身体现实“在场”与“不在场”表达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实践着原始仪式体育阴阳哲学观的深层逻辑支撑、克服与精神超越。
4.2 假面阴阳:面具符号“能指”与“所指”
史前巫傩文化以巫术和原始宗教为母本,在实现原始巫文化转型中,人类认知事物的方式依然建立在天地阴阳哲学原型观念之上。中国传统哲学“阴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巫傩文化在实然性意义上是思维与存在的现象逻辑,通过跳傩演绎个人或群体心理镜像、心理寄托,而运动态肢体的客观实在性成为沟通阴阳之事的物质实体,孕育和构建最原初的主体话语。萨满仪式活动是滦河流域民族原始古朴的文化信仰,是被置于人神、阴阳两界之间的身份象征,用跳神舞蹈演绎灵魂世界,这在精神意义与神学层面上似与跳傩假面阴阳能指表达有相通之处,巫傩与萨满仪式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可以从假面阴阳的面具符号中探寻。
内蒙古赤峰考古发掘的玉面具、石面具、骨雕面具、岩画人面图表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面具已成为滦河中上游先民极具代表性的宗教祭祀仪式符号象征。在赤峰敖汉旗至今仍传承的古老傩戏——呼图格沁,及被誉为燕赵“乡人傩”活化石的丰南篓子灯,都是滦河流域巫傩仪式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傩舞仪式仍保留古老风貌,表演者所戴假面风格多样,彰显滦河先民悠久的面具文化艺术史。另外,面具曾是滦河流域萨满教普遍崇奉的文化符号,并借助萨满跳神仪式空间得以传承。在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祭祀、宗教、信仰诉求层面上,面具类型可分为祭祀面具、求子面具、辟邪驱鬼面具、治病祈禳面具,这在诸多史料中都得以查证[16]。在朝阳出土的契丹族面具随葬品,“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契丹国志》),契丹族覆面葬俗与傩舞、萨满跳神仪式表演时使用的巫术工具——面具和网络有关[17]。
在滦河流域巫傩面具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表演面具符号系统中,充斥着原始二元神论宗教思维,如肉体与灵魂、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天与地等,这也是假面阴阳哲学“能指”与“所指”的本义,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其中,“能指”是符号的本体意义,“所指”是基于“元符号”范畴的深层阐释。滦河流域傩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所使用面具符号的“能指”意义在于隐藏身份,赋予肉体以神性象征,以面具替代神灵的遗绪,行沟通阴阳之事;其“所指”意义则在于,表演者作为神祇象征符号试图通过“内视象”进入灵魂世界,表达求吉避祸的生命意识,映射出表演者复杂的心理镜像,面具符号所具有的原始宗教本质是巫傩面具的孑遗或嬗变,宗教性赋予萨满跳神仪式体育面具更强的神圣象征,并一直同萨满母体宗教保持密切联系。在巫傩文化中,面具是沟通人、神、鬼的媒介,是宗教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在萨满仪式体育祭祀活动中并不具有普遍性,这也是面具符号日渐式微最终走向衰亡的内因“所指”。
4.3 巫统与血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巫文化作为世界普适性的文化事相,实践着社会文明的崛起。巫傩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起源于巫,并始终没有摆脱巫文化的思维法则和行为框架,其原始性基因的法术本质成为引领滦河流域诸多民族原始信仰转轨与变迁的现象逻辑。巫傩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是人类社会认识论由“巫学”向“神学”演进的典型事件,事件的起因是早期人类对宇宙本体缺乏解释力,对科学理性鄙夷排斥的群体心理镜像折射出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形成一种超经验判断的“形上”意义的认识哲学。但巫傩只是对传统巫术逻辑范畴意义的形式调整,A·罗伯特在基督教起源的研究中认为“原始巫术有仪式无崇拜”[18],意味着巫傩本身是缺乏宗教信仰的,这种具有“巫统”意义的跳傩思维本质在于表达人与客观宇宙空间存在“超距离”的交感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是一种思维存在,形成对客观物质世界认知论的形式遮蔽。而萨满跳神仪式体育的宗教意义在于原始先民认识思维的整体提升,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构建生命意义、身体哲理与天地法则,提出“天地人三界”宇宙哲学命题,即:天为阳界,地为阴界,天产生万物,而地是万物繁衍生息之本,萨满仪式体育活动沟通天地阴阳两界,实践对立统一、和谐共生,这体现在萨满教宇宙起源论或创世说论断中,确立了宇宙三层次结构的观点。滦河流域契丹族、满族、蒙古族对血缘祖先的信仰崇拜,是在用虚构的身体符号实践着神人嬗变,原始巫统秩序被打破,血统秩序得到张扬,改变客观宇宙世界的能动性被放大,并赋予“绝地天通”的神性功能以后,人可以借助智慧、情感力量操纵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原始宇宙认识范式。
按照巫统与血统建立起来的宇宙观念体系赋予巫傩、萨满跳神演绎者以天地符号[19]。“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系辞下》),用天地思维解释宇宙世界的景象或状态。“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礼记·郊特性》),确立上界为天,下界为地,中界为人的“天、地、人”三界相通的哲学命题,祭祀、舞蹈等仪式体育活动成为连接形体与精神的立体空间。巫傩、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正是借助外在超感力量实现三界共通,在巫统与血统构成的关系谱系中确立“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赋予生命个体以“通神”功效。满族萨满史诗中把“萨满”解释为“晓彻”,即通神、交往于人神之间的使者。《蒙古秘史》把萨满巫师称之为“幻顿”,具有“通天巫”能力,再现萨满贯通天地的宇宙观。滦河流域游牧民族土方、山戎、东胡、肃慎、蒙古、满族、匈奴、突厥、契丹的萨满信仰中都有敬鬼神,祭天、地、日、月、星的习俗,这在《晋书》《魏书》《周书》《旧唐书》《元史》《金史》等均有记载,将自然现象、神灵作为崇拜对象,并依赖血缘传递,成为血统意义上的萨满守护神,在现代萨满唱词、唱曲中仍不乏巫统与血统文化的遗风。
5 巫傩向萨满跳神仪式体育嬗变的文化图式呈现
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是巫傩向宗教演进程式中的特殊文化事相,巫傩与萨满两类文化的演进关系,可以借助恩格斯的宗教历史发展“文化图式”理论来认识。“文化图式”认为宗教经历了“自然宗教→神教”“自发宗教→人为宗教”“部落宗教→民族宗教”三种图式结构[20]。北方巫傩文化形成的巫性思维对滦河流域萨满教演化生成产生了极强的统摄作用,原始宗教按照自身逻辑法则实践着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嬗变程式。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宗教文化形态特征,从文化图式角度对巫傩和萨满教仪式体育的宗教关系进行系统解释。
5.1 自然宗教向神教发展图式
巫傩是北方宗教的原初形态,实现了对纯粹巫性思维的超越,赋予人类超自然力量来达到对外在世界的支配。在乡傩、军傩、宫廷傩等傩文化系统中,驱除邪祟、媚神求愿的巫傩祭祀性文化表达了灵魂信仰的观念,用与神交流(灵魂“在场”)的方式祈求神灵庇佑,这种神性思维在宗教学意义上已然摆脱了巫性思维(支配、控制神灵),成为“神人同娱”宗教实践的早期形式,和引领滦河流域宗教发生、发展的原始基因。萨满教、喇嘛教、道教、藏传佛教等构成了滦河流域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谱系,萨满是傩变的早期形态,早于其他宗教文化,表现为自然宗教特征,如满族游牧先民生产力低下,对风、雨、雷、电、日、月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认知,在万物有灵思维引导下产生自然崇拜意识,滦河流域自然宗教由此发轫。《辽史》记载,滦河流域契丹族信奉萨满教,等级可划分为太巫、大巫、巫。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巫傩神灵观念,自然崇拜物被神化,试图通过萨满仪式体育活动表达和传递神灵旨意,实践着自然宗教向神教发展图式的转向。
5.2 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图式
恩格斯认为原始宗教是自发产生的,尚不具备系统化、规范化的神学宗教体系、信仰体系和宗教形态,但随着宗教组织不断完善,祭祀活动开始出现专职人员,实现了向人为宗教的演变。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明形成于新石器时代,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独立于身体生命力之外的灵魂幻象被对象化、客观化以后,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表象化结果表现为,灵魂意识被神灵崇拜概念所取代。爱德华·泰勒认为,原始人把个人存在作为其他物质存在的标准,用个体直接经验推论外在物质世界,实践着身体与灵魂并存的二元哲学。滦河流域蒙古先民把独立于躯体之外的灵魂称为“翁衮”[21],即萨满教神具或神偶,表达对祖先神、动物神、自然神崇拜的神灵观,实现了自发宗教“灵魂观”向人为宗教“神灵观”的逻辑推演。身体依赖灵魂哲学范式与笛卡尔的身体与灵魂并存的物质二元主义(substance dualism)立场相吻合。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在吸收巫傩神灵文化元素以后,用神灵附体的形式赋予萨满接神、通神的“特异功能”,用互动二元主义(interactionist dualism)实践着身体与灵魂合二为一,弥合精神与肉体的二元裂隙,萨满的本体功能被放大,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宫廷萨满利用职能与神威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现对民众思想的操控,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这在行为逻辑上改变了巫傩时代人人可通神的宗教无序法则,原始自发产生的宗教形态被人为宗教所替代。
5.3 部落宗教向民族宗教发展图式
融合北方巫傩元素以后,滦河流域原始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具有典型巫觋宗教特征,这对满族、蒙古、契丹、乌桓等诸多北方民族祖先宗教信仰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民族以本部落祖先发祥地的山水等自然物为崇拜对象,定期举行萨满跳神祭祀仪式活动。《辽史·地理志》记载契丹祖先居住地马盂山、浮土河,即滦河中游的平泉县,通过举行萨满祭供大典保佑本部落宗族繁衍生息。女真人奉金莲川(今内蒙古正蓝旗)麻达葛山为神山,地处滦河上游正蓝旗,萨满跳神仪式时除祭山外,还有鹰崇拜意识,“女真”二字意为“海东青”(猎鹰),在萨满祭祀神杆上挂一些供鸟啄食的肉类,充分表征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鸟图腾文化。滦河流域萨满原始部落宗教的鸟图腾意识与商族信仰有关,这滥觞于“玄鸟生商”(《诗经·玄鸟》)。丁山、童书业、胡厚宣、彭邦炯、王玉哲、金景芳、干志耿、朱彦民等诸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证实和支持了“商族”部落发源地“冀东北说”[22],使早期萨满教形成了典型的部落宗教特征。但伴随部落解体,萨满部落宗教开始走向衰落,继而被一种新的萨满民族神崇拜所取代,形成鲜明的民族性宗教形态,实践着部落宗教向民族宗教的转向。滦河流域多民族杂糅的生存状态决定了萨满信仰的多样性,各民族没有制定明确统一的教义和宗教主旨,加之,藏传佛教、喇嘛教等民族宗教及国家宗教、世界宗教的冲击,萨满宗教失去了得以传承的民族文化空间,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渐趋没落。
6 余论
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是滦河流域原始的宗教信仰,展示了滦河先民用身体语言符号及身体情感演绎人类认识、控制客观世界的思维镜像。阴阳、天地、宇宙观等哲学范畴可以解释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活动巫统与血统二元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自然法则。与北方巫傩文化融合以后萨满宗教文化被赋予巫性色彩,构建了萨满教仪式体育哲学体系,开创了古滦河文明,并经过世代嬗递形成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质的萨满跳神仪式体育信俗,成为早期氏族、部落文明的精神符号。透过岁月雾霭,依然可见滦河流域先民的生命意识、道德伦理与族群崇拜的文化意义所指。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滦河流域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活动受国家宗教、世界宗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嵌入的影响,被取代或融合而日渐式微,但也曾深受上层贵族阶级偏好,成吉思汗将萨满定为国教,努尔哈赤定期组织萨满跳神祈福活动,顺治帝从国家政治层面设立萨满跳神祭祀制度,把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活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巫傩与萨满跳神仪式体育属于萌芽状态的直观哲学范畴,缺乏对客观世界的抽象思辨,按照黑格尔哲学标准的思辨性与体系性范式要求,构建原始古朴的自然观、灵魂观、宇宙观为核心的神学框架,涵括认识世界的神秘思维与宇宙万象本源的认识哲学之维,试图用“万物有灵”“天人神三界”辩证统一的唯心、唯物主义解释混沌世界疑迷。“人体同构”的宇宙观念是在绝地天通之后“天人之道、神人嬗变”认识实践经验的总结,成为引领滦河先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行动纲领。如今所存留的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文化是变异的宗教形态(如张家口、承德等地“香头”活动),在民间习之亦颇广泛,巫性功能得到放大,已然失去了以往神教、人为宗教、民族宗教的文化基因,但在边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中依然具有相当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如滦河中上游那达慕大会、萨满神舞、二贵摔跤、背哥、单皮鼓舞、太平舞、打嘚拷、神刀舞等民俗活动事相均是萨满仪式体育文化的衍生品,形塑了具有边内外文化特色的精神文明和体育文明。外八庙、木兰围场、避暑山庄、热河文庙等机构推进了滦河流域宗教文化的繁荣,但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影响,游牧农耕文明渐趋衰落,原始宗教文明逐渐被现代科学人文主义取代,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活动也进入了传承的危机期,加之,萨满跳神仪式体育活动渐渐失去了得以延续的文化空间,最终难逃衰落的命运,但原始古朴的哲学思维定势对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宗教思维的影响依然持久,这正是滦河古老宗教文化的精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