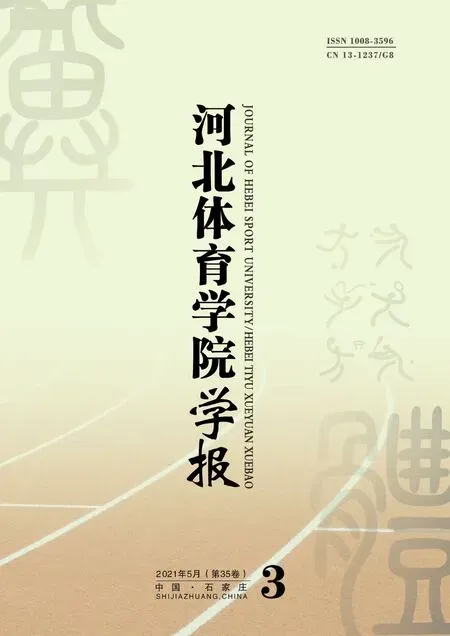源于大自然的戏剧:足球场域中的身体语汇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现行的主流体育项目的源头是古希腊竞技运动,直接来源则是英美户外体育,因此,它们同时蕴含着欧洲旧大陆和北美新大陆不同的身体理念。从户外游戏性仪式表演的视野上看,古希腊戏剧与现代足球相联通。足球是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中的一员,却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势地位。足球融合了更多动物学、进化论及原始表演的元素,因此获得了惊人的市场关注度。足球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游戏形态,却可以很好地建立起一种覆盖性很强的文化复合体。足球在中国的对应物很多,有作为国球的乒乓球,也有同为大球的篮球、女子排球,而在动作惊艳奇特方面则与传统戏曲的武功相对应。足球与中国文化的高度匹配,令其被中国人大范围地接纳,但其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又存在着理论的兼容与实践的不兼容的矛盾,并派生出一系列超体育学的问题。
1 自然游戏、狂欢仪式、聚会群体:足球蕴含着丰富的戏剧元素
竞技性、仪式性与戏剧性共融于足球之中且相辅相成,足球的场内场外都散发着多元化的戏剧元素。足球赛事的戏剧性有多种呈现方式,戏剧的节日性、祭典性与聚会性元素都很突出,因此,足球的非世俗价值也极易引起学者的注意。
德斯蒙德·莫里斯看到了足球的游戏性、仪式性与象征性,“虽然表面上球员们似乎在激烈战斗,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并不是消灭彼此,而只是越过对手,将球射向球门,以完成象征性的猎杀。”[1]兰伯特将足球赛事解读为一种象征性事件,“足球的规则通过一种方式使我们的这种期盼达到高潮:那就是进球。进球意味着重大的转折……意味着夺得世界杯冠军被历史铭记或者是成为被人遗忘的失败者。这道分界线是如此明显,而且跨越这条线的经历也同样难以忘怀。”[2]200同时,他还准确感受到了足球的戏剧性,“比赛中,突然的进球就会产生极为戏剧性的且令人满意的情感,也可能造成恶意犯规。”[2]200-201加莱亚诺认为,为了避免犯规后遭受处罚,球员大多学会了表演性地干扰乃至袭击其他球员。“有多少小剧院能够装载足球这出大戏?有多少舞台放得下那块矩形的绿草地?不说所有的球员都自顾自地用双脚表演。有一些演员在折磨同行的艺术方面是行家里手。这些人戴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圣徒的面具,朝对手吐唾沫,侮辱他,推搡他,弄迷他的眼睛,给他下巴一记老拳,肋骨也少不了来一下,扯他的头发,拽他的球衣,当他站住时踩他的脚,倒下时那就是头——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裁判干的,而巡边员只注视掠过他眼前的阴云。”[3]24-25足球场域中的表演时而会演化成一种非法行为,同时也是避祸性质的伪装。
足球的狂欢性在胜败双方都有反映,但在胜利者一方体现得更为明确。加莱亚诺曾对类似的场面做过评述,“这时胜利的人们冲进堡垒,将他们的11个英雄高高举上肩头,是这些英雄为他们带来了这史诗般的壮举,这辉煌的成就,这令他们为之流汗、流泪、流血的伟大功绩。然后我们的队长,披着再也不会被失败所玷污的祖国的旗帜,举起银色的奖杯亲吻着,这是荣耀之吻!”[3]32感觉与感性,体验与体会,构成了人类学的高度的身体性基础,而站在人类学的高度认知足球更可以看到其中的穿越性价值。“观众看戏或看球所以能够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个中因素很多,但首要因素在于‘分享’。足球与戏剧都不是‘孤芳自赏’,而是‘群芳群赏’,观众中每一个个体平时压抑的情感,由于有了群体的共鸣与支持便变得‘胆大妄为’起来,于是才有了恣肆汪洋的宣泄。”[4]高强度的精神贯穿力给足球披上了欢乐的外衣,足球由此变得光辉熠熠。
徐能看到了足球的戏剧性,并试图将其演示之戏与游戏之戏融合在一起。“所有这些游戏和运动都是模拟生活的剧情,这种模仿过程没有内在价值。然而,由于足球的规则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和机会极其富有变化的结合,从而使游戏结果不可预测,足球游戏显得十分特别。”[2]20一般而言,足球和戏剧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没有脚本,而后者有脚本,但是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理念的再现式模仿,这种理念就是人类社会建立之初即存在的一种对于英雄的模仿、崇拜、纪念。在隐喻的世界里,戏剧与足球几乎是一体的,两者充满了共融性与同一性。
无以否认,较诸传统的演剧类型,顶级足球赛事充满了极限性活力,足球场上的竞技者也比传统戏剧中的演员更具活力,他们以清一色的青年人为主导,身体强健而技艺娴熟,神情烂漫而活力四溢。足球的场域也比任何一种传统剧场更为宏大瑰丽。2019年4月18日,欧冠1/4决赛在热刺与曼城之间展开,而VAR变成了主宰者,它让比赛双方在几十秒内体验到了大喜大悲,无比夸张地强化了赛事的戏剧性[5]。经过了长时间的阵痛,足球的裁判业开始接受电子产品的指令,以求获得更大的公正性。工业化时代的所有成果都会在适当的时候进入足球领域,足球的现代性也在不断浸润着足球赛事过程。
传统戏剧大多以室内表演为基本形态,而足球将民众从相对逼仄的室内引至室外,高度自然化的环境给足球提供了更好的表现力。足球由此超越了传统的演剧空间,变成了一种户外聚会形态。正因如此,足球更像一种现代大戏。在现代性大戏剧观念的辐射下,传统戏剧的消隐态势十分明显。大自然的进化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自我表演,不妨将其作为考量人伦世界多维度表演形式的标准。足球的户外性导致了很多自然元素的出现。“1958年6月16日,在伦教举行的一场国际足球赛中……守门员道莱伊西一脚长传,球借助风力在地上一弹越过守门员的头顶直向球门飞去,进了一球。这在英国足球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6]足球和乒乓球、羽毛球不一样,它从来就无惧风雨,具有霜天烂漫的自然性。在此理念的映照下,传统戏剧或表演形态或许只能算作一种现代竞技表演形态的影子,而无法转换为一种现代性的演艺实体。
可以回忆一下传统戏剧的独特镜像。这里不妨作出一些极端性、夸张性、虚拟性、谐谑性的推论。传统戏剧并不以身体优势见长。传统戏剧带有很强的室内、局促与逆人性的元素,其强大的动能来自一种规劝、教化、人格设限、道德戒律之类的内涵。由于承担着与神沟通的外在功能,传统戏剧往往有压抑人的自然性的种种戒条,这便产生了与体育的差异。“当代人对体育运动的爱好似乎是跨地域跨文化的人类现象,和明显表现民族性的戏剧不同,体育运动的基本矛盾是游戏与竞赛的对立统一,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导。游戏要的是个人与自由,竞赛则强调集体与规则。”[7]除此之外,戏剧和体育的差异还在于虚构与真实,即便如此,二者也有兼容点。“大部分人可能会在这些人(足球流氓)身上发现关于暴力、价值等东西上的不平衡……这没什么特别之处。像足球流氓这样的人,他们混淆了真实生活与游戏;因此他们不能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给予不同的精力。他们被游戏的剧情淹没,以至于他们误以为它是现实生活中的剧情,好像足球比赛是真实生活中的一种战斗。并且,他们想成为真实生活战斗的一部分。”[2]20足球是身体直接对抗的运动,很难完全脱离暴力元素,因此,崇尚暴力者也时常成为足球生态圈子中的重要元素,它折射出人世间的本真风貌。世间有很多种类的真实性,任何人都会提出自己的真实性标准,其中不乏矛盾之处。于是,探讨足球的真实性就显得很困难。
游戏是人和诸多生物共享之物,其核心价值便是高度的自由、解放与舒张的快意,足球的游戏性中就包含了高度的精神解脱意象。贝克汉姆曾经讲述过他少年时代游戏于足球的事迹,他赖以成名的超远距离射门就来自他自身的游戏性练习。与此同时,他也回忆起和他一同踢球的同伴的沦亡史。“我有个朋友,他过去常到公园里来和我们一起玩,可他父亲是个望子成龙的人。他父亲总是说‘你不能做那个,你应该去做这个。’我那个伙伴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球员,但他不想再踢球,于是他从那以后也就跟足球无缘了。”[8]由此不难看出,当足球游戏失去了自由的前提后就很可能消亡。足球中的游戏性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指向,其概念末端则是狂欢精神。
足球和戏剧的连接点很多,大型足球赛事大多伴有戏剧性的狂欢景象。诚然,足球无法完全取代戏剧,但是足球有更为强烈而纯正的交互感、仪式感与聚会感,它一直在构建一种新型的戏剧性仪式。无可否认,球员的庆贺方式也是一种表演,雷德坎普就认为那里存在一种表演的元素。“踢入关键进球的射手大多瞬间消失在队友们一跃而成的金字塔中,常常靠记分牌和广播才能辨认出来时,在意大利逐渐形成了一种胜利礼仪。”[9]高度清晰的身体至上主义给足球带来生机,也使足球的超人类性得以体现。当然,球迷庆贺一直是聚会活动中的主导性能量。2019年11月24日,第60届南美解放者杯的决赛,弗拉门戈队2∶1逆转河床队夺冠。赛后,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庆祝,数万球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庆贺胜利,构建出一种狂欢镜像。足球赛事也由此呈现出显著的戏剧情境。
2 原始活力、英雄梦想、情感宣泄:足球对传统戏剧的超越
工业化时代以来,以戏曲、话剧为主导的近代戏剧大多和夜晚、剧场、灯光产生了联系。在各种各样灯光的映照下,人类渐渐习惯昼伏夜出,人性中的自然性也相对削弱。人们开始蜷缩在一种固化的狭小空间内或言说或高歌或模仿,却没有顶级的活性情态。
传统戏剧就是这样走向没落的。一种观赏类艺术是否没落,关键在于观众。中国学者在阐释戏剧与足球的反差时已经注意到了市场调节的作用,“足球和戏剧的差异究竟在哪里?也许足球拥有的内容恰恰就是当今戏剧缺少的东西。显然,足球构成了球迷生活的重要部分,某些时候,球迷与足球已经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他们可以为每一次进球而疯狂,也可以为每一次失败而哭泣,心理上的认同,导致一个巨大的空间发生共鸣。”[10]其实,足球优于戏剧之处就在于它是世界上至为纯粹的人性核心构件。“戏剧则不然,即使是演员声泪俱下,也难以撞开观众情感的大门,剧场原本比体育场小了不少,可为什么演员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却如此遥远,莫非这个小小的空间发生共鸣的难度更大?……无非是心理认同产生了障碍。”[10]足球的价值完全在于其具备了更为原始的野性的力量,换言之,足球的美在于人类自然生命之美,足球因此而拥有了生命核心价值,就等于拥有了生命中的最高境界。
不妨比较一下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差异。美国文化以好莱坞电影工业为核心,更看中财富与青春价值,任何人只要拥有财富或青春,都会在美国找到价值实现的途径,而失去了两者,就等于失去了在美国的主导性生存意义。欧洲则不同,欧洲文化以大量的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美的设计闻名。比较而言,欧洲文化更为厚重,生活在欧洲的每一个年龄段以及每一量级财富的拥有者大体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换言之,美国像少年,而欧洲更像中年人。如此理论推衍到足球和戏剧的领域也成立,足球更像美国,而戏剧更像欧洲。由此不难看出,足球的现代性更为鲜明,足球胜过传统戏剧的地方主要在于其自身的活力以及其宣导社会压力的功能。“人们内在的大量能量,特别是社会各阶层中有一股活跃的能量,需要释放出来,而足球场则是释放这种能量的最好场所。……足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娱乐和欣赏项目,而且起到场内表演场外受益的效果。”[11]当失去了强悍的身体极限性活力之后,戏剧的垂危感就会呈现。
戏剧是剧情的俘虏,也是演艺明星的招牌。从观剧学的角度看,球迷对顶级赛事的热恋往往肇始于追星,类似的追星现象在市井社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无以否认,现代社会中的英雄已经为各种职业所分解,出现了差异巨大、种类繁多、各显其能的职业英雄,他们当中有思想家、艺术家、足球明星,更有劳动模范、抗敌英豪、技术精英。职业英雄的梦想几乎淹没在职业性的技能体系内,人们往往很难觉察到其中的英雄性,于是,虚拟的戏剧或真实的表演便适时出现了,女人的追星梦,男人的英雄梦,都可以在戏剧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表演活动中实现,这便是戏剧和现代足球生发的缘由和存在的价值。传统戏剧的衰微也是职业化体系衰微所致,于是才出现了原始英雄复活的现象。足球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第一运动,原因在于其中始终蕴藏着原始英雄的纯然类别。
足球是自然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仪式表演,人们经常借戏剧术语来描绘足球。“C罗被换下,舞台留给了梅西一个人。”[12]戏剧学语言在当今的足球评论中屡见不鲜,向人们展示着足球与戏剧的本质联系。足球本身可以营造出一种节日风味,同时也会释放出一种超越日常的生活气息,这与人类原始社会中的仪式活动极为相似,其中的祭典性、礼仪性与表演性元素都很丰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宗教开始衰落,以体育、电影和摇滚音乐为代表的新型演艺形态成为新型的“宗教”,而足球则兼具大片与摇滚音乐的价值,成为一种值得全世界关注的超级演艺形态。很多世界知名球队都有极强的影响力,其原因很多,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它保持着一种缔造节日、创造神话的能量。莫尔特曼关注人类生活的宗教性元素,同时也对世俗性的节日有过阐释,“神圣地点和神圣时间是宗教狂喜节日的外部特征。沉醉在节日狂欢中的人们与上帝同住在圣殿中。在节日期间,时间被神圣化。所有的时间都被用完且消逝了。但是,节日喜庆时间中断了时间的流逝,并重新产生时间。每个喜庆时间都回到时间的源头,因而也回到源头的时间中。在节日的神圣时间里,人们不仅与神同在,并且与神同时。”[13]游戏与节日相伴而生,人们很难摆脱节日的精神制约,即便放弃了节日的日常性游戏,也会在其他领域重构节日,此类节日同样神圣,这便是大型足球赛事存在的理由。
足球是一种超种族、跨国界的人类聚会项目。“我一向认为,一场足球赛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而每个赛季的来临,则无异是一连串的狂欢节。因此,凡在赛季中出版的足球报纸,就相当于剧场说明书、入场券、请柬、战报、菜单、连载小说、悬念电影、辩论大赛、七嘴八舌的闲聊。总之,它一定是抢手的、有趣的,尽管它又是纸上谈兵式的。”[14]足球延伸到大众生活中,则会递进为一种节日。足球既是节日的承载物,又是仪式的再现性化身;既是一种身体的工业,还是一种古老的表演形态。足球在新的时代一直在参与一种蜕变程序,足球自身的游戏性连同其内在的生命品格,一同散发出一种超越时代、阶级、种族、地域的集约式能量。由此可见,足球的聚会性能量之强大,其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也体现在这一层面。邵培仁认为:“大众传播机构在运作管理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氛围,是由大众传播活动集体参与者的行为方式聚合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模式。”[15]在类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中,人们的情绪彼此感染,这种所谓的世界杯病态极有可能感染到现场乃至其他场域观众身边的每一个人。“观众在目击足球比赛后,更加期望球迷间发生狂热行为。换句话讲,比赛场地的狂热行为使队员的情绪更加激动,增强了他们的好斗以及看台上观众的狂热行为。”[16]其实,足球的场域弥漫着大量的以荷尔蒙为主导的极端性、本能性、扩张性、传染性元素,观看足球比赛在很多情况下就自然地演化为一种对偶像的欣赏、模仿、崇拜乃至迷恋过程。
其实,戏剧有剧本,足球也有自己的不确定的剧本,且自成体系。足球的剧本融含了更为恒定的规律性内容,它是对自然体系的一种仪式化认同。正因如此,现代性的身体文化一直在向戏剧靠拢。在现代媒介语汇中,足球的戏剧性影子随处可见。2013年的亚冠比赛期间,中国的媒体在评价韩国首尔FC队时就使用了戏剧术语。“9月25日,首尔FC主场2-0力克德黑兰独立,这代表对手半条命已经交代了。客场最终逼平对手跻身亚冠决赛。反观落后2球的德黑兰独立队,回到主场后为追上分差比赛中显得比较急躁,而首尔战术选择的余地充裕。因此首尔FC在决赛中需要上演同样的剧本。”[17]韩国首尔FC队教练崔龙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我们首尔球员拥有演员气质,表现欲极强。”[17]这篇文章直接将球赛当成了演戏。球员不是演员,却胜似演员,现代球员与传统戏剧演员的间接性融合即体现在这里。
3 艺术价值、诗意呈现、绝对精神:足球的核心意志
谢克纳试图释读欧美戏剧节内部融合不足的问题,“这个弊端是有历史渊源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戏剧,当时的盛大节庆主要就是演员和编剧之间的竞赛。对希腊人来说,重要的是竞赛,而不是团队。如果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演员分到一组,那只是巧合,因为演员和编剧之间的搭配是抽签决定的。”[18]足球也一样,其以一种大范围、大纵深、大体量的方式融入世界文化重构的进程,且一直承担着一种对足球接受国国民实施启蒙和精神改造的附属性职责。
相比较而言,偏爱艺术足球的人占多数,这可能与人类喜欢斗智而不善斗力的生活习惯乃至进化趋向有关,这种心理倾向也符合人类的进化方向。正因如此,球迷关注技巧性强的球队就十分合理。这里需要说说技巧性的典型代表——欧洲拉丁派的情况。欧洲拉丁派一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冠军杯赛中占据优势。“冠军杯赛的最初几年都是由拉丁国家的球队控制局势。先是皇家马德里队和葡萄牙的班菲加队,随后是意大利的AC米兰(1963年)和国际米兰(1964年、1965年)夺得冠军杯。1966年再次由皇家马德里队夺冠。”[19]欧洲拉丁派球队不仅在欧洲顶级赛事中有良好表现,也是世界顶级球队中的佼佼者,而出自这些球队的球星也跨出了欧洲,成为全球性的偶像。
很多中国人也极为看好艺术足球的独特价值。张晓舟曾说:“桑塔纳和克鲁伊夫奠定了我的趣味和价值观:不管好胜争强欲火多盛,总得有超越输赢的情怀,甚至丑陋的胜利,不如漂亮的失败。桑塔纳和克鲁伊夫都没拿过世界冠军,假如这算失败,那也是最漂亮的失败。假如做不了beautiful winner,那也要做beautiful loser。”[3]5-6谭运长也高度认可了克鲁伊夫的艺术足球。“克鲁伊夫是不容易被球迷忘记的。是他,以一往无前的姿态,把足球艺术的本质阐释为向前、再向前,进攻、再进攻;阐释为感性和激情;阐释为速度和技术。他的全攻全守的足球理念,把绿茵场上的表演,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迄今为止也不再重现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妙艺术。”[20]足球的确以胜败论英雄,但绝非仅此而已。“1974年慕尼黑世界杯,克鲁伊夫率领荷兰队与贝肯鲍尔的联邦德国队争夺冠军,那是场永载史册的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最经典的决赛。比赛的结果,克鲁伊夫输给了贝肯鲍尔。然而,奇怪的是,人们记住的、在往后的岁月里经常津津乐道的,却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是克鲁伊夫和全攻全守,而不是贝肯鲍尔的奖杯。”[20]另一位足球观众苗炜曾回忆:“是巴西、阿根廷、荷兰、德国这样的球队,培养起我们对足球的热情,让我们认识到足球有其风格和美学。”[21]女作家迟子建在看了欧洲杯之后频生感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足球的唯美主义者。一场不好看的球又有什么值得欢呼的?哪怕它是冠亚军的争夺战。”[22]在看与被看的意义上而言,足球的场域广大,镜像观众更是数以亿计,足球观众不仅可以轻易占据观剧空间中更多的席位,还有一种内生性能量,吸引更多民众走入足球的领域。
人们尽管偏爱艺术足球,但在绝对性的胜负律面前,没有人会忽略足球的唯胜本性。毛时安便是一位艺术足球的信徒,当他看到艺术足球的没落之时,不禁发出了无限感慨:“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届世界杯越来越像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短平快演绎,金钱熏染了足球,防守代替了进攻,实用战胜了浪漫,现实取消了艺术。拉丁派艺术大师法国队普拉蒂尼的中场铁三角赏心悦目的脚法,如弦乐小品一般美妙绝伦的短传配合,最后仍然被摒出决赛。”[23]85诗的本质在哀鸣,而哀鸣则可以呼朋引伴,构建新群体。因此,足球的诗意也在于建设一种与大众的呼应机制,人们也最终可以看到足球成为艺术的典型性跃进过程。足球可以强化人的归附力,艺术足球的欣赏者一直都在惦记南美艺术足球的高度。“开创现代足球全攻全守新思维的克鲁伊夫最终也没有把队友带上冠军王座。令全世界球迷如痴如醉的巴西南美桑巴却让跌跌撞撞的阿根廷队,让马拉多纳全场唯一一脚妙传踢出决赛,再次饮恨。”[23]86-87然而,炫技性的足球最终无法压倒功利主义的足球,竞技者对声誉的渴望再度击退了单纯的炫技冲动,人们于是看到了竞技过程中不可退让的内涵。
阿根廷在1978年夺取冠军,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留给大多数中国人最深印象的并非意大利夺得冠军,反倒是巴西队在全世界观众面前展示出来的醇正的桑巴足球风范,而1986年的世界杯几乎就等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中国人的足球启蒙始终无法摆脱南美因素。卡米罗·欧拉亚等人曾描述:“2007年4月18号,效力于巴塞罗那的莱昂内尔·梅西在国王杯对阵哥塔菲的半决赛中重演了马拉多纳的那记‘世纪之球’。他在几乎与当年马拉多纳相同的位置,奔跑了几乎相同的距离,过了相同数量的防守队员,用同样的动作绕过了守门员,用与21年前马拉多纳相同的盘球动作,在同一个位置将球以一种‘梅西’式的生活方式打进。很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但是它足够震惊全世界。梅西甚至上演似曾相识的另一幕。”[2]260-261复制之美构建出人类最具仪式化的生活理想。梅西不仅复制了马拉多纳“千里走单骑”式的进球,还复制了其“上帝之手”式的进球。“几个月后,在同一个赛季,梅西在对阵西班牙人队的加泰罗尼亚德比中,上演了类似于‘上帝之手’的表演。在巴塞罗那以0∶1落后的情况下,梅西跃起将球绕过西班牙人门将卡洛斯·卡梅尼并将球打进,同样是用的右手,进球有效。……我们可以解释说梅西就是马拉多纳的模仿者或者就是马拉多纳的继承人。”[2]261报刊文章在描述梅西的成长之路时也使用了戏剧术语,“好像梅西出道就一直在按照马拉多纳的剧本走一样,在王储成王之前,舞台和龙套也早早为他准备好了。”[24]复制还有延续性,正因为曾经制造过“千里走单骑”以及“上帝之手”的进球,梅西也被认为是足以成全阿根廷足球至高辉煌的人物。然而,梅西未能获得世界杯,更无法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上演马拉多纳式的进球。尽管如此,人们仍旧怀念那些为丰富人的精神而努力过的人。“但是这些理由似乎还是太简单了,一种更好的解释应该是个性战胜了秩序。迟早人性会获得胜利。”[2]261足球之美来自人性之美,足球的扩张来自人性的胜利。而人性的胜利反过来也可以深刻揭示出足球的纯度,它使得足球更有可能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存在。
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之前,各路媒体对比赛结局的预测充满了戏剧元素。“阿根廷与德国的决赛,会重演哪个历史版本?赛前球衣分配,对阿根廷人来说就显现出不祥之兆,1986年他们身着蓝白球衣击败德国夺冠,1990年他们身披蓝黑第二队服输给德国,而今年,以客场队服出战的阿根廷,重演了1990年的悲情。”[25]比赛的结果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德国队凭借加时赛时格策打进的一球击败了阿根廷队,类似结果让各路媒体联想到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决赛的老剧本。足球的戏剧性在此得以高扬。在大媒介时代光辉的照耀下,类似世界杯决赛这样的大阵仗足以催生出一种相对独立的戏剧类型,人们由此可见足球的核心意志。足球大赛的戏剧性内核由此而得以固化。
4 结语
从人类仪式表演与游戏展演的角度看,戏剧和足球并无二致,两者都以看与被看为核心元素,都有独特的场域空间,都有大量观众涉足其间,且代表着一种观看的力量。人们可以视之为一种神圣性仪式空间,也可以将其当成一种世俗的交际场合。然而,那里的确寄托着人类独立的意志、情感、语言、行动的融合点。从诠释人性的超越性品格方面看,足球当仁不让,一直担当着一种沟通人性原点的职责。从根本上说,足球看似平淡无奇,其实从不缺乏矫正人类行为的功能,借以防止人们脱离人性基本规程。足球一直蕴含着一种拯救的能量,它试图按照原始的进化图示复原人类的伊甸园,也将恒久地成为人性深层的一种纪念品,足球不断地更新其品格,却从未在人类肢体解放的图式内闪现出丝毫差错。足球本身就是一种超强的身体仪式,并在有效地干预人类的进化历程,防止人类为了一种无序化的动机而错失进化的正确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