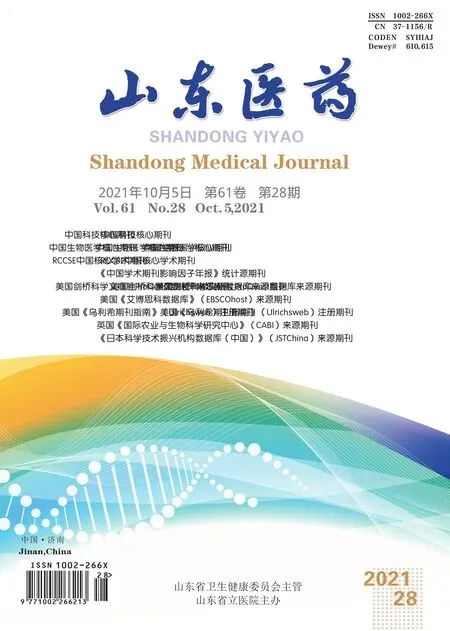CAR-T细胞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研究进展
黄鑫悦,晁旭,黄峰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咸阳 712000;2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科研科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同时也是全球第六大最常见的癌症[1]。原发性肝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治疗(肝切除术或肝移植术)、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以及局部消融疗法等。大多数原发性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难以进行手术治疗[1]。原发性肝癌已经严重危害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临床亟需改进治疗方法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和提高其生活质量。近年来,肿瘤免疫疗法因其卓越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嵌合抗原受体T 细胞(CAR-T 细胞)疗法首次应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2],同时,其在实体肿瘤治疗的应用中也展现出积极的效果,显示出CAR-T 细胞治疗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前景。随着基础研究的深入、治疗理念的更新,已有研究将CAR-T细胞治疗应用于肝转移瘤[3]。现就CAR-T结构与发展、肝细胞癌相关肿瘤抗原及CAR-T细胞治疗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策略等进行综述,为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1 CAR-T概述
CAR-T 细胞是提取的自体或同种异体T 细胞,经基因修饰后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表面无限制的抗原特异性受体,回输后能够识别和攻击带抗原的肿瘤细胞。嵌合抗原受体(CAR)的结构分为三部分:胞外抗原结合区的单链片段变量(scFv)、跨膜结构区和胞内信号区。跨膜结构区连接胞外抗原结合区和胞内区,在传递T 细胞活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由CD4、CD8或CD28等构成;胞内信号区可发挥信号传导功能,由合TCR/CD3 的ζ 链、免疫球蛋白Fc受体(FcεRI)的γ链构成[4]。
目前,CAR 的发展可分为四代。第一代是一种与T 细胞激活信号区的胞外单链抗体和CD3ζ 链相连的融合蛋白,但细胞缺乏长期存活和旺盛的增殖能力。 因此,可以通过将共刺激内域分子引入CD3CD3ζ,如4-1BB 和(或)CD28,使CAR-T 细胞在体内的持久性和抗肿瘤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由于第一代CAR的临床活性有限,第二代和第三代CAR添加了一到两个共刺激分子,如CD27、CD28、CD134(OX40)和CD137(4-1BB),以产生持久的T 细胞扩张和持续的抗肿瘤作用。第四代CAR 对其结构的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编码载体,以诱导相应细胞因子的表达,并增强免疫系统的其他效应物,以便在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中释放细胞因子,招募和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增强CAR-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4]。
CAR-T细胞治疗的技术关键点是相关肿瘤抗原的选择,靶点优先选择正常组织中表达不显著的肿瘤特异性抗原。研究表明,以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为靶点的CAR-T 细胞疗法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肝癌治疗方法[6]。最近一项研究构建了一种CAR(HYP7)T 细胞模型,该模型能够通过诱导穿孔素和颗粒酶介导的肿瘤细胞凋亡或减少肿瘤细胞中的Wnt 信号来消除GPC3 阳性的HCC 细胞,强调了针对GPC3 的CAR-T 细胞治疗在肝癌患者治疗中的潜力[7]。因此,选择原发性肝癌的相关靶点至关重要,原发性肝癌相关新靶点的发现可能会更好地促进CAR-T 细胞治疗发挥抗肿瘤效应,但在应用于临床治疗之前,仍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来验证。
2 肝细胞癌相关肿瘤抗原
运用免疫疗法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方法已经过多年的测试,运用基于抗体或细胞因子的方法,大多数虽已被证实其安全性,并且可以成功诱导肿瘤产生特异性免疫反应,但并不能体现出确切的临床效果[8]。目前与原发性肝癌相关的肿瘤抗原包括GPC3、纽约食管鳞状上皮癌抗原-1(NY-ESO-1)、MUC-1、上皮细胞粘附分子(EpCAM)、甲胎蛋白(AFP)、c-MET等。
2.1 GPC3 GPC3 具有前所未有的癌症特异性,目前正作为全球癌症免疫治疗的靶点被研究。GPC3在HCC、卵巢透明细胞癌、黑色素瘤、肺鳞状细胞癌、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Wilms肿瘤)、卵黄囊肿瘤中特异性表达。GPC3 通过结合Wnt、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生长因子来调节细胞增殖信号,在胚胎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可促进肿瘤生长[7]。GAO 等[6]研究表明,GPC3靶向的CAR-T细胞在体外可有效杀伤GPC3阳性肝癌细胞,而对GPC3 阴性肝癌细胞无杀伤作用。JIANG等[9]采用原代HCC细胞建立异种移植模型,将CAR-T 细胞过继移植到患者源性HCC 异种移植(PDX)模型中,结果表明,GPC3-CAR-T 细胞能够有效消除HCC PDX模型中的肿瘤。因此,PDX模型有可能用于评估GPC3-CAR-T细胞治疗个体肝癌的疗效,GPC3-CAR-T细胞治疗是HCC治疗有希望的候选者。
2.2 NY-ESO-1 NY-ESO-1 在恶性肿瘤中的高表达和高频率表达,以及其诱导有效整合的能力,使其成为具有动态潜力的免疫治疗靶点。研究表明,NY-ESO-1的表达与肝癌手术后较差的预后相关,这一发现的机制可能是NY-ESO-1 促进了肿瘤细胞的迁移[10];NY-ESO-1是HCC 的预后标志物,NY-ESO-1的表达越高,HCC复发的可能性越大[11]。
2.3 MUC-1 MUC-1是一种与肿瘤相关的标志物,表达于乳腺癌、卵巢癌、肺癌、前列腺癌、肝癌和胰腺癌中。该肿瘤相关跨膜分子的主要细胞外结构域由20个氨基酸的串联重复单元(PDTRPAPGSTAP⁃PAHGVTSA)组成,其核心蛋白也被异常糖基化,使得与肿瘤相关的粘蛋白在抗原上不同于正常粘蛋白。FENG等[12]评估了MUC-1对HCC细胞放射抗性的可能影响及其潜在机制,MUC-1 介导的针对辐射诱导的细胞凋亡的保护,与JAK2/STAT3 信号通路的激活以及抗细胞凋亡蛋白Mcl-1 和Bcl-xL 的诱导有关。MA 等[13]构建了两种特异性靶向MUC-1 的Jurkat CAR-T 细胞(1 代和3 代),其均可特异性杀伤MUC-1过表达的肝癌细胞。
2.4 EpCAM EpCAM 是一种跨膜糖蛋白。EpCAM+HCC 细胞显示出肝干细胞样特征,包括自我更新和分化,这决定了HCC 的生长和侵袭性。EpCAM 在HCC 中的表达与HCC 的不良预后有关,提示EpCAM 可作为危险分层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表达EpCAM 的PDC 可能是HCC 的细胞起源,PDC衍生的HCC 显示伴随CLC 成分的组织学特征,并伴随Wnt信号的激活,炎症条件下肝脏中EpCAM-PDC的异常增殖可能与肝癌的发病有关[14]。
2.5 AFP AFP 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生理功能,包括转运功能、免疫抑制、诱导细胞凋亡等。AFP在肝癌中高度表达,使其成为CAR-T 细胞治疗的理想靶点。LIU 等[15]发现,在已建立的腹腔肝癌异种移植模型中,AFP-CAR-T 细胞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活性,并且可以选择性脱粒,释放细胞因子,并裂解肝癌细胞。SHAO 等[16]对晚期肝癌患者进行AFP 应答评估,探讨AFP 水平的下降是否与晚期肝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治疗结果有关,发现早期AFP 应答者的客观有效率(73%)显著高于早期无应答者(14%),可见早期AFP 应答与ICIS 对晚期肝癌的较高疗效相关。
2.6 c-MET c-MET 是一种由MET 原癌基因编码的酪氨酸激酶受体,主要在上皮和内皮细胞、神经元、肝细胞和造血细胞中表达。目前,一些用于治疗肝癌的c-MET 抑制剂正在研究中,如施坦替尼、INC280 和卡波赞替尼等[17]。 有研究结合CAR-T细胞治疗和免疫检查点设计针对c-MET 和PD-L1的CAR-T 细胞表明,双重靶向CAR-T 细胞对c-MET+PD-L1+HCC细胞具有明显的细胞毒性[18]。
2.7 CD133 CD133 是一种五聚糖跨膜糖蛋白,在肝癌、脑瘤、肺癌和胰腺癌中高度表达。研究表明,CD133 水平升高的肝癌患者总体存活率较低,复发率较高。WANG 等[19]建立了CD133 特异性的CART-133 修饰T 细胞(CAR-T-133),发现CAR-T-133 细胞具有明显的裂解能力,对CD133+细胞产生更高的细胞因子,并能显著抑制体内肿瘤的生长;与其他组相比,肿瘤组织中CAR 基因的复制水平更高。CHEN 等[20]通过Meta 分析指出,CD133 在肝癌患者中呈现显著表达,并且与患者的总生存率和无肿瘤生存率呈负相关。
3 影响CAR-T细胞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因素和解决策略
3.1 CAR-T 细胞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影响因素 免疫细胞输注的毒副作用和肝脏的免疫抑制微环境是CAR-T 在原发性肝癌治疗中应用的潜在重要障碍。CAR-T细胞需要被运输并渗透到肿瘤部位才能发挥其杀细胞作用。静脉注射是将CAR-T 细胞重新注入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体内的有效途径。通过静脉输注的CAR-T 细胞与血管中的血液一起输入,但很少渗透到肝肿瘤部位,甚至可能严重损害其他正常器官。由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发展而来的肝癌是高度纤维化的,物理上很难穿透。这些特征使得CAR-T细胞向肿瘤部位的浸润变得复杂。CAR-T细胞治疗毒性效应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和CAR-T 细胞相关性脑病综合征[21]。在杀伤肿瘤的过程中,CAR-T 细胞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如TNF-α、IFN-α和IL-1等,从而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的“细胞因子风暴”[22]。研究表明,黄曲霉毒素B1(AFB1)产生和Caspase-3介导的细胞死亡(碎片)通过促炎性二十聚糖和细胞因子风暴触发肝肿瘤休眠逃逸,AFB1产生的碎片上调巨噬细胞环氧合酶-2(COX-2)、可溶性环氧化物水解酶(SEH)、内质网应激反应基因的表达,这可能是随后二十烷类激素和细胞因子风暴的促成因素[23]。
3.2 CAR-T 细胞治疗的解决策略 Runx3 是一种促进T 细胞在非淋巴部位滞留的关键转录因子,最近被发现是CAR-T 细胞治疗的一个潜在的重要辅助因子[24]。这些研究为免疫细胞向实体瘤组织的优先浸润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他一些策略也可以用来促进CAR-T 细胞向肿瘤组织的浸润。TACE 是肝癌非手术治疗的首选方法[25],考虑到静脉注射对肝癌治疗的不良影响,临床上可能会以介入性的方式输注CAR-T 细胞。该方法可以提高杀伤细胞向肿瘤组织的浸润效率,大大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21]。免疫检查点分子,如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结构域和粘蛋白结构域蛋白-3,目前被认为是肝癌微环境中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些分子中的一个或多个的抗体可以恢复肝癌中TIL 的功能[26]。而免疫检查点分子降低了CAR-T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CAR-T 和ICIS 的联合应用可能成为肝癌治疗的有效策略。CRISPR/Cas9 系统破坏CAR-T 细胞中PD-1 的表达可能会增强体内和体外的抗肿瘤功能[21]。随着同种异体细胞产品的使用,人们要同时考虑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和宿主抗移植物反应,这可能会限制移植细胞的植入和增殖[27]。研究表明,COX-2/SEH 双重抑制途径能有效抑制二十烷类化合物和细胞因子风暴,从而阻止AFB1 碎片诱导的肝癌进展[23]。制约CAR-T细胞治疗实体瘤成功的障碍之一是难以识别理想的肿瘤相关抗原。研究证实,GPC3 在72% 的肝癌患者中高表达,AFP 在肿瘤和血清中的高表达比例高达75%[28]。提高识别特异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制备同时针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抗原的CAR-T 细胞[29]。BURGA 等[3]研究表明门静脉输注CAR-T 细胞的抗肿瘤效果高于尾静脉全身输注。因此,局部注射CAR-T 细胞不仅可以提高CAR-T 细胞向肿瘤组织浸润的效率,而且降低了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故局部注射CAR-T 细胞可在未来成为治疗原发性肝癌和转移癌的一种有潜力的策略。近年来研究表明,趋化因子与其受体的结合在介导白细胞迁移和归巢、癌症进展和癌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0]。故可以通过改造CAR-T 细胞以表达合适的趋化因子受体。
4 结语和展望
近年来,随着分子技术的不断进步,一系列方法被应用于原发性肝癌的免疫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CAR-T细胞在临床上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应用越来越多,CAR-T技术的优势也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在临床研究上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由于CAR-T 良好的抗肿瘤作用、肿瘤的异质性以及现有治疗方法的昂贵,研究个性化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是CAR-T细胞治疗的方向。细胞剂量、输液方式和合适的治疗方案是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另外,建立以免疫学家为主导、辅以临床医生的多中心肿瘤免疫治疗团队,将极大推动CAR-T 技术的创新,并极有可能提高未来原发性肝癌免疫治疗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