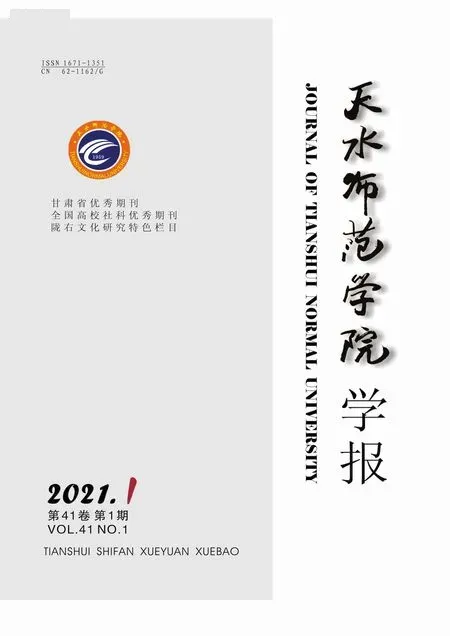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中的胡瓶
郭茂全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人员的交流、物质的交流与信息的交流。学界对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的研究日益增多,如毛民《榴花西来——丝绸之路上的植物》、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许晖《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记》、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等。研究者不仅关注丝路沿线的文化遗产,还关注商品流通、物品交换等。“漂流”于丝绸之路上的“胡瓶”讲述着独特的“丝路故事”,无论其作为实用器物、交流礼物,还是作为审美对象、艺术图像,都蕴涵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丰富信息。
一、胡瓶作为“器物”的存在
“瓶”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器物之一,在古代主要用于盛酒、汲水等,有时还可盛放药物、香料、舍利子等。瓶的材质有陶、玉、瓷、铜、金、银、玻璃等。瓶的材质器型、使用范围、社会地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胡”概念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变化。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来自许多地区的人和货物都被唐朝人称作“胡”,而在古代中国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邻人,后来用于称呼西方人,主要用来指称波斯人、天竺人、大食人、罗马人等。[1]5“胡人”“胡姬”“胡商”“胡马”“胡服”“胡笳”“胡琴”等就成为中原人对北方民族与外来物品的称呼。
“胡瓶”是一种宴饮容器,在希腊、波斯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使用,是古代中国对外来瓶器的称呼。“胡瓶”原有的器型特点是侈口,槽状流,细颈,溜肩,鼓腹,喇叭形圆高足,口沿与肩安柄。胡瓶按照材质可分为陶胡瓶、金胡瓶、玻璃胡瓶等,因玻璃器皿易碎,保存至今的玻璃瓶器相对较少。胡瓶不仅在宫廷宴饮时使用,还在漫长的丝路行旅中使用。唐人眼里的“胡瓶”一般指来自西方的瓶器,其中既有玻璃瓶器,又有金银瓶器。唐代宫廷把“胡瓶”作为贵重器物的原因不仅在于其为金银制品,还在于其为域外所献的珍稀方物。“胡瓶”的命名话语既包含着命名中的主体立场与文化定位,又包含着对异域文化的界分区隔与期待想象。本文论及的胡瓶包括域外制作而传入中原的胡瓶,也包括中原工匠仿制的金胡瓶、玻璃胡瓶、陶瓷胡瓶等。
二、胡瓶“进”中国的空间路径
“胡瓶”进入中国的路径主要是草原丝绸之路、绿洲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从源头上讲,“胡瓶”最早出现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后随着罗马帝国的东征及与东方人的贸易向东传播,进入埃及与中亚地区,并播撒到草原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胡瓶和其他异域器物一起进入中原。
古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其主要路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阴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的北部,最终到达欧洲。内蒙古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鹰形金冠、四虎噬牛纹金饰牌等都是草原丝绸之路器物交流的标志。草原地区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与波斯银壶都表征着草原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敦煌变文中的“王昭君变文”描述了单于在安葬昭君时“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的宏大情景。[2]104尽管无法从器形上确认昭君葬礼上的胡瓶与波斯胡瓶之间的联系,但也为草原丝路上的胡瓶交流提供了文字佐证。据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唐玄宗赐安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四”,安禄山则献各类金银器物,其中有“金窑细胡瓶二”。[3]9作为“胡人”后裔的安禄山,他所拥有胡瓶应来自草原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达到发展顶峰。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元代上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商贸城市。内蒙古、河北等地出土的胡瓶成为古代中国和波斯通过草原丝路交流的历史见证。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辽代墓葬中出土的胡瓶是西亚波斯萨珊制作的金银器,通辽市奈曼旗出土的辽代陈国公主墓乳钉纹玻璃胡瓶是由草原丝绸之路传入的玻璃器物。辽上京、元上都、赤峰、营州、阿拉木图、萨莱、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就构成“胡瓶”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漂流路线”。
古绿洲沙漠丝绸之路一般指从洛阳、长安出发,经秦州、金城、凉州、甘州、吐鲁番、喀什噶尔、撒马尔罕等地的丝绸之路。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壁画中,其墓门西门框绘有飞天,飞天分别手执排箫、海螺、角杯、胡瓶和长杯等乐器和物品;其石堂北壁浮雕画面N2中男女主人在家中宴饮场面,在男女主人前面跪坐一位侍者,左手持杯上举,身前放置一长柄胡瓶。[4]西安北周安伽墓葬的石门祭祀图像的供案上就有胡瓶。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秦州刺史河间王元琛豪华奢侈,家中藏有从西域来的金瓶银瓮。“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5]179甘肃天水出土屏风石棺床被认定是北周后期至隋的粟特人的贵族墓葬品,随葬物品中有一鸡首瓶;在“亭下夫妇对饮图”中的一位侍女身着长裙,右手提一胡瓶;在“酿酒祭神图”的城台之下有两个兽头,兽头口中的酒流入下方两个大瓮。大瓮间一人持胡瓶取酒,前方一人抱胡瓶运酒,一人坐着,一人跪状右手扶瓶,左手持碗喝酒。[6]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胡瓶为绿洲丝路交流的金银器物。新疆和田市布扎克村出土的单耳带流陶壶,造型为细长颈、侈口,槽状流,腹呈椭圆形,喇叭形高足,口沿至肩安柄,是晚唐时期的陶瓷“胡瓶”。洛阳、长安、秦州、凉州、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连缀成胡瓶“漂流”于绿洲丝绸之路的空间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泛指中国与外国的海上贸易交通。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指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经南海通往印度、斯里兰卡,最后到达罗马的海上交通路线。胡瓶在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港口及沿线被发现。广西北海合浦县汉代墓葬中发现东汉时期的波斯绿釉瓷瓶,瓶小口圆沿,细长颈,椭圆形鼓腹,矮圆足,颈至腹上部有手柄,肩部饰一周宽带纹,其造型与波斯陶瓶特点相符。合浦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还有印度、希腊风格的黄金饰品。福建福州出土的五代闽国皇帝王延钧的妻子刘华墓中的三尊蓝釉陶瓶是在汉代从波斯传入中国的代表性器物。[7]“合浦胡瓶”是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重要的器物见证。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M2061出土的三件玻璃碗为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的罗马玻璃中心的产品,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罗马玻璃器。广州遂溪出土的粟特铭文银碗和波斯萨珊银币的发现,就是粟特人经过印度洋,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南方沿海港口的实物证据。[8]11中亚粟特人从绿洲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多条路径“进入”中土,沿海出土的粟特玻璃胡瓶、玻璃碗及银碗等都验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器物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从南海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唐人仿制白釉绿彩高足长柄壶上可以发现,本土制作的瓷质胡瓶已开始经泉州、广州等港口“外销”至西亚、中东及北非地区。
唐代“胡瓶”的流入有草原丝绸之路的输入,还有绿洲丝绸之路以及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输入。据《旧唐书》记载,吐蕃赞普求和于唐王朝时派大臣名悉猎上表唐玄宗时曰:“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吐蕃使者也获得唐朝赏赐。“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拟甚厚。”[9]5231唐代金银器与吐蕃王朝的金银器之间有过交流。[10]唐代的金银制作借鉴、吸收了吐蕃的工艺技术。“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的金制品。”[1]616青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的吐蕃贵族墓葬壁画“射牛图”中的四人中,一人执胡瓶,一人捧银盘,一人袖手旁观,一人垂手而立。综而观之,胡瓶“进入”中国有绿洲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等多种路径。
三、胡瓶“进”中国的时间脉络
胡瓶伴随丝绸之路沿线人民的交流而传播。历史文献中有关胡瓶的记载往往与东西文化交流及国家之间的外交行为关联,胡瓶最早是以“外交礼物”或“贸易产品”的文化身份出现的。胡瓶在汉代开始传入中土。公元1~2世纪,罗马商人在丝绸之路频繁活动,把大批罗马玻璃器带至东汉洛阳。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罗马搅胎吹制的长颈玻璃瓶。林梅村认为,洛阳出土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显然与罗马商人在洛阳的商业活动密切相关。[11]129-130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墓中的乳钉纹琉璃瓶同样表征着胡瓶的文化交流特性。中亚粟特商人在“胡瓶”交流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陕西西安清禅寺出土的隋代贴饼玻璃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贴饼玻璃碗、新疆库车县森木塞姆隋代石窟出土的贴饼玻璃杯等器皿都是通过粟特商人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
胡瓶是丝路国家交流的重要外交礼物。《太平御览》引《西域记》曰:“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12]3365疏勒国为西域古国之一,位于今天的新疆喀什噶尔。古代的喀什噶尔是古印度、希腊、波斯、汉唐文明的交汇地,也是丝绸之路中国段南、北、中诸道在西端的聚结点。魏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220年至226年,其在位时曾收到作为贡品的胡瓶,显示了魏晋与西域间的器物交流。公元4世纪初,西晋时期人们开始用“胡瓶”来称呼来自西方的带柄瓶器。《太平御览》引《前凉录》云:“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12]3365据历史文献记载,张轨统治凉州的时间为公元301年至314年,而此时的西方正是罗马帝国时期。“西胡”概指中亚的粟特人,而“拂菻”为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波斯帝国的使团数次到达平城和洛阳,与北魏、东魏、西魏、北周等政权不断联络。北周大将军李贤历仕北魏、西魏、北周三朝,身居高位。宁夏固原是丝路上著名的咽喉要道,固原出土的李贤墓鎏金银胡瓶、萨珊波斯玻璃碗等当为商贸队伍送给李贤的域外珍宝。《太平御览》引《唐书》中记载:“贞观十七年,佛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颇黎、绿颇黎、石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12]3530汉学家薛爱华认为,“包括石国、史国、米国在内的许多突厥斯坦国家也都偶尔向唐朝贡献金属器皿”。[1]618胡瓶有时是蕃国或臣子敬献皇帝的宝物,有时也是皇帝赏赐大臣的器物。《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记载,隋文帝因大臣杨素有功而奖励其子杨玄奖。“拜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钱,缣三千段,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顷,宅一区。”[13]1285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奖励忠臣李大亮时云:“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9]2387-2388《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中记载,唐太宗赏赐骠骑大将军卢国公时,“赏绢六千匹,骏马二匹,并金装鞍辔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14]151胡瓶本为粟特人贮酒之物,传入唐宫廷之后,除了作为酒器外,常常作为皇帝赏玩的“自用之物”,有时在论功行赏时作为赏赐大臣的礼物。
随着中国瓷器生产的兴盛,来自域外的金银胡瓶日益减少,宋代的胡瓶以琉璃胡瓶居多。《宋史》记载大食人进献贡品有锦布、象牙、琉璃瓶、瓮香、蔷薇水等方物,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等地理著作都记述了大食贡琉璃、玻璨等物品之事。胡瓶因佛教传播具有了宗教器物的功用。在宋代佛塔中发现的琉璃胡瓶多用于盛放佛陀舍利,被深埋于佛塔地宫中。辽代契丹人崇信佛教,辽上京遗址北塔天宫遗址出土了波斯淡黄琉璃瓶,瓶口为鸟首状,颈部缠有蓝色琉璃丝为装饰,瓶柄为蓝色琉璃,执柄上端立鸟尾状扁柱。瓶口配有黄金瓶盖,瓶子的内部还有一个蓝色小琉璃带把杯。该琉璃瓶由吹制法吹制而成,瓶中藏杯,造型奇特。瓶壁极轻薄,非常珍贵,作为供养器在辽重熙年间供入佛塔。胡瓶具有器物商品、外交礼物、宗教文化的多重交流属性,并以国家外交、经贸往来、民族迁徙、宗教传播等目的“进入”中国。
四、胡瓶艺术“在”中国的多元样态
丝绸之路上的器物在置放时空与承载符号的变化中成为“物的艺术表达”的最好例证。现存的“胡瓶艺术”中,有的作为独立的器物存在,有的以审美形象的方式存在于壁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宁夏固原博物馆藏的李贤夫妇合葬墓里的鎏金银胡瓶,银瓶鸭嘴细颈,圈足单把,腹部圆鼓,颈部所带的凹槽被认为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器物风格,颈腹相接处有突起圆珠,组成一圈圆珠纹饰。器腹上有六位男女的浮雕,三组图像表现帕里斯裁判、诱拐海伦及海伦回到墨涅拉俄斯身边的故事。瓶把上部有一人头像,与瓶身上的人物不同,是中亚巴克特里亚人形象。壶把下部有两个兽头与瓶身相接。[15]陕西临潼博物馆藏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铜胡瓶,长颈,圆柄,瓶腹饰有六个头像,头发中分并结成发辫,肩颈部一周芭蕉叶纹饰,上有三周鎏金弦纹与口沿隔开。有的胡瓶保留了原有器型,但瓶腹的装饰大为简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饮酒图绢画中有肩部有管状流的胡瓶图形。陕西乾县出土的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上,一宫女捧一凤首长颈胡瓶,颈部装饰有竖条窄带,腹部装饰有斜条纹宽带,圆形细把接于颈部与腹部。内蒙古博物院藏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壶腹光滑无纹,扁圆腹,高圈足外侈,壶柄部和口缘相接处饰一人头像。唐代的新城公主墓壁画“群侍图”、李震墓壁画“托盘执壶女侍图”、唐燕德妃墓壁画“提壶男装女侍图”中都有胡瓶的形象。
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墓中的乳钉纹玻璃瓶是玻璃材质胡瓶的代表。该瓶器表面无色透明,双唇侈口,漏斗形细高颈,宽扁把手,球形腹,喇叭形高圈足,腹壁饰五排小乳钉饰,花式镂空把手由十层玻璃条堆砌而成。浙江省瑞安县慧光塔出土的宋代蓝色磨花高颈琉璃舍利瓶,宽平折沿,细长颈,球形腹,厚平底,颈部刻两道凹弦纹,腹部磨刻流畅的折枝纹,器底深蓝色与器身浅蓝色形成对比。该胡瓶材质细腻,造型简洁,色泽莹润。五代定窑白釉人首胡瓶为荷叶形口,束肩,梨形腹,腹部的三十二条棱线极具韵律感,圈足,有曲柄与口、腹上部相接,柄上端有一人头。陕西法门寺博物馆藏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盘口细首淡黄琉璃瓶,瓶腹上部有九个黑色圆饼间隔排列,瓶腹下部有六个黑色扇形饼排列,间隔中有透明玻璃圆饼插配,无柄,琉璃瓶晶莹剔透。现藏于陕西博物馆的西安长乐路隋舍利墓出土的淡绿琉璃瓶,瓶口若鸟首,执柄光滑,从瓶身上部连至瓶口,瓶身无纹饰。山西省太原市石庄头村出土的唐代白釉人首胡瓶为荷叶形口,束肩,梨形腹,口下腹身饰一枝,枝尖有一叶,有扁平曲柄与口、腹相连,胎体淡青灰色。从装饰与纹饰来看,胡瓶瓶身的装饰图案有人物图像、动物图像、抽象线条、光滑无图等类型,壁画与浮雕上的胡瓶一般无装饰图案,单件胡瓶经过捶揲、镶嵌、粘贴、刻镂等工艺后留有装饰图案。
隋唐墓葬艺术中的胡瓶形象较多。入华“胡人”墓葬中的胡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胡瓶与入华胡人生活的紧密关联。山西太原出土的隋代虞弘墓、甘肃天水石马坪墓葬、陕西西安安伽墓葬、河南安阳粟特贵族墓葬中都有胡瓶被发现。山西太原出土的隋代虞弘墓中,有一侍从俑戴尖圆毡帽,穿窄袖长袍,腰系一带,两侧系小刀、囊袋,怀抱一鸭嘴形单耳瓶;石椁雕绘之五中地上与椁座浮雕各有一大胡瓶。[16]“鸭嘴形单耳瓶”即胡瓶,现藏于日本Miho的围屏石榻是北朝入华粟特人石葬具中的一件,在其第一屏底部,舞者的下方有一个盛放葡萄酒的胡瓶,两个侍者正从大罐子里取东西。“从胡瓶的把手上,这罐子器型不是来自萨珊波斯,而是典型中亚粟特的。此处胡瓶把手出现在瓶颈,而波斯胡瓶的把手通常出现在瓶肩上。”[17]134“胡瓶”不仅出现在入华“胡人”的墓葬中,还出现在唐代贵族的墓葬壁画中。唐代墓葬壁画中的胡瓶图像有十三处,陶俑雕塑中有胡瓶者三十多处。[18]洛阳出土的唐代安国相王唐氏墓葬中有一幅“胡人牵驼”壁画,其骆驼背上有一枚短颈、厚唇、圆鼓腹、平底的“胡瓶”。西安南郊唐墓出土的唐三彩骆驼上的器物中也有“胡瓶”形象。在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两个侍女画像与胡瓶有关:一侍女一手托盘,一手持胡瓶;另一侍女一手握胡瓶,一手中用大拇指与食指轻捻一酒杯。胡瓶是唐代贵族日常宴饮中使用的重要酒器。“胡化”之风不仅盛行于唐人的日常生活,还融入其墓葬艺术。作为艺术“局部”的胡瓶形象与其他图像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五、胡瓶艺术“在”中国的造型嬗变
胡瓶艺术造型既有完全来自域外的,又有受域外胡瓶影响中国工匠仿造或创造的。胡瓶的不同造型及其影响构成胡瓶的文化生命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青釉凤首龙柄壶有凤头瓶盖,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六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圈内有胡人舞蹈图案,下有六朵宝相花。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壶柄为龙凤纹饰,龙爪抓于瓶肩,龙尾一直连结瓶足。北周银鎏金西番莲纹龙柄胡瓶也是典型的波斯风格的金银器。该瓶口部略似鸟头形,流口作鸟喙状,带盖,细颈,溜肩,喇叭形高足,口沿到腹部一侧安双龙首柄,柄的上端和口缘相接处饰有圆钮,盖与柄有锁扣相连,颈肩部与胫部饰两道粗弦纹,壶腹上下分别饰一圈莲瓣纹,壶身锤有鎏金缠枝西番莲纹。该瓶器在吸收外来胡瓶造型的基础上也融入了东方的审美元素。
胡瓶从最初的金银制作到中国化经历了“陶瓷化”的过程,并在装饰图案方面增加了凤首、龙柄等中国陶瓷常用的艺术符号。“中国工匠对胡瓶的样式、饰纹进行了改造,创造出新的瓶子。由于符合唐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因而最终发展成用陶瓷材料来仿制胡瓶。中国本土大量生产的陶瓷胡瓶满足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需求,走进了大唐寻常百姓家庭。”[19]许多工匠模仿金胡瓶制作陶瓷胡瓶,并按中原人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融入了龙凤元素,把手柄做成龙形,把流槽口做成了凤首,如唐代邢窑绿彩凤首执壶、唐三彩凤首壶等,当然瓶口形状的艺术嬗变中也有对波斯鸡首壶造型特点的吸收。唐代三彩凤首壶的胎呈白色,直口,细颈,凤首,凤眼圆睁,啄张开,噙一珠,头部额下的毛羽,壶腹椭圆,高圈足。凤冠长伸至腹为柄。腹部两面的中央雕刻着凸起四瓣形的团花,圆形器座上还雕塑垂莲瓣纹。器身交错施绘赭红、黄、青三种釉色。三彩凤头壶的造型受波斯萨珊王朝器形的影响,而三彩釉工艺和凤鸟形象为唐文化的特征。五代定窑龙柄鸡首壶敞口,颈部上粗下细。丰肩,肩下渐收,壶体呈瓜棱形,圈足,接鸡头形流,有方形龙柄,柄上端的龙口衔于壶口,下端连于壶身。壶身内外施白釉,釉色纯正温润,白里泛青。此瓶受到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影响,造型优美精巧。“胡瓶”经历了从实用物品到艺术物品的变化,而唐代制瓷工艺对胡瓶的普及则具有推动作用。
胡瓶的艺术造型在其演化中经历了完全“中国化”的过程。“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不单源自艺术形式或审美观念的需求,还伴随着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伦理融通的需求。”[20]山西博物院藏唐代白瓷人首柄执壶就是胡瓶的仿制品,束颈、卵腹、高圈足,壶柄上有人头像。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双螭柄双腹传瓶,此瓶为隋代瓷器,白胎白釉,也是胡瓶中国化的产物。明代《新增格古要论》提到元代新兴酒器时说:“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折盂、茶盅、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21]158胡瓶作为酒器的功能在宋元时期已基本丧失。宋代的“胡瓶”已与漆艺制品相关,宋朝著名文学家陈庚的诗《谢友人惠犀皮胡瓶》中以“灵犀鳞甲鸱夷腹”“雕镌尚喜兼文质”等描述“犀皮胡瓶”,诗中“犀皮胡瓶”已完全不同于唐代的金胡瓶或瓷胡瓶。明清以来,“瓶器”走向审美化,重视其艺术观赏性,而非实用性,并以“玉壶春”“梅瓶”等雅名受到文人的喜爱。因此,胡瓶的器物功能与文化意义也就随之丧失,在新的文化交流中被其他的域外器物所取代。
“丝绸之路艺术不是丝绸之路各类艺术分类研究的简单相加和组合,也不是沿线国家艺术成就的静态研究和归纳,而是在丝绸之路上发生的人类艺术创造、交流、融汇、相互影响的现象及结果。”[22]胡瓶艺术是丝路沿线人们创造与交流的艺术成果,从其在丝绸之路上“漂流”可以发现丝路艺术相互影响的痕迹。从“瓶”自身在丝绸之路上的“漂流史”来说,从希腊到西亚经历了“本土化”与“希腊化”的融合时期,在中亚又经历了“粟特化”时期,入华后又经历了“陶瓷化”时期。胡瓶在明清时代影响逐渐减弱。胡瓶像其他诸多“舶来品”一样,其“胡”的文化身份在历史的变化发展中逐渐被忘却,而变成“华”的文化血肉,乃至于有时很难辨识其来龙去脉。
六、丝绸之路上中外胡瓶艺术的双向受容
“胡瓶”的流播史、演变史是人类文明交往史的一个缩影。在罗马帝国以前,生活在亚平宁半岛的伊特鲁里亚人就生产与“胡瓶”类似的带柄玻璃壶。早在古希腊时期,希腊人制造的陶瓶上常装饰人面或兽面,瓶绘故事是希腊式胡瓶的主要特点。公元前3世纪中期,古希腊殖民者在中亚草原地区建立的希腊化的奴隶制国家“大夏—希腊王国”。在波斯希腊化时期,尤其在波斯萨珊王朝时,胡瓶制作融合了希腊风格与波斯风格。唐代金银器吸收东罗马、波斯萨珊、粟特等西亚和中亚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林梅村认为,陕西临潼博物馆藏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中的人像受到印度教战神塞健陀造像的影响。[23]可以说,胡瓶是希腊、波斯、印度、中亚国家及中国等文明频繁交流与双向受容的结果。
人们使用的器物不仅呈现着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生活与精神风貌,还体现出本土文化对域外生活方式的接受情况。外来器物通过丝绸之路,由大大小小的商贸队伍带到中原,影响了唐代的器物制作与贵族的生活方式。隋唐时代的长安、洛阳及周边城邑是外国器物的汇聚地,隋唐时代也是胡瓶使用的高峰期。雕塑、壁画、诗词、文赋等艺术作品中的胡瓶形象较多。王昌龄诗《从军行》中“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顾况诗《李供奉弹箜篌歌》中“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卢纶诗《送张郎中还蜀歌》中“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等皆表现与胡瓶相关的边塞战斗场面与日常宴饮生活。无论作为馈赠礼物,还是作为贮酒之器,胡瓶在唐代宫廷的使用较为频繁,体现出一种积极接受、吸纳的文化心态。唐人对胡瓶的喜爱与对“胡风”的推崇有关,尤其与当时社会上盛行饮葡萄酒的风气相关。高启安认为,胡瓶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明显例证,至迟在唐初就流行胡瓶注酒的宴饮方式,以胡瓶注饮葡萄酒是当时奢侈的饮食时尚。[24]美味的葡萄酒要用酒器来盛装,而肚大颈细的胡瓶就成了唐朝人眼中最佳的容器选择。唐人宴饮记忆强化了他们对胡瓶的文化记忆,由宫廷而至民间的“胡风”崇尚成为胡瓶生产的社会动能。
“胡瓶”艺术的历史溯源与流播演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写照。魏晋南北朝开始直到唐、五代时期是中原和周边民族乃至西域地区广泛交流的时期,大量具有异域风格的器物频频出现,并在纹饰和器形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的陶瓷工艺。“胡化”的审美体现出古代中国人以“胡”为“美”的审美新风尚,也显现隋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胡瓶的“物的艺术表征”的接受与传播经历了双向受容的过程。从希腊、波斯到汉、唐、元、明,从罗马人、粟特人到吐蕃人、汉人,从陶瓶、金银瓶到瓷瓶,胡瓶的器物叙事与造型呈现是“想象的他者”的方式,也是“同化的自我”的方式。人们在器物的交流中获得了对异域之物的认识,异域之物也在新的时空获得全新的文化意义。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根基,而审美文化的互通互融则是人文化成、情感化融的元场域、元空间。胡瓶文化是丝绸之路物质审美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胡瓶艺术则是丝绸之路艺术样态的重要形式之一。胡瓶艺术汇聚着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王朝战争、商品贸易、宗教传播等文化交流,也透射出人类审美文化互渗、互证、互生、共成的美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