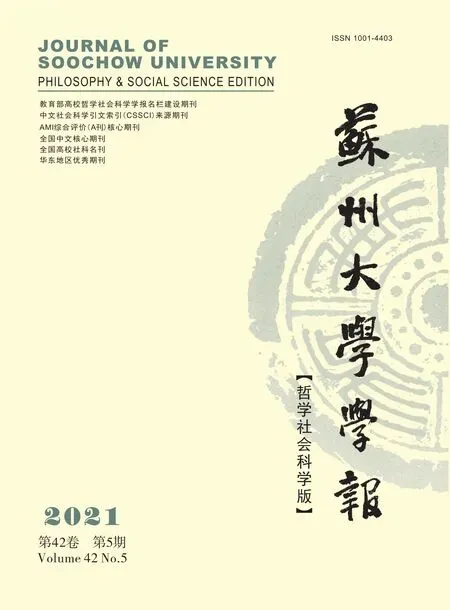女性平权与法律革新
卢 然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法律革新与女性权益
辛亥之后,共和取代王朝,政权合法性之来源从君主转移到民众,至少在名义上,法治取代了帝制,成为民国在制度层面的基本出发点。[1][2]由是,近代中国具备了双重使命:既需完成从帝制到法治的转变,实现法律的近代化,又要以民族国家制度取代旧式王朝,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立基前提是身份平等之公民的创生,因此,如何解决旧制度中所遗留的身份等级制度,成了新法律所亟待回应的历史问题。
就法律层面而言,彼时的立法者与司法者面临着复杂的情境,一方面,共和停留在框架层面,受制于传统,现代立法与司法的局面尚未打开;另一方面,国体变更之后,既需否认身份等级制度之合法性,又需对现实中大量遗留的身份等级制度进行司法因应。
面对愿景与实境之间的巨大矛盾,在立法层面,既需制定现代法律框架以促进社会革新,又应基于国情厘定新法,使其不致流于空泛无物。[3]如何对身份等级制度进行清理,进而构建起权利平等的公民制度,成为立法的历史使命。但在旧制度残余大量留存的现实面前,如何在不招致激烈动荡的情况下渐进地实现上述目标[4],成为立法者的主要考量。[5]73从民族国家建构角度来看,编纂新法无疑为执政者提供了以新社会规范重新规训国民的契机[6],经由这一过程,新生国家合法性得以确立,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之建构得以完善。[7]而从立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法典型态,可以辨析投射于其中的统治精英之理念与认知,并可体察社会习惯与新纂法典相互作用的具体历程。[8]
在司法层面,面对在立法上势必将要废除的身份等级制度,如何在实际运作中同时实现倡导平权制度与保护身份等级制度中弱势群体的目标,是极大的挑战。相较立法,司法实践也完全可以为国家的整体蓝图提供相应的行为指引(1)参见John Henry Merryman,Comparative Law and Social Change:On the Origins,Style,Decline & Revival of the Law and Development Movement,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25,No.3(Summer,1977),pp.457-491.,且兼具效率与变通之优势,在特定情境中,司法实践所起到的社会规范效应甚或优于立法。
本文之所以选择女性平权作为主题,盖因女性平权运动被视为建立现代国家之必由路径[9],在政治道德层面将女性权利问题视为典型国家责任以及社会平等权利的痼疾,而需要予以严肃的面对。[10]而保护伸张女性权利,也是塑造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方式。[11]新民族国家的塑造与性别意识的崛起密不可分,新性别秩序的构建能够极大地促进女性对于国家的认同[12],而性别意识的发展完全可以反映出新国家的现代化程度。[9]在中国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中,女性一直处于父权与夫权的结构性压迫之中,解决女性平权问题,是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2)参见Yu-xin Ma,Woman Suffragists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1911—1915,Women’s History Review,16:2,2007,183-201.Sarah E.Stevens,Figuring Modernity:The New Woman and the Modern Girl in Republican China,NWSA Journal,Vol.15,No.3,(2003),pp.82-103.
近代以来,妾制即为针对女性之歧视性制度中的显性残余。存续超过二千年之妾制(3)纳妾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至周代,参见程郁:《清至民国的蓄妾习俗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质意义上与现代一夫一妻制相违背,更在家庭关系中构建出显著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妾制既是中华法系迥异于其他法系的显要标记[13],也成为近代法律改革中无法回避的旧律遗留问题。社会思潮之演变,已将缠足、纳妾等传统社会习以为常的习俗推上道德审判台[14][15],也给彼时的立法与司法带来相应的诉求。(4)参见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吕燮华:《妾在法律上地位》,政民出版社1934年版;麦惠庭:《中国家庭改造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王世杰:《中国妾制与法律》,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4期总第91卷。问题在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传统的痼疾如何能为新法所调适?(5)参见Ziba Mir-Hosseini,Muslim Women’s Quest for Equality:Between Islamic Law and Feminism,Critical Inquiry,(Summer 2006),pp.629-645.另一项研究证明,即便在新建的民族主义政权下,妇女的地位仍然是由传统决定的。参见L.Amede Obiora,New Skin,Old Wine:Engaging Nationalism,Traditionalism,and Gender Relations,Indiana Law Review,Vol.28,(1995),pp.575-599.
现有针对民国女性权利的研究,对于女性的法律地位有一定的关注(6)参见Lisa Tran,Sex and Equality in Republican China,the Debate over the Adultery Law,Modern China,Vol.35,No 2,March 2009,191-223;Louise Edwards,Gender,Politics,and Democracy:Women’s Suffrage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2007.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11期,第1-14页。,在立法与司法层面,对于妾制的法律地位,亦有部分文献予以关注。(7)参见Kathryn Bernhardt,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960—1949,Stanford,2009,书中关注了妾的权利在民国初期的变迁,所利用材料大抵为司法档案。张仁善:《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继承案件裁判中情理法的交汇》,载《法制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3期,第1-20页;徐静莉:《“契约”抑或“身份”——民初“妾”之权利变化的语境考察——以大理院婚姻、继承判解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第34-41页;谭志云:《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妾的权利及其保护——以江苏高等法院民事案例为中心》,载《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3期,第43-48页。相应文献多以各政权下的司法实践为划分进行区间考察,但对于相关立法实践与各政权之间的相应法律理念之殊同联系缺乏细致考察。本文尝试以北洋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直至新中国的立法运动与司法实践为线索,从整体上贯穿考察妾制这一古老群体,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命运浮沉。
二、荣誉法则——北洋时期的司法策略
妾在法律上的地位变迁,可谓是道德观念从传统过渡到近现代的典型例证。在传统中国法律体系中,纳妾是作为“谋子孙之繁殖,而保男子之血统”[16]83的工具,在男性有后嗣的情况下,纳妾行为是要受到谴责乃至法律惩治的。(8)《明律》规定:“其民四十以上无子者,听娶妾,违者笞四十。”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编,1934年版,第84页。恰恰在民国期间,限制纳妾的旧道德体系已然瓦解,如观察者所言,纳妾“明着是为子嗣期续,其实是放纵肉欲罢了。现在的政界,简直拿纳妾当美事了,只要坐上汽车,要是没有几个姨奶奶,就算是缺点,就算是不识时务”[17]。新崛起的权贵,在旧礼教的束缚不复存在之后,将原先以延续后裔为目的之纳妾,变成泄欲乃至炫耀的工具。旧道德既已瓦解,新法尚未确立,能够解决纳妾问题的,也只有在社会层面倡导“男女平等”之新道德。
在礼法社会解体之际,新道德的来源之一,是新国家的构建模式,民族国家之新创须以立宪为基础,于是“立宪国应用一夫一妻制度……法律既不需有妾”[18]成了本土立法者所考量的问题,而在华西人将纳妾指为“举世滔滔恬不知耻”,更是以西洋文明为参照,将妾制引申为“家道不正,国风不良,抑非正当之婚制也”[19]。由是,礼法制消解之后,妾制以延续子嗣为目的的旧道德支撑在伦理意义上已不复存在,而在现实层面学习西方,避免西人指摘,进而证明新民族国家建立的荣誉观感成了构建新道德的重要理据。在简单化、功利化地对于西洋式道德观念的消化之下,为维系国家荣誉、推动中国改革、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9)参见[美]奎迈·安东尼·阿皮亚:《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苗华健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妾制成为被鞭挞的对象。问题在于,在道德与荣誉观已然转变的情况下,法律如何进行回应?
北洋时期,民事法律的主要渊源为从《大清现行刑律》中所选取出来的《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10)参见段晓彦:《〈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42-161页;陈颐:《“〈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寻踪:无法可守的守法主义?》,载郑显文主编:《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近代转型和未来展望》,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183页。,面对立法的滞后,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大理院的补救,是以大理院判决例及《民律草案》作为司法实务的指引文件[20]904③(11)法官可以不拘泥于《民律草案》而直接援引法律原则解释。,并赋予司法官以新理念来诠释旧法条的权力,将新思潮在审判中予以适当考量。[21][22]575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纳妾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关键性的问题。法官通过将妾与妻的法律地位明显差异化的方式,在形式意义上确认了一夫一妻制,但也将本应废除的妾制予以合法化。(12)民国八年上字106号,郭卫辑:《大理院判例全集》,会文堂书局1932年版,第211页。既然承认了身份关系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妾制合法性,那么在现代国家公民平权的使命面前,司法实践有可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提高妾的法律地位吗?
对于妾来说,因其大多出身贫寒,在身份关系中受人宰制的可能性极大,倾斜性的保护并扩张妾的权利,成为司法实践中最有可能的突破点。在大理院关于妾的身份关系认定的判决中,面对将同居女子定义为“姘识”并拒绝承认同居女子为“妾”,从而要求终止同居关系而不再承担任何义务的当事人主张,大理院驳斥了湖北高等审判厅关于“姘识行为”为同居本质的论断,更否认了对于同居女子“后以妾名,不过掩饰从前姘夫敲诈之政策”的道德化动机推断。判决中采用扩大解释方法,将出身烟尘的同居女子定义为妾,使得主张终结身份关系的同居女子可以获得生活费用。(13)参见大理院九年上字11号,载黄源盛纂辑:《景印大理院民事判例百选》,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80-794页。
大理院采用扩大解释的方法定义妾制,以使女性获得更多权益。在司法判例中,大理院采用倾斜性保护的方式,不仅让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权利(14)民国四年上字2052号,郭卫辑:《大理院判例全集》,会文堂书局1932年版,第755页。,也获得了旧律中所没有的主动协商终止身份关系的权利[23],更让妾可以在遭受家庭暴力、被夫指责通奸等特定情况下可以单方面终止纳妾关系。(15)民国八年上字177号,民国四年统字358号,郭卫辑:《大理院判例全集》,会文堂书局1932年版,第524、755页。
在子女地位与继承权利上,妾的地位亦得到显著提升。针对大众所认为的在纳妾之前“苟合生子”,从而不应将所生子纳入“庶子”的继承范围的问题,大理院在判决上再次采用了去道德化的处理方法,认定即使“母未为夫妾以前,与父所生之子,自可于母取得夫妾之身份时,亦取得庶子之地位”(16)参见大理院八年上字1401号,载黄源盛纂辑:《景印大理院民事判例百选》,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38-843页。。而在选择家庭继承人的亲属会议中,妾也获得了先前所没有的出席并表达意见的权利。(17)民国八年上字315号,民国三年上字385号,民国七年上字386号,郭卫辑:《大理院判例全集》,会文堂书局1932年版。
不独大理院,对于妾采倾斜性保护原则也成为地方审判厅所普遍遵循的原则。在1926年江苏高等审判厅定谳的一桩案件中,尽管缺乏立法依据,判决中申明“依据情理”,规定被抛弃之妾应当获得相当数额之补偿以维系生计,更不需为纳妾时从青楼赎身以及购买衣物所费资金承担任何责任。(18)参见江苏省高等审判厅民事判决,十五年控字第145号,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由是观之,在多年实践之后,倾斜性地保护妾的权益已经成为司法界的普遍共识。
当北洋时期立法进展不足之时,法官的判决实质成为道德评判(19)参见[意]皮埃罗·卡拉曼德雷:《法官与历史学家》,唐波涛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4期,第148页。,在道德观念转变的驱使之下,以解释例和判决例为手段,撬动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凝滞,对现实中的妾的平权诉求作出了法律层面的回应。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处理方式仍然存在缺陷。首先,司法机关的判决只能进行个案救治,无法实现立法手段所能达到的普遍性治理与价值宣示;其次,如果以公民平权为衡量尺度,北洋时期承认妾制合法但予以倾斜保护妾的手法,尽管现实效应上能够显著地提升妾的权益,但在法律层面反而确认了妾制的合法性,巩固了本应被新法律彻底废除的身份等级制度。
缺乏立法能力,仅仅依靠司法机构相对灵活的个案化处理,是北洋时期无法解决妾制这一典型平权问题的原因。那么,在社会动员能力与执政能力上都更为强大的南京国民政府,解决妾制问题的方案与效果则值得进一步的关注。
三、隐匿保护——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选择
相比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伊始,即已伴随着妇女解放的诉求。在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中,女性团体提出“平等”观念,主张“纳妾者以重婚罪论”,“禁止蓄婢纳妾”已然成为动员女性加入国民革命的口号。[24]305-306执政之前的诺言,也让南京国民政府在执政宣言中,明确阐明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25]285,因此,政权鼎革后的新法须回应革命中的承诺。[26]
在国民党党纲中,即作明确申明:“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27]国民政府法制局在其宣言中,即宣布“纳妾之制,不独违反社会正义,抑实危害家庭和平;衡以现代思潮及本党党义,应予废除,盖无疑义。故本案不设容认妾制之明文,以免一般社会妄疑此制可以久存或暂存”[28]345。并宣称,为废除妾制,“势不能不设置诸种关于纳妾之刑事制裁及行政处分故也。至于既存之妾及其子女,于废妾之单行法令未颁行以前,究居如何地位,则拟由法院斟酌社会情形,为之解释,以补律文暂时之阙”[28]345。
由是,革命中对女性许下的期许,以及民族国家中平等权利的基本要义,共同构建出了国民政府在妾制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而立法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更在政权鼎革之后被赋予建构新秩序、彰显政权合法性与优越性的要务。
执掌立法工作的法制局关于废妾的宣言看似铿锵有力,却没有作出立即以立法明文废除妾制的表述;相反,以“不设容认妾制之明文”回避了直接规制妾制的可能,将任务交由“废妾之单行法令”。这样表述,似乎在传达一种思路,即废妾是应当的,但并非由一般意义上的立法来完成。
官方在妾问题上的法律立场,给民法典的立法者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妾的普遍存在,使立法者需以法律手段去保护妾;另一方面,立法者认为如果在新法中仍旧将“妾”的字眼放入条文中,将显现中国社会的落后性,“难登大雅之堂,将为世界各国所窃笑”[5]75。在立法者眼中,“妾”是暴露中国落后性的符号,新法显然不宜提及“妾”的字眼,也就无法以明令禁止的方式废除妾制。
负责编定民法典的民法起草委员会所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将妾本人之地位与妾所生子女之地位分开处理。[5]75在妾的子女地位方面,自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实践就确定了所有子女的平等权利地位。(20)民国四年上字262号,郭卫辑:《大理院判例全集》,会文堂书局1932年版,第291页。在新法修订中,以“庶子”一词(21)在法典中使用“庶子”,意味着立法者对妾制的默认。,即可覆盖妾所生子女的概念范畴而不需提及“妾”的字眼。
在将“妾”如何纳入民法典保护范围的问题上,立法者选择以中国传统中的“家属”概念来涵盖“妾”[5]76,因“家属”概念在不提及妾的名称前提下,可以让立法者通过重新阐释概念的方式,将妾纳入新法典的保护范围中。但现实中的阻碍在于,传统法中“家属”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妾并不绝对符合这一条件。因此,立法者在法条中对于“家属”重新定义,将其解释为“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22)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123条第3款。。最终,妾以“家属”的面目,在新民法典中蛰伏了下来。
新民法典的编纂不仅是社会舆论关心的对象,立法委员也对于妾的法律地位表达了关切。部分立法委员认为,妾制应当通过新法的宣示而明确予以废除,《民法典》第1123条关于“家属”的扩大化解释,在字面上不仅没有明确废除妾制,反而为妾制提供了合法生存的空间,由是引起了立法委员的疑惑。在立法院大会讨论之时,女性立法委员陶玄即针对第1123条款背后的真实动机提出质疑。(23)在1928年立法院的49位立法委员中,仅有3位女性,除了参与民法起草委员会的郑毓秀博士,宋美龄与教育家陶玄为另外两人。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76页。起草委员傅秉常以“中国家庭中往往赡养远房寡居之伯母、婶母等,此为我国之良好传统,允宜保存”为理由搪塞过去。[5]76最终,在民法起草委员会没有陈述第1123条款的真实立法意图的情况下,立法院大会通过了对于新民法典草案的审核,新民法典也于1931年开始正式颁行。
立法中对于妾制的处理手法,即可以视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典化过程中,以法律技术来回应妇女平权、废除妾制的政治诉求。尽管在新法典中并未以明文方式直接废除妾制,但通过民法典中一夫一妻制的陈述,间接宣告妾制的非法性,并消除了纳妾的合法空间,又避免与现存妾制的直接冲突。而基于法典统一性与编纂技术的考虑,未在民法典中提及妾制,实际上避免了将古老的妾制纳入新法典所可能带来的概念冲突,又用“家属”概念的延展解决了对于现存妾的保护问题。如胡长清所言,法律上不容承认妾制的存在,也无须以特别规定的方式予以废除[29]388,南京国民政府以巧妙的立法技术,化解了妾制的立法难题。
与北洋政府不同,国民政府通过立法对妾制进行了根本性、体系性的调整。相比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具备了更完整的法律意识形态,也拥有更强的执行能力将法律理念变现为法典。尽管有针对国民党干涉司法独立并以意识形态干预立法进程的批评[30],但相较北洋政府,在技术层面,南京国民政府显现出立法能力与法律理念的显著进步。更重要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眼中,纳妾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以革命者面目出现并夺取政权的国民党眼中,促进女性平等不仅仅是上台前的允诺,也是塑造其统治合法性的必要途径,因此法律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回应政治诉求的手段之一。在立法中对既存妾制的暂时性包容,是为了保护妾的现实利益而非延续妾制。
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废妾方案也有诸多弊端。首先,完全技术化的处理手段将法律与民众认知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远。放弃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宣告妾制非法,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更多的负担。立法本是最有效的宣示方式,立法的间接化处理让法律的内在机理难以向大众直接传播,在民法典颁布多年后,在社会媒体上仍可见到亟需废除妾制的呼声。[27]
其次,在妾制立法的过程中,本该是妇女倡导自身权利,借此机会实现平权目标的大好时机。但立法者的暗度陈仓,实际上规避了本该引起朝野热议的女性平权话题,仅有的女性立法议员质询,还被起草者搪塞而过。如此立法,实际上拒绝了女性参与,完全由男性厘定了妾制的法律地位。女性的平等权利诉求再一次被工具化,在所谓为免除“为世界各国所窃笑”的国家利益面前,独立人格、男女平等的现代立法原则被无情侵吞,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仍然只是进行了折衷与妥协。[31]147
四、政治赋权——民族国家语境中的女权
尽管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在原则上确认了现代一夫一妻制,但并未明文否定妾制。在处理现存妾制的法律权益问题上,司法手段的多元与灵活,势必成为立法框架确立之后的解决路径。
在纳妾合法性问题上,自民法典颁布,纳妾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即被定义为非法之存在。依司法解释,在民法典颁布后订立的纳妾契约均无效,而纳妾行为则应被认定为通奸。(24)司法院民国二十一年院字,第770号。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因为纳妾而被指控通奸的实际案例。由此,妾制的合法性第一次通过司法解释例被明文否认。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新法典与司法解释例不能对于过往已然存在的妾产生效力,由是,调整现存妾的法律地位成为彼时司法实践之焦点。
在最高法院所颁布的一则判决例中,妻子对于纳妾行为的同意成了判断妾制合法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判决例规定,民法典颁布之后,任何现存的妾制在经过妻的同意或认可之后,仍被视为合法有效。一经认可,妻不得再以纳妾作为理由,提出丈夫重婚或通奸而要求离婚。(25)二十六年上字794号;上字636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由此,妻被赋予了确认妾制合法性的权利,而在实践中,妻与妾的长期共同生活可以被认定为对于纳妾行为的认可。(26)二十六年上字794号;上字636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很明显,此等规定的意图不仅是维护家庭之基本安宁,也是赋予了妻否认妾制的权利。但如此规定,也可能造成在妾的法律地位未提高的情况下,妻的地位被增强,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妾在家庭生态中的地位恶化。
仅以赋权予妻的方式,并不足以达成逐步消灭妾制的效果。提高妾的法律地位,赋予妾主动脱离身份关系的权利,才是关键所在。北洋时期,妾可通过协商解除身份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也采用类似的途径。在判决例中,明确规定了夫若要解除与妾的身份关系,则必须获得妾本人的同意或具备正当理由(27)二十一年,上字1097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但妾有权利单方面终止身份关系。(28)二十一年,上字1098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由判决例不难看出,司法官的考量,是通过倾向性的赋予权利,鼓励妾选择有利时机来摆脱身份关系。更重要的是,判决例部分重塑了亲属法上关于妾的定义。判决例否认了妾与夫的其他亲属之间的亲属关系(29)二十一年,上字2238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在家庭内部,只有妾的亲生子女才被确认与妾具有亲属关系。(30)二十一年,上字269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在此意义上,妾与家庭其他成员的法律关系更加疏离,也在实际上鼓励妾脱离身份关系。
司法解释亦明确规定,根据纳妾关系不可被视为准婚姻关系的原则,妾的性自由与婚姻自由应予以保护,妾若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甚至与他人缔结婚姻关系不应被视为通奸或重婚。(31)二十三年,院字1136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司法裁判的实际意图,是将妾与家长的关系疏离化,进而为妾脱离身份关系提供更多的现实可能。在经济权利上,司法判例又对妾的权利作了扩大化解释,规定如若妾在脱离身份关系之后生活困难,可以向原有家庭要求扶养费之给付(32)二十一年,上字2579号;三十三年,上字4412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从而为妾在脱离身份关系之后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
与北洋政府时期对于妾在消极意义上的保护不同,国民政府的司法机构对于妾体现出了更大的同情。如果说北洋政府的司法实践给予了妾更多消极意义上的“福利”,国民政府的司法机构则赋予妾更多权利,鼓励她们摆脱身份关系。司法解释例和判决例所表达出的信息相当明确:妾应当拥有权利来终止身份关系,也应当获得相应的经济扶助来应对独立之后的生计问题。
关于妾制,另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是妾对自己子女的亲权。从清代律例到北洋时期的司法实践,都规定了妻拥有对妾子女的亲权,而妾对于亲生子女并无亲权。(33)大理院三年,上字269号,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上海法学编译所1931年版,第230页。这就意味着,妻依靠身份,可以对于妾的子女的继承权作出干预。而在(34)大理院四年,上字564号;大理院五年,上字843号;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上海法学编译所1931年版,第240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妾对亲生子女的亲权是排他性的(35)司法院,院字585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妻对妾的子女的亲权也为司法实践所否认。(36)司法院,院字1226号,《最高法院裁判要旨汇编》(上),上海律师公会印行1940年版,第152页。
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实践大致展现出了渐进式废除妾制的路线,司法判决例与解释例不仅提升了妾的法律地位,也鼓励妾主动脱离身份关系。更重要的是,面对家长与妾之间的不平等现实,妾通过倾斜性的保护获得了更多权利,从而为其摆脱身份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
北洋政府的司法实践无疑改善了妾的处境,但是这种改善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社会思潮的变化,而非当局自身法律理念的进步,也缺乏体系化的改革方案。相形之下,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妇女平等理念催生了立法意义上的变革,在清晰的法律理念指引之下,法律职业阶层也通过司法实践的方式,为妾的权益提升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抛开在立法与司法层面的成果不论,在新政权用法律回应改进女性平权诉求的境况下,妾的真实处境如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妾的分布似乎体现出了高度的城乡差异。在农村地域,妾的存在并不突出,以1941年赣南地方的抽样调查为例,妾的人数在抽样乡镇中总数十七人,占总人口一万三千六百人中约千分之一点二的比例,其数量远少于占人口约百分之九的童养媳。[32]根据1932年广州市的社会调查统计,在一区共约19 200人口中,妾的数量达1 070人之多[33],这意味着,妾占到了发达工商城市人口的约百分之五。
换言之,妾制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工商城市的弊病,也因此更容易吸引社会中上层舆论的注意,而在上海、青岛等沿海主要城市,妾脱离原家庭自立也很快成了社会新闻的一部分。[34]司法针对妾的倾斜性保护措施,不仅进一步正名化了反对纳妾的道德呼声[35][36],更有司法界专业人士在媒体上详述纳妾之风险代价以劝退纳妾之人。[37][38]但如果说妾制是女性平权在工商城市的主要挑战的话,在农村地区,蓄养童养媳等制度是对女性权益的重要侵害方式,尽管有部分资料显示,在广西的部分地区,妾因可作为廉价劳力而相较蓄婢更加流行[24]246,但在整体意义上,废除妾制以及赋权予妾,解救的对象是闻风气之先的城市女性。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性“废妾”主张面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与司法回应,在技术上颇见功力:一方面以渐进之路径,赋予妾以相当程度之自主及倾斜性保护政策;另一方面,以温和的一夫一妻制立法,实际消除纳妾的合法空间,变相宣告了妾制的终结,又以替代性方案来保护现存之妾。法律以和缓的方式,因应了革命诉求,维系了社会稳定。在政权交替不断的民国,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法律体现出自身在社会转型期间的独有价值。
南京国民政府在妾相关司法实践上的不告不理政策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延续。(37)《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在婚姻法公布后的重婚、纳妾如何处理的意见》,1953年12月22日法制办字第811号。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公告中,也明确规定相关处理办法作为内部掌握不向外发表的。或许因为立法中的直接否定妾制与司法保护妾的需要,让此问题只能在司法过程中走向了与立法原意相悖的方向。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司法实践中对妾的容留与鼓励脱离政策,获得了超越政权的认同度。妾制正式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废除,直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才得以实现。但在司法实践上,南京国民政府所采用的容留并鼓励妾脱离身份关系的方式,却被沿用下来。1950年的《上海市人民法院婚姻问题解答》即申明“人民政府采取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纳妾是犯罪的行为,解放后绝对禁止。以前纳妾系封建社会所遗下的既成事实,如经涉讼,依具体情况必须脱离”[39]。但在实践中,又试图尊重那些愿意留在原家庭生活的妾,1950年的《北京司法界权威对新婚姻法中某些问题的意见》陈述“关于重婚,对新婚姻法公布之前的,可不告不理,但法律对它也不加保护,如女方提出离婚,政府可立即判离,在财产上给予照顾”[40],而在司法实践中,是将妾与重婚合并处理的。[40]由此可见,新中国在司法上对于既存妾的承认现状与鼓励脱离策略,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并无轩轾。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废妾以高度技术化方式,和缓地处理妾制以期达到女性平权的基本目的,但也存在诸多弊端:首先,以大众无法普遍接触的司法解释例与判决例来逐步废妾,实际上是将废妾的宣言限于司法职业群体之内,却丧失了普及法律常识予大众的可能,司法判决例所赋予的让妾脱离家庭的方法少有人援用,其部分原因也可归咎于此[41][42];其次,同样是女性平权问题,在农村滥觞的童养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38)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文废除童养媳制度的法律文件是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废妾的进步并不能证明近代中国在女性平权问题上足够让人满意;再次,缺乏立法的明确废妾宣示,加之司法的被动处理特征,使得迄至民国之终,妾仍旧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普遍存在。
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国家即以个人为其直接构成分子,而亲属团以逐渐减其范围”[43]1式的以“国家-公民”关系取代旧有的宗法制度是基本常识。但在前有旧礼法制度所造就的历史负担,后有新国家建立的荣誉需求之下,女性平权的任务被工具化而忽视其本义所在。妾制法律在遮掩中寻求渐进革新的路径,虽然在法律框架意义上可以摆脱家长权力的支配,但因为社会结构的问题而迟迟未能得以彻底解决。近代法律的革新目睹了父权体系的逐渐溃败,但与西方因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父权低落不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路径中,国家主义的崛起取代了父权,成为支配公民命运的新主宰。[44]41女性的法律权利尽管得到提升,但更多扮演的是默然的工具性角色。
五、余论:勾连法律近现代历程的妾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立法上首次明文规定了妾制的非法化,在司法实践上则沿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策略,并未强制消灭妾制,而以鼓励妾脱离家庭的方法,实现渐进稳妥的革新,从而彻底将绵延数千年的妾制予以终结。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权与新中国都基于统治正当性与政治道德的理由,试图推进妾制相关法律的变革。而女性在各自建政过程中的作用,也部分左右了各个政权策略的不同:北洋时期,因女性在辛亥革命中的声音寥寥,新政权以和平过渡而非革命的方式获得正统,不论是政权本身的动机,还是社会舆论的压力,都没有到势不容缓改革女性法律地位的境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男女平等”口号的提出以及女性在大革命中的角色凸显,从政权合法性层面,兑现革命口号所许下的承诺已是迫在眉睫,女性的权利伸张让以妾制为代表旧家庭成为被革新的对象,但南京政权浮于现代化的政权架构建设,而缺乏深入基层能力的痼疾(39)参见WHITE.Jenny B.State Feminism,Modernization,And the Republican Woman,NWSA Journal,Vol.15,No.3,Gender and Modernism between the Wars,1918—1939(Autumn,2003),pp.145-159.,又制约了妾制在社会层面被立即废除的可能,从而让法律扮演了渐进调适的角色;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女性的话语、权利与参与程度得到了全面的提升[45],“妇女解放”的诉求使得新中国对于妾制的废除与家庭制度的彻底改造有了更加明晰的决断,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女性平权问题在近代的法律命运,亦是近代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缩影。从西潮东渐到狂飙突进的革命思潮,在妾制相关立法与司法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北洋时期,以非体系化的司法判决例与解释例草创框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立法确立一夫一妻制,但又隐匿地保护现存妾的权益,并赋予妾权利以脱离身份关系;新中国时期,以立法明文废妾,在司法上延续了容留妾但鼓励其独立的做法。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超越了政权更迭的藩篱,在司法实践上显示出惊人的延续性,在立法上也逐步将现代价值彰显而出。如此意义上,近代中国的法律实践,不尽是由政权的更迭而区别显著,在司法技术、法律理念上,却存在着隐形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恰恰是各个政权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性所造就。正是在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中,妾制被法律手段送入了历史的旧墟。国家,也以法律改革为契机,实现了对于家庭秩序的重新塑造,法治框架下的民族国家体系,经历数十载的变革,终于大抵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