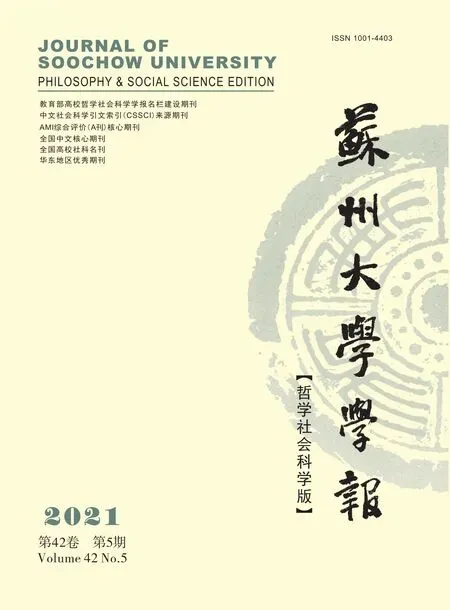新文学的先声:中晚清诗“白话文言”与叙事传统
李 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近代文学的起止,一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起点,而以“五四”新文学为结点,大体与近代史分期重合。也有依循“五四”思想启蒙的逻辑,将起点延伸到龚自珍那里。如果承认“五四”为近代文学的结点,则在思想启蒙这一维度外,还应包含文学史从文言到白话的演进逻辑。文学语言的新变,同时也是思想的新变,是新思想在为其自身寻求恰当的表达方式;而新的形式又将进一步促进思想的更新。“五四”启蒙思想与白话文学唇齿相依、相得益彰,就是最好的说明。
“五四”一代学者,以白话作为文学史的目的和方向,并以此去追溯新文学的传统和渊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便以《诗经》、汉乐府中的民歌为新文学之远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半部,未涉近世文学,然而,作者在该书自序中列了一个提纲,以明代为“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1]3,或者这就是胡适所认为的新文学的近源。以明代为近世之始,且将其与现代相关联,是当时很多学者的共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明嘉靖元年(1522)看成近代文学的开始,依据是“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而明中期是“小说、戏剧的大时代”[2]828,831,该时代的文体形式及语言贯穿至现代。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将公安、竟陵派称为“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并认为“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3]28。
“五四”一代学者以“白话”作为文学发展方向,以平民观作为文学史的道德尺度。明代中后期小说、戏剧的繁盛,文人诗文创作风气的转向,使得他们在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新文学的渊源。不过,明代的“新文学运动”,入清后又有中断和反复。周作人谓之“清代文学的反动”。此外,中国古典文学惯以诗文为正宗和主体,诗文语言和风气的近现代转向,才更具观察意义。与小说、戏曲不同的是,诗歌从文言雅语到白话,有一个“白话文言”的过渡阶段,且这一阶段也是动态发展的。“白话文言”(1)严迪昌《清诗史》提出的概念,参后。成为反传统的语言武器,与新思想的发展相呼应。
诗歌叙事传统的发扬,进一步促进了语言的变革。钱仲联说“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4]5。这一叙事性,在清代后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更贴近现实,语言也更俗白。叙事、语言的背后,蕴含着近代新的人文精神。
思想为里,语言为表,叙事为助,三者相互作用、纠缠,推动中国诗史从古典走向现代。而在清初“文学的反动”中承继明人的余绪且有所发扬扩张,将其从小说、戏剧接引到诗文,并连接到新文学的,当以小仓山房主人袁枚最为突出。袁诗接引民间活力,在语言的文、白之变中,已表现出一定的自觉性。因此,以“五四”为结点的近代文学,不妨从袁枚讲起。
一、从小仓山房到人境庐:诗语新变的自觉与深化
严迪昌《清诗史》将清后期一些五七言诗出现的口语化现象,称为“白话文言”,并认为它们“从特定意义上说也是更接近社会现实生活,更抒情化的表现,同时无疑又是对诗的贵族化的反拨”[5]886。此说予本文以极大启示。
自东汉以来,诗人百千万计,诗歌风格也千汇万状,然所用之语汇,多以历代典籍为渊薮,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一套文言雅语系统。文人作诗,要有典故、出处,要有文化积累与传承,要显示学问,以及由此种学问而培育出的性情……所有这些,通过语言、修辞表现出来,或蕴含于语言、修辞之中,与格律音韵一起,形成古典诗歌的艺术特质。
其间,虽也不乏偶用村言俗语,或戛戛独造者。以唐诗而论,如白居易作新乐府,一度衡以“老妪能解”(《冷斋夜话》卷一),致有“元轻白俗”之谓。然并未对雅言体系构成有效冲击,且在白氏本人而言,亦未贯彻始终。又有韩愈、李贺等推陈出新,然也多是熔铸经典,有本可循,且其自身很快以一种新的雅言,加入文人诗的大传统中。至明代中后期,在心学思潮所导引的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公安、竟陵反复古、尊性灵,重俚歌小说,一时蔚为风气。循此而往,或也能走出一条通往新诗之路。然清廷继立,又打断了这一更新趋势。乾、嘉之际,经史考据之风复盛,余波所及,复古、雅言、学问、道统,等等,复炽于诗文。沈德潜、翁方纲等所倡导的格调、肌理诗学,可以说就是周作人所谓的“清代文学的反动”。在这一背景下,袁子才以其性灵诗说,承继明中后期诗歌的新思潮,逆时风却顺应诗学史的发展趋势,成为古典向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桥梁。
就新思想而言,袁枚直接影响到龚自珍,而龚自珍被公认为是近代思想文化的开端;就新诗风而言,从袁枚到黄遵宪,勾画出清诗反古典的演化路径,乃现代白话诗的本土文学渊源。而袁枚的新思想,与其新的诗风、语言是形影相随的,这一新的诗风与语言,又与诗歌的叙事性相得益彰。
“性灵说”是袁枚的诗学标帜,其文学史与思想史之价值,论之者甚夥,兹不赘述。“性灵说”的核心是真实而独立的情感与性情,于诗文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摆脱古典,以时语、己语写出真我。“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6]216而当时诗坛流弊,就是依附经史之下,“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6]626。以书典为资源,是古典诗歌语言与修辞上的重要特点。所谓“雅言”,就是由书典所熔铸、陶冶的语言,而语典、事典则为普遍的修辞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袁枚反对书典,倡导语言与写作上的新变,针对的不只是当时的诗风,而是文人诗整体上的写作传统。
袁枚之诗,正是其诗学主张的实践。他自题其诗云:“不矜风格守唐宋,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教,被人强派乐天翁。”(《自题》)[7]661师心任性,突破流派家数。袁诗清浅、俗白,其近体诗,有不少用仄韵,破格律者。如《偶作五绝句》“偶寻半开梅,闲倚一竿竹。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闲倚”“儿童”失粘;《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歌声”“意欲”也失粘……袁枚非不擅格律,只是不愿刻意为其所缚而已。袁枚曾自道不喜作词,“余不耐学词,嫌其必依谱而填故也”[6]383。其于格律诗,态度亦类似。朱庭珍《筱园诗话》对袁枚疏于格律,有大段讥讽。[4]5101实际上,袁枚近体诗若以平韵结,出律的并不多。偶有出律,却能有效强化其诗自由、轻松的风格。
格律是一个方面,生动谐谑的俚语俗言,是袁枚反文人诗“雅言”传统又一着力处。朱庭珍批评袁诗“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眼前琐事,口角戏言,拈来即是诗句”[4]5102,反而揭示了袁枚诗的重要特色及其对文学史的贡献。袁诗题材上不避免细俗,器用服馔、齿痛染须等生活琐细,皆能絮絮道来;语言上,方言口语、市井俗话等,也屡见之。
袁枚有不少诗,径以“戏笔”“戏题”名题,表明其不主言志教化,而倡消遣娱乐的诗学态度。消解崇高,走下神坛,方能融入世俗。袁诗展现日常生活的诸般琐细,却又不同于以往隐逸诗人。比如和陶渊明比,哪怕是相类的题材和笔调,袁俗而陶雅,区别非常明显。说到底,陶渊明所代表的隐逸传统,乃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实践,和出仕用世,不过是一体两面。故陶诗总体上仍在言志教化系列,乃至成为文人诗歌传统的一大高标。袁枚则不然,也因此被尊崇传统诗学观的学者所诋毁,视之为“异端”。(2)陈廷焯“小仓山房诗,诗中异端也”,最为精练地概括了士大夫阶层对袁诗的认识。见《白雨斋词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3页。
在写作上,袁枚的俗白、质实,每每有鲜明的针对性,稍作比较就一目了然。比如同是写江村渔家,王士禛的《真州绝句》(其五):“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以景语叙情事,韵味悠长,体现了王诗的“神韵”美学。再看袁枚的《七里泷》:“七里泷深草树疏,青山匼匝水环纡。老翁白发手双桨,同着女儿换卖鱼。”通过场景和叙事,一方面与文人诗的美学传统拉开了距离,一方面融入市井的烟火地气,俗白而亲切。在这里,叙事对袁诗化雅为俗,显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七古《登泰山》,可谓是从精神与技法上反文人诗传统的代表。[7]40该诗多处化用前人名句,如写泰山之位势云“欲知齐鲁形如何,几丛蜗角攒蜂窝”,前句袭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之问,后句化李白《游泰山》“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厉”之“千峰”句,又将杜诗“齐鲁青未了”之大写意变为通俗的工笔细描;再如杜诗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袁则云“不登泰山高,哪知天下小”,以孔子口语入诗。又如写泰山之高及登临之旷云“脚底叶飞高鸟背,眼前海走胸怀间”,前一句既有王勃“山山黄叶飞”(《山中》)之诗意,又融入杜诗“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后一句则化用李白“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直白、通俗,而又形象、生动。经此化用,诗之语言、格调雅俗迥异。
叙事对本诗借鉴前人名句,化雅为俗,化婉曲为直至,也多有助力。如写山势之险云“后人头接前人踵”,便直接用马第伯《封禅仪记》“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的叙事场景;写登山情景:“土人结绳为木篮,令我偃卧同春蚕。两夫负之走若蟹,横行直上声喃喃”,叙事既通俗形象,又幽默生动。无论是名句翻新还是个性化的创造,袁诗采用贴近生活与时代的活语言,探索出一条有别于文人诗传统的新路径。
袁枚搅动时代的风潮,追从者遍及各个阶层。“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贱至倡优,莫不依附门墙,竞言袁氏弟子。”[8]221这里既有赵翼、蒋士铨为羽翼,以“乾隆三大家”的标识屹立诗坛,也有王文治、张问陶、郭麐这样的大家,前后延续着“性灵”的主脉。更重要的,是袁枚对“贩夫走卒”、中下层文士的影响力。罗时进观察到明清文学创作主体的一个重要嬗变,即“文柄下移”“文在布衣”[9],这对文学史从古典走向近现代至关重要。袁枚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对明清文学创作主体的下移,无疑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也正因此,袁枚及其追随者在保守派那里,被视为“异端”,谓之“谬种蔓延不已,流毒天下”[4]5102。只是历史恰恰顺着袁枚的方向,迎合了这“谬种”的蔓延。从乾、嘉到道、咸,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中,发生深刻的质变,传统诗学的社会文化基础,渐次崩塌,龚自珍的出现,使得以袁枚为导向的诗歌路径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实。只是与赵翼、张问陶等不同,龚自珍是以一种二律悖反的方式,确证了袁枚所导引的诗路。
龚自珍虽非性灵诗派,然却和袁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关系上,袁、龚家族均与乾、嘉间由黟县迁杭的“振绮堂”汪氏有联姻。[5]669思想精神以及个性气质上,袁、龚实也表现出浓厚的血脉关联,如尊情、贵真、重自我,对传统文士价值观的反叛,等等。当然,由于时代的变化,龚氏所重的“性情”,有着更多的社会现实、国计民生的内容。严迪昌说:“人们惯以龚自珍为近代文化包括诗文化的开山,然而龚定庵潜在性格中正有着袁随园的隔代熏陶。”[5]668-669这是极有见地的史论。
龚自珍与袁枚等在精神品格与思想趣味上表现出一种正相关,然而,就诗歌创作而言,龚自珍却表现出特有的复杂性。一方面,龚诗以情充之,以气行之,风流倜傥,与性灵诗派非唐非宋、重视独创有一致性。但另一方面,龚自珍又有逞才炫学、恢奇奥僻的一面,与袁枚等俗白、谐趣并不相类。如果说,袁枚等以更接地气的“白话文言”承载其反传统的新思想,依托并融汇着民间与市民的文化力量,龚自珍的新思想,某种程度上还依附旧的形式。这一旧形式,反过来又会消蚀其新思想的光芒。严迪昌说龚诗中“流露的士大夫气和名士颓唐情调不止是内容,而且形之于诗的语言。这说明,文化的超越和自新比起思想政治的锐新要艰难、缓慢得多”。“龚自珍在诗文化上反映出来的矛盾现象,何尝不证明着五七言形态的活力弹性的严重失落,与时代思潮间已缺乏同步适应性。”[5]915-916也就是说,旧的五七言形态,对新思潮的表达,已构成一种阻碍。袁枚诗的“白话文言”,以谐俗的时语剥离文人诗的积习,虽然采用五七言诗体,却在突破其顽固的惰性,而呈现出新的风貌。就诗体革新与语言新变而言,袁枚比龚自珍要走得远,沿袁枚的方向,传统诗歌就可以慢慢走向近现代,而龚自珍的诗路,则具有某种保守性。
龚自珍的思想与诗歌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光绪甲午以后,其诗盛行,家置一编,竞事模拟”[12]卷一三五,尤其对维新派来说,龚诗乃案头必备,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曾受到龚的影响,一直到南社诸人,达到学龚的高潮。不过,近代诗人学龚而特出者,多是有变革的传承,对龚诗恢奇奥僻的一面有所革新。比如杨象济,“才气横溢,有不可一世之概”“疏狂忤俗”的个性思想与身世遭际,与龚自珍极为相似,然杨氏治学及写诗,“私淑桐城铅山,亲炙长水娄江”,门径甚广且不取定庵。杨氏私淑之“铅山”,乃词曲家蒋士铨,诗名不及词、曲,然其近体诗写人伦亲情、山水乡思,情味轻盈隽永,深契“性灵”一派的清新切近。杨象济的诗,以近体最佳,有“流利凄清”[4]11457之评,其审美情调更接近“性灵”一派。陈衍将近代诗人分为樊榭、定庵两派,一则冷僻,一则流易,效龚自珍者如“人境庐(黄遵宪)、樊山(樊增祥)、琴志(易顺鼎)诸君”,便属“丽而不质,谐而不涩,才多意广”[13]42的。陈衍将龚自珍诗统归为流易一派,未免欠妥,龚诗原有涩僻的一面,然肖龚者能变之以流利,此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实际上是调和袁、龚而探索出的诗路。当龚之艰僻妨碍诗人表达新思想、叙写新事物时,袁的平易通俗就可适时纠偏矫正。樊增祥学诗之初,即“嗜袁(枚)赵(翼)”“积诗千数百首,大半小仓、瓯北体”[14],樊诗肖晚唐和龚自珍,得之风流绮丽,然樊诗流畅而不晦涩,其学诗之初所受袁、赵的影响当是一直存在的。
易顺鼎、黄遵宪等也是陈衍所称学龚而“丽而不质,谐而不涩”者。易顺鼎深于情、痴于诗、骋于才,既有袁枚的“痴”,也有龚自珍的“狂”。易氏之诗,格律诗对仗谨严、工巧,堪称近人之冠;但他的歌行体长诗,又不拘一格,每每采用大量散文化的句法,极为自由、恣肆,乃至有人谓之“格调粗猥”[15]358,则有“白话文言”的因素。
肖龚而化袁,开辟古典诗歌新境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当属黄遵宪。时隔六十年,黄也有《己亥杂诗》计八十九首。组诗内容丰富,有写家居生活、民间传说的,还有写时尚风气、域外见闻的,尤其能以山歌格调入诗,如其中的第三十、三十一、三十六、三十七诸首,清新流畅,令人耳目一新。然黄遵宪之所以能开辟新境,扛起“诗界革命”之大旗,亦在其调和袁、龚,将袁枚不主唐宋、真实表达自我的精神进一步落实到文本中。黄氏具有通达的诗学观念与进步的政治思想,他在《致周朗山函》中说:“诗固无古今也,苟能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16]291“无古今”当然“无唐宋”,“我之诗”就是“我”之所见所感的真诗,与袁枚诗论一脉相承。与前辈相比,黄遵宪对诗歌语言革新,有着更自觉的意识。黄遵宪少时读古书,就曾感受到语言的困境:“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杂感》)这种困境实际上就是言、文分离。以文人为主体的诗文写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书面语言体系。古典时代,由于社会发展变化缓慢,这一问题尚不突出。至黄遵宪生活的光绪朝,西方器物与文化一并涌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黄氏所面对的写作对象,殆非古人所可比。黄遵宪又是杰出的外交家,足迹遍及欧、亚、美三大洲,所见所闻远比时人广阔。面对如许之多的“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其于中国古典诗文言、文不合的问题,会有更深切的感受。他为印尼华侨、梅州同乡所编乡邦文集《梅水诗传》作序,有云:“语言者,文字之所从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盖文字语言扞格不入,无怪乎通文字之难也。”[16]287该序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三年(1901),维新派人士逐渐认识到全体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国家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文、言分离不仅只是关乎对现实世界的叙写,还关乎到思想的传播,国民的教化。
因此,黄遵宪提出“新派诗”的概念(3)黄遵宪第一次提出“新派诗”的概念是在1897年湖南新政期间,见其时诗作《酬曾重伯编修》:“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钱仲联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1页。,既因其进步的诗学观念,也是时势使然。现实社会的变化,黄氏自身丰富的阅历、见识,使之成为可能。此外,民间文学对黄遵宪新派诗的写作,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今梅州),“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16]142,自小熟悉且热爱客家民歌。在他的诗集中,采录客家民歌有好几十首。他的《山歌》《新嫁娘诗》等,被“五四”学者奉为白话诗的典范。黄对民歌的吸收、借鉴,随时间的推移不断自觉。1902年,他致信梁启超,探索一种“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弃史籍而采近事”的杂歌谣的创作。[16]432其民歌情结,可谓自始至终。
与龚自珍相比,黄遵宪思想上没有那么重的历史包袱,更易走出传统的阴影,祛除所谓“士大夫气”。与袁枚比,黄遵宪的文学处境更为顺当,他在语言、体式与风格上的突破,得到更多的肯定,乃至被目为新派诗的领袖,引领“诗界革命”的哥伦布。这当然反映了一种历史的趋势。
从袁枚到黄遵宪,其间诗学观念的传承、发展,对诗歌语言、体式新变的突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在文学上的表现。如果说,袁枚的“性灵”诗学观,多少还有传统高人逸士的痕迹,向上可与庄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苏轼、公安三袁等合辙。袁枚的写作,也是个人志趣性分所趋。及至龚自珍、黄遵宪等,则显然已具备很多新因素。尤其是黄的新派诗,在历史的潮涌中,被不断修正、强化,成为一代人文化使命的担当。就“白话文言”的诗语发展而言,这也是一个不断自觉和深化的过程。当梁启超、黄遵宪等明确提出“新派诗”这一命名,并谓之“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之时,诗语新变获得空前的文学史意义。
二、叙事传统在诗语新变中的意义
以“白话文言”为特征的诗语新变,思想为里,而叙事为助,前一节重在论思想而兼及叙事,本节则集中讨论叙事传统对中晚清诗语新变的意义。
中国文学中小说、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与诗文一直有雅俗之分,其所应用之语言,大抵也是与雅语相对的俗语。民间文学也多偏重叙事,叙事诗便以民间乐府最得擅场,成为文人诗叙事的模范。文人对乐府诗的仿效与改造,一在抒情增加而叙事减弱,二在语言的雅化。[17]雅言是以经典为主要资源的语言体系,在相对稳定、封闭的系统里代代相传。而民间叙事,因其无正统意义上的文化积累,反得以直接叙写劳食悲欢,依托于现实生活,语言随时随地灵动变化。因此,当部分文人意识到雅言所导致的言文分离,回归较本色的生活化语言,借重民间文学传统,尤其是叙事传统,也是极为自然的。
俗文学善于从生活中吸收、提炼语言,故能成就其语言的本色化、生活化。在雅言传统中成长的文士,以俗抗雅,或以俗化雅,是对经典所树立的文化权威的反抗,也是知识人对文化淤塞的自我清理,唯抗行新锐之士能之。越到古典时代后期,文人反经典、重通俗的现象越突出,如李贽、金圣叹等推崇白话小说,以至将其提高到与儒家经书同等地位。这既因叙事文学的艺术魅力,也因这魅力中包含有新锐的思想因素。来自民间、生活的本色白话,与由官方推崇的历代经典所组构的语言系统,雅、俗相抗,就是最明显的表征。由叙事而白话,也是文人诗语言新变的内在理路。
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诸大家,与叙事文学、叙事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蒋士铨,本以词曲闻名。他的诗算不得出色,却能壮大“性灵”诗派的声势,或与词曲的助力有关。袁枚的追随者王文治、李调元等,均是戏曲家,王有多种杂剧,李则是戏曲理论大家,有《曲话》《剧话》等问世。袁枚云其早年“不喜听曲”,然在50岁之后,却开始亲近戏曲,与友朋观剧,与伶人、剧作家交往,并且多次就戏曲的故事、表演等发表观点。[18]戏剧的语言、叙事,乃至美学风格,对“性灵诗派”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对诗语新变发生或潜或显的影响,当是可想而知的。
从乾、嘉迄光、宣,越到近代,民间叙事传统对诗歌语言革新的作用愈加显著。黄遵宪提出新派诗的艺术发展路径,就是要和各类文体融合:
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谚俗,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不失乎为我之诗。[17]3
黄氏不仅创作、改编多首《山歌》,其新派诗在语言、风格上也受到客家山歌影响,此皆为学界共识。黄遵宪参酌戏曲、民歌的建议,为梁启超所听取,梁氏主编《新小说》专辟《杂歌谣》专栏。新派诗人还倡导学堂、军队乐歌的创作,黄遵宪有《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梁启超、康有为等有《爱国歌》,已然是新的说唱文学的样式,通俗和叙事,体用相依、携手并进。
新派诗最为集中的阵地,是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开辟的专栏《诗文辞随录》《诗界潮音集》。《诗界潮音集》所登诗歌以长篇叙事诗居多,而且大部分还是组诗。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最初就刊登在这个专栏。黄遵宪的《度辽将军歌》《聂将军歌》《降将军歌》等有强烈的写实性,堪称史诗的作品,以及《番客篇》《樱花歌》《锡兰岛卧佛》等写异域风情民俗,有浓郁土风、叙事生动的诗作,均登载于该专栏。与黄遵宪并列,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另的两位:蒋智由、夏曾佑,也多有通俗叙事歌谣。夏氏较早就进行新派诗的尝试,但在梁启超主持专栏时,诗风已有所改变。蒋智由发表于《清议报》的新派诗最多,如《终南谣》《梦飞龙谣》《奴才好》《醒狮歌》《北方骡》等,可以说是“杂歌谣”体的实践。
叙事传统对于新派诗语言通俗化的意义,还在于诗人的创作,都是建立在丰富的现实生活、深入的社会实践之上。黄遵宪尝谓“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19]3,盖在此也。其时,在外而言,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千年巨变,迫使进步文人不能不走出书斋,介入对现实的反映、认识与思考。那种“游文章之林府”,穷极典籍搜罗表达的语式、词汇,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雅言传统,为诸多有识之士所抛弃。钱仲联先生说叙事是清诗的特色,这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近代,尤其如此。
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多重大事件,扭转着历史的走向,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时事成为诗人叙写的对象,同时也改造着诗人叙写的方式与风格。
黄遵宪新派诗的高潮,如《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便产生于甲午海战期间。这场战事催生了大量名作,郑观应有《闻大东沟战事感作》,袁昶有《闻金州陷》《哀旅顺口》《哀威海卫》,潘飞声作《秋感八首》,李欣荣、何桂林、沈宗略相继追和。此外,李葆恂的《感时四首》《闻旅顺炮台失守感赋》,王春瀛的《甲午三忠诗》(《左宝贵》《邓世昌》《戴宗骞》),成本璞的《辽东哀》《刘公岛为甲午海战覆军处》,张其淦的《挽邓壮节公世昌》,等等,或叙战事,或颂英烈,或评时政,诗人的写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近代时事诗又迎来一个高潮。据学者统计,近代叙写庚子国变,作者逾160多位,诗作则3 300余首。(4)参李柏霖《庚子事变文学研究》,山东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国家不幸诗家幸,念之五味杂陈。
除了动乱、战事,还有各种穷困苦痛,如水旱蝗等天灾,赋役等人祸,更是雪上加霜。罗时进《清代自然灾难诗的诗体叙事》对此有深入研究。[20]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为诗歌叙事提供了丰富且沉重的题材,使清诗为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谱写出高潮的一章。
上述诗作,有的叙事委曲详尽,有的则以议论、抒情居多,然由于反映的是国家、社会的重大“事件”,个体被这类“事件”普遍性卷入,故其体验真实、丰沛而深刻。(5)罗时进先生将文学中的“事”和“事件”作了区分,认为“事”是常态化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突变和断裂”,则构成“事件”。清诗所叙事大致有自然环境事件、社会环境事件、文化环境事件等类。“事件”叙写有其特殊性,对清代诗史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参《基于典型事件的清代诗史建构》,载《江海学刊》2020年第6期。诗人不必在典籍和文献中搜罗灵感和写作材料,直书实叙,便可成章。“事件”的“断裂”和“突发”性,使得叙事是受现实即时刺激的写作,有某种应激特征,故亦无暇雕琢,这也是此类诗在风格上偏向质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延清《庚子记事杂咏》(其十六):
夜半炮声起,听之心骇然。初疑我军起,几欲轰塌天。晨兴起即视,弹落如珠联。无屋不掀破,有垣皆洞穿。争路勇已溃,守陴兵非坚。加以火药尽,势难张空弮。生不丽谯据,死多沟壑填。徒闻辘轳转,不断声连连。虏炮隔城击,环攻东北偏。相持未终日,城阙难保全。[21]154
诗人如扛着摄像机的随军记者,镜头扫过,夜晚的炮击,黎明之后硝烟未尽的战场,一一呈现眼前。诗以第一人称的听觉、视角,依次实录,语言平顺通俗,没有雕琢。开头几句,“夜半炮声起”“初疑我军起”“晨兴起即视”,几个“起”字冗赘重复,实为诗家大忌,然诗人无暇顾此,足见本诗写作的应激性。
此类战争、灾难类叙事诗,还具有公共性写作的特征,诗人要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告知社会,唤醒国人,或者引起当局注意。罗时进考察道光以降自然灾难诗,发现不少旨在救灾劝赈,故语言通俗,易于传播接受。[20]部分时事诗、战事诗同样具备此种公共性特征。庚子国变后,乌目山僧绘《庚子纪念图》,次年在《同文消闲报》连续刊登启事征诗,迅即得到四方志士响应,后得诗100余首,汇编成集,铅印出版。不过,《庚子纪念图题词》中的诗,多为七绝,抒情、议论成分较多,叙事性不强,语言也算不得俗白。这也限制了这一公共文化事件的传播效果,使之仅限于文人间的唱和,而未能影响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从反面说明语言通俗,叙事生动,对于诗歌传播的重要性。社会更欢迎的,是周乐的《鸦片烟歌》、蒋敦复的《芙蓉谣》、狄葆贤的《燕京庚子俚词》、陈春晓的《守城谣》等类更通俗、更亲民的作品。当然,这也与作者的文学修养、知识积累有关。晚清时事诗的作者,有黄遵宪、樊增祥、易顺鼎这样的大诗人,但更多的是周乐、蒋敦复这样普通的文士。无论是客观上的限制,还是主观上的追求,他们的时事诗总体上不得不呈现出浓郁的歌谣意味。歌谣的通俗性促进了诗歌的传播,也与黄遵宪后来提倡“杂歌谣”体,在艺术观念、风格上不谋而合。
近代社会的激烈动荡,使得诗人走出书斋;国门洞开,国际交往的频繁,更使得诗人走出国门,走向东南亚,走到大洋的彼岸。西风东渐,世界物质、制度发生巨变。诗人的阅历,为古人所未曾经,而经典所未曾载。以“诗界革命”的巨擘梁启超、黄遵宪来说,皆有丰富的海外经历,中西文化的对比、冲突,促使他们对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域外的先进器物、制度,乃至风土习俗,成为他们考察探索的对象,也为他们提供了思考和写作的材料。凡此皆无典籍可循,无先例可参,只能据其闻见,征其实际情境、名目,直书而已。黄遵宪所谓“我手写我口”,既是自觉的追求,也是不得不尔,盖其无“他手”可凭藉也。可以说,是丰富的阅历,动荡、苦难而又精彩的世界,促成近代诗家国与世界叙事的大发展,塑造了一代新诗人,从而创作出古所未有的新派诗。
三、“五四”白话诗:历史多种可能性之一
将近代诗歌“白话文言”的新变看成是新文学的先声,是因为这一新变与“五四”新文学在思想、语言上有密切关联。“五四”一代文人学者,也多有将新派诗的探索,作为自己努力拓展的方向,文学史能为此提供很多例证。
比如黄遵宪所痛陈的言文分割之弊,也为新文化运动主将所激烈批评。鲁迅说:“中国的文字艰深难写,古文难读难懂,妨碍老百姓说话。[22]22”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23]96。也是新派诗人所曾努力的方向。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对白话文的八点建议,如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等,黄遵宪、梁启超等也都曾论述过。有学者甚至认为“黄遵宪所设想的新文字文体,与胡适在1916年提出的关于白话文的八点建议大致相同,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通行的白话文”。[24]250
近代新派诗体式上基本还是古典的,但也在尝试着突破,“杂歌谣”体就是最突出的表现,这对“五四”新诗影响极大。梁启超在《新小说》所开辟的《杂歌谣》专栏,载录新派诗人的“杂歌谣”诗,某种程度上直接催生了现代白话诗。在胡适《尝试集》尚未出版的1918年,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担任编辑,钱玄同、沈兼士协作,在全国发起歌谣征集活动,是年五月,在《北京大学日刊》载录刘半农所编《歌谣选》共148则。其后因主持者的变动而停顿,1920年复于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立《歌谣》周刊。该刊的目的一在民俗学研究,另一就是为文艺提供新的经验和方向。[25]歌谣征集、编选者、作者很多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周作人都有专稿讨论民歌问题。胡适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并断言“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通例”[1]15,因此,对民间歌谣极度重视,也将其视为新文学之源。《歌谣》周刊在1925年停刊之后,又在胡适推动下,于十年后复刊,胡适撰《复刊词》,对民谣的价值及其对新诗的意义做了总结式的定位:“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提高中国文学的范围,增加范本。……民间歌谣是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丽的漂亮语言,可以提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26]774而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的“杂歌谣”,正是“五四”歌谣运动的先驱。胡适将黄遵宪不避时语俗谚、追求言文一致的诗歌主张,直接称为“白话诗”。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语作诗了。他那个时代作的诗,还有《山歌》九首,全是白话的。”他还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人”[26]222。
“五四”旗手将近代新派诗看成他们的先驱,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一方面是新派诗确对“五四”白话诗有启迪,二者相关联也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吴芳吉谓“新诗之历程有五:始以能用新名词者为新诗,如黄公度《人境庐诗》是也;次以能用白话者为新诗,如留美某博士诗集是也……[27]428-458”,以新派诗、“五四”诗为前后之相续。另一方面,近代新派诗人,主观上也有强烈的诗歌改革意愿。“诗界革命”的明确号召,“诗界哥伦布”的使命自觉,言文合一的创作追求,等等,足见他们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都是指向未来,且隐约就是指向白话诗。而且,早在“五四”之前,维新派文人裘延梁在梁启超、黄遵宪的影响下,正式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6)1898年8月27日,裘延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第三个方面,“五四”学人鼓吹新派诗的声势与价值,为新文化运动壮大声势,也是一种文化策略。这也成为其后文学史家论述二者关系的一个基调。
近代新派诗与“五四”白话诗诚然有很多的共性和关联,但他们是否就是系统的历史进程中的两环呢?以“五四”白话文为方向,固可从诗歌观念、语言、体式的通俗化来向近代追溯其渊源,然近代新派诗是否就一定会走向“五四”,其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对新派诗、白话诗以及中国诗歌的未来,都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进化史观、理性历史主义总是将一切历史结局都看成必然与唯一,这种以结果来追溯因缘,并非不可,但如果绝对化,就是刘知几所谓“移的就箭,曲取相谐”(《史通·书志》)历史的规律性,应该有更宽泛的视野。古典诗歌在近代开始的语言、体式的通俗化,“五四”白话诗并不是终极结果,也不是唯一结果,这一过程或许仍在延续之中。
实际上,“五四”学人对近代新诗派的看法并不统一,以“歌谣体”诗而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等都予以高度肯定,并认为其对白话新诗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朱自清、林庚、朱光潜等,却颇多不同意见。朱自清认为歌谣是一种“幼稚的文体”,“缺乏细腻的表现力”,“从文字上,有时竟粗糙得不成东西”[28]65,对歌谣的文学价值持全面的否定。朱光潜认为“诗的固定形式是表现诗的情趣所必须的”,“歌谣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全是自然的流露;它有它传统的技巧,有它的艺术的意识。”[29]朱光潜主张要从歌谣的源头来认识歌谣艺术上的形式特征,实际上又回到了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林庚则认为歌谣不是乐府,也不是诗,“对歌谣抱太大的希望,以为新诗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出路”是行不通的,歌谣“是一件独立的东西”。[30]也就是说,对待新诗的发展,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五四”一代学者一直在探索着。虽然文学史最终是以胡适所倡导的白话诗影响最大,然而这未必就是近代新派诗的方向。
在近代历史背景下的新派诗,鉴于古典诗歌末流的饾饤琐碎,迂腐古板而提出语言、思想上的革新,其目的未必是要整体上否定古典诗歌。他们对诗歌革新的发展,也未曾预设明确的方向。今人以“五四”为目的来描绘诗歌史,其所理解的新派诗,已在不同程度上被“五四”所修改、所塑造。如胡适说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是关于白话文运动的一篇宣言书,显然就是对新诗派的策略性解读。即便是“白话”,新诗派的“白话”可能与“五四”也不一样。新派诗既有其新,也有其旧,他们对诗歌的革新,并非蹈空独创,反而是托古求变。梁启超对诗歌改革的主张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新理想入古风格”[31]51,2,107;黄遵宪对“诗界革命”的写作策略讲得更具体:“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19]3新的思想,古的体式、风格,虽然在语言上不避俚俗,但总体上还是古典诗歌。而且新诗派诸人到后期,对其诗歌变革的实践,均有所反思和后撤。胡先骕说黄遵宪“旧学根底深,才气亦大,故其新体诗之价值,远在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上。然彼晚年,亦颇自悔,尝语陈三立,天假以年,必当敛才就范,更有进益也”[32]206。黄遵宪与陈三立,诗歌风格趣向不同,然惺惺相惜。陈称黄诗“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19]1083,黄对陈也备极推崇,在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中,有黄遵宪的诸多批语,堪称陈的并世知音。[33]黄遵宪晚年的诗作,就有向陈靠拢的迹象。《人境庐诗草》卷十、卷十一,皆20世纪新作,以律诗居多,叙时事则多以典故隐括,与甲午前后的新派诗颇为异趣。在黄的自编诗集中,也不收所作军歌、校歌,或亦能反映他的态度。
梁启超晚期诗学观念也有较大转变。夏晓虹认为梁启超生命的后十年(1918—1929)向传统文学观念复归的阶段,他不再提“诗学革命”,而是开始“潜心于学术研究,注目于文学的永久价值”[34]。他批点《白香山集》,思考古典诗歌的现代转换,甚至拜同光派诗人赵熙为师,“一意学宋人”[35]。而这正是“五四”的前夜,在“五四”白话文轰轰烈烈展开之时,这位曾经主张通过诗歌、小说的语言、文体变革来促进社会进步的时代领袖,却退到幕后,重新在中国古典中寻找文学的方向。
其实,即便没有新派诗领袖的后期转向,“五四”白话诗也很难说是古典诗歌演变的终极结果,这与它自身的局限有关。“五四”新文学因其文化政治目的,与文言传统水火不容,走向偏激,且白话文又处在探索初阶,很难说在艺术上达到怎样的高度。梁启超的意见甚为中肯:“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视白话为洪水猛兽的守旧者)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而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作得出好诗,用文言也作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36]73梁启超不是简单反对白话诗,而是希望看到真正有艺术价值的白话诗:“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知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36]75其实,新文学中代表作家林庚、朱光潜等,也已经对白话文过于激进之处有所矫正,在20世纪的20、30年代,闻一多、徐志摩等致力于新诗的格律化,也在理论与实践上予以纠偏。他们努力的方向,某种程度上或正是梁启超所期待的。
显然,“五四”只是近代诗发展的诸多可能中的一种,因各种因素而成为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必然和终极。“五四”白话诗很难说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它不过是一个转型期的开始,这一转型,直至今日,仍在持续。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新诗写作,不能也不应脱离文言传统,必须综合一切有益的文学因素,才能真正完成转型,建立起能与古典相抗衡的现代诗学。
四、结语
语言、体式走出经典,走向生活与通俗,在中国诗歌中是自古就存在的现象。时至清代,从袁枚、龚自珍等开始,这一语言和体式的革新,与反传统的新思想相呼应,开启了近代诗学的进程,在黄遵宪、梁启超等新派诗那里达到高潮,并影响到“五四”白话诗。
语言是思想的表征,叙事传统因其贴近民间、现实,秉有质实通俗的特性,与这一诗史进程紧密呼应。近代社会的苦难,促进了叙事诗的大发展。叙事内容的丰满、充实,作诗故不必过多依赖典籍提供材料,且新时代、新气象为古籍中所未曾载,“我手写我口”成为可能和必须。凡此,又进一步加速了清诗“白话文言”的新变。
清代以来诗歌“白话文言”的新变,以思想为里,得叙事之助,推动了中国诗史的近现代转型。尤其是近代新派诗的“诗歌革命”,成为“五四”重要的文学和精神资源,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五四”新文学。从这个角度,不妨说它们是新文学的先声。
然而,“五四”白话诗,正如胡适新诗集的命名,是汉语新诗的“尝试”,它是历史多种合力的结果。“五四”白话诗,远未达成艺术上的圆满,亦非近代诗“白话文言”之变的终点。就艺术与审美逻辑而言,晚清近代诗歌之新变,是否必然归向“五四”,是值得追问和反思的。
中晚清以来的诗歌变革以及“五四”白话诗,在古典诗词之后,创造了中国诗歌的新传统。这是一个仍在持续生长、不断壮大的传统。如何接续百年前诗人们的思考与探索,融汇中西、参酌古今,全面完成汉语新诗的现代转型,仍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