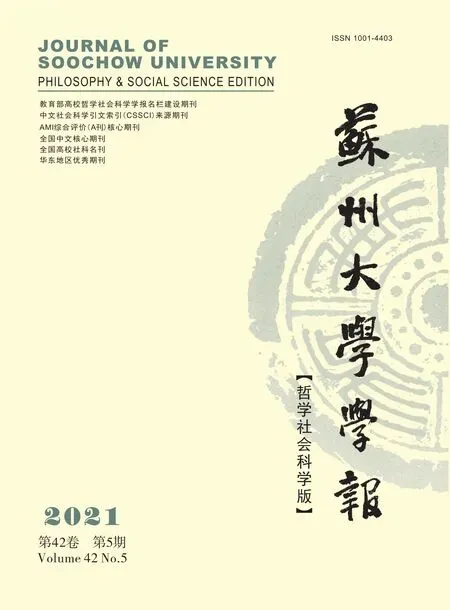应合与变转:李维桢诗学旨义的二重面向
郑利华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李维桢,字本宁,号翼轩,京山(今属湖北)人。隆庆二年(1568)举进士,选翰林庶吉士,除编修。历官陕西右参议、提学副使、右布政使等职,仕终南京礼部尚书。其平生和当时文坛王世贞、汪道昆等七子派成员的交谊较为深厚,也因此被王世贞纳入“末五子”之列。隆庆五年,李维桢与王世贞初识相通,自后彼此联系较密。万历二年(1574),王世贞抵京任太仆寺卿,李维桢从游。万历十二年,李维桢又至吴中访王世贞,宿八日而别。[1]171-310万历十年岁末至十一年春之间,汪道昆和时任徽州府推官的武陵人龙膺共同创建白榆社。该社缔构之初,成员除汪、龙二人之外,还有汪氏之弟汪道贯和叔父仲子汪道会,以及歙县人潘之恒、长洲人郭第。此后盟社规模扩展,入社中除了徽州当地人士外,又有不少来自其他地区者,所谓“诸宾客自四方来,择可者延之入”[2]591,而李维桢曾加入此社。论辈分和资历,李维桢晚于王世贞、汪道昆,属于后七子的新生代成员,但成为王、汪推重的后进之一,所谓“公(案,指李维桢)于汪、王两公稍晚一辈,而两公齐推毂之,以为将来定踞吾二人上”[3]第150册,268。这也可见他在王、汪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考察李维桢的诗学立场,作为七子派的新生代成员,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的相关阐说,固然有着和诸子相同或相近的一面,但同时,又表现出与之形成明显异别的一面。简括而言,应合与变转构成李维桢诗学旨义的二重面向,这也是本文讨论问题的主要切入点。
一、诗歌史的勾勒与宗尚脉络的梳理
检视李维桢论诗,其中所涉及的纲要性的问题之一,即关于古典诗歌的发展演进历史,他就此做过如下简略的梳理:
以诗为诗,《三百》而后,最近者汉魏,其次唐,其次明,中于温柔敦厚之指者,十得一焉。[3]第151册,76
这是以《诗经》作为衡量的标杆,概述《诗》三百篇之后,汉魏、唐、明诗承继《诗经》传统的历史演变轨迹。这一提法,近似于胡应麟“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4]326的“三变”说,其中汉魏和唐代诗歌素为七子派诸子所普遍推尚,至于将明诗视为古典诗歌演化进程中继汉魏、唐诗之后的第三个高峰,突出它的历史地位,体现出李维桢本人对于明诗的重视态度。这包括他针对特定诗体如律体在有明的创作态势而给予的非同一般的评价,如胡应麟曾“辑录本朝五七言近体为律范”,李维桢序之曰:“《三百篇》后千有馀年,而唐以律盛,垂八百馀年,而明绍之,黜宋元于馀分闰位,而莫敢抗衡。所贵乎明者,谓其去唐远而能为唐也。唐诗诸体不逮古,而律体以创始独盛,尽善尽美,无毫发憾,明律乃能俪之。所贵乎明者,谓其能以盛继盛也。唐律诗代不数人,人不数篇,篇以百计,入选十不能一。中晚滔滔信腕,遂不堪覆瓿矣。明诸大家陶冶澄汰,错综变化,人能所极,宛若天造,篇有万斛之泉,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3]第150册,497如此对有明律体包括“明诸大家”的不吝赞评,难免有为胡应麟此编大力鼓吹之意,未必全然符合明律实际创作情形,然以上赞词多少代表了李维桢本人看待明诗的基本态度。
李维桢之所以做出明诗可与汉魏和唐代诗歌相并论的断言,与他本人和后七子集团关系密切及同情七子派创辟复古大业的立场分不开。其《彭伯子诗跋》提出:“诗自唐以后无如本朝,盛于诗无如德、靖间,而继往开来,归功李、何。李由北地家大梁,多北方之音,以气骨称雄;何家申阳近江汉,多南方之音,以才情致胜。”[3]第153册,672这无非指证“本朝”继唐之后诗歌大盛,得以“继往开来”,作为七子派先驱人物的李梦阳、何景明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功不可没。其《金陵近草题辞》又说:“盖弘、正以来,诗追古法,至嘉、隆益备益精。极盛之后,难乎其继。”[3]第153册,683明代弘治至隆庆年间,正是前后七子从事复古作业的活跃阶段,在李维桢看来,这一阶段也是明代诗歌趋于盛兴的黄金时期。再具体到明代的律体,以此为样例,他所做的阶段析分和相关论评,同样用意明确:
初唐律寖盛,迨盛唐而律盛极矣。曾几何时,中不若盛,晚不若中。明洪、永之际,律得唐之中;成化以前,律得唐之晚;弘、正之际,律得唐中盛之间;嘉、隆之际,律得唐初盛之间。所贵乎明者,谓其盛于唐而久于唐也。……人情便于趋下而惮于革故,是以盛者向衰易,而衰者返盛难。明自七子没,而后进好事者开中晚之釁,浸淫于人心而莫之底止。[3]第150册,497
唐律的变化被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应该源自明初高棅、王行等人标举的唐诗四分法的基本思路[5]197-199,初盛与中晚唐律体则形成盛衰变化的鲜明对照,亦如李维桢在《唐诗类苑序》中所描述的:“唐之律严于六朝,而能用六朝之所长,初盛得之,故擅美千古。中晚之律自在,而犯六朝之所短,雅变而为俗,工变而为率,自然变而为强造,诗道陵迟,于斯为极。”[3]第150册,491再以唐律变化的四个阶段衡量明律在不同阶段的创作情形,指示前后七子活跃其中的弘、正和嘉、隆年间,多得初盛唐律体的风貌,成为明代律体盛兴的重要标志,乃意味着将明律之“盛”主要归功于前后七子,以上“明自七子没,而后进好事者开中晚之釁”而预示明律之“衰”的说法,则可与此相印证。关于前后七子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李维桢《吴韩诗选题辞》曾做出“七子于明诗为正宗,为大家,为名家”[3]第153册,694的结论。所谓“正宗”“大家”“名家”,原本是高棅《唐诗品汇》对应盛唐时期的品目[6]14,李氏借此命名七子,亦可见出其抬升诸子地位的用意。概言之,李维桢梳理《诗经》以来古典诗歌演进历史,尤其将明诗和汉魏、唐代诗歌一并标为诗歌史上的三个高峰,当是以前后七子复古业绩作为判断明诗地位的主要依据。
不过,继《诗》三百之后“最近者汉魏,其次唐,其次明”之类的统绪概括,只是代表李维桢对以《诗经》为标杆的诗歌演化史基本框架的勾画,事实上,廓清诗歌演化轨迹的重要意图之一,则是为了更明晰地确定诗歌的宗尚目标,而从他对诗歌宗尚脉络的梳理来看,实际的情形还要相对复杂。先看他以下所论:
夫嘉、隆诸君子善学六朝、汉魏与唐音也,舍六朝、汉魏与唐,而惟嘉、隆诸君子之求,故宗门渐远,而蹊径易穷。[3]第150册,713-714
今为诗者不知有唐,宁论六朝、汉魏,远则信阳、北地,近则历下、娄江止耳。求之形迹,失之神情,甚者为沈约、任昉之盗而已。[3]第150册,729
盖今之能诗者,所在而有,其法取嘉、隆以来诸公,上及三唐而止,不能求诸六朝、汉魏,安问《三百》。[3]第151册,9
啖名者才不足,而思陵驾前人,信心信腕,更立一格,不知其所掇拾仅唐中晚、宋元之剩语,而汉魏、六朝、唐初盛所不屑道也,安在其为奇为变化哉?[3]第153册,683
乐府、古诗承《三百篇》之流,而开唐以后近体之源。《三百篇》不可尚已,汉魏及六朝取法非难,而近代多攻唐体,顷又取中晚及宋元俚俗之调为真诗,欲与《三百》抗衡,而汉魏、六朝置不省矣。[3]第153册,696
综合上述,作者大致列出诗歌宗尚的主要目标,除了《诗经》这一具有标杆意义的源头之外,汉魏、六朝以及初盛唐诗都被纳入取法的总体范围。对于七子派诸子来说,作为古典诗歌原始的经典文本《诗经》,以及作为古近体重点取法对象的汉魏和初盛唐诗歌,一直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就此不必赘言,至于六朝诗歌则多不被看重。早先如李梦阳就以为,“说者谓文气与世运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7]卷五六《章园饯会诗引》,其抑贬之意居多,并因此对身为“齐人”的盟友边贡习学六朝之举深感不解。以后如谢榛提出,“六朝以来,留连光景之弊,盖自《三百篇》比兴中来”[8]卷二一《诗家直说一百二十九条》,“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8]卷二一《诗家直说一百二十九条》,轻视六朝诗歌的心向,同样昭然若揭。诚然在对待六朝诗歌问题上,李维桢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如他表示:“《三百篇》删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学富而不务华。汉魏肖古十二三,六朝厌为卑近,而求胜于字与句,然其材相万矣,故博而伤雅,巧而伤质。”[3]第150册,490又指出,“律诗昉于六朝,四六文盛于六朝”,“两者若相为用而实不同。文无定裁,伸缩由人,律诗有定体,不可损益。六朝以其为四六之文者为诗,或坐牵合,或出强造,或竞诡僻,或涉重复,而诗病矣”。[3]第150册,554在他看来,六朝诗歌以其“博而伤雅,巧而伤质”,与前相比,不仅距离《诗经》风格尚远,而且不及汉魏之“肖古”,特别是其融入讲究骈俪藻饰的四六文作法,最终不免“诗病”。或许可以说,李维桢就此作出的诸如“六朝之诗雕绘妍媚”[3]第150册,521之类的论断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是评价六朝诗歌之传统成见的某种复述。但问题尚不止此,对于六朝诗歌,李维桢的基本立场是既指出其所短,又重视其所长,并非一概抑黜。他在《唐诗类苑序》中谈及初盛和中晚唐律体汲取六朝诗歌而呈现的各自差异:“唐之律严于六朝,而能用六朝之所长,初盛时得之,故擅美千古。中晚之律自在,而犯六朝之所短,雅变而为俗,工变而为率,自然变而为强造,诗道陵迟,于斯为极。”[3]第150册,491即已说明了这一点。其实,李维桢分别六朝诗歌之“长”“短”,不得不说体现了他对待六朝文学所秉持的相对理性的态度,这从他以为不应“薄视”六朝文章的论评话语中也能见出一二。如其《邢子愿全集序》曰:“今所在文章之士皆高谈两京,薄视六朝,而不知六朝故不易为也。名家之论六朝者曰:‘藻艳之中有抑扬顿挫,语虽合璧,意若贯珠,非书穷五车,笔含万化,未足语此。’又曰:‘文考《灵光》、简栖《头陀》,令韩、柳授觚,必至夺色。’”[3]第150册,532-533据李维桢所标示的古典诗歌的宗尚系统,六朝诗歌虽不在完善而重点取法的目标之列,但显然被当作诗歌史上具有形塑意义以至不应忽略的一个过渡环节,这特别体现在其对唐诗的造就上。因此,李维桢在《青莲阁集序》中指出:“今夫唐诗祖《三百篇》而宗汉魏,旁采六朝,其妙解在悟,其浑成在养。其致在情,而不强情之所本无;其事在景,而不益景之所未有。沉涵隐约,优柔雅澹,故足术也。”[3]第150册,716换言之,唐诗得以成就,不仅与其“祖”“宗”《诗经》和汉魏诗歌有关,也离不开其对六朝诗歌的“旁采”;六朝诗歌影响唐诗的作用显而易见。尤其从“体”的变化演进来看,由彼至此,经历了逐渐严饬和完善的过程,其中律体的进化无疑更为明显。简括起来,即所谓“汉魏、六朝递变其体为唐,而唐体迄于今自如”[3]第150册,490;展开来说:“至汉魏、六朝而后诗始有篇,皆五言者;始有篇,皆七言者。汉魏古诗以不使事为贵,非汉魏之优于《三百篇》也,体故然也。六朝诗律体已具,而律法未严,不偶之句与不谐之韵往往而是。至唐而句必偶,韵必谐,法严矣。又益之排律,则势不得不使事,非唐之能超汉魏、六朝而为《三百篇》也,体故然也。”[3]第150册,491
二、中晚唐及宋元诗歌的价值分辨
如前所述,李维桢理出的古典诗歌的宗尚脉络,初盛唐诗被纳入其中。这自是展示了他和七子派相近的宗唐立场。按其区分,尽管初盛唐与中晚唐诗盛衰差异迥然,但这不等于他彻底排斥中晚唐诗。如《唐诗纪序》评及唐人各体,详辨“盛衰”态势,其中于绝句,提出“绝句不必长才而可以情胜,初盛饶为之,中晚亦无让也”[3]第150册,490,即以为中晚唐绝句并不逊于初盛唐之作,其对中晚诗价值的有限度的认肯,自此可见一端。特别在中唐诗人当中,他对白居易更是称赏有加,体现了其态度的另一面,《读苏侍御诗》云:
余友邹孚如尝言王元美先生《巵言》抑白香山诗太过。余谓此少年未定之论,晚年服膺香山,自云有白家风味,其续集入白趣更深。香山邃于禅旨,翛然物表,又不立崖岸门户,故其诗随语成韵,随韵成适,兴象玲珑,意致委宛,每使老媪听之,易解而后可,不则再三更定。是以真率切至,最感动人。威权如天子,猜刻如宪宗,读其讽谏百馀篇而善之,有自来矣。[3]第153册,623
有研究者据此以为,从李维桢对白居易诗的称赏,可以梳理出后七子对白诗所持的态度,后七子对大历以下诗的吸纳,其改变自王世贞始,在这方面王世贞又突出表现在晚年对白居易和苏轼诗的服膺。[9]392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尚需加以分辨。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曾一再贬抑白诗,如谓:“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晩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白香山初与元相齐名,时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俱分司洛中,遂称刘、白。白极重刘‘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为有神助。此不过学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时时颂李颀‘渭水自清泾至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欲模拟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极是恶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风雅不复论矣,张打油、胡钉铰,此老便是作俑。”[10]卷一四七《艺苑巵言四》《艺苑巵言》成稿于王世贞早年(1)王世贞隆庆六年(1572)自序《艺苑巵言》曰:“余始有所评骘于文章家曰《艺苑巵言》者,成自戊午(按,指嘉靖三十七年)耳。然自戊午而岁稍益之,以至乙丑(按,指嘉靖四十四年)而始脱稿。里中子不善秘。梓而行之。……盖又八年而前后所増益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録,为别卷,聊以备诸集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由此说该书“抑白香山诗”系作者“少年未定之论”,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说王世贞“晚年服膺香山”,则未必完全恰切。相比于《艺苑巵言》对白诗的不屑,晚年王世贞的态度的确有所缓和,如谓“香山数以直言谪外,晚节与缁黄相还往,通晓其理,知足少欲,不愧名字”,“操觚之士间有左袒左司者,以左司澹而香山俗。第其所谓澹者,寓至浓于澹;所谓俗者,寓至雅于俗。固未可以皮相尽也”。[11]卷四七《龚子勤诗集序》这或许与王世贞晚年心态趋于和静淡冷的变化不无关系。即使如此,他对白诗的认可还是有限度的,总体上并未越出早年轻视白诗的基本认知。如其此际评他人诗,谓“合者出入于少陵、左司之间,而下亦不流于元、白之浮浅”[11]卷四一《钱東畬先生集序》;又自嘲所作:“夫仆之病在好尽意而工引事,尽意而工事,则不能无入出于格。以故诗有堕元、白或晚季近代者,文有堕六朝或唐宋者。”[11]卷二〇〇《屠长卿》其中对白诗的基本定位未有太大改变,说到底,仍受制于“大历以后弗论”[12]104的基本思路。和王世贞的立场明显不同,李维桢以为白居易“邃于禅旨,翛然物表”,而其诗“随语成韵,随韵成适,兴象玲珑,意致委宛”,给予的评价已非同一般。又议论他人诗,谓之“不专匠心,不纯师古,内缘情而外傅景,敛华就实,斫雕为朴,书画家所谓逸品。即不知于右丞何如,夫亦白、苏流亚已”[3]第153册,681-682,也显出他对白诗的青睐。由此一端,至少可见其在对待大历以后唐诗上不以代掩人的一种取舍态度。
需要注意的,还有李维桢对于宋元诗歌所持的态度。上已指出,总体上李氏的宗唐立场是明确的,这不仅见于他对于《诗经》“最近者汉魏,其次唐,其次明”之类统绪的总括,而且见于他对初盛唐诗的大力标举,这也是他响应七子派诸子诗学立场的一个重要口号。可与之印证的是,他又在《唐诗纪序》中提出:“汉魏、六朝递变其体为唐,而唐体迄于今自如。后唐而诗衰莫如宋,有出入中晚之下;后唐而诗盛莫如明,无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昆仑也,汉魏、六朝龙门积石也,唐则溟渤、尾闾矣,将安所取益乎?”[3]第150册,490这是从诗歌递变的历史进程,明确以唐诗为标格,形容它在诗歌史上犹如“溟渤”“尾闾”一般聚汇和备该之盛势。同时,其不但区分了初盛唐与中晚唐诗的品格差异,并且涉及唐宋诗歌盛衰比较的问题。后者所谓“后唐而诗衰莫如宋”的判断,在唐人和宋人诗歌之间显然划出一道轩轾相异的界线。其《二酉洞草序》又云:“少年治经生业,既恐诗妨本务,不暇及。比入官,取功名富贵之途多端,于诗稍染指,以供应酬而已。而宋元以来肤浅庸俚之体入人易,而误人深,不能自拔。”[3]第150册,738直言宋元诗歌“肤浅庸俚”的先天不足和误导作者的负面影响,想来是他大体置宋元诗歌于“馀分闰位”的基本理由。其中李维桢对宋诗的批评相对突出,如《雷起部诗选序》说,“宋人于杜极推尊,往往得其肉,遗其骨;得其气,遗其韵。盖时代所限,风会所囿,而理窟禅宗之说又束缚之。是以丰赡者失于繁猥,妍媚者失于儇佻,庄重者失于拘滞,含蓄者失于晦僻,古澹者失于枯槁,新特者失于穿凿,平易者失于庸俚,雄壮者失于粗厉”[3]第150册,753。这是从时代风尚和学术信仰影响的角度,解释宋诗呈现颓唐之势的原因所在。不过,这些点评宋元诗歌的片段化意见还显得比较零碎,不及李维桢序新安人潘是仁编辑的《宋元名家诗选》而针对宋元诗歌所作的评价来得全面:
诗自《三百篇》至于唐,而体无不备矣。宋元人不能别为体,而所用体又止唐人,则其逊于唐也故宜。……余为童子受诗,治举子业,其义训诂,其文俳偶,无关诗道。比长而为诗,亦沿习尚,不以宋元诗寓目,久之,悟其非也。……宋元人道宋元事,即不敢望《雅》《颂》,于十五《国风》者,宁无一二合耶?……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采风陈诗,而政事学术、好尚习俗、升降污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诗者,亦孔子录十五《国风》之指也。……就诗而论,闻之诗家云,宋人调多舛,颇能纵横,元人调差醇,觉伤局促;宋似苍老而实粗卤,元似秀峻而实浅俗;宋好创造而失之深,元善模拟而失之庸;宋专用意而废调,元专务华而离实。[3]第150册,495-496
所论对于宋元诗歌既有批评又有认肯,反映了李维桢审视唐后明前处于被认为是衰微时期诗歌历史的复杂态度。站在批评的角度,他声言诗至唐“体无所不备”,而宋元诗歌“不能别为体”,终究“逊于唐”,以及引述诸诗家排击宋元诗歌之见,借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对照李、何及李、王诸子素为人知的贬抑宋元诗歌的倾向,也可说是随之呼应,大致合调。站在认肯的角度,他有意现身说法,以本人当初趋从“习尚”而“不以宋元诗寓目”,到后来“悟其非也”的认知态度的变化,说明对待宋元诗歌不应其“逊于唐”或存在诸多不足而全然排斥之。也许可以说,时至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在宋元诗歌尤其是宋诗问题上,其排击的态度较之诸子有所缓和,他序归安人慎蒙《宋诗选》云:“自杨、刘作而有西昆体,永叔、圣俞思以淡易裁之,鲁直出而又有江西派,眉山氏睥睨其间,最号为雄豪,而不能无利钝。南渡而后,务观、万里辈亦遂彬彬矣。去宋而为元,稍以轻俊易之。”还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而已”,尽管自己“尝从二三君子后抑宋者也”。但必须指出的是,其实王世贞对于宋诗的包容非常有限,出语也是相当谨慎,并未改变其“所以抑宋为惜格”的初衷,而以为不应废“人”“篇”“句”的主张,本来即以“此语于格之外者”[11]卷四一《宋诗选序》为前提。相比较,李维桢以“采风陈诗”的特殊意义,申述“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为两代诗歌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作辩护,包括由此联结《诗经》十五《国风》的传统风范,以及追溯孔子对于《国风》的取录之旨,展开阐说的基点有所不同,相对提升了宋元诗歌的价值地位,也强化了认可的力度。这应该是他在宋元诗歌问题上和王世贞等人相比而呈现的同中之异。
三、学古习法原则的再确认
在李维桢展述的重要诗学命题中,其除了围绕古典诗歌演化及宗尚脉络所作的勾勒和梳理,还有一大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他对学古与求真关系所展开的诠释。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涉及如何合理借鉴古典资源的核心问题。就倡导复古的七子派诸子来说,强调学古自是他们坚持的基本立场,体现了他们对古典资源利用的高度重视。但无论从常识的角度还是从策略的层面,他们多数又主张以求真来维持与学古之间构成的制约或平衡关系。以七子派先驱者李梦阳为例,为反驳何景明对他“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的指责,其针锋相对申明:“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倕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7]卷六一《驳何氏论文书》这段辩驳文字人所熟知,大旨即围绕习法以学古和抒情以求真的关系来展开,主张既要维护自我之真情,又须严守古人之法度。而他对诗歌所抒之“情”的质性作过如下定义,“夫天下百虑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为欢者也。情者,所为言者也”,“是故其为言也,直宛区,忧乐殊,同境而异途,均感而各应之矣,至其情则无不同也。何也?出诸心者一也”。[7]卷五八《叙九日宴集》众人之情有“忧乐”之分,发抒之径也有“直宛”之别,此即所谓“异途”。同时出自真实的内心,就能殊途同归,此即所谓“同境”。以故“同于情”,指的是诗人抒发之“情”在内质上的趋同,也即缘于“出诸心”而在纯真性上的趋同。[13]120-121这也可以用来补充李梦阳“以我之情,述今之事”说法的基本含义。
来看李维桢有关论述。在是否应该学古问题上他的表态十分明确,其《朱修能诗跋》云:
今为诗者,仿古人调格,摘古人字句,残膏馀沫,诚可取厌。然而诗之所以为诗,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无二道,惟才识之士拟议以成变化,臭腐可为神奇,安能离去古人,别造一坛宇耶?离去古人而自为之,譬之易四肢五官以为人,则妖孽而已矣。盖近日有自号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讼言。……修能《选》体法汉魏,律体法唐大历以前,古人成法,得修能而益见其精;修能韵致,得古人而善用其长。死鬼之常辞,为贤哲之话言。彼恣心信腕,偷取一时之名,庸夫俗子岂不甚快,而卒为大雅罪人。[3]第153册,636
尽管当世为诗者一味仿袭古人“调格”与“字句”的作法诚不足取,但这只能说明其学古方法存在问题,并不能由此否定学古本身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鉴于“情景事理”古今相通,并无二道,正如李维桢在《朏明草序》中声称:“夫日有九道,有十煇,有两弭,有重光,五色无主,万象生态,错综变化,不可胜数,而本真体质自如。惟诗亦然,抑扬清浊,声以代殊,代以人异,而缘情即景,陈理赋事,干之以风骨,文之以润色,无论初唐、六朝,先后万世,莫能易也。”[3]第151册,18故习学古人顺理成章,不必忌避。这是从诗歌“缘情即景,陈事赋理”的本质构成,定义其古今不二的稳定性、共通性。顺着这一逻辑,如果“离去古人而自为之”,意味着对古今无异的诗歌本质构成的悖离,担负诗不成其为诗的巨大风险。因此,“自号作祖”“恣心信腕”者的作法,令人不可接受。由是不得不说,维护学古的正当合理性,也是李维桢呼应七子派诸子复古举措的一种表态,在根本上,还源于他对后者采取的关注和同情的立场。其《吴韩诗选题辞》又说:“余尝论诗前人作法于俭,犹恐其奢;后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钟记室《诗品》谓某源出某,严沧浪云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差毫厘,谬千里,可不慎哉!七子没垂三十年,而后生妄肆诋诃,左袒中晚唐人,信口信腕,以为天籁元声。殷丹阳所胪列野体、鄙体、俗体,无所不有,寡识浅学,喜其苟就,靡然从之,诗道陵迟,将何底止?”[3]第153册,694钟嵘《诗品》论“某源出于某”或“某体源出于某”的溯流追源,成为其历史批评和全书的理论架构,旨在论析历代五言诗发展与诗人流派渊源关系。[14]48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要在指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工夫须从上做下”[15]1的习学法门。题辞标示钟、严二家品论,旨在声明辨析诗歌源流、确认学古正轨的必要性。并且,又以七子为比较对象,批评后七子时代的“后生”所作“信口信腕”,无视古人,不免沦为殷璠自序《河岳英灵集》所谓的“野体”“鄙体”“俗体”[16]40,导致诗道衰微。反过来,这也证明了七子提倡学古的正当合理性。
要确定学古的实践路径,同时则需体认古人的法度规范。在七子派诸子的复古概念当中,学古不是一个空洞性的口号而已,学古与习法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学古是基本的指导原则,习法则是这一原则的技术展开,此见下面所述。而讲究法度,也是李维桢针对学古问题做出的表态,其序汪道昆《太函集》云:“文章之道,有才有法。无法何文,无才何法?法者,前人作之,后人述焉,犹射之彀率,工之规矩、准绳也。知巧则存乎才矣。拙工拙射,按法而无救于拙,非法之过,才不足也。将舍彀率、规矩、准绳,而第以知巧从事乎,才如羿、输,与拙奚异?所贵乎才者,作于法之前,法必可述;述于法之后,法若始作。游于法之中,法不病我;轶于法之外,我不病法。拟议以成其变化。若有法,若无法,而后无遗憾。”[3]第150册,526表明创作之道既要有“才”,又须有“法”,二者不可或缺。“法者,前人作之,后人述焉”的自身逻辑,赋予了学古习法无须规避的合理性。如他形容诗歌史上独具标杆意义的《诗经》“无一字不文,无一语无法,会蕞诸家之长,修饰润色之耳”,并描述“骚出于《诗》而衍于《诗》”,以至“两汉、六代、三唐诸人得其章法、句法、字法,遂臻妙境,夺胜场”。[3]第150册,486不仅表彰《诗经》在法度层面的示范意义,且展现自《诗经》至汉唐诗法一脉相承的演进轨迹。他在序谢肇淛诗集时又指出,“盖诗有法存焉,离之者野狐外道,泥之者小乘缚律”,认为谢诗“率循古法,而中有特造孤诣,体无所不备,变无所不尽,杼轴自操,橐籥靡穷,斧凿无痕,炉锤独妙”。[3]第150册,738作为问题的两面,“泥”“法”固然不明智,但“离”“法”何尝行得通?所以他称许谢诗,除了能“特造孤诣”,又能“率循古法”。他对何景明“舍筏”说的解释,同样值得留意,其《彭飞仲小刻题辞》云:“昔信阳有舍筏之喻,盖既济而后可以无筏,未有无筏而可以济者。自顷才士恣行胸臆,若曰蹈水有道,不烦凭藉,师心徒手,矜以为奇,而卒飘荡不收,沉沦不反,孰与人涉卬否者,可自全哉?”并称彭氏所作:“或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莫不有法存焉,其舍筏也,乃由善用筏得之者也。”何景明所谓“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3]第153册,695,广为人知,要在宣示“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17]卷三〇《与李空同论诗书》。此说遭到主张“规矩”之“法”的李梦阳的反驳,以为是“出入由己”而舍“规矩”,“于法焉筏矣”。[7]卷六一《驳何氏论文书》体味李维桢的解释,其并未纠结于李、何二人的争论立场,而是着重从“未有无筏而可以济者”“善用筏得之者”的角度,诠解何氏“舍筏”说的意义所在,阐释依“法”而行、有所凭藉的必要性,故他鄙薄“才士”无视法度、“恣行胸臆”的做法。除此,李维桢在《阎汝用诗序》中也指出,何景明之有“舍筏之喻”,“岂其信心纵腕,屑越前规,要在神明默成,不即不离”[3]第150册,750,解释“舍筏”不等于“离”“法”,核心的意思和上述说法亦大致相通。
另一方面,虽然李维桢如上谓法“犹射之彀率,工之规矩、准绳也”,这一说法近乎李梦阳对于“法”的定义,即所谓“规矩者,法也”,“即欲舍之,乌乎舍”[7]卷六一《驳何氏论文书》,依循古法就是恪守必要的规矩准则,不过比较诸子对于“法”的具体解释,还是有所不同。前七子中李梦阳言法最为有力,他一面袭用规矩作法的传统之说,将“法”定义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共同准则,即定义为不同对象具有的内在、本质的共性;一面则将这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矩”之“法”,落实在诸如“开阖照应,倒插顿挫”[7]卷六一《答周子书》、“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7]卷六一《再与何氏书》这些相对细微和狭仄的规则上,作为学古实践的金科玉律,以至将“法”的普遍性和个别性混为一谈。后七子如王世贞尤其是对于诗法的诠释,则将它们提升至更加周密和细致的层次,更在意不同诗体篇章句字的具体之法,可谓为规范学古习法的路径,更专注于法度的严格审辨,体现了趋于强化的一种文学技术思维。[18]90-102反观李维桢的相关论述,他对“法”的释说,基本将其定义在诸如“射之彀率”“工之规矩、准绳”这样一种相对抽象和浑括的概念上,突出的只是“法”的原则性和纲理性,似乎无意将其解析为苛细而偏狭的律令,使其沦为板滞化和单一化,以避免所谓“小乘缚律”。
四、“性情”说的申诉动机与理论背景
当然,要在根本上辨识上述的问题,还应该联系李维桢为制衡学古而同时强调的求真主张。为说明问题,先引其以下所论:
诗本乎情,发于景,好奇者求工于景所本无,求饰于情所不足,狥人则违己,师心则乖物,穿凿附会若木偶,衣冠形神不相系。[3]第150册,723-724
余窃惟诗始《三百篇》,虽《风》《雅》《颂》、赋、比、兴分为六义,要之触情而出,即事而作。五方风气,不相沿袭;四时景物,不相假贷。田野闾阎之咏,宗庙朝廷之制,本于性灵,归于自然,无二致也。迨后人说诗,有品有调,有法有体,有宗门有流派,高其目以为声,树其鹄以为招,而天下心慕之,力趋之,诸大家名家篇什为后进蹈袭捃摭,遂成诗道一厄,其弊不可胜原矣。[3]第150册,735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记《礼》者广其说曰:“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而后世之为诗者,内不根于心,外不因于风气,或学邯郸而失故步,或持章甫而游断发文身之国,非其质矣。[3]第150册,759-760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材品殊赋,景物殊遭,亦各言其志也矣。而口实好古,寄人篱落,乐府取不可解之字,酬和次不可谐之韵,或无病而效颦,无喜而献笑。此尸祝代庖人樽俎,而不思夫鹪鹩偃鼠欲愿自足也。[3]第151册,7
诗以道性情,性情不择人而有,不待学问文词而足。故《诗》三百篇,《风》与《雅》《颂》等。《风》多闾阎田野细民妇孺之口,而学士大夫稍以学问文词润色之,其本质十九具在。即《雅》《颂》作于学士大夫,而性情与细民妇孺同,其学问文词,亦就人伦物理、日用常行,为之节文而已。今夫浣私抱衾,执筐缝裳,细事也。履武敏不坼副,亵语也。公子同归,征夫迩止,妇叹于室,有依其士,辗转反侧,首如飞蓬,隐衷柔态,谈之或含羞,而圣人悉以被管弦金石,歌宗庙朝廷,无亦谓是性情之真,通诸天下后世不可易乎?[3]第153册,622-623
以上所论尽管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但并不妨碍对其彼此相通的基本观点的梳理,综合起来,从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本质的角度,鉴于诗以言志抒情为本,只有作者根于心或出于情,才能合乎诗歌的本质要求;第二,从溯源的角度,《诗经》作为原始的经典文本,《风》《雅》《颂》各体展示了“本于性灵,归于自然”或抒发“性情之真”的品格,为后世树立了特别的典范;第三,从品论的角度,言志抒情的真实程度,决定了诗歌品格的高下,成为鉴衡诗家及其作品的一条重要标准。归纳诸说,其核心之义在于诗言“性情”以求真。诚然,放置在诗学史的层面加以观察,类似的见解在历来诗家或论家的主张中并不鲜见,由此,李维桢陈述的这些基本观点本身未必有多少新异之处,更多呈现的是诗学领域形成的某种共识。不过,这并不影响为探讨问题的方向所提供的导引意义,关键并不在于这些观点本身是否具有新创意义,而在于蕴含其中的申诉动机和理论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李维桢关注和同情七子派诸子的复古作业,甚至将明诗的盛兴主要归功于前后七子之作为,但身为经验者和见证者,他同时对诸子的复古实践和影响所及又不无疑虑。其《王奉常集序》指出:“自北地、信阳肇基大雅,而司寇诸君子益振之,海内诗薄大历,文薄东京,人人能矣,然大抵有所依托模拟。”[3]第150册,529示意诸子在引导“诗薄大历,文薄东京”的复古方向之际,也推助了文坛“依托模拟”的风气。其《吴汝忠集序》又指出:“嘉、隆之间,雅道大兴,七子力驱而返之古,海内歙然乡风。其气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厉;其格不得踰,故拟者失而拘挛;其蓄不得俭,故拟者失而庞杂;其语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诡僻。至于今而失弥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谓李斯之祸秦实始荀卿。”[3]第150册,559这又说明,七子从事复古虽有功于“雅道”昌兴,然另一方面也导致拟古流弊的发生,甚至因此成为世人眼中的始作俑者,问题两面性的然客观存在。不同于理论层面的一般推演,亦不同于常识层面的广泛宣示,李维桢亲历和见证了其时复古风气的流延变化,他的观点无疑更富有个人的经验性。在他看来,当时下作者将学古等同于单纯的模仿,乃至于形成一种风气,本身就偏离了复古的方向,有悖于学古的正当合理性:“盖今之作者争言好古,奉若功令,转相仿以成风,盛粉泽而掩质素,绘面貌而失神情。故有无病呻吟,无欢强笑,师其俚俗以为自然,袭其叫呼以为雄奇,字琢句刿,拘而不化,麋而虎皮,鸷而凤翰,迹若近,实愈远。”[3]第150册,517追究至具体的模仿目标,更能体察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在当时宗唐的背景下,士人习学唐诗趋之若鹜,伴随而来的则是过度模仿的后果,李维桢《唐诗纪序》云:
不佞窃谓今之诗不患不学唐,而患学之太过。……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称之,吊诡蒐隐,夸新示异,过也。山林宴游则兴寄清远,朝饗侍从则制存壮丽,边塞征戍则凄惋悲壮,暌离患难则沉痛感慨,缘机触变,各适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惧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于凄惋悲壮、沉痛感慨,过也。律体出,而才下者沿袭为应酬之具,才偏者驰骋为夸诩之资,而《选》、古几废矣。好大者复讳其短,强其所未至,而务收各家之长,撮诸体之胜,揽撷多而精华少,模拟勤而本真漓。[3]第150册,490-491
可以肯定的是,李维桢对学唐本身的合理性不持异议,如上他以水为喻而形容唐诗为“溟渤”“尾闾”,表彰其盛势,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之所以批评时人学唐诗风“学之太过”,还是质疑其习学不对门径。就此,他在《顾李批评唐音序》中又指擿当世学唐者:“盖今之称诗者,虽黄口小儿皆言唐,而不得唐人所从入;皆知唐有初、盛、中、晚,而不知其所由分。即献吉于唐有复古功,而其心力所用,法戒所在,问之无以对也。模拟剽剥,恶道岔出。”[3]第150册,493因为过分注重“模拟”,未免导致“本真”的流失,不仅达不到唐诗的妙境,而且面临诗道不正的风险。按此思路,当世学唐“学之太过”或谓之“不善学唐”,问题的症结在于未能合理借鉴古典资源,未能妥善处理学古与求真的关系,致使“模拟”侵蚀了“本真”。这种基于亲历和见闻而富有个人经验性的陈述,提示其并非只是简单原理或一般常识的绍介和宣说,而是寓含面向现实境况而激发的检省意识,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虽然李维桢强调“性情”说,以维持学古与求真的制衡关系,既要摆脱“野狐外道”,又须避免“小乘缚律”,以为“师古者有成心,而师心者无成法,譬之欧市人而战与能读父书者取败等耳”[3]第150册,724,其评他人诗作又声言“根于性情而润色之,事理不能违古人,而调格不欲类今人”[3]第153册,639,然以他之见,浮现当世诗坛的本质问题,并非习学古人的动力不足,而是学古方法的缺陷掩蔽了诗人真实性情的表现。其《端揆堂诗序》云:“今之时诗道大盛,哆口而自号登坛者,何所蔑有,要之模拟彫琢,夸多斗妍,茅靡波流,吹竽莫辨。试一一而覆案,其人性情行事殊不相合。”[3]第150册,720其《米子华诗序》又云:“诗至本朝嘉靖、庆、历之间,即唐人初盛时或所未逮。而顷者宿素衰落,后进多岐,业已沦于中晚。大抵尚雄奇而乏温厚,尚工巧而乏典雅,尚华赡而乏清婉。景不必其时所有,事不必其人所符,反之性情,迥不相侔。其下则任昉、沈约之贼而已矣。”[3]第151册,37有鉴于此,其围绕学古与求真关系所展开的诠释,有意识地凸显后者在二者当中的比重,强调性情表现的优先地位。他在《读苏侍御诗》中的相关陈述,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诗以道性情,性情不择人而有,不待学问文词而足。……自宋迄唐,则学问文词专用事,而性情廑有存者,流弊迄今,非但与性情不相干涉,即学问文词剽袭补缀,日堕恶道矣。吾乡二三君子起而振之,自操机杼,自开堂奥,一切本诸性情,以当于《三百篇》之指,虽不谐众口里耳,弗顾也。余尝谓以学问文词为诗,譬之雇佣,受直受事,非不尽力于其主人,苦乐无所关系。譬之俳优,苦乐情状,极可粲齿流涕,而揆之昔人本事,不啻苍素霄壤。何者?非己之性情也。独六朝人闺阁艳曲与俗所传南北词及市井歌谣,往往十五《国风》遗意,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此之谓性情,古今所同,是以暗合。盖无意为诗而自得之。其在宗庙朝廷所作,则学士大夫先有作诗意横于胸中,更仿古诗营构,故其诗受学问文词束缚,去《风》《雅》《颂》弥远。性者,天下大本。情者,天下达道。……诗本性情,而缘饰以学问文词。[3]第153册,622-623
“诗以道性情”,突出的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而“诗本性情,而缘饰以学问文词”,则指明诗以性情表现为主,学问文词缘饰为辅。诗人一己之真实性情,来源于“无意为诗而自得之”,毁损于“受学问文词束缚”。基于这一逻辑起点,李维桢追溯“自宋迄唐”诗歌史的演递轨迹,分析性情表现以专于学问文词而趋于弱化的走势,再审视诗坛的变化现状,指示流弊所及,性情表现已是沦没,加之学问文词出自模拟,终究难免“剽袭补缀”,遂致诗道堪忧。与此同时,他又注意到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在当时诗坛的作为,文中所标举的“吾乡二三君子”,即指“袁中郎、苏潜父兄弟”。他之所以将袁宏道等人视为于诗坛有振起之功者,看重的无非是袁氏等人“一切本诸性情”,认为如此正可以直承《诗经》性情表现之历史传统。这不能不说是李维桢跨越七子派的派别身份,重新检察当世诗坛的变化格局。尽管在“性情”内涵的理解上,李维桢偏重于“人伦物理、日用常行”[3]第153册,622,且以《诗经》风教精神为基本宗旨,这与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基于自然本性而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9]187的论调明显不同。[9]386-388但受以性情表现为优先选项的理念的驱使,显然他视袁宏道等人为在诗歌本质的认知上具有某种共识的合调对象。与此相关,他的《郭原性诗序》评诗友郭氏之作,谓之“大要感事而发,触景而出,矢口而成,信腕而书,慷慨激昂,欢愉胜畅,哀悼凄紧,忿恚乖暌,率皆情至之语。世人诗如强笑不乐,强哭不悲,属对次韵,剽剥缀葺,与其中之灵明、外之遘合,了不相蒙,一切结习,澄汰都尽”[3]第150册,744。又说:“迩日公安、江陵诸君子,称诗能于《三百篇》外自操机杼,无论汉魏、六朝、三唐。今得原性羽翼接响,维楚有材,讵不信哉?”[3]第150册,744也间接传递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袁宏道等人的信息。
五、结语
李维桢将汉魏、唐代及明代诗歌树为承继《诗经》传统的三大高峰,体现了他对诗歌发展演进历史的明晰勾画和定位,如果说尊尚汉魏、唐代诗歌更多本于某种经典意识,那么标举明代诗歌则不无张大其诗史地位的企图。无论如何,这些应该与他作为后七子新生代成员的派别身份和同情七子派诸子复古作业的基本立场相关联。汉魏、唐代诗歌原本即是诸子所推重的经典文本,而对明诗盛兴之格局的主观判断,则又与他凸显前后七子在有明诗坛的历史作用的根本用意相绾结。然而,对于诗歌演化史这样一种简略而明晰的勾勒,并不能完全代表李维桢面向不同历史时期诗歌品格所作的辨别,包括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宗尚目标,情形则显得相对复杂,这一复杂性也恰恰昭示了李维桢与七子派诸子之间表现在具体诗学观念上的共识及分异。有关的问题尚不止此,从另一层面来看,如此的共识与分异也反映在李维桢关于如何合理利用古典资源问题的阐说,诸如作为诗学基本命题之一的学古与求真关系的问题,由此成为他关注和诠释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在这当中维护学古习法的正当性或合理性,显示了他向七子派诸子复古立场的靠拢。但又必须看到,不啻是出于制衡的策略,更是鉴于诗坛变化的现实趋势,面对诸子从事的复古实践及其发生的负面影响,李维桢的相关反应又是十分谨慎而有所戒备,令人明显觉察到其因此激发的富有针对性和经验性的防范意识。也基于此,他强调诗歌发抒“性情之真”的重要意义,并以性情表现作为优先选项,淡化学古习法的苛律细令,乃和诸子的有关主张比较起来又有主于一己的相应变改,突出反映了在如何利用古典资源这一关键性问题上的自我认知,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带有应对明代中后期诗坛变化格局的强烈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