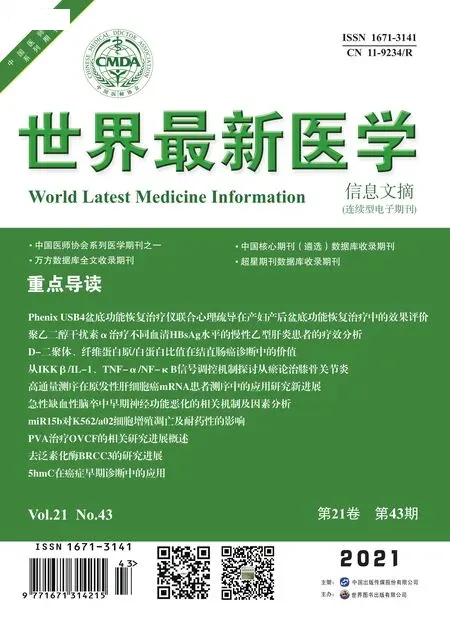自拟疏肝解郁方治疗老年郁证的临床经验举隅
黄娟,刘进进
(1.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1;2.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1)
0 引言
元·主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五郁论》中说:“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张氏通医》卷三:“郁证多缘子志虑不伸,而气先受病。”揭示了郁证与情志不舒相关,以气郁为首要表现。西医认为“焦虑状态”,即是有明显焦虑情绪,如烦躁、易怒、紧张等,通常伴有睡眠障碍以及一些植物神经紊乱的症状,如心慌、乏力、出汗等的一种状态。中医认为因焦虑状态的成因及症状表现符合郁证的特点,故此病归属“郁证”范畴。
老年人郁证多是因为对逐渐下降的身体机能的不适应,如体力下降、代谢减慢、激素水平紊乱等,表现为对外界和体内环境改变的适应能力减低,从而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没有及时得到舒缓而进一步影响身体机能,便形成了一种疾病状态。
1 因机证治
1.1 病因病机
《景岳全书·郁证》云:“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中医学认为“郁证”,是由情志不畅、气机郁滞所致,其与肝关系最密,依据脏腑间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心脾肾亦受累。肝疏泄失常,气机郁滞,肝木克脾,则出现脾不升清,运化失常;肝郁化火,火性上炎,上扰心神,故见心不守神;肝气郁结,藏血失司,疏泄失职,基于肝肾同源,肾封藏失度,藏精不能,故见肾亏精少[1]。现代医学认为“焦虑状态”病因复杂,其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表明多是存在着身心两方面的病理过程,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通常由外伤、严重疾病、不良的健康状况、压力积累等诱发[2]。
1.2 证型
郁证之病,肝失调达,气机不畅,肝络失和,故见腹胀、胁痛,肝气犯胃,胃失和降,故见脘闷嗳气,肝气乘脾,脾虚不运,故见腹胀,此为肝气郁结之证[3];气本属阳,郁久化火,横逆犯胃,胃肠内热,故见口干而苦,大便秘结,火性炎上,上犯头目,故见头痛、目赤,此为气郁化火之证;肝郁乘脾,脾失健运,水液停聚,生湿成痰,痰凝咽喉,故见咽部异物感,难咯难咽,此为气郁痰凝之证,上述诸证,从一而终,贯穿肝郁。王伟斌等的基于古今医案的郁证辨治规律研究[4]表明现代郁证以肝郁气滞为主,现代郁证的分型论治紧扣病机,以疏肝、理气、解郁为主要治疗原则。综上不论古代医考亦或是现代科研,郁证证型皆是气郁为主、气郁为先。
1.3 治法
刘师在临床辨证用药时针对老年郁证患者的治疗除了考量病因病机,还将体质特点和年龄特点纳入考虑。邓玮瑜等[5]的焦虑、抑郁状态与中医体质的研究表明,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与焦虑状态有关,其中湿热质、阴虚质与焦虑状态独立相关。老年人的年龄特点决定其体质偏弱,代谢减慢的用药表现,故用药宜少而精。自拟疏肝解郁方中多为性温之品,能行,能散,非大热以助气妄行,力稍缓但效甚专,理气、行气之效重在持久而缓和,达郁而不伤正。五味属性多为甘味,甘味能补,能缓,从食入五味而言,甘味入脾,防止肝旺传变克脾土,故补脾则肝自愈,从五味运动转化而言,辛甘为阳,发散向外,解郁尤甚。方中诸药多入肝、脾经,肝失疏泄,经气郁滞,气逆犯脾,脾失健运,脾虚气弱,故药用补脾之品,以达补脾治肝之效,将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体现尽致。
《证治汇补·郁证》中说:“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开提为次,至于降火、化痰、消积,犹当分多少治之。”故治疗理应以疏肝解郁为准则。刘师自拟疏肝解郁方为逍遥散基础上依据辨证论治施以加减化裁,加入合欢花、玫瑰花、砂仁等行气之品,黄芪等补气之品,自拟方中包含柴胡、合欢花、玫瑰花、砂仁、黄芪、炒白芍、当归、炒白术、茯苓、炙甘草等味。
2 案例分析
2.1 初诊(2019年11月18日)
患者程某,女,53岁,自诉因“间断上腹部隐痛3年”于我院脾胃科门诊就诊,查电子胃镜提示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I级),hp呼气试验阴性,间断予抑酸护胃、中药辨证方口服等药物治疗,上腹部隐痛时有反复,患者遂来老年病科求医,刘师问诊后得知患者除间断上腹部隐痛外,伴嗳气,喜叹息,偶有胃脘部冷感,近3月时有出汗,呈阵发性出汗,偶有入睡困难,无恶心呕吐、反酸烧心、咽部异物感、腹胀腹痛,无发热、咳嗽咳痰等不适,食欲欠佳,二便可。舌脉:舌淡红,苔薄白腻,脉弦。月经史:平素月经规律,经量正常,近半年月经不规律,末次月经2019年9月30日。中医辨病为郁证,肝郁气滞证,西医诊断为焦虑状态。拟以“疏肝解郁,行气散结”为治法,方药具体如下:柴胡10g,炒白术15g,茯苓15g,砂仁6g,合欢花10g,玫瑰花10g,黄芪30g,太子参15g,川芎6g,炒白芍10g,当归15g,干姜6g,白及10g,炙甘草10g,7剂,以200mL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温服,并嘱患者畅情志,规律定时入睡,睡前减少刺激性娱乐活动。
按语:患者上腹部隐痛日久,予以中药联合西药对症支持治疗后,症状稍缓解,仍自觉偶有上腹部隐痛、胃脘部冷感,伴嗳气,喜叹息,近期有阵发性出汗,偶有入睡困难,结合患者电子胃镜结果、月经情况及年龄阶段特点,中医辨病为“郁证,肝郁气滞证”,舌脉从证。西医诊断考虑为“焦虑状态”。刘师以疏肝解郁,行气散结为法,遵从“行气不耗气”的治疗准则,方中以柴胡为君药,其性升散,起疏肝解郁之效;臣以合欢花、玫瑰花佐柴胡,三者相伍,疏肝行气解郁,佐以川芎,倍增行气之效;患者常因病势缠绵,病程长久,加重焦虑情绪,再者湿性重着粘腻,难以速去,其势趋下,炒白术、茯苓二味健脾渗湿,令湿走下焦;砂仁性温,功于健脾和胃行气,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源不断,则周流不息,患者偶有胃脘部冷感,配伍干姜辛热之品,温中散寒;《难经·八难》中写道“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故添黄芪补气固表,配伍太子参健脾益气;《景岳全书·血证》说:“人有阴阳,即为血气。阳主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人生所赖,唯斯而已。”方中妙用炒白芍、当归疏肝养血,联合玫瑰花和血之效,补血不滞血,行血不伤正,白及收敛止血,研究表明白及主要成分白及多糖可以增强胃黏膜屏障作用,促进黏膜修复[6],为治疗慢性糜烂性胃炎要药,以上诸味共为佐药;炙甘草为使药,调和诸药兼健脾益气。
2.2 二诊(2019年11月25日)
患者诉上腹部隐痛稍缓解,仍有胃脘部冷感,伴嗳气,喜叹息,偶有出汗,食欲不振,睡眠欠佳,偶有入睡困难,二便可。舌脉:舌淡红,苔薄白腻,脉弦。
辨证分析:患者自觉胃脘部冷感,此为寒凝胃腑,宜加性温之白芷,解表散寒,佐干姜之温中散寒,表里共奏;因于“胃不和则卧不安”,更加神曲健脾消食和胃,茯神、首乌藤宁心安神。又因患者上腹部隐痛稍缓解,故减轻补气行气之力,去太子参、川芎二味。
治法方药:中药守前方基础上增加神曲15g,白芷10g,海螵蛸20g,茯神20g,首乌藤20g,砂仁改为10g,茯苓改为30g,去掉太子参、川芎,7剂,以200mL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温服,并嘱患者畅情志,规律定时入睡。
2.3 三诊(2019年12月02日)
患者诉上腹部隐痛、嗳气较前缓解,出汗较前减少,食欲不振,睡眠欠佳,二便可。舌脉:舌淡红,苔薄白腻,脉弦。
辨证分析:患者自觉食欲不振,此为脾胃之气运化失常,理应增强健脾和胃,故配伍鸡内金,因胃脘部冷感好转,故去干姜,防止过于辛热以灼伤胃阴,损伤胃气。
治法方药:中药守前方基础上增加鸡内金15g,去干姜,减当归剂量为10g,14剂,以200mL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温服。
2.4 四诊(2019年12月16日)
患者诉上腹部隐痛、嗳气明显缓解,纳食、睡眠欠佳,二便可。舌脉:舌淡红,苔薄白,脉弦。
辨证分析:因“血能载气”,气畅则郁自舒,故配伍延胡索活血行气,偏重活血,载气周游,疏解肝郁。
治法方药:中药守前方加延胡索10g,7剂,以200mL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温服。
2.5 五诊(2019年12月23日)
患者诉上腹部隐痛、嗳气缓解,纳食、睡眠较前改善,二便可。舌脉:舌淡红,苔薄白,脉弦。
辨证分析:患者诸症好转,气机畅达,肝郁之候得解,增川芎、减延胡索以偏重行气之功,增羌活以祛风胜湿,助茯苓、炒白术湿从表解。
治法方药:中药守前方增川芎10g,羌活10g,去延胡索、白及、茯神、首乌藤,14剂,以200mL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温服。药毕后复诊,未诉明显不适,病症愈。
3 结语
郁证多是由肝气郁滞为先,进而出现肝郁化火证、气郁痰凝证。因老年人偏湿热、阴虚的体质特点及其代谢减慢的年龄特点,郁证在老年人中极为常见。刘师自拟疏肝解郁方为治疗老年人郁证经验方,其药味精简,药量考究。全方既得逍遥散疏肝解郁之长,又添黄芪补气,合欢花、玫瑰花疏肝行气,使气畅郁舒,肝气调达。在临床应用时,应重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力求把握疾病本质,考虑个体差异,治疗分清主次先后,章法有序,灵活多变方能起沉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