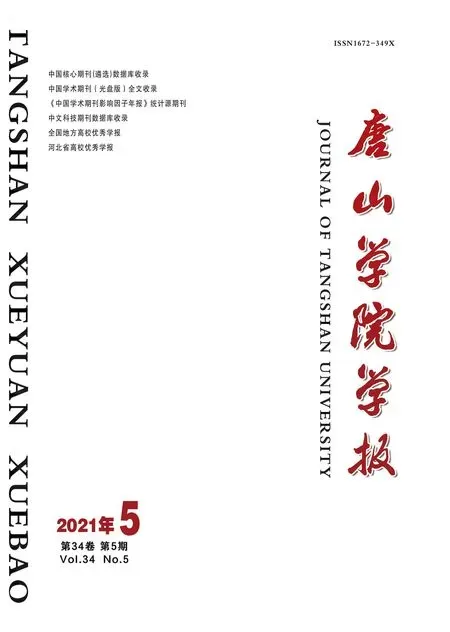张翀谪戍黔中事迹考略
陈为兵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张翀(1525-1579年),字子仪,广西柳州人,人称鹤楼先生,又号浑然子。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授刑部云南司主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因上疏弹劾首辅严嵩父子不法而被下诏入狱,后谪戍贵州都匀。值明穆宗即位,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张翀得以释归,被召为吏部稽勋司主事,历考功司员外,转文选司郎中,晋太常寺少卿,迁大理寺少卿,出抚福建,移抚湖广,因功晋大理寺正卿及得兵部右侍郎衔,以侍养归家。万历二年(1574年)起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万历三年(1575年)任满入为刑部右侍郎。万历四年(1576年)上疏致仕。万历七年(1579年)卒于家,赠兵部尚书,谥号忠简。
张翀谪戍都匀首尾十年,静心修学,开办私塾,广收门生,游览黔中山水,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名篇,为都匀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与王守仁、邹元标合称“黔中三迁客”。
一、黔中交游:但得余生赐恩放,不妨长卧白云边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召回前朝外放官员,张翀也在其列。多年之后张翀在老家广西柳州写下《广中忆贵竹诸友》:“思君明月转凄然,柳水盘江各一天。别后久稽南国信,归来重理故山田。幽怀魏阙三千里,喜庆高堂八十年。但得余生赐恩放,不妨长卧白云边。”[1]111表达了对谪戍贵州期间与诸友的十年之情和对曾经岁月的怀念。
与王阳明一路被追杀以及受到贵州当地官员监视和刁难不同,张翀谪戍历程算是波澜不惊的,初到黔中不但没遭到当地官员恶意相待,而且还不断有官员来探望并提供必要的帮助。这里有“岁戊午,余薄谴戍兹土”就“意厚而礼谦,不以显晦异态,朝夕问慰,无间寒暑”的贵州通掾、卫指挥使司松坪史君[1]36(《送经卫松坪史君序》),有由贵阳督学提升为湖藩大参“便道访余戍境,盖悯余之未闻道、未尝学”的万士和万履庵,也有“卜日命匠,然不使余知之”相与修葺读书堂的千户侯韩梦熊、王尚武以及军政使娄拱辰等政府要员和读书人,还有“不约而同,各捐金募工”给张翀在龙山之上修建龙山道院的霁川司君抚、月泉刘君镗等人,更有“当余之戍贵阳也,公来存之,泪渤渤下,赠之金而余辞焉”[1]65的黄雪峰先生,等等。可见,当时的黔地官员对张翀是百般抚恤和体贴,这固然与张翀本人学识渊博、有极好的人际口碑相关,也与严嵩力所不逮、在边疆地区触角不深有关。张翀从京城出发时朝中众多官员不但相送而且还赋诗相送的事实,也足以说明严嵩虽为权相,但其权势未能达到让朝中众臣俯首帖耳乃至噤若寒蝉的地步。
张翀在贵州期间几乎所有的贵州军政要员都与之有来往,从诗文互赠情况来看,也绝非一般的公务式交往,而且这些要员很多与张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朝中早就共事,或京城早就相知,或是同门故旧,抑或是同乡,这样的社交圈子毫无疑问为张翀在贵州提供了远比王阳明宽容多的活动空间,也为他潜心治学、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
在张翀现存诗文中,对所涉及的众多官员当属戴浑庵着墨最多,有文一篇、诗十一首,足见两人在贵州交往之频繁和情谊之深厚。戴浑庵早于张翀九年考中进士,与张翀同在刑部任职,两人志趣相同,对待朝政心领神会,所谓“朝夕得与议论,其中领要处有不约而同者也”[1]34,足见两人同为刑部郎中政见一致,配合十分默契。又加之戴浑庵也是因为忤逆严嵩,被外放贵州佥事(宪副)。在张翀抵达都匀第二年的冬天,他“以秋官郎出副贵臬,饬理都清戎务”,与戴浑庵异地相见,两人惺惺相惜,“岁暮天涯客,相逢有夙缘”,自然是“相见辄话往昔,无异在秋官时也”,并且“采蒿仍秉烛,话旧却忘眠”。但让张翀没想到的是,戴浑庵在贵州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放弃了“德威大布,上下属望甚殷”的大好局面,以身体抱恙为由毅然决然挂冠而去,全然不顾贵州巡抚、按察使、藩司和臬司等各级官员以及士大夫和百姓的苦苦挽留,而且临行未带贵州一针一线,只带走了赴任时所带的书籍资料,显示了他不留恋官位和富贵的高洁品质。作为知己,张翀在震惊、惋惜之余也对戴浑庵的行为表示了充分的理解,认为是“归而明道”,与古人无异,无可厚非。
他乡故知,流云有意,终是难忘冬日与戴浑庵坐在江滩谈天论地的场景,因此张翀接连写下了《送戴浑庵告病东归》四首诗,表达了彼此之间的伯牙子期之情和恋恋不舍。
除了这些官员之外,在黔中还有一大批跟随张翀的书生。张翀在都匀期间,当地书生争相上门拜访,执经求忝弟子之列。张翀亦“每吟诵少暇,即与诸生司子推辈搜奇于山水之间”[1]53,其渊博的学识深受诸生爱戴,并为其在都匀修建了龙山道院。据吴维岳《鹤楼集叙》记载,龙山道院修筑完毕后,都匀书生每天跟随张翀同游,将其所吟诵诗文记下,日积月累,遂成一书,但书生无力将其刊印,于是就在龙山半山腰中择一倒地的梨树刻之,由此生出一段文坛佳话,也说明了张翀在都匀书生中受爱戴的程度。
在都匀书生中,被张翀诗文提及的能确定的有霁川司君抚以及月泉刘君镗、孙亭、宋治、徐应翼、张芦江、张蓉江等,其中跟张翀感情最深的当属徐应翼。从《哭徐生应翼文》[1]28来看,徐应翼应该是在张翀初到都匀之时就带当地读书人上门拜师的第一人,在当时还不清楚张翀背后潜在的政治风险就做出这样的举动确实有点莽撞,但也反映了徐应翼拜师求学的心切和对张翀发自内心的敬重。徐应翼“颖悟超出,志气不凡”,被张翀视为“西南奇士,他日大鸣于海内者”,他不但经常与张翀“登高观溪,坐月吟风”,坐而论道,而且还持师生之礼甚敬,在张翀夫妇生病之际亲自端汤送药,早晚侍奉。可以说张翀跟这个学生,不但在学术上志同道合,“上自盘古以迄于今,明而礼乐,幽而鬼神,以达于人物、事变、典籍、文字,靡不旁及”,而且在感情上更是情同手足,“余别家兄于杨老道,把袂泫然,子复下坂,涕泗而慰余”,说明二人之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正因如此,徐应翼的突然离世,让张翀悲痛不已,写下了《哭徐生应翼文》,将徐应翼比作颜回,表达了自己对这名门生才华和修养的肯定和无尽的怀念之情。
当然跟张翀交游的黔中官员和书生也绝不仅仅有这些,诸多史书记载了都匀士人争相跟随张翀的事实,龙山道院和读书堂就是都匀各界人士通力合作专门为张翀修建的,可见黔中人民对张翀的厚待和尊敬。也正是这些交游对象的友善和关怀才让张翀得以“旦夕荷殳从其长,役役不倦;暇则逍遥图史,吟咏以自娱”[1]68,学业精进而未受干扰,因此离开黔中时用《别贵竹诸友》一诗表达了恋恋不舍之情:“十年与君游,千里与君别。把袂意不言,含杯气欲绝。渐隔潇湘云,空留夜郎月。一曲钟期弹,知音对谁说。”[1]35
二、黔中印象的改变:谁云多瘴雾,山水更清奇
贵州地处西南,自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出,贵州就被冠以“夜郎”之称,又加以长期游离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外,交通闭塞,文明未开,更是被进一步污名化。明代虽然建省,开启了改土归流的进程,但贵州在中原人士心目中依然是过去的“夜郎”,将被派往贵州视为生死之旅,“宇内往往少黔,其官于黔者,或不欲至,至则意旦夕代去”,即使做官也无人肯去,一旦有人万不得已赴任,也是如大难临头、生离死别一样。王阳明在《瘗旅文》中描写那个从中土到贵州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与仆人先后掉下悬崖死于非命的小官吏“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2]就是当时中土之士普遍心态的真实写照。非但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连祖先从中原迁至贵州后出生的读书人也瞧不起贵州,在外人面前羞于提及自己的户籍所在,尤其考中科举做了官后,更是怕人瞧不起而把先人在中原的户籍拿来登记造册,生怕贵州玷污了自己的名声,由此可见贵州在当时读书人心中的地位。
在张翀到都匀的初期,其诗文中“夜郎”一词也频频出现,而且他对当地印象极差,认为黔中“僻在广贵之冲,土酋牙列,岁相仇夺无宁日”,是“瘴疠频作”之地。“瘴楼”“罗施国”“荒戍”“瘴乡”“蛮夷”“蛮烟”等词也屡屡见诸笔端,反映了张翀谪戍初期对黔中的印象,这也跟其早期接触的中原汉族正统教育有关。这种对贵州的认知不仅体现在张翀身上,而且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同认识,譬如在张翀离京之际,他的同事刑部郎中李价就说贵州是“瘴色诸蛮暗”“古来投窜地”,他的另一个同事刑部郎中高岱则更干脆,直接说贵州是“炎荒地,吾人不宜居”,这些典型的华夷思想都给张翀造成了对贵州先入为主的印象。
但随着时间的深入及前文所述的张翀与贵州各界人士的交游,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发生了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张翀并非一人来到贵州,而是有家人相伴。给事中林应麟和吏部主事万士和的赠诗中“抗疏辞轩冕,携家入瘴烟”“一封奏事排天阙,数口携家入瘴乡”等句也说明了这一点,尤其《哭徐生应翼文》记载的“往岁余与内人有疾,子昏旦候于门外”和《除夕》中“边戍家何在,慈闱望独频。寒灯妻共语,椒酒仆重申”等诗文更是证实了至少张翀是和夫人一起生活在都匀的,所以尽管对贵州有种种的偏见和初来乍到的各种不适,有家人在旁总比他的前辈王阳明孤身一人好些。而且张翀在赴都匀之前就把其他家人安排到老家柳州,柳州距都匀并不远,其间其兄还专程来都匀探望张翀,《喜家兄至都匀》《秋日同家兄并诸公坐江沙和韵》中“今宵万里情无限,解剑风前共倚楼”“更喜白眉千里至,共看明月刀沧州”等诗句表达了他对亲人到来的无以言表的喜悦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排解了张翀对贵州的负面印象。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来自贵州各界人士的关爱和当地淳朴的民风。这种关爱来自当地官员,也来自当地书生,前文已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都匀当地普通民众对张翀的态度。据张翀《读书堂记》记载,在张翀不知情的情况下,千户侯韩梦熊、王尚武和军政使娄拱辰及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修葺读书堂时,都匀人民也自发参与进来,“各执锸争相来助,或以瓦,或以木石”,能出力的出力,能出物的出物,一座崭新的读书堂就建成了。都匀人民对中原来的读书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情让张翀大为感动,这自然改变了其原先的“蛮夷”之见。张翀将都匀人民这份情谊与苏轼在儋州时当地人“诛茅筑土,特作屋以居公”[1]2相提并论,认为自己并非“子瞻一代伟人”,都匀民众如此敬慕确实让自己受宠若惊,甚为感动,自此像苏轼一样“日与其父老子弟吟咏从容”,让读书堂成为都匀百姓读书之所。
除此之外,当地百姓还尽最大可能地在生活方面对张翀予以关怀,而且也表现出了对张翀的极大尊重。但凡官员升迁,当地人士即使长途跋涉也要上门求序,都以得到张翀的墨宝为荣,可见张翀的声望之高和当地人对文化渴求之强烈。“都匀士咸知爱重公,每获公文,视同拱璧”[1]2,这种争相读书的风气也让都匀在当时“风教寖明,异傍郡”[1]2,这其中有张翀很大的功劳,也刷新了张翀对贵州的认知,贵州再也不是他原来心目中未开化的蛮夷之地了。
最后,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也让张翀越来越喜欢贵州。在张翀踏足的黔中地带,龙山对于他来说,正如王阳明之于栖霞山;龙山石室对于张翀的意义正如王阳明之于阳明小洞天。从这一点上来说,龙山不仅是都匀一处自然景观,而且也是一处因张翀的到来而形成的人文景观,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龙山,原名蟒山,张翀经常携诸生在此游历,因山上有一处飞泉,呈龙青色,故将之更名曰龙山。当然这种更名能得到都匀民众认可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而是因为众人为张翀在此修建了龙山道院,张翀在此开门授徒,著书立说,让此山成为一座文化名山。龙山就在都匀河对面,“雄峙崔嵬,其高插天”“山势逶迤数千里,群山俱出其下,徘徊四望,南尽交广,北极湘汉,西连滇蜀,皆在目前”[1]53,让张翀叹为观止,发出了“壮哉观乎”的赞叹,随之也萌生了在此结庐而栖的想法,这一想法在霁川司君抚和月泉刘君镗的张罗之下得以实现了。
从《龙山道院记》可以得知,张翀对龙山及龙山道院是非常满意、喜不自胜的。道院周边泠然洁泉,古木藤萝,清风万壑,乌猿白鹇,白云常入其间,无不让张翀心旷神怡,宛若身处霄汉,并认为自己从数千里之外的地方来到此地栖身而居是天意,“结楼于中,遂为一方胜概”,可见张翀是非常得意的,以至于他在陪贵州督学况丹湖登龙山时是这样夸耀的:“晴空万里一高峰,山势南来似卧龙。秋霁白云归古洞,月明玄鹤下长松。泉飞石磴珠帘卷,树拥楼台紫翠封。坐对美人发幽况,乾坤何处是孤踪。”[1]103
张翀如此钟爱龙山,登龙山顶可以“峰高天上游,扪萝飞绝壁,促席宴危楼”(《九日登龙山》),还可以发现丹台,此物如“九龙飞玉舄,千丈落瑶台”,亦如“伫脚蒲团大”,如此仙境,“洞箫骑鹤子,何事不归来”?(《龙山顶偶搜一丹台甚奇纪之》)当然龙山对张翀来说,不单单有心旷神怡的景致,而且还有淡淡的乡愁和忧伤,龙山落叶,夜间笛声,粗狂醒醉,溪畔踟蹰,秋风吹发,石室独坐,可以说,龙山承载了张翀在贵州所有的情结。龙山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他遨游书海、静心凝虑、修身养性、发展心学的重要场所。
除了龙山,张翀还去过贵州其他很多地方,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也给这里的山水留下了自己的文化印记。如游都匀东山,山间清泉潺潺,让张翀心生顿悟,在泉水旁崖壁之上书写了“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谷,饮此泉水”[1]62之语,东山因此生色,名声大噪,成为一道人文名胜,深深烙上了张翀的心学印记。
再如,张翀还去了王阳明游历过的贵阳来仙洞,也赋诗两首,王阳明的两首诗分别是写春季和秋季的来仙洞,张翀则写秋季来仙洞游玩的一来一回。与王阳明两首诗中流露出的对道的追求和思乡之情不同,张翀两首诗表达出来的完全是一派恬然自适的情怀:《秋日游来仙洞舟中集事》描述的是他与朋友一起泛舟水上,撒网捕鱼,举杯畅饮,美色相伴,“朋辈连航至,悠悠点也俦”;《来仙洞归来醉笔杨安主人楼》则主要写游玩归来在杨安楼上“一饮百斗不自知,醉眠楼上天河卑。明月在户清风吹,赤脚欲伸星斗随”的酣醉和飘飘不知何似的逍遥自得。可以说,继王阳明之后这两首诗给贵阳来仙洞又添了一笔浓厚的文化色彩。
三、都匀龙山悟道:文则根极性命,诗则止于礼义
《浑然子》为张翀谪戍都匀所作,共十八篇,分别为《神游论》《田说》《樵问》《将》《明心》《士贵》《体用论》《兴废》《祸福》《忠孝》《变化》《穷理》《求知》《弭盗》《用材》《强弱》《臣道》和《高洁》。张翀自号浑然子,浑然即混沌、浑沌的意思,是中国文化中宇宙形成之前的一种状态,老子、庄子、柳宗元等均有论述,其实就是探索世界本源问题,张翀以浑然子冠名其自创的十八篇文章也有探索宇宙和人性之理的用意。
正如王阳明修文龙场静坐阳明洞悟道一样,张翀亦独坐都匀龙山石室,连续七天不言、不动、不视、不听,心游于天地之外,做到了“极言、极动、极视、极听”[1]9,《神游论》大有庄子《齐物论》之风,“光照不必乎日月,润泽不必乎雨露,变化不必乎风云,流峙不必乎河岳,积注不必乎河海,代谢不必乎四时,飞动生杀不必乎鸟兽草木。吾惟不动,是以极天下之动;吾惟不言,是以极天下之言;吾惟不视,是以极天下之视;吾惟不听,是以极天下之听”[1]9,足以证明神游就是庄子的逍遥游,而且《神游论》亦采用王阳明《传习录》师生问答方式,认为人眼看到的天地并不是自己心中的天地。“高而未始高,明而未始明,厚而未始厚,博而未始博,是天地也。是天地也者,吾衷也”,此凡事心中求的穷理态度,与王阳明“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足以证明张翀的心学倾向,这也是陆王心学发展下明代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话题。
这种心学倾向在《浑然子》其他篇目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明心》认为“有志于天下国家者,必先明诸心。能明诸心,天下国家可从而理也。不明诸心,而欲有为于天下,譬诸操不舵之舟,以之航海,鲜不覆矣”,而明心的要义在于“静以观之,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1]12。
《体用论》则提出“无动无静者,心之体也;有动有静者,心之用也”[1]13,表面上看是对王阳明“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的否定,其实不然,张翀和王阳明二人关于动静体用的论述都是基于对“心以静为体,以动为用”之说的批判。《体用论》用“车轮动而辕静,其体存乎毂”“磨盖动而盘静,其体存乎枢”“水流动而止静,其体存乎源”“舟楫以利涉也,济则动,不济则静,舵非其体乎”“权量以度物也,用则动,不用则静,星非其体乎”等例子中的“毂”“枢”“源”“舵”和“星”不正是比喻心吗?车辕、磨盖、水流、舟楫、权量的动静与否,是无关“毂”“枢”“源”“舵”和“星”等“体”的,这也正说明心是无关动静的,这和王阳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谪戍都匀是张翀难得的一段闲暇时光。在这一时期里,张翀可以息心凝虑,对宇宙、对人生、对政事等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静心著书立说,并用寓言的形式表达出来,《浑然子》“皆设为主客问答,旁引曲证,以推明事物之理”,这和刘基创作《郁离子》时的宗旨是相似的。
如《樵问》由张翀居滃菁之山与虎为伴而不相害得出“夫物不相忘而后相惧,相惧而后相害”“夫物相忘而后不相惧,不相惧则不相害”[1]11之理,显然是从自己谪戍经历得出来的朝臣处世之道。又如《高洁》显然也是就谪戍而言的,文中的林先生结茅挂席而居陋巷之中,本来就家徒四壁,孰料东里野人饮酒失火殃及其庐,里人出于怜悯之心为林先生修好了草庐并提供了一些生活用品,但林先生却以为这样让自己失去了“未尝有一物”之本有,于是“徙于深山之中,就岩石而栖,种苜蓿而食,终其身不求于世焉”[1]22,此为“处困而能不失其本”,显然是张翀自喻,是其被放逐几千里之外的一种心理自适,是警告自己身处谪戍困境也不能忘掉立身之本,这种心态也是在张翀诗文中除了偶尔流露出思乡之情之外难以见到牢骚愤懑之语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张翀还就君臣之道、为将之道、兴废之道、士贵之道、祸福之道、忠孝之道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张翀认为,作为君主一定要吸取秦朝“用商鞅之术,虽足以霸秦,而民有所不堪”而导致民众揭竿而起的教训,治民欲速则不达,宜“纾而不迫,为而不强,渐磨以仁义而不责之旦夕,维持以刑罚而不督之苛刻”[1]13,从而“天下不自知其入于治矣”;轻赋薄税是治乱之本,招徕辑亡是弭盗之源;为君者用材应该“用其所长而弃其所短,则天下皆材矣”,如“反其所短而违其所长,则天下皆无材矣”,那就是为君者的过错了。反过来作为一个臣子,也应尽臣道。张翀心中的臣道就是,作为一个臣子应该纯诚而公,没有一毫私意,有至诚之念和至公之心,“至诚则足以格君,至公则足以谋国”,此为为臣之道。
关于为将之道,张翀认为一个将领不但要有知战之道,而且还要得民之心,“同甘苦以结之,明赏罚以一之,壮威武以作之,严纪律以齐之,用才智以服之”,不仅如此,还要专和信,“忠可以贯乎金石而后主不疑,诚可以动乎鬼神而后相不忌,德可以服乎群议而后众不挠,望可以著乎中外而后权不分,如是则可以戡乱而成功”,“由知战之道至于戡乱而成功,则能将矣”。正是因为对为将之道有如此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张翀才在离开都匀回京复职后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官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期间,他指挥守备董龙剿灭了万羊山之乱,为平定广西古田出谋划策,平定南雄巨盗黄朝祖之乱,得到朝廷的认可,倍获褒奖,“到湖广一地,拜为大理卿,又为兵部右侍郎”[3]。
可以看到,除了心学思想外,张翀在《浑然子》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道理,这也足见其在都匀期间之学业精进和思考深入,丝毫不见谪戍给一个文人带来的惨痛和悲伤,这也验证了张翀在《问月赋》中假借素娥之口对自己发出的“苟前修其惘玷兮,亦奚愧于光明。絙千古以流辉兮,尚毋怠于斯征”的告诫和勉励之语。
四、结语
谪戍对于任何文人或官员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但若能够融入其中,乐在其中,这种不幸就会促成人生的转变,张翀即是如此。在贵州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张翀迅速改变初至贵州时的失落和痛苦,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蜕变,这种蜕变不但表现在张翀在贵州潜心治学、开门授徒、著书立说,还表现在他迅速融入贵州本地生活。“平生爱看山,到山便不去”的秉性让他迅速爱上贵州的山山水水。贵州山水是一种精神皈依,也为他的哲思和诗文创作提供了场所,同时他的到来也为贵州山水增添了不少的人文色彩,对于贵州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