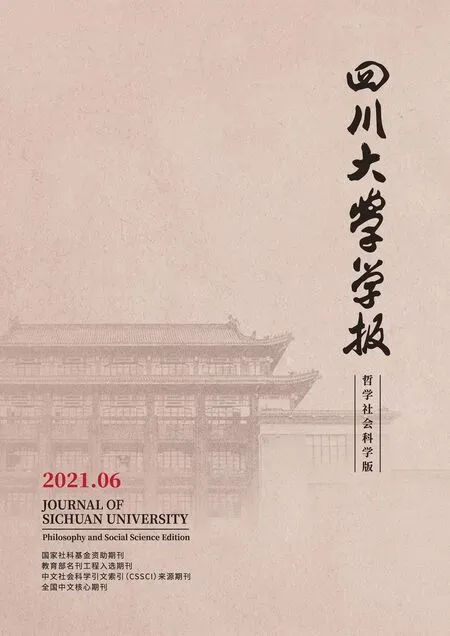在相对与绝对之间
——伯林和施特劳斯的比较研究
黄梦晓
一、引 言
人们通常认为,20世纪两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和列奥·施特劳斯是一对冤家:一个是维护现代多元价值的狐狸,一个是推崇古典自然正当的刺猬。施特劳斯批评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容易滑向相对主义,伯林讽刺施特劳斯拥有一双看到绝对真理的“魔眼”。的确,伯林和施特劳斯的主张存在差异,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受20世纪二战和冷战共同时代背景的影响,二人观点具有的某些相似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伯林和施特劳斯都对道德与政治哲学中的个人自由或者不同观点如何共存的问题进行了深思。可以说,二人都对那种普遍性观念或单一完备性原则持怀疑态度,根据该观念或原则,人们认为通过将不同价值和目的放在一个和谐的等级秩序中进行排序,可以为人类道德和政治冲突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终极的解决方案。但是,二人对于如何避免这种普遍主义或一元论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伯林选择了价值多元主义,“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和他的消极自由概念相一致,最终还是难以避免在习俗和意见中走向真理的相对主义;施特劳斯选择了苏格拉底的怀疑主义,预设了习俗和意见之上的“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1)这里的译法遵循了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做出的古典自然正当学说和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区分,虽然施特劳斯使用同一个natural right来指称二者,但是他严格区分了二者的涵义用以彰显古今之争。古典的natural right等同于natural correctness,可以译为“自然正确”或“自然正当”,现代的natural right学说则是西方17世纪以来兴起的“自然权利”学说。并基于无知之知超越习俗和意见、永恒不懈地追求真理。
就目前文献而言,专门研究伯林或施特劳斯的著述已经汗牛充栋,比较二人思想的相关文献则相对较少,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者也较少关注二人的思想相似性,(2)史蒂芬·史密斯最近发表的文章较为少见地列举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分别体现在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反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强调政治家技艺的重要性以及对政治具体事务的实践判断力。具体可参见Steven B. Smith, “Isaiah Berlin and Leo Strauss: Notes Toward a Dialogue,” Critical Review, Vol.32, Issue 4, March 2021, pp.1-17.大多数倾向于强调二人的思想差异性乃至对立,未能充分注意到两位思想家都试图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因此,已有研究或多或少对两位思想家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某种简化处理,要么将伯林的多元主义等同于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未能充分注意他基于“人性”(通过习俗和意见)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做出的协调;要么将施特劳斯的古典自然正当简化为绝对主义,未能充分注意他的苏格拉底怀疑主义是一种不断地超越习俗和意见、对“自然正当”的永恒探究。(3)例如,刘小枫对伯林和施特劳斯进行比较研究的《刺猬的温顺》这篇文章虽然较为深刻地勾勒了两位思想家的对立立场并对“狐狸哲人”伯林进行了批评,但对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了某种简化处理,没有留意到伯林基于共同人性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努力,可参见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此后,人们以各种方式为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辩护,虽然许多文章都富有创见地纠正了对伯林的简化处理,但在处理施特劳斯的问题上又或多或少地将古典自然正当简化为一种绝对主义,未能留意施特劳斯提出的苏格拉底怀疑主义同样是在寻求中间道路。可参见钱永祥:《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邓正来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一辑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1-77页;吴冠军:《价值多元时代的自由主义困境——从伯林的“终身问题”谈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4期,第26-40页。近些年一些研究者试图对上述简化解释进行纠正,就前者而言,一些伯林的研究者通过挖掘伯林自己为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进行的辩护,论证多元主义因为蕴含一个共同的“人类视野”、共同的“人性”从而可以摆脱相对主义的指责;(4)George Crowder, Isaiah Berlin: Liberty and Plu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p.114-124; Jason Ferrell, “The Alleged Relativism of Isaiah Berlin,”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11, No.1, March 2008, pp.41-56; 王敏、马德普:《价值多元论与相对主义——论以赛亚·伯林对价值多元论的辩护》,《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7-12页;马华灵:《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争论》,《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第32-40页;刘晓洲:《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主义之辨——兼论列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东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22-30页。就后者而言,一些施特劳斯的研究者近来试图从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原初涵义将施特劳斯重新定位为一个“探究式的”(zetetic)哲学家,从而摆脱绝对主义的指责。(5)Nathan Tarcov, “Leo Strauss and 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un-Hyeok Kwak and Sungwoo Park ed., Leo Strauss in Nor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20, pp.15-39; Michael P. Zuckert & Catherine H. Zuckert, Leo Strauss and 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pp.338-351; Steven B. Smith,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pp.100-107; 陈建洪:《论施特劳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上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基础,但是基于这些纠正解释对二人思想进行比较分析、重新审视二人的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尚不多见。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试图进行如下论证:首先,通过分析伯林和施特劳斯关于政治或政治生活的看法,指出二人在政治内在冲突、人类易错性、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三个方面存在非常相似的观点。其次,通过对比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和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怀疑主义,分析二人处理政治内在紧张或冲突的不同路径。这里,本文将表明二人的不同立场。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观念假设存在着超乎人类掌握范围之外的“自然”或“神性”,哲学就是不断地去探究有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自然正当。与之相反,伯林的“自然”对应的是人类自身思想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化,因此“自然权利”不是由哲学家探究,而是由人类自身活动创造或塑造的,作为长期存在于历史中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规则。最后,通过分析二人关于“相对主义”的争论,指出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仍然处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进退两难的困境,难以避免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
二、伯林和施特劳斯的思想相似性
以赛亚·伯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现在是拉脱维亚的首都,当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的犹太人家庭,六岁时搬到俄罗斯的彼得格勒,在那里目睹了1917年俄国发生的两次革命,反犹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政治氛围迫使其一家人于1921年搬离彼得格勒、前往英国,在那里度过一生,直到1997年逝世。列奥·施特劳斯同属于犹太人,1899年出生于德国,随着纳粹统治的兴起辗转逃亡到美国,于1973年逝世,两人都亲身经历并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我们很难否认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和同时期很多其他思想家一样,带有无法抹去的时代烙印。用史密斯的话说,他们都是这个背景下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在任何一种有关真理的“唯一正确答案”的强加面前保持自由的思考。(6)Smith, “Isaiah Berlin and Leo Strauss,” p.14.或者说,二人都对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一元论(monism)——认为能够为人类道德和政治冲突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终极的解决方案,将人们寻求的不同价值和目的放在一个和谐的等级秩序中进行排序——的观念持怀疑态度。具体说来,二人的思想相似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内在冲突。伯林和施特劳斯都认为,政治的本性或者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就是存在不可避免、不可根除的价值冲突。这种认识并非出于许多现代政治哲学家对人性的悲观主义假设,而是基于对人类境况的一种观察,也就是陷入冲突的人们持有的是不可调和、不可兼容的价值观。伯林在许多地方表达过这种观点,人类寻求的根本价值是多元的,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效率、忠诚、知识、幸福等等,这些价值往往是不可调和、不可通约、处于“永久的冲突状态”,价值冲突就是“人类生活固有的、不可消除的因素”。(7)Isaiah Berlin,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Henry Hardy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2, 151, 213, 214, 216, 278, 293;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2nd edition, Henry Hardy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2, 59-60, 82-83, 203, 213, 249.对于施特劳斯而言,伯林所谓人类生活固有的价值冲突就是政治生活或常识世界不可避免的意见冲突,这些意见同样是不可调和、不可兼容的,“政治事务依照其本性会遭受支持与反对、选择与抵制、赞扬与责备。政治事务的本质不是中立,而是对人们的服从、效忠、决定或判断提出一个主张”,“政治生活的特征就是持对立主张人们之间的冲突”。(8)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12,80.总之,基于对政治内在冲突的认识,双方都对任何一种声称能够为人类道德和政治冲突找到一个终极解决方案的时代潮流持怀疑态度。
其次,人类易错性。伯林和施特劳斯都怀疑我们能够获得有关“真理”的绝对正确、不可置疑的知识,人类易错性(fallibility)或者人类不完美(imperfection)这一基本境况,限制了我们获得知识的能力。特别是,伯林还否认知识是可以积累的、加增的,他认为我们对人类根本问题的认识是“经验性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特殊的情境”,纯粹属于“人类选择”,选择可以是多样的、与“真理”无关。(9)Berlin, Liberty, pp.255-256.同样地,施特劳斯反复强调人的智慧在于无知之知,(10)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125;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20.因而和伯林一样怀疑任何一种有关终极答案的宣称。但是,对于施特劳斯而言,知识不是“情境化的”或者“人类选择”的事情,而是需要个体通过矢志不渝的哲学生活去寻求发现“那个”(施特劳斯预设存在的)真理性知识、“那个”正确的选择。
最后,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伯林和施特劳斯都试图复兴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施特劳斯1954年的讲稿“什么是政治哲学”和伯林1962年的文章“政治理论存在吗”都为政治生活需要哲学、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在伯林看来,一方面,政治理论仍将继续存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固有的、不可消除的”多元价值冲突的世界,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接受了一种价值,那么致力于找到实现该种价值的最有效手段的技术统治就会取代政治理论;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多元价值冲突,持有不同价值的人们寻求对这些目标的“来源、范围和有效性”进行评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最终还是会转向政治哲学寻求评估的标准。(11)Isaiah Berlin,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2nd edition, ed. Henry Har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95-206.
在施特劳斯看来,一方面,只要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存在距离,人们就无法停止对美好生活的追问,这就意味着政治哲学不会消亡;另一方面,政治生活充斥着关于善好和正义的相互冲突的各种意见,因此“要做出健全的判断,人们必须知道那些正确的标准”,或者说需要一个仲裁者,“最卓越的仲裁者就是政治哲人。他试图解决那些既极为重要又恒久不变的政治争论”。不同于伯林,施特劳斯预设了意见和知识的分野,将政治哲学定义为“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一种尝试,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人们常常误解施特劳斯恢复这种古老分野的同时,假设了某些人能够拥有一双看到永恒真理和绝对价值的“魔眼”,但是施特劳斯从未认为任何人可以拥有“那个”真理,他反复使用的是“追求”(quest)、“尝试”(attempt)、“奋斗”(strive for)这类动词,“哲学从根本来说不是对真理的占有,而是对真理的探究”。(12)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p.12,80-81,11-12,11.施特劳斯并非意图回到古代或者复兴古代的某些“绝对价值”,而是恢复“哲学”(philosophia)的原初涵义,即对智慧的热爱。
三、价值多元主义与苏格拉底怀疑主义
如果任何人或团体宣称掌握了有关人类善的唯一正确、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伯林和施特劳斯都会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二人基于不同的理由。伯林的依据是价值多元主义,并在现代自由主义那里找到了价值多元主义的充分表达和成功经验。而施特劳斯的依据是苏格拉底怀疑主义,并在古典政治哲学那里找到一种重新评估价值的批判性思考方式。
(一)价值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
伯林反对道德一元论,也就是相信所有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答案可以融合为一个连贯的、系统的价值体系。(13)George Crowder, Isaiah Berlin: Liberty and Plu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127.在伯林看来,道德一元论是造成20世纪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根源。他们相信“唯一伟大的历史理想”、人类苦难的“终极解决方案”,“在某个完美的、在地球上可以实现的状态中,人们所追求的那些目的绝不会相互冲突”,(14)Berlin, Liberty, p.214.因此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贯彻这个终极方案,就可以正当地牺牲其他价值,任何手段包括强迫和暴力都可以根据这个绝对的终极目的得到辩护。相反,根据价值多元主义,第一,并不存在单一的、至高的价值或善,因为人类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第二,并不存在能够衡量所有价值的共同标尺,因为人类追求的价值与价值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或者不可公度的;第三,诸多价值并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为人类追求的根本价值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如果某人接受了价值多元主义,就应该理解政治是多元的、宽容的,不是用一种单一的价值践踏其他的价值,而是在相互冲突的不同价值之间进行妥协和平衡。
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让他选择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伯林看来,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保护人类选择的空间,让人们在多元价值面前进行选择成为可能,“在各种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便构成人类境况的一个无法逃脱的特征。这就赋予了自由以价值”。首先,有必要回顾消极自由的定义,“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不受他者干涉(without interference)的情况下,任其(be left to)在那个领域(the area)内,做他能够做的事情、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人”。“不受他者干涉”意味着不是自然能力的限制,也不是某种资源匮乏或贫穷,而是他人的蓄意干涉才会影响我的自由;“任其”或字面意义上的“被留下”意味着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个体;“领域”意味着一个具有边界的范围,这个边界将我和他者的干涉隔绝开来。总之,消极自由就是那个不受他者干涉的限度、范围或领域,“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其次,消极自由的限度或范围。伯林知道消极自由的领域不可能无限大,一个人不可能占有全部的领域,“我们不可能处于绝对自由状态,因此必须放弃我们的一些自由以保持另外一些”。但是无论放弃多少自由,也必须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范围或领域,让人们在这个领域内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最后,法律和政府的职能。法律和政府就像守夜人或交通警察,站在十字路口引导开往不同方向的车辆不会互相碰撞,确保每个人享有这个最低限度的自由,必要的时候以强制的方式禁止那些试图剥夺他人自由的行为。(15)Berlin, Liberty, pp.214,169,174.法律和政府保护消极自由免于他人侵犯,同时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权力本身也绝对不能入侵这个消极自由的边界。
消极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消极自由的边界应该划在什么位置?伯林没有去诉诸自然法、自然权利、“上帝的声音”、功利原则或“人类的永久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这些论证:只要它们已经被很多人认可了,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了,能够支撑人类自由选择,伯林似乎并不介意来自这些原则的论证。(16)Berlin, Liberty, pp.174, 210.但我们可以说,伯林的论证诉诸的是人类经验:“存在着并非人为任意(17)原文“artificially”在这里的含义更接近“任意地”“随意地”,而不是说人类不能制定这个边界。划定的疆界,在其中人必须是不可侵犯的;这些疆界之划定,依据的是这样一些规则:它们被如此长久地、广泛地接受,以至于对它们的遵守,已经进入什么才是一个正常人的概念之中,因此也进入什么行动是非人性的或者精神错乱的概念之中”,(18)Berlin, Liberty, p.211.这里“长久地接受”意味着习俗(convention),“广泛地接受”意味着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确立消极自由边界的那些规则取决于习俗和公共意见的人类经验。伯林提供了一种“自然权利”的经验主义版本,“自然权利”的存在基于大多数人经验到的、长期以来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人类存在方式或人性(humanity),任何试图打破那些规则、剥夺那些基本权利的行为都是“对人类基本利益、需要和渴望的真正压制”。(19)Isaiah Berlin,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Henry Hardy 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6, pp.73-74.总之,对于伯林来说,“自然”对应的是人类自身思想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化,“自然权利”不是由哲学家去探究的,而是由人类自身活动创造或塑造的,作为长期存在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规则。
(二)苏格拉底怀疑主义与最佳秩序
施特劳斯在二战和冷战体制中看到的是相对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两种“普遍主义”的对抗,让人们已经不再那么相信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基本的共同价值”。(20)Thomas L. Pangle, 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s and Intellectual Leg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1-15.在他看来,相对主义导致“我们时代”“现代性”“西方的”危机,以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为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不再承认普遍绝对价值的存在、否认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从而有导向虚无主义的逻辑可能性。他认为,相对主义让人们处于一种精神上的真空状态,抑制了批判性思考的可能,鼓励了一种对赤裸裸权力的竞逐和对强权者的消极顺从。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哲学的决裂导致了这个相对主义的后果,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时代的危机从而提倡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作为和价值多元主义的对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苏格拉底怀疑主义:第一,人们追求的价值确实是多元的、不可通约、不可调和的,但这并不意味所有价值都是可辩护的、正当的,拥有同样的有效性(validity);第二,存在超乎人类掌控范围之内的“自然”(nature)或“神性”(divinity),人类事务或者政治事务中存在根据这种自然的正当,也就是“那个”有关人类善的普遍和绝对的“真理”;第三,如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所揭示的,“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一无所知”,人类获取终极答案的能力具有一种内在的限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不断地去追求它,通过哲学生活矢志不渝地检验和超越意见(伯林所说的各种不同价值观念)、朝向真理。并且,正是因为人们对“应该如何生活”这个最重要事情的一无所知,证明了哲学生活的必要性。(21)Leo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in Thomas Pangle ed.,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259.
苏格拉底怀疑主义预设了习俗和意见之上的自然正当的存在,这在伯林看来是一种“对确定性的幼稚的渴望,或者是对我们的原始过去的那些绝对价值的渴望”,(22)Berlin, Liberty, p.217.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经验到。然而,施特劳斯从古典哲人那里认识到,任何一种关于人类善好或正当的意见,其指向的东西超越其自身,在政治哲人的辩难下不得不超越这个意见、朝向关于正当的“那个”真理性的认识,因为“所有的理解都预设了一个关于整全(the whole)的根本意识”,虽然不同社会对此持有不同的视野,但“它们都是关于同一个整全的视野”。(23)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125.正如人们关于宇宙持有不同的看法不能得出宇宙不存在,宇宙的存在使得人们对其持有一个认识,也正是同一个宇宙的存在使得人们对宇宙的意见彼此不同、相互冲突。同理,人们关于正当或者正义的不同意见预设了真正正义或正当、根据自然的正当的存在,正是同一个自然正当的存在使得人们关于正义的意见彼此矛盾,不得不超越它们自身,向正确的知识上升。
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怀疑主义和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都看到人类认识“真理”的内在局限性,因此都怀疑我们能够获得那个真理性知识,但是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长期以来人们广泛接受的历史经验就是可靠的、有效的(当然他并不否认这些经验有助于我们进行批判性思考)。苏格拉底怀疑主义不愿意止步于习俗和意见,无论它被证明为多么成功、被多少人接受、维持了多长时间,都只是一个关于部分的理解,“关于整全充分表达的探究的未完成本性并不使人们有权将哲学限制在部分的理解中,无论这个部分多么重要。因为部分的意义依赖于整全的意义。特别是,不依赖关于整全的假设猜想、只是基于根本经验基础上的关于部分的解释,最终不会优越于基于这种假设猜想基础上的其他部分解释”。(24)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125-126.
古典哲人对自然正当的追问体现对最佳秩序或最佳政体的寻求,因为政体就意味着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古典自然正当学说以其原初形式,如果完全发展起来的话,是和最佳政体学说一致的。因为根据自然什么是正当的或正义的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最佳政体的构造或者言谈才能找到其完整答案”。(25)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144.正如近来研究者注意到的,施特劳斯评价古典哲人对最佳秩序的寻求是一种“合理的乌托邦主义”(legitimate utopianism):一方面寻求超越现实政体、优越于现存政体的最佳政体,用最佳政体的标准去评价现实政体,认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另一方面强调最佳政体的“缺乏现实性”,怀疑任何一种试图在现实中实现最佳政体的努力。(26)Jun-Hyeok Kwak, “Introduction: The Reception of Leo Strauss in Northeast Asia,” in Jun-Hyeok Kwak and Sungwoo Park ed., Leo Strauss in Nor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20, p.10; Nathan Tarcov, “Will the Real Leo Strauss Please Stand Up?” The American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06, pp.120-128; Smith, Reading Leo Strauss, pp.156-183.总之,古典哲人怀疑完美社会秩序在现实中能够实现(参考柏拉图“在言辞中构想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根据祈祷的理想政体”),但同时又认为任何一种现实社会秩序都能通过哲学加以改善。古典哲人认识到他们在现实社会政治改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加以克制的,所以他们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是审慎的,表现为一种非常私人性的,对少数未来政治家的道德劝诫,朝着知识的方向通过劝诫他们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善好和正义来超越原有的意见和信念。总之,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假设存在着超乎人类掌握范围之外的“自然”,哲学就是不断地去探究有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自然正当。
(三)二者差异之比较
最后,作为总结,价值多元主义和苏格拉底怀疑主义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假设,我们应该从“经验”中去寻找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将知识视为人类自身的一种创造或塑造(invention)。这意味着,伯林并没有假设存在任何一种超越人类“选择”或人类意志之上的“自然”正当。根据这种认识论的视角,人类选择与上帝或自然并无关联,某种意义上是隔绝的。相反,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怀疑主义则假设存在超乎人类掌握范围之外的“自然”正当。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都可能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答案不是人类自身“创造的”(invented),而是“发现的”(discovered)。当然,施特劳斯并没有认为,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已经提供了那个“最终答案”。总而言之,在伯林那里由人类自身创造的、脱离上帝或自然的“知识”在施特劳斯这里不是知识、只是意见。
第二,从政治的视角看,伯林试图确立保护人类选择免于外部阻碍的边界。这个边界可以由人类“制定”,由“经验”加以习惯化。当然,伯林的习俗和社群主义的传统不一样,习俗让人类选择成为可能,而传统通常是让人类选择受到公共善的限制。对于伯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护人类选择。因此,他将价值多元主义作为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原则如果不允许我们“选择”我们“想要的”东西就不是好的原则。并且,应该设立法律来保护人类选择免于侵犯,国家的作用仅仅是交通警察或守夜人。伯林在现代自由民主政体那里找到这种价值多元主义的成功实践。相反,施特劳斯选择探究最佳秩序的问题,他并不认为最佳秩序能够实现,但他认为通过思考什么是最佳秩序,我们就能超越我们视野的局限(由我的国家或我的政体带来的视野限制),并且寻求最佳可能的政体。在施特劳斯这里,习俗或意见不能作为判断什么是最佳的标准。施特劳斯试图发现哲学的作用,引导潜在政治家或绅士朝向自然“正当”或“对自己进行哲学化”(philosophizing oneself)。
四、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两难困境
理解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和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怀疑主义二者之间的分歧,最终还是需要考察二人围绕“相对主义”产生的争论。在伯林1958年发表《两种自由概念》的牛津大学就职演讲之后,施特劳斯随后不久就发表了题为“相对主义”的文章,认为伯林的演讲是“自由主义危机的标志性文献——此危机源于自由主义已抛弃了其绝对主义根基,而且试图变得完全相对主义化”。(27)Leo Strauss, “Relativism,” in Thomas Pangle ed.,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7.此后,伯林也就相对主义问题进行了回应。(28)Berlin, Liberty, pp.145-154;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pp.73-94.
施特劳斯指出了伯林论述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伯林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价值视为有关人类目的的两种不可调和的终极价值,“前一种希望约束权威本身。后一种希望将权威置于他们自己手中。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们不是对同一种概念的不同解释,而是对人生目的的两种分歧深刻、不可调和的态度。最好认识到这一点,哪怕在实践中常常有必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妥协。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提出了绝对的主张。这些主张不可能同时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不承认二者寻求的满足在历史上和道德上拥有平等的权利(equal right)被归入人类最深刻的利益之中,就是严重缺乏社会和道德理解”。另一方面,伯林又声称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好、更真实、更人性化,出于两点原因:第一,“更真实”是因为承认人类多样的、不可通约的、永久冲突的目标;第二,“更人性化”是因为不会为了某个遥远的理想而剥夺人们的生活所需。(29)Berlin, Liberty, pp.212,216.我们很难轻易地否认伯林这两段论述是明显地自相矛盾。按理说,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价值同等终极,提出同等绝对要求,拥有同等的权利,无法根据同一尺度或同一标准进行衡量,但是伯林同时又宣称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好。价值多元主义主张所有价值同等有效的同时,又将是否承认、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所有价值同等有效”作为判断好坏的绝对确定标准。施特劳斯发现这是自由主义存在的典型问题,一方面自由主义说自由在于不受外在阻碍的人类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提出“那个”边界,预设了一个所有人都要同意和接受的绝对确定标准。如前文所述,这个边界取决于习俗和公共意见的人类经验,基于大多数人经验到的、长期以来已经接受的人性,但伯林同时又认为这个经验只是“资本主义文明晚近的果实”。
在上述提及的文献中,伯林曾经为“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做了论证,很多研究者认为伯林为多元主义的辩护是成功的,因为多元主义预设了所有人分享一个“共同的视野”“共同的范畴”“共同的人性”,使得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进行理解和评价成为可能。(30)马华灵于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参见马华灵:《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争论》,《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第32-40页。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正如他本人承认的,受到赫尔德和维柯很大的启发,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反对启蒙理性的一元论的、普遍的价值;第二,强调每个民族和每个时代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三,认为文明发展是一个“人性”(humanity)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同文明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去实现“人性”,但是跨越时间和空间它们都拥有一个关于人性的共同基础或共同视野,或者说最终会相遇在“人性”这个共同桥梁。伯林在赫尔德(以及维柯)那里找到价值多元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一种试图调和特殊价值和普遍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但是,我们可以设想,施特劳斯仍然可能会回应说,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最终落脚的只是若干个特殊经验的集合——通过他们那个交织着欲望和激情、充满个人想象与特质的“人性”共同桥梁相互之间可以交流、可以理解。伯林似乎仍然处于一种两难困境之中,要么是承认此种“人性”的特殊性和相对性,要么是将其作为判断文明和野蛮、人性和非人性的普遍绝对标准。
进一步考察发现,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伯林试图结合特殊经验和普遍价值的第三种方案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人性的“体面的习俗主义”,存在着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同的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试图通过文本所处的历史情境去理解作者的思想从而获得更加确切的知识,这个好的开端却终结于“没有一种回答可以宣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有效的”这样一种确信,因为他们认为所有那些对根本问题的回答都是受到“历史限定的”。对于施特劳斯来说,历史主义不过是用一种终极回答(finality)——“终极确信,即所有人类答案本质上和根本上都是‘历史性的’”(31)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0, No.1, Jan 1949, p.46.——取代了前人的终极回答。所以,在充分检验前人给出的答案之前,就已经“独断地排除了所有答案”,(32)Zuckert & Zuckert, Leo Strauss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p.43-44.排除了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可能性。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存在同样的问题。价值多元主义看到人类道德经验中价值冲突的深度和持久性,并且基于人类易错性(人类不完美的这个内在局限)怀疑我们能够找到“那个”最终答案或者终极真理,这个好的开端却终结于“人类价值永恒冲突、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这样一种确信,因为人类根本价值都是同等有效的。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价值多元主义不过是用一种终极回答(我们解决不了)取代了前人的终极回答,同样独断地排除了“我们要去寻找”的可能性,排除了寻找终极回答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发现,施特劳斯不满于价值多元主义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它在充分考察所有价值之前,就过早地宣称所有价值都是同等有效、独断地宣称价值冲突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并将其作为所有人都要同意和接受的绝对确定标准,从而排除了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可能性。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施特劳斯和伯林所处共同时代背景从政治内在冲突、人类易错性和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三个方面总结了二人的思想相似性。通过对比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和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怀疑主义论证了施特劳斯“自然正当”和伯林“自然权利”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性:前者假设存在着超乎人类掌握范围之外的“自然”,哲学就是不断地去探究有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自然正当”;相反,伯林的“自然”对应的是人类自身思想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化,“自然权利”不是由哲学家去发现的,而是由人类自身活动塑造出来的,体现为长期存在于某一社会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规则。最后,通过分析二人关于“相对主义”的争论,论证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仍然处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两难困境。总而言之,伯林选择了价值多元主义,“自然权利”和他的消极自由概念相一致,最终还是难以避免在习俗和意见中走向真理的相对主义;施特劳斯选择了苏格拉底怀疑主义,预设了习俗和意见之上的“自然正当”,并基于无知之知超越习俗和意见、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
就古今之争而言,施特劳斯曾经区分了“合理乌托邦主义”(legitimate utopianism)和“现代乌托邦主义”(modern utopianism),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古典哲人对“自然”——难以捉摸的命运、高深莫测的天意——的敬畏,现代哲人相信命运可以被人的力量征服;第二,不同于古典哲人对完美秩序之现实性的怀疑,现代政治哲人通过降低传统标准(德性)为较低标准(自我保存或自利)以确保较低标准的可实现性;第三,不同于古典哲人介入政治生活的审慎和克制,现代哲人通过启蒙式的大众运动来掌握权力,按照自己构想的全面美好的社会蓝图进行社会工程式的改造。特别是,在公共修辞中说服大众的时候是用一种基于欲求和激情的意见来赢得人们的认可,彻底抛弃了古典哲人关于良善和正义的追问。(33)Leo Straus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olitical Theor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69, No.4, 2007, pp.519-529.某种意义上,施特劳斯认为价值多元主义和其他“现代乌托邦主义”一样危险,因为它不经意间推动了一种最终以丛林法则(强者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而收尾的相对主义。同时,“being liberal”的原初涵义即免于习俗和意见的束缚、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也退化为一套最终呈现为法定个人权利的“自然权利”。
(本文的写作得到郭峻赫教授的宝贵指导,同时感谢《四川大学学报》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