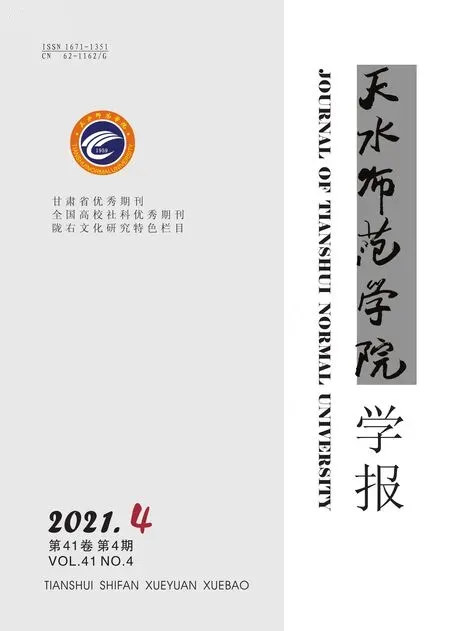近四十年杜甫咏物诗研究述评
白松涛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杜甫咏物诗状物生动、寄寓深广、手法精妙,历来赞誉甚高。如乔亿《剑溪说诗》云:“咏物诗,齐、梁及唐初为一格,众唐人为一格,老杜自为一格,宋、元又各自一格。宋诗粗而大,元诗细而小,当分别观之,以尽其变,而奉老杜为宗。”[1]1102这便明确阐述了杜甫咏物诗自成一家、承前启后的诗歌史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古典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据现有资料记载,新时期较早论述杜甫咏物诗的文章是雷履平于1981年发表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的《杜甫的咏物诗》,距今已过40年。在这期间,杜甫咏物诗的研究朝着精细化、全方位、多角度、新理念的方向发展。不过,在梳理杜甫咏物诗研究史之前,首先要对杜甫咏物诗进行厘定。这是因为“咏物”概念在杜甫时代并未上升到文体自觉的层面,导致部分杜诗在归纳咏物类型时处于模棱两可的地位。
一、杜甫咏物诗的厘定
直到南北朝时期,“咏物”尚被宽泛地理解为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例如《诗品》评价许瑶之的诗歌是“长于短句咏物”,[2]440而根据许瑶之现存的一首咏物诗《咏楠榴枕诗》可以大致推测钟嵘所说的“咏物”是指细致地描摹物象,尚不包含咏叹情志的意味。在《昭明文选》中,咏物诗被收录在游览、咏怀、乐府等题材类型中,直到宋本《李太白集分类补注》才首次列出“咏物”一类,故有学者认为“古人自觉的咏物体类意识始自宋代”。[3]1虽然唐宋时期咏物诗的归类编撰还较为模糊,但是咏物概念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即咏物不再局限于物象本身。范仲淹在《赋林衡鉴序》中说,“指其物而咏者,谓之咏物”“取比象者,谓之体物”,[4]297即认为咏物诗须选定具体的物象,并由物象生发感动、表达情志,强调“物”是咏叹的出发点和体察的落脚点。“咏物”概念从局于物象到突出咏叹情志的变化历程中,杜甫咏物诗更是起到了开拓题材、探索诗艺、丰富意蕴的典范价值,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建安陶阮之前,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5]1
现代学者在梳理历代“咏物”概念流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其作了界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洪顺隆:“一篇之中,主旨在吟咏物的个体(包括自然界和人造的),也即作者因感于物,而力求工切地‘体物’‘状物’,以‘穷物之情’‘尽物之态’,且出之以诗体的,才是咏物诗。所以题名咏物,实以写景、抒情为主的篇什……都不能把他当作咏物看。”[6]7
王次澄:“一、采取人的感觉器官能够捕捉到的自然或人事的具体物象。二、始终吟咏单一的物象,不宜同时吟咏多种事物。三、专注于事物的重点,不宜面面俱到。四、着眼于物象的形状、情趣。以物名为诗题。不包括以表现作者(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为主的作品。”[7]135
两种观点都明确指出咏物诗在艺术写作上具备的一些特质:其一,作者是带着一定的情志来挑选物象的,从创作开始就融入了个体情志,这体现在物象本身、体物角度、修辞用语、意境氛围等不同方面。其二,情志和物象两者都是表达的重点,情志的表达方式往往与物象的摹写方式融为一体。本文据此认为,咏物诗是指以自然物象、生命物象、人工器物等特定的具体物象为写作中心,将其置于审美场域里体察其形态及风貌,并由物兴感、寄托情志的诗歌。
由此界定杜甫咏物诗共计163首:其中五言律诗共77首,七言律诗共7首,排律共2首,七言绝句共16首,五言绝句共1首;五言古诗共30首,七言古诗共30首。所咏对象主要有马、月、雨、树、鹰、雁等。另外还需要具体分析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杜甫咏画诗。杜甫许多吟咏画作的诗,着意于描写画中的景物风光,想象自己身临其境,抒写所见所感,这种“人在画中游”的写法实际上是在有意模糊“画”的物质载体,属于写景诗而非咏物诗。只有将画看作综合的统一体,把画卷的物质形式和画中的具体情境统一起来,或者是只专意于咏叹画中某一物象,如杜甫《画鹰》《天育骠骑歌》《姜楚公画角鹰歌》《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等,才可以归为咏物诗;再如咏叹屏障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一诗,虽然在开头部分描写了屏障的创作由来,但主体部分是身临其境描摹山水表达归隐之趣,脱离了屏障这一物质载体,且没有着意咏叹的中心物象,故不被归为咏物诗。
第二,天象气候类咏物诗。诗人咏天象气候,难免要写与之相关的景色,如月景、雨景等,于是草木山水、鸟兽虫鱼皆可入诗。例如“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秋日新沾影,寒江旧落声”,虽不见“雨”字,却句句都是雨意;再如“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关山随地阔,河汉近人流”等都是此类写法,“以境写物”也是杜甫独具创意的状物之法。但诗人如果没有将焦点放在所咏之物上,而是完全放开来写,便不能归为咏物诗,如《雨过苏端》写诗人冒雨访友,有雨中款待之事、有雨后花草之景,但诗人是在记事抒怀,故非咏雨诗;《雷》(大旱山岳燋)写大旱农忧、祈雨救旱、风雷响动,并融入时事,此是写景记事诗,并非咏雷诗。此外如《曲江对雨》《雨二首》(青山澹无姿)、《雨四首》其三和其四、《村雨》《北风》(北风破南极)等皆不能归入咏物诗。
第三,有咏物成分但不能被简单归入咏物诗,还应该从全诗的艺术构思着眼。如《暇日小园散病》一诗前十八句写小园散步,督促耕牛准备种菜;后十二句写突然飞来的两只白鹤,详细描写了白鹤的形态,是为咏物成分。但从全诗的整体创作来看,仍非咏物诗。类似的如《对雪》《早花》《对雨》(莽莽天涯雨)等皆不宜归为咏物诗。
二、选本收录
选本的收录对于杜甫咏物诗的接受、普及和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咏物诗选本编纂的第一个高潮是清代。其中,康熙年间编订的《佩文斋咏物诗选》计486卷(附49卷),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咏物诗选,尽管此书的选诗标准极为宽泛,但收入杜甫咏物诗225首,数量居入选诗人前列,即是肯定了杜甫咏物诗的典范价值。此外俞琰《咏物诗选》、翁方纲《咏物七律偶记》、龚文藻《国朝咏物诗钞》等选诗虽不多,但都选入了不少杜诗。清代咏物诗选本的删汰去取,既梳理了历代咏物诗的经典之作,展现出咏物诗文体自觉的意识,同时也推动了杜甫咏物诗的经典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兴起了咏物诗选本编纂的另一个高潮。这些选本虽然选诗标准不一,但都普遍注意到了杜甫咏物诗的经典价值。陈新璋《唐宋咏物诗鉴赏》选诗103首,选诗范围比较狭窄,多限于草木鸟兽。其中选杜甫《古柏行》《房兵曹胡马》《画鹰》三首,虽然数量不多,但编者给予了杜甫咏物诗“入木三分,非浅见所能知晓”[8]3的赞誉。相似选本还有李起敏、白岚玲选注的《历朝花鸟咏物诗》。选注者认为花鸟咏物诗是“由感官向心灵开拓,目的不在审美形象的刻画,而在于对心灵意境的表达,在于审美情感的抒发”,“花鸟咏物诗不仅是人化自然的一种特殊表现,同时也是心灵情绪外化的特殊形式”。[9]8按此标准,杜甫的《江梅》《蒹葭》《萤火》《孤雁》等被选入书中。这些诗寄托遥深、意蕴深厚,但历来研究甚少,显示出编选者非凡的选诗眼光。陶今雁主编《中国历代咏物诗辞典》[10]划分30种物类,选诗广博,网罗杜甫多数咏物诗,但对于“咏物”概念的辨析不够谨慎,以致收入大量岁时节气类、山水游览类非咏物诗,其中就包括杜甫《望岳》一诗。刘逸生《唐人咏物诗评注》认为唐代咏物诗在南朝“纯粹咏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诗歌史的角度肯定了杜甫咏物诗破除南朝“以谜为诗”这一体物困境的成就,认为是比兴兼备的咏物诗典范,“把咏物诗的技巧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1]6该书选杜诗16首,数量颇多。此外还有王德明等选评《古代咏物诗精选点评》[12]收杜诗共13首,李之亮等选注《咏物诗精华》[13]收杜诗也是13首,赵志凡等选注《中国历代咏物诗选注》[14]收杜诗为6首。这些选本的选诗标准不同,但却从不同的角度凸显了杜甫咏物诗的典范价值,他们不仅用诗史演进的视角展现了杜诗的艺术风貌,也各自发掘了杜甫咏物诗中那些容易被学者忽视的作品。
三、艺术批评
选本编纂是着眼于古代咏物诗整体风貌进行的删汰去取,具有文体意识的编者更是着意凸显杜甫咏物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而专门针对杜甫咏物诗的艺术批评则更加深入文本,这也成为近四十年杜诗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在学位论文方面,多部研究咏物诗发展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往往列出专门的篇章来论述杜甫咏物诗,有林启兴《论唐代咏物诗》(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徐盛《魏晋至盛唐咏物诗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杨凤琴《唐代咏物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于志鹏《宋前咏物诗发展史》(山东大学2005年)等。这些博士论文都对杜甫咏物诗的艺术成就给出了很高的文学史评价,如杨凤琴就从风格类型和思想内涵两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杜甫咏物诗“集大成”的特点,于志鹏从“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多样化的艺术手法”两个角度分析、挖掘杜甫咏物诗背后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硕士学位论文中则有许多专门研究杜甫咏物诗的,如李园媛《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继承和发展》(西南大学2012年)重点从物象题材、情志内涵、手法技巧三个角度分析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的革新;丁庆勇《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杜甫咏物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重点分析了杜甫咏物诗中“民胞物与、时政关切、义勇雄心、空怀大志、刺世嫉邪、漂泊怀乡”的思想内涵和“比兴深微、以形写神、参差多态、融以叙议、雅用典故、避陈出新”的艺术特色;此外还有姚叶翠《杜诗咏物写景意象阐释中穿凿现象研究——以宋代杜诗学为中心》、曹姗姗《盛唐三大家咏物诗比较研究》等。除了上述学位论文的研究之外,以杜甫咏物诗为研究主题的专著十分有限。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15]219-246第八讲分析了杜甫咏物诗“民胞物与”的情怀基点、咏物诗的情感态度、出形入神的艺术境界、比兴寄托的手法、对宋诗的影响等,几乎涵盖了杜甫咏物诗的所有重要话题。张轶男《禅解杜诗》[16]203-244一书第五章论及了杜甫咏物诗的大乘慈悲情怀,研究了其诗中物象人格化所体现的佛禅思想。
现在研究杜甫咏物诗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细致,成果主要体现在体物艺术、物象题材、思想内涵、咏物诗史、生平阶段等五个方面。
其一,体物艺术方面。许多研究是从用典、比喻、衬托、移情等常见的角度来分析的,缺少创作论视角下的细致体察。陈岚《杜诗体物艺术新探》[17]指出,杜甫从“发掘事物的独特比喻意义”和“移情入物”两个角度发展了咏物诗,重新确立了独立咏物的传统,并开拓了形而下化、反典型化、追求经验广度的新变方向,从文本细读中寻找体物思路和新变趋势。
其二,物象题材方面。许多学者归纳杜甫咏物诗中常见的物象类型,包括马、月、雨、燕、雁等,尤以咏马诗的研究最盛。物象题材类的研究尚存在着不足:一方面,针对物象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不足,例如杜甫咏叹的物象可以分为真实和虚拟、平常和怪奇等不同类别,而这一特点也和诗歌体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除去文学鉴赏类的分析外,物象题材类研究还应该根植诗人的审美追求、时代的文学现象、社会的思想文化等,而胡可先《杜甫咏荔枝诗探幽——兼论古代咏物诗的政治内涵》[18]一文虽然是分析咏荔枝诗,但却能够以小见大,分析咏物诗的比兴传统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互动。
其三,思想内涵方面。这一类研究主要针对杜甫咏物诗中寄寓的生态情怀、儒家思想、佛家思想、个体生命历程等,在方法上往往文史互证,展现出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如程千帆、张宏生的《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19]展现了两种精神与杜甫个体思想的交融,并由此在咏物诗写作中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孙少华的《〈破船〉与杜甫晚年去蜀心境试解》[20]探讨了这首离蜀前的咏物诗所包含的宗教情结和杜甫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尤其分析了与佛教“身如破船”一说的精神联系。
其四,咏物诗史方面。许多学者是从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展开研究的,比较对象包括李商隐、白居易、韩愈、杨万里等,并由此分析唐宋咏物诗的流变历程。其中,陈才智《杜甫对白居易的影响——以咏物诗为中心》[21]一文分析杜甫咏物诗在创作态度、写实精神、艺术手法以及寓怀兴寄的写作方式等方面对白居易的影响。李定广《论中国古代咏物诗的演进逻辑》[22]将咏物诗演进史概括为“比兴体咏物诗”“赋体咏物诗”“赋比兴结合体咏物诗”“论体咏物诗”四种咏物诗创作范式的变化史,指出杜甫在唐代咏物诗创新中将赋体和比兴体结合起来的重要贡献。程千帆与张宏生合著的《“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23]则分析了杜甫体物之法的创变对宋人禁体物诗的影响。
其五,生平阶段论方面。在这方面关于杜甫咏物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秦州、蜀中、夔州时期,相关研究有聂大受《试论杜甫“秦州咏物诗”的艺术创新》[24]和《杜甫秦州咏物诗二题》、[25]林晓娜《论杜甫的夔州咏物诗》[26]等,他们将杜甫的人生际遇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分析咏物诗写作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发展,尤其发掘了物象选择与摹写所根植的复杂心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杜甫创作了大量咏物组诗,文本复加的组合形式实现了多角度叙写时事、多层次铺展心境的创作可能,但相关研究还不够丰富。
四、结语及展望
近四十年来,杜甫咏物诗的研究进入精细化、系统化的发展阶段,研究成果具有角度新颖、解读细致、视角多元、学科融合等特点。咏物诗选本对杜诗的收录不仅促进了其诗的经典化和普及化,也提供了从咏物诗史整体风貌中来解读杜诗的视角。而艺术批评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物艺术、物象题材、思想内涵、咏物诗史、生平阶段等五个方面,不过咏物题材的整体风貌、咏物组诗的文本策略及思想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
综合来看,今后的杜甫咏物诗研究还可以从新的层面切入:
第一,体物方式的精细化解读。很多学者将杜甫咏物诗的中心物象当作“抒情意象”来研究,但诸如空间、逻辑、典故、视角、事境、线索、细节等因素恰恰是展现杜甫体物方式的具体思路。在诗歌叙事性研究视野下,咏物诗的中心物象并不被全然视作意象,而是成为具有勾连信息、唤醒记忆、承载事件等作用的“事象”。这意味着“物”不仅处于指向情感世界的“意境”,还处于层次丰富、跳跃变化的“事境”之中,因此咏物诗中的“叙事”便可被认为是具有独创价值的体物与状物之法。这一分析跳脱了长久以来的抒情论话语体系,而且是从体物状物的创作论视角展开鉴赏分析,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杜甫咏物诗的“诗史品质”的挖掘。这一品质并不指向史事类诗歌的平静叙述,而是在挖掘个人心灵史的过程中还原公共生活史,将诗人所咏之物放在更广阔的多重世界中进行考量。杜甫在感时伤物的情感基础上,将人生经历和时代历史融入所咏之物。同时杜甫的人生行旅又无不牵连着时局的变化,个人情感轨迹与社会公共历史在文本中高度融合。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追溯至《钱注杜诗》中钱谦益开创的“文史互证”治学之法,咏物诗的研究也可以因此打开多重视野。
第三,杜甫咏物诗的辨体研究。杜甫的咏物诗创作偏爱五律,清人雷松舟在《龙山诗话》中也说“咏物诗,唐人最夥者,莫逾杜陵。杜陵诸诗,五律十七。然观其诗,皆词在个中,意超象外,有不即不离之妙”,[27]1788然而历代论及咏物诗体制与内容关系的诗话少之又少。清代俞琰的咏物诗创作观颇有新意,他在选编《咏物诗选》时认为咏物诗适合“稳顺声律,不蔓不支”[28]3的文本体制,所以选杜诗以律绝为要,如《月》(四更山吐月)、《天河》《春夜喜雨》等。当然,杜甫咏物诗的近体和古体各有所擅、特色鲜明,两类诗中物象性质、章法布局、抒情方式等多有不同,其与诗歌体裁之间的牵制、互补关系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此外,杜甫的咏物组诗的文本组合逻辑革新了李峤百咏的平面线性连接,对晚唐咏物组诗的复合叙事亦有深远影响,这一结构开拓了咏物诗的体式与容量,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