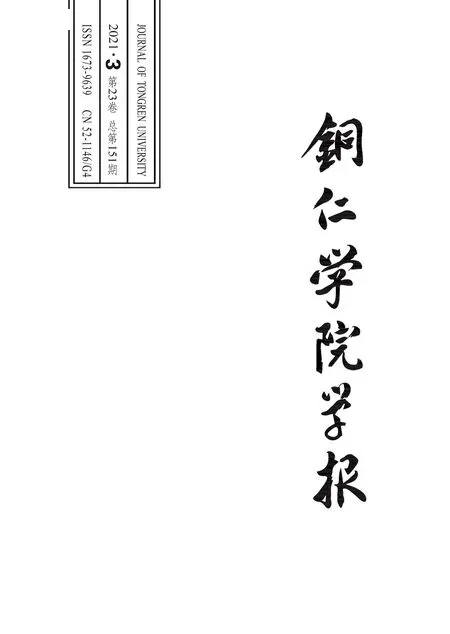论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的初步进展
姚正平
论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的初步进展
姚正平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史学学科化指的是历史学从传统意义上的一门“学问”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的变化过程。它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建设:一方面是指自身理论方面的建设,诸如史学概念的明晰、对历史著述和历史本身的明确区分、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高度一致等;另一方面表现在科系、学会、学术杂志的创办等。虽然在学科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总体来说,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初步形成。
史学; 学科化; 理论; 制度
所谓的史学学科化,指的是历史学从传统意义上的一门“学问”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的变化过程①。对其深入研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对当前学科体制下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既往的研究较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问题做深入分析。对一些重要问题,如近代高等师范学校在史学学科化中的作用、史学学科化进程中的“史地合一”现象等关注不够。本文从理论层面,诸如近代意义的史学概念的明晰、对历史著述和历史本身的明确区分、史学研究法上的高度共识,实践层面从科系、学会等方面,作专门探讨。
一、新的史学理念与中国近代史学学科化
在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进程中,贯以近代新的历史学理念的,首先要提到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分六期刊载了《新史学》,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也提出他心目中的“新史学”。在其中的《史学之界说》一文,他对史学之概念,首次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将史学的定义分了三个层次,“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7-10。这种对史学如此系统之定义,在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还是第一次。到了近代的西学东渐,“虽然中国人也引进、翻译甚至写作了不少西方的史学著作,但大都带有应急的色彩,没有形成对史学的一种较为系统的看法”[2]。而梁启超首次试图对史学所下的定义,与以往相比,不仅系统,而且相当自觉,如梁启超自己就说到:“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1]7
梁启超对史学概念的定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迈向学科化进程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其之后,不少学者都注意对史学的概念辨析。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第9、10期上,连载长文《史学概论》,在批评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自己对史学的认识,“史学者,研究社会之分子之动作之发展之科学也”,并对此定义进行了详细的解说[3]。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专门谈到了“什么是历史学”。他对史学的定义是:“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4]这种对史学自觉地、明确地定义,反映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逐步建立,特别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教科书尤其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在绪论中普遍地都会谈到史学理论问题,其中首先提及的就是对历史的定义②。这表明历史著述应首先注意对史学的定义,已成为一种常识而被写进历史教科书,而对何谓历史应首先进行明晰方面所达成的普遍共识,是史学在理论方面,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初步建成的重要表现。
对历史著述和历史本身的明确区分。在传统史学中,学者向来很少注意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降至近代,伴随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对二者的关系才开始有了自觉地辨别和剖析。而学界在谈到此问题时,常认为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区分,首先源于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事实上,在李大钊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阐明二者之不同了。如缪凤林,他在1921年11月《史地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与哲学》一文,就已对二者有了明确的辨别:“通常言历史者,皆以历史,为过去事实之纪(记)载,叙述与描写二字即足尽其义蕴,此实未明历史之真谛。盖其所言,乃组织成书之历史,而非历史之本体;乃历史之历史,而非历史之真象也。然则历史之真象,究为何乎?曰演进与活动而已。”[5]缪凤林在1923年11月又发表了《历史之意义与研究》一文,进一步对二者进行了区分:“昔班孟坚有言曰:‘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贯(冠)德于百王,故采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此以历史为过去事实之记载,实古今史家同具之观念。然细加审查,似其所言,仅指组织成书之史,而非史之本体。质言之,乃史书而非即史也。盈天地间,层叠无穷,流行不息之现象,生灭绵延,亘古亘今,是名曰史。有人焉,抉择是中一部分之现象,以一己之观察点,考察其因果关系,笔而出之是曰史书。史书之描述,于事实纵极逼真,栩栩欲活,要为事实之摹本,非即事实之自体。故凡昔贤之所著述,与夫吾人之所诵习者,惟为史之代表。(或名曰史之史)真正之史则非吾人所得而知。汉人之生活史也,《汉书》者,记载汉人一部分之生活者也(此就多分言,亦有记载汉以前事者)。谓《汉书》为汉一部分生活之写真,可也,谓《汉书》即汉人之生活,不可也。”[6]这非常清晰地讲到了客观历史本身与历史著述间的区别与联系,表现出相当的卓识。这种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明确区分,是中国近代史学学科化在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
理论方面,判断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重要标志,还应包括专业化的训练。陆懋德曾指出,这种专业化的训练对提升历史学专业化的重要作用:“凡历史必须专业化,犹如一切科学皆须专业化。将来必须等到历史技术日益专门,而普通人未受训练者,对于历史不敢开口,不敢动笔,而后历史之地位增高。”[7]而史学方法的传授就是专业化训练的一个主要渠道和标志。20世纪初以来,史学方法论类的课程已被要求在大学堂内开设,如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不论是万国史学门,还是中国史学门都要求以主课的形式开设史学研究法[8]358-361。民国建立之后,亦是如此。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成立的历史学门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西洋史学类,而这两类都需开设史学研究法[8]711。特别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史学方法类的课程更是被普遍开设起来。如北京大学史学系,从1929年傅斯年担任史学方法论的教师以来,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史学方法论的开设从未间断[9]。而且各大学史学方法论课程讲授的内容基本相同。[10]233-234在史学研究法上达成的高度共识,对史学学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巴勒克拉夫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尽管西方史学界在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这一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双方实际上达成妥协,一致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这样的共识被写进当时大量出版的历史研究工作指导手册,当作一种规范固定下来,“而且实质上毫无变化地一代一代传下去。”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后来出版的诸多史学方法论著作同19世纪末出版的此类著作,特别是朗格卢瓦和塞纽博斯《历史研究导论》作一对比,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容并没有太大区别。这标志着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诞生[11]。从史学研究法达成共识这一角度,可以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初步形成。
二、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在学科建制方面的逐步确立
在中国史学学科化进程中,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需要在外在建制方面的保障。这首先表现在大学科系的设置上。近代中国大学史学科系的设置,较早可以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晚清名士喻长霖在其所撰的《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说:“己亥秋,学生招徕渐多,将近二百人,乃拔其尤者,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12]这可视为近代大学设置史学科系之雏形。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分为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等八科,文学科大学下设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等九门[8]348-357。这里史学科系一分为二,中国史学门与万国史学门分别单独设系。民国建立后,颁布了新的学制,公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分为文科、理科等七科,其中的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四门,并对历史学类应开之科目作了比《奏定学堂章程》更为详细的规定[8]708-710。大学规程虽如此规定,但由于经费、生源与师资的原因,并未设置史学门[10]100-102。这种状况持续了五年,直到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才发生改变。蔡元培到任后,欲大力发展文理两科,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每科增设一门,即史学门及地质学门”[8]832。史学门的创设,意义颇大,虽然它在创设初期一度遭遇冷落,但它的创建,却是近代中国史学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沈兼士回忆道:“北大新文学运动,那是人所共晓的。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13]
值得指出的是,民国时期出现了不少高等师范学校。这些高等师范学校虽然在史学人才的培养目标上,与北京大学这样大学类的高校多有不同,但是这些高等师范学校成立时间较早,亦多聘用名师,且课程设置较为齐全。因此,探讨近代高校史学科系的建立,民国建立的诸多高等师范学校亦是不可忽视的面相。
为培养中等学校与师范学校师资的需要,教育部决定成立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其分预科、本科、研究科,其中本科分国文部、历史地理部等六部,并对各部所应习之科目作了规定。历史地理部所应习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14]。民国建立的不少高等师范学校随之建立史学类科系,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等,其中又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最早。1913年8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遵照教育部之前的科系规定,增设历史地理部,开设的课程包括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地理(测绘学)、法制经济、国文、英文、考古学、人类学、体操等[15]。需指出的是,尽管教育部亦颁布了要求大学类高校建立历史学门的法令,但在1917年之前,创办史学科系的大学其实很少,甚至连当时最负盛名的北京大学直到1917年,在蔡元培的努力下,才创办了中国史学门。大学科系建制上,史学科系这种被冷落的局面,反倒使民国时期这些高等师范学校所创办的史学科系的意义凸显出来。可以认为,民国初期,史学学科在科系上的建设,很大程度体现在这些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学科系上。
考察民初《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大学规程》中关于史学科系的科目安排,会发现20世纪20年代以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在此时已较为明显体现出来。如《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要求历史地理部开设的课程除了历史、地理等专业课,以及体现师范类院校特点,各部所必修之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之外,还规定以必修的方式开设法制、经济、考古学、人类学等课程。而《大学规程》亦要求历史学门开设考古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课程。不过,因为民初大学中的史学科系一度并未设置,所以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较早是在高等师范学校主要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学科系中体现了出来。
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进程中,亦十分重视史学会的创办。近代高校出现较早的史学会,是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设的史地学会。它不仅创办了以史学为主的史学杂志——《史地丛刊》,而且举办了一系列演讲。从1915年到1919年,史地学会共举办讲演109次,演讲人基本都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的学生成员,题目涉及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宗教史、学术史、史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等方面,对打造史地学会浓厚的学术氛围,推动近代史学人才的培养,起了良好的正面效应[16]。1922年3月,史地学会“鉴于简章有不完备处”,制定了新的简章,作了不少变动。其中一个较大的改变就是,将研究部分为十二个组,包括:制造组、摄影组、翻译组、地方调查组、时事编辑组、中史研究组、西史研究组、史学研究法组、地理研究法组、史学原理组、教科书审查组、教科书编制组[17]。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史学与地理已分开研究,体现了当时学术分科背景下,史学和地理分离的趋势;二是史学又具体分为中史研究组、西史研究组、史学研究法组、史学原理组等,体现了史学专门化的特点。
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类似,且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还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创办的史地研究会。史地研究会源于1919年成立的地学研究会,但在1920年召开的地学会第二届选举会上,“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所以“决定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并发行《史地学报》[18]。
南高师的史地研究会宗旨与北高师的史地学会基本一致,都是致力于史学与地学的研究,不过两者有一明显的区别,即北高师史地学会的会员多由史地部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而南高师的史地研究会却将其会员严格限定为南高师的学生,且基本都来自文史地部③。不过,他们通过聘请教师作为指导员的方式,来加强教师对史地研究会学生的指导[19]。
史地研究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亦逐渐认识到分科研究、专门研究的重要性。1922年6月,第五届史地研究会召开本届最后一次大会,决定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分组研究,并提出初步的规划,“本会会员之研究,自学报发表外,尚未能尽量进行。推原要因,在于混而不析,故职员会议主张此后分组研究,会员多数赞成。当时暂拟之组如次:史学组、中国史组、西洋史组、东亚史组、中亚史组、时事史组、考古组、历史教学组;中国地理组、世界地理组、地质学组、气象学组、地理教学组”[20]。在第六届史地研究会运行期间,会员就以上各组进行报名,除“签名过少之中亚史、考古学、地理教育各组”外,其余各组均成立。而从史学和地理各组的报名情况来看,报史学类各组的人数显然要高于地理学类各组的人数④。
可以看出,史地研究会为避免史地学的研究“混而不析”,意识到史学和地理学应分而治之,同时,因史学范围甚广,又将史学分成中国史组、西洋史组、东亚史组、历史教学组、史学理论及方法组等,体现出史学的学科化和专门化的趋向。
北京大学建立较早的史学会应是1919年成立的通史讲演会,设于国史编纂处内,会员以北京大学史学门学生、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和名誉征集员为主体,“余如本校教授、讲师及本校学生,愿入本会,尤为欢迎”[21]。1月21日更名为史学讲演会,采取分组研究模式,包括通史组、学术史组、法制史组、宗教史组、交通史组、经济史组、地学史组、风俗史组[22]。1922年4月,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鉴于“史学范围广大,图籍繁多,纵贯古今,横极中外,非群策群力广为稽考,而以一人驰骋其间,若涉大海,茫无津涯,欲其周遍综贯,盖亦难矣”,于是发起史学读书会,希望通过分工协作,进行各国史、各专门史的分别研究,以达到一理想之“溥遍史”与国史[23]。1922年11月15日,召开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因时间仓促,只是简单宣布了史学会委员名单及具体职责[24]。11月29日,召开第二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大学史学会简章》,对史学会的宗旨、会员资格、机构设置、研究事项、经费来源等等都做了规定。其中“研究事项”中,提到史学会研究科目暂分为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历史学和考古学等数种,要求“会员须就上列各科认定一种或数种,将共所研究者,提出讲演,或勒成论文,交付委员会发表”。此外还规定请学者进行讲演,以及“为便于发表研究心得及与国内外同志交换知识,得发刊杂志或各种单册及丛书”[25]。这已经是相当规范的史学机构了,不仅强调需分组以便进行专门之研究,而且注意到通过会员讲演、发表专题论文、请学者讲演以及创办专业杂志的方式,加强学术交流,推进史学的专门研究。
除了上述几种史学会外,20世纪20年代后,也兴起了不少的史学会,如1926年,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人柳诒徵、张其昀等人创办中华史地学会、燕京大学于1927年创立历史学会,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史学会被创办起来[26]。
三、余论
可以看出,20世纪初以来,在西学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史学已开始了学科化的进程,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在学科化的进程中,本身又表现出来一些不成熟的地方,这不仅体现在史学科系、史学会和史学杂志偏少,亦表现在这些史学科系、史学会、史学杂志多是以“史地”为名。这种将历史学和地理学合在一起创立科系、学会和学术杂志的做法显然与近代学术分科背景下史地走向分离的趋势是相悖的,亦不符合史学学科化进程中,应创立独立的史学科系、学会和学术期刊的要求⑤。不过,这种状况到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了改变,不仅这一时期诸多独立的史学科系、史学会和史学杂志创办了起来,而且即使在这些“史地合一”的科系、学会、学术期刊中,史学和地理亦走向了分离[27]。这是外在建制方面的走向。在理论方面,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除了上述叙述相关内容之外,我们发现,史学理论及方法的问题在此时受到特别之重视。这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大量史学概论类书籍的集中出现⑥;一是历史教科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开篇基本都会专门谈到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而大量史学概论书籍的出现,特别是史学理论问题被当作必须首先叙述的重点内容而写进历史教科书,表明历史研究中史学理论及方法之重要性,已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而被学人所分享。这种对史学理论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自觉反思,恰是史学学科的初步形成,在内在理论方面的重要体现之一。
① 关于一门学科形成的标志,吴国盛认为,判断一门学科的建立,在于两种范式的建立,一种是“观念层面的”,一种是“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观念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或者具体地说是一种研究纲领,以便同行之间相互认同为同行,以便新人被培养训练成这项学术事业的继承者;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共同体,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瞿葆奎、唐莹也指出,“评判一门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否成熟,其指标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属于‘理论’方面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一是属于‘实践’方面的——是否有代表人物、著作、学术组织、学术刊物等”。虽然讲的是教育学学科,但为我们思考历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分别参见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81页;瞿葆奎、唐莹《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代序》,转引自唐莹《元教育学——西方教育学认识论剪影》,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② 参见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王恩爵《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页;朱翊新《初中历史》(第1册),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2页;陆东平、朱翊新《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2页;周传儒《初中世界史教本》(上册),建设图书馆1933年版,第1页;白进彩《高中本国史》(上册),文化学社1935年版,第1-2页。
③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后,公布了《国立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简章》,会员扩至本校教师及校外人士,但会员仍基本上是文史地部的学生。
④ 参见《史地研究会第六届情形汇纪》,见《史地学报》1923年第2期,第152页;《史地研究会第六届纪录》,见《史地学报》1923年第4期,第163-166页。
⑤ 这里使用“不成熟”一词,并非意在比较“史地合一”与以史地分离为代表的学术分科孰优孰劣。史学学科化进程中的“史地合一”现象也并非近代中国所独有,日本、欧美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亦有这种现象,分别参见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1页;张其昀《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见《史地学报》1922年第1期;郑鹤声《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见《史地学报》1924年第8期。实际上,近代中国科系、学会、期刊上的“史地合一”对史学的发展、史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亦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这种注重类似通才培育的教育模式对今人过于强调学术分科多有启示,值得深入研究。
⑥ 有学者对此有较为详尽的统计,参见周文玖《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19页。叶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321页。
[1] 梁启超.新史学[C]//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C]//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583.
[3] 衮父(汪荣宝).史学概论[J].译书汇编,1902(9):105-112.
[4] 李大钊.史学要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3.
[5] 缪凤林.历史与哲学[J].史地学报,1921(1):1.
[6] 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J].史地学报,1923(7):23.
[7]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M].北平:独立出版社,1945:9.
[8] 奏定大学堂章程[C]//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9] 尚小明.北大史学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8-112.
[10]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6-8.
[12] 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C]//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459.
[13] 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C]//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372.
[14]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C]//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725.
[15] 1913年立学规则[C]//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78.
[16] 本会沿革[J].史地丛刊,1920(1):133-134.
[17] 会务纪事[J].史地丛刊,1922(1):2.
[18] 纪录[J].史地学报,1921(1):1-2.
[19] 史地研究会第六届情形汇纪[J].史地学报,1923(2)151,154-155.
[20] 史地研究会第五届纪事[J].史地学报1922(1):148.
[21] 国史编纂处纪事[N].北京大学日刊,1919-01-17.
[22] 国史编纂处开会纪事[N].北京大学日刊,1919-01-24.
[23] 发起史学读书会意见书[N].北京大学日刊,1922-04-19.
[24] 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N].北京大学日刊,1922-11-23.
[25] 北京大学史学会启事[N].北京大学日刊,1922-12-12.
[26] 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J].史林,2005(3):52.
[27] 姚正平.近代中国学术分科背景下“史地合一”现象原因论析——以史地期刊为中心[J].江汉学术,2018(4).
On the Preliminary Progress of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YAO Zhengping
( 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discipline refers to the change process of historiography from a traditional knowledge to a modern subject. It includ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uction. The former mainly refer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theory, such as the definition of history, the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works and history itself, and the high consistency i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y, and so on, while the latter is reflec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partments, societies, academic journals, etc.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immature a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general, historio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as taken shape from the late 1920s to the early 1930s.
historiography, discipline, theory, system
K092
A
1673-9639 (2021) 03-0121-07
2021-02-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史学与地理学关系的发展与互动研究”(17YJC770039)。
姚正平(1984-),男,安徽淮南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学。
(责任编辑 车越川)(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