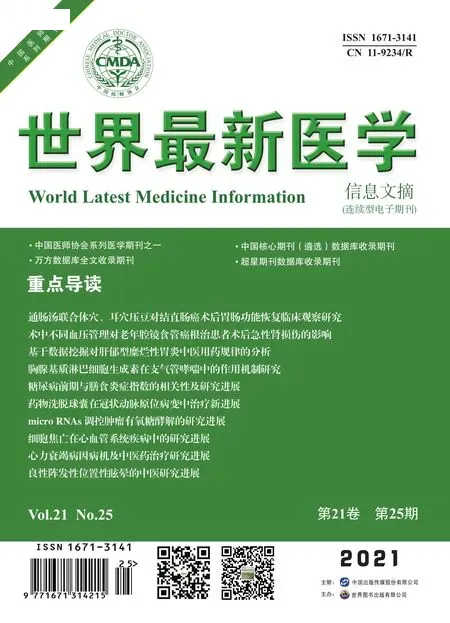血小板/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与冠心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龚明强,闫杰,徐御政,伊鑫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河北 唐山 063000)
0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糖尿病及肥胖等发病率的上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逐年上升,而其中的冠状动脉疾病所引起的心脏疾病目前在全球死亡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1]。虽然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的诊断和治疗策略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但CVD患者的数量和疾病的成本正在成倍增加[2-4]。冠心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心血管内科疾病,其形成的机理十分复杂,炎症和脂质积累是动脉粥样硬化作为一种慢性疾病的两个基本特征。炎症不仅是一种局部反应,而且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血小板释放参与血管炎症和血栓形成的血栓素、促炎趋化因子、转化生长因子b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胰岛素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等生长因子[5-6]。血小板活化在冠状动脉疾病(CAD)的所有步骤中起着重要作用[7]。活化的血小板参与血栓形成,以应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内皮细胞侵蚀,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血栓疾病或不良CV事件的发展[8]。另一方面,淋巴细胞计数是生理应激的指标,与炎症呈负相关;较低的淋巴细胞计数代表心血管风险和死亡率的增加[9-11]。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PLR)是两种重要的相反炎症途径的综合反映,很容易从一个完整的血液计数中计算出来。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也是一种廉价的工具,比血小板或淋巴细胞计数更具预测性。通过将血小板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相除来计算PLR。该PLR最初作为全身炎症生物标志物来预测肿瘤疾病的预后[12-15]。近年来,PLR已被用作各种CV条件下的预后指标。单核细胞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程中促炎物种的主要来源。在动脉粥样硬化中,修饰的低密度脂蛋白(LDLs)被巨噬细胞清除;这些被招募到血管壁中,诱导炎症细胞因子在炎症组织中的释放。因此,炎症胆固醇酯负载斑块产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通过抑制巨噬细胞的迁移和LDL氧化,以及胆固醇从这些细胞流出,中和单核细胞的促炎和抗氧化作用,表现出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此外,HDL在抑制单核细胞活化和单核祖细胞增殖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单核细胞的积累和HDL-C的减少可能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CVD)。本文就PLR及 MHR与冠心病的关系进行如下综述。
1 PLR在冠心病中的作用研究
1.1 PLR与急性冠脉综合征
由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的高死亡率,当前已存在不同的方法来提高早期识别高危患者的疗效,例如:使用高灵敏度肌钙蛋白、急诊科基于胸痛患者的CT冠状动脉造影结果进行评估和创建快速识别的胸痛中心[16-18]。破裂或侵蚀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上血栓的形成通常是ACS病理生理学的基础。血小板活化(粘附和聚集)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19]。血小板被血管壁细胞释放的物质激活,分泌出可参与血管炎症细胞因子以及促炎性趋化因子[20]。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斑块的不稳定、破裂,并且在复杂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处形成的血栓中血小板起着重要作用[21-23]。血小板计数与急性心肌梗死(AMI)风险增加和AMI后短期和长期死亡率相关[24-27]。平均血小板体积(MPV)是衡量血小板大小且主要与AMI、缺血性心脏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HF)有关[25-26]。 除了血小板活性增加外,血管壁的炎症似乎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及其不稳定也很重要[28]。淋巴细胞是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慢性炎症的重要组成部分,急性心肌梗死时,淋巴细胞浸润缺血再灌注心肌,表达多种白细胞介素(ILs),这些白细胞介素在单核细胞的迁移和诱导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的表达中起重要作用,低淋巴细胞计数与AMI死亡率增加 有关[29-30]。PLR是强调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的两个主要成分(血栓形成和炎症)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血小板和淋巴细胞计数的升高与心血管疾病的不良结局有关[31]。因此,PLR升高在预测不良心血管疾病结局方面可能比单独使用一个参数都更好。PLR在ACS中的预后重要性已经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探讨[32]。Hudzik等人研究了入院PLR对糖尿病合并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临床疗效和长期预后的诊断价值,结果表明,PLR值对院内和远期死亡率是一个较好的预测指标,虽然相对于预测晚期死亡率的PLR临界值,预测院内死亡率的PLR具有较高的临界值(分别为155和146),但PLR依旧是院内和远期死亡率的独立风险因子[33]。PLR在ACS患者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众所周知,它是与炎症程度相关的一个预后指标。我们有理由认为PLR是ACS患者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个良好的预后指标。
1.2 PLR与稳定型冠心病
既往研究都表明,在炎症以及血小板增多的众多生物标志物中,明显存在着与冠心病相关联的标志物。PLR结合了血栓形成和炎症参数,在预测稳定型冠心病(CA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负荷和心血管预后方面可能比单用血小板或淋巴细胞计数更有价值[34-35]。Trakarnwijitr等人研究发现PLR与CAD之间存在年龄相关性,高PLR是老年高危患者CAD的独立指标,但与年轻患者早期CAD呈负相关,鉴于他们在老年和青年患者中发现PLR和CAD之间的年龄相关关系,作者推测导致早发CAD的炎症途径与老年患者不同,早发冠心病可能与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比例失调以及高水平T淋巴细胞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有关[36-37]。在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中,用Gensini评分结合炎症标志物CRP对1646例稳定型CAD患者的PLR与CAD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PLR是严重CAD的独立预测因子,多元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PLR与CAD严重程度有显著相关性[38]。稳定型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在某些方面与ACS不同[39]。然而,炎症机制的作用是相似的。因此,可以推测PLR是反映炎症状态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预测稳定型CAD患者的不良结局和预后。
2 MHR在冠心病中的作用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高单核细胞计数和低HDL-C水平可能与炎症和氧化应激有关,据报道,MHR是几种心血管疾病中的一种新的预后指标[40-44]。董昭杰等研究表明MHR与冠脉Gensini 评分呈正相关(r=0.39,P<0.001)[45]。Karatas等发现MHR与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有关[46]。阿克戈兹等在文献中指出,MHR与 STEMI患者院内阶段和近五年内发生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cardiac event,MACE)以及长期死亡率具有独立相关性[47]。其他研究表明,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中,支架血栓形成率是MHR值升高的2.2倍。在这些患者中,MHR被报道为支架内血栓形成的独立预测因子(HR,1.08;95%CI,1.02-1.17)[48]。坎波拉特在文献[49]中指出了氧化应激水平的升高以及冠脉慢血流现象的发生都与MHR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此外,有研究显示较高的MHR水平可能预测STEMI患者PCI术后造影剂性肾病的发展(OR,4.48;95%CI,1.38-14.5)[50]。在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中,用SYNTAX评分评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和复杂性,在评分较高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中,MHR和CRP水平呈正相关(r=0.390),且显著高于评分≥23分的患者[51]。在接受了成功的裸金属支架的心绞痛患者中,MHR最高的患者的再狭窄率高于MHR最低的患者,两项不同研究的数据表明,MHR是支架再狭窄的独立预测因子(OR,1.45;95%CI,1.06~1.88)和(OR,1.29;95%CI,1.15~1.49)[52-53]。以上研究得出MHR能较好的预测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及可作为评估冠心病预后的一个指标。
3 小结
血常规和生化检测在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中很普遍,与其他炎症因子相比,PLR及MHR的获得简单方便,比较经济,便于计算。由于目前关于PLR及MHR与冠心病的研究处于起始阶段,仍然需要大量的实验去进一步研究证实,目前针对PLR及MHR在冠心病患者发生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将来或许可研制出新的药物用于阻断这一进程的发生,延缓冠心病的发生,为冠心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