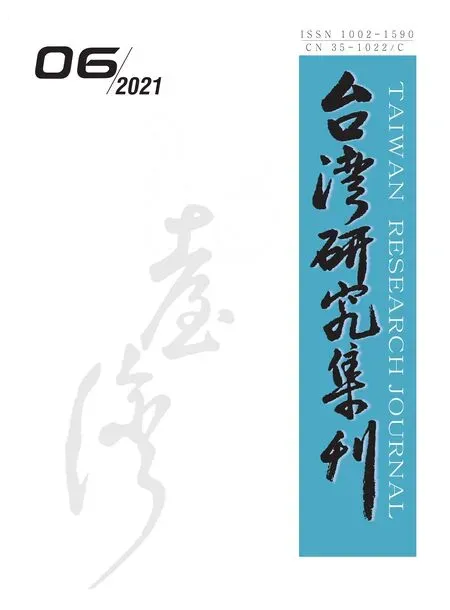论推进两岸完全统一的渐进治理路径
刘国深
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早在1950年初,中共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①孙亚夫、李鹏等著:《两岸关系40年历程》,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2页。尽管当前的两岸关系几近“极限爆炸”边缘,但大陆方面依然高举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大旗。②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http://www.gwytb.gov.cn/stzyjh/202110/t20211009_12383418.htm,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1月11日。大陆方面展现出从容不迫的自信和定力,意味着两岸双方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渐进夯实和平统一的基础。201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③赵博、许雪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2014年9月26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http://www.gwytb.gov.cn/zt/xijinping1/201504/t20150410_9544780.htm,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这一讲话再次明确:“领土主权统一”是当前两岸关系的“存量”,解决“政治对立”问题才是“两岸复归统一”所要追求的“增量”。中国内战遗留下的“政治对立”,本质上就是治理国家的道路之争、主导权之争。公共行政领域提出的治理理论对于海峡两岸的启示是:两岸双方可以尝试让两岸的公权力部门和民间社会力量成为两岸复归统一进程中的四大治理主体,从而摆脱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统治-被统治”思维窠臼。经由渐进治理的新路,两岸完全统一的进程将把海峡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历史、法理和政治事实,落实到两岸人民更加美好、体面、安全、方便、低成本的共同生活中。
一、渐进推动“两岸完全统一”之道
2008年12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再次强调:“1949年以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由此可知,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台湾问题,并不是追求中国的领土、主权统一,而是在维护中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存量”基础上,如何结束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实现国家治理统一的问题。两岸政治对立,本质上就是中国境内两个政权争夺治理国家、代表国家的权力,这一性质并不因台湾地区的政党更替而改变。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当局不仅失去治理国家的主导权,而且在主流国际社会丧失代表中国的实力和地位。至此,虽然大陆方面不承诺放弃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和平统一至今仍然是对台大政方针的主旋律。当前我们面对的“两岸完全统一”问题,本质上就是海峡两岸如何结束内战遗留的政权对立,建立起两岸双方共同接受并遵守的国内政治新秩序。
尽管实现两岸完全统一的方式仍然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作为专业的涉台研究人员,寻求以更高“性价比”的方式实现两岸完全统一是我们的天职。202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表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①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http://www.gwytb.gov.cn/stzyjh/202110/t20211009_12383418.htm,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1月11日。据此笔者认为:“如果说和平解决是追求至善,一旦选择武力解决则一定是迫于无奈。”②刘国深:《两岸关系发展模式及其趋势分析》,《台海研究》2021年第1期,第6页。因此,以和平方式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实现祖国最终完全统一,是大陆对台工作事业之“常”,以武力方式完成两岸最终统一则是“变”。尽管我们在感情上都期盼早日实现两岸统一,但两岸完全统一是以和平方式、战争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有没有时间表?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统领全局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手上。即使国家最终被迫选择以战争方式实现统一,也不会提前公布动武时间。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家事务已高度复杂和分化,全民恪尽职守,各行各业学有专精、术有专攻才是正道。
两岸完全统一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研究。我们既可以用“只争朝夕”来描述我们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进程的紧迫感,也可以用“气定神闲”来形容中央在涉台重大决策问题上的冷静和理智。我们必须将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去思考,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2000年以来的两岸综合实力对比和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功能来看,两岸关系的政治市场格局已经从所谓的台湾当局“卖方市场”转变为大陆主导下的“买方市场”,两岸关系主导权掌握在大陆手中,在两岸关系中处境艰难的不是大陆方面,恰恰是台湾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前相比,大陆方面遏制“台独”分裂的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这一趋势,“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比我们更着急,这才是蔡英文当局疯狂推出“台独边缘政策”、美国方面赤裸裸地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搞“离岸制衡”和“切香肠”式挑衅(也就是所谓的打“台湾牌”)的真正原因。
笔者认为,在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面前,任何抗拒和阻挠都是苍白无力的。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理和政治现实,落实到两岸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的融合上,在夯实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上实现两岸完全统一,这一路径不但可行,而且最符合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面对“台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挑衅,中国政府既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坚定落实对台大政方针,也有能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非和平的方式管控好台湾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两岸最终统一问题上始终都保留着三种基本的方式:一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二是以武力方式实现统一;三是“以战逼和”的方式实现统一。推进两岸完全统一是国家重大系统工程,必须使用综合实力,不能简单地把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系统控制、综合施策,理解成只有战争方式或和平方式两种选择。即使在台湾研究领域,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员也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有在各行各业井井有条、互相尊重、互不干扰、互为依托的状态下,渐进推进两岸完全统一,才能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最大化。
二、治理理论对两岸完全统一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交流交往产生大量的两岸共同事务,逐渐形成跨越海峡的“两岸间社会”。两岸密切的投资和贸易往来更是为两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在两岸政治对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两岸共同发展和人民交流交往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两岸公权力部门都是不小的挑战。在敌对关系结构之下,两岸公权力部门是难以围绕两岸民间共同事务进行有效合作的。为了解决两岸民间社会存在的大量治理问题,双方不约而同地引进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从震惊世界的1986年“华航货机事件”开始,两岸双方授权民间组织在香港进行接触、对话、谈判。这一模式为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开创了新路,此后的两岸红十字组织、海协会和海基会等受权民间机构成为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的重要参与者。2014年2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陆委会主委王郁琦首次举行会谈,这是两岸公权力部门第一次直接对话。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张王会”标志着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两岸公权力部门与民间社会之间、两岸民间社会之间形成了完整的共同事务合作治理机制。
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就是从传统的国家、政府等公权力部门自上而下的统治和管理,转变为公权力部门让渡、下放一部分权力给民间社会,由民间社会组织以市场机制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甚至由它们承担部分公权力部门委托的社会管理功能。简·克伊曼(Jan Kooiman)认为:“治理概念具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性的增长;治理不仅事关公共部门,也事关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①[英]史蒂芬·奥斯本编著:《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包国宪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显然西方学者更多关注政府公权力部门向民间社会组织让渡或下放一部分权力,但这一认识是狭隘的。笔者认为,权力的让渡和下放实际上并不仅仅发生在公权力部门与民间社会之间,公权力部门内部、府际关系之间也存在权力下放的问题;管理权限发生交叉重叠时,同级公权力部门的平行机构之间也可能发生权力让渡。对于海峡两岸来说,不仅大陆方面公权力部门存在多层级的上下分权问题,台湾方面也存在分权问题。大陆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承担了大量的两岸交流合作事务,台湾一些县市政府甚至村里组织也在两岸交流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组织庞大复杂的公权力部门内部做好权力的纵向分权和横向让渡,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尽管两岸政治对立尚未结束,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冲突还大量存在,但海峡两岸已然存在法理上和政治上的某些秩序,这些规则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或认可。对于中国大陆方面来说,将台湾地区作为中国境内一个特殊地区进行管控,这不是什么“新闻”,而是既成事实。台湾方面虽然仍在抗拒大陆方面的管控,但这样的抗拒是有限的。如果台湾方面“抗争”的尺度过大,必然招致大陆方面对台湾更近距离、更紧迫的直接管控。这在过去几年的两岸政治、经济、军事、涉外政策互动中有大量例证。台湾方面有些人认为“大陆方面从来没有治理过台湾”,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台湾当局的涉外活动早已处在中央政府的治理行动之下,台湾地区电信诈骗犯受到大陆司法部门治理和审判的也不在少数,台湾周边常态化的军事存在也是中央政府管控台湾地区的例证。近年来,大陆方面陆续出台大量惠台政策、在陆台湾居民同等待遇政策及其落实办法,最近还公布了对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的措施。这些都说明中央政府对两岸政治、军事、外事、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领域共同事务的治理正在逐步推进和落实之中。当然,在内战尚未正式结束的情况下,不同领域治理的力度和成效有所不同,有些领域的对台治理能力还是比较初步甚至是低下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央地关系”,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实行“有限治理”,换个角度说也是一种“央地分权”或地方自治模式。
依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完全统一”后,台湾地区将拥有高度自治权。海峡两岸确立起共同依循的政治秩序以后,台湾地区将实施“一国两制”,中央与地方分权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台湾地区现有的优势和长处有可能成为两岸完全统一后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在治理理念下,参与两岸治理的主体还可以包括且不限于民间社会组织。“一国两制”之下,民间社会可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解决涉及两岸的共同事务问题。为此,在两岸完全统一之前,可以结合治理理念率先推动两岸合作治理。在目前两岸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公权力部门的合作治理遇到不少困难,而治理理论的多元合作模式为两岸合作治理预留了一定空间:即使台湾当局不合作,大陆方面公权力部门与台湾的民间社会之间依然可以合作,两岸民间组织之间更可以继续合作。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我们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①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19年1月2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http://www.gwytb.gov.cn/zt/xijinping1/201901/t20190102_12128140.htm,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1月11日。从上述讲话可以看出:只要民进党愿意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可以继续合作。在民进党当局与大陆官方建立合作基础之前,目前的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可以由大陆方面公权力部门及民间社会组织与台湾其他政党、团体、各界代表性人士进行合作。
三、两岸渐进治理的局限性
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中的渐进治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治理理论,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有所为有所不为。西方治理理论多少存在着“去政府化”“去国家化”的倾向,这些方向不适用于两岸统一进程。两岸政治对立的本质和大陆方面具备压倒性优势的现实,决定了两岸统一进程中的渐进治理虽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但不必讳言大陆方面公权力部门居于主导地位的客观事实。在两岸治理过程中,大陆方面要尽可能包容和尊重台湾方面的参与者,但涉及公权力权威和强制力行使领域,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有时会非常尖锐。这种控制与抗拒的博弈往往是不可协调的,冲突不可避免时就必须以实力地位来说话,这将是两岸走向完全统一过程中绕不过去的规则。两岸渐进治理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国家下的两个实力悬殊的对立政权。两岸渐进治理的模式可以是台湾地区公权力部门参与的“两岸共同事务全面合作治理”,也可以是在台湾当局“缺位”情况下,大陆公权力部门及民间社会力量与台湾地区民间社会力量合作下的“两岸共同事务不完全合作治理”。这种涉及公权力之间的对抗,最终将基于实力地位产生一种新的平衡,如果不能取得平衡,就会影响到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的形态和有效性,弱势一方可能在某些领域被限缩参与治理的机会。
马英九在台执政时期,两岸公权力部门的合作上了一个大台阶,台湾方面不仅扩大了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的参与,而且在国际社会扮演了比过去几十年更多的角色。民进党当局在台执政后,部分两岸事务的合作治理遇到困难。民进党当局在两岸共同事务治理领域的角色扮演明显萎缩,国台办与陆委会、海协会与海基会的直接往来甚至停摆。但是,两岸公权力部门的合作治理实质上没有完全停止,有些事务转由民间机构“代偿”了,例如疫情期间国台办、海协会与全国台企联、各地台商协会的密集互动就是一种官民合作治理的方式。由于两岸间社会已经达到一定规模,ECFA等两岸签署的几十项协议不同程度地继续执行。如果没有得到双方公权力部门的认可和协助,这些合作治理是不可能存续的。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在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的进程较之马英九执政时期困难了许多。
大陆方面在两岸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平统一的艰巨性,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两岸最终完全统一的进程必须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多元参与。在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中搞“去国家化”“去政府化”是完全不可行的,民间社会力量是两岸公权力部门的合作者。西方主流治理理论并没有否定权威的重要性,强制性治理也是治理的方式之一。我们毕竟生活在政治社会,国家强制力是不可或缺的。在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中,参与两岸渐进治理的所有主体都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基础上,为两岸人民更加体面、安全、方便、低成本地生活在一起发挥正能力;否则,以大陆方面公权力部门为首的其他参与主体有责任采取行动进行规范和制衡,这也是治理主体自身的治理问题。
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中的渐进治理虽然是以和平、合作方式为主,但也不能排除使用强制力。大陆对“台独”分裂势力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也是一种治理手段,甚至是渐进治理的必要补充。在两岸政治对立结束之前,两岸共同事务的多元合作治理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障碍,这是渐进治理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在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强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当前两岸治理主体之间的分权并不都是和谐有序的,特别是台湾当局的角色、功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一些参与治理主体的治理也要多元施策,除了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实力与权力博弈外,如何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文化氛围等环境变迁入手,从根本上约束各治理主体的行为,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B.盖伊·彼得斯(B.Guy Peters)曾经提出“元治理”的概念。他说:“元治理可解释为,公共部门内部的大量组织和管理过程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种状态通常被描述为治理),进而有必要对治理的各个构成要件施以一定的控制。”“元治理工具强调对社会和经济的引导。”“元治理被认为是趋向于对公共部门的行为环境进行控制,而不是对行为本身进行直接控制。”①[美]B.盖伊·彼得斯:《元治理与公共管理》,见[英]史蒂芬·奥斯本编著:《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包国宪等译,第34页。对于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中的渐进治理来说,如何在治理过程中通过环境变迁来约束和改变治理主体,“元治理”的确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实际上,两岸融合发展就是一种“元治理”,在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规范和约束台湾当局的治理角色及功能,不失为与大陆方面公权力部门管控台湾问题并行的另一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