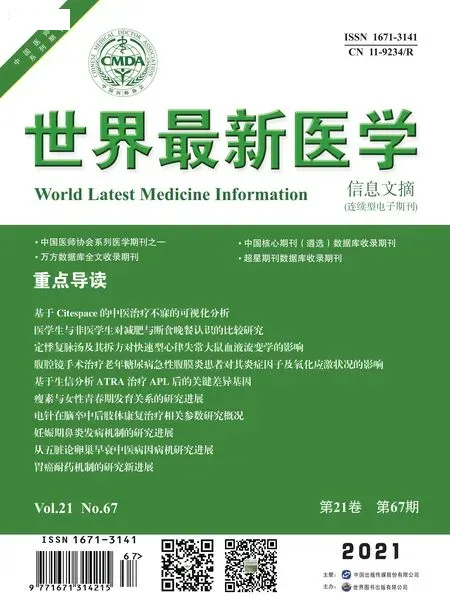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与家庭无效环境的相关研究
路文文,刘铁榜通信作者)
(1.济宁医学院,山东 济宁 272000;2.深圳市康宁医院,广东 深圳 518001)
0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心理健康问题。同时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事件的频发,敲响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警钟。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全球爆发加剧了这些担忧,原因是与社会、家庭、经济和健康压力有关的风险因素增加,此外典型的支持系统也发生了变化[1]。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探索家庭无效环境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为减少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发生,减少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对其家庭造成的困扰提供帮助。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e self-injury,NSSI)是指在没有自杀意念的情况下,直接而蓄意地伤害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其特征是自我伤害,主要发生在四肢和腹部,在青少年患病率高达17%-18%[2]。虽使用的定义和方法不同,不同研究对NSSI患病率的估计大致相同,根据Swannell Martin等人的meta分析,青少年NSSI患病率为17.2%,且地理区域差异不大[3]。在描述自伤的功能时,通常使用四因素模型,即自我、社交的积极及消极的强化作用;例如,自我积极强化是在NSSI行为中体验到积极的感觉(如活着的感觉);自我消极强化指减少消极的情绪体验(如紧张、愤怒);社交的积极强化是指加强社交互动(如获得关注、传递信号),而社交的消极强化则是逃避不愉快的社交互动(即结束争吵,拒绝学习)的一种手段[4]。Mars B研究表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出现也是青少年自杀行为最重要的预测因子之一[3]。
Linehan在1993年首次提出家庭无效环境(family invalidation)的定义:指父母对儿童个人情感表达的否定、忽视、惩罚等一系列不恰当反应[5]。随着心理学及精神卫生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家庭无效环境这一主题。不同专家学者赋予这一概念不同的理解和外延,由张英俊等人总结:家庭无效环境是指照料者对儿童情绪体验、感知觉体验、认知体验、个人行为体验的表达做出惩罚、忽视、否定、审判性反应,及非法化、虐待、过度保护以及病理性的反应[6]。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1.1.1 资料来源
由本文作者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于万方医学网、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及PubMed数据库进行了多次检索,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1年2月。
1.1.2 检索策略
在万方医学网、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采用关键词检索“家庭无效环境”“家庭环境”“父母”“照料者”“情绪调节”“情绪认知”和“青少年”和“非自杀性自伤”;在PubMed数据库中采用MeSH:Family主题检索,检 索 到“Families”“Family Life Cycles”“Family Life Cycle”“Family Members”“Filiation”等25个 词,选 取与本文相关的18个主题词进行((Family [Title/Abstract])OR(Families[Title/Abstract]))等高级检索,检索到28946篇文章;在PubMed数据库中采用MeSH:non-suicidal self-injury主题检索,检索到“Self-Injurious Behavior”“Self Injurious Behavior”“Intentional Self Injury”等26个主题词,选取与本文相关的21个主题词进行((Self-Injuriou Behavior[Title/Abstract])OR(Non Suicidal Self Injury [Title/Abstract]))等高级检索,检索到9991篇文章。最后将两次检索到的文章进行(合并)AND检索,检索到59篇文章。
1.2 文献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1)主要叙述家庭无效环境或父母批评、父母虐待等家庭无效因素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相关的文献;(2)中英文文献。排除标准:(1)不符合本文主题的文献;(2)2010年之前发表,对目前研究现况不重要的文献;(3)寻找不到全文的文献。
1.3 文献筛选与质量评估
按照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文献,查看其文献的影响因子及刊登期刊,结合文献内容、评估量表、研究方法、样本量等问题,最终一共纳入48篇文献。选取的文献可充分了解,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与家庭无效环境的现况研究。
2 NSSI与家庭无效环境相互关系
2.1 NSSI与家庭无效环境呈正相关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有研究发现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与青春期的情绪调节困难存在显著联系[7],理论上来说,随着大脑前额叶区域的持续成熟,情绪调节发展在青春期表现出积极的成长轨迹,但情绪调节发展变化的个体差异值得我们去关注[8]。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家庭无效环境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缺乏情绪的认知与调节能力[9],从而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表达、自我发展、人格发展、亲人依恋等多方面[6]。一项在中国安徽农村中学的研究发现大部分NSSI青少年有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问题,如家庭凝聚力的缺乏、父母的批评、父母的过度保护、过度参与、亲子沟通不良等[10]。本文中家庭的无效环境主要从家庭成员、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及家庭成员关系这三方面来分析。
2.1.1 家庭成员
首先从家庭成员分析,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父母在家庭成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父母也是孩子主要的照料者;如青少年的父母存在药物滥用、精神疾病、监禁等问题,则青少年自我伤害的几率是普通青少年的三倍[11]。在一项前瞻性的研究中发现父母情感的不稳定是唯一能够区分非自杀性自伤组和有自杀企图组的因素[12];在王玉龙等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当父母角色的缺席,父母的照料、支持和监督减少时,青少年NSSI行为有增加的可能[13]。当照料者为非亲生或为寄养时,青少年NSSI行为的发生率高于一般青少年[14]。在儿童福利系统中,非自杀性自伤和自杀行为非常普遍,青少年信任的父母给予的支持,与青少年自我伤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15]。家庭无效环境与青少年NSSI行为存在某种级联反应,当照料者发现青少年有NSSI行为时,照料者通常会感到负罪感、恐惧和羞愧感,这种负面情绪和自我评价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过度警惕,增加照料者对孩子行为的控制;然而青少年会觉得这是一种侵犯,从而导致家庭功能恶化,进一步增加青少年NSSI的风险[16]。
2.1.2 家庭互动
在家庭成员的互动中,父母对孩子的威胁、羞辱或侮辱等重复的行为模式统称为情感虐待,情感虐待的经历可能会干扰儿童调节强烈负面情绪的能力(如愤怒、悲伤、恐惧或羞耻),然后使用NSSI不适当地管理这些情绪[17]。父母的高度批评、责备等高情感的表达,也会使孩子对自己产生消极的表现,反过来增加NSSI的可能性[18]。儿童被忽视与情绪调节不良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情感忽视及身体忽视也是青少年NSSI的危险因素[19]。有关儿童及青少年被虐待的研究有很多,但较少单独叙述身体虐待对青少年NSSI的影响,大部分研究是与性虐待同时分析。家庭中存在不同形式的虐待,而身体虐待或性虐待,可以改变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的有效疼痛感受器,降低疼痛的阈值,从而加重青少年NSSI的可能[20]。研究发现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是通过影响情绪表达能力和情绪应对能力来影响青少年的NSSI行为[21]。统计研究发现遭受过身体虐待的青少年进行NSSI行为的几率比未受虐待的青少年高出49%。而遭受过性虐待的青少年进行NSSI行为的几率比未受虐待的青少年高出60%[22]。
2.1.3 家庭关系
最后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分析,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的不良家庭环境,对亲子关系产生负性调节作用,而不良的亲子关系会使家庭环境进一步恶化[23]。亲子关系囊括了亲子间的凝聚力、亲子依恋及亲子间的疏离感等方面。有NSSI的青少年与无NSSI的青少年相比,与父母的关系质量更差[24]。一些研究在确定亲子关系与早期NSSI相关的具体维度时发现,亲子关系中的恐惧和疏远是唯一可以预测NSSI的维度;但具有性别差异性,在女性中有类似的结果,而男性的分析中没有显著性[25]。对比亲子关系及照料者经济地位时发现,亲子关系间的凝聚力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亲子间的凝聚力比照料者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更显著[26]。不安全型依恋儿童的痛苦反复得不到解决,会使他们自身调节情绪能力的发展受到损害,从而出现NSSI行为;不安全的亲子依恋通过情感和行为问题成为青少年NSSI的潜在风险因素[27]。Martin等人发现,依恋与更频繁与严重的NSSI相关[28],在亲子间的疏离感这种关系中,青少年的情绪被长期忽视,即便没有虐待,仍然是NSSI的危险因素[29]。
2.2 NSSI与家庭无效环境的评估
2.2.1 NSSI的评估
文献中出现的非自杀性自伤的评估量表很多,本文仅选取临床上常见且信效度较高的2种量表。自我损毁功能评估(FASM)由Lloyd等于1997年编制,用于评估自我报告的自伤行为的方法、频率和功能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包含11种自伤行为清单,了解患者在过去一年里自伤的基本情况;第二个部分包括了22个自伤行为的动机陈述的清单,如:情绪管理、人际影响、自我惩罚等功能。值得我们关注的是,FASM在正常人群和精神科病人样本中都适用。蓄意自伤量表(DSH)由冯玉结合Graze于2001年编订的,并且在郑莺的 《中学生行为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删减、修改原来问卷的条目,最终形成的。包括18个条目和1个开放式问题。该量表主要用于评估患者自伤的频率、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自伤的类型。
2.2.2 家庭无效环境的评估
家庭无效环境的评估目前尚无信效度明确的量表,目前较为常见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及家庭环境量表尚未纳入性虐待、躯体虐待等无效因素,因此本文考虑纳入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来填补这一空缺。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CTQ-SF)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Bernstein等编制,由国内赵幸福译成中文,用于评估儿童期家庭被虐待经历的自陈式问卷。该问卷共28个条目,6个因子:躯体虐待、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性虐待和不良环境。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是由瑞士学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编制。EMBU中文版最早在1993年由中国医科大学岳冬梅修订。问卷分为六大类:(1)情感温暖;(2)惩罚、严厉;(3)过分干涉;(4)偏爱;(5)拒绝、否认;(6)过度保护。共66个条目,父亲量表不含有19,24,26,38,41,47,54,63;母亲量表不含有5,10,18,20,21,40,49,66。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由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在美国心理学家MossRH编制的“家庭环境量表(FES)”的基础上修订改写而成。该量表含有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征:(1)亲密度;(2)情感表达;(3)矛盾性;(4)独立性;(5)成功性;(6)知识性;(7)娱乐性;(8)道德宗教观;(9)组织性(10);控制性。
2.3 NSSI在家庭无效环境方面的治疗及干预
2.3.1 家庭早期识别
早期发现和干预对减少青少年NSSI的负面后果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首次自我伤害的年龄小于12岁,可能是重复自我伤害和潜在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30]。青春期是预防和干预NSSI的关键期,因此照料者应提高对青春期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识别,减少青少年NSSI的发生。
2.3.2 家庭角色扮演
通过对家庭功能的评估发现,没有自伤史的青少年与其父母对家庭功能的评估基本一致;但有自伤史的青少年对家庭功能评估比其父母的更差[27]。因此我们以家庭为基础干预,侧重于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改善换位思考任务,可以让父母和青少年了解彼此对自我伤害等问题的看法。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换位思考可能是基于家庭的青少年自我伤害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
2.3.3 家庭依恋
有研究表明加强家庭之间亲子依恋的治疗可能会有效地改善青少年的NSSI。例如孩子学会了更好的沟通技巧,父母学会了更有效地回应孩子的行为和需求。反过来,依恋安全的改善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降低青少年自我伤害的风险[23]。这些方法在预防青少年自我伤害方面的有效性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3.4 家庭支持
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对自我伤害的治疗和干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Tatnel等在对1973名青少年进行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家庭支持的减少预示着自我伤害的维持(≤12个月),而家庭支持的增加预示着自我伤害的停止[31]。家庭支持是治疗青少年NSSI的重要方法,即使青少年已经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也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支持,减少家庭无效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
3 小结与展望
家庭环境是孩子成长中最为重要的环境,父母角色的缺失、父母的虐待、亲子关系较差等无效家庭因素,与日后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呈正相关。因此我们应该在孩子的成长中避免或减少无效因素的存在,从而减少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出现,甚至是减少自杀。即使家庭无效因素已经出现,家庭无效因素的减少仍会降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风险。也可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通过家庭角色扮演、加强亲子依恋、增加家庭支持等方法,减少家庭无效环境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