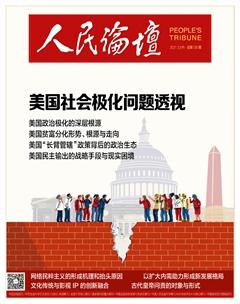美国贫富分化形势、根源与走向
陶涛
【关键词】中产阶级 贫富分化 机会平等 反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71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而言,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一国国内贫富分化会经历一个先恶化而后不断改善的过程。但是在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二战后普遍却经历着一个相反的过程。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逐步缩小,美国的中产阶级一派欣欣向荣。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大,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程度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一趋势持续了近40年。自2020年以来,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系统性失败,使贫富分化的形势愈加严峻。由于较长时期内不平等的体制性根源难以得到解决,这种严峻形势将长期持续。
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过贫富分化加剧而后减缓的过程。19世纪下半叶,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不斷扩张,工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激增。一方面,在这一经济欣欣向荣的“镀金时代”,资本垄断不断加深,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资本家和大财团手中。截至1910年,占美国人口10%的群体拥有全社会高达80%的财富,其中一半以上集中于前1%群体;而另一方面,底层工人收入低、工作条件差,陷入长期贫困。市场垄断、环境污染和民众普遍的沮丧感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激发了一系列进步运动。20世纪初,美国政府改革税法,对高收入、高额财富征收累进税,颁布反托拉斯法,允许工会组织罢工。之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对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重新洗牌,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财富不平等现象得以大为缓解。二战结束时,美国前10%群体的财富占比降到65%。二战结束后,机会平等、经济平等的价值理念得以持续,累进税、遗产税、强势工会和金融管制等经济制度抑制了收入和财富集中。20多年间,美国经济强劲发展、国民财富不断扩张,机会平等造就了顺畅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了“美国梦”,中等收入阶层不断扩大,贫困家庭日益减少,“中产阶级的美国”得以形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导致贫富分化日趋加剧。

贫富分化来自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美国收入不平等体现了绝大多数底层和极少数顶层之间的分化。总体来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从1985-2013年,美国收入基尼系数从0.34上升到0.40,达到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水平。虽然同期发达国家国内收入不平等普遍加大,但绝对水平远低于美国,基尼系数在0.35以下,甚至0.3以下。收入不平等加大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收入水平变动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底层群体工资小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极少数顶层群体工资大幅上涨。根据华盛顿特区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工资水平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一直在下降,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缓慢上升,直到2017年才回升到1980年的水平。从1980年到2018年的30多年间上涨幅度只有4.1%。与此相对,顶层群体工资水平却是数百倍的增长。1965年,美国企业高管年薪是普通员工的20倍,1978年增长到29.9倍,但到1995年大幅提升为122.6倍,2000年跃升为376.1倍,2008年金融危机后差距有所下降,经济复苏后又回升,2014年依然高达303.4倍。此外,顶层群体除了工资收入之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报告,2015年,前1%家庭收入的只有不到40%来自工资性收入,而后90%家庭收入的80%以上来自工资性收入。就是说,一方面,底层群体工资水平长期无增长、收入来源单一;另一方面,顶层群体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且有其他多种收入来源。这两方面因素导致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和前1%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美国中低层收入和财富缩减、顶层收入和财富大幅提升,造成了“贫者贫富者富”和“中产被挤压”的贫富分化。美国政治家桑德斯在其著作《我们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当今美国的贫困率为13.5%,高于20世纪60年代,贫困人口达4310万人之多;儿童贫困率最高,有19.7%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1999年到2014年间,贫困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增加了约10%。由于收入和财富更多向顶层集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占比不断下降。中等收入家庭是家庭收入位于该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水平的75%与200%区间的家庭,在这个区间之上的为高收入家庭,之下的为低收入家庭。中产阶级一般指的就是中等收入家庭。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OECD国家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比例平均而言处于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64%,21世纪10年代中期降到61%。其中,美国下降幅度最大。2017年美国有60%的人口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收入家庭人口,而实际中等收入人口占比只有50%,为发达国家最低。也就是说,不仅贫者更贫,那些在二战后数十年间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家庭的一部分已滑入低收入群体,难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不难发现的一个事实是,近40年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提高。不平等是当代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和正常现象吗?新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不平等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经济自由的含义就是人们拥有获得不平等结果的权利,恰恰是不平等的结果激励各种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努力提高生产率以获得丰厚回报。自由市场竞争激励资源有效配置,驱动经济不断增长,使国家和个人财富日益增加。经济繁荣和财富扩张自然会向下渗透,形成涓滴效应,改善底层收入和福利,实现整体福利改善。所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是正常现象。但不幸的是,这个观点的两个论断——自然结果和涓滴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并不成立。
首先,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并非基于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所谓自然结果,指的是投入获得相应回报。受教育水平低的简单劳动的生产率低,报酬低;而受教育水平高的熟练劳动,其生产率高,报酬也高。生产率差异造成了收入差距。比如,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因而会改变其报酬的差异。全球化激励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要素竞争,会提高生产率更高的劳动或资本的回报,也会通过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其报酬。回报的不平等体现了要素生产率和需求的差异。作为现实结果的不平等不是“自然”的结果,取决于所有劳动者和资本是否可以自由地、机会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美国存在过高的经济租金,体现了机会的极不平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美国公司利润30多年来在实际市场利率下降的情况下不断增长。企业利润大于资本回报表明一部分本该属于劳动者的报酬被资本攫取了。此外,部分行业过高的市场集中度、一些倾向于保护富人的土地管制、甚至越来越多的职业许可政策都激励了寻租行为。大量寻租行为和过高的租金表明不平等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是机会不平等下的非自由竞争的结果。
另一个证据是美国工资收入差距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越来越弱。受教育程度某种程度上反映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20世纪80-90年代,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差距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关性很大。1980年制造业白领工人工资是蓝领工人的1.5倍左右,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加到1.7倍。这一变化是白领实际工资持续上涨的同时蓝领工人实际工资大幅下降带来的结果。但是近20年来,大量的寻租行为不断增强市场势力,收入不断向大企业、大资本、垄断性行业倾斜,美国工资差距越来越大,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越来越弱,要素的生产率不再是决定其收入的关键因素。
其次,经济增长没有通过涓滴效应实现水涨船高式的福利改善。在涓滴效应作用下,经济增长会带来整体福利改善,在社会中上层收入和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底层的收入也持续稳定提高,生活、健康和教育因此得到改善,财富得以积累,存在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但从美国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来看,涓滴效应并没有发生有效的作用。第一,几十年来在国家财富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底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几乎没有增长,造成贫者更贫,大量底层人口陷入再贫困化,营养、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都难以得到相应改善。第二,中产家庭向下层滑落意味着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被阻断,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也没有得到改善。第三,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的贫困化加剧。20世纪60年代,美国白人的收入是黑人的 2.5 倍左右,20世纪80年代之后,种族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近些年一个典型白人家庭的财富是黑人家庭的8倍。这种差距之下,美国黑人相对于白人更加贫穷,使得种族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加剧。
收入之所以向少数行业、少数群体集中,是因为市场并未实现充分竞争,回报没有自然地流向投入者,而成为少数群体的经济租金。福利之所以没有向底层大多数渗透,是因为向上层倾斜的民主制度、经济制度,导致财富向顶层集中。倾斜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市场竞争中的机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是机会不平等下扭曲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向上层倾斜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令发达国家陷入经济滞胀,之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等自由理念取代平等的价值观,美国经济制度转向推崇私有化、放弃强征累进税、削弱工会、放松金融管制,推动美国经济走向新版“镀金时代”。一方面,经济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推动之下飞速扩张;另一方面,財富不断集中,社会流动性趋于停滞,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持续疲软,陷入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一度高达9%,贫困人口进一步增加。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10年美国贫困人口达4620万人,贫困率高达15.1%,为52年来最高。房地产泡沫破灭使中产家庭的资产严重缩水,经济衰退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加剧了他们向社会底层下沉。危机冲击之下,大众对不平等的怨恨不断升级,不满情绪一触即发。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大众走向街头抗议前1%群体对其他99%群体的极端不平等,抗议社会不公、政治不公,变革不平等的民主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国不平等与贫富分化形势恶化达到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推进反全球化措施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21世纪以来,信息通讯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不断降低跨国生产和经营的成本,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了全球性的生产和供应网络,不仅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很多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也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因而降低了对美国低技能群体的需求。因此,叠加了技术进步效应的全球化很容易成为美国失业和工资差距加大的替罪羊。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断采取措施,发动贸易战,增加贸易和投资壁垒。来自国外的进口规模下降和本国生产规模扩大,在短时期内确实会增加某些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有利于缓解经济萧条。但是中长期内,由于低价进口品减少,物价上涨、消费支出增加,将令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企业应对国内高工资和生产成本的方式是不断增强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这将导致资本对劳动的进一步替代,使得反全球化的就业效应在中长期内失去作用。
虽然收入不平等有所缓和,但是财富高度集中、中产被掏空的状况并没有改善,民众对美国中产阶级境遇的失望、对不平等民主的愤怒不断积累,推动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保守主义浪潮的兴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在加大反全球化的同时,实施了一系列反移民措施,激化了种族矛盾,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侵蚀了美国经济复苏以来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改善,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社会经济形势令美国不平等和财富分化的形势更加严峻,而反全球化措施未能根本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必须对不平等采取新的行动,转向有效率且更公平的经济增长被广泛讨论。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将推动倡导机会平等、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即包容性经济增长确立为政策目标,体现了政府层面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政策清单包括利用货币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增加就业和收入;扩大对低收入家庭的支出来促进机会平等;减少寻租行为,寻求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累进税等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这也表明政府层面对机会不平等和市场不公平竞争这一内在根源的认识及解决方向的针对性。
2021年11月,价值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终于出台,显示了政府在提振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方面的信心和努力。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化解疫情之下的经济萧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如前所述,一定时期内确实能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但既难以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贫富分化。因为美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对经济增长潜力造成几方面不利影响。首先,中产群体萎缩、底层群体巨大,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导致总需求不足。其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造成的教育、培训、营养、医疗等机会不平等,削弱了劳动者的质量,对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投入具有负面效应。最后,由于底层群体庞大,社会对基础设置、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投资的动力不足,造成公共投资规模有限,削弱生产率提高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改善公共投资不足,不能解决影响长期增长的其他问题,与推进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清单更是相距甚远。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镀金时代”的再现。不平等和财富分化形势严峻亟待采取行动在美国已经达成共识,作为根源的机会不平等正在不断被揭示——不平等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是向上层倾斜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不公正的结果。机会不平等背后的价值观和经济理念正在反思、辩论与碰撞中,在回归机会平等的价值观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念成为主流思潮之前,即便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蓝图已然绘制,政策制度清单也只会停留在纸上。无论如何,在不触动制度根源的前提下,反全球化措施只能治标。走向包容性经济增长,美国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严峻形势还将持续。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②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How to fix economic inequality?, 2020.
③Elise Gould,Decades of ris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S, 2019.
④Lawrence Mishel and Alyssa Davis,Top CEOs Make 300 Times more than Typical Workers,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Issuer Brief,2015.
⑤OECD,Under Pressure: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OECD Publishing,2019.
責编/孙垚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