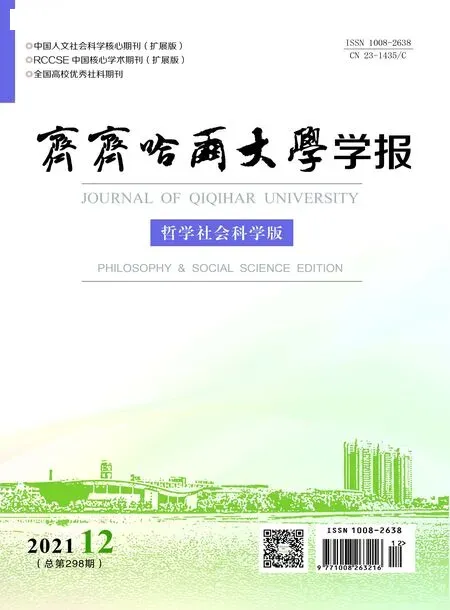宋代笔记俗语词的词义衍生与演变考论
齐瑞霞
(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
宋代是笔记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产生大量俗语词的历史时期。笔记发展到宋代,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空前发展;又由于笔记具有写作的随意率性,内容的不拘一格,形式的不循规矩等特点,也形成了其“语言鄙俚,不以文饰”[1]的文体风格和语言特色,突出表现为出现了大量俚俗乡言,使得笔记成为俗语词存在的重要载体,也为汉语俗语词研究提供了直接和丰富的基础语料。
词汇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有很多俗语词,在其产生初期,词义相对直白易懂,但时间久了,逐渐成为了疑难词语。朱熹讲读《尚书》时就提到了词汇由“易晓”到“难晓”甚至“理会不得”的问题。《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人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若使古人见今之俗语,却理会不得也。”所以,只有将具体的词语置于一个发展变化的序列中,通过搜寻其早期或关键性用例,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其词义形成及流变过程。词义衍生作为词义形成的重要方式,是在词的理性意义基础上,因受到认知范围、句法环境、语法功能等因素的影响,经过引申、泛化、虚化以及语法结构的重新分析等而衍生出新的词义,这也是宋代笔记中俗语词词义形成及演变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一、词义泛化与专指
(一)词义泛化
有些词语由于表达的需要而临时扩大使用范围,由此词义发生泛化。如果这种用法频繁发生,泛化后的词义就会逐渐稳定下来,从而被人们接受和认可,于是就形成了该词的一个新义项。宋代笔记称谓类俗语词中有的就是由古代的官职称谓或亲属称谓经过泛化而形成的。
如“博士”,战国时期即为官职称谓,至宋已逐渐成为对精通某种技艺或者从事某一类职业的手艺人的尊称。宋代笔记中常见“酒博士”、“茶博士”、“医博士”等称谓。又如“待诏”,在唐朝时本为官职称谓,宋时也发展为对手艺人的尊称,如“琴待诏”、“书待诏”、“棋待诏”等,而且理发匠也被称为“待诏”。再如“黄门”,也本是官职名,是“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的简称。因汉代设立的黄门令、中黄门等职也可以由宦官担任,所以,黄门也用来指宦官,后来民间用以指称天生没有生育能力的男子。《齐东野语》卷十六:“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命之曰黄门。”上述三例最初皆为官职称谓,至少到宋时就已泛化为一般性称谓类俗语词,词义范围扩大了。
亲属称谓词的泛化在宋代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哥”。宋代称兄为“哥”,用法与现代汉语无异。《鸡肋编》卷上:“呼父为爹,谓母为妈,以兄为哥,举世皆然。”也可称“哥哥”。《齐东野语》卷十三:“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脱,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冠,则有万回佛自怀中坠地。其旁者云:‘他虽做贼,且看他哥哥面。’”至宋,“哥”词义产生泛化,突出表现在宋人名字中喜用“哥”,但“哥”仅表示男性,已无“年长”的意思,用于名字中多表示“亲近”义。如《夷坚志》中有“王小哥”、“孙五哥”、“詹小哥”等,《武林旧事》艺人中有“谢兴哥”、“刘春哥”、“王安哥”、“阮舍哥”、“金寿哥”等。而且宋代歌女也被称为“奴哥”“姐哥”等,这里“哥”的词义中,“男性”这一区别特征已经消失,仅表示一种亲昵的感情色彩,词义进一步泛化。
(二)词义专指
与词义泛化相反,词义专指是原本适用于一般领域中的词,使用过程中词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仅限于特定领域中使用,从一般词语转变为专指。宋代笔记中较多此类俗语词用例,如“门客”、“娇客”。“客”在古代指那些被有身份或地位之人豢养的人,因其有一定学问技能,常寄居于达官显贵门下,为其服务,故称“门客”。至宋代,原义已渐少用,较多的成为对延请的家庭教师的敬称。《老学庵笔记》卷三:“秦会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孙为门客,王会以妇弟为亲客,郭知运以离婚为逐客,吴益以爱婿为娇客。”
“娇客”,本指尊贵的客人,宋代则专指女婿。《云麓漫钞》卷十:“秦太师十客:施全刺客,郭知运逐客,吴益娇客,朱希真上客,曹咏食客,曹冠门客,康伯可狎客,又有庄客以及词客,汤鹏举恶客。”、“娇客”成为对女婿的称呼,适用范围缩小。黄庭坚《次韵子瞻和王子立风雨败书屋有感》:“妇翁不可挝,王郎非娇客。”任渊注:“按今俗间以婿为娇客。”
(三)词义经历专指和泛化的多次演变
有些俗语词的词义,在专指和泛化间经历多次变化,如“官人”,在宋代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词义就经历了由专指而泛化,再到专指的变化过程,即“赐官于人→为官之人→尊称男子→丈夫”,而且后期的泛化和专指均出现于宋代。
“官人”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官”为词类活用,名词活用为动词,“官人”属动宾结构短语,指“赐官于人”,因此“官”可理解为“任用、重用”。这种用法宋代依然保留,如曾巩《徐禧给事中制》:“至于决狱、官人、条陈、法式之事,莫不当考察焉,其任可谓重矣。”、“官人”经过词汇化后,更广泛地用作名词,指“为官之人”。如《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杨倞注:“官人,群吏也。”又如唐韩愈《王适墓志铭》:“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人。”此处“官人”与“凡人”对举,可知“官人”为“为官之人”。
宋代“官人”词义开始泛化,称谓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由称呼“为官之人”成为对一般男子的尊称。《通俗编》卷十八:“唐时唯有官者方得称官人。宋以后,官人之称遍于士庶。”[2]宋代笔记如《春渚纪闻》卷二:“仲甫曰:‘吾观官人之碁,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尽着耳。’”其它如“陈官人”(《齐东野语》)、“王小官人”(《癸辛杂识》)、“蔡官人”、“张官人”、“傅官人”、“李官人”、“崔官人”(《梦粱录》)等,皆用来尊称男子,“官人”词义泛化。
此外,“官人”在宋代还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词义又由泛化变为专指。《夷坚甲志》卷二:“陆氏晚步厅屏间,有急足拜于庭,称郑官人有书。命婢取之,外题示陆氏三字,笔札宛然前夫手泽也。”《陔余丛考》卷三十七引《夷坚志》:“次山丧妻后,入京参选,偶游相国寺,与亡妾遇。惊问之,妾曰:‘现服事妈妈在城西一空宅,官人可以明日饭后来相会。’”[3]两例中的人物关系,均为夫妻,一为前妻,一为亡妻。这一用法,应该是在“官人”词义泛化的基础上,将“官人”这一称谓词从社会领域移用到夫妻间的称谓系统,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固定用法。
二、实词的虚化
笔记俗语词中,不仅包含实词,也有口语化程度较高的虚词,其词义或功能多是经由实词虚化而形成。虚化即是由实词向虚词的转化,通常指语言发展中意义实在的词逐步转化为意义较虚,或无实在意义仅表示语法功能成分的过程或现象。依据宋代笔记中虚词类俗语词的音节构成,可把实词虚化分为两类:单音节的实词虚化和双音节的实词虚化。
(一)单音节实词虚化过程分析
单音节虚词的形成,是在语义和句法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从虚化的程度看,可将单音节虚词的形成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意义具体实在的实词转化为意义较为虚泛的实词,如宋代笔记中量词类俗语词的产生,即由具体的实词语义转变为较为抽象的实词意义的俗语词;另一种是由实词义进一步虚化为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词。
1.实词虚化为量词。如“掐”,拇指和另一手指尖相对按压或切入,本为动词,后发展为量词,表示拇指和另一手指捏着的数量。《老学庵笔记》卷七:“王荆公所赐玉带,阔十四掐,号玉抱肚,真庙朝赵德明所贡。至绍兴中,王氏犹藏之。”至今在方言中仍有使用。
2.实词意义由具体变得抽象。如“吃”,宋时有“遭受”义。《洛阳缙绅旧闻记》卷四:“盖食客不量去就,各乘之而出矣。守忠敛容曰:‘不得无礼!称他诸秀才为一队措大,后度如此,即吃杖。’”《醉翁谈录庚集》卷二:“卖卦秀才,文理全乖,冒称进士,且请吃柴。再三省问,道理胡来,既是告求,且与封案,如敢再来,定行科断。”、“吃杖”、“吃柴”,都是指“挨打”,“吃”为“遭受”义,“杖”、“柴”皆指打人的工具,这里是借用工具来转指动作本身。宋代笔记中,“遭杖”也可称作“餐”。《墨客挥犀》卷五:“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惭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日,曾吃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餐”的这一用法与“吃柴”语义相通,也可相互印证。
“吃”语义虚化的原因,与“吃”后接的宾语有关。“吃”作为具体动作词,后边的宾语通常是需要咀嚼的固体食物。宋时“吃”也可与“酒”、“茶”等液体饮品相搭配,如“吃酒”、“吃茶”,在使用范围上有所扩大。当“吃”后的宾语,不再是可以食用的东西,如“柴”、“杖”等时,“吃”的语义就发生虚化,产生出“遭受”义。《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谚云:‘吃拳何似打拳时。’此言虽鄙,实为至论。”、“吃拳”、“打拳”意义相对,“打拳”为主动性的,“吃拳”则为被动性的,主动与被动的区别十分明显。因此,“吃”的“遭受”义,是“吃”转化为表示被动介词的语义基础。“吃”用作“被”,早在变文中己有用例,如《敦煌变文集》卷一《王昭君变文》:“黄羊野马捻枪拨,鹿鹿从头吃箭川 (穿)。”[4]
3.实词转变为虚词。“转”、“翻”由动词虚化为副词,即是如此。“转”、“翻”,均为动词,都表示“翻转”义,后虚化为副词,表示“反而、转而”。《洛阳缙绅旧闻记》卷四:“中令遽曰:‘尔忧主人如此,却出恁言,转教我不安。’”《夷坚乙志》卷七:“建炎元年,自都城东下至灵壁县。县令毕造,已受代。檥舟未发,闻路君至,来谒曰:‘家有仲女,为鬼所祸。前后迎道人法师治之,翻为所辱骂,至或遭棰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愿辱临舟中一视之。’”、“转”、“翻”的虚化,语义上与原来的动词义有直接联系,其虚化的条件主要是“转(翻)”出现在“转(翻)+V”结构中。在这样的结构中,后面的“V”承担主要的动词义,“转(翻)”变成次要动词,并开始虚化。
(二)双音节实词虚化过程分析
与单音节的实词虚化相比,双音节虚词在形成过程中,虚化实现的过程则相对复杂,比单音节虚词多了一层虚化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单音词先组合成短语,然后词汇化为复音词,最终虚化为虚词,即先词汇化再虚化;二是单音词先虚化为单音虚词,然后单音虚词组合成短语,最终词汇化为复音虚词,即先虚化再词汇化。
1.词汇化——虚化。如“大段”,本指长度计量单位,意为“大部分”,后固化成词,形容数量大,进而由长度数量虚化为程度大小,成为副词,表“特别”义。《侯鲭录》卷七:“世言卢绛病,梦一白衣妇人啖以甘蔗,为歌《菩萨蛮》词,曰:‘后相见于固子陂。’其词末句云:‘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此词人俱能道之。而杨大年《谈苑》中末句不同,云:‘独自凭阑干,衣襟生暮寒。’不知孰是。予尝谓‘芭蕉生暮寒’妙甚,与‘衣襟’大段相远,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再如“万一”,本为数词,指万分之一,后用作假设连词,表示一种存在可能性极小的情况。《容斋三笔》卷四:“他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此用法出现较早。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世间多不信至道者,则悠悠者皆是耳。然万一时偶有好事者,而复不见此法,不值明师,无由闻天下之有斯妙事也。”现代汉语沿用。
2.虚化——词汇化。如“些”,代词,表少量。唐代已有用例,宋代表现活跃。《容斋续笔》卷十四:“寇忠愍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处之,真宗令更与些恩数,惟演但乞封国公。”并且产生了以“些”为核心的复合词,如“些儿”、“些个”、“些子”等,多为“些”与后缀“儿”、“个”、“子”等构成的附加式合成词,语义上依然表示少量。《醉翁谈录丁集》卷一:“老绿赪红半草莱,羞容无语倚墙偎,初无茉莉些儿韵,遽敢争先茉莉开。”《癸辛杂识》后集:“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好,但矮些个。’”《青箱杂记》卷一:“翌日,彭献诗谢之曰:‘昨夜黄斑入县来,分明踪迹印苍苔。几多道德驱难去,些子猪羊引便来。’”
对于“些”字的各种形式,吕叔湘先生认为唐五代多用“些些”、“些子”,宋代则多用“些”、“些儿”。[5]其实宋代笔记中,“些子”的用例也较多,并出现由“些”与词缀“儿”、“个”连用构成的三音节附加式合成词“些儿个”。《夷坚丁志》卷十八:“珍女独处,漫自书云:‘逢师许多时,不说些儿个,及至如今闷损我。’援毫之际,客忽来。”
再如“则个”,语气助词,多用于句末表示祈使语气。《齐东野语》卷九:“庆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问则个。’谓李福也。”《鸡肋编》卷上:“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着”、“者”、“咱”应是同一语助词的不同形式。“则个”作为宋代新产生的语助词,其前身是语气词“着”。“着”从“者”得声,“者”为入声字。元代以后,北方入声消失,而南方仍有入声,所以“则个”是“着”入声的读法,在形式上由一个字衍为两个字“则个”。[6]
三、短语词汇化
汉语词汇研究中,双音复合词和短语之间的划界一直比较困难,其中缘由应是因为许多双音复合词都是由短语发展演变而来。对此,有人认为在词汇化的过程中,短语是双音复合词最主要的来源。[7]也就是说,短语由原来临时的、松散的组合,逐渐变为结构紧凑、词义固化的复合词。在词汇化过程中,语义的变化是区分短语和词的重要特征。短语表达的意义,一般是构成它的组合成分正常的句法意义,但是词义并不等于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有些俗语词的形成及其词义演变也是短语词汇化的结果,具体可以分为短语的词汇化以及跨层结构的词汇化。
(一)短语的词汇化
短语的意义一般是较为直观、明显,但在使用中一旦出现引申,语义常会由具体直观变得抽象模糊,这一转变过程也会伴随语义的变化而发生功能上的变化。如常用俗语词“没兴”,指“倒霉、晦气”。《老学庵笔记》卷四:“晁之道与其弟季比同应举,之道独拔解。时考试官葛某眇一目,之道戏作诗云:‘没兴主司逢葛八,贤弟被黜兄荐发。细思堪羡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夷坚丁志》卷十:“斋中钱范二秀才。诣之曰:‘道人何为者?’对曰:‘异事异事。八坐贵人,都着一屋关了。两府直如许多,便没兴不唧溜底也是从官。’”其中“没兴”是指运气不好,“不唧溜”指不太聪慧。
宋代其它文献中也有用例。宋陈着《江城子》:“应怪痴人,虚妄做浮生。正值楼台多簇燕,教没兴,不开晴。”《五灯会元》卷二十:“平生没兴,撞着这无意智老和尚,做尽伎俩,凑泊不得。”《张协状元》第八出:“经过此山者,分明是你灾。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是说因为从前做了很多坏事,现在许多倒霉的事情就会一起降临。这句话也成为后世小说中常用的一句俗语。《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不是郓哥来寻这个人,却正是: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金瓶梅》第四十七回:“这一来,管教苗青之祸从头上起,西门庆往时做过事,今朝没兴一齐来。”
“没兴”作“倒霉”义,被认为义同“没幸”,其中“幸”为好运,“没幸”即是没好运、倒霉。这一解释对上述用例皆可说通。只是“没兴”在近代汉语中还有其它的用法,如《牡丹亭》第十出:“偶到后花园中,百花开遍,睹景伤情。没兴而回,昼眠香阁。忽见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醒世恒言》第七卷:“转了这一念,反觉得没兴起来,酒也懒吃了。”此处“没兴”更多的是没有兴致、心灰意懒的一种状态。现代汉语中“扫兴”、“败兴”,都是指兴致被破坏,由此产生沮丧懊恼的负面情绪。因此,“没兴”的“倒霉、晦气”义,应是由其字面义“没有兴致”引申出来的。
(二)跨层结构词汇化产生的语义变化
跨层结构是指不在同一个句法层面上,而只是在表层形式的线性语序上相邻近的两个成分的组合。有些俗语词的产生通过跨层结构的词汇化而形成,且伴随词汇化的结束,语义和用法也发生了变化。
如“终不成”,在宋代笔记中保留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为状中结构,指最终没有完成或实现。《老学庵笔记》卷三:“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吴淑修《太祖国史》,亦终不成。”另一种则是用来表示反问或揣度的语气副词。这种用法出现于宋。《齐东野语》卷十一:“恭圣笑曰:‘终不成他特地来惊我,想是误耳,可以赦罪。’于是子母如初焉。”其它如《朱子语录》卷一百三十九:“如杨墨,杨氏终不成自要为我,墨氏终不成自要兼爱,只缘他合下见得错了。若不是见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
这种新用法的产生,是由于“不成”的用法发生了变化,从句法结构演变为语气副词。语气副词“不成”的形成,其间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是原本不是一个结构单位的“不”与“成”,经过重新分析,凝固成词;二是“不成”在表示揣度的语境中反复出现,受到语境的影响,其表达的否定语义变得模糊,逐渐处于否定和揣度的中间状态。语气副词“终不成”,用“终”修饰“不成”,在语气上比“不成”更为强烈。
(三)不完整的词汇化
短语的词汇化有时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词汇化的结果,一是实现了由结构到词的转变,即已完成词汇化过程;二是仍旧处于词汇化过程中,可称之为“不完整的词汇化”。如“吃香”。宋时为给帝王贺寿,三班院需要凑钱用于招待僧侣,供奉香合,这笔钱即为“香钱”,判院官从香钱中获利,即为“吃香”。《归田录》卷二:“三班院所领使臣八千余人,莅事于外,其罢而在院者,常数百人。每岁干元节醵钱饭僧进香,合以祝圣寿,谓之‘香钱’,判院官常利其余以为餐钱。群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优,又岁收粪墼钱颇多,以充公用。故京师谓之语曰:‘三班吃香,群牧吃粪’也。”据此可知,“吃香”是“吃香钱”的省略形式。又如宋代群牧司出售马粪赚取“粪墼钱”,“吃粪”就用来指赚取“粪墼钱”,为增强戏谑意味而称作“吃粪”。因此“吃香”这一形式是为了与“吃粪”保持结构上的对仗,而形成的临时组合。现代汉语中,“吃香”表示“受欢迎、被人重视”,泛指一切受欢迎的事物、现象,词义发生泛化,最终由动宾结构的短语凝固成词。其语义的形成,应与宋代俗语词“吃香”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