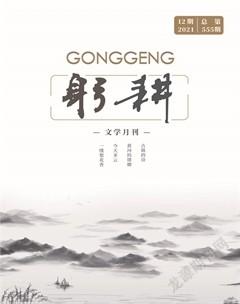母亲的针线筐
李修对
许多年前,母亲也不过三四十岁的样子,她的手边时常放着一个精巧漂亮的针线筐,圆形的,有握边,半尺深,放些顶针、花线、铺衬等针头线脑的,用着挺方便。其实,它是用筷子粗细的白蜡条编制的,里外涂上了黑漆,就成了黑明发亮的针线筐,是常伴母亲身边的一个寻常物件。据说,这是母亲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用了大半生不曾离手。近些年多次回老家虽然留意针线筐,却不见了它的踪影。
父亲主外,春种秋收,田间地头把汗流,耕锄打耙,不误农时,劳作不辍。母亲主内,一日三餐,忙上忙下,调理生活,使我们吃喝不愁。但是,也有烦心的时候,每至换季时节,母亲一双手忙开了花,春来做夏装,秋临做冬装,一大家子人人要换新装,换被褥,赶集撕布,操持针线,做衣裳、做鞋子,弹棉花、做被子,春上忙一春,秋天忙一秋,紧赶慢赶,也才勉强够一家人穿上换季衣裳,不受冻、不窘迫。这时候,母亲的针线筐一天到晚不離手,裁裁缝缝,补补连连,时常忙到大半夜才收工。多年长此以往,母亲落下了腰疼病,患上了腰肌劳损,都是为操持家务累出的病。每至腰疼,我见过母亲在父亲跟前使性子,唠叨父亲不知心疼她。但母亲从不在儿女面前叫苦叫累,埋三怨四,她把心里的苦痛全埋在了心底。这就是我那一贯吃苦耐劳操持家务的母亲,像天下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为儿女、为家庭、为社会付出艰辛的劳动,甚至是健康和生命!
母亲的针线筐是她的心坎儿事。她常常坐在堂屋蒲草团子上做针线活儿,一坐就是一老晌,不急也不躁,不是纳鞋底就是做鞋帮,再不然就是缝衣服、补鞋子、补袜子,有时还一针一线地在鞋帮上扎花绣朵,我记得母亲给我二姐就绣过一双漂亮的绣花鞋。母亲勤于操持,给老的做了再给少的做,给大的做了再给小的做,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家务活儿。记得我五岁时刚刚记事,母亲让二姐哄我,她让我骑在脖子上,背着我到处跑,不小心一下子把我从她的脖子上摔下来,一头栽到地上,鼻眼乌青,当时断了气儿,好一阵子才“哇”一声哭出声来。母亲听说后,气得放下针线筐就去绕着粪坑追打二姐。还记得有一次,十五六岁的春姐学着母亲的样子,端起母亲的针线筐自己补袜子,母亲用时到处找不到针线筐,急得直嚷:“谁见我的针线筐啦!”嚷了半天没人应,母亲发了脾气,“都给我找针线筐,找不到就别吃饭!”我们姊妹一群就开始到处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针线筐。等了一阵子,还是春姐从外面端着针线筐回来,交给了母亲。母亲问春姐:“你拿针线筐干啥去啦?”春姐怯声怯语地说:“补袜子去了。”母亲看着春姐胆怯的样子,自己也恼不起来。
母亲做针线活儿,用的是针线筐。每天忙过厨房的烧锅燎灶、洗洗刷刷的事情,就是坐下来穿针引线,缝缝补补,忙个不停。前院的大姆也做针线活儿,她没有针线筐,用的是一个用细竹篾编制的小竹筐儿,很精致也很实用,里边装着做针线活儿用的东西。大姆与我的母亲是妯娌,大姆原本与大伯生有一女,因为是行中老大,我们称呼为大姐,但因大姐得了不治之症,活到二十七岁就病逝了。大姆守着大伯过活儿,老夫妻俩相依为命,免不了常有孤独之感。大姆常带着她的小竹筐到我家,与母亲说着闲话,做着针线活儿,或是纳鞋底儿或是做衣裳。两个人边谈边做活儿,妯娌俩相处得好,也谈得来,从没有红过脸,挺开心地过着每一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十年前,大姆因患老年病不幸去世。她因无儿无女,是我的弟弟小忠一家为大姆操办了后事,把她送到北山,埋在大伯的坟边。自此,母亲就少了一个合心合意的做针线活儿的伙伴儿。
母亲的针线筐像个百宝盆,我们的穿戴用度都从这里边出。但凡穿衣戴帽、穿鞋穿靴,都是母亲一双手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才使得我们有穿有戴,不挨冻。打从记事起,母亲每天都在围着她的针线筐转,不曾稍有懈怠。她清楚明白,不抓紧时间缝衣做鞋、洗洗浆浆,孩子们就缺衣少穿。到换装季节不能及时换装,上不得人前,孩子们看着寒酸,大人的颜面也没处搁。母亲一辈子志刚傲强,不肯落人后,这就是母亲的为人性格。她拿一个针线筐用心用意地打扮着她的孩子们,打扮着我们的年年岁岁。
如今,母亲也老了。到今年她已经是一个八十七岁的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近些年,她虽然衣食起居还能自理,但已失去劳动能力,针线筐是再也端不动了。好在,时代已是大变样,母亲的吃穿用度由她的子女侍候着。但自从五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就一天到晚心里发急,作为儿女我们都很同情母亲,知道这是母亲失去老伴儿的空落感所致的“急症病”。除了经常劝慰母亲要想开些,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在生活上也给母亲以很好的调剂,做她喜爱吃的饭菜,让她吃好穿好玩好,安度晚景,颐养天年。
前天回老家,见到母亲身边又摆着那个掉漆泛白的针线筐,里边也还装着碎布针线,母亲时不时地翻翻捡捡,却再也无力做针线活儿了。看到这些,我心里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我时时牵肠挂肚的母亲,总也忘不了她的针线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