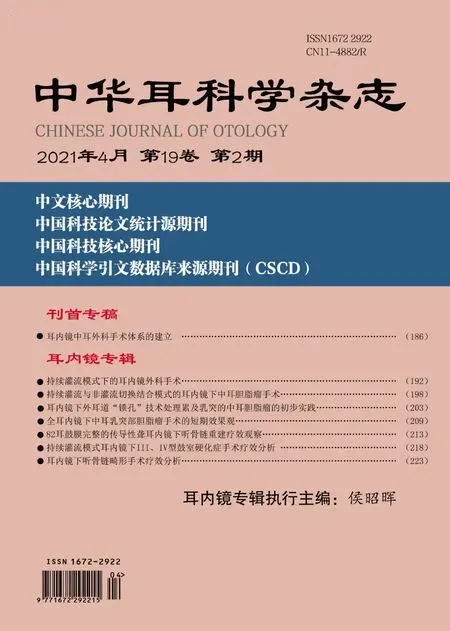氨基糖苷类药物耳毒性机制及耳保护策略研究进展
李熙星 张光远 陈雨濛 崔卫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河北 050000)
目前已知有150多种药物具有耳毒性,这些药物包括氨基糖苷类、糖肽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铂类抗癌药物、环利尿剂、奎宁和水杨酸镇痛剂等。虽然许多药物的耳毒性在停药后会消退,但氨基糖苷类抗生素(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AmAn)的使用可导致永久性听力丧失。在我国,AmAn致聋位于国内药物致聋的首位。据报道,一些氨基糖苷类药物对耳蜗毒性更强,而另一些则对前庭毒性更强[1]。药物的耳毒性将影响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对具有遗传易感性的患者造成极重度且不可逆转的耳聋;对于儿童而言,即使轻度听力损失也会对其言语发育及心理社会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对AmAn的内耳毒性过程以及如何在细胞水平上对其预防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并在药物治疗AmAn所致耳蜗毒性和预防耳蜗损伤上有所进展。迄今为止,尚无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保护内耳免受损害和预防相关听力损失的药物。然而,各种临床前研究都显示出了希望,目前也有一些临床试验的支持数据。迫切需要在这一有希望的领域内进行更多的研究。本文重点对AmAn耳毒性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当前的耳保护策略作一综述。
1 AmAn的耳毒性机制
AmAn损伤内耳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大量证据表明氧化应激诱导耳蜗毛细胞和血管纹边缘细胞凋亡坏死[2],其中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常作为凋亡通路的催化剂。AmAn的作用是与细菌核糖体结合,抑制细菌蛋白的合成,而线粒体核糖体在结构上比真核核糖体更接近细菌核糖体[3],AmAn通过抑制线粒体蛋白生物合成来抑制顺乌头酸酶,该酶是线粒体呼吸链的重要组分,其活性丧失使呼吸链功能出现异常,氧自由基增多,导致铁离子的积累,使这些铁离子络合,通过芬顿反应 (Fenton reaction)生成ROS[4]。此外,Fe2+/3+-AmAn-络合物与花生四烯酸形成三元络合物,通过脂质过氧化促进ROS的形成[5]。如果ROS的产生超过了固有的抗氧化能力负荷,并触发耳蜗内细胞死亡通路,就会发生细胞死亡,降低听觉和/或前庭功能[6]。
那么AmAn又是如何进入内耳组织及毛细胞来发挥细胞毒性呢?首先,其通过主动转运机制穿过血-迷路屏障(BLB)进入内耳[6],早期的耳蜗研究表明,外淋巴液中的AmAn含量高于内淋巴液,提示外淋巴液中的AmAn是毛细胞毒性的主要来源[7]。尽管AmAn在全身给药后进入外淋巴液,但它们不容易通过这种途径进入毛细胞[8]。用荧光标记的庆大霉素(GTTR)进行的实验表明,在鼠耳蜗中,GTTR优先被血管纹状体吸收,且纹状体边缘细胞显示出更高的GTTR荧光强度[9]。耳蜗中庆大霉素的免疫荧光检测还揭示了整个耳蜗中广泛的细胞标记,优先标记了边缘细胞[9,10]。这些数据表明,全身应用的AmAn从毛细血管运输到边缘细胞,然后被清除进入内淋巴,即血管纹-内淋巴液途径[11]。AmAn主要通过立体纤毛机械电传导(MET)通道进入毛细胞,此通道随着声音或加速度的变化而打开和关闭[12]。MET通道是大的、非选择性阳离子通道,对Ca2+离子具有较高的渗透性[13]。来自内淋巴液的Ca2+离子被认为在含有带负电残基的前庭浓缩,进一步被选择性过滤器内其它带负电的残基吸引,从而进入毛细胞[13]。最新研究表明,MET通道是由TMC蛋白二聚体形成的,有两个孔,每个孔对应10个跨膜结构的TMC分子[14,15]。在孔隙区存在几种带负电荷的氨基酸,也存在几种带正电荷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可以形成进入和退出的屏障[14]。MET通道孔隙非常大,最窄处的直径至少为1.25~1.5 nm[16],足以允许AmAn和其他大型阳离子进入毛细胞胞浆。AmAn进入毛细胞的其他途径也存在,其中一种是毛细胞顶端和突触极的内吞作用,尽管还没有发现其参与细胞毒性的直接证据[12,16]。另外,瞬时感受器电位(TRP)通道作为非选择性阳离子渗透通道家族,与MET通道一样,对Ca2+离子具有很大的通透性[17]。TRPA1被认为是一种化学传感器,由炎症、氧化应激和组织损伤过程中释放的各种刺激性化合物以及细菌内毒素激活[17]。TRPA1通过内毛细胞(IHCs)和外毛细胞(OHCs)表达,并被认为存在于OHCs的基底外侧膜上。实验证实经螯合剂BAPTA预处理使MET通道失活后,激活的TRPA1通道促进了AmAn的吸收[18]。激活后,TRPA1的孔径可以从1.1 nm扩大到1.4 nm,这表明TRPA1通道可以在耳蜗应激(例如,噪音暴露)时激活,可能增加AmAn进入OHCs[19]。TRPV1和TRPV4是另外的候选AmAn渗透通道,两者都在血管纹和毛细胞中表达。最新研究表明,TRPV1参与了AmAn诱导的细胞毒性,且炎症可上调TRPV1的耳蜗表达,从而加重药物引起的听力损失[20]。
2 AmAn的耳毒性影响因素
AmAn耳毒性的个体差异和易感性常表现有家族遗传性,线粒体核糖体RNA中选择性的基因突变(主要是A1555G)导致与氨基糖苷类化合物具有更高的结合力,并可导致蛋白质合成过程中mRNA的误译,导致细胞死亡[21]。这些易感患者即使用常规剂量或极小剂量的AmAn即可发生耳毒性反应。线粒体基因组中还发现了其他突变,这也容易导致AmAn引起的听力损伤[22]。
血清中较高的药物浓度、给药间隔缩短、给药次数增多、累积给药剂量增加等是引起AmAn耳毒性的重要因素[23]。最近一项大型研究报道,通过短期治疗、监测药物水平及调整剂量,可以使庆大霉素对听力末梢器官的影响最小化[24]。另外,给药途径及局部给药部位对AmAn耳毒性作用亦有影响,椎管内给药最危险,其次为静脉和肌肉注射[25]。鼓室给药时,药物也可通过圆窗膜或经中耳血管进入内耳发生中毒,且中耳存在炎症时更能增加药物的耳毒性[26]。
AmAn也可经胎盘进入胎儿血循环,造成胎儿耳蜗螺旋器损害,尤其在妊娠早期(最初3个月)更为明显,这与机体发育不全、生理病理变化有关。另外,婴幼儿和老年人对AmAn的耳毒性具有高风险性[26]。
此外,噪声、炎症、与一些药物的联合使用(如万古霉素等)等均可诱导AmAn的耳毒性[27]。最近,还有报告指出艾滋病毒合并感染与AmAn诱导的听力损失的高发生率相关[28]。
3 AmAn的耳毒性防护策略
迄今为止,AmAn尚不能完全被同样有效且耳毒性较小的药物所替代。因此,考虑到其耳毒性的风险,定期行听力检测是必须的。通过适当的高频听力测试,可以发现早期损伤,并考虑替代治疗。此外,记录和考虑个别危险因素(如年龄、先前存在的听力损失、肾功能不全和经验证的药物基因组标记)对于识别需要更密切监测的高危患者,选择可能的替代药物或耳保护剂至关重要。针对AmAn的耳毒性,目前已提出两种主要的耳保护策略。一是减少内耳细胞对药物的吸收,以防止细胞毒性;另一种是干扰AmAn诱导的细胞毒性的机制。
3.1 减少AmAn的细胞摄取
斑马鱼侧线(zebrafish lateral line)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可以高通量筛选使毛细胞免受耳毒性的化合物。最近一项对500多种天然化合物的筛选发现,四种新的双苄基异喹啉衍生物(Berbamine,E6 Berbamine,Hernandezine,Isotetrandrine)是降低毛细胞对AmAn摄取的耳保护剂[29]。另外,ORC-13661作为是一种由Oricula制药公司最新开发的口服药物,是一种高亲和力的外毛细胞机电换能器(MET)通道的渗透阻滞剂,它可以可逆地阻断毛细胞MET通道来降低AmAn耳毒性[30]。但MET通道阻滞是否是这些化合物的主要耳保护机制还有待验证,因为其中有几种也会影响其他离子通道[31]。在局部或全身给药后进行体内试验,以确保这些化合物能够进入分隔的内淋巴液,这一点也至关重要。目前,Etimicin(ETM)作为第四代氨基糖苷(AGs),由于其高效和低毒的特点,已在临床应用。其耳毒性的机制仍不清楚,但对大鼠耳蜗毛细胞进行体外实验表明,ETM最小的耳毒性是由于它在靶细胞线粒体中积累较少,随后对线粒体功能的抑制也较少[32]。这些结果为发现高效低毒的新型AGs提供了新的策略。由严重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增加了AmAn的耳蜗摄取和随后的耳毒性[33]。在AmAn治疗之前或期间给予抗炎药对于依那西普(一种阻断促炎信号传导受体TNFα的抗体)在改善噪声诱导的听力损失方面可能是有效的[34]。依那西普和其他抗炎药可以减轻耳蜗炎症并且还可以减少氨基糖苷类的耳蜗摄取,以更好地保持听觉功能[35]。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AmAn通常是治疗危及生命的败血症的必需品[36]。NICU环境噪声很高,并且NICU的工作人员的听力损失发生率显著增加[37],可能是由于环境声级的协同效应增加了AmAn的耳蜗摄取[38]。因此,降低NICU中的环境噪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3.2 降低AmAn的细胞毒性
N-乙酰半胱氨酸和D-蛋氨酸等抗氧化剂可在临床前模型中降低AmAn诱导的耳蜗毒性[39],支持药物诱导产生活性氧导致耳毒性的观点。一些抗氧化剂对AmAn和顺铂均表现出耳蜗保护作用,提示氧化应激诱导是这些耳毒性药物细胞毒性的共同机制[40]。假若如此,那么减少顺铂耳毒性的剂量方案也可以转化为对AmAn引起的耳毒性的耳保护方案。
组蛋白的乙酰化有利于各种转录因子和协同转录因子能与DNA结合位点特异性结合,激活基因的转录,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则发挥着相反的作用。AmAn治疗还导致核组蛋白的低乙酰化,减少与DNA结合的转录因子,降低基因表达[40]。HDACs的特异性抑制剂在耳蜗外植体中具有耳保护作用[41],但在体内往往不具有耳保护作用[42]。因此,候选耳保护剂的有效性必须在体内进行验证。
另外一个创新的策略是开发像安普霉素(apramycin)这样的AmAn,它对真核生物线粒体核糖体的亲和力最小,同时对临床病原体保持强大的活性[43]。最新研究报道,阿普霉素在一定浓度下未观察到隐性听力损失的迹象,被认为是临床使用的有希望的抗生素[44]。此外,对西索米星(庆大霉素的生物合成前体)的特定胺基团进行修饰,生成了一种改进型AmAn即N1MS,研究表明感染大肠杆菌膀胱的小鼠经西索米星治疗后毛细胞减少75%至85%,听力严重受损,而N1MS治疗既消除了尿路的细菌感染,又保留了毛细胞,同时不损害听觉和肾脏功能[45]。研究结果确立了N1MS作为非毒性AmAn,并支持靶向修饰作为产生非毒性抗生素的有希望的方法[45]。
另一个有希望的方法是激活热休克蛋白(HSPs),包括HSP70,以促进毛细胞对抗AmAn的耳毒性而存活。热休克通过诱导支持细胞表达和分泌HSP70起到对内耳毛细胞的保护作用。有趣的是,在临床前模型中,暴露于足以对耳蜗产生短暂压力的声音中,HSP7和HSP32表达上调,从而显著降低AmAn引起的听力损失[46]。
尽管上述两种耳保护策略是可行的,但通过在临床环境中的仔细监测来识别有危险的病人仍是至关重要的。最有希望的治疗可能是精准医疗,它将在分子水平上选择性地诊断和/或治愈患者。目前认为12S rRNA基因突变增加了AmAn耳毒性的敏感性,大约17%的耳毒性受试者的12S rRNA基因发生突变[47]。为了减轻氨基糖苷类药物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评估其家系或在使用AmAn之前筛选其12S rRNA基因来预测个体的耳毒性风险。医务人员应询问患者是否有类似家族史,并筛选患者或其家属的12S rRNA基因突变。该基因的突变携带者应避免接触AmAn,并使用替代药物进行治疗,以减少诱发耳毒性听力损失的可能性,这将降低耳毒性的风险。
4 结语
在过去的70余年,自从AmAn的发现并应用到临床,其耳毒性等副作用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应用其控制感染的同时,也应注重对其耳毒性机制的深入研究并开发有效的耳保护策略。目前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临床试验中用于预防AmAn耳毒性的药剂数量令人鼓舞。尽管FDA的药品审批过程是严格的,但是临床前和临床试验表明,在不远的将来,一种或多种有效的耳保护剂将有望获得FDA批准应用到临床[6]。关于AmAn耳毒性机制及耳保护机制的研究已获得了大量的信息,为制定新的耳保护策略奠定了基础,也为学术界和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到药物研发,在多个层面进行合作,以防止药物导致的听力损失,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